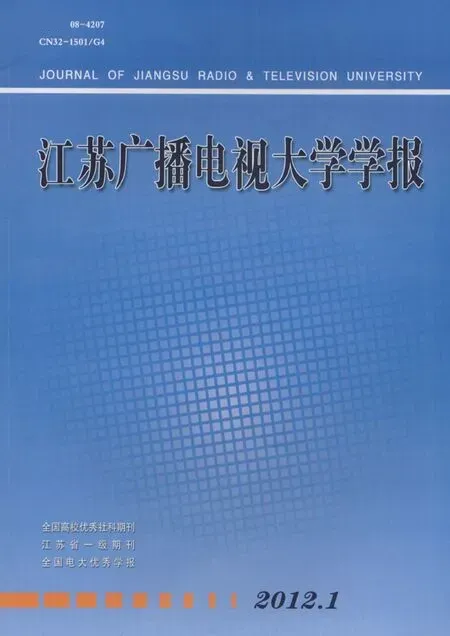《楞嚴(yán)經(jīng)疏解蒙鈔》的文獻(xiàn)學(xué)價(jià)值
王彥明
錢謙益,字受之,號(hào)牧齋。因出生于佛教信仰氛圍濃厚的虞山錢氏,自幼便受佛教浸染,師友中奉佛者頗多,故受影響很大。明亡后,因有降清之經(jīng)歷,歷來受人詬病。晚年奉佛日深,因不滿于當(dāng)時(shí)佛教的種種弊端,錢氏以護(hù)法居士的身份,對(duì)當(dāng)時(shí)佛教出現(xiàn)的種種問題,尤其是禪宗內(nèi)部的種種弊病,予以揭露與批判。為改變佛教衰微之局勢(shì),錢氏于佛教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觀點(diǎn),其中最為重要、最具前瞻性的觀點(diǎn)即是反經(jīng)明教,提出通過經(jīng)典的閱讀、義理的研究來改變教內(nèi)空虛的習(xí)氣。《楞嚴(yán)經(jīng)疏解蒙鈔》即是此種思想指導(dǎo)下的產(chǎn)物。梁?jiǎn)⒊壬凇吨袊?guó)近三百年學(xué)術(shù)史》中認(rèn)為錢氏雖人格極不可取,“但他極熟于明代掌故,所著《初學(xué)集》《有學(xué)集》中,史料不少。他嘗親受業(yè)于釋憨山德清,人又聰明。晚年學(xué)佛,著《楞嚴(yán)蒙抄》,總算是佛典注釋里頭一部好書。他因?yàn)槭菛|林舊人,所以黃梨洲、歸玄恭諸人都敬禮他,在清初學(xué)界有相當(dāng)?shù)膭?shì)力。”[1]
對(duì)錢謙益的文獻(xiàn)學(xué)方面的研究,研究者多注重于其《絳云樓書目》《絳云樓題跋》及其藏書方面*此方面的研究成果,據(jù)筆者所見,有:王雅新《〈絳云樓題跋〉研究》,山東大學(xué)2009年碩士學(xué)位論文;賈衛(wèi)民《錢謙益與〈絳云樓題跋〉》,《新世紀(jì)圖書館》2010年第3期;鄭子云《書賈與錢謙益藏書關(guān)系發(fā)微》,《新世紀(jì)圖書館》2007年第3期;袁丹《錢謙益與文獻(xiàn)學(xué)》,武漢大學(xué)2002年碩士學(xué)位論文,文中對(duì)其著述情況作一簡(jiǎn)介與評(píng)價(jià),考察著述版本流變及其被焚毀情況,對(duì)其圖書編撰學(xué)、藏書來源、版本的鑒定考評(píng)辨?zhèn)蔚确矫嬗枰蕴接懀恍烀牢摹跺X謙益著述與藏書之研究》,臺(tái)北大學(xué)碩士學(xué)位論文;孔愛峰《錢謙益〈列朝詩(shī)集〉的編纂學(xué)研究》,蘇州大學(xué)2005年碩士學(xué)位論文;王紅蕾《淺析〈絳云樓書目〉的若干問題》,《中國(guó)圖書館學(xué)報(bào)》2010年第6期;王紅蕾《〈絳云樓書目〉各抄本互異原因略考》,《文獻(xiàn)》2010年第3期。,對(duì)于錢氏佛教文獻(xiàn)學(xué)方面的研究非常少。而若忽略了錢氏佛教文獻(xiàn)學(xué)層面,對(duì)其作一評(píng)價(jià)的話,是不全面也是不完整的。筆者有感于此,即以《楞嚴(yán)經(jīng)疏解蒙鈔》(以下簡(jiǎn)稱《疏解蒙鈔》)為例,作一簡(jiǎn)要探討,不當(dāng)之處,祈請(qǐng)指正。
一、辨章學(xué)術(shù),考鏡源流
章學(xué)誠(chéng)在《校讎通義》中言及目錄學(xué)的功用時(shí)有一經(jīng)典之論,“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xué)術(shù),考鏡源流;非深明于道術(shù)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后世部次甲乙,紀(jì)錄經(jīng)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闡大義,條別學(xué)術(shù)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于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2]“辨章學(xué)術(shù),考鏡源流”言之雖易,若真正達(dá)到這一目標(biāo),實(shí)非易事。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guó),至明末清初,在長(zhǎng)達(dá)一千六百多年的承繼發(fā)展過程中,產(chǎn)生了諸如天臺(tái)宗、華嚴(yán)宗、唯識(shí)、禪宗等種種派別,各有其自成體系的教理教義與修持方法,或師徒授受,或教外別傳,承繼發(fā)展,蔚為大觀。派別之間的分歧,自不待言,就同一派別而言,亦有分歧。如同為天臺(tái),有山家與山外之分;同為禪宗,有南頓北漸、祖師禪與如來禪之別,五家七宗,亦有不同。自宋以后,雖儒釋之間、佛教內(nèi)部各派之間互相融通,但各家之間,卻并未因融通而失去界限,相反卻為保持自家之優(yōu)勝之處而爭(zhēng)端不斷,陳垣先生《清初僧諍記》一書之研究,便為最好的說明。《楞嚴(yán)》一經(jīng),因“以人法為名,常住真心為體,圓通妙定為宗,返妄歸真為用,上妙醍醐為教”[3]741,“無論是從華嚴(yán)的真心緣起,還是天臺(tái)的止觀正定,都可以透過某種解經(jīng)的策略而在該經(jīng)中找到自家宗旨的認(rèn)定。”[4]除龔先生提到的天臺(tái)、華嚴(yán)兩宗之外,禪宗及歷代文人士大夫?qū)ζ涠际种匾暎杞庵鳎址备弧VT疏解者在疏解經(jīng)文的過程中,依據(jù)本宗派的教理教義加以闡發(fā),各自帶有本門的思想特點(diǎn),亦因觀點(diǎn)不同,抑揚(yáng)有差,為維護(hù)自家利益,競(jìng)相為說,紛爭(zhēng)不斷。如何在目錄著作及解題中充分展現(xiàn),為目錄作者之難事,亦為幸事。錢謙益晚年“歲凡七改,稿則五易”而成《楞嚴(yán)經(jīng)疏解蒙鈔》,可謂集大成之作,而其卷首的《古今疏解品目》,著錄題名,附以解題,“辨章學(xué)術(shù),考鏡源流”,充分展示出目錄學(xué)的這一功用。
探源討流,為錢謙益一貫的學(xué)術(shù)特色,觀其全集,于經(jīng)學(xué)、史學(xué)及詩(shī)文批評(píng)之論,大都循此套路展開。錢氏的《疏解蒙鈔》,亦體現(xiàn)此種治學(xué)特點(diǎn)。他在《古今疏解品目·永明寺智覺壽禪師〈宗鏡錄〉》解題中云:“古師弘法,確有淵源。今人習(xí)而不察,間有采剟,徒取駢偶之詞,資為旁義而已。蒙之鈔略,披文揀集,廣引證明,零義單詞,罔敢遺闕。欲使學(xué)者知古義有所從來,勿尋枝而失干也”[3]82,明確指出錢氏疏解此經(jīng)之目的,是使后學(xué)“知古義有所從來,勿尋枝而失干”,其《疏解蒙鈔》也確實(shí)體現(xiàn)了這一特點(diǎn)。《古今疏解品目》中,按唐、五代吳越、宋、勝國(guó)蒙古(元)、皇朝(明)五個(gè)時(shí)期,依次而列。于諸多《楞嚴(yán)》疏解中,從探源角度,考察出“此經(jīng)疏解之祖”、“此經(jīng)科判之祖”、“臺(tái)觀解經(jīng)之祖”、“唐人以禪宗解經(jīng)者,自長(zhǎng)慶一宗,即溫陵諸師之祖也”,將后人解經(jīng)科分所據(jù)之慧振的《科判》、華嚴(yán)解經(jīng)所據(jù)之惟愨法師之疏、天臺(tái)解經(jīng)所據(jù)弘沇法師疏及禪家解經(jīng)所據(jù)的道巘禪師的《楞嚴(yán)說文》,條列無余。在書目的解題中,若為疏解之祖者則標(biāo)其源,并略述后世疏解之傳承情況;若為后世之疏,則標(biāo)其所本,以明其源,如后世有本之而作疏者,則簡(jiǎn)而述之,以見其流。此類在《古今疏解品目》中甚多,故略舉幾例。
崇福寺惟愨法師疏
愨公于至德初年,得房相家筆受經(jīng)函,發(fā)愿撰疏,計(jì)十一年始下筆,勒成三卷,目為《玄贊》,文義幽頤,盛行西北,實(shí)此經(jīng)疏解之祖也。《高僧傳》云:“愨公撰疏,夢(mèng)妙吉祥乘狻猊自其口入,及將徹簡(jiǎn),寐中見由口而出。”在乎華嚴(yán)宗中文殊智也。永明《宗鏡》,引愨公論楞嚴(yán)六十圣位,深契華嚴(yán)圓融法界之旨。人知長(zhǎng)水釋《楞嚴(yán)》用華嚴(yán)宗旨,而不知其原本于愨公也。長(zhǎng)水解經(jīng)首“一時(shí)”,有“說法”、“領(lǐng)法”四對(duì)。《金剛刊定記》云:“此是愨公《楞嚴(yán)疏》意。”故知長(zhǎng)水之疏,于《玄贊》采擷多矣。《萬松錄》載愨師八處徵心,科解尤奇。[3]82
此段解題對(duì)惟愨法師《玄贊》的疏解過程、后世承襲,予以說明,尤其對(duì)于長(zhǎng)水疏的影響,則引《金剛刊定記》為據(jù),發(fā)別人所未發(fā),疏通證明,可見一斑。
又如:
長(zhǎng)水疏主楞嚴(yán)大師子璇撰《義疏注經(jīng)》十卷
長(zhǎng)水初依靈光敏師學(xué)賢首教觀,尤精于《楞嚴(yán)》。已而得悟于瑯琊,受扶宗之付囑,乃依賢首五教,馬鳴五重,詳定館陶《科判》,采集愨、沇、敏節(jié)諸家之解,釋通此經(jīng),勒定一家。是中修治止觀,參合天臺(tái),揀辨心識(shí),圓收《宗鏡》。理該教觀,又通經(jīng)論,性相審諦,悟解詳明。裴相之贊圭山云:“文廣理一,語(yǔ)簡(jiǎn)義圓。”以方長(zhǎng)水,良無愧焉。今茲鈔略,奉為準(zhǔn)繩,期于研照智燈,刊落枝蔓。紫柏有言:“長(zhǎng)水疏經(jīng),為百代心宗之祖。”卓哉斯言!即寂音義學(xué)之訶,亦可以息喙矣。……稟長(zhǎng)水之學(xué)者,有蘇臺(tái)元約《疏鈔》,宋時(shí)盛行于世,今不傳。又有道歡法師《手鑒》及《釋要》等,皆鈔類也。今略見海眼《補(bǔ)注》及桐洲《集注》。……泐潭曉月禪師《標(biāo)指要義》……閩僧咸輝《楞嚴(yán)經(jīng)義海》三十卷。已上二書,皆長(zhǎng)水之流派也。[3]82
此解題,亦將長(zhǎng)水《義疏注經(jīng)》的取材來源、《蒙鈔》的疏鈔所據(jù)、時(shí)人對(duì)長(zhǎng)水《義疏注經(jīng)》的評(píng)價(jià)及對(duì)后世《楞嚴(yán)》疏解之作的影響,予以明確的交代。
而于孤山法慧法師智圓、吳興凈覺法師仁岳諸書下題云:“自智者大師遙禮《楞嚴(yán)》,入滅遺記,于是孤山圓師,首先奮筆,思應(yīng)肉身比丘之讖,用三止三觀貼釋此經(jīng)。吳興岳師,力扶孤山,張皇其說。自時(shí)厥后,講席師承,咸以臺(tái)觀部屬《楞嚴(yán)》,無余說矣。今按孤山教義分明,文詞富有,十部疏主,宜其擅名。然其分配三止則觀網(wǎng)未圓,錯(cuò)解三摩則義門未確。春前夏滿克定說經(jīng),則時(shí)教未審,蓋亦山外一家之言,非此經(jīng)通義也。吳興分衛(wèi)得悟,若拓虗空,詞辨從橫,穿穴經(jīng)論,妨難側(cè)出,結(jié)彈繁興。方諸古人,良多新解。未免自尊己德,下視先賢,未能善自他宗,抑亦招建立過。當(dāng)其雪謗扶宗,已無上古;豈知靈芝開口,更有后人。此病于今正煩,未能縷指。”[3]83此其在華嚴(yán)一系的立場(chǎng)上,對(duì)天臺(tái)諸書經(jīng)疏源流作出的說明,于各家疏注之功過是非,略一評(píng)判,而學(xué)術(shù)史之意義,則暗含其中,自有價(jià)值與意義所在。
《古今疏解品目》在編排體例上,也顯現(xiàn)出探源討流的特點(diǎn)。清初通理作《楞嚴(yán)經(jīng)指掌疏懸示》,在言及《疏解蒙鈔》體例時(shí)云:“按《蒙鈔》有正書,有附引(謂正書下雙行附引)。今依灌頂疏,皆作正書。”[3]166所謂“正書”,即《疏解蒙鈔》在排列歷代疏解時(shí),將其重要者單行列出;而“附引”則分兩種情況:一為正書經(jīng)題下的解題,二為受正書疏解著作影響而作的屬于同一疏解體系的疏解之作。如長(zhǎng)水的《義疏注經(jīng)》下附引“稟長(zhǎng)水之學(xué)者,有蘇臺(tái)元約《疏鈔》,宋時(shí)盛行于世,今不傳。又有道歡法師《手鑒》及《釋要》等,皆鈔類也。今略見海眼《補(bǔ)注》及桐洲《集注》”。[3]82天如惟則《會(huì)解》下附引云:“洪武中盤陰沙門洪闊稟承天如,輯《冥樞會(huì)解》十卷。萬歷中檇李幻居真界,輯《楞嚴(yán)纂注》,燕中講師如相兼采《合論》、《管見》等,輯《古今合解》,皆是《會(huì)解》枝流,故不別開。”[3]84云棲袾宏《楞嚴(yán)摸象記》下附引云:“一時(shí)講師由云棲而出者,柴紫乘時(shí)有《講錄》十卷,云棲廣莫撰《直解》,虞山鶴林大寂撰《文義》,各十卷。消文貼釋,咸有可采。”[3]86通過附引,將一派疏解之源流影響所及,揭示無余。通理所作《楞嚴(yán)經(jīng)指掌疏懸示》,將此附引打散,全部改為正書,則未見錢氏之用心,亦使目錄探源討流的功能湮沒無聞,實(shí)為可惜。
除《古今疏解品目》外,尤可注意者為卷末五錄之二《佛頂序錄》,其中輯錄自長(zhǎng)水而下諸家疏解之序錄,或可視為目錄著錄輯錄體之體現(xiàn)。在目錄著錄中收存諸家序錄,最早始于梁僧佑《出三藏記集》,其后南宋末王應(yīng)麟《玉海·藝文志》、元馬端臨《文獻(xiàn)通考·經(jīng)籍考》輯錄眾說,列于原文后,可視為輯錄體成熟之作。朱彝尊《經(jīng)義考》、謝啟昆《小學(xué)考》、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皆沿用其體,成為目錄著錄之重要體式。《佛頂序錄》共收歷代《楞嚴(yán)》疏解題跋文字21篇,從中可看出《楞嚴(yán)經(jīng)》天臺(tái)、華嚴(yán)、禪宗等諸家疏注重心所在。其序云:“肇表三空,叡贊二匠,圓覺宗通,弘傳神唱。隨具宗眼,宿承臺(tái)嗣,義海互騰,藻火交熾。都為序録,庸表正令,展卷歷然,交網(wǎng)懸鏡。輯佛頂序録。”[3]729此序與《古今疏解品目》前后對(duì)應(yīng),對(duì)讀之后,自有相得益彰之效,亦為錢氏佛教目錄學(xué)成就之體現(xiàn)。
二、忠于原典,謹(jǐn)于校勘
忠于原典,努力探尋并試圖恢復(fù)經(jīng)典的原貌,是一個(gè)文獻(xiàn)整理者所必須具備的最基礎(chǔ)的素質(zhì)。明代書籍之刊刻,多有改動(dòng)原文的弊端,朱元璋實(shí)開此種風(fēng)氣之先。在有明一代諸家書刻中,毛晉汲古閣本則相對(duì)而言,較為可信,尤其影宋之刻,則達(dá)到以假亂真之境界。在現(xiàn)存錢謙益與毛晉往來書信中,多見二人間商討校書之作,錢氏校書之嚴(yán)謹(jǐn),可見一二。《疏解蒙鈔》一書,亦反映出此種特點(diǎn)。
宋代閣臣中疏解《楞嚴(yán)》的為王安石與張無盡諸人,張氏的《楞嚴(yán)海眼經(jīng)》則多按己意而改動(dòng)經(jīng)文之處,錢氏在其解題中云:“無盡刪修《楞嚴(yán)》,竄易緣起,移置前后,芟除重復(fù),改定圣位。削匿王指河之事,換槃特誦帚之因,信意增減,師心博易。全經(jīng)面目,抹摋殆盡。越僧慧印謂為妙喜所印贊,公然題目,標(biāo)為新舊二經(jīng)。雷庵受師抗詞駁正,累數(shù)千言。……推無盡之本病,蓋有兩端:一則禪人習(xí)氣,高抬宗眼,脫略教宗。觀其論太極邪因,料簡(jiǎn)清涼,數(shù)行之中,引疏而遺鈔,則于他經(jīng)可知。一則有宋儒者,學(xué)粗心大。廬陵敢非《十翼》,河南擅更《戴記》,繆妄成風(fēng),無盡遂衡加于教典也。吾為此懼,普告來者。妙喜復(fù)起,不易斯言。”[3]84又在《咨決疑義十科》中再次指出:“《海眼》刪修,流傳繆種,以凡心自生圭角,或消文間有抵牾,無復(fù)參祥,輒加涂乙,甚者妄稱定本,矯亂經(jīng)文。特設(shè)此科,嚴(yán)為駁正。……身非譯匠,敢改梵文,律在同科,法當(dāng)并按。今于此類,鐫削無余,除識(shí)一端,以懲妄作。”[3]105張無盡之改動(dòng)《楞嚴(yán)》,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gè)方面:一為改換經(jīng)名,并認(rèn)為是據(jù)梵本而改,此為錢氏所駁,“張無盡不依唐譯,改題為《清凈海眼經(jīng)》。輙云‘房融不見古本,今依梵本改正。’房筆受竺文,何云未見古本?張所據(jù)梵夾,豈是極量重來?無稽之言,良所不取。”[3]748-749其二為根據(jù)己意刪改經(jīng)文。如卷一“阿難已知”句下錢氏云“張無盡《海眼經(jīng)》刪‘如來下’十三字,補(bǔ)十八字,云:‘曾于毗耶離城揀擇行乞,悲心不善,被長(zhǎng)者訶。’雷庵受師彈駁甚厲。以改竄經(jīng)文,其過易見,標(biāo)以示戒”。[3]135卷五周利盤特迦酬佛所問圓通“佛問圓通,如我所證,返息循空,斯為第一”句下引張無盡語(yǔ)云“今刪廿六字,添二十字,庶與經(jīng)論無違。又二十五門闕思而剩鼻,減息入思,觀門具足。下文文殊偈,亦修三句”。[3]405對(duì)此,錢氏為鈔其文后,按以“私謂”云:“無盡刪修,敢于變亂經(jīng)文,改竄偈頌,非圣用罔,莫此為甚。”[3]405卷九“上歷菩薩六十圣位,得意生身,隨往無礙”句下“今刪去能成就下經(jīng)文二十四字”,錢氏云:“姑仍其舊文,以戒妄作。”[3]644其三為隨意調(diào)整經(jīng)文次序。如卷八“斯亦輪回,妄想流轉(zhuǎn),不修三昧,報(bào)盡還來散入諸趣”句下,張無盡此段論仙趣之文,移于第九卷論阿修羅趣下,已遭東吳雷庵正受的批駁,認(rèn)為“仙趣優(yōu)于人而劣于天,合次于人之后,天之前”。[3]593卷十“阿難,是五受因五妄想成”句下云:“張無盡《海眼經(jīng)》移此文‘妄本無因’下至此三十五行,入第三卷十四紙‘第一義諦’句下。無盡不了如來重?cái)⑽尻幎摻探渖钜猓袪课膭?shì),妄率改修。其過不小,故特明之。”[3]694
錢謙益對(duì)張無盡刪改經(jīng)文之舉,繼雷庵正受之后,大加批判,并以期達(dá)到警世的作用。但經(jīng)文在流傳過程中,因版本不同,傳抄者水平不一,出現(xiàn)異文情況亦屬難免。針對(duì)經(jīng)文中的異文,錢氏一一校出,并在卷末出校記,注明經(jīng)文異文。若兩可通者,則注出各本異文情況,不予取舍;若可明斷為誤者,則注明取舍。如“卷一之二”卷末校云:“經(jīng)文‘即應(yīng)如來’,長(zhǎng)水及諸本并同,溫陵本作‘為應(yīng)如來’。‘即汝一身,應(yīng)成兩佛’,定本云‘佛字當(dāng)改物字,義圓。’今人繆妄如此,舉以立戒。”[3]162“卷第一之三”卷末校記云:“經(jīng)文‘皆由不知真際所指’,干道、紹興及海眼、溫陵并云‘真際所詣’,惟長(zhǎng)水本作所指。……‘既無我眼,不成我見’句下,長(zhǎng)水、溫陵及干道、紹興二本,俱無‘以我眼根’四字,會(huì)解添出,流俗本仍其誤耳。定本卻注云‘藏本闕此四字,應(yīng)補(bǔ)。’其陋如此。長(zhǎng)水本‘非我見性,自開自合’,諸本作‘有開有合’,乾道、紹興及溫陵等并同,今且從長(zhǎng)水。”[3]187
三、鉤沉輯佚,取材廣泛
自唐惟愨法師疏解開始,歷代諸家疏解之作繁多,其中有得以弘傳者,亦有散失亡佚者。錢謙益疏解此經(jīng)時(shí),正值其以藏書而雄踞一時(shí)的絳云樓化為灰燼之后。雖往日藏書盛況已不可睹,半生辛苦都為祝融取之而去,但從《疏解蒙鈔》中,亦可反映出其取材之廣與疏注之精。錢謙益《疏解蒙鈔》,于諸家舊疏,廣泛鉤沉,搜羅頗豐。清初通理所作《楞嚴(yán)經(jīng)指掌疏懸示》,則是在錢謙益《古今疏解品目》基礎(chǔ)上擴(kuò)充而成,其“錢謙益先生《疏解蒙鈔》”條下云:“先生自稱蒙叟,蓋謂取諸家疏解而以蒙義鈔之。上取崇福已下諸師,以長(zhǎng)水為司南。仍復(fù)網(wǎng)羅多家,衷其得失,其搜剔之心良苦”[3]166,對(duì)其取材之廣與用力之勤,略示一二。據(jù)《大正藏》及《續(xù)藏經(jīng)》中所收《楞嚴(yán)經(jīng)》疏解之作,見存者約為54種,其中見于《大正藏》者1種,見于《續(xù)藏經(jīng)》者53種。就疏解創(chuàng)作時(shí)代而論,作于宋代者8種,作于元代者1種,作于明代者30種,作于清代者14種,年代作者不詳者1種。錢謙益的《古今疏解品目》,共收《楞嚴(yán)經(jīng)》疏解類著作計(jì)54人63種,其中唐代4種,五代1種,宋代18人21種,元代4種,明代27人33種。除福唐沙門可度的《楞嚴(yán)經(jīng)箋》未收外,將此前《楞嚴(yán)》疏解著作囊括無余。
當(dāng)然,《古今疏解品目》中所著錄之書,當(dāng)時(shí)并非全部見存,也有部分亡佚之作。有書雖不存,但其只言片語(yǔ)僅存于諸家疏注之中,錢氏將其輯之而出。此類則有真際崇節(jié)法師《刪補(bǔ)疏》、檇李靈光洪敏法師的《證真鈔》,“未見全文,略見《義海》諸錄。”[3]82“蘇臺(tái)元約《疏鈔》,宋時(shí)盛行于世,今不傳。又有道歡法師《手鑒》及《釋要》等,皆鈔類也,今略見海眼《補(bǔ)注》及桐洲《集注》。”[3]82又有從通行本中單獨(dú)輯為一書的,如元天目中峰幻住明本的《楞嚴(yán)征心辨見或問》一卷系從“《中峰廣錄》別出”,天如惟則的《楞嚴(yán)會(huì)解》有高麗麻谷將惟則補(bǔ)注之語(yǔ)別出;紫柏達(dá)觀的《楞嚴(yán)解》系從《紫柏全集》中別出;等等。
在《疏解蒙鈔》經(jīng)文疏解中,錢氏先用大字列經(jīng)文,次低一字大字列經(jīng)疏*所用解經(jīng)之疏文,以長(zhǎng)水為主,《宗鏡》及其他諸家疏文亦兼有采之。,后以小字廣列諸家之作,以解疏文,亦有兼解經(jīng)文的。若遇諸家疏解不通之作,則另列“引證”一條,于三藏十二部經(jīng)廣征博引,疏通證明,此處最見錢氏搜集用功之處。若遇諸家疏解矛盾或其自認(rèn)為錯(cuò)誤之處,則詳列諸家觀點(diǎn),并按以“私謂”,以明取舍。此種征引編排之匠心,卷末五錄之《佛頂通錄》中透露出一二,“蒙謂引雷庵之論以駁無說,不若移妙喜之書以駁無盡,所謂借婆裙帔拜婆年也。同是大藏也,安得尊《般若》而易《首楞》;同是刊經(jīng)也,安得贊張相而訶孫尹。識(shí)法者懼自語(yǔ)相違。若不以妙喜駁無盡,殆又將以妙喜駁妙喜也。”[3]792
四、揀擇異同,疏以存史
錢謙益曾任史官,具有強(qiáng)烈的史官意識(shí)與存史意識(shí),明亡后,此一意識(shí)顯得更為強(qiáng)烈和突出。80卷之《列朝詩(shī)集》,以詩(shī)存史,乃其為存明代之詩(shī)而有意之作;20卷之《錢注杜詩(shī)》,以詩(shī)證史,詩(shī)史互證;200余卷之《明史》,雖毀于絳云樓火災(zāi)之中,而存以至今的《國(guó)初群雄事略》《明史斷略》《太宗實(shí)錄辨證》,亦見其史識(shí)、史才與史學(xué)考據(jù)之功力。錢謙益強(qiáng)烈的史官意識(shí),亦貫穿于佛教經(jīng)典整理與相關(guān)史論中。他對(duì)史傳燈錄撰寫之重要性與緊迫性,有著充分的認(rèn)識(shí);對(duì)僧人傳記之書寫規(guī)范,也提出了自己的三點(diǎn)原則;而《初學(xué)集》《有學(xué)集》二集中存留下來的大量的僧人塔銘與傳記,更是其佛教史觀的鮮明體現(xiàn)。同樣,在《疏解蒙鈔》中,他的史官意識(shí)亦得以展現(xiàn)。
《疏解蒙鈔》中的史學(xué)意識(shí),前論《古今疏解品目》中已見一端。其后之《佛頂五錄》,共分佛頂圖錄、佛頂序錄、佛頂枝錄、佛頂通錄、佛頂宗錄5部分,可視為《楞嚴(yán)經(jīng)》之傳譯、疏解、流傳、授受之史的概述,現(xiàn)一一簡(jiǎn)論如下。
《佛頂圖錄》共收?qǐng)D19幅,如序所云:“目雖在面,假鏡以尋,圖像引目,可此鏡心。心如畫師,巧幻遷改,茫茫七趣,填設(shè)繪彩。道場(chǎng)法界,天宮地獄,觀網(wǎng)交羅,燦然尺幅”[3]703。其中前2幅圖為楞嚴(yán)持咒結(jié)壇圖,第3至第6幅為涉及佛教宇宙觀念的大千世界、須彌山、忉利天宮諸圖,第7至第15為關(guān)涉此經(jīng)具體內(nèi)容的諸如二十五有、楞嚴(yán)圣位等圖解,第16至18為臺(tái)家關(guān)涉楞嚴(yán)觀法之圖,其中第18幅《總會(huì)楞嚴(yán)十義之圖》,錢氏注云:“后一圖所謂《總會(huì)十義》者,未知出于何宗。以古人立此觀法,師資相承,必有來自。今既未能根尋原委,對(duì)決是非,則寧過而存之,庶后之君子,或參考而有得焉”[3]703,此言表現(xiàn)出濃厚的史料輯存意識(shí)。
《佛頂枝錄》為錢氏輯《楞嚴(yán)》疏解序跋之作,或可視為輯錄體目錄著錄之作。《佛頂枝錄》分傳譯、證本、藏教、弘法、義解、悟解、隨喜7個(gè)部分,搜集歷代目錄史傳資料中關(guān)于《楞嚴(yán)經(jīng)》的史料,分門別類,加以輯錄,可視為一部《楞嚴(yán)》之接受史。傳譯部分輯《結(jié)古今譯經(jīng)圖記》《宋高僧傳》《釋氏稽古略》《佛祖通載》等史料,對(duì)《楞嚴(yán)經(jīng)》的傳譯過程予以揭示,并對(duì)房融潤(rùn)文之疑提出回應(yīng),從章法、文法、句法、字法四個(gè)方面分析了《楞嚴(yán)經(jīng)》的潤(rùn)文之妙,充分肯定了《楞嚴(yán)經(jīng)》獨(dú)具文學(xué)色彩的一面。證本一節(jié),引《經(jīng)律異相》《佛國(guó)記》《法苑珠林》《高僧傳》等記載,考察了《楞嚴(yán)經(jīng)》經(jīng)本持誦流傳情況,考證了唐前流傳之《首楞嚴(yán)經(jīng)》為《首楞嚴(yán)三昧經(jīng)》,“王舍城阇崛山所說,非舍衛(wèi)國(guó)祇桓精舍所說之《首楞嚴(yán)》也”[3]748,對(duì)晉宋已有持誦而智者大師不見于隋的質(zhì)疑予以解釋。藏教節(jié)中則通過大小乘諸經(jīng)的考查,對(duì)阿難與摩登伽的宿世歷劫因緣進(jìn)行考察,“未可以為人天小教,概從鐫削也。今通會(huì)諸經(jīng),節(jié)而錄之,亦證本之馀耳。”[3]749弘法專載歷代《楞嚴(yán)經(jīng)》弘傳之事;義解則記《楞嚴(yán)經(jīng)》義理參究之事,其中多為《古今疏解品目》諸師解經(jīng)之余事,以天臺(tái)、華嚴(yán)二家為主;悟解篇載因《楞嚴(yán)》而開悟之事,以禪家為主,以教外諸人開悟之事附之于后。
《佛頂通錄》與《佛頂宗錄》分別從教家與宗家入手,籍以說明宗通與宗通“橫豎自在”,有調(diào)和二家跡象。其中《佛頂宗錄》從垂示宗旨、參會(huì)公案、舉拈偈頌三個(gè)方面入手,從二土初祖開始,通過禪宗諸師歷史的考察,對(duì)當(dāng)下禪宗內(nèi)部出現(xiàn)的種種弊病以史實(shí)的回應(yīng),企圖以此為禪林中人建立一標(biāo)的,使似盛而衰的禪家諸派走上發(fā)展振興之路。正如其序所云:“魔民亂宗,蛇鬼橫縱,拂蕩教網(wǎng),拍盲鼓聾。亦有邪慧,掠宗附教,吹網(wǎng)貯風(fēng),離鏡覓照。攝為宗錄,證明別傳。春在華枝,月落萬川。”[3]807
五、余論
錢謙益《疏解蒙鈔》,為其晚年一部力作,亦為錢氏頗為滿意之作,自云“自今已往,一切大乘契經(jīng),與夫諸圣造論,宗趣深遠(yuǎn),義疏繁芿者,胥當(dāng)依佛頂之例,權(quán)閣今文,先宗古釋。務(wù)俾先佛心宗與古師教眼分齊吻合,血脈疏通,大義炳然,微言不墜。然后網(wǎng)羅多家,衷其得失,將使四河俱入,勿令一漚自認(rèn)。如是則如來之慧命續(xù)矣,法燈衍矣。宗教不患乎分涂,魔外不憂其熾盛矣。”[3]80書成后,遍示于當(dāng)時(shí)佛門諸師如蒼雪徹、蕅益旭、含光渠、松影省、勖伊閑、介立旦、雪藏韶、介丘殘、石林源及好友陸孟鳧等人。雪藏紹師大為贊揚(yáng),并作偈兩首以贈(zèng),可見此書在當(dāng)時(shí)教界之影響。清初通理作《楞嚴(yán)經(jīng)指掌疏懸示》,后列《楞嚴(yán)經(jīng)》古今疏解之作凡68家,明及明前62家,其中54家取自于錢氏《疏解蒙鈔·古今疏解品目》,可見其受錢氏影響之大。令錢謙益生前所料不及的是,乾隆一朝,他本人名列貳臣,其書屢遭禁毀,《疏解蒙鈔》“但以其筆墨不慎,奉旨撤出藏函”,此書亦無聞?dòng)诮探纾敝两溃?jīng)梁?jiǎn)⒊岢S著晚明佛教及錢謙益研究的開展,此書逐漸為學(xué)人所重視。
又錢謙益文獻(xiàn)學(xué)方面的成就及對(duì)后世的影響,是學(xué)界近年來較為熱鬧的一個(gè)話題,與之而起的對(duì)其藏書、書目題跋、版本目錄方面考察亦多,成果也豐。就錢氏本人而言,若缺少對(duì)其佛教文獻(xiàn)的探討,終非完璧。錢謙益的佛教文獻(xiàn)學(xué)成就,如其經(jīng)本題跋、經(jīng)典疏注、文字校勘、版本目錄諸方面,都取得了較大的成就。本文所成,雖有感于此,卻苦于識(shí)見淺薄,難窺其萬一,只借其《楞嚴(yán)經(jīng)疏解蒙鈔》,對(duì)上述種種作一簡(jiǎn)單描述,以期拋磚引玉。
[1] 梁?jiǎn)⒊?中國(guó)近三百年學(xué)術(shù)史[M].北京:遠(yuǎn)方出版社,2004:196.
[2] 章學(xué)誠(chéng).文史通義校注[M].葉瑛,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 945.
[3] 錢謙益.楞嚴(yán)經(jīng)疏解蒙鈔[M]∥藏經(jīng)書院.新編卐續(xù)藏經(jīng).臺(tái)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
[4] 龔雋.宋明楞嚴(yán)學(xué)與中國(guó)佛教的正統(tǒng)性——以華嚴(yán)、天臺(tái)《楞嚴(yán)經(jīng)》疏為中心[J].中國(guó)哲學(xué)史,2008(3):3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