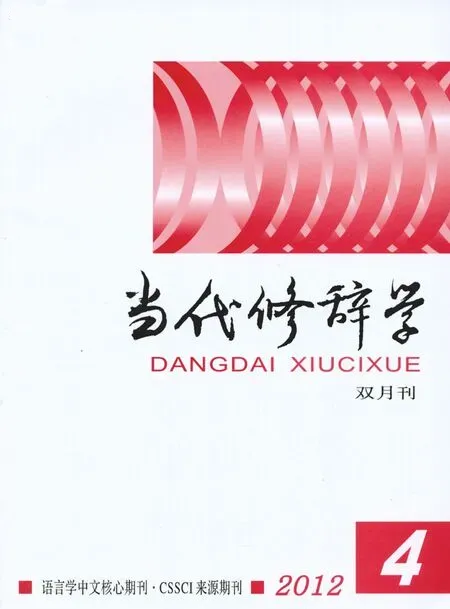詞語(yǔ)、對(duì)話和小說(shuō)*
朱莉婭·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
(法國(guó)巴黎第七大學(xué),法國(guó)巴黎)
祝克懿 宋姝錦 譯 黃 蓓 校
(復(fù)旦大學(xué)中文系,上海200433)
在“人文”領(lǐng)域內(nèi)進(jìn)行科學(xué)操作的有效性總是受到質(zhì)疑。然而引人注目的是,頭一次,此種質(zhì)疑產(chǎn)生于被研究結(jié)構(gòu)的內(nèi)部,而該種結(jié)構(gòu)從屬于科學(xué)邏輯的一種邏輯。這里涉及的是語(yǔ)言邏輯(尤其是詩(shī)性語(yǔ)言的邏輯);它的明晰化來(lái)自于“書寫”(é criture)——我指的是那種能夠明顯展示出詩(shī)性意義之構(gòu)成的“動(dòng)態(tài)書寫”(gramme dynamique)。于是,文學(xué)符號(hào)學(xué)面臨著兩種選擇:要么沉默與放棄,要么繼續(xù)努力,建構(gòu)起一種同構(gòu)于此種非科學(xué)邏輯的模式,亦即一種同構(gòu)于詩(shī)學(xué)意義的架構(gòu);而詩(shī)學(xué)意義正處于當(dāng)今符號(hào)學(xué)關(guān)注的中心。
俄國(guó)形式主義被當(dāng)代結(jié)構(gòu)分析尊為思想源頭,這一門結(jié)構(gòu)分析的學(xué)說(shuō)曾因?yàn)槲膶W(xué)和科學(xué)之外的理由而面臨與以上兩種選擇相同的抉擇,不得不暫時(shí)停下腳步。幸而有()的推動(dòng),研究仍在進(jìn)行。他的作品代表了這個(gè)運(yùn)動(dòng)最卓著的成果,也是超越理論局限的楷模。巴赫金不像語(yǔ)言學(xué)家那樣必須恪守專業(yè)技術(shù)的規(guī)范,他寫作文思泉涌,甚至帶有預(yù)言性。當(dāng)今敘事學(xué)的結(jié)構(gòu)研究所關(guān)涉的根本問(wèn)題,他都有所論及,這使他約四十年以前所勾勒的文本研究具有了當(dāng)下意義。作為作家,也作為學(xué)者,巴赫金為結(jié)構(gòu)主義打開(kāi)了一個(gè)動(dòng)態(tài)的面向。他率先推翻了文本的靜態(tài)切割的觀念,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動(dòng)態(tài)的模式。他的學(xué)說(shuō)主張文學(xué)結(jié)構(gòu)不是不變的存在,而是在和結(jié)構(gòu)互動(dòng)時(shí)產(chǎn)生。這種動(dòng)態(tài)結(jié)構(gòu)主義的出發(fā)點(diǎn)是,“文學(xué)語(yǔ)詞”不再被視為一個(gè)“點(diǎn)”(即固定含義),而是一個(gè)多重文本“平面交叉”,是多重寫作的對(duì)話。書寫者包括作者、讀者(或角色)以及當(dāng)下或過(guò)去的文化背景。
文本空間內(nèi)的詞語(yǔ)
把詞語(yǔ)的特殊地位界定為一種能指,通過(guò)它在不同文類或文本中標(biāo)示不同的(文學(xué))理解模式,將詩(shī)學(xué)分析放置在現(xiàn)代“人文”科學(xué)的關(guān)注中心——也就是放在(,思想的真實(shí)實(shí)踐①)和(,通過(guò)差異的匯集彰顯意義的場(chǎng)所)的交集處。探究語(yǔ)詞的地位首先是探討其在句子中與其他詞的聯(lián)結(jié)(復(fù)雜語(yǔ)義關(guān)系),然后移至更大序列的關(guān)聯(lián)層面尋找相同的功能或關(guān)系。針對(duì)詩(shī)學(xué)語(yǔ)言實(shí)踐的空間概念,首先必須界定文本空間的三個(gè)維度,不同的語(yǔ)義組和詩(shī)學(xué)序列就是在這個(gè)空間中發(fā)生作用。對(duì)話的三個(gè)維度,分別為寫作主體、讀者或外部文本三種元素的對(duì)話。如此一來(lái),語(yǔ)詞的地位②是由(文本中的詞語(yǔ)同時(shí)屬于作者和讀者)決定的,也是由(文本中的詞語(yǔ)指向先前的或共時(shí)層面的文本集合)決定的。
然而,在一本書的對(duì)話空間中,受話者僅作為話語(yǔ)而存在。從而融入與作者本人的書寫形成對(duì)照的他話語(yǔ)(他文本)。因此水平軸(主體—讀者)和垂直軸(文本—情境)交匯,凸顯了一個(gè)重要的事實(shí):即每一個(gè)語(yǔ)詞(文本)都是語(yǔ)詞與語(yǔ)詞(文本與文本)的交匯,至少有一個(gè)他語(yǔ)詞(他文本)在交匯處被讀出。在巴赫金的著作中,他稱之為()與()的兩個(gè)軸沒(méi)有明顯的區(qū)別。表面看論述似乎欠缺嚴(yán)謹(jǐn),實(shí)際上是巴赫金為文學(xué)理論首次做出的一個(gè)深度闡釋:任何文本的建構(gòu)都是引言的鑲嵌組合;任何文本都是對(duì)其它文本的吸收與轉(zhuǎn)化。從而,()的概念取代了主體間性的概念,詩(shī)性語(yǔ)言至少能夠被()解讀。
因此,描寫語(yǔ)詞在不同文類(文本)中特定的運(yùn)作模式要求有一個(gè)()的方法。首先,我們必須把文學(xué)體式看作是非完善的符號(hào)系統(tǒng),“它的意義藏在語(yǔ)言下面,但缺不了語(yǔ)言”;其次,跳出語(yǔ)言學(xué)模式的范疇,從意義擴(kuò)張的原則出發(fā),使用更大的話語(yǔ)單位,例如句子、回應(yīng)、對(duì)話等。所以,我們可以提出并論證以下假說(shuō):任何。小說(shuō)尤其是語(yǔ)言對(duì)話的外化。③
詞語(yǔ)與對(duì)話
俄國(guó)形式主義學(xué)者執(zhí)著于“語(yǔ)言對(duì)話”的思想。他們強(qiáng)調(diào)語(yǔ)言交際的對(duì)話性④,并且認(rèn)為作為()的“萌芽形式”(forme embryonnaire)⑤,是對(duì)話的副產(chǎn)品。其中一些人區(qū)分了獨(dú)白話語(yǔ)(“相當(dāng)于一種精神狀態(tài)”)⑥和敘事(“獨(dú)白語(yǔ)篇的藝術(shù)模仿”)⑦之間的區(qū)別。艾亨鮑姆(Boris Eikhenbaum)對(duì)果戈里(Gogol)的《外套》的著名研究就是基于上述理論基礎(chǔ)。艾亨鮑姆指出,果戈里的文本涉及了敘事的口語(yǔ)形式及其語(yǔ)言特征(語(yǔ)調(diào)、句法構(gòu)式、詞匯等)。他得出和兩套敘事模式,并分析兩者間的關(guān)系。但是,他似乎沒(méi)有注意到在涉及口語(yǔ)語(yǔ)篇之前,敘事作者通常涉及另一人的話語(yǔ),而他的口語(yǔ)語(yǔ)篇僅是次要的(因?yàn)樗耸强谡Z(yǔ)語(yǔ)篇的載體⑧)。
比起俄國(guó)形式主義者對(duì)對(duì)話與獨(dú)白間的區(qū)別之解讀,巴赫金所賦予的區(qū)別意義更加廣闊。對(duì)話與獨(dú)白的分野并不對(duì)應(yīng)于敘事與戲劇中與(獨(dú)白與對(duì)話)之間的區(qū)別。巴赫金認(rèn)為,對(duì)話可以是獨(dú)白的,所謂的獨(dú)白也可以是對(duì)話。于他而言,“對(duì)話”與“獨(dú)白”關(guān)涉到語(yǔ)言學(xué)的基礎(chǔ)架構(gòu),其研究需要藉助文學(xué)文本研究的,而這種符號(hào)學(xué)不應(yīng)停留于語(yǔ)言學(xué)方法或邏輯規(guī)則,而是從它們出發(fā)進(jìn)行自我建構(gòu)。“語(yǔ)言學(xué)研究語(yǔ)言本身,研究它的特屬邏輯與它的單位;它們使對(duì)話交流成為可能。但是語(yǔ)言學(xué)并不關(guān)心對(duì)話關(guān)系本身。……對(duì)話關(guān)系不能還原為邏輯或具體的語(yǔ)義關(guān)系,因?yàn)檫壿嫾罢Z(yǔ)義本身并不含有對(duì)話要素。它們需要語(yǔ)詞成分,需要成為闡述與表達(dá),需要成為不同主體定位,之后才能產(chǎn)生對(duì)話關(guān)系……取消邏輯和具體的語(yǔ)義關(guān)系就沒(méi)有了對(duì)話關(guān)系,然而,對(duì)話關(guān)系絕無(wú)可能被還原為邏輯與語(yǔ)義(對(duì)話關(guān)系有其自身獨(dú)有的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詩(shī)學(xué)問(wèn)題》)
巴赫金一方面堅(jiān)持對(duì)話關(guān)系和純粹的語(yǔ)言學(xué)關(guān)系之間的差別,一方面卻又強(qiáng)調(diào)敘事的結(jié)構(gòu)元素(如,作者/角色,我們還可以加上闡述主體與言說(shuō)主體)之所以存在,是因?yàn)閷?duì)話性源自于語(yǔ)言本身。語(yǔ)言的這種雙重性巴赫金沒(méi)有多加解釋,但他卻堅(jiān)持“對(duì)話是語(yǔ)言唯一的生存領(lǐng)域”。今天,我們已經(jīng)在語(yǔ)言多個(gè)層面找到了對(duì)話關(guān)系:第一,在二元內(nèi)部,;第二,在語(yǔ)言系統(tǒng)內(nèi)部(作為集體契約的系統(tǒng)、獨(dú)白系統(tǒng)以及與他人對(duì)話中所實(shí)現(xiàn)的關(guān)聯(lián)性價(jià)值系統(tǒng))。第三,言語(yǔ)系統(tǒng)內(nèi)部(重要的是“組合性”,即不是純粹的創(chuàng)造,而是基于符號(hào)交換的個(gè)體形成)。在另一個(gè)層面上(可與小說(shuō)的雙值性空間相比較),甚至“語(yǔ)言的雙重性”也被指出,即組合性(syntagmatique,通過(guò)外延、在場(chǎng)和轉(zhuǎn)喻來(lái)實(shí)現(xiàn))與系統(tǒng)性(sys té matique,通過(guò)聯(lián)想、不在場(chǎng)和譬喻來(lái)實(shí)現(xiàn))。把這兩個(gè)語(yǔ)言軸的對(duì)話交換作為小說(shuō)雙值性的基礎(chǔ),從語(yǔ)言學(xué)的角度分析它們,這相當(dāng)重要。值得關(guān)注的還有雅各布遜(R.Jakobson《普通語(yǔ)言學(xué)文集》()第九章)關(guān)于雙重結(jié)構(gòu)和它們橫跨代碼/訊息關(guān)系的論述 ,其相關(guān)學(xué)說(shuō)有助于闡明巴赫金關(guān)于對(duì)話性存在于語(yǔ)言內(nèi)部的觀點(diǎn)。
雙值性
術(shù)語(yǔ)“雙值性(ambivalence)”指歷史(社會(huì))植入一個(gè)文本,文本也植入歷史(社會(huì));對(duì)于作者來(lái)說(shuō),這兩者是一回事。當(dāng)巴赫金提及“敘事中交匯的兩種路徑”時(shí),他認(rèn)為寫作是對(duì)先前文本集合的閱讀,而文本是對(duì)其他文本的吸收與回應(yīng)。他視復(fù)調(diào)小說(shuō)的形成是對(duì)狂歡話語(yǔ)的吸收,而視獨(dú)白體小說(shuō)為文學(xué)結(jié)構(gòu)的一種壓制。因?yàn)閷?duì)話性,巴赫金稱之為“梅尼普(M é nipp é e)諷刺體”。以這種觀點(diǎn)來(lái)看,單從語(yǔ)言學(xué)角度是不能完全掌握文本的。巴赫金認(rèn)為他所謂的,基于語(yǔ)言對(duì)話性發(fā)展出來(lái)的()科學(xué)能夠幫助我們理解互文關(guān)系,亦即在十九世紀(jì)被稱為文學(xué)的“社會(huì)價(jià)值”或道德“聲音”的。洛特雷阿蒙(Laut ré amont)意圖通過(guò)寫作實(shí)現(xiàn)一種。在他的作品中,這種道德由文本的雙值性實(shí)現(xiàn):《馬爾多羅之歌》()和《詩(shī)選》()自始至終都是與以往文學(xué)資料庫(kù)的對(duì)話,是對(duì)之前文本的不斷的抗議。對(duì)話性與雙值性合二為一,使作者在以同一種方式進(jìn)入歷史的時(shí)候,能夠表達(dá)兩種道德:否定時(shí)亦為肯定。
從對(duì)話性與雙值性可以得出如下結(jié)論:在某一文本的內(nèi)部空間以及,詩(shī)性語(yǔ)言具有雙重性。索緒爾的詩(shī)的(“Anagrammes”)從擴(kuò)展到:?jiǎn)挝弧耙弧保ǘx;“事實(shí)”)在這里是不存在的。從而,“定義”、“規(guī)定性”、符號(hào)“=”的內(nèi)涵以及被設(shè)定在能指與所指之間存在縱向(層級(jí))關(guān)系的符號(hào),都不適用于詩(shī)歌語(yǔ)言,因?yàn)楹笳甙鵁o(wú)數(shù)組合融匯的可能。
在總結(jié)他們的思想之前,我們應(yīng)該關(guān)注受其思想影響產(chǎn)生的一種觀點(diǎn):即所有基于0-1序列的邏輯系統(tǒng)(真—假,虛無(wú)—存有)對(duì)解釋詩(shī)歌語(yǔ)言運(yùn)作是無(wú)能為力的。
科學(xué)的發(fā)展實(shí)際上都基于一種邏輯方法,而這種邏輯本身建立于希臘(印歐)句式。這種句式以主語(yǔ)—謂語(yǔ)開(kāi)頭,以識(shí)別、判斷和因果關(guān)系發(fā)展。現(xiàn)代邏輯,從弗雷格(Gottlob Frege)和皮阿諾(Giuseppe Peano)到盧卡西維茨(Jan Lukasiewicz)、阿克曼(Robert Ackermann)和徹奇(Alonzo Church),都是從0-1序列逐漸發(fā)展形成的;布爾(George Boole),一開(kāi)始從事于集合論研究,他發(fā)明的數(shù)學(xué)公式更切合語(yǔ)言邏輯——但是所有這些在詩(shī)性語(yǔ)言的領(lǐng)域內(nèi)都是無(wú)效的,因?yàn)樵谀抢铮?”不再是有限的。
因此,如果不修正這些現(xiàn)存邏輯(科學(xué))方法,那么就不可能將詩(shī)性語(yǔ)言形式化。文學(xué)符號(hào)學(xué)必須在()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在詩(shī)學(xué)邏輯中,)觀念能夠具體體現(xiàn)0-2區(qū)間內(nèi),以0為起始標(biāo)志,1則被絕對(duì)地僭越了。
在從0到特定的詩(shī)學(xué)雙重性的“連續(xù)體的能量”中,人們意識(shí)到:(語(yǔ)言的、心理的和社會(huì)的)“禁律”是1(上帝、法律、規(guī)定)。詩(shī)性語(yǔ)篇是擺脫此“禁律”的唯一一種語(yǔ)言實(shí)踐。東西方有兩位學(xué)者都指出了運(yùn)用亞里士多德式的邏輯來(lái)分析語(yǔ)言時(shí)產(chǎn)生的缺陷,這絕非偶然。一位是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哲學(xué)家張東蓀(Chang Tung-Sun),提出了一種語(yǔ)言學(xué)范疇(即表意字)。在那里,陰—陽(yáng)“對(duì)話”取代了上帝;另一位是巴赫金,他試圖在革命的社會(huì)中通過(guò)一種動(dòng)態(tài)的理論建構(gòu)來(lái)超越形式主義。巴赫金將敘事話語(yǔ)逐漸引入史詩(shī)話語(yǔ),他認(rèn)為敘事是禁令,是的,從屬于符號(hào)1,從屬于上帝。因此,史詩(shī)是宗教和神學(xué)上的;所有符合0-1邏輯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敘事都是教條主義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小說(shuō),巴赫金稱之為獨(dú)白式小說(shuō)(如托爾斯泰的小說(shuō)),更傾向于在這樣的空間內(nèi)發(fā)展演進(jìn)。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描寫、“角色”的定義、“人物”的生成、“主題”的發(fā)展,所有這些描寫敘事都屬于0-1之間的搖擺,因此也都是的。狂歡話語(yǔ)是唯一完全達(dá)到0-2詩(shī)學(xué)邏輯的話語(yǔ)。通過(guò)采納夢(mèng)境的邏輯,它違背了語(yǔ)言與社會(huì)道德的規(guī)則。
事實(shí)上,狂歡節(jié)對(duì)語(yǔ)言規(guī)則、(邏輯規(guī)則、社會(huì)規(guī)則)的違背之所以能夠成立并且有效,因?yàn)樗袷兀ǎ?duì)話理論并不是“暢所欲言”,它是一種((洛特雷阿蒙Laut ré amont),一種除了0之外的必要的。我們需要特別強(qiáng)調(diào)對(duì)話的特性是(),從而完全絕對(duì)地把自己與明顯存在于一些現(xiàn)代“情欲”和仿作文學(xué)中的偽叛逆區(qū)別開(kāi)來(lái)。后者將自己視為“浪蕩子”和“相對(duì)化”,它的行動(dòng)場(chǎng)是內(nèi)在包含()。因此,它只是獨(dú)白式的補(bǔ)充,并沒(méi)有取代0-1區(qū)間,于對(duì)話理論的理論構(gòu)架毫無(wú)用處。對(duì)話理論意味著與規(guī)則的絕對(duì)決裂,它所包含的對(duì)立因素不是非此即彼的關(guān)系。
從詩(shī)學(xué)語(yǔ)言的對(duì)話性和雙值性觀念出發(fā),巴赫金對(duì)小說(shuō)結(jié)構(gòu)進(jìn)行了再評(píng)價(jià)。這個(gè)研究采取的形式是在敘事中對(duì)詞語(yǔ)進(jìn)行分類——分類與言語(yǔ)的類型學(xué)有關(guān)。
敘事中的詞語(yǔ)類型
根據(jù)巴赫金的研究,敘事中有三類詞。
第三類是指這樣一類詞:作者可以作用于他人語(yǔ)詞,給它一個(gè)新的意思,同時(shí)保留它原有的意思。結(jié)果就是一個(gè)詞有了兩個(gè)意義:它變成了()。因此,雙值詞(Le mot ambivalent)就是兩種符號(hào)系統(tǒng)疊加在一起的結(jié)果。隨著文本類型的不斷演變,雙值詞出現(xiàn)在梅尼普和狂歡文本中(我會(huì)回到這一點(diǎn))。兩個(gè)符號(hào)系統(tǒng)的接合使文本具有相對(duì)性,有距離地使用他人語(yǔ)詞是文體風(fēng)格形成帶來(lái)的結(jié)果。與之相反()(更確切地說(shuō),巴赫金指的是())將被模仿物(被重復(fù)物)嚴(yán)肅對(duì)待,讓它保有原貌,只是將其占為己有,而沒(méi)有相對(duì)化。第一類雙值詞的特點(diǎn)是作者為了自己的目的而采用他人的話語(yǔ)——不違背其思想;作者跟隨他人話語(yǔ)的方向,同時(shí)卻也使它相對(duì)化。雙值詞的第二種類型,如(),非常地不同。作者在這里引入了一個(gè)意義,與他人語(yǔ)詞的意義相反。雙值詞的第三種類型,如內(nèi)在(),特點(diǎn)是他人語(yǔ)詞對(duì)作者語(yǔ)詞產(chǎn)生主動(dòng)的(改動(dòng)的或修辭的)影響。作者“說(shuō)話”,但是“他話語(yǔ)”持續(xù)不斷地出現(xiàn)與干擾作者的話語(yǔ)。通過(guò)雙值詞的這種類型,他人語(yǔ)詞通過(guò)敘事者語(yǔ)詞呈現(xiàn)。例子包括自傳、辯詞、問(wèn)答和隱跡對(duì)話。小說(shuō)是唯一一種出現(xiàn)雙值詞的體裁類型;這是小說(shuō)結(jié)構(gòu)的獨(dú)有特征。
指示詞或歷史詞的內(nèi)在對(duì)話性
單義性或客觀性的概念被用于獨(dú)白及與獨(dú)白有關(guān)的史詩(shī)、抑或指示詞與對(duì)象詞。單義性無(wú)法抵御心理分析或語(yǔ)義分析。對(duì)話性與言語(yǔ)的深層結(jié)構(gòu)是同延的。盡管巴赫金和本維尼斯特沒(méi)有這樣說(shuō),對(duì)話性還是作為普遍的闡述原則在巴赫金的指示詞語(yǔ)層面出現(xiàn),同時(shí)在本維尼斯特的“”層面出現(xiàn)。故事,正如本維尼斯特的“言語(yǔ)”本身的概念,通過(guò)敘事中的說(shuō)話者預(yù)設(shè)了一個(gè)中介,有對(duì)他者的指向。為了描述指示詞或歷史詞的內(nèi)在對(duì)話性,我們需要借助于寫作的心理機(jī)制,即寫作作為作者與自己(亦即與另一人)對(duì)話的痕跡,作為作者與自己的遠(yuǎn)離,作為作者呈闡述主體和言說(shuō)主體的分裂。
正是通過(guò)敘事行為,敘事主體面向另一個(gè)人或他者;在與另一個(gè)人或他者的關(guān)系中建構(gòu)敘事(在這種交流關(guān)系的影響下,蓬熱(Francis Ponge)對(duì)“我思,故我在”提出了自己的改寫:“我說(shuō),你聽(tīng),故我們?cè)凇!睆亩僭O(shè)了一種從主體性到雙值性的轉(zhuǎn)變)。因此,我們認(rèn)為敘事(超越了能指/所指關(guān)系)是敘事()和()——他者之間的對(duì)話。受話者就是閱讀主體,代表著一個(gè)雙重定位統(tǒng)一體:相對(duì)于文本它是能指,相對(duì)于敘事主體它是所指。因此,這個(gè)統(tǒng)一體是一個(gè)二元對(duì)立體(D1和D2),雙方彼此對(duì)話,建構(gòu)起一個(gè)代碼系統(tǒng)。敘事主體(S)被引入,因此降級(jí)為一個(gè)代碼、一個(gè)不存在的人或者一個(gè)由第三者(他/她,人物角色即表達(dá)主體)傳達(dá)的(如作者即闡述主體)。作者因?yàn)榧尤氲綌⑹孪到y(tǒng)中,其敘事主體身份有所變動(dòng);他既不是虛無(wú)的,也不是任何人,而是從S置換到D,從故事轉(zhuǎn)換成言語(yǔ),從言語(yǔ)轉(zhuǎn)換成故事的可能因素。他變得隱匿、不在場(chǎng)、空位,從而使結(jié)構(gòu)得以這樣存在。在敘事的源頭,在作者出現(xiàn)的那個(gè)時(shí)刻,我們?cè)庥隹瞻住.?dāng)寫作通過(guò)敘事結(jié)構(gòu)將語(yǔ)言系統(tǒng)外化,文學(xué)就碰觸到了一個(gè)神經(jīng)的痛處;我們看到死、生和性等問(wèn)題的出現(xiàn)。在這個(gè)作者所處的無(wú)名氏位置、在這個(gè)零度的基礎(chǔ)上,角色的()就誕生了。接下來(lái)的階段,它就變成了一個(gè)()。所以,在文學(xué)文本中,“0”是不存在的;空無(wú)轉(zhuǎn)眼間被“1”取代(他,專有名詞);實(shí)際上是“2”(主體與受話者)。正是受話者、他者、外在性(它的對(duì)象是敘事主體,并同時(shí)被表現(xiàn)和表現(xiàn)著)將主體轉(zhuǎn)變成,也就是說(shuō),讓敘事主體走向零度、否定、排斥這個(gè)構(gòu)成作者的層面)在這個(gè)主體和他者之間、作者和讀者之間的交互運(yùn)動(dòng)中,作者被建構(gòu)成一個(gè)能指,文本也被建構(gòu)成兩個(gè)話語(yǔ)的對(duì)話。
角色(人物)的構(gòu)建方式也允許S分裂成S(a闡述主體)和S(e言說(shuō)主體)。變化如圖1:

圖1
圖1 涵蓋了精神分析學(xué)家在分析對(duì)象的文本里發(fā)現(xiàn)的代詞系統(tǒng)[10](圖2):
在文本(能指)層面——在Sa和Se的關(guān)系中——我們看到主體與受話者的對(duì)話,所有敘事都是圍繞此對(duì)話建構(gòu)的。言說(shuō)主體相對(duì)于闡述主體,正如受話者相對(duì)于作者;通過(guò)使闡述主體虛空,從而將其植入寫作系統(tǒng)。馬拉美(Mallarm é)稱這種功能為“(詩(shī)人的)喑啞”。

圖2
我們剛才描述的這種面對(duì)敘事與小說(shuō)采取的方法,取消了文學(xué)實(shí)踐中無(wú)能為力的“所指·能指”的概念區(qū)分;取而代之的,是“對(duì)話性能指”。“能指代表另一個(gè)能指的主體”(拉康Lacan)。
敘事歷來(lái)都是由敘事所指向的受話者建構(gòu)起來(lái)的對(duì)話母體構(gòu)成。任何敘事,包括歷史敘事與科學(xué)敘事,都包含由敘事者和他者協(xié)力形成的對(duì)話二元體。這個(gè)二元體表現(xiàn)為Sa/Se的對(duì)話關(guān)系。Sa和Se彼此互為能指和所指,但只構(gòu)成兩種能指的對(duì)調(diào)。
然而,只有通過(guò)一定的敘事結(jié)構(gòu),作為二重符號(hào)與雙值寫作的對(duì)話才能在文本(文學(xué))現(xiàn)象層面上,在(詩(shī)性)言語(yǔ)的實(shí)際組織中得到外化。
發(fā)展言語(yǔ)類型學(xué)
巴赫金的激進(jìn)變革在于通過(guò)文本的動(dòng)態(tài)分析促進(jìn)文類的重新配置,號(hào)召我們積極發(fā)展建立言語(yǔ)類型學(xué)。
史詩(shī)獨(dú)白
這種語(yǔ)言的系統(tǒng)模式(相似性——雅各布遜)在史詩(shī)空間內(nèi)普遍存在。屬于語(yǔ)言橫組合軸的轉(zhuǎn)喻聯(lián)系是很罕見(jiàn)的。當(dāng)然,聯(lián)想和轉(zhuǎn)喻在此是作為修辭手段,但絕不會(huì)是結(jié)構(gòu)組織的原則。史詩(shī)邏輯是通過(guò)特殊尋求一般;于是,它假設(shè)了物質(zhì)結(jié)構(gòu)內(nèi)的層級(jí)結(jié)構(gòu)。故,史詩(shī)邏輯是因果的,也就是說(shuō)是神學(xué)的:它是一種從本義上理解的()。
狂歡節(jié):身體、夢(mèng)境、語(yǔ)言結(jié)構(gòu)以及欲望結(jié)構(gòu)之間的同源性
狂歡化語(yǔ)言的特點(diǎn),包括重復(fù)、“不連貫”(在無(wú)限的空間背景中仍然是有邏輯關(guān)系的)和非排他性對(duì)立,它們猶如空集合(ensembles vides)或單個(gè)的總和(sommes disjunctives):分離不同意思的詞,又將它們組織在一起,產(chǎn)生了比其他任何言語(yǔ)都明顯的對(duì)話性。狂歡通過(guò)質(zhì)疑基于0-1區(qū)間的語(yǔ)言規(guī)則,挑戰(zhàn)上帝、權(quán)威和社會(huì)規(guī)則;只要它是對(duì)話性的,它就是反叛的。由于其是具有顛覆性的言語(yǔ),所以就能夠理解在我們的社會(huì)中,為什么“狂歡節(jié)”一詞具有強(qiáng)烈貶損意味和唯一諷刺意味了。
因此,狂歡節(jié)的場(chǎng)面中,雖沒(méi)有燈光,沒(méi)有劇院,但同時(shí)卻既是舞臺(tái)也是人生,既是游戲也是夢(mèng)境,既是言語(yǔ)也是表演。于是,便成為使語(yǔ)言脫離線性(規(guī)則)的約束,能夠如三維戲劇那樣上演的唯一處所。更深一層,這也意味著反面:戲劇是語(yǔ)言的處所。于是,出現(xiàn)了一條重要原則:所有詩(shī)的言語(yǔ)都是戲劇化的,詞語(yǔ)可以戲劇化排序(從數(shù)學(xué)意義來(lái)講)。狂歡話語(yǔ)展現(xiàn)出“思想狀態(tài)猶如戲劇曲折”(馬拉美)這種呈現(xiàn)舞臺(tái)特征的狂歡話語(yǔ)正是體現(xiàn)“戲劇是朗讀一本正在寫作的書”的唯一空間。換句話說(shuō),這個(gè)舞臺(tái)是話語(yǔ)保持其自身“潛在無(wú)限性”(借用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的術(shù)語(yǔ))的唯一處所,這里各種限制(再現(xiàn)、獨(dú)白)和對(duì)他們的悖逆(夢(mèng)境、身體、對(duì)話)相共存。狂歡傳統(tǒng)被梅尼普諷刺體話語(yǔ)所吸收,并由復(fù)調(diào)小說(shuō)付諸實(shí)踐。
在普遍化的狂歡舞臺(tái)上,語(yǔ)言戲仿自己和相對(duì)化自己,否定自己的表現(xiàn)功能,(引起了搞笑的效果),卻又無(wú)法從表現(xiàn)中脫離出來(lái)。語(yǔ)言的橫向組合軸在這個(gè)空間中外化,并通過(guò)與系統(tǒng)軸的對(duì)話,建構(gòu)起由狂歡饋贈(zèng)給小說(shuō)的雙值性結(jié)構(gòu)。雙值性的,既是表現(xiàn)的又是反表現(xiàn)的,狂歡結(jié)構(gòu)是反基督教和反理性主義的。所有最重要的復(fù)調(diào)小說(shuō)都是梅尼普諷刺體和狂歡結(jié)構(gòu)的繼承者(拉伯雷、塞萬(wàn)提斯(Cervantes)、斯威夫特、薩特(Sade)、巴爾扎克(Balzac)、洛特雷阿蒙(Laut ré amont)、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ievski)、喬伊斯(Joyce)和卡夫卡等人的著作)。它的歷史同時(shí)也是同基督教及其表現(xiàn)作斗爭(zhēng)的歷史;意味著這是一種對(duì)語(yǔ)言的探索(性與死),一場(chǎng)對(duì)雙值性神圣地位的確立。
我們需要注意“狂歡話語(yǔ)”在使用中的模糊性。在當(dāng)代社會(huì),它越來(lái)越意味著戲仿,從而更加鞏固法規(guī)。人們趨于忽視它的的一面(辯證轉(zhuǎn)換意義上的謀殺、憤世嫉俗和革命)。這一方面正是巴赫金所強(qiáng)調(diào)的,也是他在梅尼普諷刺體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所認(rèn)識(shí)到的。狂歡節(jié)的笑并不是簡(jiǎn)單的戲仿;它也不是喜劇,也不是悲劇;而是二者共存,可能可以說(shuō)它是(正因如此,狂歡舞臺(tái)不是法規(guī)的舞臺(tái),也不是對(duì)法規(guī)的戲仿,而是法規(guī)的)。現(xiàn)代寫作提供了幾個(gè)明顯的例子,可視為此種類型的與同時(shí)上演的普遍化舞臺(tái);在這里不復(fù)存在,因?yàn)檫@不是戲仿,而是(安托寧·阿爾托Antonin Artaud)。
史詩(shī)話語(yǔ)與狂歡話語(yǔ)是歐洲敘事的兩股源頭,根據(jù)時(shí)代和作者,有時(shí)前者更重要,有時(shí)后者更重要。民間狂歡話語(yǔ)傳統(tǒng)在古典時(shí)代晚期的個(gè)人文學(xué)中仍然十分明顯;直到今天,它還是活水之源,在灌溉文學(xué)思想的同時(shí)將之引向新的方向。
古典人文主義推進(jìn)了史詩(shī)獨(dú)白性的消解。后者在當(dāng)時(shí)根基之牢固,出于話語(yǔ)之重要:一方面有演說(shuō)家、政治家口若懸河,另一方面有悲劇與史詩(shī)的存在。在另一種獨(dú)白體興起(隨著形式邏輯、基督教和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的人文主義的興盛[11])之前,古典時(shí)代晚期產(chǎn)生了兩種文體,語(yǔ)言的對(duì)話性從而得以彰顯。這兩種文體是()和()。它們立足于狂歡話語(yǔ)傳統(tǒng),成為日后歐洲小說(shuō)的催化劑。
蘇格拉底對(duì)話:作為個(gè)人解構(gòu)的對(duì)話
蘇格拉底對(duì)話在古代流傳甚廣:柏拉圖、色諾芬(X é nophon)、安提西斯(Antisth è nes)、埃斯基涅斯(Eschines)、斐多(Ph aé do)、歐幾里德(Euclid)和其他先哲都參與其中(盡管只有柏拉圖和色諾芬的對(duì)話被流傳下來(lái))。與其說(shuō)這是一種修辭文體,不如說(shuō)它是一種民間與狂歡的文體。它起初只是一種回憶錄(蘇格拉底與其學(xué)生的討論集)。它打破了歷史的限制,只保留了蘇格拉底通過(guò)對(duì)話探索真理的過(guò)程,以及在敘事框架中記錄對(duì)話的結(jié)構(gòu)模式。尼采指責(zé)柏拉圖忽視了酒神式悲劇,但是蘇格拉底對(duì)話卻采用了狂歡場(chǎng)景的對(duì)話和反抗結(jié)構(gòu)。依照巴赫金的說(shuō)法,蘇格拉底對(duì)話的特點(diǎn)是用對(duì)話方法尋求真理,與聲稱掌握既定真理的官方的獨(dú)白式話語(yǔ)相對(duì)立。蘇格拉底的真理(“意義”)是說(shuō)話者的對(duì)話過(guò)程的產(chǎn)物;它是具有關(guān)聯(lián)性的,觀察者的自主視角顯示出了它的相對(duì)性。它的藝術(shù)在于想象的,在于符號(hào)的。引發(fā)這種語(yǔ)言關(guān)聯(lián)網(wǎng)絡(luò)的兩個(gè)特有機(jī)制是對(duì)照法(同一話題的不同話語(yǔ)的沖撞)和引發(fā)法(一句話引發(fā)另一句話)。言語(yǔ)的主體是非個(gè)人的、匿名的,由構(gòu)建他們的言語(yǔ)所隱藏。巴赫金提醒我們,蘇格拉底對(duì)話的“事件”就是言語(yǔ)的本質(zhì):通過(guò)話語(yǔ),質(zhì)問(wèn)與檢驗(yàn)一個(gè)定理。因此,這類話語(yǔ)實(shí)踐本來(lái)就是與創(chuàng)造它的人(蘇格拉底和他的學(xué)生)聯(lián)系在一起的,或者更確切地說(shuō),話語(yǔ)是人及其活動(dòng)。我們可以說(shuō)它是一種具有交匯特征的話語(yǔ)-實(shí)踐,因?yàn)椋ǎ┡c()的分離——前者作為行為、論證、差異,后者作為再現(xiàn)、認(rèn)知、理念——在蘇格拉底對(duì)話形成的時(shí)期還沒(méi)有完成。但是,蘇格拉底對(duì)話主義卻有一個(gè)重要的“細(xì)節(jié)”,就是言語(yǔ)主體的所處的唯一情景是激發(fā)對(duì)話。在柏拉圖的《申辯篇》()中,蘇格拉底的審判與等待宣判死刑的場(chǎng)景決定了他的言語(yǔ)是一個(gè)人“站在邊沿上”的自白。這種絕對(duì)情景將詞語(yǔ)從所有單一的客觀性和表現(xiàn)功能中解放出來(lái),給它打開(kāi)了象征性空間的大門。話語(yǔ)泰然面對(duì)死亡,生成另一種話語(yǔ);這類對(duì)話將排除在外。
蘇格拉底對(duì)話與小說(shuō)中的雙值詞語(yǔ)之間的相似之處是顯而易見(jiàn)的。
蘇格拉底對(duì)話體并沒(méi)有持續(xù)很長(zhǎng)時(shí)間,但是卻產(chǎn)生了其他好幾種對(duì)話體,包括源于狂歡民俗的。
梅尼普諷刺體:作為社會(huì)活動(dòng)的文本
一、梅尼普諷刺體的名稱,取自公元前三世紀(jì)加達(dá)拉(Gadara)的哲學(xué)家梅尼普(M é nippe)之名(他的諷刺作品已經(jīng)遺失,但是我們通過(guò)第歐根尼·拉爾修(Dio gè ne La?rce)的作品得知它們的存在)。羅馬人采用這個(gè)術(shù)語(yǔ)命名公元前一世紀(jì)形成的一種言語(yǔ)類型(瓦羅Varro的《梅尼普諷刺》())。這種文體的出現(xiàn)還要更早些;第一個(gè)代表人物可能是安提西斯,他是蘇格拉底的一個(gè)學(xué)生,也是蘇格拉底對(duì)話的作者之一。赫拉克利特(H é raclite)也寫過(guò)梅尼普式作品(據(jù)西塞羅Ci cé ro記載,他曾創(chuàng)造一種類似的言語(yǔ)類型,稱為);瓦羅(Varro)賦予了它明確的形式。其他例子還包括塞內(nèi)加(S é n è que)的,佩特洛尼厄斯(P é trone)的《薩蒂里孔》(),盧坎(Lucain)的諷刺作品,奧維德(Ovid)的《變形記》(),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的《小說(shuō)》(),各種希臘“小說(shuō)”、古典的烏托邦式小說(shuō)和羅馬諷刺作品(賀拉斯Horace)。在梅尼普諷刺體的領(lǐng)域中,逐漸演化出謾罵、獨(dú)語(yǔ)和怪誕的其他下位言語(yǔ)體式。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基督教文學(xué)和拜占庭文學(xué);它存在于各種形式中,幸存于中世紀(jì)、文藝復(fù)興和宗教改革,一直流傳至今(如喬伊斯、卡夫卡和巴代耶Bataille的小說(shuō))。這種狂歡式文體——像普羅修斯(Pro té e)一樣可彎易變,能夠?qū)⒆约郝凉B入到其他文體中——對(duì)歐洲文學(xué)的發(fā)展,特別是小說(shuō)文體的形成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
梅尼普諷刺體既是喜劇的,也是悲劇的,更確切地說(shuō),在同樣的場(chǎng)景下,它像狂歡話語(yǔ)一樣是嚴(yán)肅的;通過(guò)文中語(yǔ)詞的定位,它擾亂了政治和社會(huì)。它使言語(yǔ)突破了歷史的限制,并大大激發(fā)了哲學(xué)和想象力的創(chuàng)造性。巴赫金強(qiáng)調(diào),“排他性”的地位在梅尼普諷刺體中增強(qiáng)了語(yǔ)言的自由度。怪誕幻想(通常是神秘的)和象征主義與可怕的自然主義融合在一起。在妓院、強(qiáng)盜的巢穴、小酒館、露天市場(chǎng)和監(jiān)獄中,在情欲的放縱中,在神圣的禮拜中等等開(kāi)拓發(fā)展。詞語(yǔ)不怕道德譴責(zé),它從預(yù)設(shè)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中解放出來(lái);沒(méi)有高尚與墮落的區(qū)別,但也與之相融相洽。詞語(yǔ)將它們視為自己的專有領(lǐng)地,視為自己的創(chuàng)造之一。為了解決存在的“終極”問(wèn)題,學(xué)術(shù)問(wèn)題被推到一邊:這種話語(yǔ)將解放了的文學(xué)語(yǔ)言指向哲學(xué)的普世主義。它不區(qū)分本體論和宇宙論,而是將他們合并成生活的實(shí)際哲學(xué)。幻想的元素從不出現(xiàn)在史詩(shī)或悲劇作品中,卻在此大行其道(例如,在盧坎的《伊卡羅梅尼普》(),瓦羅的《恩迪彌翁》()和后來(lái)的拉伯雷、斯威夫特和伏爾泰(Voltaire)的作品中,一種從上俯瞰的獨(dú)特視角改變了觀察的角度)。精神的病態(tài)狀態(tài),如瘋狂、人格分裂、妄想癥、夢(mèng)與死等,成了敘事材料(它們影響了莎士比亞和卡爾德隆Calderon的作品)。據(jù)巴赫金研究可知,這些元素與其說(shuō)有主題意義,不如說(shuō)有結(jié)構(gòu)意義;他們毀掉了人的史詩(shī)性和悲劇性的整體,以及人對(duì)身份和因果律的信仰;它們暗示人失去了自己的完整性和單一性,失去了與自己的一致。同時(shí),他們也表現(xiàn)出對(duì)語(yǔ)言和寫作的探索:如在瓦羅的《畢馬爾庫(kù)斯》()中,兩個(gè)馬庫(kù)斯(Marcus)討論能不能用轉(zhuǎn)義辭格寫作。梅尼普諷刺體傾向用令人反感和古怪的語(yǔ)言。這些“不合適”的表述非常獨(dú)特,表現(xiàn)為冷嘲熱諷的直率,對(duì)神圣的褻瀆和對(duì)禮節(jié)規(guī)矩的攻擊。這類話語(yǔ)由強(qiáng)烈的對(duì)比反差組成:貞潔清高的妓女、慷慨大方的強(qiáng)盜、哲人實(shí)際上的自由和他的奴隸地位等等。它運(yùn)用劇烈的變化更迭;高和底、升與降,所有類型的任意結(jié)合。語(yǔ)言似乎癡迷于“雙重性”(語(yǔ)言自身的運(yùn)動(dòng)就是通過(guò)書寫重疊外部)與矛盾對(duì)立邏輯,而不是固定意義的同一邏輯(logic of identity)。這是一種無(wú)所不包的文體類型,放在一起猶如一條引文之路。它包括所有文體類型(短篇故事、書信、演講、散韻文結(jié)合體),這些文體類型的結(jié)構(gòu)特點(diǎn)指出了作者與他本人文本和其他文本的距離。這種話語(yǔ)的多文體性和多音調(diào)性以及本身用詞的對(duì)話性都解釋了為什么古典主義或其他任何專制社會(huì)中使用梅尼普諷刺體小說(shuō)進(jìn)行表達(dá)。
總的來(lái)說(shuō),這種寫作是對(duì)身體、夢(mèng)境和語(yǔ)言的探索,移植到當(dāng)下主題就是:這是一種當(dāng)時(shí)的政治性新聞學(xué)。這種話語(yǔ)外化了當(dāng)時(shí)的政治和意識(shí)形態(tài)沖突。詞語(yǔ)的對(duì)話性實(shí)用哲學(xué)與唯心主義、宗教形而上學(xué)的戰(zhàn)爭(zhēng)(也是與史詩(shī)的戰(zhàn)爭(zhēng))。它形成了一股與神學(xué)(與法規(guī))進(jìn)行對(duì)抗的社會(huì)和政治思潮。
二、因此,梅尼普諷刺體的結(jié)構(gòu)是矛盾的,核心是西方文學(xué)的兩種趨勢(shì):一是如表演一樣通過(guò)語(yǔ)言再現(xiàn)事實(shí);一是作為一種符號(hào)的相關(guān)系統(tǒng)探索語(yǔ)言。梅尼普傳統(tǒng)中的語(yǔ)言既是對(duì)外在空間的再現(xiàn),同時(shí)也是“生產(chǎn)自我空間的一種實(shí)踐”。這種雙值性的文體首先表現(xiàn)出(相對(duì)于生活,這是一種次級(jí)活動(dòng);在這一活動(dòng)中,人描寫自己并觀看自己表演,最終創(chuàng)造出“人物”與“角色”);其次是精神世界(一種直接發(fā)生的活動(dòng),特征是圖像,姿勢(shì)和言行。通過(guò)這些,人們將自己的有限寄寓在客觀中。第二個(gè)方面將梅尼普式結(jié)構(gòu)與夢(mèng)境和象形文字的結(jié)構(gòu)聯(lián)系起來(lái),或者可能和阿爾托(Artaud)構(gòu)想的“殘酷戲劇”[12]聯(lián)系起來(lái)。如同殘酷戲劇,梅尼普諷刺體“與個(gè)人生活不同,與彰顯個(gè)性的個(gè)人生活方面不同,而是等同于一種清除了人類的個(gè)人特質(zhì)的自由生活。人在這種生活中,只不過(guò)是一種映像。”如同殘酷戲劇,文體并不在于凈化(catharcis),而是殘酷的慶典,但也是一種政治行為。它不傳播任何確定的信息,除了表明自己是變化中的永恒歡樂(lè),并在當(dāng)下行為中精疲力盡。它產(chǎn)生在蘇格拉底、柏拉圖和詭辯派之后,所屬的年代是一個(gè)思想不再是實(shí)踐的年代。(它被認(rèn)為是一種表現(xiàn)的事實(shí)說(shuō)明,()的分離已經(jīng)發(fā)生了。)同樣的,文學(xué)成為“思想”,變得意識(shí)到自己是符號(hào)。疏遠(yuǎn)自然與社會(huì)的人,變得疏遠(yuǎn)自身,在梅尼普式寫作的雙值性中發(fā)現(xiàn)“內(nèi)在”自我,并“具象化”這種發(fā)現(xiàn)。諸如此類的標(biāo)志是現(xiàn)實(shí)主義表現(xiàn)形式的先驅(qū)者。但是,梅尼普諷刺體話語(yǔ)忽視神學(xué)原則下的獨(dú)白性(或者說(shuō)是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的人-神原則;如果有這些原則,它在表現(xiàn)功能方面會(huì)被強(qiáng)化。它所遭受到的“專制統(tǒng)治”是文本的控制(而不是話語(yǔ)作為先于它存在的世界的反映),或者更是它自己的結(jié)構(gòu),通過(guò)自身來(lái)建構(gòu)和解讀自己。它將自己建構(gòu)成一種(),始終保持著。梅尼普諷刺體話語(yǔ)將這種雙值性傳遞給了小說(shuō),首先是復(fù)調(diào)小說(shuō),這種小說(shuō)既不知道法規(guī),也不知道等級(jí)制度,因?yàn)樗怯商幱趯?duì)話關(guān)系中的眾多語(yǔ)言要素構(gòu)成的。梅尼普諷刺體話語(yǔ)不同部分關(guān)聯(lián)原則當(dāng)然是(相似、非獨(dú)立,因此是“現(xiàn)實(shí)的”),但也可以是鄰近的(類推、并列,因此是“修辭的”——不是克羅齊的美化修辭,而是通過(guò)語(yǔ)言進(jìn)行及存在于語(yǔ)言中的雄辯)。梅尼普式的雙值性由多個(gè)兩兩相對(duì)的空間[13]交流組成:場(chǎng)景空間與文字空間、語(yǔ)言的表現(xiàn)空間與語(yǔ)言內(nèi)部的實(shí)踐空間、系統(tǒng)與短語(yǔ)、隱喻與轉(zhuǎn)喻。這種雙值性傳遞給了小說(shuō)。
換言之,梅尼普諷刺體(還有狂歡話語(yǔ))的對(duì)話性被理解為一種關(guān)于關(guān)系和類推法的邏輯,而不是一種關(guān)于實(shí)體與推理的邏輯,這是對(duì)亞里士多德式邏輯的反抗與抵制。梅尼普式對(duì)話主義正是從形式邏輯的內(nèi)部,在與之接觸的同時(shí)反駁它,并指向另一種思維方式。確實(shí),梅尼普諷刺體話語(yǔ)正是在反對(duì)亞里士多德哲學(xué)的過(guò)程中發(fā)展起來(lái)的,而且復(fù)調(diào)小說(shuō)的作者似乎都反對(duì)建立在形式邏輯基礎(chǔ)上的正統(tǒng)思維的結(jié)構(gòu)。
顛覆性小說(shuō)
一、在中世紀(jì),梅尼普思潮被宗教的權(quán)威所控制;在資產(chǎn)階級(jí)時(shí)期,它又受制于個(gè)人主義與物質(zhì)主義的專制。只有現(xiàn)代性——擺脫了“神”的時(shí)候——才釋放出小說(shuō)的梅尼普力量。
如果說(shuō)現(xiàn)代社會(huì)(資本主義社會(huì))不僅接受了小說(shuō),而且宣稱在小說(shuō)中認(rèn)識(shí)到了自我[14],這種小說(shuō)指的獨(dú)白式敘事的范疇,就是通常所說(shuō)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范疇,刪減掉了所有狂歡和梅尼普的元素。它的結(jié)構(gòu)是在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形成的。相反,梅尼普諷刺體和對(duì)話小說(shuō),拒絕使用敘事與史詩(shī)手法,就只有忍辱偷生,被稱為是不可讀的、邊緣化的、被嘲弄的。在現(xiàn)代性小說(shuō)中,這種小說(shuō)遭遇了與狂歡話語(yǔ)在中世紀(jì)被教會(huì)拒之門外一樣的命運(yùn)。
小說(shuō),特別是現(xiàn)代的復(fù)調(diào)小說(shuō),吸收梅尼普諷刺體元素,表現(xiàn)了歐洲的思想,努力突破由因果關(guān)系確定的同一實(shí)體的思維框架,走向另一種通過(guò)對(duì)話前行的思維模式(一種關(guān)于距離、關(guān)系、類推、非排他性和超限對(duì)立的邏輯)。因此,小說(shuō)被認(rèn)為是一種次級(jí)類型(新古典主義及其他類似主義)或是具有破壞性的(我所想到的是幾個(gè)世紀(jì)以來(lái)復(fù)調(diào)小說(shuō)的最主要作家——拉伯雷、斯威夫特、洛特雷阿蒙、卡夫卡和巴代耶——那些過(guò)去一直是并且仍然是堅(jiān)持處于正統(tǒng)文化邊緣的人),也就不足為奇了。詞語(yǔ)和二十世紀(jì)小說(shuō)的敘事結(jié)構(gòu)非常清楚地表現(xiàn)了歐洲思想如何違抗自身構(gòu)成。身份、物質(zhì)、因果和定義被推翻了,別的東西被采納了:類推、關(guān)系、對(duì)立,因此也有了對(duì)話性和梅尼普式雙值性[15]。
這份由巴赫金開(kāi)始著手整理的全部歷史名冊(cè)讓我們覺(jué)得像是博物館的陳列品或檔案管理員的工作。但是盡管如此,它仍然根植于我們的現(xiàn)時(shí)思考中。如今被書寫的所有東西不是顯示出解讀和重寫歷史的可能性就是顯示出不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在新一代的所宣稱的那種文學(xué)作品中十分明顯,這些作品被精心制作成或。馬拉美是第一批理解小說(shuō)的特點(diǎn)的先驅(qū)者之一(我們必須強(qiáng)調(diào),巴赫金的“名詞”具有在歷史中定位某種寫作類型的優(yōu)點(diǎn))他曾說(shuō):文學(xué)“向來(lái)只是先前創(chuàng)造的東西或接近本源的東西的靈光一現(xiàn)”。
二、我現(xiàn)在提出敘事意義有兩種組織類型,基礎(chǔ)是兩種對(duì)話范疇:(1)主體(S)?受話者(D),(2)闡述主體?言說(shuō)主體。
第一種類型暗含了一種對(duì)話關(guān)系,但第二種卻是預(yù)設(shè)了這種對(duì)話形式中的模式關(guān)系。第一種決定文體類型(史詩(shī)、小說(shuō)),第二種決定文體變體。
在小說(shuō)的復(fù)調(diào)結(jié)構(gòu)中,第一種對(duì)話類型(S?D)在書寫文本中完成自身;呈現(xiàn)自我的方式是對(duì)這一話語(yǔ)的永恒挑戰(zhàn)。此時(shí),作者的對(duì)話者是作者自己,但卻是作為另一文本的讀者。寫者即為讀者。一旦他的對(duì)話者是文本,他自己就只是一個(gè)文本重讀自身,就像重寫自身。因此,只有當(dāng)一個(gè)文本相對(duì)于另一個(gè)文本建構(gòu)自身,形成雙值性,對(duì)話結(jié)構(gòu)才會(huì)出現(xiàn)。
另一方面,在史詩(shī)話語(yǔ)中,D是一個(gè)超文本的完全統(tǒng)一體(神或群體),把對(duì)話性相對(duì)化乃至排除,把它約化成獨(dú)白。鑒于此,就能夠很輕松地理解,為什么不僅僅是十九世紀(jì)的所謂經(jīng)典小說(shuō),而且還有具有任何意識(shí)形態(tài)主題的任何小說(shuō)都傾向于史詩(shī)敘事,從而造成了對(duì)真正小說(shuō)結(jié)構(gòu)的背離(這就是為什么托爾斯泰的獨(dú)白寫作是史詩(shī)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對(duì)話寫作就是小說(shuō)的)。
在第二種模式的框架內(nèi),能夠發(fā)現(xiàn)一些可能性:
a.闡述(é non cé)主體(Se)與零度闡述主體(Sa)一致。可以由“他 /她”(非個(gè)性化名字)或由專有名詞指稱。這是敘事產(chǎn)生初期最簡(jiǎn)單的手法。
b.闡述主體(Se)與言說(shuō)主體(Sa)一致。這就產(chǎn)生了第一人稱敘事:“我”。
c.闡述主體(Se)與受話者(D)一致。這就產(chǎn)生了第二人稱敘事:“你”。例如《罪與罰》()中拉斯柯?tīng)柲峥品颍≧askolnikov)的客體指向詞。米歇爾·布托爾(Michel Butor)在《變化》()中不斷地探尋這種寫作手法。
d.闡述主體(Se)同時(shí)與言說(shuō)主體(Sa)和受話者(D)一致。如此一來(lái),這個(gè)小說(shuō)就變成了對(duì)寫作的質(zhì)問(wèn),展現(xiàn)出對(duì)話結(jié)構(gòu)的空間。同時(shí),文本就成了對(duì)外在文本集合的閱讀(引用與評(píng)注),因此就形成了雙值性。通過(guò)運(yùn)用人稱代詞和匿名提問(wèn),菲利普·索萊爾斯(Philippe Sollers)的《戲劇》()中對(duì)人稱代詞及引用的使用,便是此種情況的一例。
從而,對(duì)巴赫金的解讀呈現(xiàn)出一種范式,見(jiàn)表1:

表1
最后,我想強(qiáng)調(diào)巴赫金思想的重要性(關(guān)于詞語(yǔ)地位、對(duì)話與雙值性),以及由此而展開(kāi)的新視角的重要性。
通過(guò)將詞語(yǔ)的地位(statut du mot)確立為文本的,巴赫金超越了句子和辭格,從更深的層次討論結(jié)構(gòu)。()觀念給作為原子集合的文本形象增加了一個(gè)緯度,即文本的關(guān)系維度。其中,詞語(yǔ)的功能就像是量子單位。那么,詩(shī)性語(yǔ)言模式的構(gòu)成問(wèn)題就不僅只是線性或表層的問(wèn)題,而是和——集合論和新數(shù)學(xué)為之提供了形式。敘事結(jié)構(gòu)的現(xiàn)代研究使敘事結(jié)構(gòu)能夠完善地描述功能(主要的或輔助的)和標(biāo)記(就其本身而言或作為信息)[16]。按照特定邏輯或修辭范式就能夠描述出敘事的詳細(xì)步驟。這些研究的價(jià)值當(dāng)然無(wú)可置疑;但是我們也可以追問(wèn),在這一類研究里,、將敘事層層劃分而異質(zhì)于敘事本身的“超語(yǔ)言”是否地位過(guò)重;而巴赫金的原始方法,即將語(yǔ)詞及其在對(duì)話中的無(wú)限可能置于中心,是否更為簡(jiǎn)單明了。
對(duì)話原則的理念,得益于黑格爾甚多。但千萬(wàn)不能與黑格爾的辯證法相混淆。黑格爾的辯證法建立在三元組之上,充滿爭(zhēng)辯與投射(超越的行動(dòng)),并沒(méi)有超越建立在物質(zhì)與因果關(guān)系上的亞里士多德的傳統(tǒng)思想。對(duì)話原則在關(guān)系理念上吸收它們,從而取代這些觀念。它并不奮力追求超越,而是追求和諧,但是始終把決裂(對(duì)立和類推)的思想暗指為一種轉(zhuǎn)變的形式。
術(shù)語(yǔ)“雙值性”完全可以適用于歐洲文學(xué)當(dāng)下這段過(guò)渡時(shí)期——是一種“雙重實(shí)際經(jīng)驗(yàn)(現(xiàn)實(shí)主義和史詩(shī))”與“實(shí)際經(jīng)驗(yàn)”本身(語(yǔ)言探索和梅尼普諷刺)的共存(雙值性)的時(shí)期。日后,文學(xué)所具有的思維方式也許與繪畫的思維方式相似:通過(guò)形式傳達(dá)本質(zhì),將(文學(xué))空間構(gòu)圖作為(文學(xué))思想的揭示手段而非借助所謂“寫實(shí)”。這就需要通過(guò)語(yǔ)言研究小說(shuō)的空間及其變化,從而在語(yǔ)言和空間之間建立起緊密的聯(lián)系,迫使我們將語(yǔ)言和空間作為思維方式進(jìn)行分析。通過(guò)分析表演場(chǎng)景(現(xiàn)實(shí)性的再現(xiàn))的雙值性和實(shí)際經(jīng)驗(yàn)(修辭)的雙值性,我們可能注意到他們之間產(chǎn)生斷裂(或連接)的那條線。可以把這條線看成是一個(gè)運(yùn)動(dòng)的圖像,(在這個(gè)運(yùn)動(dòng)中,)我們的文化抽離出自身,從而超越自身。
對(duì)話兩端間的路徑徹底消除了我們哲學(xué)領(lǐng)域中的因果、目的等問(wèn)題,并欲將對(duì)話原則置于比小說(shuō)更廣闊的思維空間。對(duì)話原則超越二元主義,可能會(huì)成為我們這一時(shí)代智識(shí)結(jié)構(gòu)的基礎(chǔ)。小說(shuō)及其他雙值文學(xué)結(jié)構(gòu)的優(yōu)勢(shì),(狂歡)群體活動(dòng)對(duì)年輕人的吸引,量子交換,對(duì)中國(guó)哲學(xué)的關(guān)聯(lián)象征的興趣……僅以這幾個(gè)當(dāng)代思想的顯著因子為例,它們都強(qiáng)化了這一假說(shuō)。
1966年
注 釋
*本論文的理論起點(diǎn)源于米哈伊爾·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兩本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詩(shī)學(xué)問(wèn)題》(,Moscou,1963) 以及 《拉伯雷的著作》(Moscou,1965)。巴赫金的研究明顯受三十年代語(yǔ)言文學(xué)領(lǐng)域的一些蘇聯(lián)理論家(Voloshinov,Medvedev)的影響。他目前正在從事一本有關(guān)話語(yǔ)類別新書的寫作。
①“語(yǔ)言是一種實(shí)踐的、既為別人存在因而也為我自身而存在的、現(xiàn)實(shí)的意識(shí)……”(——《德意志意識(shí)形態(tài)》(),K·馬克思(K.Marx)、F·恩格斯(F.Engels)Ed.Sociales,1961,p.79)
②從語(yǔ)詞的地位出發(fā),巴赫金正在撰寫一部關(guān)于“話語(yǔ)的種類”的著作(1965年8月)。巴赫金的見(jiàn)解有與索緒爾(“Anagrammes”,雜志,1964年2月)形成交集的部分,也提供了文學(xué)文本分析的新方法。我們?cè)诖酥唤榻B其中的一部分。
③“實(shí)際上,結(jié)構(gòu)語(yǔ)義學(xué)家提及文本的語(yǔ)言學(xué)基礎(chǔ)時(shí)指出,一節(jié)擴(kuò)展開(kāi)的段落可被視為等同于一種語(yǔ)法上更為簡(jiǎn)單的交際信息單位,并將稱為“自然語(yǔ)言運(yùn)作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A.J.Greimas,p.72)。正是“”這一理論原則允許我研究文體結(jié)構(gòu)中語(yǔ)言內(nèi)在結(jié)構(gòu)的外化(擴(kuò)展)。
⑧似乎那個(gè)被一直稱為“內(nèi)心獨(dú)白”的東西就是最強(qiáng)大的方式。通過(guò)這種方式,一個(gè)完整的文明能夠?qū)⒆陨順?gòu)想成一個(gè)共同體,是一種有組織的混亂,最后就是一種超然。但是,這種“獨(dú)白”可能只存在于那些假裝要重現(xiàn)“語(yǔ)流”的所謂的物理現(xiàn)實(shí)的文本中。西方人的“內(nèi)心”狀況是一種這樣有限的文學(xué)感受(懺悔的形式,持續(xù)的心理演說(shuō),自動(dòng)書寫)。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弗洛伊德(Freud)的“哥白尼”變革(發(fā)現(xiàn)了主體內(nèi)部分裂)通過(guò)假設(shè)控制主體本質(zhì)外化的基本原則與語(yǔ)言有關(guān)且在語(yǔ)言之中,從而結(jié)束了對(duì)內(nèi)部的虛構(gòu)。
⑨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將集合論的觀點(diǎn)引入到對(duì)詩(shī)學(xué)語(yǔ)言的思考中僅僅具有隱喻意義。這么做是合情合理的,因?yàn)槲覀兛梢栽趤喞锸慷嗟逻壿嫼驮?shī)學(xué)邏輯的關(guān)系中與可量化和無(wú)窮盡的關(guān)系中進(jìn)行類推比較。
⑩參見(jiàn) Luce Irigaray,Communication linguistique et communication sp é culaire(《語(yǔ)言交流與鏡像交流》),,no.3.
[11]我很想強(qiáng)調(diào)西方個(gè)人主義的模糊角色。它,包括身份概念與實(shí)體論者、亞里士多德的古希臘的因果思想和原子論思想有關(guān)。幾個(gè)世紀(jì)以來(lái),它強(qiáng)化了西方文化中激進(jìn)的、科學(xué)的或理論的方面。另一方面,因?yàn)樗慕⒒A(chǔ)是“自我”與“世界”的差異原則,所以,引起了對(duì)這兩個(gè)概念之間的中介物的尋找,或者是對(duì)各自層次劃分的搜尋,從而使一種相關(guān)邏輯能夠建立在形式邏輯的要素之上。
[12]Th é atre de la Cruau ét,殘酷戲劇(或稱殘酷劇場(chǎng))是法國(guó)戲劇家安東尼·阿爾托在其著作《劇場(chǎng)及其復(fù)像》中提出的一種超現(xiàn)實(shí)主義戲劇形式。——譯者
[13]巴赫金思想中也許是這種場(chǎng)景,當(dāng)他寫“小說(shuō)的語(yǔ)言既不停留在表面,也不存在于線性序列。而是各種表相交叉的系統(tǒng)。作者就像一個(gè)造物主一樣創(chuàng)造與小說(shuō)有關(guān)的所有事,并不能停留在任何語(yǔ)言表面上。相反,他駐扎在由各種表相相交所形成的控制中心里。而不同表面與作者中心的距離各各不同。(“”,,8(1965)。實(shí)際上,作者只不過(guò)是這些中心的連接而已。給他確定唯一的中心,就會(huì)將他強(qiáng)制于一個(gè)獨(dú)白性的、神學(xué)上的位置。
[14]所有的小說(shuō)理論家都知道這個(gè)觀點(diǎn):A.Thibaudet,R é flexions sur le roman,1938;Koskimies“,Th é orie des Romans”,,I,ser.B,t.ⅩⅩⅩⅤ,1935;G.Lukacs,(Ed.fr.,1963)等。韋恩·布斯(Wayne Booth)的《小說(shuō)修辭學(xué)》()(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接近“作為對(duì)話的小說(shuō)”的觀點(diǎn)。他的“可靠性敘述者”與“不可靠性敘述者”接近巴赫金的小說(shuō)對(duì)話理論,但是他沒(méi)有建立小說(shuō)“亂真”與語(yǔ)言符號(hào)之間的關(guān)系。
[15]在現(xiàn)代物理學(xué)和中國(guó)古代思想中也表現(xiàn)出這種狀況,因?yàn)檫@兩者也同樣反對(duì)亞里士多德哲學(xué),反對(duì)獨(dú)白性,具有對(duì)話性。參見(jiàn)Hayakawa S.I.‘,What is meant by Aristotelian structure in language’,,New York,1959;Chang Tung-sun‘,A Chinese philosopher’s theory of knowledge’,,New York,1959,以及雜志第38號(hào),題為(中國(guó)式邏輯);Joseph Needham,,vol.Ⅱ,Cambridge,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