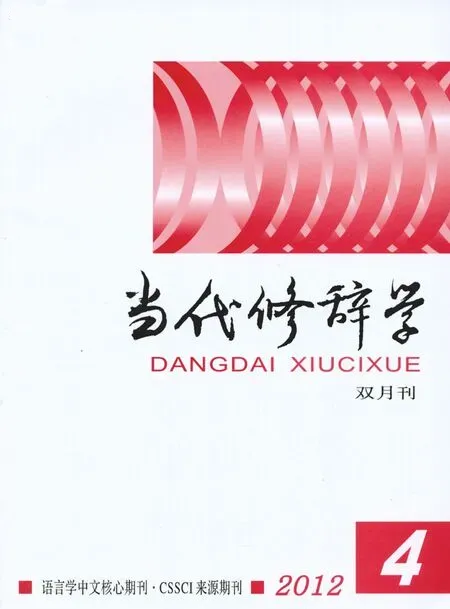非自然會話的語體特征及信息流向*
——一項基于語體學方法的考察
劉承峰
(華東師范大學對外漢語學院,上海200062)
提 要 語體分類有多種維度,以準備性/隨機性、單向性/交互性、在場/非在場、即時/非即時和冗余/非冗余等語體特征為依據,可區分出自然會話和非自然會話。非自然會話基于交際過程中的準備性,必然在信息傳遞方向上具有單向性,傾向于傳遞冗余信息,傳遞過程可以具有空間上的非在場性和時間上的非即時性。在綜合以上五個語體特征基礎上,可把非自然會話中的信息傳遞模式分為五種:信息傳遞對象為聽者、信息傳遞對象為聽者和不在場第三方、信息傳遞對象為在場第三方、信息傳遞對象為不在場第三方和信息傳遞對象為在場第三方和不在場第三方。
一、非自然會話及其語體特征
1. 非自然會話
語體是修辭學的一個重要課題,也是語法學中觀察或者解釋語言現象的一個維度,相關研究經歷了從語體的整體語言表現特點的描述到將語體分解為特征或要素的轉變,如方梅(2007)、張伯江(2007)等就是從語體特征和語體要素角度對相關語體進行的研究。
自然會話中的交際雙方在即時的、非預設的交際現場選擇、調整會話方式并完成交談過程,把沒有經過預先計劃或準備的信息直接傳遞給受話者。例(1)中的對話就是一種伴隨動態交際場景而進行的隨機性會話:
(1)妹妹:哦,好燙!
哥哥:你小心啊,小心燙嘴。
妹妹:我沒事。就像你說的,菜一定要趁熱吃對不對?
哥哥:來。這個才是你的。
妹妹:哥你搞錯了吧?這么多淀粉質,你想把我吃成肥婆啊?不行!
哥哥:不把你養得白白胖胖,別人還以為我虐待你呢。(電視劇《心戰》第23集)
與自然會話相對,存在另一種會話類型——非自然會話,如:
(2)我們剛在車站廣場找了一圈,又到候車廳進行搜索,可是什么人都沒有找到,那么,下面我們要向哪里去搜查?(電視劇《千鈞一發》第16集)
例(2)中,言者是警察,聽者也是與其剛剛共同完成對現場搜查的警察,“在車站廣場找了一圈,又到候車廳進行搜索,可是什么人都沒有找到”都是兩者共同經歷的已知信息,因此,言者所傳遞該信息對聽者來說為不需要的冗余信息。
非自然會話是根據會話本身的準備性等語體特征所得出的一種語體類型,會話行為并非現場直接觸發,而是經過言語控制者充分的設計或者準備,這種設計或準備體現于交際過程、選詞造句中。準備性還體現在信息傳遞的單向性,即言者或言語控制者的目的是為了傳遞自己的信息,而不是為了聽取對方反饋。在這樣的交際過程中,在場的交際雙方實為言語控制者傳遞信息的形式載體,信息通過這一載體向接收終端傳遞,如現場聽者為信息接受者,信息具有在場性、即時性和非冗余性;如信息流向終端不是在場聽者,則具有非現場性、非即時和冗余性。
2. 非自然會話的語體特征
1)準備性/隨機性
準備性指的是言語控制者(或為言者)在會話發生之前對會話方式的預設,即順應語言運用領域,選定針對不同對象、不同環境的語詞、句法格式和敘述邏輯等一系列語言特質要素并綜合運用。隨機性是與準備性二元對立的語體特征(以下各組語體特征的關系同此)。如:
(3)車子剛才拋錨了,一堵兩個小時,現在快十點了。(電視綜藝節目《鑒證實錄》第二集)
例(3)把雙方白天共同經歷的事件“車子剛才拋錨了,一堵兩個小時”加以復述,這對聽者來說完全不必要,其真實動因是這一信息在前面劇情沒有播出,編劇認為需要向觀眾傳遞這一信息從而保持情節上的連貫性,同時為后續情節展開提供鋪墊。因此,準備性體現在編劇作為言語控制者對該會話進行的提前預設。
2)單向性/交互性
在非自然會話中,因為言語控制者對會話方式已經預先設定,這也造成此類會話中信息傳遞流向的單向性,即言者把信息傳遞給聽者或者真正的信息最終端,而不是一種具有交互性的對話行為。如:
(4)老鴇:你這個小沒良心的浪蹄子,這些天你閉門謝客,我就知道你有浪心了。小蹄子那么多人出一千兩的銀子,想見你一面,你都不行,那隆中堂的公子,給你五千兩銀子,替你梳攏你也不肯。這可倒好,你(引注:劉墨林)一文沒有,你(引注:蘇舜卿)就把你囫圇的身子,送給這落第的窮酸了。我跟你拼了。
劉墨林、蘇舜卿:……(電視劇《雍正王朝》第27集)
例(4)中的老鴇在見到劉墨林、蘇舜卿前已經知道兩人要私奔,并對陳述內容早就有所梳理,目的就是捉奸成功時向劉墨林為蘇舜卿贖身要價提供理據支持,其目的并不是為了與對方交流或者聽取對方辯解。
3)非在場性/在場性
在非自然會話中,形式上是會話雙方的即時交流,但在多數情況下信息傳遞的終端并不是在交際現場的聽者,而是場外的其他對象,這就是信息傳遞的非在場性。如:
(5)A:原告委托代理人姓名,工作單位,代理權限。
B:王睿婧,睿婧律師事務所,一般代理。(鄧星亮房屋確權案模擬法庭審判)
(6)王:第三份證據是調查筆錄,第一份筆錄是對證人劉紅亮(原、被告的妹妹)的證言,第二份調查筆錄是對張超(原、被告的叔叔)的證言。
審:傳證人劉紅亮出場。
審:證人你要如實陳述,實事求是,能做偽證,否則要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你清楚了嗎?
劉:清楚。
審:證人,的姓名等情況。
劉:劉紅亮,1964年出生,種田,現住在西坂大隊下坂村,侯特是我哥哥。(鄧星亮房屋確權案模擬法庭審判)
例(5)中的原告委托代理人姓名、工作單位、代理權限和例(6)中的證人姓名都屬于訊問者和犯罪嫌疑人共知的信息,其意圖并不是自己對該信息的再次確認,而更多體現的是一種程序意義,即便于書記員記錄、向旁聽席申明,也可備卷宗的復檢等等,因此,其信息傳遞的對象并不完全是聽者,還包括非在場的對象,即信息傳遞具有非在場性。
4)非即時性/即時性
自然言語行為中交際雙方的當下在場決定了交際的即時性。而非自然會話因為具有信息流向對象的非直接在場性,其信息傳遞在時間上可以具有非即時性。如∶
(7)A:劉真老師跳國標舞的力量感太差了。你別告訴她。
B:是啊,你每次都這么說,即使我不說,她也會看電視的啊。(電視綜藝節目《康熙來了》,20120512)
例句(7)中的言者A是節目主持人,經常調侃“劉真老師”,在該會話中,她也是通過現場陳述,希望向B或者電視觀眾傳遞其對劉真老師的看法,這一信息傳遞達到劉真老師與對話時間肯定存在時間上的間隔。再如:
(8)你也知道,本來我們在美人村很要好的,可現在卻為了爭名奪利而……(電視劇《真假東宮》第3集)
例句(8)中的交際雙方都來自美人村,雙方幼時共同生活成長,其感情親密融洽,這是雙方共知的背景信息,不需言明。因此,言語控制者如編劇的目的是通過在場的監視太監向敵對者傳遞兩人幼時關系親密這一信息,這凸顯了信息傳遞的非即時性。
5)信息量冗余性/非冗余性
非自然會話中的信息傳遞如具有非在場性和非即時性,即真實信息流向不是在場聽者時,為了達到完整傳遞己方信息,要把在場聽者已知或者不需要信息加以重述或轉述,這就會造成一般意義上的信息冗余。如果把信息傳遞對象的考察范圍擴展,細分信息接收者的類型,信息的其他可能流向納入考察視野,那么就不存在所謂的信息冗余。如:
(9)翌日,也就是8月24日,我們攻擊廣州,直逼重慶。父親現在對下一步有什么樣的打算?(電視劇《解放大西南》第3集)
(10)A:父親,我從成都回來了。
B:事情辦得怎么樣?(電視劇《解放大西南》第7集)
例句(9)中的言者為蔣經國,聽者為蔣介石,蔣介石對蔣經國所說的“8月24日,我們攻擊廣州,直逼重慶”當然知曉,之所以通過蔣經國之口對該信息再次說明,其目的就是為了給觀眾提供這一前面劇集沒有展示的背景信息。例句(10)與例句(9)相同。
二、非自然會話中的信息流向
我們搜集了11部電視劇中的78個會話片斷、綜藝節目中的18個會話片斷、其他類別節目中的21個會話片段,這總計117個會話片斷可以根據不同的語體特征分別歸入五種信息傳遞模式。
模式1:信息傳遞對象為聽者
這種信息傳遞模式的語例在我們搜集的117個非自然會話片斷中占據一定比重,共有10段,占比8%。在會話發生前,言者對于即將發生的交際做好了敘述準備,其目的不在于雙方的相互交際,而主要是一種個人信息或者情緒的單向傳達或者宣泄。如,
(11)A:(沉默)你剛才說我不講理,那好,我就讓大家看看到底誰不講理:開始是你說不想吃川菜,我選了粵菜,你又抱怨粵菜不開胃,現在你又說我不懂得體貼你!你倒是說說到底是誰的問題?!
B:……(電視劇《愛情公寓》第8集)
例句(11)是一個爭吵片斷,準備在會話中發生前已經完成,一般體現為會話中的延時停頓,這主要是在即時的爭吵中A沒能站得上風,所以,在經過自己思路或者情緒的整理后對爭吵對象B進行“系統反擊”。
因此,上述信息傳遞模式中,言者是有準備的,其信息流向為在場聽者,信息傳遞在時間上是即時的,其信息從量上來說非冗余。我們可以圖示如下:

圖1 :信息傳遞對象是在場聽者
模式2:信息傳遞對象為在場聽者和不在場的第三方
信息傳遞對象除在場聽者,還可能同時包括不在場第三者,我們搜集的117個片斷中出現15個,占比13%。如:
(12)A:小甜甜減肥好成功哦,希望下次party她可以參加。
B:是啊,我在節目上也為之一驚,那下次見嘍。(電視綜藝節目《康熙來了》,20111102)
例句(12)中的小甜甜不在場,A所傳遞的信息“小甜甜減肥好成功”為A新獲得信息,在告知B的同時,A同時希望通過B向小甜甜傳遞他對小甜甜的正面關注,并把這一體認傳遞給第三方——小甜甜。
不在場的第三方還有可能是事件關涉方。在一些新聞訪談類節目如事件調查、新聞深度播報中,主持人經常對在場嘉賓用經過反復多次運用的準備性語句“本節目將繼續追蹤報道”、“請關注后續追蹤”、“我們將繼續關注事件進展”等語句結束報道。當然,只有少量的節目會有真正的后續報道。此類表達的信息傳遞對象表面看來是虛擬會話中的受話者,即觀眾,但是實際上節目真實意圖是把該息傳遞給被報道事件中的參與者或者利益相關方,并借以傳遞節目的責任感或職業性,在客觀上也許可以達成節目制作方對事件參與者情緒上的安撫或者在行為上的警示。
因此,上述信息傳遞中,言者對其表述方式是有準備的,但是其信息流向為在場和不在場的兩類對象,信息傳遞在時間上也是即時和非即時并存,對在場的聽者來說,其信息量是非冗余的。
這種傳遞模式可以圖示如下:

圖2 :信息傳遞方向是聽者和不在場第三方
模式3:信息傳遞對象為在場的第三方
非自然會話的信息傳遞對象除了非在場第三方之外,還有可能是身處交際現場但沒參與會話的在場的第三方,我們搜集的117個會話片斷中出現30個,占比26%。如:
(13)自從你父親參加顧維鈞的組織,被日本人暗殺之后……(電視劇《狐步諜影》第12集)
例(13)中的言者和聽者都沒有親歷“父親參加顧維鈞的組織,被日本人暗殺”這一事件,但是都掌握該信息,言者之所以把這一信息進行重述,其目的就是把信息傳遞給在交際現場的第三方,即劇中人物唐億民。
在日常的言語交際中,當存在信息不便直接傳遞給真正的在場第三方時,交際一方可以通過向聽者即形式上的受話者傳遞信息,從而即時把該信息傳遞給在場的第三方。如:
(14)A:我這個包花了我5000元,你看怎么樣?(用眼睛余光看旁邊的同事C)
B:還好了。(電視劇《東邊日出西邊雨》第3集)
例(14)中,A所傳遞的信息“買了一個5000元的包”的真正對象不是聽話者同事B,而是處于交際現場的同事C。因為在前面的情節中,同事C曾經嘲笑A不會打扮、服裝廉價等,因此A通過向同事C傳遞其包之貴重這一信息對C進行反擊,以與其達成一種競爭心理的均衡狀態,如對方沒有奢侈品皮包、只有廉價包,而自己擁有名牌包等等。
因此,上述信息傳遞中,言者對其表述方式也是有準備的,但是其信息流向為在場對象,信息傳遞在時間上是即時的,對在場的聽者來說,其信息從量上來說是冗余的。如圖3(圖中虛線箭頭表示非主要交際對象。下同)所示:

圖3 :信息傳遞方向為在場第三方
模式4:信息傳遞對象為不在場的第三方
此類信息傳遞模式的語例在我們搜集的117個片斷中數量最多,共出現42個,占比36%,但是其類型較為復雜,有如下三種情況:
A.事件為言者、聽者雙方共同經歷或共知,已知信息傳遞給非在場的第三方。如:
(15)好不容易等你說跟我結婚,可過了一個禮拜,你又說不結。現在回到香港,我要好好想想怎么向朋友和家人交代了。(電視劇《溏心風暴》第33集)
例(15)中的“好不容易等你說跟我結婚,可過了一個禮拜,你又說不結”都是雙方共同經歷的事件,是雙方的共有信息,通過加以重述告知或者提醒對方自己氣憤的情緒,但其真實目的是通過就信息的復現向觀眾傳遞兩人之間之前的感情起伏,因為這一劇情之前劇集沒有展開,只能通過角色之口來加以展現,并把相關信息傳遞給第三方,即觀眾。
再如,如在體育節目中,尤其是在現場直播的解說中有更多的類似表達,因為體育賽事的觀眾中一部分可能對相關的賽事細節不是非常了解,需要主持人對相關的專業信息加以介紹,以便利用信息上的補足來吸引入門觀眾,從而建立并擴大固定的收視人群,提升節目收視率。如徐盛桓(1984)在討論語言的冗余性的時候,提到如下例句:
(16)A:今天晚上舉行的比賽項目,是男子自由體操、女子自由體操、男子單杠、女子高低杠四項。
B……(轉引自徐盛桓1984)
單杠只有男子項目,高低杠也只有女子項目,因此,例(16)中的“男子單杠、女子高低杠”存在信息冗余。但是,該句中A信息傳遞的對象并非共同主持節目的對話嘉賓B,如果觀看比賽或者聽取播音的觀眾或者聽眾對該項體育項目不熟悉,確實可以通過這種重復限定來達到信息傳遞的準確性和有效性,這也體現這一冗余信息的存在價值。
B.言者親歷事件,聽者沒有親歷但是對相關信息已知,此時的信息傳遞對象也是非在場的第三方。如:
(17)還是那句話,要不是送報紙的幾天沒見到他,也不會這么早就發現他的尸體。接下來,鑒證人員要進一步進行搜證,請大家配合。(綜藝電視節目《鑒證實錄》第三集)
例(17)中,因為“送報紙的幾天沒見到他”從而引起別人注意,并導致最后“發現(他的)尸體”。這一事件對于在場的鑒證人員來說雖然沒有親身經歷,但是作為案件的一個背景信息都已知曉,同樣因為這一事件在電視劇的正常進展中都沒有播放,只能通過“角色重述”來把這一信息傳遞給觀眾。
C.言者經歷,聽者未經歷并對信息未知,信息傳遞給非在場的第三方。如:
(18)我們把古玩店里里外外找了個遍,可就是沒找到啊。(電視節目《第四片甲骨》(25))
例(18)中的言者“我們”即警局人員把古玩店里里外外找了個遍,名叫“二姑娘”的聽者并未參與這一事件,對此信息不知,但是二姑娘對這一信息主觀上完全沒有獲知的意圖;同時,在后續的會話中,這一信息沒有相應的延續或者深究。實際上言者訴說這一信息的目的還是把前面劇集中沒有能夠呈現的內容傳遞給觀眾,其中的二姑娘完全是一個形式上的信息傳遞“媒介”。
因此,上述信息傳遞中,言者對其表述方式是有準備的,但是其信息流向為不在場對象,這也造成信息傳遞在時間上的非即時性,對在場的聽者來說,其信息從量上來說是冗余的。
我們可以圖示如下:

圖4 :信息傳遞方向為非在場第三方
模式5:信息傳遞對象為在場的第三方和不在場的第三方
信息傳遞對象還可能是在場的第三方和不在場的第三方,我們搜集的117個片斷中出現數量為20個,占比18%。如:
(19)我是你大哥,我的江湖經驗告訴我……(電視劇《包青天之七俠五義》第30集)
(20)“什么?帶子出問題了?”(電視劇《美麗背后》第19集)
例(19)中的“我是你大哥”這一關系兄妹雙方是共知的,但是陳述者是把這一信息傳遞給同在現場的第三方即劇中人物展昭,向其明確與聽者的關系,從而希望得到展昭支持其后續的行為的效果;同時,因為對于兩人的關系,之前的情節中沒有說明,也可以把這一信息告知第三方——觀眾。例(20)中,說話者和警察通電話,罪犯丈夫在旁邊,這一句話表面是針對警察的對話,實際上的信息傳遞目的是其丈夫,并間接地把該信息傳遞給第三方——觀眾,因為該角色是第一次出現,從而達到了申明其身份的作用。
此外,電話對話中的非連貫表達也屬此類,如在電話通話中,也經常會有這種信息冗余問題,李萍(2005)曾對相關問題進行過研究。如:
(21)喂喂,爸爸,我是小冬啊!(轉引自李萍2005)
小冬是獨生子,聽到其聲音,其父親應該能判斷其身份,尤其是加上“爸爸”的稱呼之后,其身份聽話者肯定明確,因此,從信息量差分析的角度分析,“我是小冬”是一種冗余話語;但是也有另外一種可能,即小東被綁匪綁架,而又被迫與爸爸通話索要贖金,這時,小東的自我稱呼就不是冗余的,因為這些信息的傳遞對象表面是爸爸,但更重要的是在場的第三者綁匪,因為綁匪要通過這電話聯系確認其身份關系,此外還有可能是在監聽中的警察。
因此,上述信息傳遞中,言者對其表述方式是有準備的,但是其信息流向為在場和不在場兩類對象,信息傳遞在時間上是即時的,對在場的形式聽者來說,其信息從量上來說冗余的。可以圖示如下:

圖5 :信息傳遞對象為在場第三方和非在場第三方
三、結 語
相對于自然的話語,非自然言語行為具有其自身表達以及信息傳遞上的特點。鑒于該類話語中信息傳遞對象的復雜性,非自然會話在信息傳遞模式上與自然會話具有傾向性上的不同,言語控制者通過聽者這一信息傳遞中的一個形式對象,實現了部分信息的成功傳遞。
根據上文的分析,本文考察的117個會話片斷中分屬于不同信息傳遞模式的情況統計如下:

表1 :非自然會話語體特征與信息流向對應
我們假設,一個會話片斷具備的語體特征越多,越接近于典型的非自然會話,如模式4中的會話片斷。事實上,模式4中的會話片斷在我們考察的117個會話片斷中所占比例也最多,為36%。而模式1中的會話片斷具備的語體特征最少,在考察的片斷中所占比例也最小,為8%;其他模式居中,模式2、3和5的會話片斷所占比例接近,分別為13%、26%和18%。
五個語體特征在非自然會話中出現的頻率是不均等的,根據不同信息傳遞類型進行系統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下面的統計:

表2 :五個語體特征在信息傳遞模式中的分布
其中準備性和單向性是每一個信息傳遞模式中必備的特征,我們稱之為“標記特征”;信息冗余則是在傾向上來說具有運用的較大比例,我們稱之為“傾向特征”;不在場和非即時則是可以隱現的特征,我們稱之為“隱現特征”。
本文的分析主要是一種語義傾向定性分析,對于非自然會話傳遞的信息的語言形式特征沒有進行系統分析,對于信息的冗余性也沒有展開,這些問題我們將另文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