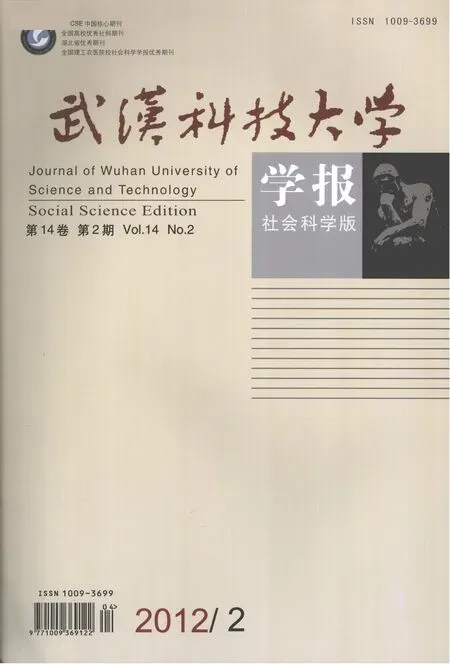法經濟學視野下的鄉村治理規則選擇
馬運全
(1.山東大學 經濟研究院,山東 濟南250100;2.中國人民銀行 濟南分行,山東 濟南250021)
近年來,我國城市化進程日新月異,城市文明不斷向農村地區滲透和傳播,城鄉一體化已成為市場經濟深入發展的必然過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必將推進傳統鄉村社會的分化和變遷,導致鄉村治理模式的重構。在此過程中,傳統性與現代性的碰撞聚焦為國家層面的法律與地方性的民間法的沖突與對抗。因此,研究國家法與民間法在鄉村治理中的選擇性和適用性對于發揮多元法律資源的共同優勢、實現鄉村良性治理具有重要意義。
一、文獻綜述
關于鄉村治理中國家法與民間法的關系問題,存在一元和多元化兩種視角。一元論者主要關注國家法的發展,強調國家法律的唯一性。多元論者主要研究國家法與民間法的共存問題,更為強調民間法在現代鄉村治理中的積極作用。
蘇力認為,當國家法與民間法發生沖突時,不能公式化地強調以國家法來同化民間法,而應當尋求國家法與民間法的妥協與合作[1]。
王亞新等認為,中國的鄉土社會既不完全聽命于國家的正式法律,也不完全認同民間法,民間社會是共同秩序觀念和國家正式體制的結合體,國家法和民間法的關系可以被歸納為“秩序的多元化”[2]。
王肅元等根據國家法與民間法在法律供給與需求方面的內在關系,認為民間法具有帕累托改進的性質,能得到人們普遍的和自覺的認同,有時即使制定法律的數量沒有增加,其制度框架的存在價值原則取向本身也會影響和干擾民間社會秩序的形成[3]。
趙曉力指出,民間法和國家法之間的關系存在三種變化:國家法正式繼承民間法、民間法正式被納入到國家法體系之中以及民間法被國家法“雙重制度化”[4]。
黃宗智認為,在國家法與民間法之間有一個中間狀態,從最初提出訴訟到最后判決之間的調解過程被稱為第三領域,這一領域銜接了國家法與民間法[5]。
趙旭東指出,國家法以及民間法中的村規民約、傳統習慣等在鄉村治理中產生的影響是多方位的[6]。
廖成忠根據法律多元論揭示了我國社會客觀存在的國家法與民間法多元法律格局,考察了鄉村都市化背景下發生的典型糾紛及其解決方式,分析了民間法與國家法的文化背景,提出在法的制定和實施上通過文化整合來處理沖突,建設和諧社會[7]。
唐喜政認為,民間法不僅是鄉土社會的內生秩序,更是鄉土社會法治化進程的重要本土性資源,并提出我國鄉土社會的法治化應善待民間法,給予民間法一定的生存空間,強化民間法的司法介入,發揮民間法的司法功能,重塑民間法的權威,同時,還要推進鄉村治理,為民間法的運行創造良好的人文環境[8]。
司春燕認為,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國家法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但孕育和根植于鄉土社會的民間規范還有很大市場;國家法和民間法存在著對立和互動的關系;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要實現兩者的協調與互動,關鍵在于國家正式制度要為國家法與民間法的良性對接提供互動渠道和對話空間[9]。
于彬等指出,在現代性特征越來越明顯的鄉村社會,作為國家正式法律的“國家法”在維護社會秩序、促進社會和諧、保障新農村建設中已成為不可或缺的力量,但鄉土社會的民間法仍然是鄉土社會中維持秩序的權威力量,國家應建立二者之間均衡互動的調節系統,發揮二者各自的作用,以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10]。
吳杰華從應然與實然的角度,探討了鄉村治理中民間法與國家法的調適與嵌合問題[11]。
趙海怡等從法經濟學的視角,指出民間規則是通過私人自主博弈而實現的最優產權安排,國家立法應有限度地干預,同時,國家法不應介入低交易成本條件下的私人自主博弈,并應避免公共選擇對集體選擇的替代和排擠[12]。
綜合來看,上述研究具有以下特點:①對鄉村治理規則問題的研究集中于法學、社會學領域,運用經濟學理論分析的較少;②大量的研究局限于國家法與民間法的互動關系,較少將二者納入現代鄉村治理的框架中;③傾向性觀點認為民間法是國家法的補充,應利用國家法改造并最終取代相對落后的民間法。
二、傳統鄉村社會治理的基本特點
(一)傳統鄉村社會規則以民間法為基礎
傳統農村是以宗族為載體、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支持、以血緣為紐帶的地緣性集合體。這個集合體的人是在熟人社會里長大的,社會常態的生活是終老是鄉[13]。社群的組織結構以自然經濟為基礎,通過穩定的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在社群內部形成穩定的差序人際關系格局,禮治則作為社會公認的行為規范,經過世代教化,使社群成員形成主動服從于傳統的習慣,并歷經千年而不變,不斷進行著自身的再復制,進而維系著整個社會的穩定有序。鄉村治理的規則是以習慣、民俗、倫理、道德等為表現的民間法,這些規則在鄉民長期生活、勞作、交往和利益沖突中顯現,人為創造或是自然生成,通過文字或口耳相傳相沿成習。對規則的長期教化養成了個人對規則的敬畏之感,外在的規則化成了內在的習慣。民間法作為一種“地方性共識”[14],與之相對應,作為由國家專門機關制定和認可的法律法規等在鄉村的作用和功能卻是有限的。
(二)以宗族為代表的組織是傳統農村治理的重要力量
在鄉村社會中,主要依靠以宗族為代表的社會組織的自治來完成和實現鄉村治理。宗族不僅是一種意識也是一種制度和組織,更是一種經濟組織,其主要依靠兩種手段實現對鄉村的治理,一是依靠手中掌握的相當數量的經濟資源,這些經濟資源不僅可以強化宗族的權力,而且本身就是鄉村公共品供給所需的資源;二是依靠長期以來形成的社會輿論和集體情感。在不流動、具有長遠預期形成的熟人社會里,人們對那些不合作者的強烈負面感情在治理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強烈的負面感情類似涂爾干所講的“集體情感”,即如果有一個人僅僅因為自己的小利而不合作,從而破壞了大家的好事,則每個村民都會憤怒難當,都要前去對其實施懲罰。
(三)村規民約仍然是爭議解決的重要依據
理論上講,國家法在構建法治社會過程中應當起到主導作用,但在傳統的農村地區,村規民約仍然被人們廣泛和長期地運用,甚至部分取代了國家法。在真實的社會場域中,特別是在遠離動力源的廣闊鄉村社會,人們的行為方式和彼此之間的社會關系,并不完全由國家法直接控制,而更多地依賴于各種層次、范圍的“關系網絡”,這也直接造成了普通民眾對國家成文法的冷漠與疏遠。
但是,隨著人口在城鎮相對集中,城市文化、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不斷向農村地區擴散,對農民傳統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造成沖擊甚至改變,塑造了新型的村民人際關系,推進了農村社會結構的變遷,促使鄉村引入新的治理結構。民間法日漸衰微但仍起到巨大作用,國家法大舉進軍但有時仍顯進展緩慢。
三、鄉村社會治理規則選擇的經濟學解讀
當事人之間產生糾紛,究竟選擇何種規則進行解決取決于成本付出和預期的收益。作為理性的經濟人,尤其對那些收入有限的農民而言,在試圖解決糾紛之前,都會對在糾紛解決過程中的“投入”和“產出”進行評估和預測,“私了”還是“官辦”決定于顯性成本和隱性成本的大小。
筆者以微觀經濟學中的無差異曲線為基礎[15],構造了當事人選擇適用民間法和國家法的決策模型,基本假設如下:①將發生糾紛的當事人假定為具有代表性的理性人;②給定當事人初始的配置狀況和既定的收入;③民間法和國家法是兩種可供選擇的商品,且民間法沒有違背法律的強制性規定;④民間法和國家法的價格表現為需要投入的成本;⑤國家法的價格為P1,價格構成包括訴訟費用、律師費、交通費用以及可能的行賄開支等。民間法的價格為P2,價格構成主要包括尋找解決組織耗費的時間、精力、資金等,很大一部分是交易成本。
以民間法的價格不變、國家法的價格下降為例進行分析(見圖1),其中線段MB為當事人初始的預算線。

圖1 國家法價格下降后引起的總效應變化
在國家法價格未變化之前,當事人的預算線為MB,該預算線與無差異曲線U1相切于a點,a點就是當事人效用最大化的一個均衡點。在a點上,當事人對國家法的需求量為OA。現在假定國家法的價格P1下降,使得預算線由MB移到MN,新的預算線MN比另一條代表更高效用水平的無差異曲線U2相切于b點,b點為國家法價格下降后的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點。在b點上,當事人對國家法的需求量變成了OC。比較a、b兩個均衡點,國家法的需求量增加量為AC,這是國家法價格下降以后引起的總效應。以下分兩部分分析:
1.國家法對民間法的替代效應
作一條平行于MN的補償預算線FG,與U1相切于c點,剔除由于國家法價格下降而引起當事人實際收入增加的因素,使得當事人維持原有的收入水平(預算資金)。這時,預算線MB所表示的相對價格P1/P2大于預算線FG所表示的。隨著相對價格P1/P2的變小,當事人為了維持原有的效用水平,必然會沿著U1的a點下滑到c點,增加對國家法的購買而較少對民間法的購買,國家法也就完成了對民間法的替代,替代的數量為AB。
2.國家法價格降低的收入效應
當預算線FG推回MN的時候,當事人的效用最大化的均衡點就由U1上的c點回復到線U2上的b點。相應的需求量的增加量BC必然是收入效應。很顯然,這是由于國家法價格的降低而引起當事人實際收入水平的提高,從而改變了當事人的效用水平。
分析模型背后的法律含義,須要從當事人適用國家法和民間法的價格入手。在產生糾紛的鄉村社會,選擇適用法律的成本很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內容:訴訟的費用、代理律師的費用;尋求法律支持的發現成本;程序是否簡潔;法官能否公平裁決;能否有效執行;隱性的“丟面子”等,簡而言之,就是人們購買司法正義的價格。選擇民間法的成本包括:尋求解決的組織可能發生的費用;裁判的公正性;能否獲得執行等。兩種模式都可歸結為人們人力、物力、財力和精力的消耗。選擇的關鍵是衡量哪種模式帶來的潛在收益大或者耗費的成本低。比如,國家降低訴訟費用、簡化訴訟程序、提高審判的公正性和執行效力,從而導致購買司法正義的價格下降,當事人自然會傾向于選擇國家法來解決糾紛。在司法腐敗嚴重、尋求法律保護的成本高昂的時期,尤其是加上中國傳統的厭訟觀念、參與訴訟帶來的“丟面子”的影響,極大地決定著當事人的決策,此種情形下人們往往尋找民間組織甚至是黑社會來實現自己的利益,這就給民間法帶來了生存的空間。
四、國家法與民間法在鄉村治理中的定位
在鄉村治理中,國家法與民間法共存并發生作用。當購買司法正義的成本較高、當事人傾向于選擇適用民間法的時候,國家法是否應予干預?干預的限度是什么?在城鄉一體化背景下建立現代鄉村治理結構,如何處理二者的關系?這些問題涉及到二者的定位問題。
國家法與民間法共同構成了鄉村治理的規則架構。國家法是由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社會行為規范,系正式制度。民間法基本上可以歸為非正式制度的范疇。二者的本質區別在于,國家法的效力來源于法定的、潛在的國家強制力的保障,是外部國家立法界定和強制實施的產權安排;而民間法的效力是通過私人博弈而實現的,是一種合意的產權安排。鄉村治理規則的適用,實際上是解決如何在社會成員之間進行合理的資源配置,如何在利害關系人之間分配權利和義務,選擇什么樣的解決機制能夠使人們的成本付出最小化,以及如何基本滿足各方對正義的需求。
發生糾紛時,當事人是尋求國家法的外部強力保護還是通過借助民間法的實施組織為中介進行談判,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交易成本的大小,尤其在講究面子的農村地區。科斯指出,如果市場的交易費用為零,不管權力初始安排如何,當事人之間的談判都會導致那些使財富最大化的安排,即市場機制會自動地驅使人們談判,使資源配置實現帕累托最優。在交易費用大于零的世界里,不同的權利界定,會帶來不同效率的資源配置。法律制度對產權的初始安排和重新安排的選擇是重要的[16]。
通過科斯的理論我們可以理解為,如果信息是完全的,交易成本為零,當事人選擇何種規則無關緊要。如果存在交易成本,當事人對交易成本進行衡量后會自動選擇糾紛處理的規則,而法律是可能的選項之一。國家法干預的時機在于當事人自主談判成本過高,以至于無法達成協議,或者當事人的私下談判給社會帶來極大的負效用。
在不違反法律強制性規定的前提下,國家法根本不應介入民間法可以發揮作用的領域,應尊重當事人基于成本和收益的衡量而作出的自主選擇,否則可能造成對資源配置的扭曲。
鄉村治理的現代化進程中,民間法是否應永遠存在?我們認為,依法治國的“法”不應僅限于國家制定的成文法律,還應該包括在那些特定地區、特定群體中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民間法。現代鄉村治理應當是多元的,法治社會的建設應該具有包容性。
主張國家法強行地納入鄉村治理,實際上是將公共選擇的結果強加于特定群體,干涉了特定群體集體選擇形成的規則,是借助于外部強制力附加給當事人的一種產權安排,這未必能起到預期的效果。
當代國家的立法實際上是通過民意代表行使權利制定出在一國領域內普遍適用的規則,是一種公共選擇的結果。然而,公共選擇的結果未必是有利于大多數人的[17],利益集團在立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影響[18]。由國家法確定的強制性的產權安排模式很可能侵犯了一部分人的權益。而民間法是特定地區的特定群體集體選擇的結果,是適用于特定范圍內調整彼此合作與競爭關系的具體產權安排。這種安排得到了群體成員的認可和遵守。如果國家法沒有合適的理由主動去占領、排擠民間法的空間,無異于是一種公共選擇對集體選擇的替代[12]。
根據奧斯特羅姆的自主組織和自主治理理論[19],當人們在同樣的環境中居住了相當長的時間,有了共同的行為準則和互惠的處事模式,他們就擁有了為解決公共池塘資源使用中的困境而建立制度安排的社會資本,通過建立信任和建立社群觀念,從而在擁有了這些社會資本的基礎上來解決新制度供給的問題,并且讓公共池塘資源使用者通過自我激勵去監督人們的活動、實施制裁以保持對規則的遵守。這種治理方式可以隨著組織規模、自然環境、社會系統等因素的變化而隨之變化,關鍵是要與當地的生態環境、人文環境、風俗習慣等相適應。因此,高效率的自主治理未必一定要引入外部的強制性力量。
綜上所述,在鄉村治理中,國家法與民間法各得其所,只要民間法不違背公序良俗,就可以讓其自然存續并發揮作用。
五、鄉村社會良性治理的實現路徑
第一,要以國家法的價值取向為引導。民間法具有地域性、自發性、內控性和人身依附性的特點。有些民間法根植于農村特定的土壤,主要依靠主體的心理認同而非外部強制力實施,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具有強烈的身份依附性。這些特點與建設統一、平等的法治建設目標相抵觸,長期來看不利于整個社會秩序的形成和維護。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加快,日益變化的鄉村社會對規則的強烈需求也不是長期積累沉淀的民間法所能承擔的。因此,在兩者的理性互動模式中應當以國家法為最終價值取向。
第二,大幅降低當事人適用法律的成本。在當前農村治理中,大量的國家法難以通行,難以進入基層并成為真正的規則。如果發揮國家法在鄉村治理中的主導作用,就必須運用市場的手段降低法律成本,吸引當事人選擇適用國家法。為降低法律成本,就需要減少各種直接的、間接的法律開支,降低適用成本。因為較高的法律價格和制定效率的低下就會使當事人減少購買司法正義的消費量,轉而選擇替代商品即民間法。例如,國家可以降低訴訟的費用、放寬簡易程序的條件、縮短案件審理的期限、增加法律援助的力量、提高案件執行力度等措施降低當事人適用法律的成本。
第三,包容性國家法應注重對民間法的吸收。現代法治是以國家制定法為中心,但社會中的習慣、道德、風俗等也是社會秩序和制度的組成部分。任何正式制度的設計和安排,都不能不考慮這些非正式的制度,如果沒有內生于社會生活的自發秩序,沒有非正式制度的支撐和配合,正式制度也就缺乏堅實的基礎,難以形成合理的、得到普遍和長期認可的正當秩序。如果完全消除民間法,壟斷的鄉村治理機制很可能割裂了與優良傳統的聯系,將帶來巨大的社會成本。吸收民間法優點的過程,就是降低價格的過程,能夠真正獲得人們的信任。尋求正義的成本下降,人們的效用水平提高,有助于良性治理的實現。
第四,當民間法違反國家法的強制性規定時,國家法應當有限度地進行干預。以村規民約為例,村規民約或者村民會議的決定,雖然是村民集體意志的體現,但是受歷史的、文化的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封建傳統思想仍然影響著許多農民,崇尚男尊女卑、漠視婦女權利的情況仍然存在。尤其是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一些地方出現了多數村民集體排斥處于弱勢地位婦女的現象,違法剝奪婦女土地承包權和相關財產權益。對于這種違反法律規定和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行為,需要法律強化糾錯機制,消除民間法的不利影響。如修改后的《村委會自治法》規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規民約以及村民會議或者是村民代表會議的決定,侵犯村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合法財產權利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請人民法院予以撤銷”。
[1] 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61.
[2] 王亞新,梁治平.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3] 王肅元,馮玉軍.國家制定法與民間法的供求分析[J].甘肅社會科學,1999(2):53-54.
[4] 趙曉力.中國近代農村土地交易中的契約、習慣與國家法[J].北大法律評論,1999(1).
[5] 黃宗智.法典、習俗與司法實踐:清代與民國的比較[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6] 趙旭東.權力與公正——鄉土社會的糾紛解決與權威多元[M].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7] 廖成忠.中國鄉村都市化中的民間法與國家法沖突[J].重慶社會科學,2006(2):94-98.
[8] 唐喜政.鄉村治理視野中民間法的完善及策略[J].廣西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0(7):40-42.
[9] 司春燕.城鄉一體化進程中國家法與民間法的沖突與協調[J].前沿,2010(7):74-78.
[10]于彬,王蕊蕊.鄉土社會中國家法與民間法的博弈[J].前沿,2010(5)(下):3-4.
[11]吳杰華.應然與實然:鄉村治理中民間法與國家法的調適與嵌合[J].法制與經濟,2009(6):38-39.
[12]趙海怡,錢錦宇.法經濟學視角下國家法的限度[J].山東大學學報,2010(1):1-11.
[13]梁治平.習慣法和國家法 [M]//清代習慣法:社會和國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
[14]賀雪峰.鄉村的前途:新農村建設與中國道路[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7:87.
[15]高鴻業.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97-100.
[16]Ronald H 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Law and Economics,1960,3(10).
[17]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場與國家:80年代的政治經濟學[M].平新喬,莫扶民,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9:124.
[18]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M].陳郁,郭宇峰,李崇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87.
[19]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集體行動制度的演進[M].余遜達,陳旭東,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296-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