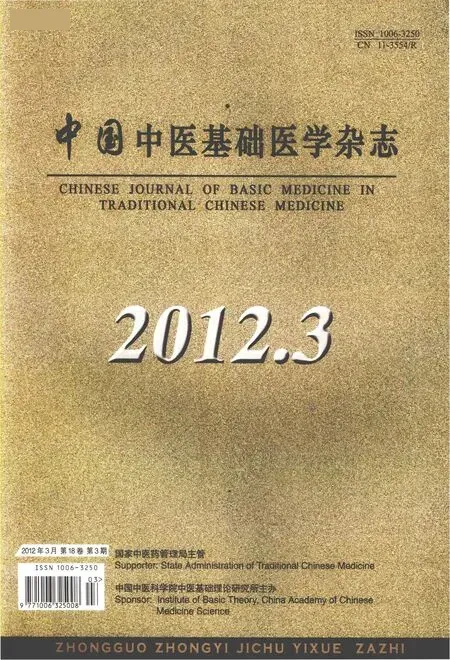《內經》“逆順”發微
王鴻度
(瀘州醫學院中西醫結合學院,四川 瀘州 646000)
在古老的醫籍《黃帝內經》的許多篇目中,“逆順”反復出現,甚至或直接用作篇名,如《靈樞·逆順》、《靈樞·逆順肥瘦》等。據筆者粗略統計,《內經》中“逆順”并提凡32處之多,其中《靈樞》有18篇27處,《素問》有3篇5處,至于經文中分別提及的“順”或“逆”者,則不勝枚舉。它主要用于補充闡述“天人相合”規律,解釋人體生理機能、病理轉歸、病勢吉兇、臨床治療策略等,所以“逆順”在中醫學理論體系里是一對重要的范疇。
筆者進一步探討發現,“逆順”首先是一對哲學范疇,它同“陰陽”、“五行”等學說一樣,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理論成果。因此,揭示和認識“逆順”的哲學意義、考證其對中醫學的移植滲透過程以及所產生的影響,將有助于全面理解中醫學術體系形成問題。
1 “逆順”的哲學淵藪
1.1 來源
筆者查閱先秦以前的重要哲學古籍,如《易經》、《道德經》、《莊子》等并無“逆順”共用之例;雖或有單個“逆”或“順”的概念,所表達的也只限其基本字義。“逆順”作為一個哲學范疇,似乎最早見于“黃老學派”的哲學思想。“黃老學派”以道家思想為中心,融入名法之要,又兼采陰陽、儒、墨諸家,后人稱之為“新道家”[1]。關于“逆順”的觀點,是該學派哲學上的重要貢獻之一。
由于《內經》成書也恰在“黃老學派”流行時期,故黃老哲學乃至“逆順”的觀點不可能不在《內經》中有所反映。但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東漢時其傳世經典《黃帝書》數種已亡佚,以致其學術菁華湮沒,使后人一直難窺堂奧。
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帛書《經法》、《十大經》、《稱》、《道原》等首尾一貫,自成體系。據考證,正是秦漢流行的《黃帝書》的重要部分,故史學界命名為《黃老帛書》[1]。這些資料補足了戰國末至秦漢哲學史上這一重要學派的可靠史料,也為研究“逆順”范疇提供了依據。
1.2 哲學底蘊
《黃老帛書》基于道家宇宙觀,把“道”看作天地萬物的總規律。“道”的根本性質是“虛同為一,恒一而止”(《道原》)。這就是說,眾多事物中有根本之道,即“一”,萬物皆受一個總規律支配。“道”的運動具有客觀必然性,《十大經·本伐》說:“道之行也,繇(由)不得已。”
《經法·四度》載:“極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李(理)也”,即天道人事共同的最根本規律是“極而反,盛而衰”。但是,人類社會規律較自然規律表現得更為特殊、復雜。“或以死,或以生,或以敗,或以成,禍福同道,莫知其所從生”;“絕而復屬,亡而復存,孰知其神?死而復生,以禍為福,孰知其極”?如此紛雜的“人事”就生出一個“逆順”的道理,“順則生,理則成,逆則死”,否則就會“亂生國亡”(《經法·論約》)。所以認為“人之理”又多出“審知順逆”問題,這是“天道”和“人道”的重要區別。
“逆順”的提出,即著眼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規律的差異,“審知順逆”就是認識和研究人類社會的客觀規律,從方法論講也即是“執道”、“循理”、“審時”、“守度”的過程。
所謂“執道”,即明于宇宙普遍規律而無私欲。如《經法·道法》說:“故唯執道者,能上明于天之反,而中達君臣之半(畔),富密察于萬物之所終始,而弗為主,故能至素至精,浩彌無刑(形),然后可以為天下正。”“執道”要從根本上著眼,故《經法·四度》說:“執道循理,必從本始。”“執道”關鍵一環,在審定形名,“刑(形)名已定,逆順有立(位),死生有分,存亡興壞有處,然后參之于天地之恒道,乃定禍福死生存亡興壞之所在。是故萬舉不失理,論天下而無遺策”(《經法·論約》)。
所謂“循理”,《經法·論約》說:“物各合于道者,胃(謂)之理;理之所在,胃(謂)之順,物有不合于道者,胃 (謂)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胃(謂)之逆。順逆各自命也,則存亡興壞可知。”理是道的具體化,“順逆同道而異理,審知順逆,是胃(謂)道紀”。也就是要求根據“道”來具體研究和處理這些復雜的順逆關系。
所謂“審時”,即善于掌握和利用時機。帛書一再強調“圣人不巧,時反是守”(《十大經·觀》)。但其時機客觀地存在于事物的變化之中,“其未來電,無之,其已來,如之”。“明明至微,時反以為幾”。“幾”指事物在發展中轉折的契機。“天道”獨立地不斷地運行,人們在“天道環周”面前“靜作失時”,反而會處于被動地位。
所謂“守度”,即注重事物變化的數量關系及其一定的限度。“度”也是一定的數量標準。“八度者,用之稽也”,即規、矩、繩直、水平、尺寸、權衡、斗石等,都為確立統一的“度”。推而廣之,自然事物和社會生活的各方面都有其特定的“度”,如果“變恒過度”、“過極失當”,就會促使事物走向反面,造成嚴重后果。
2 “逆順”在中醫學中的地位及其應用
正如上述,由于《黃帝書》佚失,黃老哲學在東漢就不再傳世。所幸《黃老帛書》的出土,使我們有機會得窺全豹,了解黃老哲學中“逆順”精髓,從而重新審視其移植滲透于中醫理論的過程,評價其所起的作用和影響。
2.1 基本地位及過程
“逆順”這對特殊范疇,是黃老學派對“人道”特殊本質的概括和反映,也是戰國、漢初時期哲學思想的精華之一。這種具有時代特征的理論思維成果,理所當然地被移植滲透進同時期的《黃帝內經》中,并在《內經》反復強調其重要性:“明知逆順,正行無問……不知是者,不足以言診,足以亂經。”《靈樞·師傳》更明確說:“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陽脈論氣之逆順也,百姓我民,皆欲順其志也。”
醫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人。把“逆順”移植于醫學理論之中,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因為與自然規律相比,人體諸現象不僅受天地陰陽之道支配,而且還有逆順問題。正如《靈樞·逆順》云:“氣之逆順者,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脈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余不足;刺之大約者,必明知病之可刺,與其未可刺,與其已不可刺也。”說明不論人體生理、病理以及治療等方面,都有“逆順”的存在。接下來,“執道”、“循理”、“審時”及“守度”,也具體化為諸多醫學專業的課題,轉化為人體與自然關系、人體內部臟腑組織器官之間關系、人體正邪關系以及治療分寸的把握。因此,《內經》“逆順”再不只是一般字義,而有更加深刻的哲學內涵和專業指向。當其提及“逆順”時,大多數情況下是在指出與“天道”或自然規律相合,但又不盡相同的是關于人體生理、病理的復雜規律。
“逆順”在《內經》中的移植滲透,有一個漸進的過程,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據筆者考證,《素問》中除“至真要大論”、“五運行大論”和“六微旨大論”外,其余各篇均未完整提及“逆順”,而有些篇中卻有“從逆”提法,其含義非常接近。但在《靈樞》情況則為之大變,不僅有2篇作用篇名,而且有13篇(主要集中于后半部)多處論述。這提示我們:①《素問》多數篇目成書較早,當時“逆順”觀點或尚未成熟;②“從逆”的提法可能是“逆順”的早期雛形;③“至真要大論”、“五運行大論”和“六微旨大論”等篇大論,專家認為是后人補撰,故“逆順”被完整地提出;④《靈樞》至少后半篇目可能是漢初或稍前的作品,較全面地汲取了黃老哲學的精義。再從文字和哲學意義上比較,《內經》與《黃老帛書》有驚人的一致,后文將討論。
2.2 在中醫學的應用
2.2.1 生理學機能 “逆順”在人體生理學上應用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在天人相合的基礎上闡述自然規律變化對人體的影響。如《素問·六微旨大論》載:“至而不至,未至而至如何……應則順,否則逆,逆則變生,變則病。”這是自然界運氣對人體的影響。又如《靈樞·五亂》載:“經脈十二者……五行有序,四時有分,相順則治,相逆則亂。”十二經脈上應“天道”,而有“時”的逆順關系,故“經脈十二者,以應十二月。十二月者,分為四時。四時者,春秋冬夏,其氣各異,營衛相隨,陰陽已知,清濁不相干,如是則順之而治”。如若不循此理,則“相逆為亂”,“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脈,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于胸中”。
二是對人體各系統組織具體的作用和功能加以解釋。如《靈樞·五癃津液別》論五谷之津液生理,“此津液五別之逆順也。”《靈樞·逆順肥瘦》云:“脈行之逆順……手之三陰,從臟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總述經脈走行規律。《靈樞·營氣》論述營氣生理,說:“此營氣之行,逆順之常也。”這個“逆順之常”不僅指營氣循行流注,還概括了營氣生成及其生理功能等。
《內經》援用“逆順”闡釋人體生理時,總能從天人之際把握“道”、“理”、“時”等關系,更尊重“度”的制約。如《靈樞·逆順肥瘦》說:“不能釋尺寸而意短長,廢繩墨而起平木也,工人不能置規而為圓,去矩而為方。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順之常也。”明于斯,則如“臨深決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循掘決沖,而經可通也。此言氣之滑澀,血直清濁,行之逆順也”。可見《內經》深得黃老哲學“逆順”之精妙!
2.2.2 形氣體質 人的形質稟受于先天,又與后天有密切聯系,在發病學上尤其有重要意義。《靈樞·逆順肥瘦》歸納提出“逆順五體”,即壯年人(含肥人、瘦人)、血氣和調之常人、強壯之人和嬰兒。《靈樞·根結》釋道:“逆順五體者,言人骨節之大小,肉之堅脆,皮之厚薄,血之清濁,氣之滑澀,脈之長短,血之多少,經絡之數。”逆順五體,歸根結底是根據不同人群的差異特點所得出的體質分類。這是“執道”過程中,重視確定“形名”的體現,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故《靈樞·陰陽二十五人》說:“審察其形氣有余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
2.2.3 病理機制與診斷 《靈樞·玉版》明確提出:“諸病皆有逆順。”《靈樞·口問》說:“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敗,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稽留,經脈虛空,血氣不次,乃失其常。”說明人體在各種病因作用下,陰陽氣血經脈等不順反逆,是疾病發生發展的基本機理。例如“膨脹”病理解釋:“脹者……衛氣之在身也,常然并脈循分肉,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五臟更始,四時循序,五谷乃化。然后厥氣在下,營衛留止,寒氣逆上,真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為脹也(《靈樞·脹論》)。”
《素問·五運行大論》記載:“從其氣則和,違其氣則病,不當其位者病,迭移其位者病,失守其位者危,尺寸反者死,陰陽交者死。先立其年,以知其氣,左右應見,然后乃可以言死生之逆順。”這是從運氣的“逆順”判斷病情的吉兇。《靈樞·順氣一日分為四時》云:“是不應四時之氣,臟獨主其病者,是必以臟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起也……順天之時,而病可與期。順者為工,逆者為粗。”病甚病起有時,在中醫診斷或者治療上均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治療中“順天之時,而病可與期”。防治應從所勝所不勝臟考慮,這對于時間醫療學亦有不可忽視的貢獻,對一些疑難怪癥的治療開辟了新的思路,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內經》特別還提出“逆證”以警世,如《靈樞·玉版》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其在逆順焉……以為傷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內藥而嘔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項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脫,是五逆也。除此五者為順矣。”
2.2.4 臨床治療 《靈樞·海論》提出:“得順者生,得逆者敗;知調者利,不知調者害”的基本原則。治療上“審守其輸,而調其虛實,無犯其害,順者得復,逆者必敗”。
《靈樞·邪氣臟腑病形》曰:“刺之有道乎……刺此者,必中氣穴,無中肉節。中氣穴,則針游于巷;中肉節,即皮膚痛。補瀉反則病益篤。中筋則筋緩,邪氣不出,與其真相搏,亂而不去,反還內著,用針不審,以順為逆也。”說明治療(針刺)之道有度可守,有理可循。《靈樞·根結》還記錄了“刺不知逆順,真邪相搏”的嚴重后果。
《靈樞·九針十二原》說:“往者為逆,來者為順,明知逆順,正行無問。逆而奪之,惡得無虛,追而濟之,惡得無實,迎之隨之,以意和之,針道畢矣。”在臨床治療方面,《內經》對針刺的“逆順”討論較多,形成了“道”、“理”、“時”、“度”非常完整的體系,說明針刺療法此期已成熟起來。
[1]肖萐父,李錦全.中國哲學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96-300.294-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