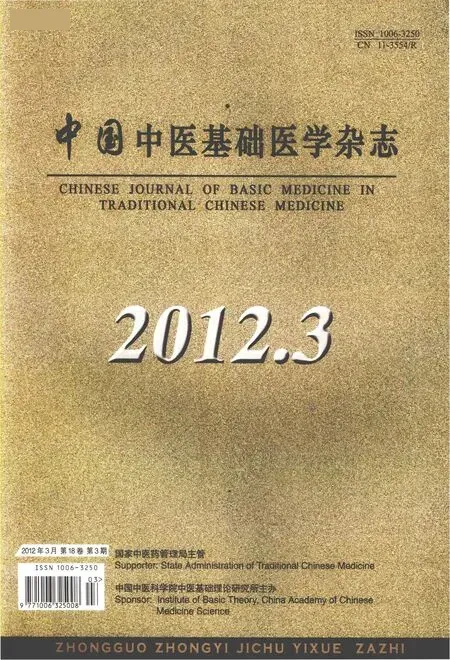丁櫻治療小兒過敏性紫癜經驗
都修波,閆永彬,丁 櫻
(河南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兒科醫院,鄭州 450000)
過敏性紫癜是臨床常見的出血性疾病,屬中醫學“血證”、“紫癜”、“肌衄”等范疇。本病是常見的毛細血管變態反應性疾病,是由多種原因引起的廣泛性的毛細血管炎,臨床表現以皮膚紫癜最為常見,同時可伴消化道黏膜出血、關節疼痛和腎炎等癥狀,常反復發作并最終累及腎臟而致不同程度的腎損傷。丁櫻教授在長期臨床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治療經驗,茲將其治療小兒過敏性紫癜的經驗介紹如下。
1 序貫治療
丁櫻教授認為,本病病機演變存在一定的序貫性,其發病之初多為外感風熱、濕、毒等邪,或進食魚、蝦等腥發動風之品,邪入血分,迫血妄行,灼傷脈絡,血溢肌膚則發為皮膚紫癜;血溢關節腔隙之間,則為關節腫痛;血溢胃腸之間則為腹痛、嘔血、便血;血溢膀胱腎絡之間則為尿血、溺血 。皮膚紫癜及各種出血消失之后,離經之血即為“瘀血”,以瘀血阻滯為突出表現。當瘀血消除之后,體內伏熱,血分不寧,每致紫癜復發。病至后期,耗氣傷血,傷陰損陽,脾腎虧虛,封藏失職,精微下泄,而致尿濁、水腫之癥。因此,丁櫻教授認為其病機可以概括為血熱妄行、瘀血阻絡、伏熱擾血、脾腎虧虛4個病理階段,4個階段之間存在上述序貫性的演變規律。《素問·至真要大論》曰:“謹守病機,各司其屬”,“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故其病機的序貫性決定了治療的序貫性。他在治療上十分推崇《血證論·吐血》:“惟以止血為第一要法……故以消瘀為第二法……故以寧血為第三法……故又以補虛為收功之法。四者乃通治血證之大綱”,從而提出初以止血消癜、繼以活血化瘀、繼以寧血安絡、而后補虛護腎的序貫療法。
發病之初以止血消癜為法,因風熱傷絡、血溢肌膚者,方用銀翹散加紫草、茜草以疏風清熱、涼血止血消癜;血分熱盛、絡損血溢者,方以犀角地黃湯或清營湯加茜草、蒲黃炭以清熱涼血、止血消癜;濕熱痹阻、血溢關節腔隙者,治以清熱利濕、止血通絡,方以四妙丸加赤芍、忍冬藤、三七粉;胃腸積熱、血溢胃腸且胃腸道出血者,治以清胃瀉火、涼血止血,方以葛根芩連湯或清胃散,加蒲黃炭、地榆炭、大黃粉、三七粉;血分熱盛、灼傷腎絡、尿血溺血者,治以清熱利水、涼血止血,常用小薊飲子加藕節、白茅根。當各種出血及皮膚紫癜消退之后,以離經之血所致瘀血為主要表現,治療以活血化瘀為主,以清除體內離經之血,否則瘀血不去、新血不生,而新血不生,瘀血亦不易去除。丁師常用桃紅四物湯、血府逐瘀湯加減以活血化瘀,祛瘀生新,使體內的瘀血得以清除,血脈得以暢通。止血消癜、活血化瘀之后,體內每有伏熱或感受風熱引動伏熱,使血分不寧,紫癜復發。丁師常以犀角地黃湯加蒲公英、連翹,或以清營湯加蟬衣、僵蠶,或以銀翹散加生地黃、丹皮、赤芍、玄參,靈活加減,以寧血安絡,使血分安寧,不再妄行。補虛護腎是本病后期的治療大法,丁師常以經驗方治療:太子參、生黃芪、菟絲子、桑寄生、白術、茯苓、薏苡仁、山藥、芡實、當歸、丹參、生地、益母草、甘草以益氣養陰、健脾益腎。有血尿者加女貞子、旱蓮草、白茅根、大小薊,蛋白尿者加金櫻子、芡實,水腫者合五皮飲。丁教授提出的序貫療法是從系統的高度把握本病復雜的中醫辨治,對提高臨床療效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為醫者提供了一條全新的診療思路[1]。但是,本病病機復雜,臨床上又當觀其脈證,隨證治之,靈活對待,方可萬全。
2 善用藤類藥物
過敏性紫癜其病機的實質是各種病因引起的絡脈的損傷。正如《靈樞·百病始生》所云:“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后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于腸外。”在上在外之絡,謂之陽絡,在下在內之絡,謂之陰絡,過敏性紫癜乃全身絡脈為病,全身上下內外之絡皆病。現代醫學稱該病為全身廣泛的毛細血管炎,與中醫學所言絡脈為病不謀而合,因病位在絡,故病程長,易復發,纏綿難愈,邪入絡脈是造成病變遷延難愈、容易復發的主要原因。因此,丁櫻教授治療本病緊扣絡脈損傷的病機,臨床用藥常加入通絡之品,而選用通絡之品時尤善用藤類藥物。
《本草便讀》云:“凡藤蔓之屬,皆可通經入絡。”丁櫻教授指出,藤蔓之屬,纏繞蔓延,猶如網絡,縱橫交錯,無所不至,為通絡之佳品,一者可以直接去除絡脈病邪,一者可以引諸藥直達病所。常用的藤類藥物有雷公藤、忍冬藤、青風藤、海風藤、絡石藤、雞血藤、鉤藤、首烏藤等。通過多年臨床實踐,觀察到藤類藥物的應用是解決過敏性紫癜及紫癜性腎炎絡脈損傷、絡脈瘀滯、絡脈不暢的一把利劍,可以有效地減少復發,預防和減輕腎臟損害。對于風熱邪毒、郁蒸肌膚、灼傷絡脈為病者,常用忍冬藤、青風藤、海風藤以祛風清熱,解毒通絡;濕熱痹阻、絡脈損傷、關節腫痛者,常用忍冬藤、絡石藤以清熱利濕,通絡止痛;胃腸積熱、腸胃絡傷、腹痛便血者,常加大血藤、忍冬藤以清熱解毒,活絡止痛;濕熱內蘊、傷及腎與膀胱之絡而為溺血尿濁者,以忍冬藤、大血藤、絡石藤清利下焦,除腎絡熱邪;病程日久耗傷氣血、瘀阻腎絡者,以雞血藤、首烏藤養血補血,活血通絡。過敏性紫癜患兒,若存在心煩不安、失眠多夢或頭目眩暈者,則加入首烏藤、鉤藤以養血安神、祛風通絡。丁櫻教授認為,雷公藤具有祛風濕、活血通絡之功,為藤類藥物的代表,通過配伍可應用于各類證型之中。現代藥理研究表明,多數藤類藥物有類似非甾體抗炎藥的直接抗炎作用,又有免疫抑制作用[2],為藤類藥物在過敏性紫癜中的應用提供了依據。
3 注重調理脾胃
小兒臟腑嬌嫩,形氣未充,為稚陰稚陽之體,脾常不足,因此治療小兒疾病應時時顧護胃氣,調理脾胃,只有脾胃健運,氣血化生有源、臟腑氣血充足,才有利于疾病的恢復,在小兒過敏性紫癜的治療中更是如此。因風熱傷絡,或血熱內熾、濕熱痹阻、胃腸積熱者,治療上常用清熱解毒、清熱涼血、清熱利濕或清胃瀉火之品,但這些藥物易耗傷中氣,損傷脾胃,因此丁櫻教授常于相應方藥中加入陳皮、薏苡仁、砂仁或白豆蔻,以顧護胃氣,和胃健脾;胃熱傷陰者,常加玉竹、石斛或花粉清養胃陰;脾胃升降失常、脘腹脹滿者,常加入枳實、白術、荷葉以復脾胃升降之職。因瘀血阻絡者,在使用活血化瘀藥時,要注意避免使用如水蛭、虻蟲、乳香、沒藥等克伐之品,以免克脾傷胃,常酌情加入黨參、黃芪、山藥或白術等藥以恢復脾胃之氣。因脾胃氣虛、反復感冒、紫癜頻繁復發者,遵《金匱要略》:“四季脾旺不受邪”,常用六君子湯合玉屏風散,以健脾益氣固表,使脾氣健旺,自不受邪矣。萬密齋《幼科發揮》云:“脾胃壯實,四肢安寧。脾胃虛弱,百病蜂起,故調理脾胃者,醫中之王道也。”可見調理脾胃當為過敏性紫癜治療的重要一環。
4 活血化瘀貫穿始終
過敏性紫癜為出血性疾病,導致本病的病因雖然各異,但最終的病理歸屬則同,血溢脈外是其相同的病理機轉,離經之血即是瘀血,溢于脈外之血,不得消散便形成瘀血,瘀血是血溢脈外的病理產物,又可加重血液外溢,從而使本病反復發作、纏綿難愈。瘀血貫穿本病全過程。現代醫學認為,過敏性紫癜的基本病理變化是全身性小血管炎,主要為免疫復合物沉積于毛細血管壁,造成血管內皮損傷及血管內皮下膠原暴露,從而激活血小板及凝血酶導致高凝狀態,使血液的凝固性增高,有利于血栓的形成[3],相當于中醫學離經之血不能及時排除消散而停滯于臟腑、經絡的瘀血形成過程。
丁櫻教授認為,瘀血是本病發病關鍵因素之一,常兼夾于臨床各證型之中,強調活血化瘀法應貫穿本病治療的始終。丁櫻教授提出本病的序貫療法與活血化瘀貫穿本病始終,相輔相成,在序貫治療的基礎上,活血化瘀一根紅線貫穿始終,根據不同的病因及瘀血的多少,隨證加減,靈活變通,使瘀血得以去除,血循常道而不外溢,諸癥自然得除。對于風熱傷絡夾瘀者,治以疏風清熱涼血、活血化瘀,常選銀翹散加生地、丹皮、川芎、赤芍、當歸、丹參等。血熱妄行夾瘀者,治以清熱涼血、活血化瘀,常選犀角地黃湯加當歸、丹參、川芎、紫草等。陰虛內熱夾瘀者,治以養陰清熱,活血化瘀,常選知柏地黃湯加丹皮、丹參、當歸、赤芍等。氣陰兩虛夾瘀者,治以益氣養陰清熱、活血化瘀,常以經驗方生黃芪、太子參、菟絲子、桑寄生、茯苓、薏苡仁、知母、女貞子、當歸、丹參、生地、川芎、益母草、甘草。丁櫻教授強調,過敏性紫癜屬于出血性疾病,在活血化瘀藥物應用過程中,要處理好化瘀和出血的關系,可酌情使用具有化瘀、止血雙重作用的藥物,如三七、茜草、蒲黃等,做到化瘀不傷正、止血不留瘀。
[1]丁 櫻,閆永彬,都修波.扶正祛邪多維序貫療法辨治小兒腎病[J].中醫雜志,2010,51(9):848-849.
[2]趙勝華.藤類藥的分類及應用[J].江西中醫藥,2002,33(4):47-48.
[3]王廣州,李曉玲,馬素麗.過敏性紫癜合并高凝狀態及肝素抗凝治療研究[J].實用全科醫學雜志,2007,5(10):9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