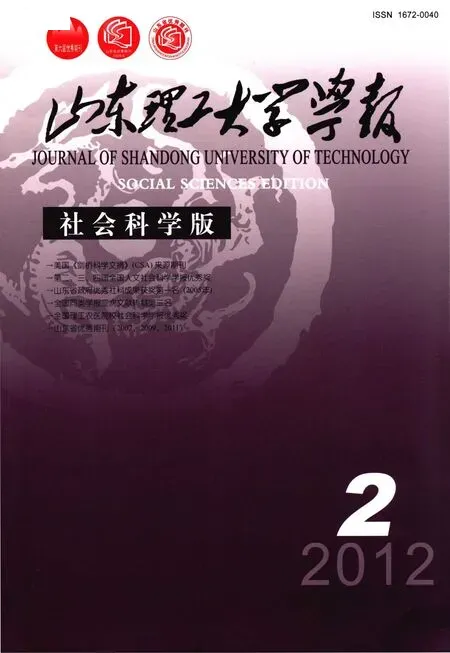孔子傳播思想研究
仝冠軍
(中國出版集團公司戰略發展部,北京100010)
一、孔子的傳播理念
孔子的最高傳播理念是“和而不同”,具體表現為“仁”與“禮”的統一。
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謂“和”、所謂“同”,其實都是就個體與他人以及社會的關系而言。作為傳播主體的人,首先是一個生命體,必然要追求自我道德的圓滿、自身個性的張揚和欲望的滿足,這是個性化的過程;其次,他又是一個社會性的人,他必然置身于紛繁復雜的社會網絡之中,受到各種社會關系、社會規范的制約,追求自身與社會的協調,這又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個性化與社會化之間必然會產生一種緊張的關系,而孔子認識到了這種緊張關系,他所說的“和而不同”,正是要使個體的自我發展、自我表現與社會、群體的認同呈現出和諧的狀態。就傳播而言,理想的狀態就是:既要發揮傳播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又要使傳播活動符合特定的社會規范;傳播者既能夠做到隨心所欲,又能夠不逾越規矩。這種理想狀態具體表現為“仁”與“禮”的統一。
“禮”是《論語》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孔子對自己的兒子說,“不學禮,無以立”,“禮”是傳播的一個重要原則。《左傳·隱公十一年》引用“君子”的話說:“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禮是一個社會得以正常運轉的必要體系,是確定人與人關系、地位的標準,是人際傳播活動必須遵循的一種原則。但是最完美的傳播狀態應該是“仁”和“禮”的統一。
關于“仁”和“禮”的關系,馮友蘭認為:“仁”和“禮”是互相矛盾的。“仁”是屬于個人的自由這一方面的東西;“禮”是屬于社會的制度這一方面的東西。“仁”是屬于自然的禮物這一方面的東西;“禮”是屬于人為的藝術這一方面的東西。自然的禮物和人為的藝術是對立的。對立必然相反,相反就是矛盾。但是相反而又相成,矛盾而又統一。沒有真情實感為內容的“禮”,就是一個空架子,嚴格地說,就不成其為“禮”。沒有禮的節制的真情實感,嚴格地說也不成其為“仁”。所以真正的禮,必包含有“仁”;完全的仁也必包含有“禮”。[2]164-165
孔子對“仁”有多種解說,最基本的意思還是“仁者愛人”,即強調一種人和人之間的平等關系,強調人的主體地位。“仁”是對傳播的一種自在的要求,側重傳播主體個人的品德,這是達到最高傳播境界的前提,因為唯有傳播者的素質都達到一定層次,方能有理想的傳播活動;“禮”則是一種外在的要求,是就個人與他人以及整個社會的關系來說的,能夠與社會融洽相處,傳播主體離“仁”也就不遠、他們的素質也就達到一定層次了。能夠將此兩者完美融合,既不違仁,又合乎禮,方為孔子心目中完美的傳播狀態。
二、孔子的傳播符號論
(一)傳播符號的劃分
孔子認識到,不僅言語可以起到傳播信息的作用,非言語符號同樣具有這種功能。《論語·學而》(以下僅稱篇名)云:“巧言令色,鮮矣仁。”《顏淵》云:“察言而觀色……色取仁而行違。”在這里,孔子將“言”與“色”并舉,認為它們都是傳播信息的符號,在傳播活動中,應該綜合傳播主體的言語和表情等非言語符號,綜合分析、判斷,才能夠得到接近客觀事實的信息。在傳播過程中,孔子特別注意適當運用這些傳播符號,《季氏》云:“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這主要是從傳播者這一方面來說的。
(二)語言的遮蔽性
所謂語言的遮蔽性,是說語言有時候并不能表達一個人的真實想法。語言的遮蔽性不僅僅是傳播主體使用不當的問題,更主要的是傳播主體的品德問題。《公冶長》云:“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這是說,有些人明明心里對別人有著無盡的怨恨,在語言和表情上,卻做出親昵的樣子。《先進》云:“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僅從一個人的言論加以判斷,很難弄清楚他是真的君子,還是通過言語和神情偽裝。《憲問》云:“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僅僅依靠言語,不能判斷一個人的德行。語言的遮蔽性還被用來委婉地對別人進行勸戒。那么我們如何通過言語了解一個人的真實想法呢?《子罕》云: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為貴。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所謂“繹”,是說能夠對傳播內容加以分析判斷,并辨別真偽。《為政》云:“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了解一個人,不但要通過他的所言,還要通過考察他的行為:做了什么事情?采取什么手段?做完事情之后神情是否安穩?等等。總之,要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加以判斷,才能夠不被一個人的言語所迷惑。
(三)語言的工具性
《論語》的最后一章是《堯曰》,《堯曰》的最后一句話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這一段話揭示了孔子對語言的工具性的認識。“君子知命”是從哲學意義上來說的,可以視作孔子的人生觀的一個方面;“君子知禮”是從社會層面來說的,“禮”主要指人與人之間的行為準則,是君子處身立世以及自我修養的重要方面,“禮”本身就是人與人之間各種關系的反映,是一種理想的傳播秩序;“君子知言”與前兩者并列,是君子成就功業和獨善其身的重要保證,其重要性同樣不言而喻。換句話說,孔子認為,語言是人際傳播中最重要的媒介,不知言,無以知人;不知人則難以自立于社會,處理不好人際關系,不能保證言語和行為都合于禮;不能自立于社會,言行不合于禮,則難以成為君子,更不要說達到“知命”的境界了。
作為重要的傳播工具,語言的威力在孔子看來是巨大的,《子路》云: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一個國家的興盛與衰敗均非一日之功,所以孔子說“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但是追究起來,國家的興衰與國君的關系卻是莫大的,其根源可以從國君的言語中反映出來,如果國君知道為政之難,善納忠言,便可以“一言興邦”,如果濫施權威,胡亂發號施令,迷戀于自己的“話語權威”,則會“一言喪邦”。所以孔子認為為政者應當謹慎使用語言這種傳播工具。
(四)傳播符號的規范化
傳播符號的規范化有助于提高傳播效率,擴大傳播范圍,在政治層面還有利于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融合。孔子時,在各地方言之外有“雅言”,“雅言”可能就是當時的官話。《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可見孔子在教育弟子以及為人主持儀式的時候,使用的是官話而不是方言。在孔子以后,雅言甚至影響到了文字的統一,進而影響到了民族的融合。
朱自清說:自從有了私家著作,學術日漸平民化。著作越來越多,流傳也越來越廣。“雅言”便成了凝定的文體了。后世大體采用,言文漸漸分離。戰國末期,“雅言”之外,原有齊語、楚語兩種有勢力的方言。但是齊語只在《春秋公羊傳》里留下一些,楚語只在屈原的“辭”里留下幾個助詞如“羌”、“些”等;這些都讓“雅言”壓倒了。[6]99
傳播符號規范化的另一層內涵,是孔子提出的“正名”理論。《子路》記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
孔子所處的社會,周禮已經難以維持,傳播符號所代表的事物和實際生活中的事物已經脫節,所以孔子要正名,使傳播符合和它所代表的事物一致起來。孔子所謂的“名”,其實不盡是周禮中的那一套傳播符號,而是經過了自己損益的一套新的傳播符號。孔子正是想通過推行這一套新的傳播符號,以規定社會現實,重建社會秩序。
(五)語言的表達能力
語言雖然是人類最重要的傳播工具,但是有些東西卻是語言難以準確表達的。比如孔子所謂的“道”,就很難用言語表達清楚。《陽貨》云:“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朱熹注曰:“學者多以言語觀圣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3]180但是在另一層面來講,語言的表達能力又是無限的。孔子通過“詩教”,彌補了語言的上述缺陷。所謂“詩教”,即是孔子通過教弟子學習《詩》,啟發他們從中獲得啟發,得到新的知識,而不是局限于原詩的意思。
《八佾》記載: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為也?”子曰:“繪事后素。”曰:“禮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矣。”原詩是在描述一位姣好的女子目光流盼,嫵媚動人,“素以為絢”是先施以粉底而后用五彩,在詩句中是說女子本身的條件很好,加上裝飾就更加漂亮。而子夏從中領悟到了“仁”與“禮”、“質”與“文”的關系,認識到一個人在自身修養達到“仁”之境界,再約之以禮,方可為君子。這種教育方式大大延展了語言的表達功能,充分發掘了語言的表達潛力。
徐復觀認為:由春秋賢士大夫的賦詩言志,以及由《論語》所見之詩教,可以了解所謂“興于詩”的興,乃由《詩》所蘊蓄之感情的感發,而將《詩》由原有的意味,引申成為象征性的意味。象征的意味,是由原有的意味,擴散浮升而成為另一精神境界。此時《詩》的意味,便較原有的意味為廣為高為靈活,可自由進入到領受者的精神領域,而與當下的情景相應。盡管當下的情景與《詩》中的情景,有很大的距離。此時《詩》已突破了字句訓詁的拘束,反射出領受者的心情,以代替了由訓詁而來的意味。試就《論語》孔子許子貢、子夏可與言詩的地方加以體悟,應即可以了然于人受到《詩》的感發的同時,《詩》即成為象征意味之詩的所謂“詩教”。此時的象征意味與原有的意味的關連,成為若有若無的狀態,甚至與之不甚相干。[7]5
孔子通過這種斷章取義的詩教,使《詩》發揮了更大的教育作用,語言的傳播能力得以提高。
在詩教的過程中,傳播者的主體性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在詩教之外,孔子更多地使用譬喻,拓展語言的表現能力,賦予語言以盡量多的意涵。《子罕》云:“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孔子以此來比喻為學要堅持不懈,積少成多,而不可中道而止,功虧一簣。再如《子罕》: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子曰:“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前者比喻學而不成,后者則寓意深廣,在不同語境下會有不同的引申意義。孔門弟子受孔子影響,也經常使用這種委婉的方式發表自己的見解,如《子罕》載子貢言:子貢曰:“有美玉于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等等。
三、孔子的傳播目的論
孔子以為,傳播的最終目的在于由“學”而“習”,在于“言”和“行”的統一。孔子的傳播目的論帶有很強的實踐理性色彩。《學而》的第一章是《論語》一書的開篇,云:“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周群振認為:“本章列《論語》首篇之首章,義旨精神,誠足以涵蓋全書綜和之思行意理也不遺。大抵為孔子晚年自省生命歷程之所成就,而以昭示并啟迪門人者。自外觀之,若有三事;揭其內蘊,實系整體一貫之展露,動發之機,則盡在‘學而時習之’一語之為因。”[8]2這一章大致交代了孔子對傳播目的的看法。
《子路》云:“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這里就表現出鮮明的實用理性。孔子以《詩》教育弟子,其重要的目的就是使弟子們可以從容應對各種政治場合,以詩篇為外交手段,所謂窮經以致用。這是春秋時士大夫的遺風。
《季氏》曰:陳亢問于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在這里,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孔子教學的目的,是為了培養弟子的語言運用能力(言)、社會交往能力(立)。詩是當時社會交際的重要手段,禮是當時社會交際的重要規則,學習這些知識,正是為了實用目的。
《詩》本是一部詩集,是文學作品,孔子在教學過程中卻更加注重其指導社會、人生的一面。《陽貨》載: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將《詩》的實用價值可謂挖掘殆盡了。
在“學”與“習”的順序上,孔子主張先“學”而后“習”。《先進》曰:“子曰:‘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在選用人才的時候,傾向于那些先學習禮樂知識,而后去從政、學以致用的所謂“野人”,對那些先從政再去學習的“君子”,則不那么看好。子路由于不遵守這一點,被孔子斥之為“佞”:“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后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由于大多數人輕易出言而惰于施行,孔子提出了“慎言”的主張: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學而》)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里仁》)
子曰:“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里仁》)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讱乎?”(《顏淵》)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憲問》)
子曰:“其言之不怍,其為之也難。”(《憲問》)
孔子對傳播目的的看法其實是對中國“慎言”傳統的一種繼承。春秋時期,人們認為出言不慎會給自己或者國家帶來災難,是一種被動的、逃避式的態度。在孔子這里,更加強調的卻是傳播主體的言論責任、社會責任,是一種積極負責的態度。
四、孔子的受眾思想
作為一位教育家,受眾思想構成了孔子傳播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一)風草論
所謂“風草論”,其實源于《論語》中的一段話:“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草上之風的比喻較為形象地表述了孔子對傳播效果的認識。一方面,孔子認為,有德者或者在位者(所謂“君子”),對民眾的教化恰如風過草偃,效果會非常明顯。《論語》中還有相似的論說: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子路》)
子曰:“茍其身正矣,于從政乎何有?”(《子路》)
這與“魔彈論”非常相似。魔彈論的缺陷在于過分夸大了傳播者的威力,而低估了受眾的能動性。但是孔子的“風草論”與“魔彈論”并不完全一致。另一方面,“魔彈論”認為傳播內容一下子就可以打倒受眾,對受眾過于低估。而孔子認為傳播的威力雖然巨大,但是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受眾一定會受到傳播內容的影響,但不象“魔彈論”說得那么絕對。風吹過去以后,草自然會逐漸站起來,只有不斷被大風吹拂,才可以使草完全倒下去,因此取得理想的傳播效果非一日之功。《子路》:“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即使有道的君主,想要使民眾歸之于仁,至少也要一世——30年的時間。對民眾的教化要循序漸進,不可操之過急。“風草論”較“魔彈論”的高明之處就在于它沒有絕對夸大傳播的威力,同時還關注到了那些對傳播內容具有極強“免疫力”的兩種人:“上智”與“下愚”。
(二)層次論
孔子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傳播活動要考慮到受眾的不同層次。孔子在傳播實踐中正是這么做的。同樣是請教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對顏淵說的是“克己復禮”,對司馬牛說的是“仁者其言也讱”,對樊遲則簡單地說“仁者愛人”。
孔子時,民眾的知識水平總體而言還是比較低下的。因之孔子提出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觀點。學界一般認為這句話只是對當時民眾知識水平的一種客觀反映。民眾層次不同,所以不必采取一律的傳播措施,務必使人人都“知之”。錢穆認為:“民性皆善,故可使由。民性不皆明,有智在中人以下者,故有不可使知者。若在上者每事于使民由之之前,必先家喻戶曉,日用力于語言文字,以務使知之,不惟無效,抑且離析其耳目,蕩惑其心思,而天下從此多故。”[4]208
對于“愚民”之說,郭沫若也力辯其誣:要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為愚民政策,不僅和他“教民”的基本原則不符,而在文字本身的解釋上也是有問題的。“可”和“不可”本有兩重意義,一是應該不應該;二是能夠不能夠。假如原意是應該不應該,那便是愚民政策。假如僅是能夠不能夠,那只是一個事實問題。人民在奴隸制時代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故對于普通的事都只能照樣做而不能明其所以然,高級的事理自不用說了。原語的涵義,無疑是指后者,也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意思。舊時的注家也多采取這種解釋。這是比較妥當的。孟子有幾句話也恰好是這兩句話的解釋:“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孟子·盡心上》)就因為有這樣的事實,故對于人民便發生出兩種政治態度:一種是以不能知為正好,便是閉塞民智,另一種是要使他們能夠知才行,便是開發民智,孔子的態度無疑是屬于后者。[11]90
孔子在這里強調的只是受眾的層次問題,而非反對傳播的愚民政策。
五、孔子的歷史傳播思想
《論語》中孔子不止一次地表明自己的好古情結。他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又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的許多知識即來源于歷史。談到古代的禮制時,孔子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孔子學習歷史知識主要是通過文獻,文即古代典籍,獻指的是賢人。在孔子之前,沒有私家著述。想要獲取知識,大概只有從當時知名、博學的史官那里問學了。
徐復觀以為,“史”乃是孔子學問的最主要來源:文是簡冊,是直接由史所記;獻是賢人,此處則應指的是良史。我們可以說,孔子在知識方面的學問,主要是來自史。史之義,莫大乎通過真實的記錄,給人類行為,尤其是給政治人物的行為以史的審判,此乃立人極以主宰世運的具體而普遍深入的方法。所以孔子晚年的修《春秋》,可以說是他以救世為主的學問的必然趨勢,不是偶然之事。[7]151
徐復觀在解釋“文獻”的同時,提出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即“史的審判”。在周代,歷史的審判已經代替宗教的審判,成為約束當政者的主要手段。孔子時,史官制度已經受到嚴重的破壞,不少史官流落民間,歷史的審判這個責任于是便開始落實到以孔子為代表的新的知識階層的肩上。于是便有了孔子的修《春秋》,便有了“微言大義”。也許在孔子看來,運用具體的歷史事實來表達自己的政治態度、表達自己對此社會的批判,要比單純運用哲學化的抽象的語言更容易為受眾所接受,也更有利于自己的觀念獲得充分、形象的表達。徐復觀對此所作的解釋,頗為精當:
司馬遷《史記·自序》對此加以引述:
“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載之“空言”,是把自己的思想,訴之于概念性抽象性的語言。用近代的術語,這是哲學家的語言。“見之于行事”,是把自己的思想,通過具體的前言往行的重現,使讀者由此種重現以反省其意義與是非得失。用近代術語說,這是史學家的語言。①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三卷)1-2頁,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徐復觀還認為:“由先秦以及兩漢,思想家表達自己的思想,概略言之,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或者可以說是屬于《論語》、《老子》的系統。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來,賦予概念性的說明。這是最常見的諸子百家所用的方式。另一種方式,或者可以說是屬于《春秋》的系統。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古人的言行表達出來;通過古人的言行,作自己思想得以成立的依據。這是諸子百家用作表達的一種特殊方式。”見同書第1頁。
即使在今天,受眾也更喜歡在生動的敘述中獲取知識,而不太喜歡直接接受抽象的學術觀點。這主要與知識的獲取難度相關:經傳播學者研究發現,受眾選擇接受一個觀點與否,取決于這個觀點對他的價值以及獲取、理解這個觀點的費力程度如何。可以用下面這個公式表示:

對受眾而言,理解抽象語言的費力程度顯然大于理解具體的歷史事實的費力程度,因此他們往往更加傾向于選擇后者。
孔子還時常“托古立言”,“把一些古代的人物如堯、舜、禹、湯、文、武尤其周公,充分地理想化了,每每在他們的煙幕之下表現自己的主張”。[11]82-83這種傳播方式對后世造成的影響也許遠遠超出了孔子的想像。不但后來的諸子百家爭相“援古”,以證己是而人非,后代的解釋經典的寫作方式很有可能也源于此。孔子非常重視歷史,對古人之言是非常崇拜的,他自己也說過“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的話。這種敬畏古人言論的思想發展到極致,再加上集權政府的提倡,在古人陰影下寫作的解釋經典的著作才逐漸成為封建社會學術寫作的主要方式。
總體來說,孔子的歷史傳播思想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孔子非常重視歷史典籍的流傳和學習,并以此作為教學內容(所謂“文”,是孔子教育之一科),并注重口述資料的采輯和傳播;第二,孔子認識到了“載之空言”和“見之于行事”兩種表達方式傳播效果的不同,因此注重通過歷史事實表達自己的思想,對后世的學術風格有重要影響;第三,孔子發明了“托古立言”的傳播方式,利用人們的好古心理,借用一些理想化的歷史人物之口,來表達自己的觀點,以增強說服力,取得更好的傳播效果。
六、孔子的輿論思想
孔子對輿論抱著較為開明的態度:“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子常常以輿論作為評價人的主要參考: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先進》)
子貢問曰:“何如斯不謂之士矣?”……曰:“敢問其次?”(孔子)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子路》)
如何在輿論與獨立思考之間平衡,是傳播活動中的一個難題,孔子提出了自己的解決辦法: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子路》)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衛靈公》)
將輿論與自己的觀察、判斷綜合起來,加以權衡,就能夠得出接近事實的結論,就會盡量少犯錯誤。對于那些在位者而言,掌握這個原則更為重要,因為這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政治的清明與否。
[1]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0.
[2]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4]錢穆.論語新解[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
[5]王宇紅.用自己的聲音說話[J].語文建設,2000,(10).
[6]朱自清.經典常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7]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三卷)[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8]幺峻洲.論語說解[M].濟南:齊魯書社,2003.
[9]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10]李彬.傳播學引論(增補版)[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
[11]郭沫若.十批判書[M].上海:東方出版社,1996.
[12]張舜徽.中國文獻學[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13]胡正榮.傳播學總論[M].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7.
[14]曠新年.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胡適[J].讀書,2002,(9).
[15]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