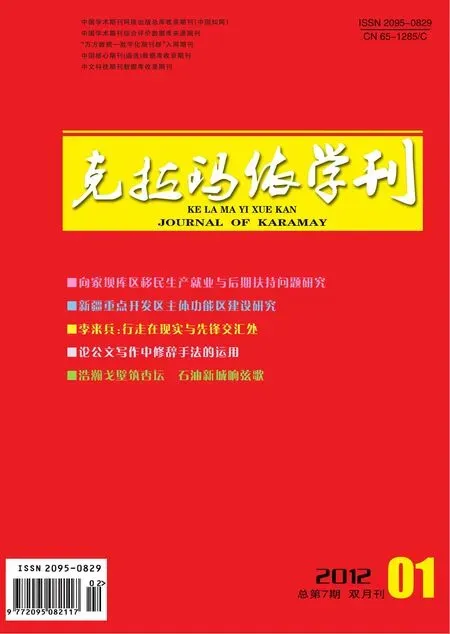“胡須”墓初探
張陸云
(新疆師范大學歷史與民族學學院,新疆烏魯木齊830054)
上個世紀前半葉,原蘇聯考古學家在哈薩克斯坦的卡拉干達地區發現一類結構奇異的古代遺存。這類遺存地表部分的建筑形式獨特,基本上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在地表用卵石或土堆砌而成的,大都有兩個封堆,或南北相鄰,或東西相伴,兩個封堆個別上下疊壓;另一部分由從墓葬向外伸出的兩列很長的弧狀石堆構成,這兩列石堆即所謂的“胡須”,“胡須”的方向幾乎都朝東,大多長40—50米,最長的可達到300米。
原蘇聯學家最早見到這種遺存的時候,懷疑其為墓葬,并因其封堆向外伸出弧狀石列,其外觀很像山羊的胡子而命名為“胡須”墓。
一、“胡須”墓主要分布介紹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以為“胡須”墓主要分布在以卡拉干達為中心的哈薩克斯坦的中部地區(詳見文后作者自編附表),是塔斯莫拉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但在其后的研究探索中發現,在哈薩克斯坦的其他地方也零星存在此類墓葬形式。后來,日本和俄國學者又在蒙古土瓦等地陸續發現此類墓葬。
1989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文物普查時,于阿勒泰市西南沙爾胡松附近的一片墓地發現一座有奇特地表標志的墓葬,這座墓葬由圓形封堆向東伸出兩排很長的石列,石列南北相對,并向外彎曲成弧狀。這是在新疆發現的第一座“胡須”墓,隨后在天山裕爾都斯盆地、阜康市南泉、博州哈日圖熱格、玉科克沿線山脊的臺地上、托里縣等地陸續發現了“胡須”墓。
從中外“胡須”墓的發現看,其地理分布有一定的規律。“胡須”墓多分布在高山或盆地植被豐盛地帶,地勢起伏不大,比較平緩,這些地區水草茂盛,比較適合游牧民族生存。所以,研究者認為這類遺存可能與游牧民族在歐亞草原上的活動和遷徙有關,如圖例廟爾溝鎮西石堆墓群M 2封堆平剖圖。
二、“胡須”墓的年代討論
僅從地表奇特的建筑很難斷定“胡須”墓的年代,并且這些“胡須”墓中多無隨葬品,只有少數隨葬一些陶片,年代特征也不明顯。所以,關于“胡須”墓出現和流行的年代,學術界爭論較大。
哈薩克斯坦把“胡須”墓存在時期的文化命名為塔斯莫拉文化,它分為前后兩期,前期年代為公元前7—6世紀,后期年代為公元前5—3世紀,卡德爾巴耶夫認為“胡須”墓屬于斯吉泰時期,即公元前的7—3世紀。阿魯斯諾娃在東哈薩克斯坦發掘了幾座屬于公元3—5世紀的“胡須”墓,甚至在南哈薩克斯坦還發現被認為是公元7—8世紀的“胡須”墓。
在新疆胡沙爾松發現的“胡須”墓的形式與東哈薩克斯坦發現的墓例一樣,年代也許是公元后的3—5世紀[1]。但天山裕爾都斯“胡須”墓的年代,與哈薩克斯坦“胡須”墓的形態不同,目前尚未找到解決其年代問題的線索[2]。
相對而言,蒙古發現的“胡須”墓,其“胡須”的形態、構造也很奇特。但是由于它與鹿石共存,推測其年代便有了可能性。鹿石的年代是公元前10世紀前后到公元前7世紀左右,與克列克蘇爾一同是否有鹿石尚不能最后確定。
三、“胡須”墓的意義探究
“胡須”墓是一種跨界分布的遺存,這類奇異地表建筑的遺存,究竟是什么性質的遺存?是結構奇特的墓葬,還是古代人主要用以祭祀的建筑?自從“胡須”墓發現以來,學者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至于“胡須”墓的象征意義,卡德爾巴耶夫注意到“胡須”墓的次墓中常常發現有馬骨,便把這種現象與希羅多德記述的馬薩該塔依人的儀禮連接起來進行解釋。馬薩該塔依人只崇拜太陽神。次墓中的馬骨認為是向太陽神提供的祭品。“胡須”的方向朝東表示的是太陽的崇拜。但是為什么在墓地中“胡須”墓很少,五、六座墓中只有一座“胡須墓”?卡德爾巴耶夫解釋說,因為營造一座“胡須”墓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只有在社會中具有特權階層的人才有這種能力,但是他并未解釋埋葬習俗和太陽神崇拜是怎樣結合起來的。
索羅金把封堆墓和“胡須”聯系起來考慮,提出了一種新的解釋。他認為組成“胡須”的一個個石堆,表示一個個儀式的列席者,由“胡須”的內側到末端,其社會地位逐漸降低。上述觀點的一個共同的前提是,均認為被葬者是一位很有權力的族長。如果僅從建筑規模這一點上講,它很難說是為了特權階層而修建造的。劉學堂在《“胡須”墓之謎—中亞草原地帶一種奇特的文化遺跡解讀》則提出了另一種解釋,他認為“胡須”墓中出土的隨葬品貧乏簡陋,不可能是當時社會中的特權階層者的墓葬,但“胡須”墓結構獨特,而且一處墓地常常只有1或2座,表明其墓主人又有區別同一墓地其他墓葬主人的特殊的社會地位,可以認為是薩滿[3]。
日本學者在關于“胡須”墓的總結中,寫道在明確性別的墓例中,女性比較多,為此引發了筆者的思考,在這樣一種特殊的墓葬結構中,墓主人一定是具有特殊社會地位的人,女性居多,可以認為這一時期女性的地位較高,那在從古至今,女性地位最高的當屬母系氏族時期。另外有很多關于薩滿產生于母系氏族的神話故事,這一類神話在北方民族中相當普遍,說明薩滿產生于母系氏族。[4]早期多為女薩滿,而且還兼任首領,另外根據前文中對“胡須”墓發現的地理環境的分析,筆者大膽地推測“胡須”墓是游牧民族薩滿的墓葬,很可能是母系氏族時期產生的女性薩滿的墓葬,它即是埋葬女性薩滿的墓,又是祭祀的宗教建筑。
確定了“胡須”墓的主人的身份——游牧民族的薩滿,可以更好地分析“胡須”墓的“胡須”這一種特殊的封堆標志。從現有的資料看,“胡須”墓的封堆有圓形和半圓形,這種形狀的封堆是用來祭月的,都屬于薩滿教原始祭祀內容。這在歷史典籍和民族民俗材料中有大量的記載。對此筆者很認可這種自然崇拜的觀點,幾乎世界上的各民族都存在過日神信仰,太陽崇拜所體現的內容實際上就是原始文化系列的如太陽崇拜中的巫術內容,巫術性的內容突出表現在拜日和祭日上,另外也反映在日神神話中[5]。在太陽神話和太陽崇拜中日神的創世能力是一個突出的方面,它包括太陽與大地之母結合而孕育大地的神話,太陽與月亮的結合而造萬物的神話,《禮記.禮器篇》:“大明生于東,月生于西,此陰陽之別,夫婦之位也。”顯然,此處大明即太陽,日月相合,象征著男女婚配,此為人類生存繁衍的神靈觀念,據傅道彬《中國生殖崇拜文化論》中對周易八卦研究,他總結出“乾+坤—氣—萬物”化生的公式,這種把神話信仰與生殖崇拜相結合的創世觀念,對于處于早期文明時代的人們具有較普遍的意義。總之,這一主題的儀式程序是日神發出孕育萬物之光,灑向大地之母或月亮女神,人類萬物便由此產生。而“胡須”墓的“胡須”所呈現出的圓形或弧形,很顯然是對太陽和月亮的崇拜,只是以這樣一種形式反映出來,它包含更多的是過去的人們對于族群繁榮發展、代代相傳的觀念,因此,是不是可以認為也有生殖崇拜的意義呢?
另外,對于“胡須”墓有次墓室埋馬骨的現象,通過對前文墓室主人的分析,筆者認為這種現象與他們所生活的環境密切相關。在游牧民族中,馬的作用是無法比擬的,馬是他們的交通工具,是他們的放牧工具,更是他們賴以生存的物質資料,結合過去很多的埋葬習俗,都會將死者生前經常用的或對死者有很大作用的物品一同埋葬,所以埋馬骨不僅僅是反映對馬的崇拜也是反映他們希望死者在另一個世界也能生活富裕的一種愿望。
[1]張玉忠.天山尤魯都斯草原考古新發現及相關問題[J].新疆文物,1996,(1).
[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阜康市南泉“胡須”墓[J].新疆文物,1996,(2).
[3]劉學堂.疆史前宗教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4]王宏剛.薩滿初論[J].長春師院學報,1993,(1).
[5]湯慧生.北方民族薩滿教中的火神、太陽及光明崇拜[J].青海社會科學,19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