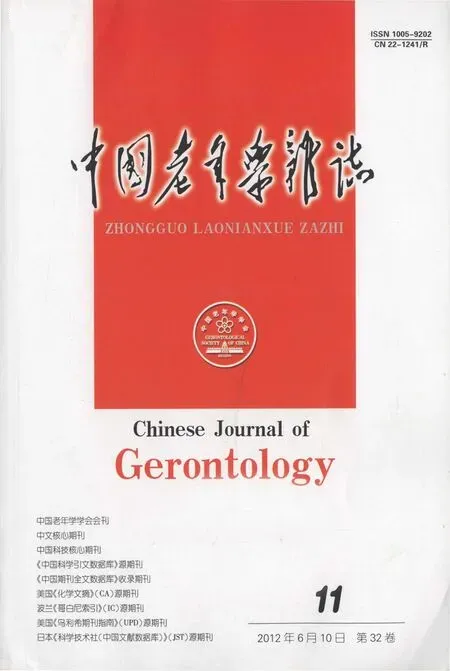國外老年人口長期護理籌資模式潛在的問題與啟示
彭 榮 凌 莉
(廣東商學院經貿與統計學院,廣東 廣州 510320)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長期護理是指在一段比較長的時間里為身體功能有障礙而缺乏自我照顧能力的人,提供日常生活活動幫助、健康照料、情感援助和社會服務。盡管長期護理的對象可以是所有年齡層的人,但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老年人占有絕大多數的比例。研究表明,中國的人口老齡化趨勢將導致巨大的長期護理需求〔1〕。但是,由于我國尚未建立長期護理保障制度,長期護理公共籌資來源缺乏,目前主要依賴于家庭和個人自付的長期護理籌資模式面臨巨大的挑戰。長期護理籌資問題是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建設中的重要環節。通過比較德國、日本和美國的長期護理籌資模式,發現其潛在的問題,有利于為我國長期護理制度的建立提供有益的參考。
1 國外長期護理籌資模式潛在的問題
長期護理基金來源包括公共和私人兩部分。公共部分的籌資模式主要有三種:社會保險計劃,以德國、日本和荷蘭為代表;社會援助計劃,以美國和英國為代表;上述兩種模式的混合計劃,以法國為代表。私人部分的籌資主要來源于商業長期護理保險和私人儲蓄及其家庭資助。
1.1 德國和日本長期護理籌資模式的問題 德國和日本是世界上較早實施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的國家,也是成功引入社會保險計劃運行長期護理制度的國家。目前來看,德國的長期護理系統運作良好,其長期護理籌資方案成功地大幅減少了低收入群體對公共援助系統的依賴。日本通過實施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增加了社會保障的財政來源,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醫療保險體制下“社會性入院”所帶來的醫療保險費用支出上升的趨勢。但是,從長期來看,德國和日本的長期護理籌資方式仍然存在潛在的令人不安的趨勢。
1.1.1 護理保險基金征收方式潛在的問題 公共長期護理基金可以通過一個專門的來源籌集,比如保險費和工資稅等特別稅,也可以來源于普通稅收。以德國和日本為代表的社會長期護理保險系統的基金就來源于前者。德國年滿15歲且有應稅收入的勞動者都要繳納以工資稅形式貢獻的護理保險基金。日本則規定40歲及以上的人必須參加護理保險并繳納相應的工資稅或收入相關保費。但是,德國的勞動者要在繳稅至少5年后,才具備申請護理賠償的資格。日本則規定在一般情況下,65歲才具備申請護理賠償的資格。也就是說,他們在享有申請護理賠償的資格之前,必須為長期護理基金的原始積累做貢獻。這種做法的弊端是,長期護理保險賠償標準很難改變,特別是降低。因為,人們認為他們在享受權益之前已經為護理基金作了貢獻。可以看到,像美國、法國之所以可以快速且大幅度的縮減護理保險賠償標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的公共長期護理保險的基金來源于普通稅收,而不是特別稅。
1.1.2 現收現付的籌資方式潛在的問題 德國和日本的護理保險基金均采用現收現付的原則來籌資。現收現付籌資方式的重要特點是以支定收,不留或留很少的儲備基金。德國和日本現收現付籌資方式的風險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1)如果老年人口數量增多,年輕人數量不變或減少,要保持現有的支付水平就必須增加繳費;(2)即使不考慮人口結構的變化,也可能由于預期與現實的差異帶來財政風險。德國和日本的長期護理系統均根據失能等級設定固定的短期人均護理費用,依此推算短期的長期護理成本。長期護理的短期成本從理論上來講是可以預見的。但是,如果不能正確的估計失能率和償付標準的話,以現收現付為基礎的長期護理保險計劃將出現財政赤字。比如,德國長期護理系統的現金流從1999年開始一直出現低微的負值,維持現行的護理標準需要在未來幾年顯著的增加工資稅稅率。據估計,到2040年,德國長期護理保險工資稅稅率將不得不從目前的1.9%提升到至少3.2%〔2〕。考慮到扶養比的增長,德國的一些分析家對這種趨勢表示非常擔憂〔3〕。
1.1.3 無需收入審查等支付制度潛在的問題 德國和日本的長期護理系統均不設收入審查制度,也就是說,只要申請者能說明其護理需求是合理的,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護理服務援助。日本的長期護理系統甚至為受益人的全部護理費用提供90%的補償。自付10%對高收入者的生活不會產生任何影響,隨著收入的增加和通貨膨脹甚至會激發護理服務的過度使用。但是,對低收入者而言,可能因為無力支付10%的費用而被迫減少或放棄護理援助。
在長期護理保險金的支付方面,德國和日本都設定了認證期。設置一定的資格認證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少管理成本,但也容易將一些真正需要護理的人拒之門外。另一方面,保險金的支付只依賴于受益人的健康狀況,與繳費多少及繳費時間長短無關,這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顯得不公平。
1.2 美國長期護理籌資模式的問題 美國長期護理籌資的來源主要有四個:老年醫療輔助計劃(Medicare)、低收入家庭醫療輔助計劃(Medicaid)、商業長期護理保險和自付資金。2008年,美國的長期護理費用由Medicare、Medicaid、商業長期護理保險和自付負擔的比例依次為18%、43%、7%和28%〔4〕。
1.2.1 公共籌資計劃的問題 美國的公共長期護理保障計劃包括Medicaid和Medicare,它們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老年人和貧困人群的長期護理需求,但是其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Medicaid不保障中產階級的長期護理需求。因為Medicaid計劃關于收入與資產的限制條件,基本上是申請者只有耗盡資產才能夠格。其次,因為完全免費,Medicaid有被濫用的風險。比如,2001年Medicaid計劃的總支出中,超過35%的部分被用來支付長期護理費用〔5〕。為了控制Medicaid計劃的成本,政府一方面增加稅收,一方面降低最低資產標準以控制Medicaid計劃準入門檻,結果導致居民負擔增加、受益人群被動減少的局面。第三,Medicaid不重視補償居家護理,費用支付嚴重偏向機構護理。1991年至2001年間,在由Medicaid支付的長期護理費用中,居家護理費用所占比重雖然從14%提升到29%〔5〕,但是仍有超過2/3的費用用于支付護理院護理。因此,使用Medicaid計劃的人會盡量選擇機構護理,這必然導致長期護理費用的大幅上升。
1.2.2 私人籌資計劃的問題 私人籌資計劃的問題包括商業長期護理保險覆蓋率低和對私人角色的忽視。目前,美國的長期護理籌資改革的方向主要側重于加大商業長期護理保險的發展。通過擴大州和聯邦政府稅收優惠,由聯邦政府出資舉辦的營銷活動等手段,鼓勵消費者購買商業長期護理保險。但是美國的商業長期護理保險市場占有率仍非常有限,僅覆蓋了不到10%的人群。商業長期護理保險產品價格高、價值不確定是美國人不愿意購買私人長期護理保險的重要原因。
在美國的長期護理籌資模式中,私人角色對長期護理的重要性往往被夸大的公共籌資作用所掩蓋。因為通常收集的長期護理支出數據只包括用于家庭衛生保健設施和專業的護理服務的醫療保險支出。這些服務雖然由長期護理機構提供,但是卻與長期護理主要適用于個人日常生活照護的本質有根本的不同。醫療保險覆蓋了部分的長期護理服務,但這些服務的重點在于預后康復和與治療相關的護理服務。與過分強調公共籌資相對的是,長期護理支出數據無法全面反映私人籌資對護理服務的貢獻。許多的數據只注重公共籌資來源的支出,無視非正式家庭護理或私人融資的作用。實際上,美國的大多數需要長期護理的老年人居住在家里或者社區,而不是在養老院。大多數需要長期護理的人依賴家人和朋友的幫助,包括資金援助。美國居住在家里或者社區的老年人接受的護理服務小時數中,85%的服務時間是免費的〔6〕。居住在家里或者社區的老年人中,不到10%的人僅僅依賴正規的或付費的長期護理服務〔7〕。
對私人負擔的不重視還在于忽視了來源于個人的直接的長期護理支出。因此,具有較多的長期護理需要的個人承擔了巨大的財政負擔,而那些有幸沒有長期護理需要的人則免于這項財務負擔。據估計,美國長期護理費用分布表現出高度的偏態:現時65歲的老年人中,有一半人不需要長期護理,因而無需花費任何長期護理費用;1/4的人長期護理費用少于1萬美元;有6%的老年人將花費超過10萬美元用于長期護理;大約有3/10的老年人在死亡之前都不需要長期護理,但是卻有1/5的老年人需要超過5年的長期護理〔8〕。
1.2.3 長期護理保險計劃保障不足的問題 美國長期護理籌資方式的根本問題不在于公共籌資來源和私人籌資來源的分配比例,而是缺乏保險保障—公共的或商業的保險,以保護有較大的長期護理需求的老年人支付昂貴的長期護理費用,獲得全面的長期護理服務。研究表明,1/5居家的美國老人報告他們沒有得到所需要的護理服務〔7〕。
美國商業長期護理保險的本意是采用市場的方式滿足不被公共長期護理計劃覆蓋的中產階層的護理需求。但是,正如前文所述,私人長期護理保險產品市場占有率低下,其原因除了消費者對產品沒有信心外,還有就是保險人對消費者的選擇。由于長期護理需求通常被認為與個人健康緊密相連,保險人會根據消費者醫療保險的使用情況選擇被保險對象。如果保險人通過評估后認為,該消費者在購買長期護理保險后不久就會發生保險賠付申請,保險人將拒絕向其出售保險產品。因此,有緊急護理需求的人往往得不到保險保障,只得自我承擔風險。據美國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01~2003年,沒有任何健康保險的人數分別為占總人口的比例為14.6%,15.2%和15.6%。
2 對我國的啟示
任何一個國家在建立長期護理系統時都要考慮三個重要的問題,一是如何提供護理服務,二是如何籌集服務所需的資金,三是如何評估受益人的護理需求。護理服務的供給方可以是家庭、公共部門、私人公司或者三者的組合。籌資可以通過商業保險、自付、稅收或社會保險。對護理需求的評估工作可以由供給方、籌資方或合法的私人機構來執行。但是,護理服務的資金來源顯然是建立長期護理制度要考慮的最重要的問題。盡管我國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的必要性得到了研究者們的一致認可,但是究竟應該借鑒德國和日本經驗還是美國經驗卻沒有定論。結合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人口老齡化狀況、文化背景和生活習俗,本文認為從國外的長期護理籌資問題中可以得到以下啟示。
2.1 公共籌資負擔應該與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公共計劃可以是一種權利,比如德國和日本的社會長期護理保險計劃,它通過設定一個開放式的籌資約定,向每一個合乎標準的人提供事先計劃好的津貼。公共計劃也可以以固定預算的形式來操作,比如美國、英國和法國的公共長期護理計劃,它通過設置資格門檻、限制服務或建立等待機制等來控制計劃的成本。不論是哪一種計劃,公共籌資負擔都應該與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日本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的建立,加強了對個人責任的強調,通過自付10%的聯合支付制度約束個人對護理資源的不當使用,但是卻造成了個人經濟負擔的不均,特別是大幅增加了低收入老人的經濟負擔。另一方面,現收現付的籌資方式進一步加大了政府社會保障制度的財政危機。如果經濟能夠穩定快速增長,政府可以加大投入力度,居民收入能穩定增長,財政危機就可以平穩過渡。但是,如果經濟不能穩定增長,日本的護理保險制度將問題重重。
在美國,Medicaid僅負責最低收入人群的長期護理費用補償。廣大中產階層必須依賴私人籌資計劃解決長期護理費用問題。顯然,美國的公共長期護理籌資計劃覆蓋面不夠寬,這似乎與美國的經濟發達程度不匹配。因此,美國國內關于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改革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對我國而言,盡管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水平遠不及日美等發達國家。目前老年人的長期護理責任主要由家庭承擔,以家庭成員提供護理為主,或者用現金形式以市場價格來雇傭保姆。另外,有一些老人在醫院的老年病區或老年醫院享受長期護理服務,利用現有的公費醫療和醫療保險為長期護理付費。可以說,我國的公共長期護理籌資功能是缺失的。由于老齡化、少子化、家庭規模小型化和人口流動等原因,家庭成員能夠提供的長期護理越來越少,而同時由醫院提供的長期護理服務又帶來了極大的浪費,所以必須重視長期護理問題,逐步完成從家庭承擔長期護理功能到社會承擔的轉化。
當然,也可以看到,我國的各項社會保障還處于較低的水平,政府也多次表明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的立場。我國是否有條件建立護理保險制度雖然尚在討論之中,但是從國外長期護理保險制度中吸取教訓,考慮經濟發展水平對公共籌資能力的影響是非常必要的。
2.2 聯合支付制有利于控制成本 不論是對居家護理還是機構護理,大多數國家都要求護理服務使用者直接支付部分護理費用。聯合支付制有利于降低道德方面的風險,遏制不必要的護理服務使用,從而控制成本。雖然固定比例的聯合支付制在操作上比較方便,但是相比于浮動的與收入相關的聯合支付制,本文認為后者更能體現社會公平。日本的聯合支付制規定,不論是居家護理還是機構護理使用者都要自付10%。這一規定不考慮低收入者的支付能力,可能會迫使低收入者減少護理服務利用,從而導致更多的社會不公平。
2.3 應該審慎選擇長期護理保險籌資方式 目前國外常見的長期護理保險籌資方式有:現收現付制,如德國、日本和荷蘭等;完全積累制,如美國、英國和法國等。現收現付制和完全積累制這兩種籌資方式各有優劣。現收現付制可以應對通貨膨脹所帶來的風險。但是,這種籌資模式與人口結構有密切的關系,當老齡化嚴重時,就會增加長期護理費用的支出,年輕一代必須增加繳費才能保持基金平衡。完全積累制以收定支,在職時完全積累,退休后按月支付,支付水平取決于過去的積累數額。完全積累制通過強制儲蓄,使個人一生的收入和消費均等化,能夠實現自我保障,不會引起代際沖突。但是,完全積累制要求幣值穩定、物價穩定、經濟穩定,否則基金保值增值的風險較大。同時,完全積累制下,基金積累多,時間跨度長,要求有很強的基金投資和管理能力。
本文認為可以從我國養老保險籌資出現的問題中吸取經驗和教訓,考慮直接采用部分積累制,它是現收現付制和完全積累制兩種模式的結合。部分積累制既能夠保留現收現付制保險金的代際轉移、收入再分配功能,又能夠實現完全積累制刺激繳費、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既能夠減輕現收現付制福利支出的剛性,又能夠克服完全積累制個人年金收入的過度不均,并保證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既能夠利用完全積累制積累資本、應付老齡化危機的制度優勢,又能夠化解完全積累制造成的企業繳費負擔過重與基金保值增值的壓力。
2.4 應該正確定位商業護理保險的功能 美國是典型的實行商業長期護理保險的國家。商業長期護理保險的初衷是為了承保廣大的不被Medicaid覆蓋的中產階級的長期護理風險。但是,由于長期護理風險的特殊性,美國盡管實施了許多優惠政策刺激消費者購買長期護理保險產品,它的市場占有率仍然遠未達到預期的目標。
我國尚未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居民的保險意識和商業保險消費能力以及保險市場的規范度與美國相比還有較大的距離,因此應該正確定位商業長期護理保險的市場功能,有針對性地開發長期護理產品。商業長期護理保險作為商品,其盈利性決定它只能作為長期護理籌資的輔助手段。
1 Rong Peng,Li Ling,Qun He.Self-rated health status transition and longterm care need,of the oldest Chinese〔J〕.Health Policy,2010;97(2):259-66.
2 H?cker J,Raffelhüschen B.Denn siewussten was sie taten:Zur Reform der Sozialen Pflegeversicherung〔J〕.DIW Vierteljahreshefte zur Wirtschaftsforschung,2004;73(1):158-74.
3 Arntz M,Sacchetto R,Spermann A,et al.The German social long-term care insurance:structure and reform options〔EB/OL〕.http://econstor.eu/dspace/bitstream/10419/34303/1/544113039.pdf,2009-12-30.
4 Gleckman H.Long-term care financing reform:lessons from the USand abroad〔EB/OL〕.http://www.commonwealthfund.org/~ /media/Files/Publications/Fund%20Report/2010/Feb/1368_Gleckman_longterm_care_financing_reform_lessons_US_abroad.pdf,2010-12-30.
5 Brien EO,Elias R.Medicaid and long-term care〔EB/OL〕.http://www.kff.org/medicaid/loader.cfm?url=/commonspot/security/getfile.cfm&PageID=36296,2009-06-10.
6 LaPlante MP,Harrington C,Kang T.Estimating paid and unpaid hours of personal assistance services in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provided to adults living at home〔J〕.Health Services Res,2002;37(2):397-415.
7 Feder J,Harriet LK,Friedland RB.Long-term care financing:policy options for the future〔EB/OL〕.http://ltc.georgetown.edu/forum/ltcfinalpaper061107.pdf,2009-06-10.
8 Kemper P,Komisar HL,Alecxih L.Long-term care over an uncertain future:what can current retirees expect〔J〕?Inquiry,2005;42(4):33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