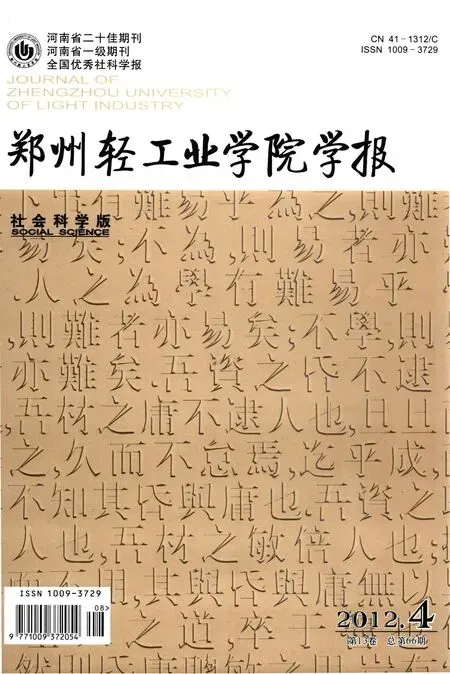論孔子的社會秩序觀
王軍
(1.南京大學政治系,江蘇南京210093;2.江蘇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鎮江212003)
儒學中包含著十分豐富的社會秩序思想。瞿同祖[1]曾言:儒家是以維持社會秩序為目的的。“五四”思想界的激進主義者往往將儒學視為維護封建專制的意識形態,而儒家關注社會秩序的做法也成了很多人攻擊儒學的口實。之后,學界對儒家社會秩序思想進行客觀研究者不多,對孔子秩序觀的研究情況更少。基于此,本文試圖在解讀相關文本的基礎上,梳理和歸納孔子的社會秩序思想,并發掘其在當代社會的積極意義,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對現實秩序的判定與對理想秩序的設定
判定社會秩序優劣的標準是社會秩序觀的基本內容之一,也是理解孔子社會秩序觀的前提。孔子判斷社會秩序優劣的標準是:“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2](P174)禮樂制度和戰爭出自天子或出自諸侯分別是判定社會秩序優劣的標準。“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2](P174)在孔子看來,禮樂征伐如果不是出自天子而是出自諸侯,那么就不會長久;出自大夫或陪臣就更是如此。在西周鼎盛時期,禮樂征伐專屬于天子;周平王東遷之后,隨著周王室的衰微,五霸迭興,“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現象頻繁出現。而在一個人治的社會中,由于缺少法的有效約束,上行下效是無法避免的現象,諸侯的僭越必然帶來大夫、陪臣的僭越,社會秩序的混亂也就無法避免了。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孔子才會說:“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2](P174)
依據上述標準,孔子判定春秋時期是一個無序的社會:“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2](P175)理想的社會秩序顯然不是這樣的。在孔子看來,理想的社會秩序必須做到人安其位、各司其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P128)此處涉及君臣、父子兩對關系,其中又以父子關系更為核心,這也是移孝作忠的根據。該論斷雖有維護等級制度的意向,但更重要的是強調君臣父子要盡到各自的職責。先看父子關系:“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2](P40)父子之間存在著割舍不斷的血緣關系,但這種關系不是絕對平等的,對父母的孝是最基本的要求,子對父是可以“諫”的,關鍵是要注意方式。再看君臣關系:“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2](P30)雖然后儒移孝作忠,但君臣關系并不等同于父子關系,臣對君的忠是有條件的,即君以禮待臣。由于君臣之間不存在類似父子之間無法割舍的關系,因此兩者之間的關系甚至可以解除:“以道事君,不可則止。”[2](P117)可見,孔子對君臣關系的理解,絕非后世所宣揚的愚忠。當然,孔子也明確反對臣弒君的行為:“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2](P153)可見,理想的社會秩序是君臣、父子各盡其責,否則就是“禮崩樂壞”的無序社會。
在《論語》中,孔子關于君臣、父子秩序的設定只是一個比較低的要求,更高層次的要求體現在《禮記·禮運》的相關描述中:“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戶外而不閉,是謂大同。”[3]這是儒家對理想社會秩序的經典描述,也是對孔子社會理想的進一步升華。然而,現實的社會并非一個理想的有序社會,因此,如何變現實的無序為理想的有序就成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二、對傳統秩序的創造性詮釋
為了實現理想的社會秩序,孔子對前人的思想資源進行了一番選擇,并做出了創造性的解釋。
第一,從周正名。作為一個十分熟悉傳統的思想家,孔子重構秩序時首先想到的是如何選擇、利用“三代”資源。“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2](P26)“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2](P28)顯然,孔子從周,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周比夏、商兩代的文獻更為豐富,而更為根本的原因則是孔子認為周文化比起夏、商兩代有更多的優勢。然而,孔子時代周文疲弊,各種僭越行為造成了名實混亂。因此,孔子提倡正名:“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與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與其言,無所茍而已矣。’”[2](P133-134)
孔子所謂正名,主要有兩層含義:其一,“名實一致,即循名求實,有君之名,須有君之實質;有臣之名,須有臣之實質。父子亦然”;其二,“名分相符,即依名守分,有君之名,須守君之本分,有臣之名,須守臣之本分。父子亦然”。[4]表面上,孔子的這種做法是在維護既有的等級名分,因此有人將其等同于“恢復已經衰頹的周禮中的等級名分”,繼而認為其思想是守舊的——如馮友蘭[5]在其《中國哲學史》中就持此觀點。其實,孔子倡導正名是有其現實原因的,決非“復古倒退”,其目的是強調人們(主要是為政者)要主動約束自己的欲望以符合自己的“名分”,而非簡單地恢復西周的禮樂制度。這是對制度的重整而不是簡單的“恢復”,它有利于社會的安定和發展,在當時具有積極意義。通過正名,可以使人各安其位、各司其職。如此,各種因欲望張揚而造成的僭越行為就會逐漸消失,社會也會逐漸回到符合禮之要求的秩序之中。
第二,以仁釋禮。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在孔子看來,問題的關鍵并不是禮樂制度本身的崩潰,而是人們內心對禮樂秩序的忘卻最終使其成為沒有靈魂的、僵死的軀殼:“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6]這種拘泥于禮的形式而忽略禮的本質的現象,在當時是很普遍的。因此,孔子才會感嘆:“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2](P185)為了使禮樂獲得新生,孔子援仁入禮,就是要喚醒人們內心對禮樂秩序的自覺。當然,孔子所說的禮樂并不完全等同于西周初年的禮樂,它已經從外在的規范變成內在的自覺了。為了將禮樂秩序植入人的內心,孔子將其解釋為人之根本:“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2](P24)既然仁是人之本質,則只要將仁喚醒,就可以重構人內心的秩序,而內心秩序的外化就可實現社會秩序的重構。
這種重構有可能嗎?在孔子看來,這是完全可能的。一方面,孔子認為人性平等,所謂“性相近也,習相遠也”[2](P181);另一方面,仁根植于人性之中,所謂“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2](P74)。當然,在孔子那里,仁的含義十分復雜,但“仁之成就,始于主觀之情感,終于客觀之行動”[7](P57)的特征,保證了禮樂制度可以通過仁獲得新生。非但如此,作為主觀情感的仁,還是安頓人心、處理人心秩序的最重要的原則與手段。
三、對社會秩序中不同主體的安頓
理想秩序的實現離不開人。在孔子看來,不同的人其作用是不同的:君子是實現理想秩序的主體,是主動者;而普通民眾則是需要被安頓在這一秩序中的分子,是被動者。
1.提倡君子人格
重構理想的禮樂秩序離不開君子,這一重任主要由君子承擔。為什么只有君子才能承擔起重構理想社會秩序的重任?這涉及到理想與現實的問題——雖然人性平等,但理想并不等于現實,現實中人與人是有差距的,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2](P61,P181)。所以,重構社會禮樂秩序的重任只能由“中人以上”的君子承擔。然而,君子有什么樣的規定性呢?有人認為,君子在先秦儒家的話語體系中,“指稱的基本對象是政治中人,而不是后來寬泛意義上的道德指稱”[8]。說君子主要是處于政治上的在位者而非普通民眾是正確的,但并不全面。在孔子那里,君子還應包括道德高尚者,如“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2](P1)中的“君子”顯然不必是政治上的在位者,政治上的在位者只是其原始義。因此,理想的君子是德與位同時具備者,類似于柏拉圖所說的“哲學王”。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孔子所說的君子不是普通的、作為蕓蕓眾生的百姓,而是能夠擔當道義的人。
擔當道義的君子應如何重構秩序呢?在孔子看來,就是通過君子的“修己”達到“安人”、“安百姓”的效果:“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2](P159)君子“修己”是喚醒自己內心對秩序的自覺,這是重整外在秩序的基礎;“安人”、“安百姓”則主要是通過君子恪守秩序而對百姓產生示范作用來實現的,所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2](P11,P12)。用莊子的話說,就是由“內圣”而“外王”[9]。與莊子“內圣”為本、“外王”為末[10]不同,在孔子那里“內圣”固然很重要,但絕不能取代“外王”。雖然“內圣”是“外王”的基礎,但“外王”是孔子一生都未曾放棄的追求,只要有機會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是十分樂意做官的,因而子夏說的“學而優則仕”[2](P202)也是符合孔子本意的。即便孔子晚年不再求仕,一心編(著)書、授徒,也仍然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無論是以“思無邪”為宗旨的《詩經》,還是記載古代圣王治國之政治經驗的《尚書》,都表現出其明顯的政治意圖,而《春秋》所體現的“春秋大義”的政治立場和意圖更是十分明顯;在講學中,孔子也并非以培養有知識的人為目的,而是為了培養能夠實現“王道”的士與君子。所以,在孔子那里,“內圣”與“外王”是其思想內在的、不可分割的兩個向度,內在秩序與外在秩序兩者缺一不可,他們之間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輔相成的。然而,“內圣”就一定能達到“外王”嗎?孔子想到了這個問題,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一些補救措施,主要體現在其治民之術中。
2.養民、教民、治民并舉
除了君子,世上更多的是普通民眾,如何安頓這些人是重構理想社會秩序無法回避的大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孔子提出了三個策略,即養民、教民、治民。
首先是養民。養民是孔子一貫的主張:“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2](P136-137)如何養民?孔子云:“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2](P4)又云:“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11](P12)孔子之所以重視養民,一方面與其仁的精神相關[7](P60),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認識到必要的財富是德性與秩序的基礎。這與“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12]的道理有相通之處。但孔子并不提倡以追求財富為目的,而認為財富應該是完善德性的手段,所謂“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11](P12)。在財富分配上,孔子明確主張:“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2](P172)這仍然是出于對秩序的考慮。
其次是教民。在孔子那里,養民是為了給社會秩序的安定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然而理想的秩序并不會隨著基本物質生活的滿足而自然建立,因此需要對民眾進行教化。孔子的教化理論十分豐富,其最基本的做法就是以身作則,所謂“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2](P129)。又云:“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2](P138)“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2](P135)在位者與君子以身作則是教化民眾的關鍵,君子、民眾都做到“正”,方能實現社會的安定與秩序的重建。
最后是治民。現實中并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通過教化而遵守秩序的:一方面,有些人是不好教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2](P81)——此句中的“可”不是“可以”而是“容易”之意,這與孔子“有教無類”[2](P170)的主張完全一致。這是顯而易見的:對于某些人,讓他照著做可能比讓他知道為什么要這樣做更容易。另一方面,總是存在一些不受教因而教不好的人,這也是事實,因為教育并不是萬能的。對于“不好教”(不易教)和“教不好”的人,采用強制手段即政與刑也就無法避免了。然而,孔子認為,政與刑的作用是消極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2](P12),因此政與刑只是實現教化和社會秩序重建的輔助手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蕭公權才會說孔子“傾向于擴大教化之效用,縮小政刑之范圍。其對道德之態度至為積極,而對政治之態度殆略近于消極”[7](P63)。
四、孔子社會秩序觀的當代價值
孔子通過從周正名與以仁釋禮對傳統秩序的創造性詮釋,以及通過提倡君子人格與養民、教民、治民并舉來安頓社會秩序中不同主體的思想,對我們構建與維系良性社會秩序有重要啟示。
第一,良性的社會秩序需要不斷融入新的時代精神。孔子的社會秩序觀并不是對西周舊秩序的簡單重復,而是依據仁的精神對傳統秩序的創造性詮釋與重構。伴隨著春秋時期人文精神的躍動、井田制的瓦解和現實王權的衰落,維系以禮制為特色的社會秩序的各種力量對比發生了極大改變,原有秩序岌岌可危,這是孔子改造周禮的最根本原因。而孔子改造原有禮制秩序的基本方式就是融入當時正在蓬勃興起的人文精神。與古代社會相比,當今社會的發展更是日新月異,文化觀念的碰撞與交流更加頻繁。因此,良性社會秩序的建構與維系,必須不斷地輸入時代精神以適應變化了的現實。
第二,良性社會秩序的建構與維系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孔子重視養民,主要是強調要讓百姓在經濟上實現富足,在此基礎上才可能對百姓進行有效的教化。這一認識十分樸素,卻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現代社會也是如此,要想建構并維系良性社會秩序,必須滿足人們最基本的物質生活需求,且這種需求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提高。
第三,良性社會秩序的建構與維系需要教育與感化。人們對物質的欲求有時是無止境的,孔子正是意識到這一點,才尤其重視教化的作用,將教化作為重構社會理想秩序的基本手段。當今社會要建構與維系良性的社會秩序,亦應對國民進行教育與感化。當然,這種教育不能僅停留于標語、口號,而要變生硬呆板的道德說教為潤物無聲的綿綿細雨,以增強其親和力、感染力,讓外在的道德規范變成內在的德性品格。
第四,良性社會秩序的建構與維系需要制度的保障。面對那些無法教化的民眾,孔子并沒有排斥政與刑的作用。現代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同樣如此,秩序的建構與維系仍然需要一定的強制措施,而這離不開較為完備的制度保障,如此方能避免政隨人遷,保證政策的延續性和社會的穩定性。
第五,良性社會秩序的建構與維系需要榜樣的示范作用。孔子認為君子在重構社會秩序的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啟示我們,社會秩序的建構需要發揮榜樣的作用。政治上的在位者和公眾人物的言行會對社會產生極大的示范作用,網絡時代這種示范效應尤為顯著,因此政治上的在位者及公眾人物必須自重。另外,要有意識地發現和保護那些能對社會秩序產生積極影響的榜樣,要有一定的激勵機制,并對之進行倡導和宣傳,以充分發揮其促進良性社會秩序建構與維系的示范作用。
[1] 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M].北京:中華書局,1981:270.
[2] 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3] 阮元.十三經注疏[M].北京:中華書局,1980:1414.
[4] 薩孟武.儒家政論衍義[M].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2:38.
[5]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M].北京:中華書局,1961:36,78-89.
[6]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1:1457.
[7]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8] 趙明.先秦儒家政治哲學引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83.
[9] 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984.
[10] 方勇,陸永品.莊子詮譯[M].成都:巴蜀書社,1998:881.
[11]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2] 戴望.管子校正[M].上海:上海書店,19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