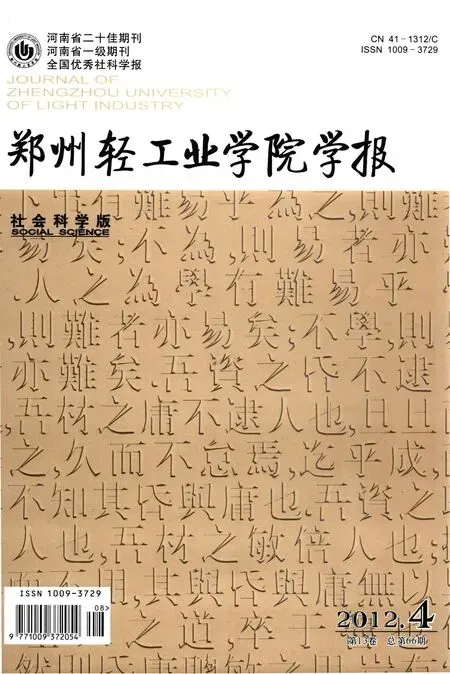“終結論”與社會主義憲政
高建軍,苗沛霖
(1.鄭州市管城區人民政府法制辦,河南鄭州450004;2.鄭州大學法學院,河南鄭州450001)
20世紀末,“終結論”者面對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內取得的“勝利”歡呼雀躍,并認為終極社會已近在咫尺,“勝利的曙光”馬上就會照亮大地。然而近20年來,“終結論”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挑戰,資本主義不僅沒有取得勝利,反而危機日益深重。相反,以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取得了民主憲政建設的巨大成就,“中國模式”成為西方之外的典型范式。在中國,近年來社會主義憲政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無論憲政理論研究還是憲政實踐,都說明資本主義民主憲政不僅不是歷史的終結,反而被社會主義憲政所超越。學界探討社會主義憲政者較多,卻鮮有人把“終結論”與社會主義憲政相聯系進行研究。本文擬在分析“終結論”所遭遇的挑戰之基礎上,探討社會主義憲政對資本主義民主憲政的超越及通往社會主義憲政的橋梁。
一、“終結論”的提出
1989年,正值蘇東發生劇變之時,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國家利益》雜志發表了《歷史的終結》一文,認為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1](P1)。自由民主的理念無法再改善。[2](P24)4年后,他在《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一書中重述了這一觀點,并針對其他批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福山[1](P1)聲稱,之前人類社會的種種社會制度因為具有嚴重的缺陷而走向衰落,當前的自由民主制度因為不存在內在的根本性矛盾而代表了人類歷史的方向。福山的這一論斷并非毫無根據,在20世紀的最后25年,在世界范圍內確實發生了令西方自由民主主義者為之興奮的事情,帶有西方色彩的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圍內取得了很大勝利,如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從而使西方世界認為歷史的終結已為期不遠。[1](P4)不僅福山持這樣的觀點,其他不少學者面對蘇聯解體、柏林墻倒塌等一系列歷史事件,提出“民主現已成為唯一具有普遍正當性的政府形式”,認為世界許多地區向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靠攏是20世紀最重大的變遷,民主化正在成為一個全球現象,它包圍著東亞、俄羅斯、東歐、中東和非洲地區,從右的方面席卷了權威主義政權,從左的方面沖擊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權。[3]
當然,福山們的某些觀點是有道理的,如他認為“民主在各個地方和各種人中的成功意味著自由平等的原則不是空穴來風,也不是種族偏見的結果,而是作為人的人性的發現”[1](P58-59)。當今世界上,除了極少數專制政權對這些價值仍然嗤之以鼻外,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價值觀已經得到了普遍認可,包括自詡為自由民主國度的各西方國家在內的多數政權,至少在形式上都把民主和自由的實現當做自己的核心價值目標。這就是說,民主和自由的價值及其存在的制度架構——憲政、法治等,代表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方向和世界絕大多數人的價值觀。但同時還應看到,即便在本質上具有一致性,民主和憲政在形式上卻有著千姿百態的表現,關于自由的內涵也有著不同解釋,因此實現民主與自由的途徑也就會有所差別。而福山等西方自由民主主義者之論實質上是延續了冷戰思維模式,以資本主義民主否定其他民主制度與發展形式,“人權”這一最為核心的政治法律概念成為東西方意識形態之戰的前哨。
二、“終結論”遭遇的挑戰
福山的觀點代表了相當一部分西方人的看法。由于一些歐美國家成功地實現了現代化,于是一些人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無論采取多么有特色的發展模式,最終都將走上西方的“民主”道路。不幸的是,關于“歷史終結”的論點并沒有得到更多的證明,西方的憲政民主和自由主義模式在同非西方文明的交鋒中也未能取得勝利。就“歷史終結論”本身而言,可以看做是“社會主義終結”的一種隱喻。當福山宣告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已經徹底“戰勝”共產主義的時候,法國學者德里達卻給這個“好消息”劃上了句號,他說這場所謂的“勝利”可能預示著一場災難。盼望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度獲勝的人們,做夢也想不到類似“9·11”的災難在等著他們,“獲勝”所帶來的災禍并不比它帶來的利益要少;馬克思主義的“失敗”很可能只是表面上的,馬克思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后一人,他的“幽靈”不是一個,還有其他“幽靈”們。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終結”,或者說“歷史的終結”,其實只是某種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的終結,僅僅代表了特定的歷史概念。他雖然在一個舞臺上終結,卻在另一個舞臺上發揮影響。[2](P11)相反,如果我們只能聽到一種聲音:如果美國模式成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標準模式,整個世界成為美國文化的附庸,英語最終替代了其他語言,而各民族忘記了自己的母語,這不僅不能看做是民主自由的勝利,而恰恰是它的悲哀。[2](P15)
正如我國學者周峰所說,“歷史的終結”可能已經不是“社會主義的終結”,而是“資本主義的終結”。周峰認為,福山所推崇的西方政治經濟制度,即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和自由民主制度,面對新近發生的使全球為之震蕩的經濟危機,不免失語。隨著這種帶有所謂“普遍主義”特點的發展模式在世界范圍內的推廣,其結果不僅不是世界大同,反而將導致各個國家和地區價值世界的失序和顛倒,而對于“現代馬克思”的呼聲則越來越高。同時,在這次經濟危機中,中國可謂獨樹一幟,令世界刮目相看,中國獨特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已引起眾多西方學者的興趣,并稱其為“中國模式”。[4]“中國模式”的提出否定了西方模式的所謂普遍性,并且具有比“東亞模式”更強的說服力。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認為,中國是一個拒絕“華盛頓共識”而又能成功融入全球市場的典范,在世界范圍內,中國社會主義發展范式已被判定為“中國模式”。[4]這里的“華盛頓共識”代表了傳統的西方自由主義,可以說是西方模式的價值內核。“中國模式”的提出至少說明了現在做出“歷史終結”的判斷顯然為時過早,西方模式未必就代表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方向,西方模式所追求的價值也未必是人類的終極價值。
更進一步來說,民主憲政的價值不容置疑地取得了普遍的承認,但它僅僅是民主憲政本身獲得了認可,而非西方模式所取得的“勝利”。民主本身作為一種政治實踐和政治制度,可以生長于古希臘、古羅馬社會,也可以生長于當今世界的各個國家。迄今為止人們還沒有發現一種通行于全球、適合于每一個國家的民主模式,將西方的制度模式塑造為“標桿”的做法只是一相情愿。
三、社會主義憲政對“終結論”的超越
“終結論”以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遭遇了來自社會主義憲政理論與實踐的顛覆性挑戰。歷史經驗已經證明,在西方之外也可以有不同類型的憲政民主制度。事實是,在資本主義民主憲政之外還存在著一種更高級的制度形式,即社會主義憲政。社會主義憲政并沒有否定憲政的普世價值,也沒有完全拋棄資本主義憲政的某些形式或外殼,但是其實質與內涵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政治、法律學說中,對社會主義憲政民主的闡釋占據了重要地位。當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資本主義民主制度進行批判之時,所提出的關于人權、法治、民主的理論是社會主義憲政的思想源泉。
在對資本主義民主憲政進行批判的基礎上,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社會主義憲政觀。不過馬克思和恩格斯討論最多的還是民主問題。在分析民主的階級性之時,馬克思總結了民主的一般特征,他指出,民主的一般意義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在民主制中,國家制度本身只表現為一種規定,即人民的自我規定。……在民主制中則是人民的國家制度”。“然而民主制獨有的特點是:國家制度在這里畢竟只是人民的一個定在環節”[5](P39-40)。在階級社會中,民主實質上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統治,是實現階級利益的政治形式。所以,“國家內部的一切斗爭——民主政體、貴族政體和君主政體相互之間的斗爭,爭取選舉權的斗爭等等,不過是一些虛幻的形式——普遍的東西一般說來是一種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在這些形式下進行著各個不同階級間的真正的斗爭”[6](P84)。工人階級也應當利用資本主義的民主形式,盡可能地爭取自己的民主權利,構建自己的民主制度。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6](P293)在為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所作的“導言”中,恩格斯再次重申:“爭取普選權、爭取民主,是戰斗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之一”,有效地利用普選權等資本主義議會民主形式,是無產階級爭取民主的新的斗爭方式。[7](P602)由此開創了科學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
在論及人權問題時,馬克思認為,無論作為法定權利還是一種政治主張,人權的產生、實現和發展都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之上,“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5](P12)。社會主義對人權的確認和保障,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的,是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必然要求。不僅如此,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在本質上為人權的保障和發展提供了平等的社會經濟基礎。
社會主義憲政、民主和人權思想在中國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不過就目前而言,社會主義制度本身還比較年輕,而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之上的社會主義憲政尚沒有成熟的歷史經驗。即便如此,社會主義憲政還是表現出了不同于資本主義憲政之處,如具有中國特色的多數民主制、對社會公平和實質正義的追求等。這本身正是對資本主義憲政的一種糾錯與超越,并再次驗證了“終結論”的荒謬。
四、通往社會主義憲政的橋梁
在資本主義憲政理論遭遇重大挑戰以及西方民主政治暴露出固有缺陷之時,通過對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揚棄和超越,社會主義憲政得以建立,并在資本主義內部架起了通往社會主義憲政的橋梁。
1.民主社會主義
民主社會主義產生于巴黎公社之后。出于對巴黎公社失敗的反思,馬克思、恩格斯發展了自己的思想,特別是在《〈法蘭西階級斗爭〉導言》一文中,恩格斯提出一個新的觀點,即隨著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度的發展,無產階級政黨可以在將來的某個時候,于民主國家內部,通過議會民主等途徑,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但是,與此同時,恩格斯并沒有否定暴力革命,并特別聲明無產階級沒有放棄自己的革命權。
民主社會主義同科學社會主義在本質上是相通的,即都是要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世界。但是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存在區別,前者主張和平過渡,后者主張暴力革命。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共產黨宣言》中暴力革命的方法同樣是有局限性的,一種和平的建立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的手段是可以存在的。[7](P595-603)民主社會主義借助資本主義制度內成熟的憲政機制,以和平的方式將工人階級的利益訴求加以表達,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實現,這種方式可以避免暴力革命所帶來的巨大破壞。
當社會開始按照既定的目標有序發展時,就應當以合乎理性的方式來推進民主憲政建設,而不能總是訴諸過激的手段。無論是超越資本主義,還是超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暴力革命都只能是最后的選擇。而且就資本主義民主制度自身來看,它也在不斷地吸收社會主義理念,并通過制度內的變革與調整來實現自我的更新與發展,這些制度內的調整為資本主義憲政向社會主義憲政的邁進提供了契機。民主社會主義正是生長于資本主義內部的社會主義力量,它架起了由資本主義憲政通往社會主義憲政的橋梁。當然,民主社會主義不等于科學社會主義,恰恰是通過對民主社會主義的超越,科學社會主義顯示出了自己的生命力。同樣,通過對民主社會主義的超越,科學社會主義憲政制度才能夠在資本主義憲政基礎上發育成熟。在我國,雖然歷史的發展已經否定了“補課”的可能性,但并不否認從西方憲政的發展歷程中汲取經驗,并建立一種超越民主社會主義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憲政。
2.市場社會主義
經濟民主就其本身而言,并非經濟和民主的簡單結合。有學者將經濟民主解釋為“不過是人們在一定的經濟關系中享有的某種自主的權利,是人處于主人的地位分享經濟利益”[8],并進而強調人在經濟領域的主體地位和自主權利。即便單單從人民主權原則出發,經濟民主也必然要求尊重人的主體性地位。同時,經濟民主是對資本主義“政治平等”與經濟不平等并存現象的糾正,主張將政治民主與平等的原則貫徹于經濟過程。而社會主義尤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出,為經濟民主的發展并超越資本主義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載體。
馬克思也曾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提出批評,但他所批評的不是市場機制本身,而是對資本主義內部的勞動力市場和資本市場的批判。市場社會主義摒棄了存在于上述兩個領域的弊端,并保留了一般商品和服務市場領域。在經濟民主模式下,勞動力市場被消滅,資本市場也被投資的社會化所取代。在這一點上,經濟民主原則發展了馬克思的基本理論。不過市場社會主義并不贊成政府對企業的微觀運行進行直接干預,而是由作為企業主人的勞動者按照自我管理的方式進行自主決策,價格由供求關系決定。[9]
雖然資本主義的市場機制受到批評,市場經濟卻在資本主義體系內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并不斷完善,它同樣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也使得這一機制的弊端不斷暴露,從而提出了糾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是通過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超越而建立起來的,并奠定了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發展的經濟基礎。
3.民生福利原則
雖然存在很多爭議,但是民生福利原則顯然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基本的憲政原則,并為多數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所接受。然而民生福利原則與資本主義多少有些格格不入,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政治與福利原本是分離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工業化社會的到來,壟斷資本的出現、貧富分化的懸殊、市場機制的失靈、社會矛盾的加劇等一系列問題使得國家對經濟社會活動的大規模介入和干預不可避免,西方的憲政理論也隨之發生轉向,民生福利原則開始成為一個基本的憲政原則。很顯然,這種加入了國家干預的資本主義已經不再是純正的自由資本主義,而是一種混合模式,在經濟上被稱為“混合經濟”[10],在政治思想領域也漸漸演化出一種積極憲政理念,政府負有促進公共福祉的義務則成為憲政理念從消極向積極轉變的主要特征。面對社會現實的迫切需求,西方各民主國家的政府紛紛扮演起慈善家的角色。
福利國家的誕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它旨在調整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結構,修復資本主義政治的合法性基礎,并通過調節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來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從而延續資本主義的生命。但是福利原則畢竟與資本主義的本質背道而馳,從其運作結果來看,福利原則正在破壞資本主義的固有邏輯,全方位的社會保障政策消解了勞動者參與勞動市場的心理,瓦解了資本主義的存在基礎。[11]但是這種瓦解并非一種倒退,而是在資本主義母體內發生的對資本主義的揚棄,是社會主義因素在資本主義內部的成長。
五、結語
作為人類共同文明成果的憲政,在其普世價值之外還存在著明顯的地方性特征,不同的本土資源之上生長出的憲政亦會千姿百態。當然,并非所有的憲政模式都是理想的、可以學習或預期的,在標榜憲政民主的資本主義世界,貧窮國家仍然是大多數,即便是被當做楷模存在的憲政國家也同樣面臨著自身無法克服的結構性矛盾。社會主義憲政雖然是新生事物,但已經顯示出較強的生命力與不可替代的優勢。這些都昭示著資本主義憲政必然被逐漸發展成熟的社會主義憲政所替代的歷史前景。
[1] [美]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M].黃勝強,許銘原,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2] [英]斯圖亞特·西姆.德里達與歷史的終結[M].王昆,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3] [美]霍華德·威亞爾達.民主與民主化比較研究[M].榕遠,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1.
[4] 周峰.“歷史終結論”下的中國道路[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05-12(03).
[5]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8] 王慎之.經濟民主論[J].學習與探索,1987(5):23.
[9] 張嘉昕.施韋卡特的經濟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評析[J].科學社會主義,2011(2):143.
[10] Case,Karl E,Fair,Ray C.Principles of Macroeconomics,Globalization[M].Prentice Hall,2004.
[11] 郭忠華.資本主義困境與福利國家矛盾的雙重變奏[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