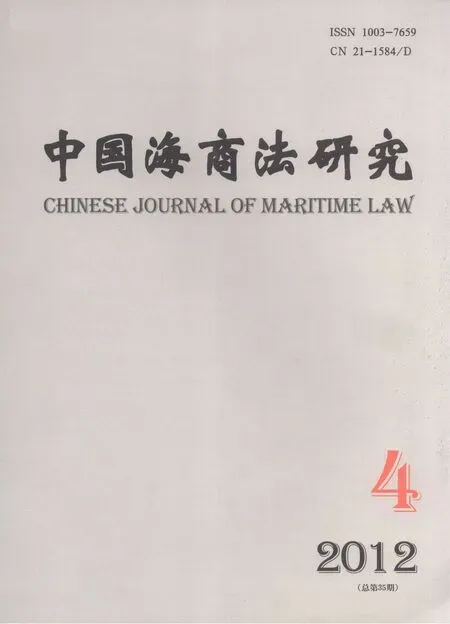海洋公共資源損失的索賠主體研究
邵 琦
(京衡律師集團舟山事務所,浙江 舟山 316000)
隨著能源需求不斷增加,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國。自2008年起中國年進口石油逾2億噸,2010年中國進口石油達2.39億噸,目前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已超過50%。據統計,1988年到1997年10年間,在中國海域共發生了溢油事故1 856起,平均每年186起,其中溢油50噸以上的事故74起,溢油量達3.7萬噸;1998年到2008年10年間,中國沿海發生了718起船舶溢油事故,溢油總量達11 749噸,平均每年發生事故71.8起,其中溢油50噸以上的事故34起,溢油量達10 327噸。由于中國石油進口數量將會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而進口石油90%以上是通過海運方式完成的,油污事故頻發,海洋環境受到威脅,亟待加大預防和保護力度。[1]
一、海洋公共資源損失的權利主體和索賠主體
所謂海洋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的民事權利主體,是指參加海洋環境污染損害賠償民事法律關系,對海洋環境污染損害賠償享有權利的人。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域使用管理法》均十分明確地規定“海域屬于國家所有”,因此這一民事權利主體又可分為一般主體和特殊主體,一般主體是受到此侵權行為侵害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社會組織,特殊主體是國家。然而當海洋公共資源遭受損失時,不可能由國家直接出面進行民事索賠,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簡稱《海洋環境保護法》)規定:“對破壞海洋生態、海洋水產資源、海洋保護區,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的,由依照本法規定行使海洋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代表國家對責任者提出損害賠償要求。”但是,對污染造成的海洋公共資源損失,究竟應由哪個部門代表國家提出索賠,法律規定尚不夠明確,而在司法實踐中,代表國家提出漁業資源損失的行政機關有漁業主管機關、海洋主管機關、環保主管機關,甚至還有漁業協會。僅就漁業主管機關而言,充當民事主體的既有省、市、縣(區)各級機關,又有海區漁政局、省級漁政執法機構。可見,對索賠主體的界定隨意而混亂。
二、中國與海洋環境污染損害賠償有關的現行法律規范
目前,在海洋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的法律適用問題上,中國已形成一個基本的法律體系,對海洋環境污染的責任主體、承擔法律責任的范圍、方式以及行政主管機關對于海洋環境污染事件處理的職能等都作出了規定。
(一)國內相關立法
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簡稱《民法通則》,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第124條規定,違反國家保護環境防止污染的規定,污染環境造成他人損害,應當依法承擔民事責任。
第二,《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第65條、第68條規定,因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污染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因第三人的過錯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被侵權人可以向污染者請求賠償,也可以向第三人請求賠償。污染者賠償后,有權向第三人追償。
第三,《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簡稱《環境保護法》,1989年12月26日起施行)第41條規定,造成環境污染危害的,有責任排除危害,并對直接受到損害的單位或者個人賠償損失。賠償責任和賠償金額的糾紛,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由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或者其他依照本法律規定行使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處理;當事人對處理決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當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
第四,《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簡稱《海商法》,1991年7月1日起施行)第十一章對船舶油污損害的賠償責任限制問題作了相應規定。
第五,《海洋環境保護法》(2000年4月1日起施行)第90條規定,造成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的責任者,應當排除危害,并賠償損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過失,造成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擔賠償責任。對破壞海洋生態、海洋水產資源、海洋保護區,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的,由依照本法規定行使海洋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代表國家對責任者提出損害賠償要求。
第六,《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簡稱《防污條例》,2010年3月31日起施行)第50條規定,造成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的責任者,應當排除危害,并賠償損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過失,造成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擔賠償責任。
第七,《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簡稱《最高院會議紀要》,法發[2005]26號)中“關于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糾紛案件”一節,對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糾紛案件的法律適用、索賠主體、索賠范圍等內容作了規定。
第八,《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2011年7月1日起施行)。該解釋對船舶油污損害賠償案件從適用范圍、案件管轄、油污責任、賠償范圍與損失認定、船舶優先權、油污責任限制及債權登記與受償、油污索賠代位受償權等方面作了詳細的規定。
(二)中國參加的國際條約
第一,《〈1969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1992年議定書》,也稱《1992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簡稱1992 CLC),中國于1999年1月5日加入該公約,2000年1月5日該公約對中國生效。1992 CLC第1條第6款規定,“污染損害”系指:(a)油類從船上溢出或排放引起的污染在該船之外造成的滅失或損害,不論此種溢出或排放發生于何處;但是,對環境損害(不包括此種損害的利潤損失)的賠償,應限于已實際采取或將要采取的合理恢復措施的費用;(b)預防措施的費用及預防措施造成的進一步滅失或損害。第3條第1款規定,除本條第2款和第3款規定者外,在事故發生時的船舶所有人,或者,如果該事故系由一系列事件構成,則第一個此種事件發生時的船舶所有人,應對船舶因該事故而造成的任何污染損害負責。
第二,《2001年船舶燃油污染損害民事責任公約》(簡稱《燃油公約》),中國于2008年12月9日加入該條約,2009年3月9日該公約對中國生效。《燃油公約》第1條第9項規定,“污染損害”系指:(a)由任何地點發生的船舶燃油逸出或排放引起的污染在該船之外造成的損失或損害,但是對環境損害的賠償(不包括此種損害的利潤損失在內),應限于實際采取或將要采取的合理恢復措施的費用;(b)預防措施的費用和由預防措施造成的進一步損失或損害。
《民法通則》第14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規定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但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海商法》第268條作了同樣的規定。《最高院會議紀要》第141條進一步明確,中國加入的1992 CLC適用于具有涉外因素的締約國海洋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糾紛,包括航行于國際航線的中國船舶在中國海域造成的油污損害賠償糾紛。非航行于國際航線的中國船舶在中國海域造成的油污損害賠償糾紛不適用該公約的規定。
研究上述法律規范后可以發現,中國現行法律下,海洋環境污染損害一般民事主體權利時,其民事權利主體是明確的,即應該是權利受到損害的相對人。但是對海洋環境污染造成海洋公共資源損害的,中國現行法律并未明確應由哪個部門作為索賠主體代表國家行使索賠權,即使有所涉及,也是非常模糊的。例如:《海洋環境保護法》第90條第2款和《最高院會議紀要》第146條規定中所謂“行使海洋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涉及多個行政機關,針對個案究竟該由哪個機關代表國家就海洋環境污染造成的海洋環境損失向油污責任人提起訴訟并不明確,并因此造成司法實踐中的混亂。
三、司法實踐中對于海洋公共資源損失索賠主體的認定
在中國海事法院已經審理終結的諸多海洋環境損害賠償案件中,代表國家就海洋公共資源損失行使索賠權的主體繁多。
在1999年“廣東省漁政海監檢查總隊湛江支隊訴東亞油船有限公司海洋環境污染損害賠償上訴案”①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1999)粵高法經二終字第327號民事判決書。中,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認定,廣東省漁政海監檢查總隊湛江支隊是依法成立的行使國家海洋漁業管理權的行政機構,有自己的名稱、組織機構、場所及獨立經費,是保護湛江港附近海域漁業資源的主管機關,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因而是適格的訴訟當事人。在其管轄區域內的海洋因污染事故造成國家損失時,有權代表國家要求責任者賠償損失。因此,漁政支隊以自己的名義提起訴訟符合法律規定。
在2007年“天津市漢沽區水產局訴天津國際游樂港有限公司海上施工致漁業資源損失賠償糾紛案”②參見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2007)津高民四終字第124號民事判決書。中,法院認定,根據《海洋環境保護法》第5條第4款的規定,漢沽區水產局作為涉案海域的漁業行政主管部門,行使海洋環境監督管理職權,負責保護漁業水域生態環境工作,依法負有該海域的天然漁業資源保護職責。本案中,游樂港公司在該海域開發的“基輔號航母工程”項目給天然漁業資源造成損害是不爭的事實。漢沽區水產局作為該海域的漁業行政主管部門所作的調查及天津市漁業生態環境監測中心出具的評估報告,確定了由于游樂港公司的施工項目給漢沽區八卦灘及以南水域的天然漁業資源造成損害及具體損失。根據《海洋環境保護法》第90條第2款的規定,對于該項損失,漢沽區水產局有權向責任者游樂港公司行使索賠權,提出賠償要求。
在2002年“‘塔斯曼海’油輪海洋環境污染損害賠償案”中,國家海洋局授權天津市海洋局代表國家提起海洋生態損失索賠,天津市漁政漁港監督管理處代表國家提起漁業資源損失索賠、天津市塘沽區大沽漁民協會等多家漁民協會代表漁民就漁業資源遭受的損失提起海洋捕撈損失索賠,最終都獲得天津海事法院的支持。
在2003年“Sekwang Shipping Co.,Ltd.所屬‘大勇’輪(M.V.‘DAE MYONG’)船載苯乙烯泄漏案”中,上海市環境保護局、農業部東海區漁政漁港監督管理局、上海海事局作為索賠主體對Sekwang Shipping Co.,Ltd.申請設立海事賠償責任限制基金向上海海事法院提出異議,法院對各個主體的資格均予以認可。
在1999年“珠海市環境保護局、廣東省海洋與水產廳訴臺州東海海運有限公司、中國船舶燃料供應福建有限公司‘閩燃供2’輪油污損害賠償糾紛案”中,珠海市環境保護局作為環境保護的主管機關,廣東省海洋與水產廳作為漁業主管機關,分別就污染造成的環境和漁業資源損失向責任人提起索賠,法院對兩個主體的資格均予以認可。
在1996年“‘南航油2’輪和‘薌油11’輪碰撞造成油污損害賠償案”中,廣東省海洋與水產廳、番禺市新盈鎮紅港村民委員會、東莞鎮港灣管理區、東莞市新灣鎮新灣管理區等單位,委托廣東省漁業協會向海事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南海航運公司和漳州輪船公司賠償因油污事故造成的漁業資源和漁業生產損失,法院受理了此案并對原告的扣船申請予以支持。
通過上述案例可以發現,當油類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質污染海洋環境事件發生后,代表國家對海洋環境損失主張權利的有省、市、區各級海洋局(水產局),有各級漁政監督部門,有環境保護局、海事局,甚至還有漁業協會。正是由于司法實踐的導向作用,現實中不同行政機關之間甚至同一機關上下級之間常常發生索賠權爭議,給正常的索賠帶來許多負面影響。因此,規范海洋公共資源損害的索賠主體已刻不容緩。
四、海洋公共資源損害的民事索賠主體確定
在海洋環境資源遭受損失時,其民事權利主體毫無疑問應該是國家,因中國對行政機關行政職權的劃分實行分層決策、分類管理和屬地管轄相結合的原則,就公共資源的損失不可能直接由國家來主張權利,所以立法中也都是規定由相關行政機關代表國家行使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49條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可以作為民事訴訟的當事人。《民法通則》第50條規定,有獨立經費的機關從成立之日起,具有法人資格。而《海洋環境保護法》第90條第2款規定,對破壞海洋生態、海洋水產資源、海洋保護區,給國家造成重大損失的,由依照本法規定行使海洋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代表國家對責任者提出損害賠償要求。因此,行政機關作為民事主體參與海洋環境損害賠償的法律關系,主張索賠權,無論是程序法還是實體法,都有明確的依據。
(一)根據行政權限的橫向劃分,結合受損害的海洋公共資源的類型等因素,確定海洋環境污染案件的行政主管機關
不同的行政機關被法律賦予不同的行政職權,而作為行政職權三要素之一的行政權限,是法律賦予行政主體行使職權的范圍和界限,要求行政機關在行使職權時應嚴格遵守,一旦超越該“限度”,便構成行政越權,視為無效。[2]確定海洋環境污染的行政主管機關涉及行政機關的橫向權限劃分,所謂橫向權限,是指無隸屬關系的行政主體之間權力行使范圍的劃分,而這種權限又可分為區域管轄權限和公務管轄權限,區域管轄是指“行政主體系統中確定同級行政主體之間首次處理行政事務的分工和權限”;公務管轄是指“不同性質的行政事務歸屬不同的行政機關管轄”。[3]由于行政機關充當民事主體僅是個例,通常情況下行政機關是作為行政主體履行職能,中國有關海洋環境保護的法律和涉及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的行政法規、規章,更多地也只是規定行政機關對海洋環境的行政管理職能和權限劃分,而對其民事權利鮮有涉及,因此,海洋環境污染事故發生后,需要由行政機關代表國家對責任人提起索賠時,只能根據法律對行政機關橫向職權的劃分來確定其對應的民事權利范圍。
根據《海洋環境保護法》第5條,國務院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負責全國防治陸源污染物和海岸工程建設項目對海洋污染損害的環境保護工作;國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門負責全國防治海洋工程建設項目和海洋傾倒廢棄物對海洋污染損害的環境保護工作;國家海事行政主管部門負責港區水域內外非漁業、非軍事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的監督管理;國家漁業行政主管部門負責漁港水域內外漁業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的監督管理,負責保護漁業水域生態環境工作。
這一規定首先以污染的來源或者說污染的種類對各行政機關的行政職能進行劃分,將“陸源污染物和海岸工程建設項目對海洋污染損害”歸為第一類,將“海洋工程建設項目和海洋傾倒廢棄物對海洋污染損害”歸為第二類,將“船舶污染海洋環境”歸為第三類。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治海岸工程建設項目污染損害海洋環境管理條例》第2條,“海岸工程”是指位于海岸或者與海岸連接,工程主體位于海岸線向陸一側,對海洋環境產生影響的新建、改建、擴建工程項目。根據《防治海洋工程建設項目污染損害海洋環境管理條例》第3條,“海洋工程”是指以開發、利用、保護、恢復海洋資源為目的,并且工程主體位于海岸線向海一側的新建、改建、擴建工程。因此,《海洋環境保護法》排除了環保主管部門對船舶污染事故的行政管轄權,也排除了海洋行政主管部門的管轄權,而對第三類“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的管轄權又按船舶用途和水域功能進行劃分,由國家海事行政主管部門、國家漁業行政主管部門等進行管轄。2010年3月31日,國務院又根據《海洋環境保護法》頒布實施了《防污條例》,并規定海事管理機構具體負責防治船舶及其有關作業活動污染海洋環境的監督管理;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漁業主管部門負責處理漁港水域內外漁業船舶污染事故。據此,海事管理機構職能是:負責港區水域內非軍事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的監督管理工作,非軍事船舶是指漁船、貨船、客船;負責港區水域外非漁業、非軍事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的監督管理工作,非漁業、非軍事船舶是指貨船和客船。漁業主管部門職能是:負責漁港水域內非軍事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的監督管理工作,同樣,非軍事船舶是指漁船、貨船、客船;負責漁港水域外的漁業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的監督管理工作;負責所有漁業水域的生態環境保護工作。
盡管上述職能分工是明確的,但由于《海洋環境保護法》第5條中使用的“港區水域”和“漁港水域”的概念在現實中往往是重疊的,根本無法予以區分,從而造成海洋環境污染個案中,產生類似行政職權的非排他性,導致民事索賠主體重疊或者缺位。行政法理論中的行政管轄權排他性是指任何一項行政事務只能由一個行政主體行使管轄權,從而確保行政主體行使行政職權的有效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中對同一行政違法行為,行政機關不得給予兩次以上的行政處罰的規定正是基于這樣的法理基礎。[4]
發生海洋油污事故后,根據《海洋溢油生態損害評估技術導則》(HY/T095-2007,國家海洋局2007年4月發布,2007年5月1日起施行)可以進行評估的海洋環境損失,包括溢油造成的海洋生態直接損失、生境修復費、受損生物種群恢復費和調查評估費,海洋生態直接損失又包括海洋生態服務功能損失和海洋環境容量損失兩部分。而《最高院會議紀要》第150條規定的油污損害賠償范圍包括因海洋環境污染造成的漁業資源和海洋資源損失,這種損失應限于已實際采取或將要采取的合理恢復措施的費用。漁業資源是指水域中天然隱蔽和在一定經濟、技術條件下可供采捕的各種經濟動植物的種類和數量,以及適于養殖業的水域、灘涂等自然條件的總稱。[5]而海洋資源是指海洋空間所存在的一切資源,是海洋中各種類型資源的一種總的稱呼,屬于復合型的資源系統。根據職能劃分和專業優勢,毫無疑問,漁業資源的主管機關和損失的民事索賠權應歸屬漁業行政主管部門,而除了漁業資源以外其他海洋資源損失的主管機關和民事索賠權應歸屬海事管理機關。
因此,在海洋環境污染事故中,在以行政機關管轄權限劃分為依據的前提下,還必須結合行政機關的專業特長、受損害公共資源的類型等綜合因素,決定民事索賠權的歸屬。
(二)根據事故發生地點所在的行政區域,確定應由哪一級行政部門具體行使民事索賠權
“行政主體的權限劃分,可以分為橫向分權和縱向分權。由于行政權限的不同,橫向分權的各行政主體的權限,一般都比較明確,但就縱向權限而言,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行政主體的縱向權限沒有明確的劃分。有關法律也只有原則性規定,以致于下級越權行使上級的職權,特別是上級越權行使下級的權限十分突出,且得不到有效解決,嚴重地影響了行政系統高效、迅速地運轉。”[6]于是,在按照行政機關橫向權限的劃分確定海洋環境污染索賠應歸口哪個行政部門管轄后,很難依據行政機關縱向行政權限的劃分方法來認定究竟該由哪一級行政機關充當民事索賠主體。如果根據行政主體的縱向權限逐級遞減的方法確定應由哪級行政機關作為民事主體,不但會嚴重削弱基層行政機關的管理職能,而且會大大降低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和效率。
在海洋環境污染事件發生后,事故應急處理和事故后果補救一般都是由承擔該區域行政管理職能的行政機關組織實施,由此產生的費用和損失應該由組織實施者代表國家提出民事索賠,這樣才能做到責、權、利的高度統一,充分提高地方各級行政機關處理突發事件的積極性和效率。所以,事故發生在哪級政府管轄的行政區域內,就應由哪級政府的行政主管機關代表國家行使民事索賠權。《海洋環境保護法》第5條規定,沿海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使海洋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的職責,可以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本法及國務院有關規定確定;《防污條例》第4條、第76條已明確海事管理機構和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漁業主管部門保護海洋生態環境的職能。這些規定為縣級及縣級以上政府主管機關代表國家對公共環境資源損害事件提起索賠提供了法律依據。因此,應該通過司法解釋進一步明確,對于某個海洋污染事故公共資源損失的索賠,如污染海域在縣(區)行政區劃內的,由當地縣(區)級地方人民政府的行政主管部門代表國家向責任人提出索賠;如污染海域跨縣(區)行政區域的,則由上一級市人民政府的行政主管部門進行索賠;跨市的,則由省級人民政府的行政主管部門進行索賠;跨省則由國家行政主管部門或其指定的機關進行索賠。同時允許跨區域的行政機關之間協商確定由一方作為索賠主體。
美國《1990年油污法》規定,對于油污損害自然資源,屬于聯邦或者由聯邦管理、控制或者附屬于聯邦的自然資源,向聯邦政府承擔責任;屬于州或者由州管理、控制,或者附屬于州的自然資源向州政府承擔責任;屬于印第安部落或者由印第安部落管理、控制,或者附屬于印第安部落的自然資源向印第安部落承擔責任。因此,美國也是以行政管理權的級別劃分為依據確定自然資源損害的索賠主體。
基于以上論述,對于“ZOORIK”輪油污泄漏事故造成的海洋漁業資源損害,嵊泗縣海洋與漁業局作為縣級負責漁業行政主管部門,應是代表國家對轄區海域內發生的污染事故進行索賠的最適格的主體。而東海區漁政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漁政漁港監督管理局的派出機構,適宜在東海海域發生跨省的海洋污染事故時,代表國家行使漁業資源損失的民事索賠權。
(三)引入公益訴訟制度,作為對海洋公共資源損失索賠機制的補充
公益訴訟制度是指對違反法律、法規,侵犯社會公共利益和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的行為,任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都可以根據法律的授權,向人民法院起訴,要求違法者承擔法律責任的制度。
由于海洋環境污染事件比較復雜,索賠費時耗力,而索賠所得嚴格上應上繳國庫,雖然不同主體爭搶索賠權的情況時有發生,但無人代表國家主張權利的現象也不是個例。在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日趨嚴重的背景下,有必要引入公益訴訟制度以加強對環境資源的保護力度。目前有些地方已開展環境損害公益訴訟的司法實踐,如無錫市中級法院和市檢察院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的試行規定》;云南省昆明市中級法院、市檢察院、市公安局、市環保局聯合發布了《關于建立環境保護執法協調機制的實施意見》,規定環境公益訴訟的案件由檢察機關、環保部門和有關社會團體向法院提起訴訟。[7]但筆者以為,應允許更多的主體參與公益訴訟。《環境保護法》第6條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并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據此,法律應當賦予國家機關、有關組織、公民個人以環境公益訴權。當然,為了防止濫用訴權,對公益訴訟應建立嚴格的司法審查制度和前置程序,即公益訴訟必須完全出于維護公共利益的目的,同時必須明確,只有在負有法定義務的行政機關怠于履行其義務時,才能提起公益訴訟。
五、結語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在幾易其稿后于2011年5月公布,但非常遺憾的是,該解釋仍未明確公共資源的索賠主體問題。筆者以為,及早解決油污損害賠償的索賠主體問題,對順利解決實務中發生的索賠主體爭議,規范國家索賠行為,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1]劉貴祥.正確審理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糾紛案件不斷加快海洋環境司法保護工作步伐[N].人民法院報,2011-06-15(2).LIU Gui-xiang.Corrretly hearing case of compensation for oil pollution from ships,speeding up marine environment juridical protection[N].People’s Court Daily,2011-06-15(2).(in Chinese)
[2]周湘偉.行政權法定與越權無效——略論行政執法權的行政法律制約[J].湖南行政學院學報,2008(7):39-42.ZHOU Xiang-wei.Legal authority and invalid overstepping of right——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restrictions of administrative law over the right of law enforcement[J].Journal of Hunan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2008(7):39-42.(in Chinese)
[3]肖登輝.行政管轄略論[J].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24(9):45-49.XIAO Deng-hui.Study on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J].Journal of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09,24(9):45-49.(in Chinese)
[4]章劍生.行政管轄制度探索[J].法學,2002(7):28-32.ZHANG Jian-sheng.Delving into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J].Legal Science,2002(7):28-32.(in Chinese)
[5]孫憲忠.中國漁業權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10.SUN Xian-zhong.Research on fishery right of China[M].Beijing:Law Press,2006:110.(in Chinese)
[6]郭秋麗,蘇福.行政主體縱向權限法制化芻議[J].行政論壇,2001(6):47-49.GUO Qiu-li,SU Fu.Small talk on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vertical power for administrative subject[J].Administrative Tribune,2001(6):47-49.(in Chinese)
[7]宗荷.什么是環境公益訴訟[N].中國環境報,2009-03-31(8).ZONG He.What is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N].China Environmental News,2009-03-31(8).(in 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