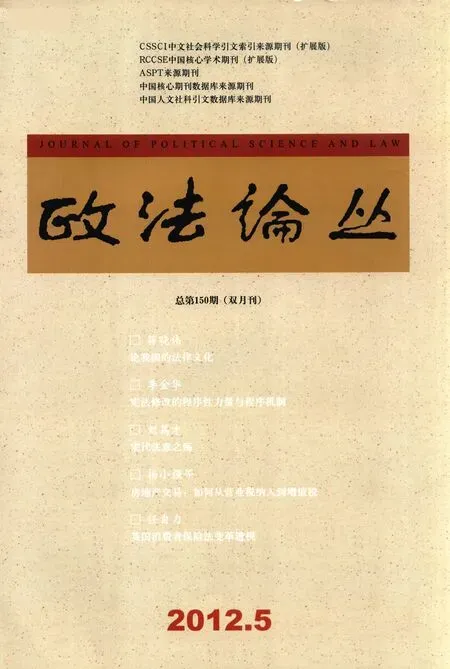中西方選舉傳統的分歧、沖突與融合
周葉中朱道坤
(武漢大學法學院,湖北武漢430072)
中國古代就有所謂的選舉制度,但那時候的“選舉”,指的是某種選賢任能的人事制度,而非現代意義上的民主選舉。古代意義的選舉通常包括察舉和科舉兩個基本類型,在這種場景之下,選舉等同于選才,這一特有傳統在相當程度上塑造了傳統中國的文化秉性和社會結構。
一、選才與選舉
中國古代選舉在形式上體現為一種選賢任能的人事制度,但其實質卻在于構建皇權與地方勢力進行權力競爭的平臺。
(一)選賢任能:中國式選舉的核心思想
中國古代選舉制度的核心在于選賢任能,“賢”是道德高尚,“能”是才華卓越。在儒家學者看來,君主要治理好社會,就必須選拔賢能之人,否則無以達到善治。這種選賢任能的思想在中國的人事制度中一以貫之,形成了中國社會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傳統。進而言之,選賢任能的問題,在中國古代甚至可以上升為治國安邦的首要問題。早在先秦時期,孔子就曾從兩個不同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過解釋:(1)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論語·為政)(2)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于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論語·顏淵十二)
漢代的董仲舒則進一步闡發了孔子關于人才選拔的觀點。認為“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為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為剛也;考實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是故天執其道,為萬物主,君執其常,為一國主。天不可以不剛,主不可以不堅。”他進而認為這是順應天道的做法。在這種思想引導下,中國古代政治逐漸產生了一種以人才為本的價值理念。
以人才為本的理念在古代政治家的治國實踐中也極為突出。諸葛亮就認為:“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唐太宗也指出,“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在這些名臣、皇帝眼中,用人的成敗,決不僅僅是個人事問題,更在相當程度上成為國家興亡的主要原因,這在中國古代是一種極為常見且非常合乎傳統的思路。
(二)從察舉到科舉:中國式選舉的發展路徑
中國最早的人事制度是“世卿世祿制”,它適應的是一種封建制的國家結構形式。在先秦時期,天子將土地分封給諸侯、卿大夫,并以此為基礎建立地方政權,各諸侯、卿大夫乃是土地的主人,因此以世襲的方式進行官爵的授受,其官爵與土地相聯系,也隨著土地進行世襲。顯然這一制度不可能起到選賢任能的作用,但它卻適應了當時的政治形勢。
而在封建制衰微、郡縣制興盛的漢代,產生了一種被稱為“鄉舉里選”的人事制度,即由地方官員察選人才,推薦給中央,并由中央考核任用。這使官僚體系中不再充斥一個個家族,造成了政治體系的刷新,進而產生錢穆所稱的“讀書人的政府,或稱士人政府”。[1]P13漢代察舉制是對選賢任能思想的貫徹,在漢朝初期也確實發揮了較好的作用。然而,掌握察舉權的地方官員、士紳有極大的裁量權,他們極易利用權力徇私舞弊,從而出現“舉孝廉、父別居;舉秀才,不知書;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的惡劣情形。東漢末年,察舉制度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原先掌握于地方官紳由地方官紳控制的察舉權轉移到中央政府手中,形成所謂“九品中正制”。其基本內容是:由中央政府選擇現任中央機構官吏出任州、郡的“中正”,州設大中正,郡設小中正。這些大、小中正官的職責是將轄區內的人才品評為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以供政府擇選任用。[2]P93這一制度避免了地方選人不當的問題,在其發展初期起到了部分作用。但隨著門閥大族的迅速發展,這些門閥大族迅速占據所有中正官職位,這一制度反而加劇了門閥對于人事的控制,產生了我們所熟知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與門閥大族之間存在著極為密切的聯系,九品中正制成全了門閥勢族對政權在人事上的控制,而門閥勢族則更加塑造了這一制度的頑強生命力。
九品中正制實施約四百年后,隋朝統一南北,中國又成為一個大一統的帝國,皇權因此再一次變得空前強盛。隋文帝遂挾著這種威勢,取消“九品中正制”,代之以考試為核心的科舉制度,用統一考試的方法選取人才。唐朝沿襲這一制度,并將其發揚光大。科舉替代察舉(包括九品中正制),至少有三個重要意義:(1)科舉替代察舉制度的過程,體現的是中央權力對地方選官的控制。(2)科舉替代察舉,體現的是社會階層流動的進一步加強。“維持社會流動,對皇權更為有利。因為這不但保證了官僚的素質與更新,而且能夠抑制門閥化、貴族化與封建化傾向可能對皇帝權勢的過分分奪。”[3]P289(3)科舉制度維系了中國基本的社會公平,它提供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一個溝通橋梁。
然科舉制度亦并非包治百病,其弊端也是顯為易見。特別是到明清兩代,以八股文為考核內容的科舉制度,更是產生了嚴重的危害:(1)科舉制度無法選拔真正的人才,反而造就腐儒,敗壞斯文。顧炎武先生甚至將科舉與焚書坑儒相提并論:“秦以焚書而‘五經’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經’亡。今之為科舉之學者,大率皆帖括熟爛之言,不能通知大義者也。”[4](2)在科舉制度之下,官員任職不得不采用地區回避政策,這使得地方官員皆出自外鄉,對當地風土人情全不了解。“今之選人,動涉數千里,風士不諳,語音不曉……。”[5](3)在科舉制度之下,國家權力結構頭重腳輕。然而,“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終于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興亡之途罔不由此。”[6](4)在科舉制度之下,無法避免胥吏為害。官員在入仕前投身科舉,沒有治政之能,入仕后又缺乏對當地風土人情的認知,極易被胥吏架空。正是由于這些弊端,對科舉制度進行改革的記載就一直不絕于史。然而,雖然歷朝歷代都有人提及科舉改革,也有人對此付諸實踐,但總體說來,這些實踐彎彎折折地想要回到漢代舊制,卻總是窩窩囊囊地走回老路。
(三)政道問題的治道解決:中國式選舉的本質
在中國歷史上,人們費盡心思地在察舉和科舉之間搖來擺去,卻又脫離不開這兩個選擇的藩籬,更加找不到仕官制度的救贖之道。這種現象,當可歸因于中國政治學說中“有治道無政道”的傳統。在牟宗三先生看來,政道是國家政權的歸屬問題,治道則是政治活動的治理問題。“中國在以往只有治道而無政道,亦如只有吏治,而無政治。吏治相應治道而言,政治相應政道而言。”[7]P1這個學術問題的出現,與中國的政治傳統密切關聯。“三代以后之政體,皆君權最重之時代也,皆偽朝也;三代以后之學術,皆文禍最重之時代也,皆偽學也。”[8]P735“君權最重”,即意味著君主毋庸置疑地把持政權,政道問題也因此無從探討了。
郡縣制下“君權最重”,它意味著地方勢力缺乏獨立與君主權力的合法性。特別是在秦朝統一天下之后,中國不可逆轉地成為一個郡縣制國家,在這一制度影響下的中國政治,整體上可歸納為皇權統治下的官僚政治。在郡縣制度的總體框架下,地方的門閥、勢族雖然常有勢力,卻無法獲得可供其封疆裂土的合法建制權力。這也就構成這個政道問題的中國面貌——天下為一人之天下,這人便封官許爵,派人牧守四方,并以此構成政道之基礎。然而,君權專制下的地方勢力又將何以自處?為了滲透進皇權政治這個框架,地方勢力唯有透過干涉人事安排來搶奪政治上可能有的些微優勢;皇權勢力顯然也不會坐以待斃,而需要從門閥以外的人群中選拔官員,從而維護皇權。因此,當皇權式微而門閥勢強之時(如魏晉南北朝),會產生九品中正制這樣嚴重依賴門閥勢族的制度,當皇權隆盛而門閥衰敗之時(如隋、唐、宋、明、清),就會產生科舉制這樣高度依附皇權勢力的制度。
正因如此,在皇權政治的“政道背景”下,以用人為本的“治道思想”顯得更有市場。門閥勢族和君上大權圍繞著“吏治”這個關鍵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論證和博弈。這個論證邏輯造成如下后果:當政治家和學者們發現科舉存在的諸多弊端時,卻找不到一個更合適的替代路徑。雖然從這一思路出發,古代中國人早已將如何選賢任能,如何監察弊端,如何踐行教化的問題研究到極致,但這畢竟存在視域上的局限性。中國古人囿于傳統政治學說的治道路徑,無從越軌。及至近代,中國面臨亙古未有之變局,以及西方思潮之劇烈突襲,人們方才發覺議院、民權之說,似乎是一個別樣的路徑。
二、事權與選舉
與中國古代的情形類似,在西方政治發展過程中,王室與貴族之間的權力競爭也非常明顯。然而,在西方封建制度下,君主的權力并非那么至高無上,因此,二者在形式上有著顯著不同:中國的皇權與門閥勢族之間的競爭,集中于人才選拔權的爭奪;而在西方,王室與貴族之間的權力競爭,則體現為事權的爭奪。此時,選舉的主要意義更多地在于確定由哪個階層來決定事務,而非由誰來擔任官職。
(一)保護民主的抽簽制
古希臘是西方政治傳統的起源地。古希臘時期的民主制度,深刻影響了此后的西方政治思想。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古希臘的多數城邦進入了所謂民主時代。此時,抽簽制成為一種主流的人事制度,并實際成為平民階段爭奪事權的一種方式。
古希臘當時的主要政治共同體是城邦。作為一個政治團體,城邦比東方的許多國家要小得多,人口也少得多,這就使城邦能夠形成自治的傳統,并使那些自由公民(大約占人口總數的1/20)有可能進行直接的政治參與。公元前500年左右,經過梭倫和克里斯提尼等人的改革后,古希臘的主要城邦雅典開始實行以民眾大會為核心的直接民主制度。雅典為此通過設立如下三種制度,維持民主制,避免僭主制或寡頭制:(1)公民大會制度。根據這一制度安排,公民大會是政治的核心,獲得完整公民權的人都可以自由進入公民大會參政。(2)為保護民主政治,雅典還設立了陶片放逐法,以防止僭主政治或寡頭政治再起。根據這一制度,每當年初召開公民大會時,如大會認為有必要實行一次放逐公民的表決,便再行召開表決的大會,會上公民將他認為可能危害城邦民主制度的人(所謂“危險人物”)的姓名,書寫在陶片上并投入陶罐中,只有達到六千陶片才能通過一件放逐案。[9]P63(3)雅典還用抽簽的方法設立一個由500人組成的議事會。它由從每個部族里面抽簽選出的部分年滿30歲以上的公民組成,是主要的常設行政機關,代表所有部族。500人議事會的職責包括:監督所有官員,針對議案對公民大會提供資訊及建議,內外政策的執行與日常事務的決策。[10]500人議事會的任期為一年,不得連任。
為了維護雅典的直接民主,抽簽制即成為其唯一選擇。因為一旦開始競選,就極難有辦法避免貴族利用其財產、權勢來控制選舉,而一人一年的短暫任期,則可以避免任何人運用其權勢獲得更多的利益,因此,平民的統治在這個時候成為制度的必然結果。
(二)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等級選舉制
公元前4世紀后半期,馬其頓征服古希臘,古希臘民主制度隨之湮滅。公元476年,日耳曼人摧毀了西羅馬帝國的古典文明傳統,重新塑造了西歐的政治生活面貌。中世紀的歐洲,基于其土地制度而形成一種封建體制,社會從而分化為復雜的等級并形成相應秩序。
中世紀的歐洲封建制和中國先秦時期的封建制有著類似之處,其核心在于可供建制的貴族領地、可供統治的人民——這正如孟子所說,“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盡心下)在這種封建制下,爵位和封地都是可以繼承的,并因此維持貴族的傳承關系,地方諸侯與中央之間存在一定的獨立性。地方諸侯是地方土地的所有者,而不是王室的官員,他們只須向王室效忠并繳納稅貢,從而獲得王室的庇護,而無須應付王室的無盡索取。地方諸侯能夠以相對獨立的身份面對國王,并進而主張自身的權利。
在封建世襲制的社會基礎下,西方中世紀的部分國家實行等級代表制,這種代表制的代表性基礎在于,明確承認階級差異,以及特權階層的存在,反映了西方貴族制下代表制的獨特階級屬性。1295年11月13日,英王愛德華一世為征收稅款召集議會。奉詔出席議會的有:2位大主教、19位主教、48位大修道院院長、7位伯爵、41位男爵、每個主教管區的2位教士代表、每個郡的2位騎士、每個市的2位市民、每個自治市的2位市民,等等,總計約400人。其中騎士、市民由郡守主持,在各郡、各市中選舉產生。[11]P1法國國王則在1302年召開第一次三級會議,其目的在于對抗教皇,法國三級會議的第一等級是高級教士,第二等級是貴族,第三等級是市民代表。
(三)維護資產階級事權的階級代表制
毫無疑問,等級會議仍然是建立在世襲制基礎上的封建議會制度。而世襲制有其明顯的弊端:一方面,政府中的部分人基于出身獲得官職,本身卻可能不具備施政的能力;另一方面,世襲制造成社會層級的固化,不利于社會秩序的穩定。等級會議制度的不平等性,在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遭到了革命者的猛烈抨擊。1788年,法國的西耶斯發表了他的名篇《論特權》,并于次年初出版《第三等級是什么?》,這可以說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戰斗檄文。在文章中,西耶斯對法國的等級會議制度進行了嚴厲駁斥,認為“所有特權都是不公正的,令人憎惡的,與整個政治社會的最高目的背道而馳”,更主張第三等級就是一切,就是整個國家,[12]P3要求第三等級獲得其應得的政治地位。
1789年5月5日,法國三級會議開幕。6月17日,該會議以第三等級代表為主通過決議,改稱為“國民議會”,7月9日,又改稱為“制憲議會”。[13]P70第三等級拋開前兩個等級獨立行動,破壞了等級代表制,拉開了大革命的序幕,并逐漸影響到整個西方社會。但法國大革命帶來的并非民主下的秩序,而是暴亂和以民主為名的殺戮。直到代議制度發展起來,并成為一種可行的制度選擇,民主制度才真正洗脫了“暴民主政”的血色印記。這一時期,代議制度成為民主的制度選擇,民主開始變得理性、溫馴,并且進一步具備可操作性。正如托馬斯·潘恩所言,“代議制以社會和文明作為基礎;以自然、理性和經驗作為指導。”“代議制集中了社會各部分和整體的利益所必需的知識。它使政府始終處于成熟的狀態。”[14]P241在近現代國家和社會管理過程中,代議制度已經成為近現代國家的組織制度,并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民族國家的形成而成為發展民主制的關鍵所在。
然而,雖然代議制理論將民主與議會聯系到一起,使民主成為一種和平、可馴服的決策手段,并且全面否認了人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性,較于前述等級代表制在形式上有明顯的進步,但在實踐操作過程中,它并不能真正實現人的平等,金錢取代了爵位、神職成為制度基礎。恩格斯在評述英國憲法的時候就曾指出,“這里所有的人,沒有一個人能夠說自己不是靠賄賂而是由選民自由地選出來的,賄賂的規模從來還沒有像現在這樣大,城市代表的席位完全公開拍賣,誰出的價錢高,就賣給誰……我們看到,掌握大權的下院是用什么方法補充成員的;現在的問題是:實質上究竟是誰統治著英國呢?是財產。”[15]P687財富的力量在選舉過程中影響過于巨大,從而將名義上的平等選舉變成了階級選舉。“富人通常對進入公共生活具有某種抵觸情緒,而窮人則往往不愿意選舉富人擔任公職。但這并不影響富人獲得比窮人更強的影響力……不會妨礙叮當響的美元操縱整個選舉過程;也不妨礙整個立法機構和相當數量的國會議員感覺到那些強有力的大公司和大財團的影響力。”[16]P126
既然財富在這個過程中如此重要,那么話語權自然會掌握在那些掌握財富的人們手中,那些人是誰呢?只有資產階級。各種財團、利益集團想方設法通過控制政黨進行競選,從而控制議會、政府當中政治果實的產出,進而間接控制政治事務的決定權。
三、碰撞與合流
選舉制度,在中國和西方循著不同的價值取向發展、演進。浩瀚海洋和崇山峻嶺的阻隔,使二者缺乏交集,更無溝通。然而,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遭遇了一個“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變局帶來了科舉制廢除的種種內因與外患。
(一)內因:地方勢力的再度勃興
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以士、農、工、商四個階層為基礎組建起來的社會,其中紳士是第一階層,在政治活動中發揮重要作用。然而傳統的紳士并非門閥,更非軍閥,他們沒有軍事上的力量,只是維護皇權政治的相對忠誠的讀書人。然而,到了19世紀中葉,太平天國的起義活動造成中國大范圍的混亂,為了鎮壓起義,中央政府只有讓地方紳士更多地介入到軍事事務當中。咸豐三年(1853年)三月初六,咸豐皇帝發布上諭,要求各地進行團練,“……督同在籍幫辦團練之士紳實力奉行,各就地方情形妥為布置,但期守衛鄉閭不必拘執成法……一切經費均由紳民量力籌辦,不得假手吏役……”[17]P108
當時正在湖南的曾國藩接到了朝廷的命令后,在原籍編制團練,逐漸形成赫赫有名的湘軍集團。這時的曾國藩,充分任用湘籍官紳充當湘軍主帥,極力協調與湘省督撫大員的關系,在湖南酌量變通辦理,廣辟財路,展開了一系列“剝民以飼兵”的籌餉活動,推行了戰時財經政策,為湘軍解決了巨額的費用。[18]至此,軍隊、軍需統歸于軍事統帥一人掌控,也就打開了地方勢力膨脹的大口子。到1862年,長期擔任曾國藩幕友的李鴻章,在曾的指示下招募淮勇,組建淮軍,形成中國另一個龐大的軍事集團。
湘軍、淮軍雖然鎮壓了太平天國運動,保住了清朝搖搖欲墜的皇權,但也形成一批尾大不掉的漢族地方勢力。在曾國藩率領湘軍南征北戰的過程中,他逐漸掌控了這支雄兵,特別是在1860年江南大營兵潰之后,曾國藩受命為兩江總督,節制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此時,曾國藩既有軍隊,又有軍餉,已經不能再被簡單地視為皇帝的官僚,實際已成為一方豪強。自此之后,地方勢力的擴張已呈不可阻擋之勢,他們甚至已經突破了地方的狹窄勢力范圍,形成了雖不可靠,但仍有力的聯盟。
(二)外患:科舉變革的直接動因
變局之產生,無非是內憂外患交雜之下的難解之謎。1840年之后,中國面臨的外患成為變局發生的直接原因。原先破敗不堪的君權政治,若非外患侵擾,似乎亦可修修補補地將就一下,但外患叢生,內憂繼起,變革與否,已不是君主所能擅自決斷的了。在這個背景下,梁啟超在《變法通議》一書中,對科舉制度進行了一番有趣的評論。他首先肯定了科舉制度的好處:“國初因沿明制,稍加損益……取士以科舉,雖不講經世,而足以揚太平……”但他接下來又說,假如能夠一直閉關鎖國,而無外敵之擾,那么,用這樣的舊法,并且時常加以修改,也不是不能治理天下,“而無如其忽與泰西諸國相遇也。”[19]P10-11這里說的就是新問題的總起源——中國此時已不可能繼續閉關鎖國,裝作和“泰西諸國”不認識了。
綜觀清末學者在這個時期對科舉制度多持批評的態度,其批評固然有許多老調重彈之處,但由于老麻煩又加上新問題,也就稍稍有了一些特殊性。這種特殊性有三個方面的內容:(1)科舉制度阻礙了西學的傳播。有識之士多意識到,如果不傳播西學,鉆研科技,國家將無法發展進步,從而難以走向富強。然而科舉制度的存在,使大量士子沉迷于八股文,不愿學習“無用”的西學。嚴復就指出,“言時務者,人人皆言變通學校,設學堂,講西學矣。雖然,謂十年以往,中國必收其益,則又未必然之事也。何故?舊制尚存,而榮途未開也……欲講實學,非另立選舉之法,別開用人之涂(途),而廢八股、試帖、策論諸制科不可。”[20]P40(2)依附科舉而生的舊學者,無法應對其所面對的困境。特別是在滿清統治之后,中國知識分子越來越失去應付困境的能力。中國知識分子開始不能議政,于是只能轉向考據之學。“到清末民初和西方接觸時,面對種種大問題的挑戰,中國的知識分子卻喪失了反應的能力,就是因為已喪失了學問的傳統。沒有學問就沒有思想、思考力,因此也沒有觀念,更不會表達觀念;只有感性、世俗的聰明是沒有用的。”[21]P181(3)議會制度的引介,使科舉有了新的改革路徑。在傳統的皇權社會,科舉的替代品只有察舉制度,可是歷史已經表明,察舉制度產生的禍害,比科舉還要激烈一些。在這樣的因緣際會之下,當西方議會制度出現之時,它就必然演變成一條新的道路。
彼時彼刻,開議院成了眾人矚目的事情,也成為突破“科舉——察舉”困局的“第三條道路”。由此開始,中國人開始鼓吹一種民選的“選舉”制度——這個提法對西方學者來說可能有些奇怪,因為在西方人看來,“選舉”本就是民選。但在中國,這二者之間并不是那么順暢地聯系在一起的。
(三)博弈:權力版圖的此消彼長
1905年,擁有長達1300年歷史的科舉制度終于廢除了。然而在此過程中的博弈卻頗值得分析。
第一,傳統紳士階層和新知識分子總體上不主張廢除科舉:(1)傳統的紳士階層其實在總體上是不想廢除科舉的。雖然一些進步官紳基于對科舉禁錮思想的憤恨,以及對于西學的推崇,強烈要求廢除科舉,但當時的學界,多數人還是以科舉為安身立命之本和出人頭地之途。(2)即便是在維新派中,也有相當多的人主張對科舉進行改革,而不是廢除,他們的主要攻擊對象是八股文取士,而不是科舉本身。甚至一些根本沒有在科舉場上獲利的人,如康有為等,對科舉制度本身也是贊美有加。
第二,清廷也不想廢除科舉。比如說,在1901年底,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因庚子國變躲在開封,還未返回京城之時,就下達諭令要進行科舉考試。記錄此事的吳永說:“在如此倉皇播越之中,而對于下年之鄉、會試,尚復兢兢注意,足見當時視取士之典尚為鄭重,猶有汲汲求賢之遺意也。”[22]P121-122面對極為嚴重的財政困難,選擇以賣官鬻爵的方式籌措資金,準許富民捐納得官,以至于官員數量激增,本就造成了仕途壅塞,[23]P206因此以科舉取才,似乎更多的是一種象征意義。科舉象征了什么呢?根據此前的敘述,我們已經明了,科舉考試是中國封建社會皇帝掌控權力的一個極重要方式,國家能夠進行科舉,至少部分說明它作為正朔的地位。事實上,清廷此時的科舉政策,其選賢任能的意義已經小到堪可忽略的地步,惟因其政治意義尚存,所以就必須進行下去。
既然學子不想廢科舉,朝廷也不想廢科舉,那么真正要廢除科舉的是哪些人呢?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初二,一些人寫了一封名為《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并妥籌辦法折》的奏折,并得到批準,這些人包括:袁世凱(直隸總督)、趙爾巽(盛京將軍)、張之洞(湖廣總督)、岑春煊(署理兩廣總督)、周馥(署理兩江總督)、端方(湖南巡撫)。從身份上看,這些官員全部為地方督撫,并無一個是樞要官員;從勢力來看,袁世凱作為李鴻章的繼承人,張之洞作為救亡名臣,其所代表的實為中國當時最強大的經濟、軍事集團。這種聯銜奏請的威力非常強大——早在1901年春,盛宣懷就對張之洞、劉坤一、袁世凱剖析過聯銜奏請變法的奧妙:“疆臣同志,朝廷易于決斷,一妙也。疆臣有權,能說即能行,二妙也。”[24]
好一個“疆臣有權,能說即能行”!這實在是一句再確實不過的話。如果我們結合之前的敘述,就可以更加明顯地看出,晚清在科舉制度存廢問題上的斗爭,并不能算得上一場關于是否能夠培養出人才觀念的斗爭,它更多的是一種對政道分歧的有效反映。那些地方督撫,在自身所轄地區大興學堂,但朝廷卻繼續進行科舉,這就擋住了其門生入仕的途徑,也妨害了自身勢力的發展,如果不廢除科舉,地方督撫仍然難以獲得他們在政治上應有的優勢。正是在這些封彊大吏的推動下,科舉制度于1905年得以廢除。
四、移植與斥異
雖然中國傳統的“選舉”制度已于1905年廢止,但由這一傳統而引起、沉淀的社會觀念,決不可能因為清廷的一紙詔書就得到根本性改變。它與西方制度之間仍然存在著巨大差異,并從一些更加隱晦的層面影響著中國近現代的選舉,進而引起一系列認識上的歧異。
(一)民智問題
舊觀念與新傳統之間的首要沖突體現為“民智”說。既然中國傳統選舉的首要目的在于選出一個“恰當”的統治階層,那么,當選舉權要從君主轉為人民行使之時,也就極為自然地產生所謂“民智”問題——如果不開“民智”,以愚昧的人民來選舉賢能,似乎總是靠不住的。因此,自議院制度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之日起,中國學者就開始擔憂這個關系到中國人能否堪當選舉任務的問題。
實際上,在西方的選舉制度中,人民選舉一個人,不是打算讓他成為一個統治者,而是為了讓他能夠作為自身主張的聲言、倡議者。在這個思路下,古希臘人甚至可能接納一個靠抽簽的方式當選的議員——因為他也隸屬于這個階層。西方選舉的目標在于體現階層的意志,而不是制造出一個新的階層,這就不同于中國。對于中國而言,選拔官僚的目的并不在于使其代表某個階級。一縣的長官、一省的長官,并非該縣、該省的領主、貴族,他只是政權的代表,并基于皇帝的命令征稅、保民,施行教化。在費孝通先生看來,“官僚是皇帝的工具,工具只能行使政權而沒有政權。貴族是統治者的家門,官僚是統治者的臣仆。”[25]P2官員只是皇帝的僚屬,他們是依靠皇帝認可甚至親自執行的考試,硬生生制造出來的階級,自然就沒有靠這些官僚組成事權型議會的可能了。在西方的選舉當中,選舉人的問題會變得更加緊要,因此,候選人所隸屬的階級就變成更緊要的問題,他們必須表現得和選舉人一樣,并且讓選舉人更多地知曉他們。而在當時中國的選舉當中,候選人的問題無疑更為關鍵。皇帝必須為他的統治找到合法性基礎。在儒學的框架下,這個基礎顯然與統治階級的智識有密切關系。中國政治當中的精英主義,上等人對下等人的統治,在這個觀念下慢慢根深蒂固。
到清末時,在中國人看到外國的選舉狀況后,這種類似的觀念仍在頑固堅定地發揮作用。當時的著名學者、外交官黃遵憲曾在1884年目睹美國大選的狀況,并在1902年給梁啟超的信中再次回憶這個事件:“每舉總統,則兩黨力爭,大幾釀亂,小亦行刺,則又爽然自失。以為文明大國如此,況民智未開者乎……而仆仍欲奉王權以開民智,分官權以保民生,及其成功則君權民權兩得其平。”[26]P491梁啟超也基本支持這個觀點。在他的一篇著名論文中,更是主張“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權”:“今之策中國者,必曰興民權。興民權斯固然矣,然民權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權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權;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權;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權……昔之欲抑民權,必以塞民智為第一義;今日欲伸民權,必以廣民智為第一義。”[27]P27民權的反對者也持此論。張之洞說:“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將立議院歟?中國士民,至今安于固陋者尚多,環球之大勢不知,國家之經制不曉,外國興學立政、練兵制器之要不聞,即聚膠膠擾擾之人于一室,明者一,暗者百,游談囈語,將焉用之?”[28]P19清廷也是拿這個理由推遲國會召開的。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日(1910年初),面對各省咨議局請愿代表要求召開國會的請求,清廷下發《俟九年預備完全定期召集議院諭》,宣稱“我國幅員遼闊,籌備既未完全,國民智識程度又未畫一,如一時遽開議院,恐反致紛擾不安,適足為憲政前程之累……總之憲政必立,議院必開。”宣統二年五月二十一日(1910年),清廷再次重申該主張,發布《仍俟九年預備完全定期召集議院諭》。宣統二年十月初三(1910年),面對國內的巨大壓力,清廷發布了《縮改于宣統五年開設議院諭》,在縮短預備立憲期限的同時,也強調“恐民智尚未盡開通,財力又不敷分布,操之過蹙,或有欲速不達之虞……”[29]P641
孫中山固然不會以此為由反對議會制度,但他也非常強調官員要有智識上的限制。在1906年,他說:“就選舉上說,那些略有口才的人,便去巴結國民,運動選舉。那些學問思想高尚的人,反都因訥于口才,沒人去物色他……將來中國的憲法,必要設獨立機關,專掌考選權。大小官吏必須考試,定了他的資格,無論那官吏是由選舉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須合格之人,方能有效。[30]P330到了1924年,孫中山更是提出將人分為三等,也就是“先知先覺,后知后覺,不知不覺”的三類人群,進一步推進了前一種說法。
關于民智問題的類似觀點還有很多,我們不再贅述。這類觀點在清末、民國以及當代中國,都得到極為廣泛的支持,并極為深刻地影響了選舉制度在我國的發展。
(二)政綱問題
政綱,乃是政黨的一個要素。從現代民主理論來看,政綱乃是政黨參加競選的主張,也是政黨一旦執政之后實行的政策。政綱是選民了解政黨的首要因素,是政黨的精神氣質,也是政黨不同于派系的關鍵。“政黨有政綱,有組織法,有黨內外政治行為的規律……派系沒有政綱,只對某一個或某一些問題有特別的看法。派系即使有組織也沒有明確的組織法,派系政治行為的標準不是‘討論,表決,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傳統的恩惠和忠誠的交換關系。”[31]P89
如以政綱為標準,則許多政黨在本質上就是派系。民國初年,國內雖有三百多政黨,然而多半沒有明確的政綱,有政綱的,也往往以“民主”、“立憲”等空泛詞語為主,至多聊勝于無。有學者評述說:“蓋吾國人對于政黨政治之觀念,極為薄弱。當政黨之結合,初步以政見也,或臭味相投,或意氣相孚,質言之,感情的結合而已,然此猶其上焉者也。其下焉者權勢的結合而已,金錢的結合而已……茍欲施行政黨政治,其必出于毀黨造黨之一途,且必有真正超個人的黨綱,高尚純潔的人格鍛煉,方足以舉政黨之實利以利國家。”[32]P6-7但對于大部分中國人甚至黨員來說,綱領實在是太過陌生的詞語。
黃鐘毀棄,自然瓦釜雷鳴。政黨既不能用政綱加以區分,也就無法區別于傳統社會中的朋黨、會黨之屬。黨綱缺乏凝聚力,那些黨員也就只有凝聚在某些領袖人物的身邊,形成新的派系關系。
(三)異見問題
異見問題有兩個方面:一是反對黨的反對意見,二是黨內同志的異議。這兩種異見在民初都是不被接納的。
我們國家傳統中就是沒有忠誠的反對派的觀念的——反對政見與反對持有政見的人是高度一致的。政見之分就是君子小人之分,政治治理得不好,定是執政者聽信了小人。比方說,在北宋黨政最劇烈的時候,歐陽修寫了一篇著名的論文《朋黨論》。他在其中主張:“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甚至還說“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歐陽修的這篇文章不可能對政爭起到良好的作用,因為他將朋黨分為“君子之朋”和“小人之黨”,而將個人政見與其品行更加緊密聯系起來,自然難有什么好結果。
民初的政爭問題也是這種情況的絕佳反映。在這一時期,政黨之間的斗爭變得你死我活,無所不用其極。具體來說,對于異己者,民國時期的政客(甚至學者)有三種做法:(1)鏟除,此法以暗殺最為極端。比方說宋教仁、陶成章、史量才、李公樸、聞一多、韓復渠等人都是因暗殺而亡。(2)兵迫,也就是拿軍隊圍困議會,迫使議員服從。這其實是形式上的議會政治與實質上的軍閥政治共存的怪胎。這種事情,袁世凱做過,曹錕做過,段祺瑞做過,甚至孫中山也做過。1912年2月13日,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咨文和推薦袁世凱的咨文,臨時參議院竟做出遷都北京的決議。孫中山和黃興大為震怒,訓斥了議員中的同盟會員,要求參議院次日復議。14日,黃興甚至派出士兵警衛會場,使臨時參議院做出更正,決議首都為南京。[33]P149(3)潑污。包括兩種:其中一種方法是在公共辯論的時候分別立場,對某個觀點的持有者進行尖酸刻薄的人身攻擊。在魯迅和梁實秋的論戰中,兩人都站定立場,將論戰從文藝領域轉換到惡劣的人身攻擊,最終因魯迅提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這個標簽而達到高潮。另一種方法則是潑污水,造謠言。比方說陳西瀅就說魯迅是收了蘇聯人的錢的,是所謂的盧布黨,又有人說魯迅是日本特務,云云。這些做法就完全丟開了政見爭執的本意,成了意氣之爭。
黨內意見同樣沒有得到寬容。民國時期,孫中山等人對黨內異見是基本反對的。孫中山堅持強調,革命要成功,關鍵在于服從領袖。二次革命失敗后,孫中山于1914年6月發布《致陳新政及南洋同志書》,認為同盟會與國民黨失敗的關鍵在于組織紀律的缺乏。“當時黨員雖眾,聲勢雖大,而內部分子意見紛歧,步驟凌亂,既無團結自治之精神,覆無奉令承教之美德,致黨魁則等于傀儡,黨員則有類散沙。”[34]P92因此,孫中山強調黨必須服從于一人。“無論何黨,未有不服從黨魁之命令者。而況革命之際,當行軍令,軍令之下尤貴服從乎!是以此次重組革命黨,首以服從命令為惟一之要件。凡入黨各員,必自問甘愿服從文一人,毫無疑慮而后可。”他還在給黃興的信中非常明確地提出,“弟所望黨人者,今后若仍承認弟為黨魁者,必當完全服從黨魁之命令。因第二次之失敗,全在不聽我之號令耳。所以,今后弟欲為真黨魁,不欲為假黨魁,庶幾事權統一,中國尚有救藥也。”[34]P89所謂真黨魁,就是全黨都服從的黨魁。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要分析一個制度的當下問題,就必須了解其過往。選舉制度并非無源之水,其產生和發展自然與一定的歷史文化傳統休戚相關。不同國家之所以能夠產生不同的選舉制度和選舉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選舉制度歷史發展情況的差異。從這個意義上講,選舉制度源流的研究決非單純好古。選舉傳統的影響遠比某項具體制度更加深遠,它有助于我們理解某個特定國家選舉制度、政治傳統形成的歷史文化背景,更有助于我們梳理當下問題出現的脈絡和癥結所在。因此,雖然我們一直在分析選舉制度在清末民初首次沖突的情形,但我們也可以明顯看到,傳統的延續性,使得這些問題仍不時地影響、干擾著我國當前的選舉發展,這也是該研究的現實價值。
[1]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2]陳茂同.中國歷代選官制度[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
[3]閻步克.察舉制度變遷史稿[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4]顧炎武.日知錄·朱子周易本義.
[5]顧炎武.日知錄·選補.
[6]顧炎武.日知錄·鄉亭之職.
[7]牟宗三.政道與治道[M].臺灣:學生書局,1996.
[8]張枏,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0.
[9]孫道天.古希臘歷史遺產[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
[10]楊益誠.古希臘雅典民主政治之發展與運作[J].興國學報,2007,7.
[11]蔣勁松.議會之母[M].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
[12][法]西耶斯.論特權·論第三等級是什么[M].馮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
[13]郭華榕.法國政治制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14][英]托馬斯·潘恩.潘恩選集[M].馬清槐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1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6][意]加埃塔諾·莫斯卡.政治科學要義[M].任軍鋒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三冊,咸豐三年)[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18]熊英.論湘軍餉源與湖南地方財政之關系[J].軍事歷史研究,2000,1.
[19]梁啟超.變法通議[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20]嚴復.論世變之亟:嚴復集[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
[21]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2]吳永.庚子西狩叢談[M].長沙:岳麓書社,1985.
[23]張仲禮.中國紳士:關于其在十九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M].李榮昌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
[24]關曉紅.科舉停廢與清末政情[J].中國社會科學,2004,3.
[25]吳晗,費孝通.皇權與紳權[M].上海:觀察社,1948.
[26]黃遵憲.黃遵憲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27]梁啟超文集[M].北京:線裝書局,2009.
[28]張之洞.勸學篇[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29]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M].北京:中華書局,1979.
[30]孫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1.
[31]陳志讓.軍紳政權[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
[32]謝彬.民國政黨史[M].北京:中華書局,2007.
[33]李金河.中國政黨政治研究(1905-1949)[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
[34]孫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