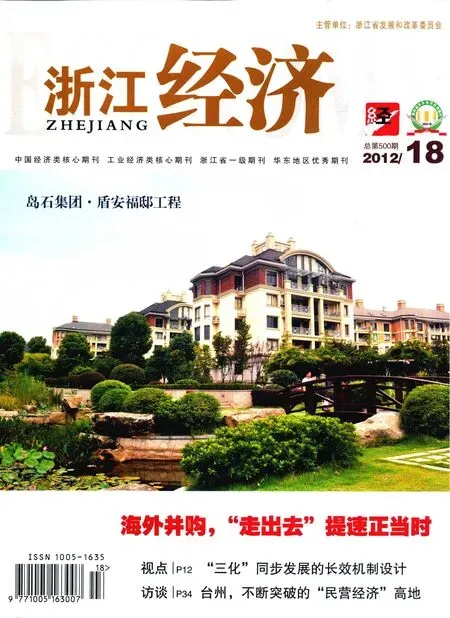慈善事業發展與收入分配改革
□ 文/呂鑫 葉托
慈善事業發展與收入分配改革
□ 文/呂鑫 葉托
收入分配改革是在國民收入差距日益增大背景下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的有效措施,其通常采取調整初次分配和社會保障再分配的方式實現目標。而除了以上兩者之外,筆者認為:慈善事業同樣能夠起到調整收入分配的作用,且作為一種自愿的再分配機制,其調整具有自身的特點和優勢。
慈善事業是一種“自愿的再分配”。雖然慈善事業與社會保障同為再分配,但兩者在開展的主體和強制力上存在明顯差異:社會保障是由政府主導開展,主要通過稅收形式進行財產的轉移,進而實現財產的再分配,是基于公權力強制開展,因此可以視為一種“強制的再分配”;慈善事業則是由公民自發開展,主要通過大量穩定的慈善捐贈實現財產的再分配,完全是由公民“自愿”開展,因而可以視為一種“自愿的再分配”。
當然,慈善事業雖具有“自愿性”特征,但并不等于政府不能對其調整規制。事實上,與社會保障中政府“直接”調整具體的再分配不同,政府對慈善事業的調整可以采取“間接”的方式,具體來說包括慈善組織的成立、慈善募捐的開展、慈善捐贈的稅收優惠等。在此意義上,筆者認為政府將慈善事業納入到收入分配改革中并不存在理論問題,但在具體制度層面上如何促進慈善事業發展仍需探討。就我國目前的慈善事業而言,諸多制度性問題已經顯性,必須從以下三個方面改變:
首先,保護公民開展慈善的權利。慈善事業的發展依賴于眾多的公民長期、專門的從事,因此對公民慈善權利的保護構成了慈善事業的基本條件。而其中最為重要的包括兩項權利:第一,公民慈善結社的權利,結社權利對于慈善的意義在于,慈善事業的發展有賴于團隊化的協作來實現慈善目的。為了促進慈善事業發展,應當降低公民參與慈善的門檻,針對慈善社團成立采取備案制,以鼓勵更多的公民參與其中。第二,公民慈善募捐的權利,如果說慈善結社權利使公民在慈善事業中獲得了合法的身份,那么募捐的權利則使得慈善組織能夠獲得運行所需的物質條件。事實上,募捐行為猶如慈善事業的“關節”,募捐者通過募捐和捐贈連接了捐贈者與受贈者,而這樣的“募捐-捐贈”構成了現代慈善活動的主要模式,因此要保障現代慈善事業有效開展必須保障募捐的“通暢”,亦即保障公民的慈善募捐權利。
其次,規制政府的“慈善”行為。如果說保護公民慈善的權利是慈善事業發展的基礎,那么規制政府的“慈善”行為,尤其是政府直接開展的慈善活動則構成了其發展的前提。嚴格規制政府“慈善”行為有著充分理由:一方面,“政府辦慈善”將改變慈善事業的性質,其公權力背后的強制力將改變慈善“自愿、平等”的性質,并導致“被慈善”、“被捐贈”現象的發生;另一方面,當政府在享有監督權力的同時又有權開展慈善,其結果使政府充當“運動員”和“裁判”的雙重角色,由此造成慈善事業由于缺乏公平競爭性而得不到充分發展。因此,必須改變規制政府參與開展慈善活動,而將其重點轉變為監督慈善活動。
最后,完善慈善監督機制。就政府在慈善領域的職權而言,監督而非參與則是真正需要重視之內容。對于如何完善慈善監督,從學理上來說包括了兩個部分:首先,慈善監督應橫向拓展,建立針對慈善募捐的全程監督機制;其次,慈善監督應縱向深入,建立透明的運行機制。此外,還應當賦予政府相應的監督職權,這包括了對慈善組織活動內容進行查實的“調查權”,以及對慈善組織違反規定進行懲處的“處罰權”,并且還要對政府本身的責任予以明確,以督促其積極行使監督職權。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以社會保障和公平為導向的收入分配改革開始受到普遍的關注。如果我國的收入分配改革僅僅將關注點放在市場的初次分配和社會保障的再次分配,那么很可能意味著,在這一改革過程中我們并沒有充分地利用各種分配和再分配形式。筆者認為,在我國的收入分配改革中,慈善事業的作用和地位同樣應該得到各界的重視。慈善事業并不像大部分學者所說的是一種“三次分配”機制,而仍然是一種“再分配”機制,只不過是一種自愿型再分配機制。作為一種自愿型再分配機制,慈善事業具有其獨特的特點和優勢,不僅可以有效地補充以社會保障為主要形式的政府強制型再分配機制,還可以起到凈化社會風氣的作用。
浙江工業大學法學院/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