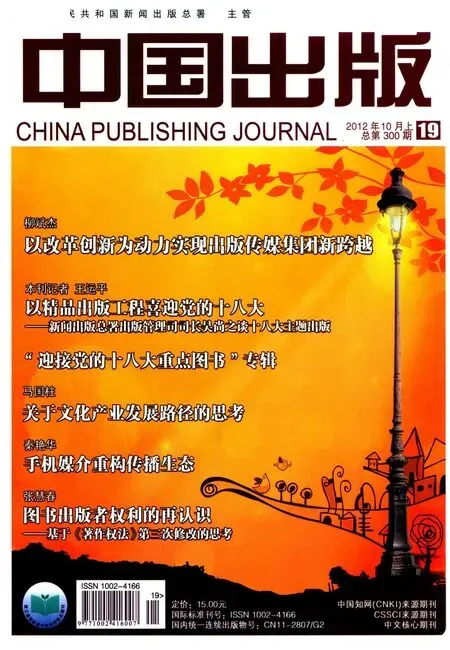網絡版權保護中的利益平衡機制
文/黃秋娜
網絡環境下的版權保護呈現出利益主體多元化的特征,其利益平衡訴求與印刷時代相比也更復雜、更特殊,網絡版權方面的制度設計必須反映這種新的利益平衡要求。
一、利益平衡是版權法的宗旨
社會中存在各種各樣的利益主體與利益關系,因為利益資源的有限性與利益主體欲望的無限性,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利益沖突,“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調整及調和上述種種相互沖突的利益,無論是個人的利益還是社會的利益。這在某種程度上必須通過頒布一些評價各種利益的重要性和提供調整這種種利益沖突標準的一般性規則方能實現”。[1]“法律是適應利益調節的需要而產生的,法律的發展根源于利益關系的變化,法律制度實質上是一種利益制度”。[2]法律調整利益,是通過規定權利義務來實現的。“權利和義務貫穿于法律現象邏輯聯系的各個環節、法的一切部門和法律運行的全部過程”。[3]在權利義務為主的私法領域,無處不在進行各方利益的平衡。不同的私法規范,調整不同的社會關系。不同的社會關系,參與主體不同,利益訴求不同,相應地,法律進行利益平衡的機制也不同。具體到版權法,其調整版權利用與版權保護關系,既要保護版權人利益以鼓勵創作和創新,也要保護公眾利益使其能夠自由接近文化作品,其利益平衡機制是賦予作者人身權及財產權同時又做出某些權利限制。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締結的版權條約,其目的之一便是保持“作者的權利(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的權利)與廣大公眾的利益尤其是教育、研究和獲得信息的利益之間的平衡。”我國《著作權法》第一條開宗明旨地規定:“為保護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作者的著作權,以及與著作權有關的權益,鼓勵有益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的作品的創作和傳播,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和科學事業的發展與繁榮,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可見,利益平衡是版權法的基本宗旨和目的。
二、網絡版權語境下新的利益格局
復制和傳播技術的不同會形成不同的版權利益格局。網絡環境下的利益格局與傳統印刷時代的利益格局并不相同。一方面,在印刷時代,利益主體為著作權人、出版商和公眾,連接著作權人與公眾的是出版商,知識的傳播與利益分配依附于由出版商控制的印刷技術,出版商通過與著作權人簽訂出版合同進行利益分配,作品的發行量與出版商的利益密切相關,所以出版商不僅關注作品本身的質量,也同著作權人一樣關注作品是否被侵權。另一方面,因為作品和載體的不可分離性以及對印刷技術的依附性,使得作品侵權的成本較高而且容易被發現和識別。可以這樣說,在印刷時代,《著作權法》通過規定作者的著作人身權與財產權以及合理使用制度、權利用盡制度、版權期限制度等能較好地平衡著作權人、出版商與公眾的利益。在網絡環境下,利益主體為著作權人、網絡服務商和公眾。網絡服務商更多地提供了一種連接著作權人和公眾的媒介,其只提供存儲空間而不提供內容,所以不會去審查作品是否侵權。盡管如此,網絡服務商仍有自己獨立的利益追求,其可以通過廣告費、流量費贏利。這就形成了網絡環境下的利益格局:版權人、網絡服務商、公眾三足鼎立。對版權人的利益考量涉及作品的推陳出新及文化事業的繁榮,對網絡服務商的利益考量涉及互聯網產業的發展,對公眾的利益考量涉及人類文化、信息資源的共享。版權法必須區分版權人、網絡服務商與公眾各自的利益,必須為版權人與公眾利益、版權壟斷與信息分享之間的博弈提供良好的平衡點。其中促進網絡技術創新和互聯網事業的發展是網絡環境下特殊的要求,是網絡版權利益平衡的重要支點和出發點。同時,網絡技術的發展只能是而且必須是有效保護版權人的利益而不是壓縮、限制版權人的權利。如果一味保護互聯網事業而偏袒網絡服務商,就會置版權人于不利,挫傷其創作的積極性,公眾的利益也必然受損。版權法必須順應這一時代要求,平衡各方利益,使版權人通過網絡傳播作品獲得好的收益,又能加速互聯網產業發展,促進信息文化資源的繁榮,同時又不妨礙公眾自由接近、利用作品的權利。
三、版權法在新的利益格局下應采用的平衡機制
(一)建立版權信息平臺與版權交易中心以明確版權權屬及流轉關系
我國的版權制度實行自動保護原則,作品完成之后不論是否登記都受版權法保護。在網絡環境下,公眾創作文化藝術作品的熱情被激發出來,作品的創作不再是少數人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成為版權人;借助網絡這個媒介,作品的創作與發表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作者可以邊創作邊發表;作品的獨創性也因為思想與表達的二分法、復制與粘貼的便利而難以確定;作品向公眾公開并迅速傳播變得輕而易舉。因為沒有一個版權信息的發布、登記、查詢、交易平臺就容易造成版權權屬不清,即便作品使用者有合法使用的意愿,也可能因為版權授權通道不暢而非法使用,這樣就會造成侵權行為頻頻發生。如果建立一個版權信息平臺,版權人就可以通過這個平臺進行版權的聲明與登記,雖然該登記不是強制性的要求,卻可以與自動保護原則相配合為原創者提供有力的保護,公眾也可以通過這個平臺進行版權查詢,這樣就明確了版權權屬關系,促進了版權信息資源共享。在此基礎之上,建立版權交易中心,使版權所有人和使用人通過交易中心這個平臺發布供求信息,互相滿足各自的需求,既利于版權的流轉及有序的交易秩序的形成,也有利于減少侵權行為的發生。
(二)合理界定技術保護措施的“有效性”以保護版權人
在網絡環境下,作者不需要借助傳統出版商的印刷設備即可輕易地在全球復制和傳播作品。與此同時,公眾借助于互聯網,對作品進行上傳、下載使作品的非法傳播也變得低成本、迅速而且范圍廣。如果不采取相應的保障措施,版權人通過網絡提供作品會心存顧慮,網絡侵權也會普遍存在。使用技術措施保護和管理版權具有傳統保護方法無與倫比的優越性。傳統印刷品的版權保護主要是事后救濟,在計算侵權損害賠償時,一直有難以確定賠償額的弊病,因為無論是侵權人的獲利數額還是版權人的受損數額都難以確定。而采用技術措施保護版權則屬于事前控制,可以防患于未然。為此,各國版權法幾乎無一例外地賦予了版權人技術保護措施。美國的《千禧年數字版權法》(DMCA法案)規定了兩種類型的技術措施:“訪問控制措施”和“著作權保護措施”。歐盟的著作權指令借鑒了《千禧年數字版權法》,規定著作權人可以使用有效的訪問控制或保護措施,例如加密、轉化作品或防復制機器等對作品進行保護,但要求一項技術措施必須實現保護目標,才是“有效的”技術手段。[4]我國《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第四條規定,為了保護信息網絡傳播權,權利人可以采取技術措施。但該條例沒有詳細規定技術措施有效性的具體條件。筆者認為,在對技術保護措施有效性的界定上,如果過于寬松,會導致“有效性”的要求被虛置,從而損害公眾的權益。反過來,如果過于嚴格,則容易導致技術保護措施的立法目的落空,損害版權人的利益。所以,合理界定技術保護措施的有效性關乎版權人和公眾之間的利益平衡。“有效性”的判斷既不能以版權人主觀上有無使用技術措施保護版權的意圖為標準,也不能以該技術保護措施能否被專業人士破解為標準,應當以非專業普通用戶所用的通用工具為標準,如果這樣的用戶不能破解技術保護措施,則可以認定技術保護措施的有效性。
(三)正確適用避風港規則以發展互聯網事業
互聯網事業的發展,使得信息和思想的傳播更有效、更廣泛,給人類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變化,所以互聯網產業本身的發展也是人們要特別關注的。如果網絡服務商動輒得咎,則其對于提供網絡速度與能力的投資也會心存顧慮,那么網絡技術與互聯網產業的發展就很難進行。“對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行為加以控制,是為了更加有效地保護著作權,但這種控制又是適可而止的,其目的是為互聯網產業的發展留下空間”。[5]在制度設計上就是給網絡服務商提供有條件的免責,即避風港規則。該規則最早出現在美國并被大多數發達國家采用。我國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也規定了避風港規則,其目的是促進網絡經濟的正常運轉和繼續增長。避風港規則下,當網絡服務商只提供存儲空間而不對信息進行加工處理時,一旦網絡服務商被告知侵權,則其有刪除侵權內容的義務。如果網絡服務商履行此義務,則免除責任。所以,避風港規則包括通知與刪除兩個方面。因為版權人熟悉自己的作品,故版權法將發現侵權的責任分配給了版權人,一旦其發現有侵權行為即可通知網絡服務商;網絡服務商掌握有刪除、屏蔽技術,能夠及時制止侵權行為,所以網絡服務商一旦被通知其所控制的網絡空間中存在侵權內容,就應當及時刪除、屏蔽,這樣就不承擔侵權責任。如果網絡服務商在得到通知后或者明知侵權而不采取措施進行刪除或屏蔽,則要承擔侵權責任。但是避風港規則正在被一些網絡服務商濫用。一些網站存儲有成千上萬的未經授權作品,卻以用戶上傳、網站不知情為由,將避風港規則作為擋箭牌。更有甚者,一些網站專門組織人員職業性地上傳他人作品,也謊稱用戶上傳、網站不知情,援引避風港規則逃避責任。這些行為嚴重侵害了版權人的利益,也擾亂了互聯網行業經營秩序。對此,應當正確適用避風港規則。對于存在大批量、大面積侵權作品的網站應當規定其承擔共同侵權責任,而不能就事論事,僅就某一版權人的作品是否被侵權作為適用避風港規則的依據。另外,對于熱播、知名的影視、音樂等作品應當要求網絡服務商采取必要的過濾技術,承擔更嚴格的注意義務,以避免未經授權作品被用戶上傳,保護版權人利益,也促進互聯網行業的良性競爭秩序的形成。
(四)擴大合理使用的范圍以保護公眾利益
合理使用是在一定條件下對已經公開發表的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也不支付報酬但必須指明作品的作者的使用方式。合理使用制度是版權法平衡版權人與社會公眾利益的重要制度設計,它通過對版權人的權利限制來保障公眾接近作品并利用作品的權利,以保障社會文化資源的傳承與豐富。因為任何作品都是個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結合,公眾享有合理使用權是其繼續創作的基礎與源泉。不論在印刷時代還是在網絡時代,公眾都應當享有合理使用權。只是在網絡環境下,公眾的合理使用范圍因為版權人的技術保護措施而受到更多的限制。比如,版權人的訪問控制措施可能使公眾在接觸作品之前就要支付費用,這就和印刷時代有很大不同。所以,“技術保護措施也是一把雙刃劍,它有可能防礙公眾對信息產品或文化遺產的接觸或獲取,因而技術保護措施的普遍應用可能潛在地摧毀公眾利益與私人利益之間存在的利益平衡”。[6]為了解決網絡環境下的合理使用問題,版權法允許特殊情況下對技術措施進行規避。如我國《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第六條規定了八種合理使用的情形,在第十二條規定了四種可以規避技術措施的情形,其中有三種合理使用的情形可以規避技術措施;其他可以合理使用的情形,如果版權人采取有訪問控制措施并且以付費為條件的話,使用人必須先付費而后才可合理使用,這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合理使用。在接觸作品是合理使用的前提的條件下,如果作品僅以數字化形式存在,就意味著可以規避技術措施的范圍大小在某種程度決定了合理使用的范圍大小。顯然,我國關于可以規避技術措施的情形的規定縮小了合理使用的范圍。對此,可以借鑒美國的做法,將非贏利性圖書館、檔案館和教育機構列入實施技術規避措施的主體范圍,使其服務對象通過這些機構的免費使用而無償使用,給合理使用在網絡環境下提供保障。所以,我國版權法應當擴大實施技術規避措施的主體范圍,以降低技術保護措施對合理使用的消極影響,更好地平衡版權人與社會公眾的利益。
[1][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398
[2]趙震江.法律社會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249
[3]張文顯.法理學(第2版)[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109
[4]王遷.技術措施的“有效性”標準[J].電子知識產權,2007,(9):47
[5]孔祥俊.論網絡著作權保護中利益平衡的新機制[J].人民司法,2011,(17):57
[6]高富平.尋求數字時代的版權法生存法則[J].知識產權,201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