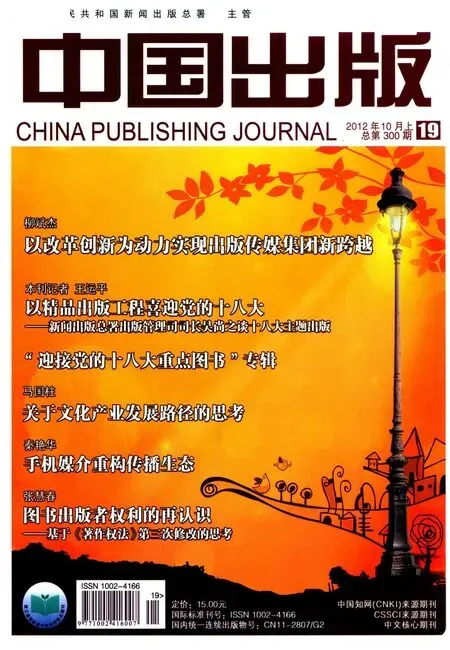圖書出版者權利的再認識——基于《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的思考
文/張慧春
版權法的立法目的是鼓勵作品的創作和傳播以促進文化的發展,為確保該目標的實現,一方面要確保作者享有獲得報酬的權利,另一方面也要保護出版者權利。我國《著作權法》中,圖書出版者相關權利的立法一直以來存在爭議,《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草案中,對出版者權利的調整回應了學術界長期以來的爭論。沿著版權法發展的脈絡來研究出版者權利的演變可以看出,賦予出版者鄰接權主體地位是合理的,將專有出版權回歸到合同權利體系中僅是恢復了其本來面目,這種權利的回歸無疑將會增強作者在開發版權利益過程中的議價能力,但為了確保《著作權法》立法目的的實現,還需要增加作者的適當報酬請求權。
一、圖書出版者的權利
(一)相關概念的辨析
出版就是作品的復制和發行。“出版者是指為了滿足公眾需求,依法取得以向公眾出售或出租為目的而復制作品的組織或個人”。[1]出版權是指作者為了保障作品的復制與發行而許可給出版者的權利。顯然,出版權是從著作權中引申出來的使用權,它存在于著作權的一個組成部分之中。也就是說,它存在于向出版者許可的排他性的復制權與發行權之中。出版者權是出版者基于向公眾傳播作品而享有的權利。概言之,出版權屬于作者,出版者權屬于出版者,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從上述定義中可以看出,實施“出版”行為的主體是享有復制、發行權利的人。那么從版權法角度分析,出版的主體可以是作者本人,但實際上出版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投入,一般作者很難承擔。所以,承擔出版行為的主體往往是實力雄厚的出版商。出版權作為復制權和發行權的組合,需要經過作者的授權才能由出版者享有。通過以上概念的辨析可以看出,在出版領域內明晰作者與出版者之間的法律關系是構建出版法律體系的基礎。
(二)圖書出版者權利的國外立法
1.美國以合同法為主體的立法模式。出版者權與出版權關系密切,可以說出版者要獲得出版者權首先要取得作者的授權,在美國法律中有關出版的法律問題一般通過合同法來解決。“出版歸根到底是版權的轉讓和許可,版權的轉移都是通過合同來完成”。[2]《美國版權法》第203條僅對版權的轉讓和終止做了規定。在版權合同中,出版者通常會與版權人就以下內容作出約定,包括:版稅計算、授權期限、結賬清單、庫存圖書銷售期限、其他相關權利及保留權利。近年來,隨著出版業的不斷發展和向互聯網擴張的趨勢不斷加強,美國學者對出版權的發展做了分析并認為,目前《美國版權法》所發揮的利益調整作用不能保證版權法立法目的的實現。因為,僅依靠版權合同無法確保作者獲得合理的報酬,進而提出學習《德國版權法》的相關規則。
2.德國較為全面的立法模式。作者要確保出版者獲得的是對作品的專有出版權,并有義務對出版中存在的權利障礙予以排除。作者還負有競業禁止義務,在特定的時間內不把任何自己的具有同樣內容的作品交給其他出版社進行出版。德國法律中賦予出版者的利益包括,出版者有義務對作品按照相應的目的并以正常的方式進行復制與發行并有義務對作品的出版進行校對,除此之外,還必須向作者本人交付一定的報酬。“通常情況下,報酬是以出版者收入分紅的形式分配的,如果出版合同中約定了報酬,那么該出版者還有義務支付報酬,如果出版者所獲得的利益、好處與作者所獲得的報酬相比比例明顯失調,作者擁有基于報酬合理的‘變更請求權’”。[3]這是《德國版權法》為貫徹憲法中規定的作者在作品利用中的經濟參與分配權而制定的“作者適當報酬請求權”,保護的理由在于,相對于那些主要的作品利用商而言,在市場上以及文化經濟中,作品創作人在組織上與經濟上都處于弱勢地位,這種弱勢地位會對供求原則所產生的適當報酬之獲得造成障礙。
(三)我國有關圖書出版者權利的立法
我國《著作權法》將出版者的權利規定在第四章“出版、表演、錄音錄像、播放”中,第四章所保護的權利是典型的鄰接權。但是,根據國際公約的規定,圖書報刊的出版權不包括在相鄰權的范疇內。因此,中國現有版權保護制度實際上包括了出版法的內容。[4]
我國《著作權法》規定,圖書出版者出版圖書應當和著作權人訂立出版合同,并支付報酬,非經著作權人的同意或授權,出版者無權擅自出版作者的作品。出版者要獲得這種同意或授權,必須經過出版合同予以確認。圖書出版者對著作權人交付出版的作品,按照合同約定享有的專有出版權受法律保護,他人不得出版該作品,這被認為是賦予了圖書出版者專有出版權。在出版者與著作權人的義務配置方面,《著作權法》規定著作權人應當按照合同約定期限交付作品。圖書出版者應當按照合同約定的出版質量、期限出版圖書。圖書出版者不按照合同約定期限出版,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圖書出版者重印、再版作品的,應當通知著作權人并支付報酬。圖書出版者經作者許可,可以對作品修改、刪節。圖書出版者有權許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的圖書的版式設計。概言之,我國《著作權法》賦予了圖書出版商專有出版權、有限的對作品的修改權、版式設計的專有使用權,并對出版合同以及出版合同中出版者與著作權人的義務作出一般規定。
二、我國圖書出版者權利的立法爭議
(一)對專有出版權的質疑
專有出版權是出版者的權利,出版者權源于作者的出版權,作者將復制、發行權許可給出版商,這是出版商取得出版權利的依據,也是取得專有出版權的依據。可見專有出版權并不是著作權的權利類型。我國《著作權法》規定了“專有出版權”,看似這是法律賦予出版者的法定之權。“但是,法定權利是指按照法律規定而享有的包括民事、行政、訴訟等方面的權利。一方面,法定權利區別于應有權利,即基于人性、人格和人道基礎上的自然屬性所應當享有的權利;另一方面,法定權利也區別于合同權利,合同權利是合同雙方平等協商的結果”。[5]不能忽略的是,在《著作權法》中確認了專有出版權的同時,還存在出版合同條款,出版商要取得專有出版權就必須與著作權人簽訂出版合同,從根本上說,專有出版權是出版者基于合同取得的合同權利,不是法定之權。在《著作權法》中專門規定專有出版權,反應出立法的邏輯混亂。
(二)對圖書出版者鄰接權人地位的質疑
在鄰接權制度中加入對圖書、報刊出版者權利的規定,是我國《著作權法》的一個特點。嚴格來說,這種體例是很不恰當的。“與藝術表演人、錄音制品制作人和廣播電視組織對作品的演繹創作不同,出版者的編輯、復制、發行他人作品的行為,對原作品的內容與形式不具有任何新的創作成分。而版式設計作為一種作品,其權利也并不一定屬于出版者”。[6]總之,享有鄰接權的本質原因,是從事了演繹創作,從而使原作品獲得了新的表現形式。但是,作為出版者,既沒有創作的職能要求,也沒有創作結果,對作品形式的完成沒有作出實質性的貢獻,卻被置于同演繹創作者同等的法律地位,這反映了立法的不完善。
三、對圖書出版者權利的歷史反思
(一)圖書出版者與版權法的發展
1.出版商之間的競爭促成了版權制度的產生。印刷術出現后,出版業逐漸形成發展起來,市場需求的增加帶來了高額的利潤回報,盡管出版商們財力雄厚,但他們最懼怕的是第三方加入競爭印刷出版同一版本的圖書。“要收回投資以確保自身的利益,就不能允許擅自復制作品,出版商經過不斷協商難以達到預期效果,不得不借助于王室的力量,這樣產生了出版特權制度”。[7]可以說,版權的產生源自資本主義興起后在貿易政策上規制商業競爭的需要。版權,就其本來意義而言,即是禁止他人印刷出版同一版本圖書的權利。這一時期,作者是被排除在出版利益群體之外的,作者出版的作品都是一次印刷,一次付酬,出版商通過控制作品的復制權而謀利,作者沒有對出版作品的議價能力。
2.從出版特權到以作者為主體的版權法。《安妮法》的出臺標志著以作者為主體的版權法誕生,但是《安妮法》的頒布實際上確立了出版商的版權,出版商的成功在于利用了“浪漫的作者觀念”改變了圍繞版權的爭論,從此版權爭議的焦點不是圍繞在出版商壟斷之上,而是圍繞著作者展開。[8]《安妮法》頒布后,作者分享版權利益有了法律支持,但并不代表作者們的議價能力提高了。“一些學者認為出版商通過以作者的名義捍衛版權,卻通過合同剝奪作者的議價能力”。[9]作者要出版圖書必然要選擇與出版商合作,通過出版合同分配利益,作者成為版權法主體,但出版商仍然是版權法的主要得益者。
3.技術進步帶來新一輪沖擊,作者的議價能力增強。歷次技術的變革,在改變版權產品的生產方式和傳播方式的同時也產生了新的貿易形式和新的利益相關者,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版權法的發展與演進。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出版商對產品的控制不斷加強,一方面,使用技術措施保護版權受到版權法的認可;另一方面,互聯網產業的發展也使得新興市場主體從事互聯網出版,出版行業的競爭空前激烈,新的傳播作品的模式,使得作者與讀者的距離拉近,甚至不需要出版商作為橋梁。
版權法的產生和發展離不開出版商的推動,但版權法最重要的目的卻是促進作品的創作和傳播,促進文化的發展。作者是作品的創作者,出版商是作品的傳播者,只有協調好兩者之間的利益,才能確保版權法促進文化發展目的的實現。從版權史的發展角度看,作者從來缺乏對于作品的“議價能力”,對作品利益的分配,往往由占有強勢地位的出版者享有,盡管技術的進步沖擊了版權產業的格局,作者的議價能力提高,甚至在網絡環境下,作者有可能成為出版者,自己出版作品。目前雖然互聯網拉近了作者與讀者的距離,但終極目的還是通過傳播作品獲得利益,互聯網出版產業依然是存在成本與風險的,一般的作者無法抵御商業風險的壓力,還需依賴一個中間媒介,這個媒介可以是傳統的出版商,也可以是網絡內容提供商。只能說傳播的快速和便捷,擴張了出版的界限,出版不可能也不應該消亡,出版依然擔負著傳播作品、促進文化發展的職能,這也決定了,版權法需要繼續調整出版者和作者的關系,確保立法目的的實現。
(二)對我國圖書出版者權利的再認識
現有立法的爭議與我國出版行業的特殊性有關。在計劃經濟時代,出版行業作為宣傳部門,擔負著宣傳黨政國策的重要使命,以國營出版社為主體的行政事業化出版體制是我國出版行業的特色。“在這種背景下,《著作權法》中特地為保護出版社的權利而規定了‘專有出版權’以及出版者的鄰接權,這是行政力量直接作用的結果”。[10]
賦予出版者鄰接權人地位并不是立法缺陷。縱觀版權法發展的歷史,出版者的權利與著作權的密切關系絕不低于被國際公約承認的鄰接權人,甚至更為緊密。“雖然國際公約中沒有確認出版者鄰接權人的地位,但國際公約并不禁止成員國在本國立法中的變通規定”。[11]賦予出版者鄰接權人地位,有一定的立法意義,也不違背國際公約。我國立法之所以出現邏輯混亂,是將圖書出版者的專有出版權放入鄰接權中,而專有出版權是典型的合同權利,不具有鄰接權的性質。出版雖然沒有改變作品的傳播媒介形式,但是在出版過程中要對作品進行裝幀設計和排版設計,這些設計體現了出版者的創造性勞動。從這一層面上說,出版者理應獲得鄰接權人的地位。
四、結論
《著作權法》第三次修改(修改草案)回應了理論中對出版者權的一些爭論,在草案中,將專有使用權的內容并入到第五章第一節著作權和相關權合同之中,承認了專有出版權的合同權利性質。對出版者權利的規定保留了版式設計權。草案采用了相關權概念來統稱包括出版、表演、錄音錄像、播放在內的鄰接權。有學者認為,鄰接權和相關權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而已,在《伯爾尼公約》中,使用鄰接權概稱以上權利,在《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中則用相關權來代替鄰接權。依照此觀點來看,我國《著作權法》仍然承認出版者的鄰接權人地位。
《著作權法》草案明確專有出版權由當事人雙方約定行使,并采取書面合同的方式確認。在合同中沒有約定專有使用權的,視為許可使用的權利為非專有使用權。這樣的修改賦予了作者出版作品更多的選擇權,增加了作者的議價能力。顯然,我國《著作權法》對出版權的修改受到了《美國版權法》的影響,將權利義務都歸入合同領域來調整。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版權法》中為平衡出版者與作者之間的利益,還有相關的制度支持,例如《反壟斷法》《合同法》,而且代表作者利益的行業組織也為作者爭取利益提供了有力支持。在科技不斷變革制度的新形勢下,我國《著作權法》的修改應該確保利益分配的基本原則,確認作者的報酬請求權。將出版權確認為合同權利,只是還其本來面目,在出版者的地位依舊強勢的情況下,作者的議價能力并不會因為法律賦予其協商的地位而增強,應該學習德國法中的立法經驗,賦予作者報酬請求權以及變更請求權,才能從根本上發揮版權法促進作品的創作和傳播實現文化的繁榮功能。
注釋:
[1]黨躍臣,曹樹人.網絡出版知識產權導論[M].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6:5
[2]李明德.美國知識產權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12
[3]雷炳德.著作權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4
[4]李芬蓮.專有出版權的屬性界定及修法建議[J].中國出版,2010,(9):41
[5]徐春明.質疑專有出版權[J].知識產權,2002,(5):32
[6]劉春田.知識產權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62
[7]吳漢東.知識產權基本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33
[8]黃海峰.知識產權的話語與現實[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1:25
[9]MAUREEN A.O'ROURKE.A BRIEF HISTORY OF AUTHOR-PUBLISHER RELATIONS AND THE OUTLOOK FOR THE 21ST CENTURY[J].COPYRIGHT OF THE USA,2005,(21):497
[10]賀湘君.論出版者權[D].湘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55
[11]張乃根.國際貿易的知識產權法[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