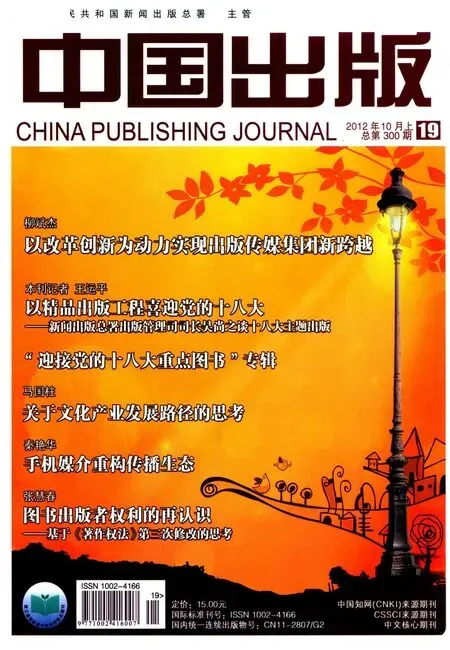辦刊主體變遷與晚清留日學生期刊的發展
文/葉 建
19世紀末期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后,大批中國青年赴日留學,并在日本逐漸形成了一股政治、學術力量。20世紀初,晚清留日學生創辦了大約97種學生期刊,[1]并通過多種渠道將期刊銷售到國內外華人世界中去,進而影響了晚清的政治、學術格局。關于晚清留日學生期刊的發展,學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本文試從辦刊主體變遷的角度對這一問題加以探討,以期發現學術與政治間的生態關系。
一、興起:跨省留日學生團體期刊時代(1900~1902)
1900年11月,《開智錄》創刊于日本橫濱,同年12月出改良第一期,每月兩冊,停刊于1901年春,具體卷數不詳,據馮自由指出,“出版至十余號而止”。[2]它是由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學生鄭貫一、馮自由、馮斯欒等三人創辦。19世紀末,鄭貫一因所讀學校經費短缺改組而去《清議報》工作。1900年,梁啟超從日本遠赴美國,《清議報》筆政由麥孟華攝理,期刊開始受康有為的直接干預,稍涉急激之文字俱不許登載。“諸記者咸以為苦,而莫敢攖其鋒。鄭乃約同學馮懋龍、馮斯欒同創《開智錄》,專發揮自由平等真理,且創作歌謠諧談等門,引人入勝”。[3]換言之,鄭貫一難以忍受《清議報》辦刊風格的變化,于是倡導并創辦了《開智錄》。鄭貫一對康有為等人辦刊風格的不認同,事實上為后來《開智錄》的停刊埋下了伏筆。在《開智錄》創辦初期,鄭貫一與《清議報》的關系比較良好,而且出于各種現實因素的考慮,其發行及印刷上只能借助于《清議報》,“凡有清議報銷流之地,即莫不有開智錄”。因《開智錄》文字淺顯,立論新奇,世界各地華僑“多歡迎之,尤以南洋群島為最”。這直接影響了海外保皇會工作的開展。于是,《清議報》不許《開智錄》在該報館印刷,并解除了鄭貫一的編輯職務。《開智錄》“以無所憑借,由是告終”。[4]
1900年12月,《譯書匯編》在日本東京創刊,每月出版一期。《譯書匯編》社成員與勵志會有密切關系,均為其骨干。勵志會是1900年東京中國留學生團體,“研究實學,以為立憲之預備;養成公德,以為國民之表率;重視責任,以為辨辦之基礎,”[5]開跨省份留學生團體創辦期刊之先河。當時參與《譯書匯編》社成員來自江浙沿海各省,據《譯書匯編》第二年第3期刊登的社告,其中除戢翼翚為湖北籍、金邦平為安徽籍外,周祖培、錢承鋕等其他12人均來自于江蘇、浙江兩省。他們中大多是政法專業留學生,對中國的現實和命運多為關注,“政治諸書乃東西各邦強國之本原,故本編亟先刊行此類,至兵農工商各專門之書亦有譯出者,以后當陸續擇要刊行”。[6]《譯書匯編》最初讀者訂閱較少,每期往往印一千份以上,而銷量僅有十之一、二,但因譯筆流利典雅,內容新穎,很快獲得巨大成功,“國內讀者紛紛訂閱,有時甚至要重印”。[7]
二、初步發展:同鄉留日學生團體期刊興起時代(1902~1905)
1901年7月,清政府下詔廢止八股文,改試策論,并選派學生出洋,且有酌用東西洋畢業學生之議。這前后,留日學生數量劇增,據清國留學生會館第一次報告“同瀛錄”統計,1898~1900年留日學生總數為143人。1901年年終人數至274人;1902年8月止為614人,年終達千余人;1903年,在校人數最少不低于1454人,1904年在校人數最少不低于2560人,最高可達3000人。1905~1906年,留日學生總數已達12909人。[8]這時,日本留學生中一部分人的人生目標較之以往發生了巨大變化,很多人熱衷于利祿的追求,不再從事思想啟蒙等與之不相符的活動,從而導致了勵志會等以交換知識、聯系感情為宗旨的跨區域組織的解體,其機關刊物亦受牽連,《譯書匯編》被迫改革,自第9期起改成以登著述為主、編譯為輔的形式,后來又改名為《政法學報》,宣稱“專主實學,不事空談,自始至終無一篇簡文章,無一句空泛話”,要使之成為“政法學界之燈”。[9]
然而,無論是出于政治宣傳,還是出于聯系感情的目的,相對穩定的團體組織需求始終存在。在這種氛圍中,一種以同鄉師友關系為紐帶的的群體開始出現,他們把鄉土情感訴之于濃厚的眷鄉之情,并輔之以強烈的政治訴求。在早期,這種區域性的群體往往是以同鄉會的面目出現。譬如湖南懇親會,為湖南籍留日學生和同省游歷日本的士紳組成,旨在“對于同鄉加厚情誼,對于同國聯絡聲氣,對于世界研究學術”;[10]湖北同鄉會由“湖北留學同人團結而成”,旨在“敦睦鄉誼,砥礪學行推廣一切公益事件”;[11]浙江同鄉會,由“吾浙留學生及官紳游歷或寄居日本者所組織”,旨在“篤厚鄉誼為主”。[12]這些留日學生同鄉會亦創辦期刊作為機關刊物,如《湖北學生界》《浙江潮》。這些以同鄉會為創辦單位的留日學生期刊,在1902至1905年間得到了迅猛發展,據不完全統計,主要有《游學譯編》《湖北學生界》《浙江潮》《直說》《江蘇》等十余種期刊。
三、高潮:同鄉留日學生團體期刊轉型與分化時代(1906~1908)
留日學生期刊的發展引起了清政府的不滿與恐慌。1902年,清政府設立了駐日留學生監督處,管理留日學生。1903年,又出臺了《約束游學生章程》,曰“妄發議論,刊布干預政治之報章,無論所言是否,均屬背其本分,應由學堂隨時考察防范,不準犯此禁令”,如有刊發書報,“但有妄為矯激之說,紊綱紀害治安之字句者,請各學堂從嚴禁阻。或經中國出使大臣總監督查有憑據,確系在日本國境內刊刷翻印者,隨時知會日本應管官署,商酌辦法,實為查禁”。[13]然而由于各種原因,清政府鞭長莫及。到1905年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緣于日本政府對中國留日學生期刊的監管日趨嚴厲,當時日本文部省頒布《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指出“受選定之公立或私立學校,不得招收為他校以性行不良而被飭令退學之學生”。[14]在當時語境下,“性行不良”指的是留日學生從事的革命活動。在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的夾擊下,以同鄉會機關刊物出現、傳播相對激進言論已變得不太現實。部分學生期刊開始分化、轉型,出現了《音樂小雜志》《教育》《法政雜志》《醫藥學報》《法政學交通社雜志》《衛生世界》《農桑學雜志》等十余種專業性的期刊。
鑒于很多同鄉會機關刊物不能刊登其革命言論,同盟會成員聚合自身力量,創辦了《云南》《洞庭波》《晉乘》《河南》《豫報》《四川》《關隴》《夏聲》等一批學生期刊來宣傳革命思想。此時的同盟會員創辦的期刊大都是采取省份命名的方式。之所以這樣,一方面受到《浙江潮》等雜志的影響,強調從鄉土出發啟發明智,譬如《夏聲》社同仁認為“蜀之鵑,浙之潮,洞庭之波,鳴其不平,以為激勵,大抵皆憂時愛國之士發憤悲傷之所為作也,且即地制名,動人較易不忘,厥本義尤厚焉”。[15]同時也有便于宣傳革命的目的。吳玉章回憶說,“1906年以后,《民報》運進國內就較前更加困難了。為此,留日學生中各省的革命同志,又紛紛以本省的名義創辦和繼續出版報刊,分散地運進國內,進行革命宣傳”。[16]
四、沒落:專業性學會創辦的學生期刊(1909~1911)
1909年始,留日學生數量劇減,年底降至3000人,1912年減至1400人。而這距離1907年1萬人的留學數量,已經是遙不可及的,這使得大規模人力投入期刊的創辦已變得不太可能。同時,國內已創辦了大量的學術及綜合性期刊,從日本辦刊再轉道運回國內銷售也顯得不合時宜。在這種局面下,中國留日學生只能借助于日本的學術優勢,通過專業性學會辦刊的形式,傳播思想。在當時,專業性學會創辦的學生期刊大致有《女報》《海軍》《中國蠶絲業會報》《湘路警鐘》《南洋群島商業研究會雜志》《鐵路界》《工商學報》《浙湖工業同志會雜志》《中國商業研究會月報》等9種,其他的群體創辦的學生期刊僅有《憲政新志》《中國青年學粹》《陜北》《教育今語》等幾種。換言之,專業性學會創辦的學生期刊在此時成為了留日學生期刊的主體。然而留日學生期刊的這種發展,并不能掩飾其發展高潮的褪去。據有學者考證,從1901~1911年間,每年留日學生期刊實際保有量是:1900年2種,1901年4種,1902年3種,1903年12種,1904年11種,1905年8種,1906年14種,1907年32種,1908年24種,1909年10種,1910年11種,1911種8種。[17]換言之,此時較之前的1907、1908年,無論是保有量,還是創刊量上,都是無法比擬的。
五、在創刊主體變化中晚清留日學生期刊呈現的特色
20世紀初的留日學生期刊,由于創辦主體的變化,其發展大體上呈現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其一,從創辦者的籍貫來看,東部城市逐漸向內陸及邊疆城市蔓延。1902至1905年,當時知名的幾家留日學生期刊基本上都是浙江、江蘇、湖北等比較開放的沿海、沿江地區留學生所辦,而自1906年始,這種格局有了比較大的突破,出現了《鵑聲》《云南》《四川》《夏聲》《滇話報》《晉乘》等相對封閉的內陸腹地省份留日學生所辦的期刊。之所以會這樣,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內地城市留日學生人數的增多。1905年年底,沿海等地留學生大量歸國,其中浙江籍留學生200余名,云南、四川等內陸地區留學生人數不減反增。錫良奏稱:1905年的四川省“自風氣盛開,東游相繼,官費而外,自費游學者,不下四五百人”。[18]又如江西籍留日學生,在1904年2月只有27人,5月清政府選派學生留日,從1905年始,人數逐漸增多,尤其是自費生增長迅猛,據不完全統計,到1908年,前后留日學生人數猛增了250多人,其中1906年的人數就達近200人。[19]
其二,留日學生期刊大都卷數不固定,極易停刊。留日學生期刊的經費通常由會員集資而成,經費不足是其常態。在早期,期刊主要作為同鄉會組織的機關刊物,經濟境況相對好一些,但即便如此,有限的經費也只能是維持編輯部的基本運轉,不少刊物連工作人員的薪水與來稿稿費都拿不出來。譬如《江蘇》,“本會會員及本部辦事各人皆各盡公眾之義務,不領薪水亦無酬勞”,[20]這種現象在1905年后同鄉友朋創辦的期刊上表現得尤為明顯,譬如景定成等人創辦的《晉乘》出了3期,之所以短命,“因經濟拮據而停刊”。[21]此外,清政府對留日學生期刊的管制日益森嚴,亦對其發行與銷售造成了極大的影響。1904年5月8日,清廷軍機大臣鹿傳霖致函各省督撫,要求查禁《新民叢報》《浙江潮》等各種“悖逆”書刊,28日袁世凱因軍機處函“通飭各屬暨各學堂禁閱新書、新報”,“各書坊鋪店不準代售以上所開各書報,官紳士庶均不準購閱,原有者立即銷毀。[22]1905年錫良曾發告示張禁《鵑聲》“有藏者則比室株連,獲主筆則就地正法”。[23]這其中,盡管有個別雜志因清政府的查禁而名聲大漲,銷量劇增,但這畢竟只是暫時而已,情況并沒有維持多久。
其三,學生期刊銷售網絡往往借助于師友、同鄉關系。晚晴留日學生大都缺乏足夠的經濟基礎和強大的社會關系,其期刊銷售只能借助于熟人網絡。從《開智錄》開始,便是如此。《開智錄》是依托于與鄭貫一關系密切的《清議報》。后來,盡管大多學生期刊在國內都設有發行所,或代理處,但不難發現,所謂的發行所或代理處,大多是學校、書店及新聞機構,《游學譯編》的代派處多是廣智書局、官報館、文海閣、梁溪務實學堂等文教機構,《湖北學生界》的代派處則是開明書店、文明書室等文教機構。這些機構或多或少地與留日學生存在師友或同鄉關系,譬如《湖北學生界》的總發行委托湖北省武漢市中東書社;《浙江潮》由浙江籍汪康年創辦的上海《中外日報》總發行;《游學譯編》曾在蘇報館設總派報處;山西同鄉會創辦的《第一晉話報》總發行為山西太原師范學堂及教育研究會。
[1][17]谷長嶺,葉鳳美.辛亥革命時期的留日學生期刊[J].新聞春秋,2011,(2)
[2][3]馮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4]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5]勵志會章程[J].譯書匯編,第2年第12期,1903年3月
[6]簡要章程[J].譯書匯編,第1年第1期,1900年12月
[7][14]實藤惠秀著,譚汝謙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
[8]蘇貴民.辛亥革命前中國留日學生人數考正[J].社會科學戰線,1981,(4)
[9]本學報十大特色[J].政法學報,第1期,1903年4月
[10]湖南懇親會草章[J].游學譯編,第2冊,1902年12月
[11]湖北同鄉會章程[J].湖北學生界,第1期,1903年1月
[12]浙江同鄉會簡章[J].浙江潮,第1冊,1903年2月
[13]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
[15]百無.夏聲說[J].夏聲,第1期,1908年2月
[16]吳玉章.吳玉章回憶錄[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78年
[18]錫良.錫良遺稿[M].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19]黃耀柏.清末江西留日學生述論[J].江西社會科學,1992,(1)
[20]江蘇同鄉會調查部公約[J].江蘇,第4期,1903年6月
[21]趙瞻國.景梅九年譜簡編[A].運城文史資料(山西)[C].第10輯,1990年
[22]投函[N].警鐘日報,1904-05-28
[23]丁守和.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