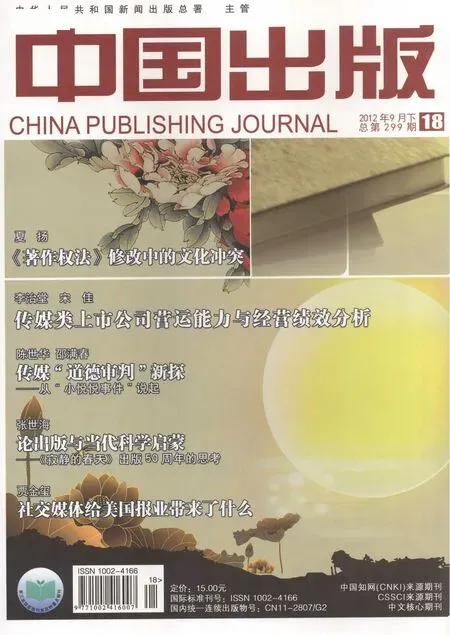微博語(yǔ)境下的消費(fèi)主義文化*
文/佘世紅
一 、何為消費(fèi)主義文化
1970年,法國(guó)著名社會(huì)學(xué)家波德里亞出版了《消費(fèi)社會(huì)》一書(shū),他在書(shū)中指出消費(fèi)社會(huì)是這樣的一種生活方式:消費(fèi)的目的不是為了實(shí)際需要的滿足,而是在不斷追求被制造出來(lái)、被刺激起來(lái)的欲望的滿足。消費(fèi)主義的產(chǎn)生是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由短缺經(jīng)濟(jì)走向過(guò)剩經(jīng)濟(jì)的結(jié)果。由于普遍的供過(guò)于求,消費(fèi)就成了資本增值的重心,刺激消費(fèi)、創(chuàng)造新的消費(fèi)欲望就成了首要的任務(wù)。維爾斯(Wells)曾明確指出“消費(fèi)主義”和“生產(chǎn)主義”的區(qū)別,他認(rèn)為“消費(fèi)主義”是伴隨著發(fā)達(dá)國(guó)家中物質(zhì)消費(fèi)文化的增加而產(chǎn)生的,而“生產(chǎn)主義”是動(dòng)員社會(huì)人口去工作,并在非消費(fèi)領(lǐng)域中增加勞動(dòng)生產(chǎn)率。[1]
在消費(fèi)社會(huì)中,消費(fèi)主義文化自然大行其道,成為消費(fèi)社會(huì)的主流文化現(xiàn)象。消費(fèi)主義文化就是以消費(fèi)為主導(dǎo)的文化。它在消費(fèi)社會(huì)中主要表現(xiàn)為兩個(gè)方面:一方面,商家為了刺激商品的消費(fèi)與傳媒合謀生產(chǎn)和制造出大量的消費(fèi)文化(廣告文化是其主要表現(xiàn)形式);另一方面,傳統(tǒng)的、被認(rèn)為是精英的文化也被過(guò)度包裝和消費(fèi),以消費(fèi)文化的形式出現(xiàn)。因而,消費(fèi)社會(huì)是消費(fèi)主義文化產(chǎn)生的社會(huì)基礎(chǔ),消費(fèi)主義文化是消費(fèi)社會(huì)中的主要文化表現(xiàn)。弗雷德里克·杰姆遜也發(fā)出這樣的感慨:“這就是消費(fèi)主義,我們經(jīng)濟(jì)體系的關(guān)鍵,它也是我們?nèi)粘5纳罘绞剑谖覀兊娜粘I钪校覀兯械拇蟊娢幕c娛樂(lè)產(chǎn)業(yè)用一種史無(wú)前例的形象與媒體轟炸,對(duì)我們?nèi)諢o(wú)一日的進(jìn)行無(wú)止境的訓(xùn)練。”[2]在弗雷德里克·杰姆遜的感慨中,我們看到媒介與消費(fèi)主義文化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guān)系,無(wú)處不在的媒介廣告與媒介天生交織在一起的娛樂(lè)產(chǎn)業(yè)和大眾文化不僅刺激了消費(fèi)主義文化的產(chǎn)生,也是消費(fèi)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shí)上,在高度發(fā)達(dá)的媒介社會(huì)中,媒介是消費(fèi)主義文化生產(chǎn)和傳播的主要平臺(tái)。
二、消費(fèi)主義文化特征
微博出現(xiàn)之后,專家學(xué)者對(duì)其特點(diǎn)進(jìn)行了不同解讀。張佰明認(rèn)為嵌套性是網(wǎng)絡(luò)微博發(fā)展的根本邏輯。[3]孫衛(wèi)華、張慶永認(rèn)為微博的特征是文本碎片化,半廣播半實(shí)時(shí)交互,自媒體、草根性更加突出,更為個(gè)體化、私語(yǔ)化敘事特征。[4]微博生產(chǎn)和傳播信息更加自由、更加快速,已經(jīng)成為消費(fèi)主義文化生產(chǎn)的重要平臺(tái)。微博語(yǔ)境下消費(fèi)主義文化的特征有:
1.消費(fèi)主義文化生產(chǎn)主體更多元。在傳統(tǒng)大眾傳媒時(shí)代,只有媒體機(jī)構(gòu)和組織享有生產(chǎn)信息的權(quán)利,因而,在大眾傳媒時(shí)代,消費(fèi)主義文化的生產(chǎn)主體是大眾媒體。然而,在微博傳播語(yǔ)境下,消費(fèi)主義文化生產(chǎn)更加多元,就目前來(lái)看,消費(fèi)主義文化的生產(chǎn)包括以下幾個(gè)來(lái)源。
一是個(gè)人在微博上呈現(xiàn)的帶有消費(fèi)主義特征的日常生活,如上傳奢侈品等炫富行為。二是企業(yè)或其他營(yíng)利組織利用微博傳播消費(fèi)主義文化,如企業(yè)在微博上宣傳產(chǎn)品或服務(wù),實(shí)現(xiàn)銷售目標(biāo)。
2.消費(fèi)主義文化生產(chǎn)內(nèi)容更多。微博傳播是一種典型的自媒體傳播,普通大眾可以自由的傳播和分享信息或圖片,消費(fèi)主義文化生產(chǎn)的內(nèi)容也多于大眾媒體時(shí)代。很多網(wǎng)民常常在微博上分享消費(fèi)體驗(yàn),還有些網(wǎng)民喜歡在微博上曬出自己富裕的生活。有些人是想借助微博來(lái)滿足自己的虛榮心,還有些是想通過(guò)“炫富”來(lái)獲得注意力,不管他們最初的動(dòng)機(jī)是什么,他們?cè)谖⒉┥匣ハ嗯时鹊摹办鸥弧钡男袨樯a(chǎn)了大量的消費(fèi)主義文化。由于微博的嵌套性和互動(dòng)性的特點(diǎn),微博博主所發(fā)布的信息會(huì)受到更多人的回應(yīng),回應(yīng)的網(wǎng)民也會(huì)生產(chǎn)更多的信息,這樣一來(lái)就會(huì)有更多的普通網(wǎng)民也加入了消費(fèi)主義文化的生產(chǎn)。事實(shí)上,在消費(fèi)社會(huì)中,消費(fèi)主義文化是無(wú)孔不入的。微博作為一種自媒體的傳播方式,不僅生產(chǎn)了很多社會(huì)新聞信息,同時(shí)也生產(chǎn)和傳播了大量的消費(fèi)主義文化。
3.消費(fèi)主義文化傳播速度更快。微博是及時(shí)信息發(fā)布的平臺(tái),微博是與手機(jī)媒體結(jié)合的最緊密的自媒體,公眾不僅可以隨時(shí)隨地通過(guò)微博來(lái)發(fā)布信息和圖片,同時(shí),公眾在微博上發(fā)布的信息和圖片也會(hu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傳播出去。因而,微博平臺(tái)上發(fā)布的消費(fèi)信息、圖片以及張揚(yáng)消費(fèi)主義文化的觀點(diǎn)和視頻會(huì)快速地傳播開(kāi)來(lái)。比如,在“郭美美”事件中,一個(gè)注冊(cè)的名字是“郭美美Baby”的20歲的女孩于2011年6月21日在新浪微博上發(fā)布了自己開(kāi)名車、背名包、住別墅的一些圖片,經(jīng)過(guò)網(wǎng)友們的互動(dòng)轉(zhuǎn)發(fā),當(dāng)日她的微博粉絲便從4000多飆升到55萬(wàn)多人。[5]
三、消費(fèi)主義文化對(duì)傳媒公共性的影響
微博是一種創(chuàng)新性的自媒體,它已經(jīng)成為消費(fèi)主義文化生產(chǎn)和傳播的重要平臺(tái),與傳統(tǒng)媒體一樣,消費(fèi)主義文化在微博上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傳媒的公共性。但是,由于微博的傳播模式與傳統(tǒng)媒體的根本差異,微博生產(chǎn)和傳播的大量的消費(fèi)主義文化一方面消解了傳媒的公共性,另外一方面對(duì)傳媒的公共性產(chǎn)生了一定的逆向刺激,呼喚傳媒發(fā)揮其公共性的本質(zhì)屬性。
1.公共性:傳媒的本質(zhì)屬性
德國(guó)社會(huì)學(xué)家哈貝馬斯在《公共領(lǐng)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一書(shū)中提出了公共領(lǐng)域的概念。當(dāng)時(shí),“公共領(lǐng)域”是一個(gè)特定的歷史范疇,是從18世紀(jì)至19世紀(jì)初英、法、德三國(guó)的歷史語(yǔ)境來(lái)闡明的一個(gè)理想類型,指由具有批判性的私人所組成的以公眾為主體的資產(chǎn)階級(jí)公共領(lǐng)域。在這里作為私人的公眾可以自由地集合、自由地表達(dá)他們的意見(jiàn),通過(guò)對(duì)普遍利益問(wèn)題展開(kāi)討論,形成公眾輿論,并且和公共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直接相抗衡。[6]他同時(shí)指出當(dāng)公共領(lǐng)域中的公眾達(dá)到較大規(guī)模時(shí),公眾交往就需要一定的傳播和影響手段,這時(shí)就要求大眾媒介成為公共領(lǐng)域的媒介。他進(jìn)而闡述了大眾傳媒的作用,并詳述了早期的小型報(bào)刊怎樣使得“私人”聚合而成公眾,公眾如何以報(bào)刊為平臺(tái)和論壇來(lái)形成批判性公共輿論的過(guò)程和狀態(tài)。[7]哈貝馬斯的分析表明傳媒公共性是與生俱來(lái)的,傳媒的發(fā)展是由于公眾交往的需要,公眾利用大眾傳媒形成的“公共領(lǐng)域”對(duì)公共問(wèn)題進(jìn)行討論、互動(dòng),進(jìn)而形成公眾輿論來(lái)對(duì)抗公權(quán),參與社會(huì)公共事務(wù)的管理。因而,我們可以說(shuō),公共性是傳媒的本質(zhì)屬性之一,這一點(diǎn)已經(jīng)得到了學(xué)界和業(yè)界的認(rèn)同。
2.消費(fèi)主義文化對(duì)傳媒公共性的消解
在消費(fèi)社會(huì)中,傳媒主要的功能是消費(fèi)信息的傳遞。傳媒不只是為公眾提供大量的各種廣告信息,同時(shí)媒介自身也成為公眾最離不開(kāi)的消費(fèi)品,從而被徹底地“消費(fèi)化”了。消費(fèi)社會(huì)中大眾傳媒制造的大眾文化已經(jīng)走向極端地“媚俗化”和“娛樂(lè)化”,娛樂(lè)占據(jù)著大量的媒體空間和資源,這就是尼爾·波茲曼所謂的“娛樂(lè)至死”的真實(shí)表現(xiàn)。大眾傳媒極力營(yíng)造消費(fèi)的氛圍,消費(fèi)需求被不斷地制造出來(lái),消費(fèi)欲望被不斷地刺激,個(gè)人占有欲極度膨脹,享樂(lè)主義、物質(zhì)主義成為生活的軸心。大眾傳媒已經(jīng)成為少數(shù)權(quán)勢(shì)人物營(yíng)利的工具,這就意味著媒體的環(huán)境監(jiān)測(cè)和社會(huì)監(jiān)督作用的缺失,進(jìn)而導(dǎo)致媒體對(duì)民主和正義的守望功能也不斷衰微。羅伯特·麥克斯切尼將矛頭指向了不斷集中的聯(lián)合媒介體系,他認(rèn)為媒體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受到最大商業(yè)利潤(rùn)的刺激,多數(shù)媒體通過(guò)兼并、合作等方式變得越來(lái)越集中,媒體變得越來(lái)越富有,民主卻越來(lái)越貧窮。[8]張金海、李小曼認(rèn)為傳媒公共性的缺失是政治和經(jīng)濟(jì)雙重邏輯制約的結(jié)果。[9]毋庸置疑,消費(fèi)社會(huì)中的大眾傳媒極力營(yíng)造消費(fèi)主義文化,已經(jīng)偏離了“公共責(zé)任”的軌道,傳媒的公共性存在缺失。
3.消費(fèi)主義文化對(duì)傳媒公共性的逆向刺激
微博作為新媒體的代表,它生產(chǎn)了大量消費(fèi)主義文化,同時(shí)也快速傳播消費(fèi)主義文化。從這個(gè)層面上來(lái)說(shuō),消費(fèi)主義文化在微博媒體上的膨脹消解了傳媒的公共性。但是,當(dāng)消費(fèi)主義文化在微博媒體上盛行的時(shí)候,呼喚實(shí)現(xiàn)傳媒的公共性——這看上去是個(gè)悖論,事實(shí)上卻是合理的。消費(fèi)社會(huì)中存在三類人:第一類人在符號(hào)的消費(fèi)中狂歡,得到滿足,他們極力迎合消費(fèi)主義,炫耀消費(fèi)帶來(lái)的符號(hào)價(jià)值和身份認(rèn)同。這類人掌握著社會(huì)大量的資源、權(quán)力和財(cái)富。第二類人極力爭(zhēng)取成為符號(hào)消費(fèi)的自由人,他們渴望體驗(yàn)符號(hào)消費(fèi)的狂歡,渴望進(jìn)入上流社會(huì),尋求身份認(rèn)同。他們通過(guò)努力有可能成為第一類人,他們?cè)谙M(fèi)社會(huì)中占有一定的資源,并擁有一定的財(cái)富。第三類人完全被排斥在符號(hào)消費(fèi)游戲之外,他們永遠(yuǎn)無(wú)法獲得上流社會(huì)的身份認(rèn)同,不可能實(shí)現(xiàn)符號(hào)消費(fèi)的狂歡。他們擁有的資源和財(cái)富最少,他們沒(méi)有權(quán)力,是社會(huì)的底層,第三類人在整個(gè)消費(fèi)社會(huì)中占有絕大多數(shù)。當(dāng)?shù)谝活惾死梦⒉┟襟w大力宣揚(yáng)消費(fèi)主義文化的時(shí)候,第二類人可能是跟隨、附和,然而第三類人卻是充滿了質(zhì)疑和反感,他們是“草根大眾”的代表,會(huì)通過(guò)微博表達(dá)自己的意見(jiàn)和看法,抵制過(guò)度消費(fèi)主義文化;同時(shí),他們期望傳媒承擔(dān)起社會(huì)公平、正義的責(zé)任。比如在“郭美美”事件中,郭美美在微博中曬出自己奢侈的生活,高調(diào)宣揚(yáng)消費(fèi)主義,大多數(shù)網(wǎng)民并沒(méi)有贊同她的消費(fèi)理念和奢侈生活,反而懷疑她的身份和財(cái)產(chǎn)的來(lái)源,在網(wǎng)民們跟蹤報(bào)道和關(guān)注下,挖掘出我國(guó)慈善事業(yè)運(yùn)作中存在的一些問(wèn)題。
事實(shí)上,消費(fèi)不僅是一種欲望,更是一種權(quán)力和資源的分配。在傳統(tǒng)媒體時(shí)代,消費(fèi)主義盛行,由于媒介傳播權(quán)控制在媒介組織手中,受眾只能被動(dòng)接受消費(fèi)主義文化,很少有“發(fā)聲”的機(jī)會(huì)。而在微博時(shí)代,傳播的模式發(fā)生了徹底的改變,傳統(tǒng)的受眾和傳者的地位也發(fā)生了改變。當(dāng)消費(fèi)主義文化在微博媒體上盛行時(shí),公眾就會(huì)強(qiáng)烈抵制消費(fèi)主義文化,同時(shí)促進(jìn)媒體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社會(huì)的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從而爭(zhēng)取社會(huì)公平和正義,促進(jìn)社會(huì)不斷改革和進(jìn)步。微博盛行以來(lái),已經(jīng)有很多個(gè)人因消費(fèi)主義欲望膨脹而“炫富”,網(wǎng)民和公眾通過(guò)微博來(lái)表達(dá)自己的意見(jiàn)和看法,督促傳統(tǒng)媒體介入調(diào)查“炫富”背后的財(cái)富來(lái)源。因而,在微博語(yǔ)境下,消費(fèi)主義文化的張揚(yáng)對(duì)傳媒公共性具有一定的逆向刺激作用,也就是說(shuō),消費(fèi)主義文化一方面消解了傳媒的公共性,另一方面又促進(jìn)了傳媒公共性的有效發(fā)揮。
[1]萊斯理·斯克萊爾.全球體系的社會(huì)學(xué)[M].合杰譯.美國(guó):約翰·霍普金斯大學(xué)出版社,1995
[2][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遜,三好將夫編.全球化的文化[M].馬丁譯.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1
[3]張佰明.嵌套性:網(wǎng)絡(luò)微博發(fā)展的根本邏輯[J].國(guó)際新聞界,2010,(6)
[4]孫衛(wèi)華,張慶永.微博傳播形態(tài)解析[J].傳媒觀察,2008,(10)
[5]佘世紅,賀麗青.微博語(yǔ)境下的新聞專業(yè)主義與新聞工作者角色的體認(rèn)——以“郭美美”事件為案例[C].香港中文大學(xué)《傳播與社會(huì)學(xué)刊》5周年國(guó)際學(xué)術(shù)會(huì)議,2012
[6][德]尤爾根·哈貝馬斯著.公共領(lǐng)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M].曹衛(wèi)東,王曉玨,劉北城,宋偉杰譯.北京:學(xué)林出版社,1999
[7]黃月琴.公共領(lǐng)域的觀念嬗變與大眾傳媒的公共性——評(píng)阿倫特、哈貝馬斯與泰勒的公共領(lǐng)域思想[J].新聞與傳播評(píng)論,2008
[8][美]羅伯特·麥克切斯尼.富媒體,窮民主:不確定時(shí)代的傳播政治[M].謝岳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
[9]張金海,李小曼.傳媒公共性與公共性傳媒——兼論傳媒結(jié)構(gòu)的合理建構(gòu)[J].武漢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科學(xué)版) ,2007, (11)
- 中國(guó)出版的其它文章
- 論《大學(xué)語(yǔ)文》教材的規(guī)范性、職業(yè)性與創(chuàng)新性——基于對(duì)2011年高職院校相關(guān)規(guī)劃教材的抽樣分析
- 以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機(jī)制保障高校體育類學(xué)報(bào)質(zhì)量的研究*
- 晚明插圖本圖書(shū)的盛行及其傳播功能
- 傳媒類上市公司營(yíng)運(yùn)能力與經(jīng)營(yíng)績(jī)效分析
- 媒介技術(shù)變革下的藝術(shù)網(wǎng)絡(luò)化
- 簡(jiǎn)析梁?jiǎn)⒊瑫?shū)評(píng)《紹介新著〈原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