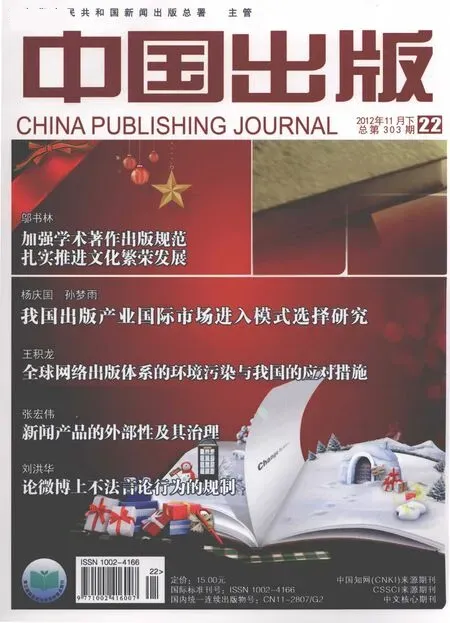論微博上不法言論行為的規制
文/劉洪華
微博已經“成為一種新的社會生活方式,”[1]它極大地拓展了言論傳播渠道,個人可以自己通過微博發表意見,各級政府部門也開辦官方微博,與民眾溝通,甚至在國際上,各國已將微博作為一種外交方式,即所謂“微博外交”。[2]微博已經并必將進一步深刻地影響當今社會。但是,微博在給我們帶來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目前,辱罵和謠言已經成為微博的兩大公害。辱罵是嚴重的侵犯他人人格權的不法行為。而通過微博傳播謠言更會擾亂社會秩序,導致嚴重后果,2011年通過微博謠傳的海鹽核污染事件[3]即是典型例證。微博是人們言論自由的平臺,但是言論自由不是無任何限制的,辱罵和謠言絕不是言論自由的象征,我們必須對微博上的不法言論行為進行規制,以使微博能更好地服務社會。
一、關于微博言論行為規制的錯誤認識
微博是新生事物,其誕生為人們的言論自由提供了廣闊空間。然而,微博是一種網絡虛擬平臺,具有虛擬性和傳播快捷性等特點。由于其虛擬性,人們在微博上的言論往往少了很多拘束和謹慎,具有侵權內容之言論時有出現;由于其傳播快捷,微博上的言論會在瞬間廣泛傳播,造成廣泛的社會影響。侵權性質的言論或者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謠言一旦在微博上傳播,其影響范圍將極其廣泛,危害后果極其嚴重。目前人們對微博言論行為的規制,尚存在以下錯誤認識。
第一,認為規制微博上的言論行為會打壓言論自由。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微博的確是人們言論自由的新興平臺,但是,言論自由并不意味著可以隨心所欲。人們既沒有辱罵他人的自由,也沒有制造謠言和傳播謠言的自由。微博上的言論自由必須有一個邊界,規制微博上的言論行為并非要打壓言論自由,而是限制不法言論行為,使人們的言論自由得以更充分的實現。辱罵和謠言絕不能代表言論自由,若不對微博上的辱罵和謠言加以制止,則作為文明時代產物的微博就可能帶來不文明的辱罵和謠言時代。
第二,認為微博上辱罵和造謠者眾多,法不責眾,難以找到違法者,于是對這些不法行為只能聽之任之。筆者認為這是一種錯誤認識。其一,在微博上辱罵他人嚴重侵犯了他人的人格權,在微博上傳播謠言會造成嚴重社會危害后果。沒有一個社會視辱罵和謠言為正常,我們同樣不能縱容這種行為。其二,難以找出違法者,既有微博設計本身的缺陷,也有缺乏制約機制的原因。恰當的辦法是完善微博本身和建立制約機制,而不是以此為借口不處理違法者。
第三,認為辱罵和造謠為個人找到一個發泄口,是社會的緩壓器。這種認識更不能接受。個人不能以一種錯誤的方式去緩解壓力,更不能以給別人帶來痛苦的方式去緩解壓力。
微博促進了社會進步,但也帶來了問題。我們既不能因為其存在問題而因噎廢食,摒棄微博,也不能忽視問題的存在,使微博帶病前行。正確的辦法是探討微博上不法行為泛濫的原因,找出應對這些不法行為的對策。
二、微博上不法言論行為泛濫的原因探討
1.自主性和大眾性加劇了不法言論行為的泛濫
自主性和大眾性是微博區別于傳統媒體的最大特點,也是微博的生命力所在。但是,自主性和大眾性也加劇了一些不法言論行為的泛濫。自主性表現為個人通過微博可以隨時隨地自主地傳播信息,表達意見,不像傳統媒體必須由編輯選擇決定發表什么信息。在傳統媒體時代,為了保證媒體不至成為不法言論傳播的工具,媒體自身有過濾審查社會信息的機制,那些辱罵和謠言都被傳統媒體的編輯過濾掉了。沒有過濾審查是微博的優勢,但也正因為如此,微博成了某些不法言論傳播的工具。微博是一種大眾化的言論平臺,理論上幾乎所有人都可以通過微博發布信息和發表意見。大眾性給了所有人快捷傳播自己言論的機會,但是同時,由于缺乏制約機制,加之羊群效應的影響,微博成了辱罵和謠言的集散地。
2.缺乏制約機制是不法言論行為泛濫的根本原因
微博的技術特點使微博成為謠言和辱罵傳播的理想工具,但這只是形式上的。這種形式上的原因還容易滑向素質論,認為在大眾傳播時代,傳播者的素質良莠不齊是微博上不法言論行為泛濫的主要原因。然而,素質論者無法解釋,為什么一些通常意義上的高素質者在微博上也會口無遮攔,臟話連篇。筆者認為,缺乏制約機制是微博上不法言論行為泛濫的根本原因。那些人在傳統媒體上和微博上截然不同的表現,源自于傳統媒體的嚴格的制約機制,而作為自媒體的微博恰恰缺乏這種制約機制。在傳統媒體上,作者的稿件要通過編輯的審查,還要由主編定稿。在嚴格監督制約下,由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責任定位,即使有人有不軌的想法最終也難以實現。但這一事前制約機制在微博上蕩然無存,加之目前微博的設計缺陷,使得違法者的責任很難追究,即使被追究,其所付出的違法成本也非常低。這種事前制約機制不存在,事后制約機制又難以發揮有效作用的狀況,才是導致微博上不法言論行為泛濫的根本原因。
總之,目前微博上不法言論行為泛濫的根本原因是治理機制沒有跟上快速發展的微博技術。現有的治理停留在傳統媒體時代。盡管法律已對辱罵和造謠提供了充分的處罰依據,但是微博畢竟是新技術的產物,傳統的治理機制和方式必須針對微博的特點進行調適或完善,才能實現對微博上的言論行為的有效規制。
三、微博不法言論綜合治理機制探討
1.微博上不法言論行為規制現狀
(1)國家機關對微博上不法言論行為的規制
國家機關是治理微博上不法言論行為的主導力量。國家機關運用相關法律,治理微博上不法言論行為,為公眾言論指引正確的方向。行政機關是治理微博上不法言論行為的重要力量。我國相關行政法律法規對網絡言論行為作了最直接的規定,如《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第57條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利用電信網絡制作、復制、發布、傳播含有侮辱或者誹謗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信息,也不得利用網絡散布謠言。《治安處罰法》規定,對于“散布謠言,謊報險情、疫情、警情的”(參見《治安處罰法》第25條)和“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參見《治安處罰法》第42條),公安機關可以依法進行治安處罰。人民法院通過依法處理微博上的侵權案件和犯罪案件,規范微博上的言論行為。但是,僅僅依靠國家機關對微博的治理還是不夠的,一方面,國家機關對微博的規制一般都是事后處理,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如,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的追究,都是微博上侵權或犯罪行為發生后才進行;另一方面,微博的信息量像海洋一樣,僅僅依靠警方和其他國家機關的力量,不足以治理微博上的不法行為。
(2)微博運營商對微博秩序的規制
我國法律明確規定了微博運營商協助規制微博秩序的責任。《侵權責任法》第36條明確規定:“網絡用戶利用網絡服務實施侵權行為的,被侵權人有權通知網絡服務提供者采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網絡服務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時采取必要措施的,對損害的擴大部分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網絡服務提供者知道網絡用戶利用其網絡服務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運營商可以通過技術措施事前過濾辱罵性語言,也可以事后接受投訴,采取刪除等措施。不過,運營商治理同樣面臨一些問題。第一,事前只能過濾一些辱罵性語言,而謠言是無法過濾的;第二,面對海量信息,運營商治理的能力也難以企及。據報道,新浪微博有多達300人的信息過濾團隊。[4]然而,即使有3000人的過濾團隊,也無法處理數以億計的不當信息。因此,如果僅僅依靠運營商治理微博,那么運營商要不就疏于管理以節約成本,否則嚴格管理的成本難以承受。
目前由國家機關和運營商主導的治理機制對微博環境治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僅僅依靠這些治理機制還是不夠的,應當建立綜合治理微博的機制。
2.綜合治理機制的主要內容
言論自由不是辱罵和造謠的自由,微博絕不能成為“公共廁所”。[5]治理微博上的不法言論行為,要堅持綜合治理原則。綜合治理主要指,對微博上言論行為的規制要綜合利用多方面的力量,以國家機關的規制為主導,微博運營商從技術等層面協助治理,充分發動群眾,組建微博自律協會對微博進行日常性規范管理,同時在法律規制方面強調發揮民事懲罰性賠償責任的威懾力。
就我國微博治理的具體情況來看,當前進行綜合治理需從以下幾方面展開。第一,政府要加強對微博治理的力度,運營商需從技術層面為微博的規制提供更多的支持。政府應當充分調動現有執法力量,盡量做到有法必依;運營商應當做好事前對不良信息的過濾,并為其他治理提供技術支持。第二,法律規制方面,要發揮民事賠償責任的威懾力。通過法律規定微博用戶的義務,對于違反義務侵犯他人權利的,施之懲罰性賠償責任,并建立網上法庭便利微博侵權案件的處理。第三,發動群眾力量,組建微博自律協會,對微博進行日常化規范管理。
完善對微博言論侵權行為人的民事責任的追究和建立微博自律協會機制,是當前我國微博治理的重要工作,下文將重點論述這兩方面。
四、用戶義務及對應的民事責任的規范
1.微博用戶的義務
權利往往與義務相對應,微博用戶行使言論自由權時必須承擔相應的義務。微博用戶的義務主要有審查義務和實名發言的義務。
(1)對自己作品的審查義務
微博上的作者,既包括微博博主,也包括評論者。評論者指的是僅僅評論他人微博而不轉發的人。微博上的作者是自己作品的編輯,必須對自己所寫的文字負責。具體地說,微博上的作者應當承擔以下但不限于以下義務:第一,對自己發布的信息的真實性負責。微博時代,是全民皆記者的時代。既然微博用戶做了記者的事,那么就要履行記者的責任。記者的首要責任就是必須保證自己發布的信息的真實性。微博用戶所發布的信息,必須經過核實。如果故意捏造事實,首先要受到微博自律協會的處罰,如果造成了一定的社會危害,還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當然,對于一些并非故意的失實報道,為鼓勵新聞傳播,可以免責。第二,作者不得發布可能侵犯他人權利的內容。這里著重指的是不得通過微博發布辱罵他人的言論和圖片。微博擁有巨大的傳播效力,在微博發布辱罵他人的言論和圖片將造成受害人嚴重的精神傷害。對此法律不能容忍。
(2)對轉發作品的審查義務
微博用戶對轉發作品的審查義務主要包括:第一,博主不得轉發失實的微博。如果博主轉發了內容失實的他人微博,可能要承擔一定的法律責任。對不同的博主,要有不同的處理辦法。粉絲越多,責任越大。也就是說,對于粉絲數量大于一定數量(比如粉絲數量超過一萬人)的博主,應當加強其審核責任。未經審核轉發失實消息,應當承擔相應責任。對于數量不大的博主,由于其轉發的影響力有限,可以免除其審核責任。第二,博主同樣不得轉發可能侵犯他人的權利的微博。例如,對于侵犯他人隱私權的,侮辱、誹謗他人的微博不得轉發,否則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3)實名發言和轉發的義務
對于要不要實名,爭議很大。同意者認為,實名可能可以抑制謠言和辱罵的產生;而反對者則認為,在目前的形勢下,可能會干預言論自由。筆者認為,實名是自己負責的前提。不過為了不對言論自由產生影響,要區別對待。第一,對于一些粉絲較少的微博,可以實行前臺匿名、后臺實名的方式。運營商必須要保證微博用戶的后臺個人信息安全,非經法院同意,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微博匿名的主要意義在于保護用戶匿名發聲的權利。一個人可能基于情面等方面的考慮,要求匿名發表意見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一些人只是想在網上發表自己的觀點,但并不想把這些觀點帶入生活中去。考慮到匿名微博可能更換名稱,應當給每個匿名微博配置與其后臺信息專一對應的賬號。這樣,每個人只可能注冊一個微博,而不可能通過注冊多個微博以逃脫責任。第二,對于粉絲眾多的用戶,由于其微博具備公共性的特征,用戶應當實名。此時微博不再是這些用戶的私人空間,而更多具有公共媒介性質。微博用戶應當公開自己的部分信息以便利公眾監督。
2.對違反義務的微博用戶的民事責任的追究
(1)對嚴重違法者追究懲罰性賠償責任
目前在我國,網絡用戶侵權責任的承擔與其他一般侵權責任的承擔沒有原則的區別。利用網絡侵權,如利用微博辱罵、誹謗他人,侵權手段更隱秘、更便捷,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更廣泛,侵權后果更嚴重,僅承擔一般的民事責任,對侵權人威懾力不夠,且與其違法行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不相稱,應該采取懲罰性賠償。
懲罰性賠償是損害賠償的一種,與補償性損害賠償相對,是指當被告以惡意、故意、欺詐或放任之方式實施加害行為而致原告受損時,原告可以獲得除實際損害賠償金之外的損害賠償。[6]該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其目的在于對被告施以懲罰,以阻止其重復實施惡意行為,并警戒他人和保護公共和平。我國立法首次規定懲罰性賠償是1993年《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目前,我國立法已經規定了若干懲罰性賠償責任,《侵權責任法》第47條確立了懲罰性賠償責任在侵權法中的適用。在英美法中,懲罰性賠償產生的早期主要適用于誹謗、誘奸、惡意攻擊、私通、誣告、不法侵占住宅、占有私人文件、非法拘禁等使受害人遭受名譽損失及精神痛苦的案件。[7]
通過微博發布不法言論,辱罵、誹謗他人會使受害人遭受更大的名譽損失和精神痛苦,我國應當借鑒英美法系國家的名譽權損害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制約微博上的不法行為,以解決這些案件的精神損害無法衡量以至于無法得到賠償的問題。美國學者丹·道布斯(Dan Dobbs)也認為,懲罰性賠償具有補償心靈痛苦( intangible injury)的功能。[8]大陸法系經典民法理論認為,損害賠償的基本功能在于補償受害人,該種補償不能超過損失的數額,否則會給受害人以不當得利。受大陸法系民法理論的影響,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引進和適用在我國是非常謹慎的。目前,這種觀點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我國學者一般都認可侵權法的懲罰侵權人和制裁侵權行為的作用,并且侵權法中明確規定了懲罰性賠償責任。筆者認為,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嚴重的微博侵權行為,法院在決定受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時,完全可以且應當考慮懲罰性賠償的因素,以達到補償受害人和懲罰侵權人的目的。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條的規定,我國精神損害的賠償數額根據侵權人的過錯程度、侵害的手段、場合、行為方式等具體情節、侵權行為所造成的后果等因素確定,因此,對于利用微博辱罵、誹謗他人的案件,法院完全可以判處比一般同類侵權更高的賠償額。因為網絡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為了規范網絡行為,我國關于網絡侵權的相關司法解釋應該明確規定利用微博發布不法言論,辱罵、誹謗他人侵犯他人權利的,法院可判處高于一般同類侵權一倍以上的賠償金。只有加大對此類行為的懲罰力度,才能減少直至杜絕這些行為。
(2)建立網上法庭,簡化訴訟程序
由于網絡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且目前網絡侵權呈多發狀態,筆者認為,法院可以建立針對微博上辱罵、誹謗等不法侵權行為的網上法庭,以簡化訴訟程序,便捷受害人維護自身權益。
網上法庭可以按如下思路設計。第一,網上法庭是由人民法院在網上建立的聯結各主要微博網站的處理微博上不法侵權行為的法庭。第二,受害人可以直接通過微博向網上法庭起訴。受害人只需要向網上法庭提交侵權人的微博賬號、以及涉嫌侵權的截屏即可提起訴訟。第三,網上法庭在接到訴訟材料后,應當由系統自動轉發給侵權人,由侵權人在24小時內就侵權行為做出說明。第四,網上法庭應當自接到受害人訴訟材料15個工作日內就該侵權行為作出判決。第五,不法侵權行為成立的,由擁有微博賬號的人承擔侵權責任。侵權人和微博賬號所有人并非一人的,不影響所有人承擔責任。所有人與侵權人之間的責任分擔,可由所有人與侵權人另行解決。第六,受害人提起訴訟應當通過銀行轉賬支付一定的訴訟費,如果被告敗訴的,該費用由被告承擔。筆者認為該訴訟費以200元為宜,訴訟費的設置一方面可以提醒受害人謹慎起訴,另一方面也可以促進網上法庭的建設。
網上法庭設立的初期,工作量可能會很大,但是只要網上法庭能夠堅持不懈地對不法侵權行為進行處理,不法侵權行為一定會逐漸減少,人們能擁有一個文明的網絡環境。
五、微博自律協會對不法行為的規范
1.微博自律協會的性質和構建
微博上不法言論行為的治理,需要充分調動群眾的力量。成立微博自律協會來行使對微博的規范管理是行之有效的辦法。微博自律協會是由微博用戶組成的群眾性組織,與其他機構相比,自律協會對微博的管理有著自己的優勢:第一,自律協會沒有利益沖突,可以保持中立。自律協會受理員由微博用戶中的自愿者組成,自愿者參加目的更多是出于公益,這是其能公正對待各種投訴的基礎。第二,只有自律協會有能力應對微博上針對辱罵和謠言的投訴。微博上的投訴數以億計,僅僅依靠運營商和政府的力量顯然是不現實的。微博自律協會則可以組織數量龐大的受理員,處理這些投訴。
微博自律協會在性質上是由全體微博用戶組成的自律性組織。微博用戶實質上是微博自媒體的編輯,類似于傳統媒體的編輯,應當有自律組織對其行使自律管理,對于違反“職業道德”的微博編輯進行處罰,以維護微博的環境。自律協會進行的處罰屬于行業紀律處罰。目前,微博用戶可以關閉對特定人的評論。由于微博的媒體性,禁止他人評論實際上也是一種處罰。但是這種處罰相比于自律協會的處罰,是一種私罰。當然,這種私罰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即微博博主可以避免辱罵者的騷擾。但是,微博博主擁有這種權利后,很容易濫用,他不僅關閉那些針對辱罵者的評論功能,也極有可能關閉與自己觀點不同的人的評論,從而剝奪他人公平發言的機會。這樣的微博就成了一言堂。正確的做法是,由博主申訴到微博自律協會,由微博自律協會負責處罰有不當言論的人。
微博自律協會應當由運營商負責籌建,受理員由微博用戶推薦,推薦者的人數達到一定的數量,比如200人,即可成為微博自律協會的受理員。由于門檻低,微博自律協會的受理員數量可以足夠多,足以應對微博上的巨量投訴。受理員應當承諾公正地履行職責,并接受微博用戶的監督。
2.對微博上不法行為的規范
微博自律協會的職責是接受他人投訴,并對經證實的辱罵和謠言進行處罰。具體如下。
第一,投訴的范圍。投訴對象只應該是侮辱、誹謗和謠言的發布者或轉發者以及侵犯他人知識產權的人。之所以投訴僅限于上述幾項,一是因為上述幾項容易達成共識;二是必須對投訴的范圍有所限制,否則,可能限制言論表達與傳播。
第二,處罰。對于經證實的侮辱、誹謗和謠言,微博自律協會根據情節輕重,可以采取刪除帖子、禁止一定期限內使用微博、關閉微博賬號等措施。由于是微博自律協會行使處罰權,上述處罰的性質是紀律處罰,類似記者協會對記者的處罰。該處罰具有終局性,對該處罰不服的,不得起訴到法院。當然,紀律處罰并不替代法律責任。微博用戶由于違法所應當負的法律責任不因紀律處罰而免除。
第三,程序。無程序,無正義。任何處罰必須符合微博自律協會發布的投訴處罰程序。投訴程序應當如下:①投訴者向微博自律協會發出投訴。投訴者必須提交相關證據。②微博自律協會接到投訴后,將投訴材料發送給被投訴者,被投訴者就投訴可以在12小時內進行辯解。③微博自律協會將投訴材料和被投訴者的辯解隨機發送給在線的一定數量(比如20名)的微博自律協會成員,微博自律協會成員應當在12小時內就該投訴是否成立和如何處罰發表意見。④微博自律協會根據多數成員的意見決定投訴是否成立和如何處罰。
運營商應當提供技術支持保證微博自律協會可以自動地履行上述程序。
通過民事責任的威懾和微博自律協會的監督,輔之以微博用戶的自覺、社會各方面的共同關注,必將能還微博以更純凈的環境,使微博可以發揮更大的社會作用。
注釋:
[1]2011上半年度中國微博報告發布[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07-19
[2]曹斯,昌道勵.“微博外交”時代來臨 駐華使館微博各有各精彩[EB/OL].http://media.people.com.cn/GB/40728/14902747.html專家稱食用碘鹽對防核輻射無效 擔心海鹽受核污染無根據[EB/OL].http://finance.sina.com.cn/g/20110317/17499550299.shtml謠言橫飛或成“公共廁所” 微博還能搏動多久?[EB/OL].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11-03/23/c_121219055_3.htm周立波微博“公廁說”惹眾怒:成也草根 敗也草根[EB/OL].http://www.cnr.cn/allnews/201011/t20101129_507393696.html
[6]陳燦平.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理論定位與適用范圍[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7)
[7]王利明.懲罰性賠償研究[J].中國社會科學,2000,(4)
[8]Dan Dobbs.Ending Punishment in "Punitive" Damages: Deterrence-Measured Remedies[J].40 Alabama Law Review 831,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