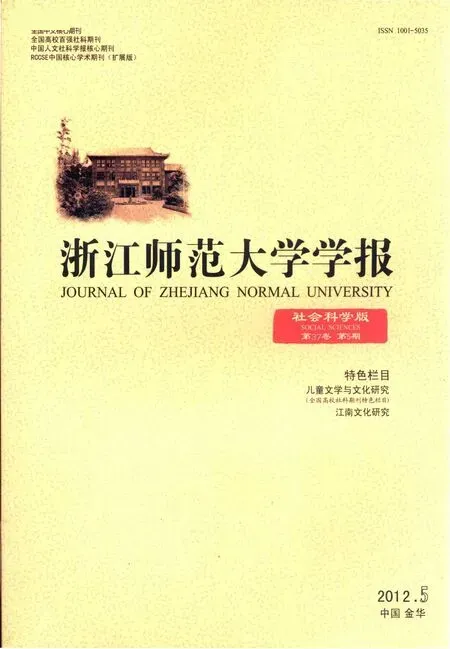“吳越爭霸”故事研究述評
潘德寶
(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春秋末期吳越兩國之間的爭霸故事,散見于《左傳》、《國語》、《墨子》、《呂氏春秋》、《史記》等典籍。經過東漢人的踵事增華,該故事首尾俱全地保存于《吳越春秋》和《越絕書》姊妹篇中,流傳后世。對該故事的研究,截止2011年3月,大陸和臺灣的碩士博士論文計有30多篇,據中國知網和臺灣、日本有關文獻目錄粗略統計,共有研究論文380篇左右,專著20多部,可見其盛。
因為“吳越爭霸”故事明顯地帶有地域性,所以江浙一帶的學報長期關注這一領域。另外,臺灣地區的論文數量雖然遠少于大陸,但卻少重復建設的弊病,加上碩士博士論文往往引入新理論、新方法,令人耳目一新,故而值得大陸學界參考。根據敘事學的基本觀點,我們將故事與文本分開,對這些研究成果加以綜述。
一、故事的文本整理及論爭
文本是故事存在的基礎。“吳越爭霸”故事最重要的兩個文本是《吳越春秋》和《越絕書》,對這兩部書作文獻整理,是研究的基礎。文獻本身的問題以及論者的不同視角,形成了一些論爭。
《吳越春秋》最早的文獻整理成果為臺灣洪丙丁的碩士論文《吳越春秋斠證》(刊于1981年《臺灣師范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第25輯),此書沒有引起大陸學者的重視。大陸最早的整理本為苗麓點校本《《吳越春秋》》(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初版,1999年經辛正審訂后納入《江蘇地方文獻叢書》)。質量較高的校本為周生春的《吳越春秋輯校匯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該本集海內外十種版本斠讎,考證翔實,“校勘精當,成為《吳越春秋》理想的版本”。
因為《吳越春秋》這一文本故事情節集中,主題鮮明,語言成熟,申明復仇報恩之義、弘宣忠信仁義之道、彰顯興衰成敗之理,思想內涵豐富,[1]加上兒女、英雄的生命本性和浪漫激情,使整個“吳越爭霸”故事帶有濃重的悲劇色彩,[2]而情節的離奇曲折,又使故事具有傳奇性,①因此,受到的關注度也就較高。
《越絕書》,有張宗祥《越絕書校注》(商務印書館,1956)、張金城《越絕書校注》(臺灣師范大學博士論文,1984)、樂祖謀《越絕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李步嘉《越絕書校釋》(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張仲清《越絕書校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等整理本。“從校勘角度來看,李步嘉校釋本為集大成之作”,王利器贊其“校釋所就,已度越錢(培名)、張(宗祥)”。張仲清校注本后十多年而出,有機會吸收各本所長,亦可參看。
當然,“吳越爭霸”故事并不只存在于這兩個文本中,《左傳》、《國語》、《史記》等書也已經有了較好的校注本,“吳越爭霸”故事的文本自然也得到了解決。但因這些著作主體并非該故事,本文就不作過多介紹了。總之,有關“吳越爭霸”故事兩個重要文本的整理工作,已經基本解決,其中周生春《吳越春秋輯校匯考》、李步嘉《越絕書校釋》兩書用功較深,推進了“吳越爭霸”故事的研究。但由于文獻本身的問題,圍繞著這兩個文本,學界在一些問題上尚不能形成共識。
《越絕書》的書名、作者與版本問題錯綜復雜,李步嘉的《〈越絕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是研究這些問題的集大成者。該書帶有綜述性質,將歷代相關討論一一列出,并出以己見,后來的研究大多沒有逸出該書討論的范圍。②首先是《越絕書》的書名問題。李著認為,《越絕書》的“絕”字學術史上有三種看法:1.作“奇絕”解;2.仿《春秋》“獲麟”之“圣人沒而微言絕”之意;3.綜合說,“絕”字“殆猶《詩》之三家異說也”。其次是《越絕書》的作者問題。有四說:1.子貢或子胥說。此說后人大多不予采信;2.袁康、吳平說。此說一直是主流觀點,為明代楊慎從《越絕書》內文隱語中提出,但倉修良《〈越絕書校注〉序》(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一文認為“袁康、吳平”子虛烏有;而李步嘉《〈越絕書〉研究》在眾人基礎上,提出“袁康、吳平”為三國時袁術的政治讖語;張仲清則提出隱語為宋末所加,而反對李說;3.“戰國人所作、漢人附益”說;4.“成非一人,無撰人姓名”說。后兩說相近,在目前沒有更多證據的情況下,此兩說為勝。最后是《越絕書》的性質問題。黃葦《關于〈越絕書〉》(《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4期)、王志邦《〈越絕書〉再認識》(《中國地方志》2005年第12期)、賀雙非《〈越絕書〉的作者、版本及價值》(《圖書館》2008年第4期)認為此書為“地方志”;倉修良《〈越絕書〉是一部地方史》(《歷史研究》1990年第4期)、《〈越絕書〉江浙兩省共有的文化遺產——兼論〈越絕書〉的成書年代、作者及性質》(《江蘇地方志》2006年第4期)等文秉承歷來目錄學的分類,認為此書為“地方史”;趙雅麗《試論〈越絕書〉的小說化傾向》(《語文學刊》2008年第17期)則承郭丹《史傳文學》一書中的意見,認為該書有小說化傾向,異于前兩種觀點。
《吳越春秋》的作者、版本雖然較《越絕書》分歧要少,但也有一定的爭論。③現存《吳越春秋》十卷皆題為東漢趙曄作。陳中凡《〈吳越春秋〉為漢晉間的說部及其在藝術上的成就》(《文學遺產增刊》第七輯,1959)一文開始懷疑《吳越春秋》的作者并非經師趙曄。上世紀80年代,曹林娣《關于〈吳越春秋〉的作者及成書年代》(《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4期)反對陳中凡的懷疑,認為“今傳本《吳越春秋》,始作者為東漢趙曄,曾經楊方刊削,皇甫遵則斟酌乎曄、方之間,重新作了編寫,今本已非曄書完帙”。此說確認了趙曄的著作權。梁宗華《現行十卷本〈吳越春秋〉考識》(《東岳論叢》1988年第1期)、周生春《今本〈吳越春秋〉作者成書新探》(《文獻》1996年第2期)、呂華亮《〈吳越春秋〉研究》第一章(安徽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5)等文觀點大致相近,在確認趙曄著作權的前提下,認為今本出于皇甫遵的編定。劉曉臻《〈吳越春秋〉研究》(山東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5)則認為今本實為趙曄舊本。這幾種說法大體上與曹林娣說相近,而又不違舊籍,可以采信。
關于《吳越春秋》文本爭論的熱點,在于其性質或體裁。曹林娣《試論〈吳越春秋〉的體裁》(《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1期)、《〈吳越春秋〉文學成就初探》(《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1期)、梁宗華《一部值得重視的漢代歷史小說》(《浙江學刊》1989年第5期)、黃仁生《論〈吳越春秋〉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文言長篇歷史小說》(《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4年第3期)、羅俊華《〈吳越春秋〉研究》(武漢大學碩士論文,2004)、付玉貞《〈吳越春秋〉試論》(四川大學碩士論文,2005)、商光鋒《〈吳越春秋〉研究》(曲阜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6)、林小云《從歷史敘事走向文學敘事——從史料的運用看〈吳越春秋〉的敘事特征》(《中州學刊》2009年第2期)等文都回顧了前人對《吳越春秋》體裁的討論,并認為該文本為小說,其中又以黃仁生先生的觀點最為鮮明;陳橋驛《〈吳越春秋〉及其記載的吳、越史料》(《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1期)、倉修良《〈吳越春秋輯校匯考〉序》(《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3期)、周生春《〈吳越春秋輯校匯考〉緒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等文則堅持舊說,認為《越絕書》雖有“小說家言”,仍不妨為史部作品。
這些論文主要從該文本的體裁特征(是不是近于編年史)、所述故事的可信度、文學性的強弱(人物形象的塑造角度)來討論其性質。我們認為,不同時代對《吳越春秋》有不同的性質定位,實際上反映著時代觀念的變化,這在其他文本的接受史上也屢見不鮮;因此,值得注意的并非各種不同見解本身的合理與否,而是形成某一類觀點的歷史背景和文化結構。金其楨《〈吳越春秋〉“內吳外越”探辯》(《贛南師范學院學報》1993年第1期)、《試解〈吳越春秋〉的“不可曉”之謎》(《史學月刊》2006年第6期)認為,今本《吳越春秋》以“傳”來題吳國故事、以“外傳”來題越國故事,指出這種“內吳而外越”的觀念隱含著寫作的歷史背景和文化結構:這是由作者以周室為正統的儒家立場和觀點所決定的。金其楨還認為,“傳”、“內傳”的區別在于:趙曄在《吳越春秋》記述吳史事的前五卷中,稱“傳”各卷的材料基本上來自于正史、雜史文獻資料,系“鈔撮”古史書匯集整理而成;稱“內傳”各卷只有少部分材料來自正史、雜史文獻資料,而相當一部分材料乃至大部分材料則來自民間傳說、遺聞逸事以及自己的想象演繹。這個結論實質上指出了趙曄自己對《吳越春秋》的定性:有“小說家言”,也有“史籍”改編,這其實為該書的“文史之爭”找出了一條新的路子。
二、“吳越爭霸”故事研究
茅盾《關于歷史和歷史劇——從臥薪嘗膽的許多不同劇本說起》(《文學評論》1961年第5-6期)這篇長達100頁的文章,最早最全面地論述了“吳越爭霸”的故事:文章第一部分考證了該故事的先秦兩漢時期的各個文本;第二、三部分展示了吳越兩國爭霸的史實;第四部分對該故事的人物作了全面的論述;最后兩部分則結合明清戲劇中的爭霸故事,為當代歷史劇的改編指明了方向。
這篇文章考證嚴密、材料豐富,提出了很多極好的意見和建議。但后來的研究者似乎視而不見。比如,此文已經提出,西施這一人物與爭霸故事的交叉當為趙曄的藝術虛構。臺灣曾永義《西施故事志疑》(《現代文學》1971年第44期;又載曾氏所著《說俗文學》,臺北:聯經出版社,1984)一文依據民間傳說、文學創作的規律,也指出西施是出于《吳越春秋》的虛構;白耀天《西施考辨》(《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4期)從考證角度指出,《墨子·親士》所載之西施材料不足據,先秦諸籍皆未言及越王勾踐獻西施事,有力地論證了西施為古代美女之通稱,“吳越爭霸”故事中的西施出諸小說家言;顧希佳《西施的傳說、史實及其他》(《民間文學論壇》1998年第1期)從民間文學的角度提出比較折中的看法,認為先秦諸子所載之西施實有其人,但“西施復國”純為小說家言,是后人附會的傳說,西施的意義并非在于吳越史實,而是文化史。這幾篇文章從不同角度佐證了茅盾的觀點。但上世紀80年代,卻有很多文章仍在考證西施的籍貫、下落等,甚至還一度形成研究的熱點,這實際上就是忽視茅盾文的結果。
茅盾之后,絕大多數的研究都不再具有如此龐大的組織,均未從全部文本整體上去考論“吳越爭霸”故事,而往往只取某一個文本進行研究,例如蘇哲《〈吳越春秋〉人物創造論》(《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4期)、林小云《〈吳越春秋〉的寫人藝術》(《欽州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等。陳雅萍《由〈左傳〉、〈國語〉看〈史記〉人物形象的特出——以吳越爭霸相關人物為例》(臺灣政治大學碩士論文,2003)挖掘了《史記》中勾踐、夫差、范蠡等人物形象;付玉貞《〈吳越春秋〉試論》(四川大學碩士論文,2005)倒是以《吳越春秋》為中心,把《左傳》、《國語》、《史記》四種文本中的謀臣、君主、奸臣的人物形象作了總結歸納,認為《吳越春秋》在塑造人物的藝術手法上有了很大的進步,但也只是涉及“人物形象”而已,遠沒有茅盾文章論述得全面。
“吳越爭霸”故事的研究重心最終落在了“人物”研究上,成果有偉立《勾踐雪恥復國》(《歷史知識》1982年第6期)、王文清《論吳王闔廬》(《東南文化》1986年第1期)、辛土成《論闔閭的社會改革和吳國的興亡》(《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1期)、王衛平《論吳王闔閭》(《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3期)、陳橋驛《論勾踐與夫差》(《浙江學刊》1987年第4期)、馮慶余《夫差與勾踐的得失》(《吉林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2期)、鐘繼彬《春秋五霸與吳王夫差》(《文史雜志》1998年第5期)、周百鳴《論勾踐的用人之道》(《歷史教學問題》2001年第1期)、黃敏《伍子胥、勾踐、夫差復仇比較——〈史記〉中復仇意識管窺》(《濱州職業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徐海通《春秋梟雄吳王闔閭——〈左傳〉中闔閭形象簡析》(《長春大學學報》2010年第7期),等等。這些文章往往只研究某一個人物,而且多數僅為生平介紹式。其中,黃仁生的《從歷史走向文學——論〈吳越春秋〉的人物藝術》(《社會科學戰線》1995年第4期)分析人物較為全面,依據性格的倫理內涵把“吳越爭霸”中的人物分成三類:一是仁君、明君與昏君、暴君形象群;二是忠臣與讒臣、奸臣形象群;三是俠義形象群。這種相互對照又相互映襯的形象系列構建,為故事的敘事動力和藝術表現的研究開啟了方向。
“吳越爭霸”故事中的其他人物,雖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終不若西施、伍子胥、范蠡那樣深入。
(一)西施
西施應該是“吳越爭霸”故事中被研究得最多的人物。考察西施形象的歷史演變,不止具有文學史的意義,還具有文化史的意義。
從演變角度研究西施形象,有3篇碩士論文收集材料較為豐富,它們是葉仲容的《西施故事源流考述》(臺灣政治大學碩士論文,1990)、謝芳芳的《〈浣紗記〉故事源流考》(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04)和張艷萍的《梁辰魚〈浣紗記〉西施形象新探》(曲阜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9)。后兩篇雖側重于《浣紗記》的研究,但都設有專章討論歷代的西施形象,指出西施乃是先秦時即廣受歡迎的美女代稱,到了東漢,才在稗官野史的附會中成為吳越歷史的一部分。而美女故事一直是最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西施故事于是在文人士大夫及地方傳說的創造因襲中,漸漸孳乳壯大,終于由一虛構體變成為動人凄美的成熟故事。
孫肅《“西施”故事的發展和演變》(《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3期)、夏玉瑤、楊淑英《西施形象考論》(《大眾文藝》2010年第17期)、曾甘霖《唐前西施形象演變考》(《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5年第4期)等論文,也是側重于西施形象的演變,同樣指出西施在先秦為美女的代稱;東漢時才成為美人計的主角;到了魏晉南北朝時隨著志怪小說的流行而有仙女的形象;唐代詩歌中的西施開始變得多元,文人對西施或贊或彈,褒貶不一。這些論文所據材料相同,得出的結論也相似。
金寧芬《我國古典戲曲中西施形象演變初探》(《文學遺產》2001年第6期)側重于“戲曲”,避開了前述論文重復之處,指出宋元戲曲中的西施大多數為“妖姬”形象。明代梁辰魚《浣紗記》發展了汪道昆《五湖游》中的西施形象,塑造了一個傾城傾國的巾幗英雄,同時指出明代也有復雜的西施形象,無名氏《倒浣紗傳奇》即以覆國罪人視西施。清代徐石麒《浮西施》則承《倒浣紗傳奇》的觀點,視西施為“妖孽”、“禍水”。梁穎珠《試論明代戲曲中的西施形象》(《閱讀與寫作》2007年第8期)、李娜《“紅顏禍水”還是復國英雄——從〈浣紗記〉看西施》(《傳承》2008年第11期)、齊曉靜《論西施形象的美化、妖化和奴化——以明傳奇〈浣紗記〉為坐標》(《蘭州教育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等文,實際上是在金寧芬文章基礎上的微調。
矢嶋美都子《西施のイメージの變遷——美女から隱逸世界の色どりまで》(《お茶の水女子大學中國文學會報》1988年第7期)、徐明安《論歷史語境和文藝話語中的西施及其文化內涵》(《紹興文理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楊杭《“越女”考釋及唐詩中的越女形象分析》(《重慶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等論文,則論述了西施在某一時代的形象。其中,以連怡婷《唐詩中的吳越人物評述》(臺灣淡江大學碩士論文,2010)較有代表性。其研究人物包含句踐、夫差、范蠡、伍子胥及西施,先以人物相關史料為佐分析人物形象的形成,再以全唐詩為主要研究材料,比較人物形象的演變并探究其中的分歧原因,探討唐代文人思想與時代背景下的共同意識。
(二)伍子胥
吳恩培《伍子胥史料新編》(廣陵書社,2007)匯編了史籍、方志等各種文獻中伍子胥的事跡與評論。正如吳恩培《吳、越文化融匯的古代例證──伍子胥文化的層累透視》(《蘇州市職業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指出的那樣,伍子胥是吳越文化交相融匯的例證,它層累地形成了伍子胥文化。因此,伍子胥研究,也是“吳越爭霸”故事人物中的重點。
簡宗梧《左傳伍子胥的形象》(《孔孟學報》1983年第4期)指出,《左傳》最早塑造了伍子胥“仁孝知勇”的形象,《戰國策》中開始凸現伍子胥“忠”的形象。高云萍《伍子胥故事的歷史演變》(《棗莊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04年第1期)認為,伍子胥的故事在《左傳》、《國語》中較為分散,約略是個性格堅韌、謀略過人、忠貞耿直的歷史人物。陳洪、姚瑤《先秦子書與伍子胥故事》(《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認為,《韓非子》、《呂氏春秋》的踵事增華,為伍子胥故事加濃了小說意味;《荀子》、《莊子》等對伍子胥的書寫極為簡短,刻畫了忠賢、強諫的人物形象。陳、姚二文認為,這些為后世伍子胥敘事奠定了基礎。
何亮《〈史記〉對伍子胥形象的塑造》(《書屋》2010年第1期)認為,司馬遷“把自己進步的歷史觀、人生理想以及對自身遭遇的怨恨不平傾注于伍子胥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了”。岳淑珍《〈伍子胥列傳〉的復仇意識及其內涵》(《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6期)則說,司馬遷在此列傳中流露出強烈的復仇意識,借此詮釋了自己的民主思想,批判了漢代的專制制度,寄寓了對個人身世的無限感慨與悲憤。王華《淺論〈史記·伍子胥列傳〉的思想傾向》(《安徽文學》2010年第1期)指出,司馬遷熱烈地宣揚了復仇思想,贊頌了復仇精神。
曹林娣《論〈吳越春秋〉中伍子胥的形象塑造》(《中國文學研究》2003年第3期)認為,《吳越春秋》中的伍子胥形象塑造具有空前性和原創性,它通過對史料的踵事增華和民間傳說的融化,運用旁見側出、對比烘染等多側面的手法,成功書寫了文武雙全、忠孝節烈集于一身的神化英雄,成為后世伍子胥形象的范本。
高云萍《伍子胥故事研究》(山東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4)從魏晉南北朝的文獻中,發掘了伍子胥死后神化色彩加濃的事實,暗示了伍子胥故事俗文學發展的可能。
龔敏《唐代伍子胥忠、孝形象研究》(《東方人文學志》2002年第6期)統計發現,唐詩、文多按照前代書面文獻抒寫伍子胥的忠孝形象。其中,唐詩側重于忠的描寫;小說筆記記錄了伍子胥在唐代民間被稱為“五髭須神”的情況,沒有記錄伍子胥的忠孝形象;《伍子胥變文》同時取材于歷史文獻與民間傳說,描述伍子胥忠孝形象比較詳盡。
童宏民《元明清戲曲小說中之伍子胥》(臺灣政治大學碩士論文,1984;臺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高云萍《伍子胥故事研究》(山東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4)指出,伍子胥到了元明清時期,已經在雜劇、傳奇、皮黃劇本等戲曲資料中都有了新的形象,在《列國志傳》、《新列國志》與《東周列國志》、《十八國臨潼斗寶鼓詞》、《吳越春秋鼓詞》、《禪魚寺大鼓書》等小說記載中也得到了表現。伍子胥故事逐漸從講話文藝到書面文學,從民間藝人的集體創作向作家文人的獨立創作轉變。
在伍子胥的評價問題上,形成了一個小焦點:被后人認為是愛國主義者的屈原,卻高度歌頌了報仇覆楚的伍子胥。針對這一矛盾現象,孫香蘭《從吳越戰爭看春秋時期的血親復仇遺存》(《南開學報》1984年第3期)、戴志鈞《關于屈賦中伍子胥的問題》(《北方論叢》1984年第6期)、王衛平《試論伍子胥與吳國的強盛》(《揚州師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4期)、朱碧蓮《論屈原與伍子胥》(《江淮論壇 》1992年第2期)、陳昭永《伍子胥二題》(《荊州師專學報》1992年第6期)、王立《從忠奸斗爭與復仇意識看屈原對伍子胥的理解和認同》(《廣西社會科學》1994年第5期)等文,深入考察了先秦、秦漢的文獻,發現它們全都贊揚伍子胥的報仇之舉;而后人認為伍子胥引兵滅國屬于叛國行為,實乃因時代觀念變化而不習先秦血親復仇的歷史事實所致。特別是朱碧蓮文,對伍子胥的滅國行為給出了恰如其分的說明。
另有一些文章對伍子胥的其他方面進行了討論。例如,金玉亭的《從伍子胥變文探討悲劇英雄的心理變動過程》(《新潮30》1975年第6期)、張立新的《逃離與眷顧——伍子胥悲劇命運的文化闡釋》(《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討論了伍子胥的悲劇命運;楊范中《從吳楚戰爭看伍員的軍事思想》(《江漢論壇》1984年第7期)、徐勇、黃樸民《關于伍子胥軍事思想的幾個問題》(《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3期)討論了伍子胥的軍事思想;王洪強《伍子胥思想研究》(華中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9)全面論述了伍子胥的政治思想、忠孝觀念及軍事思想,有一定的深度。另外,洪靖婷《〈伍子胥奔吳覆楚〉文學記述研究》(《人文與社會學報》2008年第3期)、蔣康《試論伍子胥的崇祀習俗》(《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4期)、張君《伍子胥何曾掘墓鞭尸》(《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3期)、根本誠《中國文の一特征(上)——伍子胥變文の人物描寫の限界性——》(《東洋文學研究》1966年第3期)、安本博《伍子胥傳について》(《中國哲學史の展望と模索》1976年第11期)等文也專門討論了伍子胥。總之,伍子胥的方方面面都已經得到了研究。
(三)范蠡
饒恒久《范蠡事跡與思想考論》(《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3期)、《范蠡生平考論》(《社會科學戰線》2000年第6期)據《吳氏春秋·當染》高誘注、《史記正義》引《會稽典錄》、《史記集解》引《太史公素王妙論》等文獻,考范蠡字少伯,籍貫為三戶邑,即古之丹陽,今之湖北省南漳縣西北;并將范蠡一生的行跡,劃分為三個階段:1.入越前的佯狂負俗;2.深謀滅吳的偉烈;3.功成身退、泛舟江湖的飄逸。后文還列出了范蠡的大事年表。馬懷云《論范蠡的商業經營之道》(《安陽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則從商業鼻祖的角度論述了范蠡的經營策略。
對于范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范蠡的思想上。上世紀60年代,關鋒、林聿時《范蠡的哲學思想 》(載《春秋哲學史論集》,人民出版社,1963)依當時的學術語境,認為“范蠡是春秋后期的一位重要的唯物主義思想家”,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和積極的樸素辯證法思想,把范蠡作為思想史的人物來看待,開啟了范蠡思想研究之門。另如方克《范蠡的哲學思想》(《浙江學刊》1982年第3期)、耿良佐《范蠡的“農末俱利”思想》(《寧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3期)、胡軍哲《范蠡的哲學思想及其實踐》(《益陽師專學報》1995年第3期)、商聚德《范蠡的品格及思想試論》(《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3期)、饒恒久《試論鬻熊、呂尚對范蠡思想的影響》(《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范蠡與文子之師承關系考論》(《寧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等等,都是如此。
思想史角度的研究聲勢掩蓋了相比之下顯得冷清的文學史角度的研究。《史記》特別敘述了范蠡滅吳霸越的事功。韓兆琦、陳曦《談〈史記〉中的范蠡形象》(《周口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第3期)一文,卻讀出了范蠡的“信仰”與實踐脫節和他荒誕不近人情的一面,并認為在這一點上,《史記》與《越語下》表現得頗異其趣。孫曉宏《范蠡——理性精神燭照下的人格范式》(《萍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8年 第1期)則從《浣紗記》中讀出了范蠡的“進退有據的自由意志的踐行者”以及“健康崇高的理想愛情的自我主宰者”形象。
三、“吳越爭霸”故事研究展望
盡管已經有較多的成果,但吳越爭霸故事還有待深入研究。若能運用新理論、新方法,“吳越爭霸”應能得到更深入的闡釋。黃敏《性別視角下的西施式敘事研究》(陜西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8)一文,梳理了歷代的西施故事,以病美人與美人計的實施者為內涵,總結出“西施式敘事”,并以此來觀照現當代“西施式敘事”中的女性,指出:“西施形象濃縮了其故事產生時代的社會一般觀念,隱含著中國傳統文化對美人形象塑造的傾向。西施式敘事在古典文學和現當代文學的不同際遇,說明了女性在文化意識中的邊緣化現象。”我們認為,應該還可以挖掘更多的敘事原則,作一番深入的考察。另外,前文所述研究也多集中于《吳越春秋》,幾乎沒有涉及后世的戲曲乃至詩歌,鮮少有打通古今之作;而黃敏此文又不止于“吳越爭霸”,甚至涉及到了女間諜故事,可見這一方法是有很大空間的。同時,從敘事學理論角度看,多數研究仍停留在對經典敘事學的運用上,并沒有展開敘事倫理、敘事動力、空間敘事等后經典敘事學的對話。
“爭霸”故事源遠流長,夾雜著雅、俗兩方面的文化氣息。客觀來說,這方面已經引起了一定的注意。例如,David Johnson《伍子胥變文及其來源》(《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984年第3-4期)推論《伍子胥變文》深受有關江水與祭祀傳說的影響;龔敏《唐詩中的伍子胥信仰與傳說》(《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統計、整理了唐詩中以伍子胥為題材的詩歌,認為“吳越爭霸”故事傳播中雅俗分明的現象,一直維持到了唐代,經由詩人的歌詠,才將兩者融合在一起;林思綺《從伍子胥故事的演變論歷史知識的通俗化》(《人文社會科學通迅》1995年第2期)、劉樹勝《正史·傳說·講唱文學——〈由伍子胥變文〉看伍子胥故事的嬗變》(《滄州師范專科學校學報》1999年第12期)、黃亞平《伍子胥故事的演變:史傳系統與敦煌變文為代表的民間系統的對比》(《敦煌研究》2003年第2期)等文,則側重故事的演變中的雅俗關系,黃文還從史傳系統與民間系統來說明演變的軌跡,并列“吳越爭霸故事演變軌跡”圖說明了這個發展過程。
這些論文似乎已經解決了雅俗問題,但仍只是僅僅側重于伍子胥故事,缺少對“吳越爭霸”故事的整體雅俗轉變的研究,更缺少對雅俗文化的文化土壤的論述,從而,這種“吳越爭霸”故事對地域文化的影響研究也付之缺如。
故事中極不重要的干將、莫邪,絕非爭霸故事的重心,卻在“神話—原型”批評興起后,成為重要的研究對象。這些研究發軔于海外,例如日本細谷草子《干將莫邪說話の展開》(《文化(東北大學)》1970年第2期)、高橋稔《眉間尺研究序說》(《東京學藝大學紀要》1976年第2期)、松崎治之《干將莫邪的研究——關于該故事的流傳》、《搜神記“干將莫邪”私考——傳承說話をめぐて》(《口迸先生古稀記念中國現代文學論集》,福岡:中國書店,1990)等。另有香港黎活仁的《干將莫邪故事與魯迅〈鑄劍〉——煉金術的精神學分析》(《魯迅研究年刊》,1992),臺灣張得歆的《干將莫邪故事研究》(臺灣中央大學碩士論文,2006);大陸則有金永平《干將、莫邪的傳說及演化》(《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3期)、周楠本《關于眉間尺故事的出典及文本》(《魯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5期)、李道和《干將莫邪傳說的演變》(《民族藝術研究》2006年第2期)、王璞《干將、莫邪鑄劍神話之結構分析》(《民族藝術》2003年第3期)、戴月舟《干將莫邪研究——歷史·傳說·典故》(南京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8)等。
其中,以李道和《干將莫邪傳說研究》(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2009)最為全面。書中運用“神話—原型”批評原理,認為從傳說的象征敘事和主題隱喻上看,干將莫邪鑄劍特別是眉間尺為父報仇的傳說,也可能是伍子胥故事的暗喻或象征性表達:眉間尺與伍子胥眉間闊大的狀貌特征相同;都對父親的遺言作了準確釋讀,殺父之仇刻骨銘心;其仇敵都對他們懸賞捉拿;他們都得到了各種形式的幫助,最終也報仇雪恨;而他們自己也都被鼎烹鑊煮。干將鑄劍跟伍子胥父親伍奢做楚平王太子太傅,在敘事上也有功能上的近似:他們都在任職三年之后被殺。從伍子胥角度看眉間尺傳說,不僅能抉發后者的暗喻意義、產生背景,還能順暢解釋其中君王的歧異及歷史、地理方面的矛盾。
這的確講出了新意,也對“吳越爭霸”故事有了新的理解。那么,這一研究思路是否可以用到故事的其他部分呢?我們認為,可以結合復仇母題,對“吳越爭霸”故事的文學魅力作更深入的討論,甚至還應該闡釋故事的主題演變等問題。
如果說故事演變的考察著重的是文學作品本身,那么,接受美學則會更多地關注讀者。關注對象的不同,研究的視野也就相異,只有通過多元的考察,才能真正深入理解故事的文化意蘊。但目前只有極少數文章具有方法論的自覺,能夠做到從接受美學的角度討論明清戲曲如《浣紗記》、《五湖游》、《浮西施》等;但是,這些研究幾乎沒有涉及現當代的戲劇、小說作品,這實在令人遺憾。
通過研究“吳越爭霸”故事的演變,還可以更進一步深化文學史的觀念。根據布拉格學派的文學史觀,文學作品的演變,正是“文學結構”的變化。所謂“文學結構”,即是整個時代對當時文學現象的觀感,以及具有歷史的普遍性意義的意見。而文學史就是要考察這個無形的客體“文學結構”的運動“演變”情況。[3]如果能結合歷代對“吳越爭霸”故事的接受情況,進而考察歷代的“文學結構”,而不僅止于社會思潮、社會權力分布等社會學層面的考察,那么,對該故事的研究,就具有了文學史考察的意義。
注釋:
①參見梁琦《瑰奇與伉俠:〈吳越春秋〉傳奇性淺論》(《西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和《伉俠與風注:論〈吳越春秋〉的文化張力》(《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07)。
②趙雅麗《〈越絕書〉研究》(福建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7)、韓秀麗《〈越絕書〉內外篇新探》(華東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8)、錢茂偉《〈越絕書〉研究述評》(載《浙東史學研究述評》,海洋大學出版社,2009)、張仲清《說說〈越絕書〉的作者》(載《中國越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劉暢《〈越絕書〉書名與著者問題研究綜述》(《安徽文學(下半月)》2010年第7期)諸文都帶有綜述的性質,對李步嘉的研究有一定的補充。
③王鵬《當代〈吳越春秋〉研究簡述》(《黃山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錢茂偉《浙東史學研究述評》(海洋大學出版社,2009)都對這一問題有一定的介紹。
[1]黃仁生.《吳越春秋》作為首部長篇歷史小說的思想成就[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5,24(1):93-98.
[2]林小云.原始的生命本性和浪漫激情——析《吳越春秋》的悲劇色彩[J].洛陽師范學院學報,2009,28(4):58-61.
[3]陳國球.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326-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