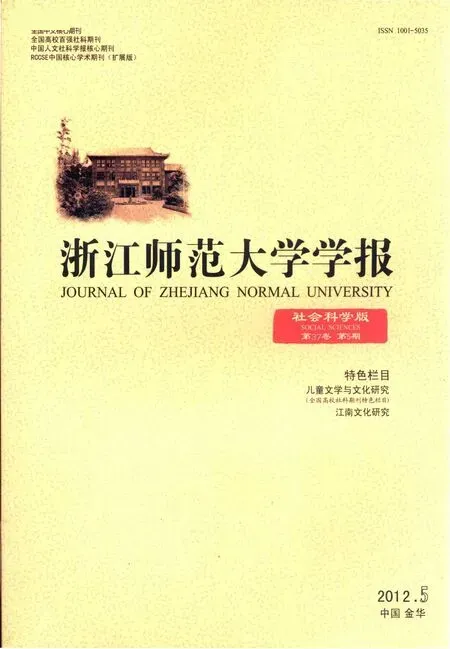社會轉型中的人民政協功能開發
馬 利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 圖書館,北京 100081)*
“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在促成經濟制度變遷的同時,也帶來了利益結構的深刻變化”,[1]傳統的社會體系和社會組織關系構成也發生了很大改變。在社會被注入新的生機和活力的同時,社會分化也不斷加速,新生的社會力量不斷涌現,社會利益群體和其各自間的利益關系也更加豐富和多元。與此同時,國家、社會、個人之間的關系和黨的執政方式、國家的施政格局,也經歷著重大調整和改變。
一、社會結構變化和社會利益關系重構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執政黨對國家、社會和個人的領導和施治是全方位的,黨、國家、社會三位一體,全面覆蓋了整體社會和全體成員,社會和個人都被歸屬于國家權力系統所統轄的體制范圍之內,其呈現的特征為:國家管理格局單一,權力系統全能而封閉,國家、社會和個人的利益關系單純而一致。這種一元化的治理體系,使得執政黨和國家的治理方式也趨于單一、直接和剛性,社會生產力和民間活力的進一步解放與煥發受到制約。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引入市場經濟后,給社會帶來的重大變化之一,就是社會和個人的自主空間不斷擴大。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下,社會資源被重新分配,原有的社會階層產生分化,在國家體制之外的多種新生社會力量迅速崛起,并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占有越來越顯著的位置。根據有關學者的研究,中國現已分化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辦事人員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商業服務業員工階層,產業工人階層,農業勞動者階層和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這十大階層,[2]社會結構由原先的相對簡單、明晰而變得復雜和多元。同時,大量民間非政府組織不斷涌現。據民政部《2010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數據統計,截至2010年底,全國各類民間組織達43.9萬個,其中民間社團達24.3萬個。[3]諸多的社會力量在國家權力體系之外的社會空間自主地從事相關活動,自我運轉和自我管理,體制力量和國家權力轄制的范圍有所收縮,國家權力的行使者——政府,也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
社會空間的擴大,社會階層的分化,帶來了社會利益的多元。新生的社會力量和不同的社會階層,形成各自的利益關系,在自身生長與發展的同時,也要求自身利益的實現。如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民營經濟迅猛發展,經濟實力不斷擴大,成為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在社會經濟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愈益顯著。在民營經濟與國家和社會的關系愈益深化的同時,民營企業主希望表達其利益訴求和進行政治參與的愿望也隨之增強了。另外,社會的轉型使社會的個體成員擁有了越來越多的個人空間,個人自由度和自主性大大增強,我國公民的公民意識、權利義務意識、利益表達意識和政治參與意識也不斷增強。新出現的社會力量組織,高度分化和多重交織的社會利益關系,使得我國社會構成經歷著重大變化,社會利益關系也經歷著變革和重組。
二、社會轉型中人民政協的作用優勢
在社會轉型和全面深刻的政治經濟等變革中,社會多元化、政治民主化是未來的主要發展趨勢。在高度分化的社會環境中,一些新涌現的社會組織和群體屬于國家政治權力體系之外的社會力量,這些社會組織和群體,帶著非政府的民間屬性,國家權力體系無法直接對其主導,因而,其既表現為與國家權力體系的分離,也形成對國家權力體系的壓力。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大量體制外社會力量的涌現和崛起,是執政黨和政府面臨的最主要的社會新格局,這些社會力量與其所代表和聯系的廣大社會公民,如果不能與政府、國家制度和權力體系形成有機的聯系,如果其利益表達和政治參與訴求不能被國家權力體系有效接納,就會影響社會和諧與政治穩定。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治民主化進程也在加速,但在中國特定國情下,現階段的政治權力體系尚無法搭建一個相對完善、成熟的制度化平臺,將各種新生的體制外社會力量納入國家整體制度化、法治化的框架之中。在現有的民主制度中,我國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民主選舉的方式,表達人民的意愿,行使人民的權力。但緣于我們的體制傳統,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所整合的主要是國家體制內的社會力量,對于體制外的社會力量,尚不能完全充分吸納。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政協制度就成為團結吸納體制外社會力量的重要平臺。人民政協是體現我國協商式民主的主體機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統一戰線組織,在幾十年的發展中,蘊含著優良的民主傳統并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人民政協的制度設計和功能屬性使其可以廣泛吸納和凝聚各種社會力量,其機構特點是一個介乎于體制內和體制外的中間組織,在機構設置和管理上,其屬于體制內,但卻又不是權力機構;在工作對象和作用發揮上,則主要在體制之外。在中國社會轉型的新時期,面對新的社會環境,人民政協的功能和作用不斷擴大,成為執政黨和政府聯系各種社會力量的重要紐帶和橋梁。
在中國政體框架中,人民代表大會作為權力機構,在國家民主政治運行中發揮中堅的作用,而人民政協作為非權力機構,也在國家民主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大而不可缺失的作用,因而成為國家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國家的政治決策,需要獲得社會大眾的普遍支持,從而使其建立在最廣泛的合法性基礎之上,而其實現的途徑,是社會公民的廣泛政治參與。由于人民代表大會主要代表和聯系的是體制內的社會力量,在多元分化的社會中,只有體制內而沒有體制外社會力量的參與和支持,將會導致國家政治決策的合法性來源不足,從而使得政治決策實施不暢或部分失效,因而,人民政協所體現的協商式民主,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重要補充,其既是中國共產黨實現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的重要組織形式,也是共產黨團結廣泛的社會力量、吸納社會各界公民代表進行政治參與的重要制度化平臺。中國有著自己的國情和政治發展環境,不適宜西方的多黨制。我國的人民政協制度為社會多種利益群體的利益表達和政治參與提供了制度化的途徑,使得國家政治決策體系能夠聽到社會各界的聲音,從而實現利益的協調和決策的調整。
人民政協的制度設計,使其具有極大的包容性、靈活性和彈性,可以根據社會力量的變化,適時地作出反應,將其吸納并對其外部關系進行協調和整合,既能協調這些社會力量與執政黨之間的政治關系,也能協調其與國家和其他社會力量之間的利益關系。人民政協所體現的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各種社會意愿、利益訴求可以在其中平等表達、充分商討,與表決民主相比較,通過協商而形成的決策能夠獲得更廣泛的公共支持,“也為行政人員的決策提供了更準確的信息基礎”。[4]因而,在中國民主政治實踐中,人民政協制度具有制度潛力和顯著的優越性。
三、社會轉型對人民政協功能開發的要求
在社會多元分化和公民社會的成長過程中,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關系紛然交織,國家政治權力體系也承受著多種利益訴求和公民社會政治參與的巨大壓力。[5]如何疏解這些壓力,則對民主政治的發展和人民政協的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社會轉型和時代潮流的推動下,人民政協在發揚統一戰線的優秀傳統,廣泛團結各種社會力量的基礎上,運用制度優勢亦可以凸顯出其民意匯集、制度表達和利益協調方面的時代主題,人民政協的功能也隨之大幅拓展,其“團結”和“民主”的制度內涵更為彰顯。同時也要看到,人民政協功能的拓展和優勢的發揮,更多地是在時代和社會要求的推動下,以探索的方式實現的。在新的社會環境下,運用好人民政協的制度資源,拓展和開發這一制度所能提供的多種復合功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民政協在民主政治建設中的獨特作用,會極大節省我國政體運行中的制度成本,能將各種社會力量和利益關系納入到國家體制的框架之中,從而促進現代國家的穩步建設和公民社會的健康發展。
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是人民政協的三大職能,由這三大職能所產生的功能主要有政治參與、利益表達、決策咨詢、民主監督、溝通協調、社會疏導等,但新的社會形勢和人民政協的工作實踐,則要求這些功能效應的突出呈現以及運行路徑和操作平臺的進一步完善,因而,對人民政協功能的深層開發并建構相應機制,是其功能實現的重要保障。
1.吸納傳導機制。團結最廣泛的社會力量,是統一戰線的法寶,是人民政協的光榮傳統和優勢。在社會高度分化和多種利益群體涌現的社會環境下,人民政協要緊密關注社會群體的變化,及時吸納一切國家體制外的社會力量,尤其是在社會領域中力量增長迅速的群體以及邊緣、弱勢群體,以使國家政治權力體系獲得最廣泛人民性。同時,雙向傳導國家政治權力體系與這些社會力量之間的信息,強化執政黨、國家與社會和公民之間的有機聯系。
2.咨詢問政機制。人民政協所匯集的是各種界別和社會力量的代表人物,他們也大都是不同專業領域中的精英人物、高端人才,代表不同社會群體相關利益的同時,也承載著各類專業知識。因而,建立國家重大決策出臺前向人民政協的咨詢制度,建立人民政協對于決策實施的方式、過程以及對社會不了解、不理解的政府舉措向政府相關部門的問政制度,是人民政協實現參政議政功能的重要機制。其將增強國家決策的科學性、民主性,政府舉措的透明性,從而獲得更多的社會共識,同時也保障政府決策的及時調整、順利實施。
3.利益表達機制。在多元社會的新環境中,人民政協應該是各種社會力量進行利益表達的重要平臺,使各種社會意愿和利益訴求通過制度性的民主渠道得以匯集并上達,避免因渠道不暢而產生社會力量的非制度表達和參與。人民政協應針對不同的利益群體和重要的界別組建專門的委員會機構,以專向聯系的方式,建立固定的民意匯集和利益表達制度,定期以多種方式匯集和傾聽不同社會群體代表的聲音,并及時向國家權力體系輸送相關信息,促進公民社會正當利益訴求向決策層的制度化表達和社會成員對這些利益的最終享有。
4.監督質詢機制。民主監督是人民政協的三大職能之一,但其相應功能的發揮,亦需落實在制度層面的安排上。對公共權力的監督和約束,防止公權的濫用和對民權的侵害,是現代政治文明的主要成果。在中國社會轉型時的民主監督中,人民政協應該發揮主體作用,其對執政黨和國家權力體系進行的黨外監督和體系外監督,具有與執政黨內部監督不同的重大意義和作用。人民政協不僅是民主黨派實施對執政黨監督的組織機構,更是廣大的體制外社會力量對執政黨和國家政治權力體系實施監督的組織機構。落實人民政協的監督權,建立行之有效的人民政協對執政體系和國家事務的定期和不定期的監督和質詢制度及其實施程序,是人民政協民主監督功能發揮的重要保證。
5.協調平衡機制。民主協商是人民政協制度的核心內涵,在中國社會轉型后,這種民主協商不僅包括政治協商,也包括利益協商。人民政協作為中國特色民主形式的主體機構,在民主協商中起著主導作用。人民政協既協調體制外社會力量與國家政治權力層面之間的政治關系,也協調體制內外及各種社會力量之間的利益關系,尤其當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利益沖突增大,社會利益關系明顯失衡的時候,人民政協更要發揮重要作用。人民政協需要建立正式的社會協商協調制度,以緩解多種利益訴求對國家權力體系施予的壓力,避免利益群體與國家權力體系的直接對峙,通過人民政協所建立的協商協調平臺,促使沖突的各方充分溝通、協商,取得互信和共識,并共同探討解決的途徑,以促進社會的穩定、和諧。
總之,隨著中國社會向現代化轉型,對人民政協功能所提出的要求也愈來愈高,人民政協需要大力加強自身建設,促進人民政協功能實現路徑的制度化、程序化、科學化,并逐步將人民政協工作納入法制化軌道,積極推進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健康發展和社會主義民主事業的進步。
[1]吳健,楊國順.構建網狀式的利益表達渠道[J].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36(1):89-93.
[2]數十位社會學學者歷時三年調查研究得出結論——中國人現分為十大階層[N].環球時報,2002-01-07(13).
[3]國家民政部.2010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EB/OL].[2011-02-09].http://cws.mca.gov.cn/article/tjkb/201102/20110200133593.shtml.
[4]克里斯蒂安·亨諾德.法團主義、多元主義與民主:走向協商的官僚責任理論[M]//陳家剛.協商民主.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2004:300-301.
[5]虞崇勝,葉長茂.人民政協:公民社會與政治國家和諧發展的重要途徑[J].中共天津市委黨校學報,2005(2):3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