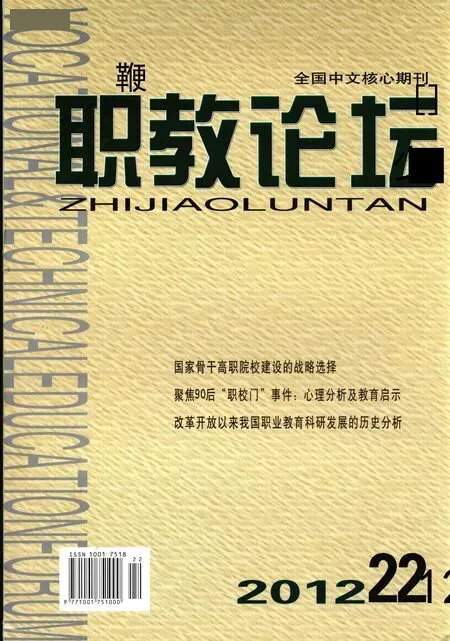沃爾夫報(bào)告與英國職業(yè)教育改革
□李建忠
一、沃爾夫報(bào)告出臺(tái)背景與教育外部環(huán)境
職業(yè)教育改革成為英國新政府上臺(tái)后優(yōu)先考量的問題。2010年5月英國聯(lián)合政府成立后,兒童、學(xué)校和家庭部隨即更名為教育部。9月9日,教育大臣邁克爾·戈夫向倫敦國王學(xué)院艾莉森·沃爾夫?qū)懶牛兴透倪M(jìn)初中和高中階段(14-19歲)職業(yè)教育進(jìn)行調(diào)研,期待到2010年底提交中期報(bào)告,到2011年春提交最終報(bào)告。2011年3月沃爾夫教授提交了英國職業(yè)教育評(píng)估報(bào)告,簡稱《沃爾夫報(bào)告》。在3月3日評(píng)估報(bào)告公布之日,教育大臣戈夫稱報(bào)告“非常出色和具有獨(dú)創(chuàng)性”,當(dāng)即接受了其中四條建議。他指出:“我們繼承的制度損害作用很大,它對(duì)兒童是不公正的,正在損害經(jīng)濟(jì),成千上萬的兒童被誤導(dǎo)學(xué)習(xí)沒有什么前途的課程;我們將改革績效排行榜、經(jīng)費(fèi)分配制度和監(jiān)管制度,給兒童誠實(shí)的信息和學(xué)習(xí)合適課程的機(jī)會(huì)。實(shí)施這些改革會(huì)很艱難,需要花幾年時(shí)間,但我們負(fù)擔(dān)不起另一個(gè)10年教育失敗的代價(jià)”[1]。
報(bào)告分析了職業(yè)教育發(fā)展的外部環(huán)境,認(rèn)為近30年來,同其他發(fā)達(dá)國家一樣,英國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和勞動(dòng)力市場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具有以下特點(diǎn):19-24歲青年人失業(yè)率高,出現(xiàn)“一個(gè)正消失著的青年勞動(dòng)力市場”。教育水平普遍提高,接受普通教育直到16歲已成為發(fā)達(dá)國家的一個(gè)規(guī)范,專門化已經(jīng)逐步向后推遲;人們普遍抱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期盼,有98%的母親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能夠上大學(xué);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水平就越高。就業(yè)經(jīng)歷和學(xué)徒培訓(xùn)有著高回報(bào);青年人在教育與就業(yè)市場之間進(jìn)進(jìn)出出,職業(yè)變換頻繁,11年間平均每人變換工作3.5次,變換職業(yè)2.5次,變換行業(yè)1.8次;18歲青年人教育生存狀態(tài)發(fā)生重大變化,接受教育或培訓(xùn)的比例從1976年的17%上升到2009年的45%;職業(yè)結(jié)構(gòu)發(fā)生根本性變化,高技能和服務(wù)行業(yè)崗位需求上升,傳統(tǒng)的低技能就業(yè)市場迅速萎縮;經(jīng)濟(jì)迅速變革給勞動(dòng)力市場帶來重要影響,政府需要積極回應(yīng)今天勞動(dòng)力市場的現(xiàn)實(shí)。
30年來英國政府一直高度重視發(fā)展職業(yè)教育。自上個(gè)世紀(jì)80年代中期建立“國家職業(yè)資格”(NVQ)以來,英國已經(jīng)完成了三代國家資格框架的開發(fā)和建設(shè),對(duì)歐洲以及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世界許多國家的職業(yè)資格框架(制度)的建立產(chǎn)生了世界性重大影響。英國許多職業(yè)學(xué)校突出產(chǎn)學(xué)結(jié)合特色,例如,在馬格斯菲特學(xué)院,歐洲航空航天培訓(xùn)中心按照產(chǎn)業(yè)國際標(biāo)準(zhǔn)利用全功能的英國航空航天公司飛機(jī)提供培訓(xùn),培養(yǎng)了大批高素質(zhì)機(jī)場地勤人員;英國鐵路網(wǎng)公司90%的學(xué)徒畢業(yè)后留在公司就業(yè);英國知名企業(yè)的學(xué)徒培訓(xùn)供不應(yīng)求,空中客車公司的學(xué)徒畢業(yè)后既有出色的生涯前景,又有繼續(xù)在大學(xué)學(xué)習(xí)的機(jī)會(huì);英國電信公司和勞斯萊斯汽車公司的學(xué)徒培訓(xùn)名額競爭比英國牛津和劍橋大學(xué)的入學(xué)競爭還要激烈。
但是英國職業(yè)教育也存在著許多問題,根本性的問題是英國有許多好的實(shí)踐案例,但沒有一個(gè)好的制度,尚未建立起一套適應(yīng)社會(huì)需要和學(xué)習(xí)者需求的、完善的職業(yè)教育制度,160年來制度建設(shè)的根本問題一直沒有解決。正如教育大臣戈夫指出的那樣:自1851年艾伯特王子建立皇家委員會(huì)以來,決策者一直在努力解決向青年人提供一種適當(dāng)?shù)募夹g(shù)和實(shí)踐教育的問題,160年后同樣的問題仍然存在[2]。
二、英國職業(yè)教育問題與審計(jì)
沃爾夫報(bào)告認(rèn)為,英國(主要指英格蘭)的職業(yè)教育主要存在著勞動(dòng)力市場要求與職業(yè)教育提供的不匹配、繼續(xù)學(xué)習(xí)要求與職業(yè)教育提供的不匹配等方面的問題。
(一)勞動(dòng)力市場要求與職業(yè)教育提供的不匹配
1.職業(yè)教育的內(nèi)容不被勞動(dòng)力市場看重。英國許多一級(jí)和二級(jí)資格證書,包括被認(rèn)為是反映了工作場所要求的國家職業(yè)資格,不管是在收入方面還是生涯進(jìn)步方面,似乎都沒有任何積極的結(jié)果。職業(yè)資格證書學(xué)習(xí)的內(nèi)容實(shí)際上并沒有被雇主和勞動(dòng)力市場所看重,可是,這些資格證書成為了高中階段(16-18歲)學(xué)生學(xué)習(xí)的主體部分。近年來引入的“基礎(chǔ)學(xué)習(xí)證書”是“個(gè)性化”的、面向大部分14-19歲低成就學(xué)生學(xué)習(xí)的課程,內(nèi)容包含職業(yè)性或?qū)W科學(xué)習(xí)。在“基礎(chǔ)學(xué)習(xí)證書目錄”上目前約有1300種這種證書,許多證書規(guī)格都非常小。其中有400種證書學(xué)分值只有5個(gè)或不到5個(gè)學(xué)分,這就是說學(xué)生可以用不到50個(gè)教學(xué)小時(shí)就可完成一個(gè)證書的學(xué)習(xí)。從勞動(dòng)力市場的觀點(diǎn)看,基礎(chǔ)學(xué)習(xí)證書不可能取得成功,因?yàn)楣椭髦豢粗貛追N熟悉的資格證書或是“真正”的工作經(jīng)歷。用拉思伯恩志愿組織首席執(zhí)行官的話說,就是“這些資格證書讓你什么都干不了,除非你再拿一個(gè)證書”。
2.資格證書不斷變化,缺乏穩(wěn)定性。勞動(dòng)力市場認(rèn)可穩(wěn)定的和熟悉的資格證書,但英國的職業(yè)資格證書一直并且仍在處于不斷變化之中。世界各國的資格證書都保持相對(duì)穩(wěn)定,而英國政府幾十年來一直都在引入新的類型的職業(yè)資格證書,學(xué)術(shù)資格至少從其名稱看一直保持相對(duì)穩(wěn)定。資格證書的品牌效應(yīng)極為重要,像倫敦城市行業(yè)協(xié)會(huì)頒發(fā)職業(yè)資格證書的歷史可追溯到19世紀(jì),現(xiàn)在仍然受到人們的看重和認(rèn)可。
3.資格證書口徑窄化,提供的特定職業(yè)崗位資格證書越來越多。青年人的就業(yè)模式意味著他們需要相對(duì)普通的而不是非常特定的職業(yè)資格證書。然而,越來越多的職業(yè)教育學(xué)生取得的是非常特定的職業(yè)資格證書。青年人在其頭10年的就業(yè)中變換行業(yè)、職業(yè)以及特定崗位非常頻繁。取得特定職業(yè)資格證書人的比例很高,但并不意味著他們一定能留在原來職業(yè)里就業(yè),并且職業(yè)資格證書等級(jí)越低,證書持有者變換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大。幾乎所有的發(fā)達(dá)國家都向14-19歲學(xué)生提供相當(dāng)普通的職業(yè)教育課程,即使是在實(shí)施學(xué)徒培訓(xùn)的歐洲其他國家,也都有大量的離崗普通教育。英國目前對(duì)16-19歲學(xué)生的教育試圖采取絕對(duì)的二分法:或者向?qū)W生提供狹窄的、特定的職業(yè)資格;或者是提供傳統(tǒng)的學(xué)術(shù)資格。目前約有1/4至1/3(30萬-40萬)的高中階段學(xué)生(16-19歲)學(xué)習(xí)的課程既不能使他們具有資格上大學(xué)或繼續(xù)升學(xué),也不能使他們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許多初中生(14-16歲)學(xué)的是學(xué)校績效排行榜鼓勵(lì)的職業(yè)課程,這導(dǎo)致他們進(jìn)入了死胡同。但是許多年輕人并沒有被告知他們選擇學(xué)習(xí)這些資格證書后果的真實(shí)情況[3]。
4.缺乏真正的工作經(jīng)歷和以就業(yè)為基礎(chǔ)的技能。雇主重視“工作歷史”和經(jīng)歷,即在一個(gè)真實(shí)的工作場所有一個(gè)合適的、帶薪工作,這完全不同于在學(xué)校教育環(huán)境里獲得的經(jīng)歷或通過政府培訓(xùn)計(jì)劃獲得的“與工作相關(guān)”經(jīng)歷。英國許多16歲和17歲青年人在教育與就業(yè)之間進(jìn)進(jìn)出出,尋求著能有助于提升他們就業(yè)能力的教育或培訓(xùn)。然而面向他們的學(xué)徒名額則很少,2009年僅有6%的雇主招收16歲學(xué)徒,11%的雇主招收17或18歲學(xué)徒。相反,在上個(gè)世紀(jì)70年代有1/4的1958年出生的青年人參加傳統(tǒng)學(xué)徒培訓(xùn),男性一般在15歲開始學(xué)徒。實(shí)際上,現(xiàn)在16-18歲青年人在全部學(xué)徒名額中所占比例從2004年的60%下降到2009年的41%。16歲和17歲青年人對(duì)高質(zhì)量學(xué)徒培訓(xùn)有著巨大需求,特別是三級(jí)資格證書層次的學(xué)徒。
5.低層次職業(yè)資格證書負(fù)回報(bào)。英國大量的實(shí)證研究表明,低層次職業(yè)資格證書,特別是國家職業(yè)資格(NVQ)對(duì)證書持有者沒有重要的勞動(dòng)力市場價(jià)值。國家兒童發(fā)展研究(NCDS)的分析發(fā)現(xiàn),低層次資格(國家資格框架中的一級(jí)和二級(jí)資格證書)對(duì)工資沒有顯著效應(yīng)。大規(guī)模的勞動(dòng)力調(diào)查數(shù)據(jù)研究也發(fā)現(xiàn),低層次國家職業(yè)資格證書和倫敦城市行業(yè)協(xié)會(huì)低層次職業(yè)資格證書的工資回報(bào)在統(tǒng)計(jì)上有著顯著負(fù)回報(bào),持有這些資格似乎就是低薪就業(yè)的代名詞。2004年迪爾登(Dearden)等人在英國年齡組研究(BCS70)中,對(duì)1970年出生的人持有的國家職業(yè)資格二級(jí)資格證書的回報(bào)進(jìn)行了深度分析,再次發(fā)現(xiàn)取得二級(jí)資格證書是同低收入有著顯著相關(guān)。國家職業(yè)資格一級(jí)和二級(jí)資格證書已經(jīng)失去了勞動(dòng)力市場價(jià)值。通過政府培訓(xùn)計(jì)劃取得的國家職業(yè)資格二級(jí)資格證書的工資回報(bào)是-22.5%,通過學(xué)校職業(yè)教育環(huán)境取得的二級(jí)資格證書為-11.6%。研究也表明,三級(jí)職業(yè)資格證書和學(xué)徒制培訓(xùn)有著強(qiáng)勢正面回報(bào)。
(二)繼續(xù)學(xué)習(xí)要求與職業(yè)教育提供的不匹配
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績效指標(biāo)的負(fù)向?qū)蜃饔茫鲆晹?shù)學(xué)和語文(英語)教育,“資格和學(xué)分框架”(QCF)導(dǎo)致職業(yè)資格重新貼標(biāo),學(xué)徒培訓(xùn)框架缺乏彈性,經(jīng)費(fèi)分配機(jī)制導(dǎo)致證書數(shù)量膨脹,職業(yè)教育教學(xué)質(zhì)量高度不均衡等,這些問題都相互關(guān)聯(lián)。
1.學(xué)校績效排行榜導(dǎo)致資格證書泡沫化。目前在關(guān)鍵階段4(初中階段)結(jié)束時(shí)用于測量學(xué)校表現(xiàn)的績效指標(biāo)體系導(dǎo)致學(xué)生獲得的“職業(yè)”資格證書數(shù)量大幅增長,16歲學(xué)生取得的所謂同等的資格證書的數(shù)量從2004年的1.5萬個(gè)激增至2010年的57.5萬個(gè),旨在提高學(xué)校在績效排行榜上的名次,但這與學(xué)生在教育系統(tǒng)或勞動(dòng)力市場里的長期利益沒有關(guān)系。從2001年起,政府所屬的課程開發(fā)機(jī)構(gòu),先是資格和課程署(QCA),隨后是資格和課程開發(fā)署(QCDA)密集開發(fā)大量課程,以保證所有資格證書都能用以提高問責(zé)測量表現(xiàn)。由于放松了國家課程管理,加強(qiáng)了問責(zé)制,結(jié)果學(xué)校課程以空前的規(guī)模和速度從學(xué)術(shù)科目轉(zhuǎn)到“職業(yè)”科目。
2.撥款導(dǎo)向機(jī)制和績效目標(biāo)妨礙學(xué)生提高數(shù)學(xué)和英語技能。數(shù)學(xué)和英語成績水平在保證學(xué)生繼續(xù)學(xué)習(xí)和融入勞動(dòng)力市場方面具有決定性意義。但是經(jīng)費(fèi)分配刺激機(jī)制和學(xué)校績效目標(biāo)則不利于學(xué)生提高數(shù)學(xué)和英語成績水平。學(xué)校對(duì)學(xué)生進(jìn)行分流,要求被分流的學(xué)生學(xué)習(xí)“關(guān)鍵技能”或“功能性技能”證書,以代替數(shù)學(xué)和英語科目學(xué)習(xí)。總體上看,取得普通中等教育證書(GCSE)數(shù)學(xué)和英語科目A*-C級(jí)成績的15歲學(xué)生比例僅為44.8%,18歲學(xué)生為49%,或者說有一半的學(xué)生沒有數(shù)學(xué)和英語科目A*-C級(jí)成績。從絕對(duì)數(shù)量上看,15歲學(xué)生中沒有取得數(shù)學(xué)和英語A*-C級(jí)成績的人數(shù)達(dá)到32.9萬人,18歲學(xué)生的人數(shù)達(dá)到30.4萬人。中央政府的撥款公式強(qiáng)力刺激學(xué)校讓學(xué)生學(xué)習(xí)一些被認(rèn)為是相當(dāng)于主流數(shù)學(xué)和英語科目的特定資格證書課程,以實(shí)現(xiàn)高位目標(biāo)。
3.“資格和學(xué)分框架”(QCF)中職業(yè)資格不完全適合14-19歲學(xué)生學(xué)習(xí)。自2011年1月1日起,在設(shè)計(jì)上突出單元和學(xué)分特點(diǎn)的“資格和學(xué)分框架”收錄了所有由監(jiān)管部門認(rèn)可的職業(yè)資格,但納入“資格和學(xué)分框架”里的職業(yè)資格需符合“QCF規(guī)范”,任何職業(yè)資格都要體現(xiàn)單元和學(xué)分特色。目前所有BTEC(商業(yè)和技術(shù)教育委員會(huì))職業(yè)資格都已重新設(shè)計(jì),以達(dá)到QCF的要求。QCF對(duì)14-19歲教育的影響可以從兩個(gè)方面看:首先,雇主對(duì)資格證書的認(rèn)可度。英國一系列的資格證書改革降低了它們在勞動(dòng)力市場上的價(jià)值,因?yàn)楣椭鞑磺宄@些資格證書的內(nèi)容是什么,它們提供了什么信號(hào)?引入QCF需要對(duì)所有職業(yè)資格重新貼標(biāo);其次,不同資格間的等值性。QCF使用“學(xué)分”旨在把所有的資格都放在一個(gè)共同的量表里。如果不同資格證書的學(xué)分?jǐn)?shù)相同,人們就可以把這些不同的資格看作是“等值”的,并且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資格中累加學(xué)分。從2001年開始,資格和課程署在所有資格中建立這種等值性,QCF的設(shè)計(jì)正是體現(xiàn)了這些原則。然而,“等級(jí)”和“學(xué)分”在形式上的等值不能并且也不會(huì)轉(zhuǎn)化為實(shí)質(zhì)性的等值。QCF主要考慮了成人(19歲以上)學(xué)習(xí)的需要,可能適合于那些已經(jīng)就業(yè)或?qū)β殬I(yè)作出了明確選擇的成人,但QCF不應(yīng)是提供給14-19歲學(xué)生學(xué)習(xí)的唯一職業(yè)資格類型。職業(yè)資格證書重新設(shè)計(jì)和全面再貼標(biāo)導(dǎo)致頒證機(jī)構(gòu)大量成本,這些成本最后都轉(zhuǎn)嫁到學(xué)生考證費(fèi)上了。
4.學(xué)徒培訓(xùn)框架僵化,缺乏適應(yīng)性。學(xué)徒培訓(xùn)框架不能完全適應(yīng)地方條件和雇主的需要。以國際標(biāo)準(zhǔn)來看,英國學(xué)徒培訓(xùn)的普通教育內(nèi)容非常少。特別是“照常營業(yè)”學(xué)徒培訓(xùn),在崗培訓(xùn)課程按照“國家職業(yè)標(biāo)準(zhǔn)”,不論個(gè)體學(xué)徒情況如何,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同樣工作角色的培訓(xùn),這也許適合成人學(xué)徒。因?yàn)樗麄冊诮邮芘嘤?xùn)之前就已經(jīng)就業(yè),對(duì)他們的職業(yè)路線非常清楚。目前學(xué)徒培訓(xùn)框架的內(nèi)容和性質(zhì)不能促進(jìn)青年人的教育進(jìn)步,這與政府鼓勵(lì)從學(xué)徒培訓(xùn)進(jìn)入高一級(jí)學(xué)習(xí)的期望不符。在一個(gè)以工作為基礎(chǔ)的路徑里要想在教育上取得進(jìn)步比20年前更困難了,而且高質(zhì)量的學(xué)徒培訓(xùn)太稀少,越來越多的名額分配給了歲數(shù)大的,而不是年輕人。
5.按證書數(shù)量撥付經(jīng)費(fèi)造成不恰當(dāng)刺激。“等值性職業(yè)資格”以及績效測量指標(biāo)給初中階段和高中階段教育都帶來了不恰當(dāng)刺激,讓學(xué)生進(jìn)入容易通過的資格證書學(xué)習(xí),這既有損標(biāo)準(zhǔn)又有損效率。高中階段(16歲后)教育經(jīng)費(fèi)撥付的依據(jù)是資格證書而不是開設(shè)的課程,在很大程度上經(jīng)費(fèi)撥付數(shù)額取決于通過的資格證書數(shù)量的多少。很明顯的事實(shí)是,資格證書越容易,學(xué)生越容易通過,頒證機(jī)構(gòu)的利潤也越高。目前的經(jīng)費(fèi)分配制度不僅給學(xué)校提供了強(qiáng)烈的刺激,讓學(xué)生學(xué)習(xí)容易通過的科目,而且也給頒證機(jī)構(gòu)提供了強(qiáng)烈刺激,讓科目通過變得更為容易。
6.合格師資和辦學(xué)基礎(chǔ)能力不足。職業(yè)教育資格證書迅速膨脹不僅導(dǎo)致許多專業(yè)課程由那些沒有接受過該領(lǐng)域?qū)I(yè)培訓(xùn)的人教授,而且造成缺乏基本的培訓(xùn)設(shè)施。不可否認(rèn),英國有些學(xué)校辦學(xué)質(zhì)量很出色,但總體看,在規(guī)模擴(kuò)張的壓力下職業(yè)教育質(zhì)量面臨下降,缺乏必要的質(zhì)量控制。這在英國也不是什么新現(xiàn)象,早在上個(gè)世紀(jì)90年代,當(dāng)國家普通職業(yè)教育資格首先引入學(xué)校時(shí),職業(yè)教育質(zhì)量就成為需要解決的一個(gè)重要問題。
三、報(bào)告建議與政府改革措施
為推進(jìn)英國職業(yè)教育改革,沃爾夫報(bào)告提出的改革四原則:教育系統(tǒng)必須停止將14-16歲學(xué)生分流進(jìn)“死胡同式”課程;教育系統(tǒng)必須誠實(shí),以免使學(xué)生受到錯(cuò)誤決策的傷害;教育系統(tǒng)必須迅速簡化,取消不恰當(dāng)刺激措施;學(xué)習(xí)借鑒其他國家有益經(jīng)驗(yàn)和最佳實(shí)踐。
報(bào)告提出以下主要建議:保證沒有達(dá)到普通中等教育證書英語和數(shù)學(xué)科目“C”級(jí)成績的每一個(gè)學(xué)生在高中階段繼續(xù)學(xué)習(xí)這些科目。建立經(jīng)費(fèi)分配和學(xué)校績效評(píng)價(jià)正向?qū)驒C(jī)制,不使學(xué)生被分流到低質(zhì)量資格證書課程。高質(zhì)量職業(yè)資格證書要由政府認(rèn)定,學(xué)校應(yīng)有開設(shè)資格證書課程的自主權(quán)。職業(yè)專門化教學(xué)時(shí)間限制在20%之內(nèi),取消以問責(zé)的理由讓學(xué)校制造大量資格證書的刺激措施。按生均標(biāo)準(zhǔn)撥付義務(wù)教育和高中教育經(jīng)費(fèi)。轉(zhuǎn)變資格監(jiān)管思路,重點(diǎn)要從資格認(rèn)證轉(zhuǎn)向?qū)︻C證機(jī)構(gòu)的監(jiān)督。取消16-19歲學(xué)生必須取得“資格和學(xué)分框架”中資格證書的硬性規(guī)定,增加數(shù)學(xué)教師繼續(xù)專業(yè)發(fā)展的機(jī)會(huì)。允許14-16歲學(xué)生到職業(yè)性學(xué)院學(xué)習(xí),使他們從高質(zhì)量職業(yè)培訓(xùn)中受益;地方雇主要直接參與質(zhì)量保障和評(píng)估活動(dòng),發(fā)放雇主學(xué)徒培訓(xùn)補(bǔ)貼,擴(kuò)大高質(zhì)量學(xué)徒培訓(xùn)機(jī)會(huì)。加強(qiáng)部際協(xié)調(diào),協(xié)同解決教育與培訓(xùn)經(jīng)費(fèi)分配等問題。在決策機(jī)制上,英國歷來就有將受委托的委員會(huì)報(bào)告或?qū)<覉?bào)告的全部或部分建議作為決策重要依據(jù)的傳統(tǒng)。2001年5月教育部對(duì)報(bào)告作出正式回應(yīng),幾乎全部接受了沃爾夫報(bào)告提出的27條建議。圍繞報(bào)告的建議,教育部提出以下職業(yè)教育改革措施。
(一)加強(qiáng)文化素質(zhì)教育,保證語文和數(shù)學(xué)成績達(dá)到基本標(biāo)準(zhǔn)
保證所有學(xué)生到19歲都能學(xué)習(xí)和達(dá)到GCSE語文和數(shù)學(xué)A*-C級(jí)成績水平。對(duì)那些不能馬上達(dá)到這些成績水平的學(xué)生,開發(fā)高質(zhì)量語文和數(shù)學(xué)課程,使他們能在以后階段取得證書。改革普通中等教育證書,保證該證書成為基礎(chǔ)教育階段學(xué)生學(xué)習(xí)成就更為可信的指標(biāo),特別是要結(jié)合當(dāng)前對(duì)國家課程的評(píng)估工作,改革中等教育證書學(xué)科內(nèi)容。
(二)改革學(xué)校績效排行榜
取消那些降低職業(yè)教育價(jià)值,把學(xué)生推入不能使他們進(jìn)入工作或繼續(xù)學(xué)習(xí)的資格路徑的不恰當(dāng)刺激措施。提高學(xué)校績效測量水平的職業(yè)資格證書應(yīng)是那些在內(nèi)容、評(píng)價(jià)和學(xué)習(xí)進(jìn)步路徑方面最適合學(xué)生的職業(yè)資格證書。使用普通中等教育證書5門科目達(dá)到A*-C等級(jí)的比例等門檻測量指標(biāo),會(huì)導(dǎo)致部分學(xué)校忽視學(xué)習(xí)好的學(xué)生。績效指標(biāo)不能讓學(xué)校只是關(guān)注特定學(xué)生群體而以犧牲其他學(xué)生為代價(jià)。為避免這種傾向,教育部繼續(xù)使用平均積點(diǎn)分?jǐn)?shù)(APS)等績效測量,捕捉不同能力水平學(xué)生的全面結(jié)果。從2011年開始,績效排行榜增加每個(gè)學(xué)校低成就學(xué)生、高成就學(xué)生和那些達(dá)到期望標(biāo)準(zhǔn)學(xué)生的表現(xiàn)差異等指標(biāo)。
(三)積極發(fā)展學(xué)徒培訓(xùn)
教育部完全接受沃爾夫報(bào)告的建議,認(rèn)為學(xué)徒培訓(xùn)被廣泛看作在工作中學(xué)習(xí)的最佳途徑。學(xué)習(xí)借鑒國外相關(guān)經(jīng)驗(yàn),保證學(xué)徒培訓(xùn)達(dá)到世界一流標(biāo)準(zhǔn),簡化學(xué)徒培訓(xùn)行政審批程序,消除官僚主義,使雇主更容易提供學(xué)徒培訓(xùn),保證政府和雇主對(duì)學(xué)徒培訓(xùn)的投入能夠產(chǎn)生最佳效果。增加學(xué)徒培訓(xùn)框架的進(jìn)步性和彈性,16-18歲學(xué)徒的普通教育應(yīng)為他們的繼續(xù)學(xué)習(xí)和整個(gè)生涯發(fā)展打下一個(gè)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調(diào)整16-18歲學(xué)徒培訓(xùn)框架中的普通教育成分,以體現(xiàn)課程學(xué)習(xí)的寬泛性。尚未達(dá)到GCSE英語和數(shù)學(xué)科目A*-C級(jí)成績水平的16-18歲學(xué)徒應(yīng)有機(jī)會(huì)繼續(xù)補(bǔ)習(xí)這些科目,到2012年9月逐步取消學(xué)徒培訓(xùn)框架中“關(guān)鍵技能”部分,將“基礎(chǔ)技能”和GCSE科目學(xué)習(xí)作為學(xué)徒培訓(xùn)中獲得義務(wù)英語和數(shù)學(xué)素質(zhì)要素的唯一得到認(rèn)可的路徑。除發(fā)揮行業(yè)技能委員會(huì)的作用外,鼓勵(lì)雇主參與學(xué)徒培訓(xùn)框架的制定和資格證書的設(shè)計(jì)。加大對(duì)學(xué)徒培訓(xùn)投入力度,商務(wù)、創(chuàng)新和技能部通過“增長和創(chuàng)新基金”增加學(xué)徒培訓(xùn)投入,提高資金分配和使用透明度,規(guī)范中介組織行為。對(duì)雇主實(shí)行補(bǔ)貼,鼓勵(lì)中小企業(yè)提供更多學(xué)徒培訓(xùn)名額,規(guī)范學(xué)徒合同管理,簡化程序,提高效率。注重發(fā)揮集團(tuán)培訓(xùn)協(xié)會(huì)(GTA)、學(xué)徒培訓(xùn)署(ATAs)、國家技能學(xué)院和國家學(xué)徒培訓(xùn)服務(wù)中心等組織機(jī)構(gòu)的作用。近幾年來,英國19歲以下學(xué)生學(xué)徒人數(shù)在穩(wěn)步增加,從2006年的10.56萬人增加到2010年的13.17萬人。
(四)關(guān)注低成就學(xué)生
低成就學(xué)生是指那些達(dá)不到二級(jí)資格證書要求的學(xué)生。沃爾夫報(bào)告建議把低成就學(xué)習(xí)者(包含有學(xué)習(xí)障礙和殘疾的、以及那些對(duì)正規(guī)教育極為不滿的學(xué)生)課程重點(diǎn)放在語文和數(shù)學(xué)核心學(xué)術(shù)技能學(xué)習(xí)以及增加工作經(jīng)歷上,改革經(jīng)費(fèi)分配方案和績效測量,重點(diǎn)關(guān)注核心領(lǐng)域和就業(yè)結(jié)果而不是資格證書數(shù)量增長。教育部接受報(bào)告的建議,認(rèn)為所有學(xué)生不論其起點(diǎn)如何,都要有機(jī)會(huì)充分發(fā)揮他們的潛能。教育部將對(duì)那些到16歲不能直接達(dá)到普通中等教育證書資格水平的最脆弱的學(xué)生提供更多的支持。英國有很高比例的學(xué)生不能達(dá)到這個(gè)關(guān)鍵水平,這損害了他們繼續(xù)接受教育和就業(yè)的前景。要采取有力措施,提高低成就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水平,讓更多的低成就學(xué)生取得進(jìn)步。高中階段的課程學(xué)習(xí)要幫助學(xué)生達(dá)到英語和數(shù)學(xué)教學(xué)要求,為他們提供有價(jià)值的工作經(jīng)歷。學(xué)習(xí)和借鑒國際經(jīng)驗(yàn),總結(jié)和推廣那些幫助弱勢學(xué)生取得進(jìn)步學(xué)校好的經(jīng)驗(yàn),對(duì)“基礎(chǔ)學(xué)習(xí)證書”進(jìn)行獨(dú)立評(píng)估,聽取相關(guān)學(xué)校和學(xué)生的意見。
(五)進(jìn)一步研究國家職業(yè)標(biāo)準(zhǔn)適用性問題
沃爾夫報(bào)告建議教育部以及商務(wù)、創(chuàng)新和技能部應(yīng)討論并就“國家職業(yè)標(biāo)準(zhǔn)”的未來及在青年教育與培訓(xùn)中的合適作用征求各方意見。教育部表示:“國家職業(yè)標(biāo)準(zhǔn)”仍是成人專業(yè)資格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它在多大程度上適用于學(xué)校職業(yè)教育要作進(jìn)一步研究。教育部將會(huì)同英國教育和技能委員會(huì),就“國家職業(yè)標(biāo)準(zhǔn)”的未來,包括如何在職業(yè)資格中最佳使用這些標(biāo)準(zhǔn)等問題,征求國家級(jí)雇主機(jī)構(gòu)、行業(yè)技能委員會(huì)、職業(yè)資格監(jiān)管部門和其他關(guān)鍵合作伙伴的意見。商務(wù)、創(chuàng)新和技能部在《建設(shè)世界一流的技能體系》報(bào)告里表示,就國家職業(yè)標(biāo)準(zhǔn)在就業(yè)市場是否適合用途征求意見和進(jìn)行調(diào)研,在就業(yè)市場上工作的性質(zhì)正迅速變化,個(gè)人變換職業(yè)更為頻繁[4]。
四、結(jié)語
沃爾夫報(bào)告以證據(jù)和事實(shí)為基礎(chǔ),深刻剖析了英國職業(yè)教育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許多有決策價(jià)值的建議,對(duì)英國的職業(yè)教育改革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分析沃爾夫報(bào)告和英國政府推行的職業(yè)教育改革舉措,我們有以下幾點(diǎn)啟示:
一是注重學(xué)習(xí)借鑒國外經(jīng)驗(yàn),特別是德國、法國和丹麥等國發(fā)展職業(yè)教育經(jīng)驗(yàn)。這也說明在當(dāng)今世界教育發(fā)展中,既要充分考慮國情,又要準(zhǔn)確把握世界教育發(fā)展趨同特征。
二是報(bào)告提出了判斷職業(yè)教育價(jià)值的重要命題。從學(xué)習(xí)者個(gè)人角度看,判斷的標(biāo)準(zhǔn)應(yīng)是其學(xué)習(xí)結(jié)果的勞動(dòng)力市場價(jià)值和教育價(jià)值,勞動(dòng)力市場價(jià)值主要體現(xiàn)在學(xué)習(xí)者就業(yè)后的收入水平,教育價(jià)值表現(xiàn)為學(xué)習(xí)者是否具有接受高一級(jí)學(xué)習(xí)的能力和機(jī)會(huì)。學(xué)校正規(guī)職業(yè)教育要立足于學(xué)生的未來發(fā)展需要,為學(xué)生終身發(fā)展奠定基礎(chǔ),改革“死胡同式”課程學(xué)習(xí),不能讓學(xué)生學(xué)習(xí)那些既沒有勞動(dòng)力市場價(jià)值又沒有教育價(jià)值的資格證書。
三是加強(qiáng)基本文化素質(zhì)教育,專門化學(xué)習(xí)向后推遲。英國在初中階段(14-16歲)就開始分流,而各國的經(jīng)驗(yàn)是義務(wù)教育階段主要實(shí)施面向全體的普通教育,過早分流不利于學(xué)生成長。學(xué)習(xí)者的基本文化素質(zhì)是勞動(dòng)力市場主體和教育提供者共同認(rèn)可的學(xué)習(xí)結(jié)果,特別是要加強(qiáng)語文和數(shù)學(xué)教育,初中階段前不應(yīng)有實(shí)質(zhì)性程度的專門化。
四是國家職業(yè)標(biāo)準(zhǔn)的適用性。成長中的學(xué)生個(gè)體不完全適合于學(xué)習(xí)成人化的、定型的技能。我國《教育規(guī)劃綱要》中“推進(jìn)職業(yè)學(xué)校專業(yè)課程內(nèi)容與職業(yè)標(biāo)準(zhǔn)相銜接”提法的合理性很值得研究,教育標(biāo)準(zhǔn)和職業(yè)標(biāo)準(zhǔn)兩套標(biāo)準(zhǔn)體系的開發(fā)主體、目的、口徑寬度和適用對(duì)象都有很大的不同。OECD認(rèn)為,職業(yè)教育注重非常特定的和實(shí)際技能可能對(duì)支持立即進(jìn)入勞動(dòng)力市場更為有效,但是對(duì)支持進(jìn)一步生涯發(fā)展和繼續(xù)教育沒有什么效用[5]。
五是關(guān)注低成就學(xué)生。它反映了政府的教育價(jià)值取向。英國教育部在2011年的初中階段(KS4)績效測量中新增了“達(dá)到GCSE英語和數(shù)學(xué)科目,A*-C等級(jí)享有免費(fèi)校餐和受照管兒童的比例”這樣的體現(xiàn)教育公平的指標(biāo)[6]。一個(gè)好的教育制度不僅要看它培養(yǎng)了多少拔尖創(chuàng)新人才,還要看它有多少學(xué)生沒有達(dá)到預(yù)期標(biāo)準(zhǔn)。
[1]Wolf Review proposes major refor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EB/OL].http∶//www.education.gov.uk/inthenews/inthenews/a0075181/wolf-review-proposes-major-reform-of-vocational-education.2011-03-03.
[2]Alison Wolf.Review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 The Wolf Report[R].March 2011.
[3]Alison Wolf.Review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 The Wolf Report[R].March 2011.
[4]Department for Business,Innovation and Skills (BIS).Further Education and Skills System Reform Plan∶Building a World Class Skills System[R].1 Dec 2011.
[5]Viktória Kis.Learning for Jobs OECD Review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United States∶Texas[R].OECD,2011.
[6]School and College Performance Tables Statement of Intent 2011[EB/OL].http∶//www.education.gov.uk/performancetables/index.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