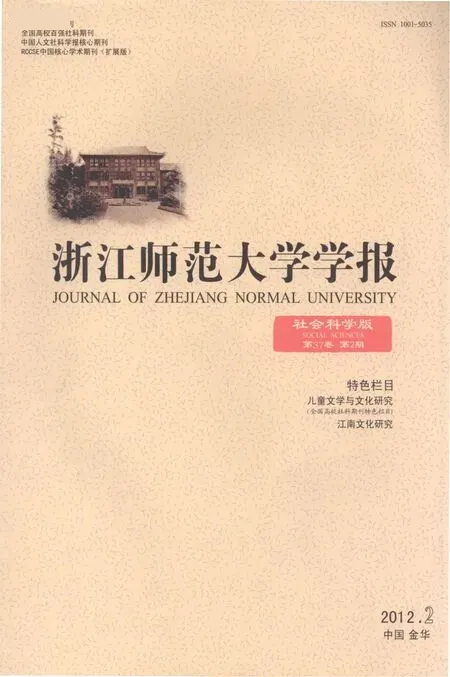明清時期《水滸傳》研究方法及其現代承傳
劉天振
(浙江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浙江 金華 321004)
明清時期的學者運用著錄、注釋、序跋、評點等傳統方法對《水滸傳》的作者、本事、成書、版本等問題進行研究,取得了許多基礎性成果。20世紀初以來,各種西方理論的引入極大地拓展了《水滸傳》研究的視野,但傳統研究方法在吸收現代理論營養的基礎上,依然展現出強盛的生命力,它們依托新式傳媒技術,采用新型撰述方式,在與現代學術理論結合、交融的過程中,共同推進《水滸傳》研究不斷邁向新的境界。
一、明清時期《水滸傳》研究方法
(一)文獻學方法
1.目錄學
水滸故事篇目的著錄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羅燁的《醉翁談錄》一書。此書在《舌耕敘引·小說開辟》中記載了南宋“說話”107個篇目中有4個水滸故事:“樸刀類”有《青面獸》,“桿棒類”有《花和尚》、《武行者》,“公案類”有《石頭孫立》。元代鐘嗣成《錄鬼簿》、明初賈仲明《錄鬼簿續編》又載錄了許多當時流行的水滸劇目。這些著錄工作為后人研究《水滸傳》的成書提供了珍貴資料。
明代嘉靖間高儒《百川書志》“史志三·野史類”著錄曰:“《忠義水滸傳一百卷》,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宋寇宋江三十六人之事,并從副百有八人,當世尚之。周草窗《癸辛雜志》中具百八人混名。”[1]其著錄體例包括書名全稱、卷數、作者、情節提要、旁證文獻等。晁瑮《晁氏寶文堂書目》“子雜類”著錄了兩種《宣和遺事》,后一種注曰“舊刻”;還著錄了兩種《水滸傳》:一種名《水滸傳》,題下注曰“武定板”;另一種為《忠義水滸傳》。顯然,晁瑮已經注意到了《水滸傳》傳世版本的差異問題。萬歷間王圻《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傳記類》也著錄有《水滸傳》,并注云:“羅貫著,貫字本中,杭州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敘江事,奸盜脫騙甚詳,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說者謂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2]但是,后來王圻在《稗史匯編》“文史門·雜書類”《院本》條的記載中,又完全推翻了前書觀點,對羅貫中的“絕世軼材”和《水滸傳》“惟虛故活”的敘事藝術大加贊賞。[3]清初錢曾《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錄匯編》第十卷“戲曲小說”著錄“古今雜劇”342種,其中專辟“水滸故事”一目,收錄《魯智深喜賞黃花峪》、《梁山五虎大劫牢》、《梁山七虎鬧銅臺》等水滸雜劇9種,[4]293“通俗小說”一目下著錄了《舊本羅貫中水滸傳二十卷》。[4]299上述諸書對《水滸傳》作者、版本、成書過程等問題的著錄及評述,為后人的研究鋪墊了重要的文獻基礎,并對后世的小說著錄工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注釋
所謂“注釋”是指對文本中生僻字詞、名物掌故、作者背景等的解釋說明。孔穎達《毛詩正義》卷一曰:“注者,著也,言為之解說,使其義著明也。”[5]受歷史上經傳注釋之學的影響,古人對小說的注釋肇端甚早。晉代郭璞注《山海經》、《穆天子傳》,開辟了小說注釋的先河。南朝劉宋時劉孝標為《世說新語》作注,援引浩博,典贍精核,后人推崇至極,“與裴松之《三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同為考據家所引據焉”。[6]劉注問世以后,一直與《世說新語》相輔而行,成為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其“注書之法”則為后代小說注釋樹立了典范。
明清時期在《水滸傳》注釋方面最引人矚目、成就最顯著者當推清代程穆衡的《水滸傳注略》。程穆衡(1703-1793),字惟淳,太倉人。乾隆二年(1737)進士,授山西榆社知縣,博聞強識,工于文章,著有《復社紀略》2卷、《太倉風土記》、《太倉州名考》、《吳梅村詩集箋注》12卷、《婁東耆舊傳》等。眾所周知,為《水滸傳》這樣渲染暴力犯禁的小說作注,在當時無疑是驚世駭俗之舉。面對正統之士的疑惑與責難,程穆衡在《水滸傳注略·小引》中辯解道:“學務其大,固已,不曰學始于博乎!學不博,則僻陋謾訑,譬鼠之窺止四壁,雞之鳴止一聲。而務博者又必抉其奧,古來著述者皆然,而是書尤著。……蓋其貫穿經史,網羅百家,旁摭二氏,衍一義,訂一言,靡不融會載籍而出之,乃數百年來從無識者。即自詡能讀矣,止窺其構思之異敏,運筆之靈幻。若其爐錘古今,征材浩富,語有成處,字無虛構,余腹笥未可謂儉,然且茫如望洋焉。”[7]429他搬出了先儒“博文博學、畜德之所”的古訓。其實,此舉受到了當時學風的直接推動,是傳統的蟲魚之學在乾嘉考據之風裹挾下滲入小說研究的一個范例。
程的注釋不僅限于字詞名物、典實制度的考證,還對《水滸》文獻、文本中的許多問題發表了精辟之見。如他對“東都施耐庵”之有無持懷疑態度:“不知耐庵何名字,宋、元人書俱無載者。唯考元人鐘嗣成《錄鬼簿》,有‘施惠字君美,巨目美髯,好談笑……’嗣成,宋末元初人,而與君美游,或即其人亦未可知。”[7]431他對貫華堂本作者題署的懷疑是有道理的,后人對《水滸》作者的研究確認了這一點。再如《水滸》第六十九回敘宋江率義軍攻打東平府時,九紋龍史進提出潛入城內,與義軍作內應,理由是他舊日曾與此地妓女李瑞蘭往來情熟。而這個枝節顯然與卷首描寫的那個年方“十八九歲”的少年英雄史進形象不相吻合。程穆衡發現了這個矛盾,他說“古本”中去當細作的是焦挺。不管程穆衡所言“古本”是否存在,他的質疑都指出了《水滸傳》在塑造史進形象時的疏忽。程的注釋、引證與分析,對于促進《水滸傳》的傳播、提高《水滸傳》的地位,均有積極作用。鄭振鐸先生曾對程穆衡的注釋給予高度評價:“為章回小說作注者,于此書外,未之前聞。程穆衡引書凡數百種;自《史》、《漢》以下至耐得翁《都城紀勝》、吳自牧《夢粱錄》,僻書頗多。《水滸》多口語方言,作者于此,亦多詳加注釋,不獨著意于名物史實之訓詁。”[7]496
又如,清代平步青《小棲霞說稗》“雙漸”條對《水滸傳》中涉及的《豫章城雙漸趕蘇卿》的故事源流進行了詳細考證。[7]494-495
(二)評點與序跋
1.評點
明清時期《水滸傳》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是評點式研究,代表人物有李贄、葉晝、金圣嘆等。經史的注疏、章句、敘錄等形式孕育了評點的思維模式,梁代蕭綺有關《拾遺記》的“錄”更可視為后世小說“回評”的先驅;但是直接對明清小說評點產生影響的還是唐宋以來的詩文評點。這種形式多為有感而發,有的放矢,精警深刻,已與作品融為一體,相得益彰,“評點靠作品而生發,作品因評點而生色”。[8]李贄等人的評點涉及到《水滸傳》的思想內涵、藝術價值及小說創作中的有關理論等問題。據袁宏道《游居柿錄》載,李贄在萬歷壬辰間曾逐字批點《水滸傳》。雖然明代冒出的許多所謂李贄評點本《水滸傳》值得懷疑,但至少百回本《忠義水滸傳敘》出于李贄之手是可以肯定的。在這篇著名的《敘》中,李贄稱《水滸傳》為“賢圣發憤之所作”,“古今至文”。[9]1488金圣嘆認為:“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10]葉晝曾偽托李贄之名評點了許多小說與戲曲,他主要從藝術角度對《水滸傳》進行了深入研究。他說:“《水滸傳》人物情事都是假的,說來卻是逼真,所以為妙。”金圣嘆則說《水滸傳》是“因文生事”。葉、李二人都指出了小說創作中藝術虛構的合理性。葉晝說:“《水滸傳》文字不好處,只在說夢、說怪、說陣處;其妙處,都在人情物理上。”[11]1426提出了小說創作中的藝術真實性問題;又在《水滸傳》第三回回評中指出其所寫人物“同而不同處有辨”。[11]48金圣嘆更將《水滸傳》對人物的個性化描寫視為其藝術成功的根本標志,他說:“別一部書,看過一遍即休,獨有《水滸傳》,只是看不厭,無非為他把一百八個人性格,都寫出來。”[12]
李贄、葉晝、金圣嘆等人評點《水滸傳》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即借題發揮、有感而發,常常突破小說研究的畛域,把《水滸》評點作為一種批判現實、張揚主體意識的方式,或者說他們的小說評點只是一種干預現實的媒介。比較而言,李贄重視的是小說內容思想的為我所用,而金圣嘆更重視小說成就的評價。但也必須指出,李、金等人借題發揮式的評點,往往有一種“六經注我”的偏執,對后世小說研究中出現且愈演愈烈的主觀臆測、過度闡釋現象是產生過消極影響的。
2.序跋
《水滸傳》成書以后,在社會上流傳廣泛,版本眾多,其面貌紛紜復雜。伴隨著許多版本流傳的還有書卷前后的序跋。這種傳統批評方式以小見大,以少總多,涵括了豐富的批評內容和形式,從文獻學的本事考證,作者、版本辨析,到作品思想內容、藝術價值的評析,既積淀了不同時代、不同角度《水滸》研究的成果,也演繹出《水滸傳》版本演變的活的歷史。由于它貼近文本和讀者,往往能夠發揮其他批評形式所不可企及的效果,對《水滸傳》的傳播及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
比較有代表性的《水滸傳》版本序跋,明代有:《天都外臣序刻本〈水滸〉敘》(汪道昆)、《題〈水滸傳〉敘》(余象斗)、《〈忠義水滸傳〉敘》(李卓吾)、《批評〈水滸傳〉述語》(懷林)、《梁山一百單八人優劣》(懷林)、《〈水滸傳〉一百回文字優劣》(懷林)、《又論〈水滸傳〉文字》(懷林)、《〈忠義水滸全書〉小引》(楊定見)、《〈出象評點忠義水滸全書〉發凡》(袁無涯)、《〈忠義水滸全傳〉序》(五湖老人)、《刻〈忠義水滸傳〉緣起》(大滌余人)、《〈英雄譜〉弁言》(熊飛)、《敘〈英雄譜〉》(楊明瑯)、《水滸牌序》(張岱)、《〈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序》(三篇)(金圣嘆)、《施耐庵〈水滸傳〉序》(金圣嘆)、《讀第五才子書法》(金圣嘆)、《〈水滸傳〉序》(張鳳翼);清代有:《〈五才子水滸〉序》(桐庵老人)、《〈第五才子書〉序》(句曲外史)、《〈水滸傳〉序》(陳枚)、《〈水滸傳注略〉小引》(程穆衡)、《〈續水滸征四寇全傳〉敘》(賞心居士)、《〈水滸傳注略〉序》(蘊香居士)、《〈水滸全圖〉序》(劉晚榮)、《〈水滸全圖〉跋》(葉德輝)、《〈第五才子書〉序》(王韜)、《〈新評水滸傳〉三題》(燕南尚生)、《〈水滸畫譜〉自序》(顛道人)、《〈水滸畫譜〉敘》(嵩昆)、《顛道人水滸傳圖本記》(耀年)、《〈宋元春秋〉序》(劉子壯)、《〈評論出象水滸傳〉總結》(王望如)。①這些序跋成為后世《水滸傳》研究最基本、最重要的資料。
(三)思想評論中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
作為一部世代累積型的長篇巨著,《水滸傳》在漫長的成書過程中,吸納、融匯了宋元明社會各階層的思想資源,其思想內涵呈現出豐富性和多元性特征。基于不同的政治、道德立場,明清時人對這部小說思想傾向的評論爭議很大。總括起來,最有代表性的觀點有兩種,即“誨盜說”與“忠義說”。
明代嘉靖時田汝成首倡“誨盜說”。其《西湖游覽志余》卷二十五云:“《水滸傳》敘宋江等事,奸盜脫騙機械甚詳。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13]后來陳繼儒《晚香堂小品》卷二十三也有此論,[7]224直到清末王韜《水滸傳序》還在重復“圣嘆及身被禍,耐庵三世喑啞”[14]的話。無疑,這種論調與官方態度是完全一致的。明清時期官方曾多次發布禁毀小說戲曲的命令,幾乎每次禁書令,《水滸傳》都名列黑名單,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錄之甚詳,此不贅述。
“忠義說”的倡導者可以明代汪道昆和李贄為代表。汪道昆《水滸傳序》對梁山好漢的忠義美德給予了高度評價:“既蒿目君側之奸,拊膺以憤,而又審華夷之分,不肯右絓遼而左絓金,如酈瓊、王性之逆。……雖掠金帛,而不擄子女。唯剪婪墨,而不戕善良。誦義負氣,百人一心。有俠客之風,無暴客之惡。是亦有足嘉者。”[7]188李贄是明代杰出的思想家,他對《水滸傳》創作宗旨的認識代表了明人對《水滸》思想評價的最高水平。其《忠義水滸傳序》說:“施、羅二公傳《水滸》,而復以忠義名其傳焉。夫忠義何以歸于水滸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滸之眾,何以一一皆忠義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則謂水滸之眾,皆大力大賢有忠有義之人可也,然未有忠義如宋公明者也。”并稱宋江為“忠義之烈”。[9]1488此外,楊定見《〈忠義水滸全書〉小引》、五湖老人《〈忠義水滸全傳〉序》、大滌余人《刻〈忠義水滸傳〉緣起》等也都發表過類似之論。這種評價模式在20世紀以來《水滸》思想研究中多次以不同形式映現出來。
二、20世紀以來《水滸傳》研究方法對明清時期研究方法的承傳
(一)文獻學方法
1.對《水滸傳》文獻的著錄
20世紀初以來問世的許多小說目錄都是在明清人工作基礎上完成的。一些綜合性的小說目錄如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上雜出版社1953年版)、《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澳)柳存仁《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年版)、(日)大塚秀高《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日本東京汲古書院1987年版)、江蘇省社科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年版)、石昌渝《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等,對《水滸傳》的著錄盡管版本數量不斷增加,編撰體例也不斷改進,但從中不難看出均受到了明清人著錄方式的影響。僅就《水滸》版本著錄情況而言,《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卷六“明清小說部”、卷九“附錄二”共著錄24種《水滸》版本;《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著錄《水滸》版本多達27種。就撰述體例而言,義項不斷擴展,信息越來越豐富,實用性越來越強。《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著錄《水滸傳》書名、卷數、存佚、載錄書目、版本面貌等項。《中國通俗小說總目》對《水滸傳》的著錄包括:書名、作者、版本、情節提要、回目等項,尤其后二項為孫氏書目所無,而這兩項對于讀者了解作品的內容概貌很有幫助。馬蹄疾《水滸書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是一部《水滸傳》的專題目錄書,全書分三編:上編“版本編”,著錄《水滸傳》的各種版本;下編“評論編”,著錄《水滸傳》的研究專著、專集和報刊散論;外編“水滸故事的各種文藝作品”,著錄有關水滸故事的各種文藝作品,分續書·仿書、小說·故事、戲曲·電影·話劇、評話·曲唱、繪畫·工藝品等五個部分。顯然,其著錄范圍更廣,信息量更大,實用性更強。另外,今人沈伯俊《〈水滸〉研究論著索引》(1949年10月-1984年12月,載沈伯俊編《水滸研究論文集》,中華書局1994年版)、白嵐玲《金圣嘆研究專著、論文索引》(載其《才子文心——金圣嘆小說理論探源》,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等,都是對傳統著錄方法的承傳與延續。
2.新型注釋學研究方法
20世紀初以來,中國古代小說研究逐步實現了現代轉型,許多新的理論與方法被引入《水滸傳》研究,但是,扎根于深厚學術文化傳統基礎上的注疏學方法仍然展現了頑強的生命力。張真如《〈水滸傳〉方言疏證》(刊于1921年5月6、11、13、14、16、17、19、21、23、27 日《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對《水滸》中涉及的眾多方言進行注釋、考證,為這部小說跨越時空局限、實現現代意義的“通俗”掃除了許多障礙。1923年上海世界書局出版的整理本《足本水滸傳》,書后附有李崇孝的《人名辭典》、《地理辭典》。余嘉錫《〈水滸傳〉之俗語》(刊于1946年10月9日《經世日報》副刊《讀書周刊》9期)對《水滸》中出現的“剪拂”、“迎兒”、“婆惜”諸俗語,結合宋代民俗一一進行考釋,不僅有助于理解文本,也對民俗學視角的小說研究有所啟迪。195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整理本《水滸》,以金圣嘆批改本為底本,并根據其他版本進行訂正,除了文字的修訂,還對一些難解詞語尤其是方言隱語作了注釋。1953年再版時,對該書注釋中存在的問題,許政揚撰有《評新出〈水滸〉的注解》(載1953年6月3日《光明日報》)一文進行專門評論。許政揚與周汝昌甚至為了給“將來更精詳的注本作個開路先鋒”,還合作撰寫《〈水滸傳〉簡注》,底本采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水滸》,但可惜只注了兩回,寫了117條注釋就中止了。[15]年何心《水滸研究》一書由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出版,全書分二十章,對《水滸傳》涉及到的官職、地名、社會風俗、衣食住行、俗話諺語等進行了詳盡考釋,深受讀者歡迎。此書后來又多次出版了修訂本。
80年代以來,一些關于《水滸傳》的辭書、工具書相繼問世。如李法白、劉鏡芙《水滸語詞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版),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百回整理本《水滸傳》為依據,共收錄詞、熟語3194條,“以《水滸傳》中的近代詞語(上起晚唐五代,下迄元末明初)為主”,[16]每一詞語釋義后附列兩個例證。胡竹安歷40多年資料積累之功編成《水滸詞典》(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89年版),“以古代白話詞匯、語法現象為主”,[17]采用音序法,分為詞語和俗語兩部分,據195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鄭振鐸序本《水滸全傳》,共收詞4673條,熟語222條,計4895條。類似的《水滸》專書詞典還有日本學者香坂順一的《水滸詞匯研究》(日本光生館1987年版),該書以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版《水滸全傳》為依據,旨在把《水滸》中的詞匯“納入各個詞類,以得出一個系統的語法體系”。這些采用現代語言學理論研究《水滸傳》的辭典,一方面具有獨立的學術價值,同時,在推動《水滸傳》傳播與普及方面更是厥功甚偉。后來還有一些關于《水滸傳》的辭書陸續問世,如王玨、李殿元《水滸大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任大惠《水滸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許振東《學生實用水滸傳辭典》(遼海出版社2003年版)、沙先貴《水滸辭典》(崇文書局2006年版)以及日本高島俊男《水滸人物事典》(日本講談社1999年版)等。這些辭書加在一起,實際可稱為文本形式的水滸知識博物館。它們已不是簡單地注釋詞語、訓詁名物或賞析故事,而是試圖匯輯與《水滸傳》研究相關的所有知識。如《水滸大觀》對《水滸》中“難點、疑點、成書背景、思想內容等等,進行了詮釋、分析和介紹,舉凡人物、地理、制度、謀略、武術等方面內容,都在搜羅撰述之列”,[18]全書包括天下奇書、人物畫廊、諢號拾趣、百科一覽、地名考略、武功精粹、謀略集錦、說古道今等八個部分。這種包容性、系統性從某種角度上講體現了現代學術交叉性、互滲性的發展大勢。
(二)“出版說明”及其他
對明清時期《水滸傳》各版本序跋文字的搜集、整理一直是現代《水滸》文獻研究的一項基礎性工作。20世紀50至80年代,這項工作的成果最為豐碩。70年代“文革”期間的“評《水滸》、批宋江”運動中,曾編輯了許多水滸評論資料之類的匯編之作,如《〈水滸〉評論資料》(《出版通訊》1975年第11、12期合刊)、《水滸研究資料》(南京大學中文系資料室編,1980年內部印刷)、《〈水滸〉序跋集》(人民日報圖書資料室編,1975年內部印行)、《水滸評論資料》(西北大學中文系編,1975年內部印行)等,這些書中除了一些批判文章,基本都是匯輯歷代《水滸傳》版本的序跋文字,雖然當時是出于政治運動的需要,但客觀上的文獻整理之功是不能抹煞的。80年代以來出版的幾部《水滸傳》專題資料匯編,如馬蹄疾《水滸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80年版)、朱一玄、劉毓忱《水滸傳資料匯編》(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其體例旨在匯輯《水滸》研究的所有資料,構建《水滸》資料庫,其中一個必有部分就是歷代版本的序跋文字。
20世紀初以來出版的眾多《水滸傳》版本中,大多附有“前言”、“出版說明”等文字,這些文字的作者多為《水滸》研究領域的知名學者,因而它們多是學力深厚、見解獨到的研究論文,往往能夠反映當時研究的最高水平。如1920年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汪原放校點整理的《水滸》,卷首附有胡適《水滸傳考證》、陳獨秀《水滸新序》、汪原放《水滸校讀后記》等文,它們以全新的方法、全新的觀點、全新的撰述形式,揭開了《水滸》現代研究史的新篇章。195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整理本《水滸》(七十一回本),卷首附載《關于本書的版本》、《關于本書的作者》二文,對于所據版本、整理經過以及《水滸》作者研究現狀等問題作了詳細說明。195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又出版一百二十回《水滸全傳》整理本,卷首載有鄭振鐸《〈水滸全傳〉序》,介紹了當時所有的9種比較重要的《水滸》版本,并對版本演變情況作了簡要評述。此序實際上反映了當時《水滸傳》版本研究的最新狀況。
(三)《水滸傳》淪為政治斗爭的工具
晚清“小說界革命”思潮中,《水滸傳》被資產階級革命家當成了政治工具,鄧狂言《紅樓夢釋真》稱《水滸傳》、《金瓶梅》“皆政治小說而寄托深遠者”。燕南尚生《新評水滸傳序》更宣稱《水滸傳》提倡“平權、自由”,并說:“《水滸傳》者,祖國之第一小說也;施耐庵者,世界小說家之鼻祖也。”[7]391民國時期,胡適、魯迅又提出《水滸傳》“反抗政府”說。②20世紀50年代以后,《水滸傳》“農民起義”說成為最權威的觀點,并被寫入教科書。六七十年代“文革”期間的“評《水滸》,批宋江”運動,又將《水滸》打成“宣揚投降主義”的書,宋江也由“農民革命的領袖”搖身變為“農民革命的叛徒”。70年代末以后,《水滸》思想研究才逐漸趨向理性,回歸文本。王學泰在一篇反思“農民起義說”的文章中曾說:“對于《水滸傳》主題與思想內容的闡發往往與當時的思想運動和政治傾向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近世更是把評論‘水滸’當作政治運動的一部分,開古今未有之先例。”[19]這種說法不可謂不深刻;但是對這種批評現象追根溯源則不難發現,百余年來《水滸傳》思想評論的褒貶抑揚、大起大落,與明清人《水滸》思想評論中二元對立思維模式是有著內在邏輯關聯的。
三、結 語
20世紀初以來,中國學術逐步完成了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包括《水滸傳》在內的古代小說研究在研究方法、撰述方式等方面,皆有很大改觀。20-40年代,在《水滸》研究界形成了以西方進化論、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及中國傳統考據學為主流的中西融合的基本格局,對《水滸傳》的成書過程、作者、版本、本事源流等問題的研究都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涌現出一批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如胡適《〈水滸傳〉考證》(初載亞東圖書館1920年版《水滸》卷首)、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新書局1932年版)第十五篇“元明傳來之講史”、鄭振鐸《水滸傳的演化》(初刊于《小說月報》1929年20卷9期,后收入《鄭振鐸全集》第四卷)等。這些成果因為方法的科學與進步,得出了一些不刊之論,為后來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以上幾位學術大師盡管借用了現代的研究方法,但同時,他們又都擁有深厚的考據學功底。著名史學家羅爾綱傾力探索《水滸傳》的作者及原本,發表了一系列考證專文,③提出《水滸傳》著者是羅貫中,原本有七十回,“用的考證方法是我國傳統的對勘方法”。[20]此觀點在八九十年代曾產生過較大影響,說服力很強,當時雖有人反對,但仍然無法撼動其觀點。[21]
80年代以來,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國內學界與世界學術接軌不斷加深,西方人文科學新方法大量傳入中土,諸如美學、敘事學、比較文學、心理學、原型批評、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接受美學、語義學、符號學、結構主義、模糊數學、闡釋學、傳播學、人類學等,受到了國內學術界的普遍歡迎,《水滸傳》研究也迎來了多元拓展、百家爭鳴的局面:一方面,新的理論視角大大開拓了研究者的視野,改變了學界的傳統思維方式。有些西方理論確實能為中國古典小說的解讀提供新的視角,尤其在文本與文化研究方面,其優勢比較明顯,可以使我們更科學、更客觀地透視中國古代小說的藝術機制;但另一方面,許多年輕學者將西方理論視為闡釋中國古典小說的靈丹妙藥,研究論著一味套用西方新術語,以生澀文飾淺陋,往往不能解決任何學術問題。如用心理學原型批評理論分析《水滸傳》人物形象,動輒說《水滸傳》中的某一人物是歷史上某種原型的再現,這種研究因缺乏直接的文獻與文本支持,根本不能產生說服力。
《水滸傳》作為一部孕育于中國文化土壤、滲透了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藝術杰作,對它的研究,如果摒棄本土的學術理念與研究方法,熱衷于削足適履、硬套各種時髦的西方理論,則難免會有舍本逐末、南轅北轍之偏失。眾所周知,對《水滸傳》作者面貌、本事源流、成書過程、版本演變、方言隱語等問題的研究,如果舍棄傳統文獻學手段的考辨、梳理、注疏之功,要想取得任何進展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要正確對待西方理論方法的運用。有些理論方法只是單單直接地拿來使用是不夠的,往往需要在借鑒、吸收的基礎上,融合中國學術傳統,這樣才能重新創造出適合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具有民族風格的新的理論方法。
注釋:
①參閱南京大學中文系資料室編《水滸研究資料》(1980年內部印行),第50-122頁。
②胡適說:“水滸的故事乃是四百年來老百姓與文人發揮一肚皮宿怨的地方。……明朝中葉的人——所謂施耐庵——借他發揮一肚皮宿怨,故削去招安以后的事,做成一部純粹反抗政府的書。”(《〈水滸傳〉考證》,見《中國章回小說考證》,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頁。)魯迅說:“(《三俠五義》)所敘的俠客,大半粗豪,很像《水滸》中的人物,故其事實雖然來自《龍圖公案》,而源流則仍出于《水滸》,不過《水滸》中底人物在反抗政府,而這一類書中底人物,在幫助政府,這是作者思想的大不同處。”(《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見《中國小說史略》附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第309頁。)
③后輯成《水滸傳原本和著者研究》一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
[1]高儒.百川書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82.
[2]王圻.續文獻通考[M]//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88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371.
[3]王圻.稗史匯編[M]//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41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403-404.
[4]錢曾.虞山錢遵王藏書目錄匯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5]孔穎達.毛詩正義[M]//《十三經注疏》本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269.
[6]永瑢,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卷140[M].北京:中華書局,1965:1182-1183.
[7]朱一玄,劉毓忱.水滸傳資料匯編[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
[8]黃霖.中國小說研究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41-43.
[9]李贄.忠義水滸傳敘[M]//施耐庵,羅貫中.《忠義水滸傳》附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0]金圣嘆.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序[M]//水滸傳會評本.陳曦鐘,侯忠義,魯玉川,輯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9.
[11]施耐庵,羅貫中.忠義水滸傳:第九十七回回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2]金圣嘆.讀第五才子書法[M]//水滸傳會評本.陳曦鐘,侯忠義,魯玉川,輯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17.
[13]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79.
[14]王韜.水滸傳序[M]//《第五才子書》卷首.清光緒十四年(1888)夏上海大同書局石印本.
[15]許政揚,周汝昌.《水滸傳簡注》幾條凡例[M]//許政揚文存.北京:中華書局,1984:83.
[16]李法白,劉鏡芙.水滸語詞詞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凡例.
[17]胡竹安.《水滸詞典》后記[M].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89:615.
[18]任大惠.水滸大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編者的話.
[19]王學泰.《水滸傳》思想本質新論——評“農民起義說”等[J].文史哲,2004(4):117-126.
[20]羅爾綱.水滸傳原本和著者研究·后記[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268.
[21]劉天振.“兩種《水滸》說”與“兩截《水滸》說”論爭述評[J].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30(1):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