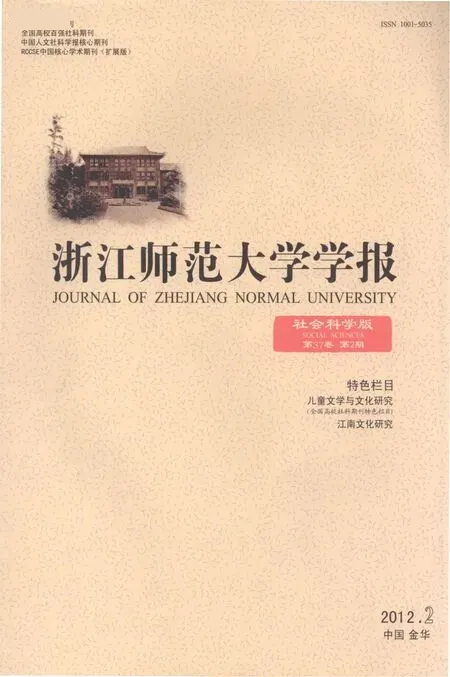俞樾《右臺仙館筆記》的近代意識
韓洪舉, 魏文艷
(浙江師范大學(xué)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 金華 321004)
俞樾(1821-1907),字蔭甫,號曲園先生,也稱舊史氏、曲園叟、曲園老人、曲園居士等,浙江德清人,是晚清嘉道年間著名的文學(xué)大師。他一生專于治學(xué)著述,《清史稿》稱其“生平專意著述,先后著書,卷帙繁富”,[1]有作品集《春在堂全書》,多達(dá)五百卷之巨。俞樾在考據(jù)學(xué)方面成就最為突出,被張之洞譽為“守樸學(xué)于經(jīng)籍將息之秋”,“列儒林真無愧色”。[2]
雖然俞樾本人并不看重他的小說,但其成就卻非常突出。正如陳節(jié)先生所說:“清末的文言小說作家中,俞樾的地位是不容忽視的。”[3]占驍勇也認(rèn)為:“俞樾在小說史上的地位與其在經(jīng)學(xué)上的地位相當(dāng),是古小說的終結(jié)者。”[4]其文言小說《右臺仙館筆記》為廣大讀者所熟悉,代表了俞樾文言小說作品的最高成就。
一、俞樾與《右臺仙館筆記》
俞樾所處的時代是中國近代意識萌動發(fā)展的時期,同時,中國文學(xué)的近代化也在漸漸發(fā)生。鴉片戰(zhàn)爭使中國由閉關(guān)鎖國變?yōu)殚_放海禁,出現(xiàn)了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作為意識形態(tài),文學(xué)的反應(yīng)更為強烈,從內(nèi)容到形式都在求“變”求“新”,都在向近代化邁進(jìn)。而小說是最能夠靈敏地再現(xiàn)社會現(xiàn)實的文學(xué)形式,小說家感受時代脈搏也最為敏銳,體現(xiàn)在小說和小說家身上的“新”與“變”,首先就是近代意識的迅速萌發(fā)。所謂近代意識,即是思想的近代化,其核心就是人道主義,這是由封閉的思維體系向開放的思維體系轉(zhuǎn)化的必經(jīng)過程,由傳統(tǒng)觀念到面向世界、社會人生轉(zhuǎn)化,在文學(xué)上主要表現(xiàn)為批判社會的墮落、呼喚人性的復(fù)歸。中國近代意識中求新、求變、求用的精神激勵著晚清文人積極思考、勇于創(chuàng)作。這種意識突破了封建士大夫原有世界觀的局限,體現(xiàn)了他們變革社會的強烈愿望,同時也流露出其憂國憂民的人文情懷。作為文學(xué)大師,俞樾不能不受到時代潮流的沖擊,加上他的家鄉(xiāng)浙江又處于沿海開放地區(qū),民主主義思想充斥社會的各個領(lǐng)域,在這種特定的歷史和地理環(huán)境下,他成為了一位具有近代意識的進(jìn)步人士。
俞樾的筆記小說集《右臺仙館筆記》共十六卷,前四卷在小說《耳郵》的基礎(chǔ)上增刪而成。俞樾創(chuàng)作此書的初衷是為了排解愛妻去世后的苦悶,事先并沒有進(jìn)行有意識的材料積累工作。《右臺仙館筆記·序》曰:“余自己卯(1879)夏姚夫人卒,精神意興日就闌衰,著述之事殆將輟筆矣。其年冬,葬夫人于錢塘之右臺山,余亦自營生壙于其左。旋于其旁買得隙地一區(qū),筑屋三間,竹籬環(huán)之,雜蒔花木,顏之曰‘右臺仙館’。余至湖上,或居俞樓,或居斯館,謝絕冠蓋,昵就松楸,人外之游其在斯乎?余吳下有曲園,即有《曲園雜纂》五十卷;湖上有俞樓,即有《俞樓雜纂》五十卷,右臺仙館安得無書?而精力衰頹,不能復(fù)有撰述,乃以所記《筆記》歸之。”由此可知,此書創(chuàng)作始于光緒五年(1879)冬。又因《右臺仙館筆記》中故事發(fā)生的時間最晚在“光緒辛巳歲立夏之日”(卷十四),即1881年5月上旬,光緒七年(1881)的《春在堂全書》已收有《右臺仙館筆記》十六卷,因此可以推定,《右臺仙館筆記》于光緒七年(1881)下半年完稿。此書創(chuàng)作的時間,正是中國歷史處于近代時期,是中國小說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zhuǎn)變的過渡期,因此,《右臺仙館筆記》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出了明顯的近代意識。
俞樾在《右臺仙館筆記·序》中寫道:“《筆記》者,雜記平時所見所聞,蓋《搜神》、《述異》之類,不足,則又征之于人,嗟乎!”將創(chuàng)作緣由和素材的來源作了大致的交代。素材主要來自作者的家人、門下弟子和友朋親眷等,另外還有不少人熱情地為俞樾提供原料,如陳廣文。俞樾的創(chuàng)作還吸引了日本來華者,《右臺仙館筆記》卷十二記載了多則有關(guān)日本國的軼事:“以上日本諸事,皆本其國人吉堂所錄。吉堂姓東海氏,名復(fù),在海外曾讀余所著書。及至中國,知余有《右臺仙館筆記》之作,錄此十?dāng)?shù)事,托余門下士王夢薇轉(zhuǎn)達(dá)于余,因粗加潤色而存之。余詩所云‘舊聞都向毫端寫,異事兼從海外求’,洵不虛矣。”縱觀全書,俞樾的小說以表現(xiàn)近代故事為主,雖然還有很多故事沒有指明來源,但均有一定的真實性,反映了當(dāng)時的風(fēng)俗人情與社會狀況。
眾所周知,小說的思想往往是一定時期社會實況的真實反映,是社會變遷的縮影,承載著傳統(tǒng)的文化精神。小說的近代化是中國社會近代化的一個側(cè)面,它緊密聯(lián)系著社會的動蕩與變遷。俞樾身處晚清,曾經(jīng)歷了太平天國運動等戰(zhàn)亂,親眼目睹了百姓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慘劇,對當(dāng)時社會動蕩、民生凋敝的現(xiàn)象有著清醒的認(rèn)識。俞樾以教書為業(yè),經(jīng)常奔走于蘇杭之間,對社會的真實狀況有著親身的感受。他曾經(jīng)為官,且名重一時,晚清的許多達(dá)官貴人都與他有交往,因此,他對社會發(fā)展態(tài)勢有著常人所沒有的感受。所以,《右臺仙館筆記》內(nèi)容十分廣泛,涉及到中國的大部分地區(qū)和社會的方方面面,深刻地反映了晚清的社會風(fēng)貌,同時也表現(xiàn)出作者開通進(jìn)步的思想。下面我們就從危機(jī)意識、重視小說的實用功能和較為進(jìn)步的婦女價值觀三個方面,來闡釋《右臺仙館筆記》所體現(xiàn)出來的近代意識。
二、危機(jī)意識
19世紀(jì)初,清王朝經(jīng)歷了18世紀(jì)的“盛世”之后已日薄西山。19世紀(jì)中后期爆發(fā)了鴉片戰(zhàn)爭,英法聯(lián)軍把侵略的炮口對準(zhǔn)已經(jīng)腐朽的東方古國,敲開了中國封閉的大門。繼此之后西方列強一步步對中國進(jìn)行大規(guī)模的侵略,造成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災(zāi)難。腐朽的清王朝在強敵面前一籌莫展,社會危機(jī)日益加深,古老的中國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在這危機(jī)時刻,一批較早覺悟的有識之士,一方面提倡改革弊政,一方面對乾嘉以來的文風(fēng)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早在鴉片戰(zhàn)爭之前,龔自珍、魏源等少數(shù)先覺者就對衰朽的滿清社會和傳統(tǒng)文化進(jìn)行了批判性的反思,萌發(fā)了朦朧的近代意識,開始對某些傳統(tǒng)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原則產(chǎn)生質(zhì)疑,要求轉(zhuǎn)換文學(xué)的發(fā)展方向。到19世紀(jì)中后期,由于清王朝政治的黑暗腐敗和帝國主義的侵略,各地農(nóng)民起義風(fēng)起云涌,社會形勢急劇惡化,先覺者的憂患意識逐漸演變成為群體的危機(jī)意識,俞樾就是這一群體中的一員。
一個小說家的社會意識進(jìn)步與否,主要體現(xiàn)在他以什么眼光去觀察社會的動向,如何從社會生活中選擇素材,又如何以文學(xué)形式反映到廣大讀者面前。即使作為一個埋首學(xué)問的經(jīng)學(xué)大師,俞樾也不能不對當(dāng)時衰頹的社會坐視不問,他把自己對社會的批判和思慮融入到了小說的創(chuàng)作中。《右臺仙館筆記》中的許多篇章都真實地展現(xiàn)了世風(fēng)日下的社會面貌和作者對社會的強烈批評。
首先,小說對封建意識形態(tài)進(jìn)行了強烈的抨擊,對殘害百姓的豪紳惡棍表示出強烈的憤慨之情。比如卷四的“民間呼縣衙曰四衙”一則,通過生動地描摹一個小縣衙的形象,對清廷官僚統(tǒng)治機(jī)構(gòu)展開了全面的暴露與抨擊,揭示了封建統(tǒng)治分崩離析、病入膏肓的末日圖景。在這則故事中,一個小小的衙役竟然在民間橫行霸道,他上面的官員是怎樣地魚肉百姓便可想而知了。老百姓沒有辦法抗衡這些驕橫的惡勢力,俞樾也感到無能為力,只能在書中借冥報來表達(dá)對他們的憎恨之情。卷八記載了“居心險惡”的沈岳良,混入太平軍中仗勢欺人,“每掠得婦女,必裸而淫之。禪國山東南有石洞,極深邃,婦女避亂者數(shù)百人入焉。沈積薪焚其洞,皆斃之”。[5]186這個作惡多端的人后來被怨鬼溺死廁中,“遍身青黑,七竅流血,臭穢不可向邇”。真是惡有惡報,令人拍手叫快。
其次,晚清戰(zhàn)亂不斷,社會上出現(xiàn)了各種各樣的騙子,其騙術(shù)花樣翻新,層出不窮。對此,俞樾也發(fā)出了批判之語。社會上偶有詐騙行為在所難免,但行騙成風(fēng)就不正常了,說明當(dāng)時世風(fēng)日下,道德墮落現(xiàn)象日益嚴(yán)重,應(yīng)引起世人的高度重視。卷三的一則故事中,俞樾將四個小故事集中在一起,講述了婦女為賊、童子為賊、士子為賊、官吏為賊這種極端不正常的現(xiàn)象。作者在文末意味深長地感嘆道:“嗟乎!外戶不閉之風(fēng),固難望于中古以下矣。”文中諸如此類的例子比比皆是。
面對腐敗的社會現(xiàn)實,俞樾感到深深的無奈,只能把對社會現(xiàn)實的不爭與憤恨寫在紙上,試圖喚醒那些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人們,讓他們對自己的處境和社會有一個清醒的認(rèn)識,從而為挽救這個風(fēng)雨飄搖的社會付出實際行動。俞樾從特定的角度詳細(xì)分析了封建統(tǒng)治下人們的生活實質(zhì),預(yù)示滿清王朝社會危機(jī)重重,前途一片黑暗。
最后,俞樾對當(dāng)時流行的愚昧迷信活動持反感態(tài)度,作品中流露出明顯的反封建、講科學(xué)的進(jìn)步思想,體現(xiàn)了作者的近代意識。雖然各個朝代都有封建迷信,但是到了晚清動蕩不安的時期,迷信更是肆無忌憚,不僅普通百姓沉迷于淫祠和邪教,一些士大夫也迷惑于神仙之術(shù),社會上彌漫著一股污濁的瘴氣。卷一的“漢陽朱勛臣”一則,記載了箕仙降于朱家之事。作者在文中不禁議論道:“余雅不信箕仙,竊謂當(dāng)今之世,而欲絕地天通,宜首禁此術(shù)也。”[5]10對迷信活動持完全否定的態(tài)度,并希望徹底禁止此類活動。又如卷七記載了江西張真人府派使者到慈溪城隍廟投書審冥案一事,作者在文中明確表態(tài):“余書雖志怪,然于此等事固不信之也。”雖然是文學(xué)大師,但俞樾卻有著模糊的科學(xué)意識,他對這些雕蟲小技有著本能的反感,批判中充滿不屑與不滿,表現(xiàn)出他在思想認(rèn)識上的進(jìn)步性與獨立性。
俞樾通過對迷信活動的否定告誡世人,千瘡百孔的封建統(tǒng)治已經(jīng)不可救藥,強烈地反映出他悲世的傷痛。
之所以選擇這些記錄事實的材料呈現(xiàn)在廣大讀者面前,是因為俞樾敏銳地體驗到了末代王朝正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jī),他從理性的高度進(jìn)行關(guān)照,并給予生動的表現(xiàn),顯示出進(jìn)步的近代意識,這是前代小說家都缺乏的,即使在同時代作家中也極為少見。
小說是現(xiàn)實的真實寫照,是社會的一面鏡子。這些“社會史料”向世人提供了末代王朝即將土崩瓦解的信息。借此,我們看到了當(dāng)時社會的真實面貌,看到了中國社會的極度黑暗和百姓生活的無比慘苦。
三、重視小說的實用功能
由于近代社會發(fā)生了時代性劇變,社會危機(jī)不斷加劇,學(xué)術(shù)界自然也受到巨大的沖擊,士林風(fēng)氣由此出現(xiàn)了很大的變化,不僅詩風(fēng)、文風(fēng)發(fā)生新變,而且詩論、文論也出現(xiàn)了以經(jīng)世文學(xué)觀為核心的變革思潮,并得到進(jìn)一步發(fā)展。文學(xué)社會功能論的強化,向民眾傳授了西方近代思想,使中國民眾革新了觀念,樹立了近代意識。文學(xué)中最淺顯易懂且趣味性又強的當(dāng)屬小說,所以,提高小說的地位成為了文學(xué)變革的重點。
小說自產(chǎn)生以來就被人們認(rèn)為是小道、殘叢小語,是“治身理家”的短書,而不是為政化民的“大道”。《漢書·藝文志》云:“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yuǎn)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后世對小說的闡述基本上沒有超出這一范圍。直至清代,正統(tǒng)觀念仍舊對小說不屑一顧,《四庫全書》就將許多小說視為“猥鄙荒誕”[6]之書。鴉片戰(zhàn)爭以來,由于受到歐美和日本文學(xué)的影響,梁啟超等為教化國民、開啟民智,達(dá)到救亡圖存的目的,提出了“小說界革命”的主張,并以小說為文學(xué)之最上乘。同時,人們也認(rèn)識到,要提高小說的文學(xué)地位,必須遵從“文以載道”的傳統(tǒng)觀念,加強小說的社會實用功能。這樣一來,原本處于附庸地位的文體——小說,終于躋身于文學(xué)的殿堂,這意味著文學(xué)內(nèi)部結(jié)構(gòu)關(guān)系的重組,也意味著文學(xué)已發(fā)生了由古代向近代根本性的轉(zhuǎn)變。盡管梁啟超等倡導(dǎo)的“小說界革命”最終未能力挽狂瀾,但小說的地位確實較之以前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作為著名的經(jīng)學(xué)家兼小說家,俞樾注意到了文學(xué)和時代的密切關(guān)系,并始終遵循“經(jīng)世致用”的文學(xué)觀念來進(jìn)行創(chuàng)作。
《右臺仙館筆記》取材偏重于具有教化意義的故事,體現(xiàn)了俞樾重視小說的社會作用的觀念和重視人情的較為開明的思想。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稱:“光緒中,德清俞樾作《右臺仙館筆記》十六卷,止述異聞,不涉因果;又有羊朱翁(即俞樾)作《耳郵》四卷,自署‘戲編’,序謂‘用意措辭,亦似有善惡報應(yīng)之說,實則聊以遣日,非敢云意在勸懲’。”[7]魯迅此說,頗有顛倒之嫌,說明此小說確有教化勸懲之意。張舜徽《〈清人筆記條辨〉序目》在談到清代筆記時也說:“有談?wù)f神鬼狐怪者,如紀(jì)昀《閱微草堂筆記》之類是也;有稱述因果報應(yīng)者,如俞樾《右臺仙館筆記》之類是也;有錄奇聞軼事者,如焦循《憶書》之類是也。”[8]俞樾在小說中宣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觀念,以達(dá)到教化民眾的目的。“百行孝為先”,這是俞樾評判一個人的重要道德準(zhǔn)則。他在小說中大力提倡孝行,寫了很多孝子孝女的故事,開篇即是“馮孝子傳”,作者的勸善懲惡之心不言而喻。另外,俞樾為了勸人行善,在小說中還寫了許多行善者皆得善報、作惡者自然遭惡報的故事。如卷八第40則記載朱新甫因一念之善和不記舊惡保全了自己和妻子的性命;卷二第23則中的張少渠也因平時行善而避免了沉船之災(zāi)。
俞樾非常關(guān)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所表現(xiàn)出來的俠肝義膽,鄉(xiāng)土氣息十分濃厚。他在小說中將目光投向了普通人,對那些有著高尚行為的平民百姓大加贊賞。如卷一中“何明達(dá)”一則,主人公只是一個普通的商人,卻能在困境中幫助別人,與前面所舉士人為賊的故事形成鮮明對比,確是“雖士大夫或不及矣”!另外,書中還記載了許多女子的俠義行為,如卷三的紅蘭。作者不但對勇于改正錯誤的人寬容待之,對具有“義行”的動物也不惜筆墨,加以表彰,如卷五說的即是鸚鵡在戰(zhàn)亂中勇救主人的故事。晚清戰(zhàn)亂頻繁,民不聊生,人人自身難保,面對動物的種種義行,只怕連人類都自嘆不如。俞樾對動物俠義的贊譽,目的是為了喚起民族靈魂的核心——道德和人性的回歸。作者把戰(zhàn)亂中平民身上的珍貴美德看作是挽救晚清的良藥。如卷三記載了安徽柳翁苦心照管故人的兒子,想盡辦法令其改邪歸正。文末寫道:“稗官小說家,固不必拘泥于事之真?zhèn)危∑渥阋燥L(fēng)世而已矣。”[5]71充分表達(dá)了俞樾希望利用小說來達(dá)到潛移默化、感化人心的愿望。
四、較為進(jìn)步的婦女價值觀
受西方進(jìn)步價值觀的影響,俞樾的視野沖破了固有的局限,顯得更加廣闊。但由于中國幾千年正統(tǒng)文學(xué)的熏陶,他對婦女價值的認(rèn)識難免帶有傳統(tǒng)的色彩。一方面,俞樾在婦女觀上仍然遵循正統(tǒng)觀念,強調(diào)婦女“敦禮”,為丈夫守貞節(jié),從一而終。如卷十五記載了翠姑因父母想要悔婚而自殺的故事;另外,小說還記載了大量烈女節(jié)婦的故事,具有濃厚的封建意識;另一方面,俞樾又是開明的。他并不是一味地講究“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將貞節(jié)看得重于一切,而是能結(jié)合“情”來說“理”,客觀地寫出封建禮教和封建婚姻制度對婦女精神的桎梏。如卷一“阿勝”篇,女主人公不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私自追尋心儀之人,這在當(dāng)時無疑是違背了封建禮教的行為;俞樾不但沒有責(zé)備她,反而是欣賞其魄力,贊之為“奇女子”,表明作者面對情與禮的沖突,理智上要維護(hù)禮,情感上卻難以拒絕人性的要求。又如邢阿金結(jié)了四次婚,丈夫死后,她也殉節(jié)而死。俞樾在文末評到:“此女四易所天,不為貞,卒殉其夫,不得不謂之烈。使其初適即得良奧,必為善婦。乃所如不合,遂歷四姓,卒成大節(jié),是謂質(zhì)美而未學(xué)。君子哀其遇可也,取其晚蓋可也。”[5]3不怪其不貞,反惜其不遇,還為她辯護(hù),在名節(jié)與情感中更傾向于“情”。
從整體上看,俞樾對封建禮教制度沒有作出實質(zhì)性的否定,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他在小說中對真情的肯定,的確有著很大的開放性和進(jìn)步性。
俞樾認(rèn)為,文學(xué)作品中必須充滿真情,這是其進(jìn)步文學(xué)觀的具體反映。文學(xué)之真情是從《詩經(jīng)》以來我國古代文學(xué)的一種優(yōu)良傳統(tǒng)。但是縱觀整個中國文學(xué)史,這種傳統(tǒng)雖然整體上是不斷傳承的,而單就某一個時期來說,卻又往往被人們所拋棄,晚清時期即是如此。清朝統(tǒng)治者為了鞏固中央集權(quán),禁錮人民群眾的思想,鼓吹“存天理,滅人欲”,從理論上否認(rèn)“人”在物質(zhì)生活中的需求和精神生活中的渴望。隨著西方民主思想的傳入,激發(fā)了深藏在人們內(nèi)心深處的情感意識。嘉道之際,與“經(jīng)世致用”相適應(yīng),文學(xué)領(lǐng)域要求因時興感、主張直抒胸臆的呼聲越來越高。作為經(jīng)學(xué)大師,俞樾在“注經(jīng)”的同時,實質(zhì)是憑借“經(jīng)文”而闡發(fā)自己的見解,即性情。與當(dāng)時的憂時感世相聯(lián)系,其真情是包含著豐富的社會內(nèi)容的。俞樾雖處于腐朽的末世,卻并不放棄對于美好人生的追求。俞樾的性情之說是有歷史淵源的,至少可以追溯到明代李贄的“童心說”與公安三袁的“性靈說”。“童心”即真心,真實的思想情感。在李贄看來,文學(xué)作品只有真假之別,而不以時代之先后論其優(yōu)劣。“性靈”即出自胸臆的自然感情,強調(diào)個性的自然流露。這些見解與封建正統(tǒng)思想相對立,具有叛逆性。明末清初,那些具有民主主義傾向的思想家為擺脫封建主義的束縛,爭取自由,曾主張文學(xué)創(chuàng)作應(yīng)表現(xiàn)人的真實情感。俞樾繼承了前人的表情說,在作品中用真情作為評論事情的標(biāo)準(zhǔn),相對前人來說具有很大的進(jìn)步性。
五、《右臺仙館筆記》的地位
近代意識作為中國文學(xué)轉(zhuǎn)型期的產(chǎn)物,是清末小說家從事創(chuàng)作的動力。要研究清末小說的積極意義和小說家們進(jìn)步的思想,就應(yīng)該探究他們內(nèi)心深處的近代意識。近代意識中極力追求個性解放、民主自由的思想,表明傳統(tǒng)的封建意識正在被動搖;但近代意識帶有明顯的過渡特征,這就決定了當(dāng)時新觀念的表現(xiàn)力尚不夠充沛,呈現(xiàn)出朦朧的性質(zhì)。
《右臺仙館筆記》是俞樾在文言筆記小說領(lǐng)域的封山之作,包含了他先進(jìn)的的學(xué)術(shù)思想和近代意識,如危機(jī)意識和重視小說實用功能的意識等,影響深遠(yuǎn)。根據(jù)陳翔華《中國古代小說東傳韓國及其影響(上)》一文記載,清刻本《右臺仙館筆記》藏于韓國的奎章閣和成均館。[9]繆荃孫在《俞先生行狀》中云:“先生《右臺仙館筆記》以晉人之清談,寫宋人之名理,勸善懲惡,使人觀感于不自知。前之者《閱微草堂五種》,后之者《寄龕四志》,皆有功世道之文,非私逞才華者所可比也。”①俞樾小說雖有濃厚的學(xué)術(shù)化傾向和因果報應(yīng)的勸懲性,但并不是直接說教,而是充分發(fā)揮小說的社會實用性功能,善于通過故事本身讓讀者領(lǐng)悟其中的道理,以達(dá)到勸懲的本意。周作人對《右臺仙館筆記》評價最高,認(rèn)為它“雖亦有志于勸戒,只是態(tài)度樸實,但直錄所聞,盡多離奇荒陋,卻并非成見,或故作寓言,自是高人一等,非碌碌余子所可企及也”。②俞樾比紀(jì)昀更高明一些。《閱微草堂筆記》注重議論,而俞樾只對自己感興趣的方面發(fā)表議論,在很多篇章里甚至不發(fā)表議論,而是通過小說的故事來傳達(dá)信息。總之,俞樾的《右臺仙館筆記》雖時有議論,但故事情節(jié)性強,所以深受廣大讀者的歡迎,流傳很廣,“在晚清志怪小說中占有重要一席”。[10]
應(yīng)該看到,由于時代和認(rèn)識的局限性,《右臺仙館筆記》還存在著很多陳舊落后的思想觀點,如對一些鬼神報應(yīng)之事的相信和宣揚。小說中很多篇章寫到鬼神,但對鬼神形象的描寫卻相對單薄。小說用大量篇幅來闡發(fā)鬼神觀點,目的是神道設(shè)教,欲借鬼神的故事來傳名教。誠如作者自己所言:“風(fēng)俗澆漓,人心涼薄,則鬼神之事,固有足以輔政教之所不及者矣。”[5]306當(dāng)然,俞樾的小說也不完全是鬼物假托。俞樾相信鬼神的存在,反對無鬼論,“講學(xué)家必執(zhí)無鬼之說,魄降魂升歸之大虛無物,由是而背死忘生者眾矣”。[5]179認(rèn)為鬼有賢愚的分別,其精氣不能長久存在。善良的人其氣輕而上揚,惡毒的人其氣濁而下沉;因此,若死而有怨氣的人,心有所系,故不能上升。可以說,俞樾的鬼神思想在那個時代是具有教化社會風(fēng)氣的積極作用的。誠如寧稼雨先生所言:“雖然作者的思想沒有跳出舊禮教的圈子,但他已感到了圈子的狹小和對人的桎梏作用,這已足彌珍重。”[11]
雖然俞樾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思想的局限性,但從他作品中所散發(fā)出的進(jìn)步的近代意識,我們?nèi)耘f可以看到覺醒中的晚清知識分子為推動社會進(jìn)步而不斷前行的軌跡。
注釋:
①詳見繆荃孫《俞先生行狀》(《藝風(fēng)堂文續(xù)集》八卷,外集一卷),清宣統(tǒng)二年刻,民國二年印本。
②此觀點參考周作人著、鐘叔河編《知堂書話》中“右臺仙館筆記”,岳麓書社1986年版,第629頁。
[1]趙爾巽.清史稿[M].北京:中華書局,1977:13298.
[2]張之洞.張之洞全集:第289卷“書札八”[M].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0346.
[3]陳節(jié).俞樾評傳[J].明清小說研究,1999(4):17-21.
[4]占驍勇.清代志怪傳奇小說集研究[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xué)出版社,2003:228.
[5]俞樾.右臺仙館筆記[M].梁脩,點校.濟(jì)南:齊魯書社,1986.
[6]永瑢,紀(jì)昀.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家類序[M].北京:中華書局,1981:1182.
[7]魯迅.中國小說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54.
[8]張舜徽.清人筆記條辨序目[J].文史哲,1979(4):45-48.
[9]陳翔華.中國古代小說東傳韓國及其影響(上)[J].文獻(xiàn),1998(3):132-154.
[10]張立旦.俞樾與通俗文藝[J].文史雜志,1989(2):8-10.
[11]寧稼雨.中國志人小說史[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