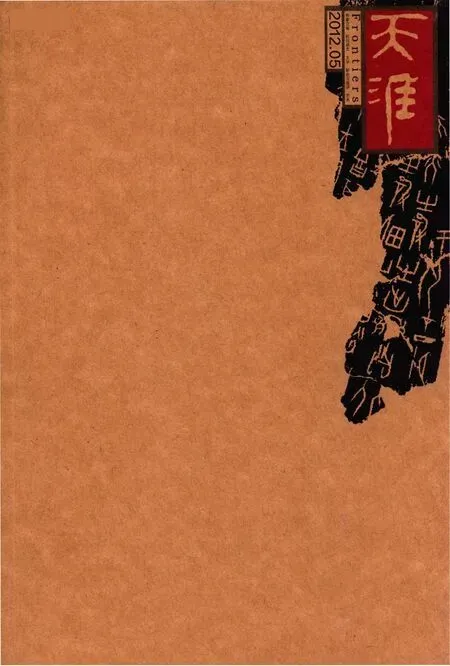新聞人的視野、知識與價值觀
王維佳
新聞人的視野、知識與價值觀
王維佳
作為采訪、編輯、傳達信息的職業(yè)者,新聞人應(yīng)該怎樣看待這個世界?或者說,新聞人眼中的世界是個什么樣的世界?一般來講,對這個問題,有以下幾種答案:
首先,當(dāng)前一種很主流的觀點強調(diào)新聞人的人道主義精神和自由、獨立的專業(yè)操守。在這個意義上,新聞人面向的是人道和自由的世界。實際上,我們看到當(dāng)代中國很多職業(yè)新聞人有著非常強烈的政治訴求,甚至是十分明確的政治立場,少見的反而是審慎的事實調(diào)查、公允的意見權(quán)衡和嚴謹?shù)馁Y料分析。其次,與第一種觀點不同,在新聞職業(yè)群體崛起之后(在我們這個社會,是從1980年代新聞改革開始),也有很多人認為新聞人的世界應(yīng)該是一個有普遍規(guī)律的世界。這種觀念背后隱藏著的是新聞與政治、事實與價值之間的相互分離。第三,在各種有關(guān)記者的傳奇故事中,我們還經(jīng)常能感受到新聞人面對的是一個充滿謊言和陰謀的世界。很多優(yōu)秀的記者既不輕信現(xiàn)象,也不相信規(guī)律。
另外一個問題是,一個優(yōu)秀新聞人的特質(zhì)是什么?
一種觀點認為,新聞人最應(yīng)該做的是客觀報道,以此滿足受眾的信息需求。我們新聞專業(yè)的同學(xué)花費大量寶貴的時間,學(xué)的不過是怎樣通過各種采寫編評的技術(shù)手段,將信息有效地傳達給受眾。第二種觀點認為,新聞從業(yè)者有替公眾來監(jiān)督權(quán)力的功能和職責(zé),諸如守望社會、輿論監(jiān)督、第四權(quán)力、社會良心等都是這種觀念的表達。第三種觀點認為,新聞人是魔鬼、是撒旦,是懷疑一切價值和事實的討厭鬼。他們到處去扒糞,對新聞線索和真相有一種永遠不放棄的貪婪和熱情。最后,甚至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新聞人是思想家和文學(xué)家,新聞業(yè)是一個有豐富想象力和能夠深入探討新聞現(xiàn)象和社會問題的職業(yè)。
以上這些問題和討論涉及新聞業(yè)的基本特征、新聞人的價值觀念和社會角色等重要的問題,對它們的不同回答,決定了我們對這個行業(yè)的不同認識,也決定著我們對待這個行業(yè)的態(tài)度。是將新聞業(yè)當(dāng)作一種現(xiàn)代社會分工中的白領(lǐng)工作,一個飯碗,一個謀生的職業(yè),還是將新聞業(yè)當(dāng)作一項值得畢生去追求的志業(yè)(vocation),當(dāng)然我在這里用的是馬克思·韋伯的詞匯。我把它作為我這次演講的題目——以新聞為業(yè),或者更準確地說,以新聞為志業(yè)。
規(guī)律的新聞學(xué),還是視野的新聞學(xué)?
我在我的新聞教學(xué)中提出了一些理念,其中一個就是“給陰謀一個機會”。我并不是說規(guī)律完全不起作用,或者說規(guī)律完全是遮蓋事實,我只是說,不輕信規(guī)律和表面事實對于新聞從業(yè)者來說是重要的。
我們知道,任何一個科學(xué)規(guī)律的形成都受限于一定的視野,視野的有限性決定著規(guī)律的不完備性。在這個意義上,新聞人對這個世界的概括或者你抽取的事實永遠跟你這個人的視野的寬窄和朝向是有關(guān)聯(lián)的,這當(dāng)然挑戰(zhàn)了各種各樣關(guān)于新聞事實、新聞規(guī)律的論述。那么這種說法有沒有道理呢?
法國有位哲學(xué)家叫梅洛·龐蒂,他在法蘭西學(xué)院發(fā)表就職演講時說了一句很嚇人的話,他說:“哲學(xué)家就是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既然我們什么都不知道,那你們?yōu)槭裁催€請我來做教授呢?就是為了告訴你們其實你們也什么都不知道。”當(dāng)然他把我們說的問題推向了極端,但他說的實際就是視野的有限性問題。他有一本書就叫作《可見的與不可見的》。所以科學(xué)在有些哲學(xué)家看來是個神話,或者追求科學(xué)、追求本質(zhì)的真實是個神話。我們未必像他那樣極端,但他提出的這些觀念和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在人類思想的發(fā)展歷程中,社會科學(xué)的思想與自然科學(xué)的思想向來是緊密對應(yīng)的。早期十六、十七世紀的牛頓力學(xué)提供了一個經(jīng)典的、完美的、普遍性的理論解釋,十八、十九世紀的社會科學(xué)也在尋求這種普遍規(guī)律的解釋。十九世紀社會科學(xué)最大的特點(也是今天我們傳播學(xué)的特點),就是尋求解釋社會現(xiàn)象的普遍規(guī)律。可是到了二十世紀之后,首先在自然科學(xué)領(lǐng)域內(nèi)對普遍規(guī)律的追求被逐漸破解,最明顯的就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他幾乎把牛頓力學(xué)那種平衡、普遍、靜態(tài)的經(jīng)典闡釋給顛覆掉了。還有就是今天經(jīng)常提到的耗散結(jié)構(gòu)理論的例子。耗散結(jié)構(gòu)理論,是一個叫普利高津的人提出的,說的是我們很難找到一個普遍、平衡的規(guī)律來解釋和預(yù)測一個復(fù)雜系統(tǒng)。在這個脈絡(luò)下,對規(guī)律的認識、對共識的認識、對價值觀念普遍適用的認識都開始被反思。最近,提出“北京共識”的那個家伙,喬舒亞·雷默,寫了一本很有趣的書,叫《不可思議的年代》,講的也是這個道理。
如果去看二十世紀非常有影響的學(xué)者的研究,你會發(fā)現(xiàn)有些人不僅研究歷史和社會,還喜歡討論認識論的問題。出版了《否思社會科學(xué)》的沃勒斯坦是一位歷史學(xué)家,但他在書中不斷提及普利高津?qū)φJ識論的重新理解。他提出一個迷思,當(dāng)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自然科學(xué)界出現(xiàn)了相對論、量子力學(xué)和耗散結(jié)構(gòu)理論之后,為什么社會科學(xué)界反而會出現(xiàn)一個追求普遍規(guī)律的高潮?對于在座的各位來說,最熟悉的例子就是美國的實證社會科學(xué)和傳播學(xué)的理論和原則。
《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現(xiàn)代化》一書也探討了這類問題:在二十世紀后半期,社會科學(xué)認識論的發(fā)展為什么與自然科學(xué)不對應(yīng)?為什么在自然科學(xué)家反思普遍規(guī)律時,社會科學(xué)家卻在把普遍規(guī)律這個東西推向極端,把發(fā)展、效果、規(guī)律、原則、定理這些東西推上極端?作者把這個問題與冷戰(zhàn)的政治結(jié)合在一起討論,他認為,在蘇聯(lián)和美國之間爭奪第三世界主導(dǎo)權(quán)這個過程中,美國有意識地向第三世界推廣了他的發(fā)展策略、原理和計劃,給第三世界輸入了這個普遍規(guī)律。也就是說,你按照我這個模式來走,今天的北京就能變成明天的紐約,今天的上海就能變成明天的巴黎。這樣一種愿景與進步論、發(fā)展主義的觀念結(jié)合起來,產(chǎn)生了對普遍原則的追求——人類的發(fā)展、經(jīng)濟的發(fā)展是有普遍規(guī)律的,是不因人的意志而轉(zhuǎn)移的。這種冷戰(zhàn)政治上的考量和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社會科學(xué)研究和人文領(lǐng)域研究對規(guī)律的理解。傳播學(xué)的發(fā)展與這個過程是非常緊密地結(jié)合的。當(dāng)我們回顧1980年代新聞改革的時候,我們發(fā)現(xiàn)很多新聞學(xué)界的前輩都在講新聞是有自身發(fā)展規(guī)律、原則、定理、體系的,它不應(yīng)該受到權(quán)力的干擾。這種觀念不單是對革命新聞史的反叛,也是與支配性的發(fā)展主義進行的對接。在今天,普世性的價值、普遍性的規(guī)律、普遍與特殊的知識和思想構(gòu)造對新聞傳播的學(xué)子們影響有多大呢?我想在座各位一定都有感受。
然而,當(dāng)我們把優(yōu)秀新聞人的實踐跟這套理論對應(yīng)起來的時候,我們則會發(fā)現(xiàn),一些偉大的新聞記者做出的報道之所以偉大,恰恰是因為它是違反常識和共識的,是挑戰(zhàn)規(guī)律的。
最近出版了一本探討新聞實踐案例書,叫做《別對我撒謊》。作者是一位澳大利亞的老記者,John Pilger。這本書中有很多的經(jīng)典案例,這些案例的共同點就是它們都挑戰(zhàn)共識。比如Paul Foot對洛克比空難的報道,通過記者的調(diào)查,在很多細節(jié)方面挑戰(zhàn)了當(dāng)時被定性為恐怖分子的爆炸活動。如美國大使館的官員在飛機起飛之前集體退機票,伊朗的恐怖分子被排除在名單之外,法庭的冗長審判并沒有提供確鑿證據(jù)等等。這位記者聯(lián)系自己的地緣政治和國際關(guān)系知識,不斷提出質(zhì)疑,并堅持進行調(diào)查,得出了一系列令人信服的結(jié)論。從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對一個成功記者來說,有時“陰謀論”的思維是如此重要,很多線索無法在表面事實和規(guī)律中呈現(xiàn),必須依靠記者的知識視野和懷疑精神去挖掘。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調(diào)查葉利欽時代俄羅斯經(jīng)濟改革的女記者弗里蘭詳細研究了整個俄羅斯經(jīng)濟轉(zhuǎn)軌的內(nèi)幕故事,包括挖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不具備條件的情況下強行推進市場改革,盧布怎樣大規(guī)模貶值,對沖基金怎樣借著私有化的契機投資能源關(guān)鍵領(lǐng)域,很多投資的大鱷們的資產(chǎn)竟然是美元持有的等等。她最后寫就了一部重量級調(diào)查性著作《世紀大拍賣》。我們可以想見,在這位記者進行調(diào)查和寫作的1990年代初期,自由市場的規(guī)律實際上是一個被主流知識界當(dāng)作圣經(jīng)一樣信奉的東西,如果記者沒有一個挑戰(zhàn)共識的思維和必要的知識視野的話,就不會如此努力去挖掘內(nèi)幕。
我很喜歡一部紀錄片,名字叫作《達爾文的噩夢》,講的是坦桑尼亞的一個湖本來是自然生態(tài)非常好的,有各種各樣的魚,其中一種食肉魚的肉非常鮮美,歐洲人非常喜歡吃。為了賺錢,當(dāng)?shù)氐钠髽I(yè)家就組織工廠和漁夫?qū)iT放食肉魚的魚苗,把小魚小蝦都吃掉了,當(dāng)?shù)氐纳鷳B(tài)平衡完全被破壞掉了。關(guān)鍵不只是自然被破壞的問題,生產(chǎn)中還出現(xiàn)了惡劣的剝削狀況,漁夫在低水平的操作環(huán)境下大量死亡,工廠操作的過程中釋放出來的有毒氣體使生產(chǎn)魚肉的女工們大量失明,漁夫的妻子們變成妓女,孩子們淪落為流浪兒童。從歐洲飛來的飛機把武器運到非洲,卻載走了鮮美的魚肉。試想這樣一位紀錄片的作者,如果沒有豐富的世界體系知識,沒有社會分層的知識,沒有對資本主義與生態(tài)平衡之間關(guān)系的洞察,如果他只輕信“世界是平的”、“地球村”和“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這些廣為宣傳的共識,如何能選取這么多有代表性的事實材料,從而制作出令人深深感慨的優(yōu)秀紀實作品。
要把這些現(xiàn)代社會生活和全球化中的各種事件進行問題化,將它們放在地緣政治、文化政治對抗之中來看待,在文化霸權(quán)的現(xiàn)狀之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些深入的調(diào)查、研究、報道的背后,都是一套能夠超越普遍規(guī)律,能夠挑戰(zhàn)主流共識的知識視野和理論體系在起作用。這些,都涉及到我們的視野和知識體系的問題。所以,我們提出一個理念叫做從規(guī)律的新聞學(xué)變成視野的新聞學(xué)。完全用規(guī)律原理去理解新聞工作,將新聞教育和新聞實踐局限在傳遞信息、寫好稿件、拍好、編好片子這樣的水平上,你永遠不能成為一個優(yōu)秀的新聞人。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提出視野的新聞學(xué),重新調(diào)整學(xué)新聞的學(xué)生的知識體系,重新讓他們看一個完整的世界景觀是什么樣子,他們在其中處于什么位置,如何將他們的文化意識與他們面臨的世界相對應(yīng)。我覺得,這些問題是才是一個成功的新聞教育中最重要的問題。它提示我們,新聞人努力的方向何在,新聞業(yè)的魅力何在。
下面我們再通過一些經(jīng)濟問題上的例子來反思規(guī)律的可靠性問題。我們在講財經(jīng)新聞的時候不能完全講采編實務(wù),因為我發(fā)現(xiàn)學(xué)生在基本經(jīng)濟問題的理解上還存在很多嚴重問題。
拉美1970年代出現(xiàn)過一群Chicago Boys,說的是受芝加哥大學(xué)經(jīng)濟學(xué)院新古典經(jīng)濟理論和貨幣主義思潮影響的拉美知識分子,回到本國運用這些理論推行經(jīng)濟社會改革政策。最典型的是智利的知識分子,按照彌爾頓·弗里德曼的理論,推行看上去很美的新自由主義經(jīng)濟政策。在這些政策遇到民主力量的抵抗時,發(fā)生了武力鎮(zhèn)壓和奪權(quán),民選政府被推翻,上臺的是皮諾切特,他在搞軍事獨裁的同時推行經(jīng)濟普遍主義的規(guī)律,結(jié)果造成了本國嚴重的經(jīng)濟災(zāi)難和人道災(zāi)難。前面提到的John Pilger拍了一個紀錄片,叫The Waron Democracy,里面講了很多類似的事例。1970年代,芝加哥大學(xué)的弗里德曼在領(lǐng)諾貝爾經(jīng)濟學(xué)獎的時候就有拉美的知識青年當(dāng)場抗議,這是諾貝爾頒獎的時候基本上沒有過的。中國的很多知識青年現(xiàn)在大概就知道為諾貝爾和平獎歡呼。現(xiàn)在中國高校很多經(jīng)濟專業(yè)的教學(xué)承襲的就是這套傳統(tǒng)。芝加哥經(jīng)濟學(xué)派的這套規(guī)律上升到國家政策的高度時會產(chǎn)生很多的問題。像張五常用賣桔子的實驗暗喻國家經(jīng)濟運行政策,盛洪講的則是賣大白菜的例子,經(jīng)濟學(xué)家會講故事啊。北大還有一個非常有名的經(jīng)濟學(xué)家,他根據(jù)非常經(jīng)典完美的經(jīng)濟理論推導(dǎo)出來了一個結(jié)論——“政府干預(yù)越多,社會的貧富差距越大”。這個東西恰巧被做過相關(guān)研究的政治學(xué)教授王紹光看到了,他利用嚴謹?shù)慕y(tǒng)計說明,福利支出和行政干預(yù)越大的國家反而基尼系數(shù)是越小的。王紹光就說,你這個理論究竟的怎樣出來的?是從規(guī)律原則的角度出發(fā)的,還是建立在對現(xiàn)實的調(diào)查分析基礎(chǔ)之上的?我們在座的想一想,在我們的財經(jīng)新聞報道中,這種用理論模型套現(xiàn)實的例子是不是不勝枚舉。我聽我的一個學(xué)生說,他進某家財經(jīng)媒體實習(xí),編輯告訴他第一個月什么都不用干,就讀哈耶克的著作,這太恐怖了,先洗腦!
一些理解經(jīng)濟現(xiàn)象的原理,很多都可以歸結(jié)為一種模式——供求曲線。在日常生活的微觀經(jīng)濟中,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需求量越大,價格會越高;供給量越高,價格會降低。如果是一個經(jīng)典的經(jīng)濟理論模型,沒有外力干預(yù),這就是一個完美的市場,它會自動趨向平衡。到一定程度就會自我反饋,超過平衡點就回來了,這是市場自發(fā)調(diào)節(jié)的體系。
但我們生活中的其他現(xiàn)象卻不能完全用這種模型去解釋了,如股票市場、房地產(chǎn)市場。2008年發(fā)生金融危機后,很多人對世界的認識都顛覆了。現(xiàn)在去書店看看的話,你會發(fā)現(xiàn)很多貨幣戰(zhàn)爭、金融戰(zhàn)爭,全都是陰謀論、權(quán)力和操縱,都是講非理性的經(jīng)濟狀況,越來越少有人用經(jīng)典的理論解釋經(jīng)濟生活了。為什么會這樣?我們用完美的經(jīng)濟模型解釋這個社會的時候解釋得這么漂亮,讓人心曠神怡,又賣桔子又賣大白菜的,為什么往往與現(xiàn)實不對應(yīng)?比如說股票市場和房地產(chǎn)市場,越貴越買,越跌越拋,如果沒有外力來調(diào)節(jié)的話就會崩潰。這些現(xiàn)象你怎樣用你的經(jīng)典經(jīng)濟理論和普遍規(guī)律來解釋?
主流經(jīng)濟學(xué)強調(diào)自我穩(wěn)定不需要干預(yù),供求曲線是自動均衡的過程。但實際上我們看到追漲殺跌。比如一家銀行給出的利率是20%,其他都是5%,那會出現(xiàn)什么狀況呢?這是國際經(jīng)濟操縱的常見狀況。如果一家銀行把利率調(diào)高到20%,所有資金都流向這家銀行了。只要你符合一個條件,就是說人們?nèi)〕鰜淼腻X小于存進去的錢,這個游戲就可以一直做下去,就可以用很小的杠桿來挑動這個資本游戲。所以在一個國之內(nèi)的銀行利率都必須是統(tǒng)一的。但在國際上就不是這樣。如果這家銀行是美聯(lián)儲呢?它調(diào)利率就會對整個國際經(jīng)濟產(chǎn)生巨大影響。資本的流動、熱錢的流動等等,這個過程中有大量的非理性的、人為的、操縱的因素存在。如果突然有一天有謠傳說銀行的資金鏈斷了,所有的錢都會撤出來,泡沫就會破滅。如果在一國中出現(xiàn)這樣的狀況,就是剪羊毛,把股價炒起來,然后突然之間資金全收回來。1997年金融風(fēng)暴,東南亞就面對這種極端慘烈的狀況。如果一國對金融主權(quán)失去了控制,比如說今天中國如果加息之后不能控制外匯涌入的話,通貨膨脹會更加嚴重。金融主權(quán)對國家來講是命根子。
我們今天講開放金融市場,接受WTO的一些條文,歷史不容得看客,如果你不去研究它,不去想它對你的生活會產(chǎn)生什么影響的話,你很可能成為歷史的受害者,很可能你的父母失業(yè),你畢業(yè)找不到工作。這一系列的問題你怎么去看待它?是用一個普遍規(guī)律完美模型去理解,還是用歷史性的知識視野去觀察?是相信表面的結(jié)論和事實,還是帶著懷疑精神去質(zhì)疑?葉利欽推行休克改革的時候,一幫知識分子跟著起哄,聯(lián)名寫信支持他用坦克威逼杜馬,結(jié)果怎么樣,改革以后最先完蛋的就是這群文人。
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我們再來看社會科學(xué)理論當(dāng)中提到的理性和非理性的界限,恐怕就不是那么明確了。比如說追漲殺跌是理性還是非理性呢?我們同學(xué)有時會說“理性點”,或者說“你這個人怎么愛國呢?愛國多么不理性!民族主義多么不理性!”我覺得在某種條件下,你所指的“不理性”很可能就比你的理性更理性。魯迅先生曾說過一句話——偽士當(dāng)去,迷信可存。老百姓自發(fā)的對迷信的看法是可愛的,但這些以一種非常復(fù)雜的知識體系和非常完美的規(guī)律模型包裝出來的現(xiàn)代科學(xué)理論有時反而會成為社會的禍害,成為霸權(quán)的工具。
新聞人的價值判斷:歷史的,還是抽象的?
我們還是從一個記者的調(diào)查經(jīng)歷講起。有一位英國女記者,叫桑德斯,她通過美國CIA的解密檔案,大量挖掘了五六十年代CIA利用文化宣傳手段對付社會主義國家的史料,其中的很多內(nèi)容非常驚人。比如我們很熟悉的暢銷書《動物莊園》,講的是一群共產(chǎn)主義的豬,被腐敗資本家壓迫,他們實在無法忍受了去造反,資本家被打倒了,但豬就成為新的集權(quán)者。作者的意思是共產(chǎn)主義和資本主義都是集權(quán)的,都是不可愛的。但CIA投資將小說改編成電影時,將丑惡資本家的形象拿掉了,呈現(xiàn)的則是共產(chǎn)主義的豬如何腐敗、集權(quán)的故事。再比如現(xiàn)代藝術(shù)的迅速崛起也與CIA的投入關(guān)系密切,CIA的官員甚至跟記者說現(xiàn)代藝術(shù)就是他們發(fā)明的,紐約的現(xiàn)代藝術(shù)博物館就完全是CIA資助建立起來的。其實,1970年代經(jīng)濟危機中出現(xiàn)了一大批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畫家,包括拉美裔的墨西哥人,拍了很多底層的悲慘狀況,這讓CIA和很多美國社會文化精英非常緊張。于是他們組織了一大群現(xiàn)代藝術(shù)家去搞創(chuàng)作、搞展覽,然后把這些現(xiàn)代藝術(shù)大規(guī)模推向第三世界、蘇聯(lián)和中國。如果有同學(xué)知道“改革開放”初期,北京美術(shù)館周圍搞的星星美展,就知道這波現(xiàn)代藝術(shù)力量有多強大。不管其內(nèi)部政治內(nèi)涵、哲學(xué)內(nèi)涵是什么,在現(xiàn)實意義上,它確實對原來的蘇聯(lián)、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知識分子造成了巨大沖擊。總之,桑德斯通過對檔案的不斷挖掘和細枝末節(jié)的整合,寫了一本非常著名和震撼的調(diào)查性的書——《文化冷戰(zhàn)與中央情報局》,從而成為一位蜚聲國際的記者和作家。
這個記者的故事告訴我們什么?一套普遍主義的價值觀念表述,例如自由、民主、人道、人權(quán)等等,有時可能成為達成某種支配性政治目標和文化霸權(quán)的工具。因而,對價值觀的判斷,一定要回到歷史中來,回到調(diào)查中來,用事實說話。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的都市新聞記者群體中,不僅對價值觀念的陳述往往脫離歷史,而且也缺少對這些觀念內(nèi)部復(fù)雜性的辨析。因此,簡單、粗糙的政治判斷成為都市新聞業(yè)被人詬病的軟肋。
前一段時間媒體都在報道伊朗的石刑事件。一個婦女參與了對丈夫的謀殺,被判通奸罪,要被施以石刑,就是放在一個坑里被石頭打死。用現(xiàn)代人的觀念來看,這是非常不人道的方式,所以很多人在抗議。但如果你經(jīng)常關(guān)注這類事情的媒體報道,你會發(fā)現(xiàn)它們總是發(fā)生在某些國家,如伊朗、阿富汗等中東國家,這些國家都有著重要的地緣政治位置。雖然尼日利亞、蘇丹等非洲國家的傳統(tǒng)封建觀念要比中東國家嚴重得多,但我們發(fā)現(xiàn)這些國家的故事往往并不出現(xiàn)在主流媒體上,這是值得大家考慮的,它折射了普遍主義價值觀背后,媒體有著預(yù)設(shè)的立場和報道框架和議程。
前幾年有一個對布什的采訪,是一位愛爾蘭的記者叫科爾曼,她顛覆了人們對采訪政治人物的傳統(tǒng)認知,以非常嚴厲的語氣,就伊拉克戰(zhàn)爭問題當(dāng)面挑戰(zhàn)布什,甚至一直在與布什搶話,把布什搞得非常生氣。事后白宮的新聞發(fā)言人嚴厲地指責(zé)了這位愛爾蘭記者。這是一次法拉奇式的采訪,把采訪者放在中心的位置,把被采訪者放在被挑戰(zhàn)的位置。布什在講發(fā)動戰(zhàn)爭的理由時,講的就是自由、人權(quán),而反過來質(zhì)疑伊戰(zhàn)的記者調(diào)用的價值資源也是自由、人權(quán)。所以,我們看到同一種意識形態(tài),在不同的語境下,產(chǎn)生了完全不同的立場。
另一個相似的例子:正要退休的拉里金剛剛采訪了到紐約參加聯(lián)合國會議的內(nèi)賈德。如果把內(nèi)賈德看作是一個魔鬼的話,從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內(nèi)賈德長期的媒體形象來看,他確實是一個魔鬼。可是在采訪的過程中,拉里金和內(nèi)賈德所使用的語言竟然是相似的——你提民主我就提法治,你提法治我就提民主,你提自由我也提自由,你提國家利益我也提國家利益——他們話語背后的價值觀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偏差,所以很多接受了內(nèi)賈德媒體刻板印象的觀眾大吃一驚。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抽象的價值觀念在面對具體問題時,往往是失效的,它總是會成為單一立場的佐證。
2009年的奧斯卡,最大的贏家是《拆彈部隊》。很多人都說它是政治正確,它所講述的是一些人在伊拉克艱苦、危險的環(huán)境下所從事的戰(zhàn)斗。而《阿凡達》講的是什么事情呢?它帶有一些美國中產(chǎn)階級人道色彩的反現(xiàn)代和反殖民意味,而且被處理成非常理想化的故事,就是現(xiàn)代化的殖民可以輕易抵抗,人們騎著大鳥就把重型武器趕走了。
我們發(fā)現(xiàn)在真實的歷史中也有這樣的事情,如中國的民間抵抗——義和團。前幾年的時候中國青年報發(fā)了一篇文章,叫做《現(xiàn)代化與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問題》,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它重新評價了我們原來學(xué)習(xí)過的義和團事件。文章作者,一位年長的歷史學(xué)家,將義和團說成是落后的、封建的,說它怎么能去抵抗現(xiàn)代的、先進的文明?他說我們原來的教科書都是給學(xué)生們喝狼奶。實際上,義和團的事情和《阿凡達》講的故事是有點像的,可是美國的中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把它講成那樣的故事,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報紙的評論中將我們的“阿凡達”講成這樣一個封建、落后反對現(xiàn)代的故事。
我們回頭來看中國的民間抵抗,實際上就是在缺少一個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狀況下,底層的農(nóng)民自發(fā)出來抗?fàn)幜耍ㄈ锏牡挚梗踔敛粌H僅是反對外國人,連在城市里的人都一起反對。我們現(xiàn)在的民族建國理念,幾十年來從來都不是以城市為中心的,只是最近幾年才變成Better city,better life。農(nóng)村中心與城市中心,這都是跟殖民與反殖民也是有一定關(guān)系的。
所以,你看中國的知識分子評論的時候,他講的是落后與先進的故事;而美國知識分子講的時候,他講的是溫情脈脈的自然觀念與冷冰冰的現(xiàn)代化的沖突的故事。這個問題就很值得我們討論了。首先,我們從美國知識分子的角度來看,他們怎么理解現(xiàn)代化?
比如說同樣是現(xiàn)代理念,當(dāng)你強調(diào)文化多樣性的時候,當(dāng)你強調(diào)文化自主與自覺的時候,你怎么看待現(xiàn)代技術(shù)與科技?我在接觸西方的知識分子的過程中,當(dāng)然我說的是左翼知識分子,我發(fā)現(xiàn)他們非常喜歡甘地。甘地是反現(xiàn)代化的,印度的國旗中間就是一個紡車的車輪,就是說不要西方大機器,要符合印度人自己選擇的技術(shù)的進步。但是他們很不喜歡毛澤東,因為毛澤東搞現(xiàn)代化、大工業(yè)。所以他們想要的是一種溫情脈脈的、文化多樣性的、甚至前現(xiàn)代的“和諧社會”,就是《阿凡達》一樣的社會。這種觀念是啟蒙時代知識構(gòu)造內(nèi)部的反叛,比如盧梭。但是問題是,對于被殖民的群體來說,我們能不能不搞現(xiàn)代化,騎著大鳥就把這些大機器趕出去。
所以,這些都是關(guān)于價值觀判斷的一些問題,我覺得它們都不是現(xiàn)代主流新聞操作的想當(dāng)然的問題,都是蘊含著很多復(fù)雜理念的問題。我們講這些問題是為了提醒在座的年輕新聞人,價值觀念有著內(nèi)部的復(fù)雜性和矛盾性張力,離開歷史現(xiàn)實,單純喊口號,對新聞業(yè)來講,可能一時會吸引些無知青年,變得很神氣,自以為聰明,什么都看透了,很有“公知”范兒,但無異于飲鴆止渴。
回過頭來看中國新聞業(yè)的問題。今天我們最主流的新聞操作的價值觀念跟今天新聞人職業(yè)群體的崛起有關(guān)系。我們可以想到一些對應(yīng)的現(xiàn)象,如法學(xué)界“法條主義”和“權(quán)利本位”意識的崛起,跟職業(yè)法律人這個群體的迅速形成和法律職業(yè)意識的崛起直接相關(guān)。新聞也同樣,1990年代大規(guī)模媒介改革以來,出現(xiàn)了都市新聞記者職業(yè)群體。他們在建立了一套與西方接軌的形式專業(yè)主義操守的同時,卻又吊詭地與沿海都市的經(jīng)濟、文化精英群體建立了政治意識上的連接。從大的方面來看,這些變化當(dāng)然對中國社會文化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yīng)特別注意一些僵化的意識形態(tài)框架形成了對新聞人好奇心和文化想象力的束縛。首先,作為一種媒介素養(yǎng),我這里特別想建議大家的是,我們應(yīng)該將都市新聞從業(yè)者普遍持有的價值觀念問題化和意識形態(tài)化,這樣我們才能透徹地洞悉他們的新聞報道和新聞評述中的政治意味。
我們先來看一幅招貼畫

我最早是在公交車的椅背上看到這幅圖片,它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政治上的沖擊力,這里面蘊含了豐富的階層之間的文化權(quán)力關(guān)系,它是一種政治無意識表達。它顯示出來的階層之間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是主角和配角的關(guān)系,他們對話的狀態(tài)、外形特征、所處的環(huán)境都觸動了我的思考。讓我反思作為文化精英的都市知識分子在當(dāng)代中國社會的意義生產(chǎn)中扮演什么角色,起到什么作用。這張圖如果放在五十到七十年代,坐在中間的可能是領(lǐng)導(dǎo)干部,也可能工人們本身就是主角,而現(xiàn)在是變成了飽含人文關(guān)懷和人道深情的中產(chǎn)階級文化精英。從一個歷史變遷的角度看,這意味著什么?它對于我們理解都市職業(yè)階層,理解當(dāng)代新聞記者群體的文化意識有沒有一點啟示呢?
我們可以很容易從新聞媒體的報道中察覺出意識形態(tài)問題。前一段時間關(guān)于“我爸是李剛”事件,中央電視臺有相關(guān)的報道。《新聞1+1》評論的標題為《可憐的孩子》,說的不是被撞的孩子可憐,而是撞人的孩子可憐。整個評論是說我們家長的教育是多么的失敗,使得孩子們沒有養(yǎng)成好的習(xí)慣。為什么從這個角度講?這個角度是不是與我們對這一事件的直覺產(chǎn)生了很大的反差呢?這個事情一出現(xiàn),老百姓和網(wǎng)絡(luò)民意立刻出現(xiàn)很大的爭論,并且這種爭議立刻轉(zhuǎn)移到官二代、富二代與底層之間的關(guān)系。央視講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教育失敗,白巖松把自己擺在了一個父母的地位上,他自己也在反思教育怎么會這么失敗,讓孩子沒有養(yǎng)成好的道德品質(zhì);第二個是醉酒駕駛,采訪的主要是李剛本人和他兒子,也有很多人說你為什么沒有采訪受害者的親屬。從問題化的意識說,他們?yōu)槭裁催x擇這個角度?我想大家可以多思考類似的問題。
前兩年的“通鋼事件”,國有企業(yè)改制出現(xiàn)了爭端,工人鬧事殺死了一個總經(jīng)理。后期的報道的核心敘事就是殺人的問題和量刑的問題,幾乎淡化了社會沖突問題。再比如媒體怎么報道最近的法國大罷工?我們的國際新聞大量采用美聯(lián)社、法新社的視頻信息,在議程上不知有意或無意,報道與他們非常接近。談到罷工,我們報道的都是坐地鐵不方便,汽車加油加不了,學(xué)生上不了課,經(jīng)濟停滯了。但很少有人去關(guān)注這些罷工的人訴求是什么東西。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的事情?
我再舉一個虛擬的例子,比如現(xiàn)在你被指派報道白毛女的故事。我們強調(diào)視野新聞學(xué),就是因為帶著不同的知識視野,記者會從不同角度進入這個故事。每一個角度都是真實的,都符合新聞?wù)鎸嵑鸵?guī)律的原則,但這些角度的社會意義是完全不一樣的。比如說你是揭發(fā)地主欺壓農(nóng)民、無惡不作,這是我們傳統(tǒng)文化宣傳中那套“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理念;還可以說保護私有產(chǎn)權(quán),楊白勞欠債還錢,如果拋開我們的文化背景單純來看這個故事的話很可能就是這個角度;還可以講勞資糾紛需要依法裁決,期待政府完善法律;或者,農(nóng)民的抵抗能力太弱,急需心理調(diào)節(jié),你去看看我們富士康的報道就是這樣;還有一種解釋,封建地租、身份等級與依附關(guān)系導(dǎo)致壓迫和反抗;或者當(dāng)成奇聞來報道,少女為躲債藏在山洞里多年,滿頭白發(fā),以吃野草和昆蟲為生,這里主持人可能會請清華醫(yī)學(xué)院的某教授來給觀眾做一番科學(xué)解釋。所以說視野、知識體系和你對問題的認識,這些東西都不是一個簡單的價值觀念的問題,回到歷史當(dāng)中去看,能不能分析到封建地租的問題、等級觀念的問題、整個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fàn)顩r的問題,你如果分析到這些問題,就不簡簡單單是價值判斷的問題。
作為一個新聞人,如何對自己的價值觀念保持自省,對自己面對的事實保持審慎態(tài)度呢?我想這還是一個知識視野的問題。回到歷史中,回到對社會發(fā)展的政治經(jīng)濟考察中,回到對知識分子文化意識的批判分析中,我們才能更清晰地認識我們報道的對象。例如前面反復(fù)提到的“底層問題”,為什么成為當(dāng)代中國社會一個如此突出的問題,這顯然與中國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中的失衡現(xiàn)象和很多結(jié)構(gòu)性痼疾聯(lián)系在一起,而這些問題的出現(xiàn)是歷史性的,只有放在歷史的演變中才能被更深刻地體察。比如你試著把這個問題放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經(jīng)濟變革中來看,從1980年代中期的地產(chǎn)開發(fā)熱、土地兼并熱、價格雙軌制和官倒、通貨膨脹,到1990年代的大規(guī)模城市化、圈地?zé)帷蟾闹瀑Y產(chǎn)流失、行賄受賄,2000年以來的新財富的掠奪、福利保障體系的解體、低價征地,大規(guī)模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一個更大的視野是中國如何融入全球經(jīng)濟體系,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中—美、鄉(xiāng)村—城市、東部—西部、官—民、貧—富等各種問題。如果你處理單個新聞事件時,有這個知識背景,那么你對中國社會結(jié)構(gòu)變動的理解會不會更全面呢?你對公共政策的理解會不會更深入呢?你在進行新聞報道時,比如報道宜黃拆遷事件時,是不是會有更公允的報道視角和更豐富的意義闡釋呢?
歷史性的知識視野和政治經(jīng)濟分析是重要的,而對各種價值觀念內(nèi)部復(fù)雜性的考量也同樣重要,它可以防止我們簡單地對新聞事件做出不負責(zé)任的判斷。如果你深入到政治思想史、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辨析當(dāng)中,就會發(fā)現(xiàn),自由也好,民主也好,平等也罷,都存在各種概念辨析和原理辨析上的矛盾和爭議,絕不能簡單地當(dāng)作口號使用,更不能代替對歷史的考察,我們只有把它們放在一個歷史的語境下去理解,才能對它產(chǎn)生充分的認識,也能對自己的價值觀念做出反省。對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敏感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當(dāng)代都市知識分子看問題的主流方式,幫助我們理解新聞記者面對一個單獨經(jīng)濟現(xiàn)象和社會新聞事件的時候為什么從這個角度切入而不是從另一個角度切入?是什么在影響他對社會和文化的理解?包括區(qū)域研究的問題,涉及到我們中國一些具體的現(xiàn)象,是中國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的歷史進程的問題,有一些看上去很久遠、很宏大的問題,實際上都是我們新聞人在進行新聞操作和理解社會的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學(xué)科體系。我們講新聞學(xué)的教育,為什么這么多同學(xué)學(xué)來學(xué)去覺得索然無味、新聞無學(xué),非常枯燥、毫無意義?
實際上,如果真的做一個新聞記者、一個新聞人,對這個社會展開自己的調(diào)查,傳播自己的觀念,學(xué)校的新聞教育是否給予你所需要的知識體系?或者說你討論的、學(xué)習(xí)的主要重心放在哪兒?這是影響學(xué)科魅力的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比如說,我們在整個中國融入現(xiàn)代的過程中所討論過的問題,對于今天的中國社會來說是不是仍然適用?中國人怎樣產(chǎn)生現(xiàn)代新聞思想?原來我們沒有民族主義,沒有自由主義,沒有對科學(xué)的崇拜,這些如何突然之間在1840年之后逐漸深入到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當(dāng)中,形成了現(xiàn)代中國人對世界的理解?中國知識分子提出過什么樣的建國方略?我們今天提出的五花八門的建國方略,在清末的時候,在民國的時候,都已經(jīng)被提出過,當(dāng)時的知識分子是怎么討論的?對今天的我們有沒有啟發(fā)意義?在解釋經(jīng)濟危機、財經(jīng)現(xiàn)象時,如何把它放在國際間的經(jīng)濟、政治關(guān)系的環(huán)境中?從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之后,到馬歇爾計劃調(diào)整戰(zhàn)略,再到里根政府推行新自由主義計劃,包括后來克林頓如何攪局,包括現(xiàn)在奧巴馬為什么面臨這么大的壓力,把這些放在全球政治經(jīng)濟歷程中來看,我們是否會獲得更豐富的、對一個單純對經(jīng)濟新聞的理解?

我們看這張圖,你也許會有點驚訝,這些著名的作家、思想家、革命家竟然都曾經(jīng)是新聞人,有的還是非常出色的新聞記者。講到這,你可能更能體會我前面講的那種將新聞人比作思想家和文學(xué)家的觀念。沒錯,很多十九、二十世紀的偉大人物都做過記者。如阿倫特、杰克·倫敦,馬克思也給《華盛頓時報》做過很長時間的評論人。狄更斯寫的《雙城記》等很多小說的素材都來源于他早年做議會記者的經(jīng)歷,也包括他對社會的觀察;海明威的小說寫作風(fēng)格也部分來自于他寫新聞的時候所練就的凝練語言的本領(lǐng);馬克·吐溫就更不用說了,他的諷刺小說也來源于做記者的經(jīng)驗;還有馬爾克斯——來自南美的大文豪,伏契克——來自捷克的革命家,法國的社會學(xué)家雷蒙·阿倫等等。甚至哈貝馬斯也短暫地做過記者。這些人的政治理念各不相同,但是他們都是十九、二十世紀非常偉大的思想家、文學(xué)家,他們都做過記者。所以記者并不是那么簡單的工作。
在近代中國,有一個現(xiàn)象值得注意,最成功的報人往往并不把新聞看作是職業(yè)邊界十分明確的一項工作,這對今天的新聞人來講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包括梁啟超、鄧中夏、瞿秋白、陳獨秀,幾乎沒有人強調(diào)我們作為一個新聞記者應(yīng)該怎樣,他們對新聞的理解與今天我們對新聞的理解不一樣,他們將其看作是對人生、社會的追求,或者是一種政治表達的途徑。當(dāng)然,這套理念放在現(xiàn)代社會有一點理想化,這是必須承認的,但同時我們也要警惕,現(xiàn)在所形成的職業(yè)意識,是否過于限制了我們的文化想象?我們是否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新聞中常常蘊含復(fù)雜的思想,蘊含著對政治、社會的豐富理解。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我并不完全贊同阿倫特的政治理念與她對問題的看法,但是她有一篇非常有名的、也是非常出色的采訪,報道的是二戰(zhàn)結(jié)束之后,在耶路撒冷,猶太人的法庭對德國戰(zhàn)犯艾希曼的審判。艾希曼是一個劊子手,執(zhí)行了法西斯的反猶的政策,屠殺了大量的猶太人。阿倫特在做這個報道的時候,本來是將其當(dāng)作普通的對二戰(zhàn)戰(zhàn)犯的審判來報道,但是她在采訪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一些有意思的細節(jié),對她產(chǎn)生了很大的震撼——人們都認為艾希曼是一個劊子手,是一個殺人魔,但是阿倫特發(fā)現(xiàn)他就是一個非常無聊的中年男人,很愚鈍地坐在那里,除了官話、大話,沒有任何精彩的發(fā)言,更沒有任何瘋狂的發(fā)言,所有的語言都是那么的平庸,并且所有的精神病測試對他一點都不起作用。這樣一個正常的人,是如何犯下滔天大罪的?所以阿倫特開始反思她之前對戰(zhàn)爭的理解,她曾經(jīng)認可戰(zhàn)爭是“極端的惡”,但現(xiàn)在她認為不對,她根據(jù)自己的采訪,提出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政治哲學(xué)概念——“平庸的惡”。艾希曼只是一個執(zhí)行人,而不是一個策劃人,也就是說他只是在沒有反抗的情況下,去無意識地助長了惡,但是他本身并不是一個極端的惡人。阿倫特的這篇報道在發(fā)表后引起了人們非常大的爭論,特別是猶太人對這篇報道非常反感,認為其在為戰(zhàn)犯說話。后來,阿倫特?zé)o法承受巨大的壓力遠赴歐洲。
我們來看阿倫特報道中蘊含的政治理念,我們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你是否支持猶太人對阿倫特的批評,是否支持猶太人的看法?他們認為艾希曼是暴行的象征,這次審判的意義已經(jīng)不局限于個體正義,而在于歷史態(tài)度。或者說你贊成阿倫特的觀點?她認為審判的意義不在于復(fù)仇,而在于正義。所以,這里涉及到挖掘歷史的態(tài)度,是在于事實,還是在于態(tài)度?事實與態(tài)度之間是什么關(guān)系?在不違反事實的情況下,你是否可以有態(tài)度的調(diào)整?你可以說,對于歷史,總有一個公正的判斷和評價?或者干脆說,一切歷史都是當(dāng)代史,歷史就是意識形態(tài)本身?我們回到中國的新聞事件也是如此,不要瞧不起新聞的操作,這些微小的事情當(dāng)中所體現(xiàn)出來的很可能是非常重大的價值觀念,非常深刻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轉(zhuǎn)變。
所以我認為,新聞不是簡單的學(xué)科。作為一個新聞人,其知識體系應(yīng)該是放在大歷史的環(huán)境中的,而不是將注意力放在規(guī)則、原則、定理和采寫編評上的知識體系。
所以,各種社會新聞和公共事件,價值觀判斷的問題,實際上可以在你擴展知識之后,對它有非常豐富的認識。對于價值、事實和歷史的關(guān)系,我們強調(diào)這樣一種認識:真理最大的敵人往往不是故意編造的謊言,而是長期流傳的似是而非的神話。馬克思也說過一句話,相當(dāng)長的時期以來,人們一直用迷信來說明歷史,而我們現(xiàn)在要用歷史來說明迷信。為什么要用歷史來說明迷信呢?因為普遍性的共識,在不同的情境下有時是不適用的,甚至是矛盾的,所以我們強調(diào)是從規(guī)律的新聞學(xué)到視野的新聞學(xué)。新聞學(xué)受到傳播學(xué)的影響很大,媒介中心、規(guī)律出發(fā)、原則出發(fā),當(dāng)然這些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它們在一定情境下有參考價值。但是問題是你不要走到另一個極端去,所以我強調(diào)給陰謀一個機會,然后要回歸歷史,知識和視野的相互決定,視野對新聞人的立場和態(tài)度的關(guān)鍵作用。
這樣來看,我覺得新聞專業(yè)是一個有非常美好前景的專業(yè),大家選擇新聞專業(yè)是非常幸運的,它可以超越社會科學(xué)死板的羈絆,它可以不囿于職業(yè)階層的僵化的意識形態(tài),這實際上是我們最大的優(yōu)勢。你想想,在大學(xué)這個門檻里,還有哪個專業(yè)是可以如此廣泛地、如此不受限制地來討論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文化問題呢?中文系的人必定得顧及到文化文本的闡釋,經(jīng)濟學(xué)的人必定得顧及到經(jīng)濟理論的延展。這些社會問題你僅僅能夠作為一個領(lǐng)域的專家出現(xiàn),而我們新聞人是廣泛地涉獵各種各樣的領(lǐng)域,這是一個擁有無窮潛力和無窮魅力的行業(yè)。但是問題是它需要掌握非常豐富的知識,你不能夠受到任何學(xué)科的限制,更不能受到我們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形成職業(yè)階層以后所出現(xiàn)的這些意識形態(tài)的束縛。這些東西會不會束縛你的文化想象力,你要去思考這樣的問題。新聞人更大的魅力是實踐、調(diào)查、參與歷史、報道歷史。
總之,這是一個視野與精神的問題,所以最后我們講到一種精神——超人,這是尼采提出的概念。尼采曾經(jīng)指出是他把有限跟無限連接在一起了,這是個偉大的思想貢獻。尼采受到叔本華很大的影響,叔本華是一個非常悲觀的哲學(xué)家,他說生命就是欲望和不滿足,不滿足就帶來痛苦,所以人生總是痛苦的,所以人生生不如死,他是這樣一個哲學(xué)觀點。但是叔本華的哲學(xué)不徹底,因為他自己沒自殺。我們清華的一位導(dǎo)師,著名學(xué)者王國維,受叔本華的影響很大,自殺了,更徹底。但尼采比叔本華進步,他溝通了有限與無限,從而找到了生命的價值。尼采說生命雖然是有限的、痛苦的,但是我可以跟無限的意義聯(lián)系在一起,我可以跟我創(chuàng)造的無限的價值聯(lián)系在一起。我們中國一個很普通的士兵也說過類似的話,就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wù)當(dāng)中去”,我覺得這是多少年來中國人說的最精彩、最偉大、最深刻的一句話,它的哲學(xué)韻味是回味無窮的。我們活著到底有什么意義?如果你不把有限的生命跟更大的意義連接在一起,你的生活真的變得很無聊了。所以我們講社會的希望在哪兒?我們講制度,我們講規(guī)律,我們講原則,我們還要講一種文化,一種“新人”的出現(xiàn),這是馬爾庫塞講的一個觀點,我覺得非常有道理。
我在給本科生講課的時候說,你們是90后,你們想想一百年前的90后,想想那一代人給你帶來的激勵,當(dāng)你遇到同樣的社會困境的時候,你怎樣促使自己產(chǎn)生更加豐富的文化想象,怎樣促使自己去更多的學(xué)習(xí)豐富的知識,來完善你對社會和歷史的理解,你才能做好新聞人,才能做好對新聞現(xiàn)象、對社會實踐的理解。這是我想要傳達的一個理念。
王維佳,學(xué)者,現(xiàn)居北京。曾在本刊發(fā)表《現(xiàn)代中國空間政治變遷中的知識分子與文化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