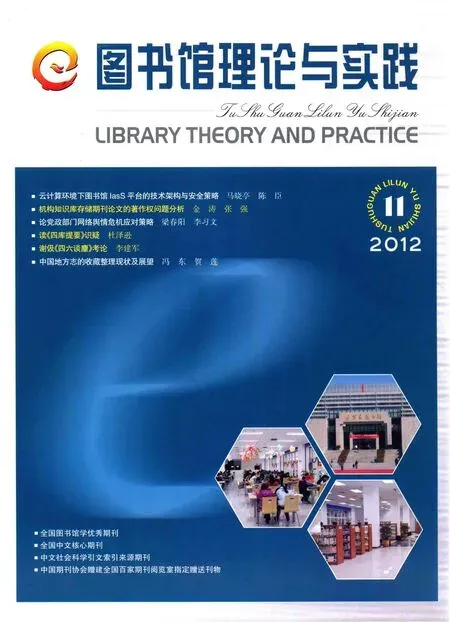由《徽州方言探秘》看同心回民話詞匯
●馬曉玲(寧夏大學 人文學院,銀川 750021)
江聲皖所著的《徽州方言探秘》一書,以方言詞匯為主線,在介紹方言語詞及對方言語詞的疏證中融入徽州獨特的民俗、民風,幽默風趣中揭示了徽州方言不同一般的語匯特色。同時,也使讀者充分的領略到了徽州方言特殊的地域性和濃郁的文化承傳性。令人興奮的是,徽州方言詞匯中竟然有不少筆者熟識的同心方言詞匯。徽州方言主要分布在皖南地區舊徽州府六縣(績溪、歙縣、休寧、黟縣、祁門、婺源),和普通話有較大差別,又兼有吳語、贛語、江淮官話等多種方言的特性,而且內部復雜多樣。無論是詞匯、語法還是語音上,徽州方言都保留了相當多的古音,被譽為古漢語的活化石。
同心方言處于蘭銀官話和中原官話的過渡地帶,與秦漢、隋唐時的權威方言─秦晉、秦隴方言有著直接的源流關系[1],又由于同心地處邊遠,環境閉塞,當地人信仰伊斯蘭教,因此保留了大量的古語詞,也被稱為“語言活化石”。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各自保留獨特特色的方言,在語音上差異極大,不可相提并論,但在詞匯上卻有著驚人的相似,雖然在使用過程中也有差別,但從方言詞語的相似可以看到,“語言像文化一樣,很少是自給自足的”。[2]但這不能說明徽州方言與同心方言之間就有詞匯的影響和借用關系。這種相似性的存在肯定有歷史的緣由。下文筆者例舉幾處徽州方言與同心方言相似的語詞。
1 媳婦
據江聲皖考證,漢代以前,尚無“媳婦”一詞,“媳”即為“息”,“息”的原義之一是指兒子,“息婦”便指兒子的妻子,今天“利息”是母錢生子錢。現在已弄不清由“息”至“媳”的演變過程了,自然也模糊了“媳”的本義,“兒媳”被解為“兒子的妻子”,后來,與“婦”組成“媳婦”,“媳”便成了“妻子”的別稱。徽州方言將兒媳稱作“新婦”,指剛作妻子的婦人,很多人誤聽為“媳婦”,以訛傳訛。“媳婦”在普通話及北方方言中指“妻子”。但在同心方言中“媳婦”一詞卻涵蓋了徽州方言與北方方言的用法。可以指“兒媳”,也可以指“妻子”,同心回民話使用“媳婦”一詞時必定要加“兒”尾或“子”尾。如,“今兒鄰家娶媳婦兒著呢!”“媳婦兒”也可以說成“媳婦子”,指兒媳。于是有“大媳婦兒”、“二媳婦兒”或“大媳婦子”、“二媳婦子”。年輕人指自己的妻子也用“媳婦子”或“媳婦兒”,但更多會用“婆”,如,“讓俺們婆去炒點菜!”順帶要說的是“俺們”中的“們”在這里并不表復數,要理解為復數就要鬧笑話了。“媳婦子”在同心方言中還有第三種用法,指代年輕的已婚婦女,如,“那個媳婦子勤快地很!”
2 姑娘
在普通話中,“姑娘”指未婚女子。與徽州方言有些相似的是在同心方言中“姑娘”分流了,在同心漢民話中單稱“姑”,在同心回民話中單稱“娘”(55調值),這里的“娘”絕不是母親而是“姑媽”,在同心方言中不稱母親為“娘”,所以不會混淆。依據排行,便有“大娘”、“二娘”、“老娘”。“大娘”與普通話中的年長婦女相混同,同心話中稱年長婦女不用“大娘”而用“老姨娘”。“老娘”指小姑媽,但在母親自稱時也用“老娘”,如,“老娘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這里主要靠聲調區分開來,前者51+55調值指姑媽,后者35+輕聲,用法同于普通話。
3 生育、養育、生養
生育、養育都是意義相同或相近的語素構成的聯合式合成詞,不生育在徽州方言中用“不生”,在北方方言中大多用“不育”,但在同心方言中選擇另一個詞“養育”中的“養”,稱“不養”,“養”即“生”,“生小孩”說成“養娃”,進而構成一個新詞“生養”,不生、不育稱為“不生養”。如此“養”在同心方言中就多了一個一項,除了同如普通話中“養羊、養花”之外,還表示“生育”之義。生育、養育、生養,生=育,養=育,所以,生=養。
4 肥、胖、壯
在普通話中,常用“胖”來形容人,用“肥”則表貶義了,如“肥頭大耳”。徽州方言很少用“胖”,夸贊人時以“壯”代“胖”,且用“滾壯”即非常胖。如徽州人一樣,同心回民對“壯”字的鐘愛還表現在宗教的禁忌語中,同心回民話中形容動物或供食用的牛、羊、雞、鴨肉時只用“壯”忌用“肥”字,但在指人的腳寬大時卻說“腳肥”。形容人時用“胖”也用“壯”,但“壯”字不能表夸贊更不能當著人面說,多是私下里對人的一種評論,如,“那個媳婦子吃地壯粘粘地啥都不會做。”
6 剛剛與將將
“剛剛”在普通話中表過去時,而“將將”應該表未來時,但徽州方言中都以未來時“將將”代過去時“剛剛”。同心方言中回民話也用“將將”代“剛剛”,“將將”使用時多兒化,也可用“將門兒”或單獨用“將”,如,“我將來一時時兒。”“他將將兒走。”方言中“將將”的使用是近代漢語詞匯的保留,如,小說《黃繡球》第二十四回:“來到隨員棧房里一問,那隨員大人將將前腳動身。”[3]161
7 潷
潷,b í 潷水,也說pié潷米湯。江聲皖在《廣韻·質韻》中查到:“潷,去滓”。明孫樓著的《吳音奇字·人事門》:“潷,音筆,有水之物,潷瀝出之。”[3]79同心方言中經常會用到這個詞,如,“把水潷b í干凈”“把米湯潷pié出來”,意思完全保留了古意。
8 經用、經吃、經看
“經用”為經久耐用的縮語,壓縮為“經”,在徽州方言中形成了以“經”為詞根的一系列詞,如,“經牢”指牢固耐用,“經著”指經久耐穿,“經燒”指經久耐燒,還有“經吃”“經看”“經餓”等。同心方言中也有一系列的“經”字詞,如:經用、經吃、經看、經穿、經燒、經打、經餓、經花、經使等。
9 歡喜、肝心
徽州方言這把“喜歡”說成“歡喜”,把“心肝”說成“肝心”,這種有意將詞序顛倒的造詞方法被公認為南方方言在構詞法上的一大特點。如廣州話有:歡喜、緊要、齊整、擠擁、宵夜、為因、鬧熱、人客、菜干、雞公、雞姆、貓公、貓姆。又如,汕頭話有:鬧熱、人客、歷日、鞋拖、風臺、裙圍、椅條、雞翁、雞母、貓母、貓娘。這是南方方言中常見倒序詞,所謂倒序是相對于普通話而言的。指的是方言中語素順序與普通話不同而詞義相同的詞。這些詞的詞素順序之所以相反,是古漢語單音節詞在形成雙音節詞的過程中出現的動搖不定的現象的遺留。大部分倒序詞都能從古籍特別是近古話本、小說中找到例證。[4]
在同心方言中也存在不少的倒序詞,有些是回漢通用的,如菜蔬、攪打、窄狹、言語等,大部分是回民話獨有的,除日常生活用語外,多出現在經堂用語中。如:牧放(放牧)、接迎(迎接)、立站(站立)、恕饒 (饒恕)、言語(語言)、忘遺(遺忘)、跡印(印跡)、現出(出現)、求乞(乞求)、怒惱(惱怒)、穢污(污穢)、康健(健康)、良善(善良)、路道(道路)、細詳(詳細)窄狹(狹窄)、照依(依照)、加贈(增加)、知感(感知)、知不道(不知道)、菜蔬(蔬菜)、攪打(打攪)等等。詹伯慧先生在《現代漢語方言》一書中認為倒序詞現象在北方方言中不常見。但實際上北方方言中也有大量的倒序詞。只不過由于方言體系、語言習慣、宗教文化等原因的不同,各方言對倒序詞的選擇及保留使用會有差異。以上提到的同心方言中的倒序詞有些我們在近代白話作品中可以找到依據。如:
窄狹:元雜劇《趙氏孤兒》第一折:“悄促促箱兒里似把聲吞,緊梆梆難展足,窄狹狹怎翻身?”
知不道:《醒世姻緣傳》第四十五回:狄員外說:“家里嬌養慣的孩子,知不道好歹,隨他罷。”《聊齋俚曲集·翻魘殃》第十回:“知不道他那心腹,見了他也就心驚,也就心驚,久下來,才傾心吐膽把你敬。”
知感:《初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七:“承蒙相公夫人抬舉,人非木石,豈不知感?”《儒林外史》第二十一回:“這一門親,蒙老哥親家相愛,我做兄弟的知感不盡。”
照依:《紅樓夢》第二十二回:“往年怎么給林妹妹過的,如今也照依給薛妹妹過就是了。”
加贈:明王守仁《傳習錄》卷上:“后世著述,是又將圣人所畫,模仿謄寫,而妄自分析加贈,以逞其技。”
南方方言中保留的倒序詞是古漢語特殊語法現象的遺留,那么,北方方言中的倒序詞現象無疑也是古漢語的遺留現象。古語詞可能在各個方言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保留,但在少數民族地區,這種保留會更長久、更牢固,這會使我們誤以為倒序詞現象可能是受其他語言影響所致,正如詹伯慧先生曾認為粵方言中存在的倒序詞現象是吸收壯侗語的結果一樣,我們可能會推測存在于同心回民話中的倒序詞也可能是受阿語或波斯語語序的影響。的確大量的倒序詞在《古蘭經》譯本中出現,比如上面提到的倒序詞中,“照依”一詞在《古蘭經》中特別普遍,如:“你們歸信著,照依一些人歸信的那樣!”口語中多簡用為“照”。如:“照你這么說,我們就沒法兒活了。”“加增”也在《古蘭經》中較為多見,如:“他們得正道的那些人,主把引領加贈給他們,與主把他們的虔敬賜給他們。”同心回民話中保留如此多的古語詞,究其原因,主要是當地的回回先民在放棄原用語轉用漢語的過程中,受到近代官話系方言特別是秦隴方言的深刻影響。秦隴方言是秦漢、隋唐時期漢民族共同語最重要的基礎方言,其方言土語中必然保存大量的古代“通語”成份。因此,同心方言中的古語詞完全是近代漢語甚至是古代漢語的遺留,特別是倒序詞現象。這也正是徽州方言詞匯與同心方言詞匯相似的歷史緣由。同心方言中倒序詞大量出現在回民話中,而且有些具有強烈的宗教文化色彩,從起源上分析,可能并沒有“別同”的初衷,但從使用上來看,確實已經具有了“別同”的功能。這可以從語言與文化的關系上得到解釋:語詞的使用強化了文化的概念。[1]275其實也可以說是宗教文化的概念強化了詞語的使用。總之,宗教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但這種作用的結果也只能是強化古語詞保留,而并不是從外語中吸收或借用。當然不能否認,由于宗教的影響,同心回民話詞匯系統中的確有一部分詞是從外語中借用來的,這部分借詞本文未涉及。
[1] 張安生.同心方言研究[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12.
[2] (美)愛德華·薩皮爾.語言論[M].陸卓元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197.
[3] 江聲皖.徽州方言探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158.
[4] 林倫倫.試探廣東諸方言倒序詞產生的原因[M].汕頭大學學報,1987(1):119-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