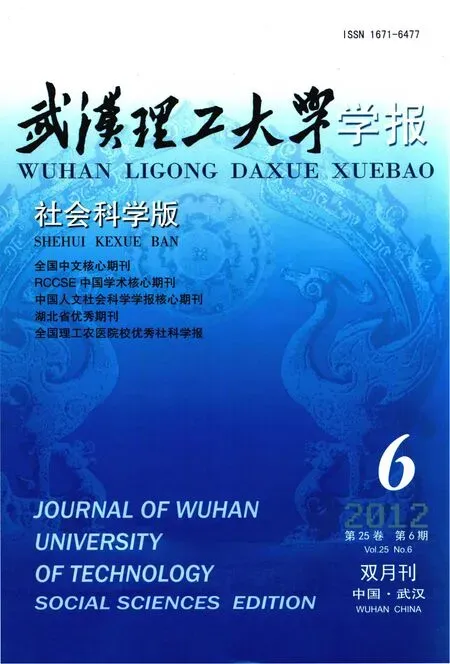超越解放的自由:略論阿倫特的革命觀
楊明佳,宋英超
(武漢理工大學 思想政治理論課部,湖北 武漢 430070)
在阿倫特為代表的共和主義看來,革命是一個具有特定意涵的現代性政治事件。既然自由立國是革命的終極目的,因此,革命就不能止于解放,而必須超越解放。本文以阿倫特的《論革命》一書為研究對象,以阿倫特對18世紀下半葉大西洋兩岸的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政治哲學比較與反思為案例,就革命與自由的關系作出闡述,以期更完整地理解阿倫特的共和主義的政治理想。
一、革命的語義學溯源
在西方語言中,英語中的“革命”一詞,源于拉丁文,最初是一個天文學術語,指的也僅僅是一種有規律的天體旋轉運動,正因為如此,西方人第一次將革命一詞用于描述特定政治事件,并非始于1640年的克倫威爾領導的反對英國專制君主的政治斗爭,而是始于1688年的英國君權旁落于威廉和瑪麗的時候,被人贊譽為光榮革命的英國人的政治妥協,“根本就不被認為是一場革命,而是君權復辟了前度的正當性和光榮”[1]32。可見,17世紀的英國政治詞匯中,革命的意思是復辟。那些革命者最初都堅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恢復被絕對君主專制濫用權力所破壞的事物的舊秩序,他們希望重返那種事物各安其分,各得其宜的舊時代。
但是現代革命在其進程中逐漸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尤其是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本身的不可逆轉的政治邏輯表明,回到舊秩序是不可能的,要防止權力濫用,避免權利被剝奪,就不能靠復辟舊的秩序,于是創建新的政治體成為革命的要義。如阿倫特所說,這些革命者“本想來一場復辟,挽救古典自由,卻演變為一場革命”[1]33。也正因為如此,美國革命的倡導者潘恩才依據那個時代的革命一詞的原始內涵,提議將法國與美國的政治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以別于英國式的光榮革命,這絕非是歷史的杜撰,而是在特定時代背景下革命一詞的內涵被拓展深化的真實寫照。
據此,阿倫特認為,革命作為一種現代政治變革方式,其一是源自革命的原初含義,那種不可抗拒的猶如天體運動般的軌跡,后來得到了黑格爾歷史必然性的哲學認證,革命被視為合乎必然性和歷史規律的行動;其二則是革命事件中所呈現出的那種創新性、進步性。這樣,革命既非古代的“造反”與“叛亂”,也不僅僅是政權的更迭,它被賦予特定的政治意義,“現代意義的革命,意味著社會的根本性變化,它標志性的一步就是——令無知者啟蒙,令全人類中受奴役者解放”[1]22。理性主義主導下的啟蒙運動建立起人的主體性,而主體性觀念支配下的人必將以自由與解放作為政治存在的基本狀態,由此,革命與人的解放和自由之間建立起了直接的關聯。由此,革命作為世俗的現代性的特定階段,阿倫特認同法國思想家孔多塞的革命定義,“‘革命的’一詞僅適用于以自由為目的的革命”[1]18。能否以自由與解放為宗旨成為鑒別政治事件為革命的尺度,而且也成為評價革命成功與否的關鍵。對此,阿倫特明確地說道:“既然自由世界通常的觀念是,判斷政治實體憲法的最高標準既非正義,也非偉大,而是自由,那么我們打算在何種程度上接受或拒絕這種一致性,就不僅取決于我們對革命的理解,而且取決于我們的自由概念。須知,自由本源上顯然是革命性的。”[1]18也就是說,在她看來,人們能否獲得自由,不僅取決于革命的行動,而且還取決于人們對自由的認知與理解。阿倫特在對法國革命與美國革命的政治哲學反思中,她得出的結論是,若要實現自由,革命就不能止于解放,而必須超越解放,將革命導向一個由公民廣泛政治參與的和平的制憲立國的新階段。按照這種共和主義的自由理念,阿倫特對18世紀的法國革命與美國革命進行了政治哲學的比較與反思。
二、解放式的自由觀:法國革命重心轉型的政治邏輯
在西方語言中,“解放”一詞源于拉丁文Livertas,意思是指不受限制和約束,或者說就是免于限制。同義字是solutus,源于動詞solve,意思是去掉約束。解放一詞又與自由“liberty”同源。因此,解放在拉丁語中幾乎等同于自由。根據美國學者費舍爾的解釋,地中海拉丁世界中的自由,是一種強調個人不依附于任何人的獨立狀態[2]7-9。在存在著自由人和奴隸之別的希臘羅馬世界,自由于是成為一種由法律確認的特殊性權利身份,奴隸可由某種原因獲得法律支持解除人身依附狀態而成為自由人。可見,在這種拉丁式的自由理念中,自由是一種免于外在強迫的獨立狀態,與后來以賽亞· 伯林所言的消極自由的概念最為接近,亦即只要這種獨立狀態得到憲法和法律的明確界定與保護,自由就已然實現,而無需更多的持續性的政治努力。
在英語中,“自由”還有另一種表達,即freedom,根據費舍爾的研究,這個詞源于古日耳曼語,描述的是一種血緣關系的共同體中每個成員與生俱來的平等權利,與liberty強調獨立及偏重于消極自由不同,這個充斥在北歐日耳曼語系中的詞所側重的是作為共同體之一員在享受權利的同時,必須履行作為成員維護共同體公共利益的義務,這里的自由就不再僅僅是個人權利,而且還有作為公民必須要有所作為,并參與到公共事務中去的義務要求,自由在這里被理解為是一種積極的政治生活方式。在西方語言中,只有英語同時交替使用freedom和liberty,從而與北歐國家語言中只用freedom和南歐國家語言中只使用liberty形成明顯區別。以上兩種不同的自由內涵及其彼此之間的政治與文化張力,也時時貫穿于美國政治進程中。其中的復雜多變的內涵,費舍爾、方納等美國學者都有專著論述,本文在此不作詳述。
眾所周知,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的誕生與近代歐洲的經濟市場化和民族國家崛起聯系在一起,自由主義者從理性的個人前提出發,相信借助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可以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和社會利益最大化的平衡,民族國家與政治之價值只在于為競爭的個體提供一個基本秩序,對于多數人而言,公共政治生活只具有工具性意義,本身并無本體性價值,在自由主義看來,政治參與也許是必須的,因為公民必須定期選擇政治代理人,以節制掌權者,但是除此之外,再多的參與也就淪為多余。基于此,自由主義信奉的自由理念本質上多是一種局限于個人權利范圍內的消極自由。一旦形成限權的憲政體制,自由主義者相信,自由就成為了現實。
站在共和主義的角度,阿倫特顯然并不認同這種消極的自由主義自由觀,她認為,法國革命的成果之所以雷聲大,雨點小,革命最終吞噬了自己的孩子,偏離了自由之宗旨,與法國人所持的這種解放式的自由觀有著直接的關系。對此,阿倫特說:“解放與自由并非一回事;解放也許是自由的條件,但絕不會自動帶來自由;包含在解放中的自由觀念只能是消極的,因此,即便是解放的動機也不能與對自由的渴望等而視之。”[1]18阿倫特的結論是:“解放是免于壓制,自由則是一種政治生活方式。”[1]21顯然,當自由被定義為一種生活方式時,僅靠解放那種一次性的政治與法律行動,自由是難以實現的。因為“如果革命僅以保障公民權利作為唯一目標,那它的目的就不是自由,而是解放,也就是從濫用權力,對歷時悠久且根深蒂固的對權利肆意踐踏的政府中解放出來”[1]21。這種革命觀,正是秉持消極自由的自由主義對革命的基本期待。在這種革命理念的支配之下,試圖建立一個真正的自由的社會共同體,就將成為一種不確定的歷史偶然性,正如法國大革命后長期呈現出來的在無政府與專制兩個極端之間搖擺的歷史那樣。
法國大革命本來也是在啟蒙運動所確立的自由原則下進行的一場理性主義的政治運動,但革命前法國是一個典型的封建等級社會結構,第三等級的不自由與嚴重社會不平等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貧困問題,使得那個時代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們對平等問題的關注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過了對自由的關注。不論是自由主義的伏爾泰、民主主義的盧梭,還是社會主義的馬布利,都毫無例外地將社會平等視為他們理論關注的重點。由此,法國人自然而然地將革命理解為一場實現自由與平等的雙重價值的運動。此外,與英國悠久的憲政保護下的自由傳統不同的是,由于法國革命前存在的不平等社會結構,于是對于民眾而言,自由乃是多數法國人從未充分享受的東西,他們便傾向于將自由理解為從等級制的奴役下解放出來。因此,一旦攻占象征奴役民眾的巴士底獄,國王便被立即送上斷頭臺,法國迅即建立了共和國,并頒布了人權宣言,多數法國人因此就相信自由已經實現。法國革命者們認為,他們應該利用革命形成的自由的專斷權威,以兌現革命時期對社會底層許諾的社會平等和幸福的承諾。阿倫特就此指出:“革命掉轉了方向,它不再是以自由為目的,革命的目的變成了人民的幸福”。[1]49“結果就是,舊政權的權力失效,而新共和國也流產了,自由不得不屈從于必然性,屈從于生命過程本身的迫切性”[1]48。最后之結局則是羅伯斯庇爾的無奈感嘆:“我們將會逝去,不留下一抹煙痕,因為,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我們錯過了以自由立國的時刻。”[1]49紅色恐怖并未帶來人民所希望的平等和幸福,而且也讓人民失去了自由,專制獨裁改頭換面,死灰復燃。阿倫特發現此種革命悖論和悲劇不僅單獨出現在法國,而且多次在不同國家上演,她不無遺憾地指出:“令人悲哀的是,我們也知道,在未曾爆發革命的國家中,自由維護得更好,無論那兒的權力環境有多么殘暴不仁,而且革命失敗的國家甚至比革命勝利的國家還存在更多的公民自由”[1]99。
以解放和自由為目的的革命最終走向自由的反面,是現代社會中法國式革命的吊詭之處。在阿倫特看來,此種局面的出現,固然與上述這些國家缺乏自由傳統以及嚴重不平等和貧困有關,但是也與這些革命背后建立在自由主義的消極自由的政治價值觀念直接相關。法國革命的悲劇,在阿倫特看來,正是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的失敗。或許洛克式的政治自由主義在英國這樣的有著悠久憲政傳統和相對平等的社會結構中,可以通過溫和的光榮革命而偶然取得成功,但是對于像法國這樣需要激進社會變革的國家而言,僅僅將自由定義為憲政和人權法案保護下的個人權利,將埋下重大的政治隱患。由理性、必然性以及革命中激發出來的群眾激情,必將沖破這些國家剛剛建立起來的脆弱的多數民主制,不可避免地將革命重心轉移到自由之外的領域,對于法國的無套褲漢而言,所謂權利首先是衣食溫飽和種族繁衍,“不是自由,而是富足,現在成為了革命的目標”[1]52。“從貧困中解放先于以自由立國”[1]122。這樣,革命內涵被無限制擴展,革命變得無所不能,似乎只要革命,就可以建立一個完美的新世界。但是,當革命被這樣理解時,革命就可能帶來各種形形色色的暴政,這種革命越是徹底,越是激進,可能就越遠離自由。
三、公共領域中的政治行動:美國革命后“失落的珍寶”
學界對美國革命及其憲法的政治解讀,長期以來均是自由主義占主導地位,美國革命被理解為洛克思想指導下的理性主義的政治運動,聯邦憲法則被視為自由主義的基本法。不過,阿倫特在《論革命》一書中并不太認同這種解釋,而是從共和主義自由觀來重新審視美國革命及其失落的遺產問題。
美國作為英國政治文化的歷史衍生品,自然繼承了英國的憲政傳統所保護的個人消極自由,因此在其革命中所蘊含的洛克式的自由主義理念毫不奇怪。但新大陸的政治革命,又非完全對英國革命的復制,它所存載的傳統,在阿倫特看來,更多的是歷史悠久的共和主義政治傳統。美國革命之所以能避免法國革命的悲劇,就在于立憲治國階段,美國的政治精英們既認同liberty的個人自由,也重視freedom所蘊含的政治自由,因此他們既重視建立一個保護個人自由的有限政府,又試圖建構一個提供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公共空間。對此,美國政治史學者方納指出:“對于現代人來說,許多革命時期的領導人既是共和主義者(因為他們關注公共福利,強調公民對政治體制的服從),又是自由主義者(因為他們極為重視個人權利的問題)。”[3]31
阿倫特之所以特別強調政治自由,與她所建構的行動哲學的前提有著直接關系。阿倫特區分了勞動、工作與行動,認為“行動是最出色的政治活動,那么,誕生性而非死性就是政治思想的中心范疇”[4]2。所謂誕生性,即復數的人在社會生活中開啟新端的能力。阿倫特相信,人之價值在于實踐和創造,在于在公共生活中彰顯每個人的個性,從而獲得他人的承認與尊重。她認為,脫離了公共生活,將自我局限于個人私利的空間里,個人將失去生活的價值與意義。“一切人類活動都要受到如下事實制約:即人必須共同生活在一起。一旦超出人類社會的范圍,行動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并且也唯有行動是如此”[5]57。因此,公共政治生活對于個人而言,就不僅僅具有工具性意義,而是具有本體性價值。與自由主義者將自由理解為個人主義基礎上的私人權利不同,阿倫特則認為,真正的自由是與共同體及其確立個體契約的各種歷史可能性分不開。共和主義的信徒阿倫特從古典城邦共和國的政治模式來理解自由之內涵:“一個自由的生活需要他人在場。故自由本身需要一個使人們能走到一起的場所-集會、市場、或城邦相宜的政治空間。”[1]20沒有在公共空間中的持續性的政治生活,那么也就沒有自由。因為“自由的實質內容是參與公共事務,獲準進入公共領域”[1]21。加拿大學者菲利普·漢森精辟地指出,在阿倫特這里,“自由與行動是密不可分的;自由是一種政治的或公有社會的現象,而行動則是真正政治的核心”[6]65。臺灣政治學者蔡英文也持同樣看法:“阿倫特的政治思想關切所在,乃是人類的實踐及其場所(即公共領域)的意義。”[7]7
正因為阿倫特從共和主義角度來界定自由,因此在她的眼里,美國革命最為珍貴的遺產,其實并不是被自由主義者最為稱道的聯邦憲法那個文本本身,而是其體現了共和自由觀的和平制憲過程。阿倫特特別看重殖民地以來的美國在市鎮層次上的公民政治參與對于后來美國革命的深刻影響,她指出,與法國革命比較,“美國革命之大幸就是,殖民地人民在與英國對抗之前,已經以自治體形式組織起來了,用18世紀的話來說,革命并未將他們推入一種自然狀態”[1]149。美國革命的這一特征,曾為托克維爾所觀察到并大為贊賞:“美國革命爆發,人民主權的教義從市鎮中產生,并占領了州”[8]56。而后來的制憲會議,在阿倫特看來,其實就是源自美國地方的市鎮會議的自然而然的放大,不僅使其制憲會議有其充分的權威,而且過程本身的和平與協商,也使美國以自由立國的革命進程逐漸擺脫了革命的暴力色彩,十分契合阿倫特基于古典共和經驗的政治概念。阿倫特這樣來界定政治的內涵,“以政治方式行事、生活在城邦里,這意味著一切事情都必須通過言辭和勸說,而不是通過強力和暴力來決定”[5]60。阿倫特推崇這種政治,將暴力與威脅視為亞洲式專制主義前政治手段。因此,阿倫特心目中美國革命的高潮定義為費城制憲以及隨后展開的全方位的為批準憲法而進行的公開辯論。“在現代的條件下,立國就是立憲。自從《獨立宣言》發動美國各州草擬憲法,制憲會議的召開就恰如其分地就成為革命的標志,這是一個未雨綢繆,以《聯邦憲法》和建立美利堅合眾國為頂峰的過程”[1]108。而在制憲進程中所呈現出來的革命原則則是,“這場革命不是突然爆發的,而是人們經過共同協商,依靠相互誓愿的力量而締造的。奠基不是靠建筑師,而是靠多數人之合力,——就是相互承諾和共同協商的互聯原則”[1]200。
一旦理性和平的公共參與成為革命的基本原則,自由就不再限定為一種消極意義上的個人自由,而是包括了公民政治參與的政治自由。政治自由所遵循的非暴力和和平協商精神,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革命初期的暴力傾向,避免革命跨越其邊界而進入其他領域。“美國革命的方向始終是致力于以自由立國和建立持久的制度,對于為此而行動的人來說,民法范圍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是不允許的”[1]78。所謂民法以外的任何事情,就是排除了借用革命暴力來調整財產關系的企圖。美國的建國者也能體會美國底層階級對社會平等的訴求,但是美國建國者們意識到,若放任革命中被激發起的欲望,可能會最終導致革命的失敗。比較《獨立宣言》與《美國聯邦憲法》不難發現,憲法作為一個政治文本,顯然比前者要來得保守和節制。不僅在憲法中默認了黑人奴隸制,而且將平等的價值嚴格限定在法律意義上。盡管憲法留下了如此之多讓人詬病的內容,但是美國制憲過程卻率先恢復了古典共和政治的樣式,即通過對話、協商和公民參與來解決公共事務的模式。
不過,阿倫特對于美國革命也頗有微詞,主要問題在于,盡管憲法的制定過程體現了共和自由的精神,但是最后形成的憲法文本中卻未能明確地將體現公民參與的市鎮層次政治安排納入其中。這種憂慮在反聯邦黨人那里早有察覺,尤其是杰斐遜,他發現,“共和國的致命危險就是,聯邦憲法將一切權力賦予公民,卻不給他們做共和主義者和以公民行動的機會。換言之,危險就在于,一切權力都賦予身為私人的人民,卻沒有為身為公民的他們建立任何空間”[1]236。因此,杰斐遜認為,要落實共和原則,就應該將縣分為街區,創立小共和國。否則,美國政府就是一個有名無實的共和國。故此,“如果革命的終極目的是自由,是自由可以呈現的一個公共空間的構建,是構建自由,那么街區的初級共和國,作為人人皆得以自由的唯一實物場所,實際就是大共和國的目的所在”[1]238。阿倫特之所以偏愛城邦樣式的小共和體制,在于她持有這樣的看法:“以政治的視角觀之,如果特定人口越多,構成公共領域的就越可能是社會領域而不是政治領域。——眾多的人聚在一起,往往會發展出一種幾乎無可抗拒的專制主義傾向,不管這是一個人的專制還是多數人統治的專制”[5]75。因此,不論是從擺脫專制,還是從展現個人的卓而不同的才華而言,都需要一個適當的公共空間。在阿倫特看來,在憲法中沒有確立街區的政治參與體系,是美國革命的最大遺憾,因為它遺失了革命中的珍寶。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革命尤其是自由立國的制憲過程,是共和主義的政治進程,但是革命后形成的以聯邦憲法為中心的政治框架卻是自由主義的。而這種政治局面的出現,實際或許也暗合著阿倫特對政治實踐的不確定性結果的理解,瑪格麗塔在為阿倫特的書作序時就這樣評價阿倫特的行動導向的政治觀:“政治發生在復數的人類當中,他們中的每個人都能行動和開啟新端。從如此互動中產生的結果是偶然的和不可預測的,因為‘實踐政治的事情,受制于多數人的同意,答案從來不在于理論或某個人的意見’”[4]2。從這個意義上講,簡單界定阿倫特為共和主義者或許違背了阿倫特的本意,在阿倫特對近代革命的政治反思中,她更看重的或許不是某種偏狹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理論,而是革命過程本身所呈現出來的政治本質的多寡。
美國革命之所以沒有吞噬自己的孩子,固然與費城制憲后形成的聯邦憲法的積極作用有關,但是顯然僅有一部憲法是不足以避免自由的危機。事實上,19世紀中葉的美國內戰,正是聯邦憲法的遺患之表現。美國之所以總體上能避免法國革命的結局,與新大陸的富庶的自然資源以及市場化所帶來的巨大財富有關,經濟發展后帶來的財富與機遇,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自由民主體制下底層階級借用多數權力來改變財富占有狀況的壓力;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還在于,雖然市鎮街區共和國并未納入憲法體制,但是殖民地以來所形成的社區自治經過世代傳承,已經成為根深蒂固的美國政治傳統。正是這種源自社區的政治參與,使得美國政治實現了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的共存,成為一些美國學者所稱道的共和自由主義的新類型,使其具有較強的政治彈性和適應力。
四、結 語
綜上所述,阿倫特的共和主義自由觀,承襲了古典希臘羅馬的政治傳統,將人的價值彰顯與公共領域的生活聯系起來,從而使其自由觀超越了自由主義推崇的消極自由,自由不再僅僅是與解放相聯系的特定的法律和政治事件,也不僅僅是被有限政府保護由人權法案所規范的個人權利,而且還應該是公民在公共領域中對公共事務的廣泛參與,自由還應該是公民的積極生活方式。只有這樣來理解自由,革命才不會偏離其宗旨,才能避免革命后的民主體制墮落為多數人的暴政。在貢斯當、伯林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那里,個人自由優先于政治自由,而在阿倫特為代表的共和主義者這里,政治自由優先于個人自由,政治自由的實現程度,不僅直接關系著個人自由的實現程度,而且也事關作為一個共同體成員的生命意義的實現與否,自由不能止于解放。阿倫特的自由觀的深刻之處,不僅在于她奠定了共和主義政治哲學的核心概念,而且為我們重新透視近現代革命提供了一種有別于自由主義的政治敘事。逝去的20世紀是一個革命的世紀,但是許多國家的革命或多或少都重復了法國革命的陷阱,解放替代了自由,結果革命是越來越激烈,而自由卻越來越稀少。或許,阿倫特的共和主義政治觀將為我們反思這些革命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理論視角。
在全球化的當代世界,共和主義傾慕的小共和國或許越來越不可能,但是共和主義悠久傳統承載的政治價值在當下并未失去意義。無論是自由還是平等,只要對于這個星球上的人們還多是有待實現的理想時,革命就可能是難以避免的,因此告別革命或許只是一些懼于法國式革命的知識分子的一廂情愿。問題的關鍵不是要不要革命,而是要理解革命的主旨,從而確立革命的方向與邊界,而這就是本文詮釋阿倫特革命觀的意圖之所在。
[1]阿倫特.論革命[M].陳周旺,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
[2]David Hackett Fisher.Liberty and Freedom[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3]方納.美國自由的故事[M].王 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4]阿倫特.人的境況[M].王寅麗,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
[5]王 暉,陳燕谷.文化與公共性[M].北京:三聯書店,1998.
[6]漢森.歷史、政治與公民權:阿倫特傳[M].劉佳林,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7]蔡英文.政治實踐與公共空間:阿倫特的政治思想[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8]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M].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