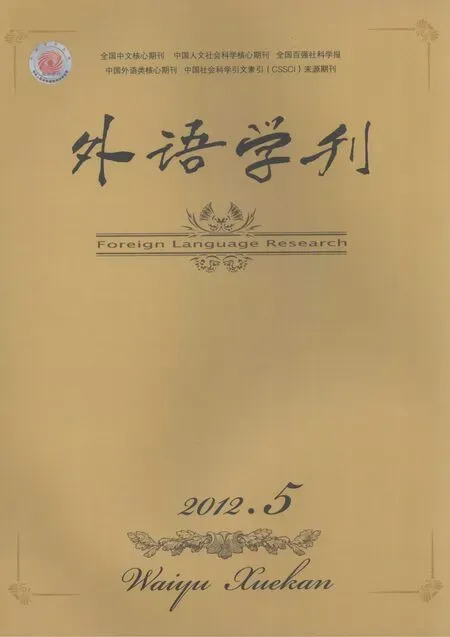格語法式微中的認知轉向:重讀 “再論‘格’辯”*
陳忠平 白解紅
(湖南師范大學,長沙 410081)
〇語言的認知維度
格語法式微中的認知轉向:重讀 “再論‘格’辯”*
陳忠平 白解紅
(湖南師范大學,長沙 410081)
“再論‘格’辯”一文多被學界劃入Fillmore格語法體系,并定性為格語法二期理論。研究發現,“再論”一文是在第二代認知科學興起的背景下依照框架語義學的基本原則考察句子語義和語法結構關系問題的理論成果,它將場景認知過程與語法關系選擇有機結合起來,突出認知語義內容在語法結構中的基礎作用,再一次體現了Fillmore語言研究在格語法式微過程中的認知轉向,因此無法納入格語法體系。
格語法;意義場景觀;語法關系;認知轉向
Fillmore于1968年發表了“‘格’辯”一文,在轉換生成語法框架中初步創建了格語法體系,旨在“發現一個語義上可以證明的普遍句法理論”(Fillmore 1968:88)。相隔近十年之后,Fillmore又發表了“再論‘格’辯”(下文簡稱“再論”)一文,重提之前的格語法話題。本文將從“再論”的撰寫背景、主要內容以及研究取向這幾個方面對該文進行剖析,闡明文中存在的不同于格語法的理論取向及范式。
1 Fillmore語言理論認知的轉向
“‘格’辯”發表后不久,也就是20世紀70年代初,基于體驗哲學的第二代認知科學開始興起(Lakoff & Johnson 1999),學者們多用原型、框架、圖式等概念談論認知和知識表征,第一代認知科學中的心智“天賦論”受到質疑,知識表征中的概念、推理被認為是依賴身體體驗后天習得而來,概念結構與意象圖式、動覺圖式密不可分,概念化與想像性思維成為研究中心,隱喻、轉喻不再受到排斥(Rosch 1973,Goffman 1974,Minsky 1975)。這些新的認知理論為語言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視角,也成為Fillmore語言理論轉向的大背景。
在這種背景下,Fillmore開始更多關注語言的意義及其理解問題。當時盛行的是客觀主義語義理論,意義被認為是符號與客觀現實之間的直接映射關系,意義的描寫必須訴諸于一套表征客觀事物及其屬性特點的基本概念。這些概念是確定的、離散的,它們處于一種客觀的邏輯關系之中,其內容的組織和理解不受人類思維心智活動的影響(Johnson 1987)。Fillmore將這一派的各類語義理論概述為意義清單理論(checklist theories of meaning),并針對這些理論提出了語義研究的場景-框架范式(scenes-and-frames paradigm),該范式中的場景既包括現實的視覺場景,也包括從各類體驗中抽離出來的典型場景,且場景多與圖式相通并用。框架則被定義為“由語言選擇組成且與典型場景相關的任何系統”,既可以“是詞語的組合,也包括語法規則或語言范疇的各類選擇”(Fillmore 1975:124),因此被Fillmore稱為語言框架。在場景與語言框架的關系上,Fillmore認為,語言框架以及其中的詞項是說話人在認知各類場景或圖式過程中逐步習得的,它們二者之間的聯系一旦為說話人所掌握,就可以在說話人的頭腦中相互激活,詞語乃至話語的意義也正是在激活的場景或圖式中得到理解(Fillmore 1975,1976b)。
Fillmore的商業交易圖式或場景就是在這一階段提出的,該圖式包含購買者、出售者、交易現金和貨物4種成分,這些概念成分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互動關系,均可在英語中以詞匯形式表征出來。如動詞buy,spend,sell,cost,pay等就是與商業交易場景相關聯的語言框架的一個重要部分,它們分別將場景中某些參與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前景化或突顯,而這些被突顯的內容,就成為以上詞匯豐富的語義內容。在話語交流或語篇理解過程中,這些詞匯中的任何一個都會在人們頭腦中激活整個商業交易圖式,其意義乃至相關話語的意義憑借場景或圖式中的概念內容就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須要指出的是,場景-框架范式中的框架不同于第二代認知科學所使用的框架概念。前者屬于語言范疇,Fillmore將它與場景相關聯,實質是要超越意義清單理論,更好地解決語言意義,尤其是詞匯意義的理解問題。后者是新的認知科學中用于知識表征的一個重要概念,“代表一種知識或信息構架”(Minsky 1975:212)。 也許是受到新的認知科學的影響,Fillmore提出上述范式之后,即對框架概念進行了重新闡釋。他明確提出,“在闡明語言系統時,不僅要描寫其語法和詞匯,還要描寫認知和互動‘框架’”(Fillmore 1976a:23)。Fillmore還進一步指出,人類存在一個習得和創新框架的過程,各類認知框架積累起來形成一個總藏,“可以對人類的體驗和知識進行組構、分類和解釋”(Fillmore 1976a:25)。這時的框架完全不同于之前的語言框架,已具有認知屬性,它與場景、圖式一起成為表征各種體驗與認知結構的概念工具,因此又被稱為認知框架。在框架與語言的關系上,Fillmore承接場景-框架范式的路向,提出框架不依賴語言而存在,但可以用來解釋語言交流和理解。正是基于框架的上述認知語義屬性,Fillmore創立了框架語義學,在場景、框架中為語言意義的理解尋求有機而全面的概念認知內容(Fillmore 1975,1976a,1976b,1982)。它標志著Fillmore語言理論在新的認知科學背景下的認知轉向。
2 “再論‘格’辯”中的意義場景觀
2.1 意義場景觀的提出
“‘格’辯”發表近十年之后,引起了“異彩紛呈的爭議”( 傅興尚 姜占民1999),Fillmore撰寫“再論”一文,主要目的是回應“‘格’辯”發表以后外界對格語法提出的各種質疑和誤解,為格在語法理論中的作用給出新的解釋。Fillmore在回應外界質疑時,分析了格語法自身的種種不足,同時坦言對于像格的類別和數目等問題仍無法解決,也不再涉及格語法中的各類轉換操作及其表征系統,因此把原來構建的格語法體系逐漸劃上了句號。
為了重新解釋格的作用,Fillmore在“再論”開篇即提出他的語義口號:“意義相對于場景而存在”(Fillmore 1977a:59)。該口號與場景-框架范式一樣,將語言表達的意義置于該表達所激活的場景中來理解,遵循了框架語義學的基本原則,本文稱之為“意義場景觀”。“再論”中,這種意義觀主要關注句子的意義和結構問題,從而為之前格語法中從語義功能角度定義的格或深層格找到了作用空間,只是這時的格或深層格已脫離了之前的轉換語法體系,深層格到表層格形式的轉換操作已不復存在。在該意義觀之下,Fillmore提出,格在語義上涉及句子結構的語義本質,用于幫助解釋句子結構成分之間的語義關系,語法上它有助于說明句子成分的語法功能。但是在此之外,在語法理論中還應有一個層面來說明句子的語法功能是如何被決定的,即句子的主語、賓語等核心語法關系是從何而來的。這一思考,涉及句法語義的本源,極具開創性。為此,Fillmore在Katz論述的句子3種功能理論(Katz 1972:113)的基礎上提出句子的第四個功能維度:定位和視角,并基于視角將可表達的信息區分為“視角內”和“視角外”信息,即“信息的視角化組織”(Fillmore 1977a:60-61)。這種信息組織方式,正如Cook對語法系統的評述那樣,像一張網將交際中須要表達的信息收在其中。其實,Fillmore在討論建立框架語義學必要性時已經提出使用視角概念,它代表了人從不同角度考察認知場景的能力,現在它和意義場景觀融合起來,試圖解決句子的語法功能問題,這進一步體現了Fillmore語言研究中的認知取向。
國內學者沒有注意到Fillmore在“再論”以及同期“詞匯語義學話題”中發生的這種認知轉向,將兩文仍看作是格語法的二期理論或后期理論,也許是忽視了Fillmore語言理論在第二代認知科學背景下發生的認知轉向。
2.2 意義場景觀下的語法關系
“再論”中Fillmore試圖在意義場景觀中為格理論找到一席之地。如前所述,場景中的成分及其互動關系構成了豐富的場景信息。說話人選取某個視角將一部分場景信息納入視角進行視角化組織,實質是突顯或前景化這一部分內容。這種視角化的信息,在Fillmore看來,可以為格理論提供主題內容,之前的格框架也可以通過為視角化信息指派語義角色而成為連接場景和句法表達的橋梁。不過,在意義場景觀之下,這種較微觀的語義格討論已沒有在格語法中的分析那樣重要,場景、視角和句子語法這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成為“再論”關注的焦點。
Fillmore首先仍以商業交易場景為例對上述三者的關系作了簡要說明。他提出,如果說話人將場景中購買者和貨物成分納入視角,則把二者之間的買入關系突顯出來,在語言表達上會使用動詞buy;若將購買者和錢幣納入視角,則突顯了該場景中對錢幣的支配使用關系,這時會使用動詞spend(Fillmore 1977a:73-74)。換句話說,商業交易場景的不同視角突顯不同場景成分間的作用關系,形成buy和spend各自不同的語義特點,也構成不同句法表現的認知動因。
在具體闡明場景、視角與句子語法之間的關系過程中,Fillmore主要探討了以下兩個關鍵問題:(1)場景中哪些成分會進入視角化組織;(2)受視角化組織的成分如何分派句中的核心語法關系(Fillmore 1977a:73)。在回答這兩個問題時,Fillmore又重點關注場景中進入視角并在語法關系選擇上成為賓語的成分所具有的突顯特征。他認為,能入句成為賓語的場景成分具有以下3個特征:(1)像人一樣具有感知力;(2)發生狀態或移位變化;(3)受完整性動作影響(Fillmore 1977a:75-79)。客觀上,人表現出來的感知反應與其受到刺激后發生較突顯的狀態變化是相通的。例如,在用木棍打人的場景中,被打者通常因其即時的感知反應會比木棍更具突顯性,因此,人們一般選擇說①a;若人們側重觀察木棍在這一場景(如氣功表演)中的變化時,則會選擇①b.
① a. I hit Harry with the stick.
b. I hit the stick against Harry. (Fillmore 1977a)
再如,在一個涉及位置變化的場景中,說話人選擇說②a還是②b,是同場景中table所指物體的移位特征相聯系的。Fillmore認為,若場景中桌子在推力下不發生移動,說話人則只會將施力者及其動作納入視角,所以導致了②a中的語法結構;當桌子在動作作用下發生移位并由此獲得突顯特征時,它就被納入視角化組織,因此,table一詞在②b中獲得了句子核心語法關系。
② a. I pushed against the table.
b. I pushed the table. (ibid)
下面一組句子也可以檢測人們對句子直接賓語與場景成分變化之間這種聯系的心理期待。
③ a. I hit the vase with the hammer, and the vase broke.
b.?I hit the vase with the hammer, but the vase broke.
c. I hit the vase with the hammer, but the hammer broke.
與③a比較,③b中并列小句所表述的內容符合人們的心理期待,因此不能使用but,③c中并列小句的內容不符合人們對場景變化的期待,所以用but幫助表示這種超出預期的結果。
關于受完整性動作影響這一特征,Fillmore則把它與下面一組經典例句所描述的場景聯系起來討論。
④ a. John smeared paint on the wall.
b. John smeared the wall with paint. (Hall 1965)
在一般場景中,類似④a中paint所指的場景成分通常會被表達為句子的賓語。至于兩句因the wall句法地位不同而存在的語義差別,Anderson認為這是由于深層結構中the wall是作部分性解讀(partitive interpretation)還是整體性解讀(holistic interpretation)而造成的(Anderson 1971)。與此相反,Fillmore在認知場景中對這種語義差別進行了解釋。他認為,the wall所指成分能被說話人納入視角,并獲得核心語法關系,是由于它經過涂抹動作獲得了完整的突顯效果(即墻全部被涂完)。相比之下,這種解釋比Anderson的分析更加自然。
3 “再論‘格’辯”:“‘格’辯”之續?
“再論”在“‘格’辯”發表近十年之后重提有關格的老話題,看似在延續格語法研究,但它在理論取向及范式上都與“‘格’辯”大不相同,已無法納入到“‘格’辯”所創建的格語法體系里。
“再論”是在第二代認知科學興起、Fillmore語言理論發生認知轉向的大背景下撰寫而成的。文中提出的意義場景觀繼承了場景-框架理論范式,體現了框架語義學的基本原則,尤其突出了人對于復雜場景信息進行視角化組織的認知能力,因此完全不同于Fillmore之前在轉換生成語法框架下進行的格語法探索。“再論”重申,語言表達的理解有賴于語言激活的場景,并進一步提出“語義研究就是對由語言創造或激活的認知場景進行研究”(Fillmore 1977a: 73-74),為框架語義學明確了研究目標。這些論述,今天已發展為認知語言學的基本理念,場景、框架同理想化認知模型、認知域等概念一起都已成為認知語言學的核心概念。
“再論”提出意義場景觀,其目的在于將框架語義學的理論范式應用到句法領域,考察句子的意義與結構關系。在此之前,Fillmore多利用認知場景或框架背景探討詞義的理解。“再論”中Fillmore把研究重點轉移到句子層面,將場景、視角、句子的意義及語法功能融合起來統一考察,形成了一條從場景經由視角到句義再到語法功能的分析路徑,揭示了句子語法關系選擇背后的認知理據,為認知語言學中的認知語法奠定了基礎(Fillmore 1975,1976a,1976b)。
“再論”試圖在意義場景觀中繼續為格理論找到留存空間,并對格的作用作出新的解釋,但這也僅是意義場景觀分析路徑中的一個環節。相比之下,場景的認知過程,即場景信息的視角化組織對句子意義及結構的影響更為關鍵。總之“再論”中格語法已默認退場,新的理論范式已成主導,“再論”已無法成為“‘格’辯”之續。
4 結束語
仔細研究Fillmore“再論”一文,并與其它相關論述比較,本文認為,“再論”是Fillmore在第二代認知科學背景下,利用框架語義學的理論范式分析解決句子語義與語法結構關系問題的理論成果。它把說話人對場景的認知過程與語法關系選擇有機地結合起來,突出認知語義內容在語法結構中的基礎作用,進一步確立了其研究的認知路向,也因此開辟了認知語法研究的新方向,極大地豐富了當代語言學研究。總之,“再論”不同于轉換生成語法框架下的格語法研究,已無法納入“‘格’辯”所創建的格語法體系。
傅興尚 姜占民. 試析從事件到句子的功能轉換機制[J]. 外語學刊, 1999(2).
Anderson, S. On the Role of Deep Structure in Semantic Interpretation[J].FoundationsofLanguage, 1971(3).
Fillmore, C. The Case for Case[A]. In E. Bach & R. Harms (eds.).UniversalsinLinguisticTheory[C].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8.
Fillmore, C. An Alternative to Checklist Theories of Meaning[A]. In C. Cogen, H. Thompson, G. Thurgood, K. Whistler, & J. Wright (eds.).ProceedingsoftheFirstAnnualMeetingoftheBerkeleyLinguisticsSociety[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Fillmore, C. Frame Semantics and the Nature of Language[J].AnnalsoftheNewYorkAcademyofSciences:ConferenceontheOriginandDevelopmentofLanguageandSpeech, 1976(280)a.
Fillmore, C. The Need for a Frame Semantics in Linguistics[J].StatisticalMethodsinLinguistics, 1976(12)b.
Fillmore, C. The Case for Case Reopened[A]. In P. Cole & J. Sadock (eds.).SyntaxandSemantics(Vol.8):GrammaticalRelations[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a.
Fillmore, C. Topics in Lexical Semantics[A]. In R. Cole (ed.).CurrentIssuesinLinguisticTheory[C]. Bloo-minton &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7b.
Fillmore, C. Frame Semantics[A]. In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Korea (ed.).LinguisticsintheMorningCalm[C]. Seoul: Hanshin, 1982.
Goffman, E.FrameAnalysis[M].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Johnson, M.TheBodyintheMind:TheBodilyBasisofMeaning,Imagination,andReason[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Lakoff, G. & M. Johnson.PhilosophyintheFlesh:TheEmbodiedMindandItsChallengetoWesternThought[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Minsky, M. A Framework for Representing Knowledge[A]. In P. Winston(ed.).ThePsychologyofComputerVision[C]. New York: McGraw-Hill, 1975.
Rosch, E. Natural Categories[J].CognitivePsychology, 1973(4).
【責任編輯王松鶴】
ExploringtheCognitiveTurnintheContextoftheDecliningCaseGrammar:ANewInterpretationofTheCaseforCaseReopened
Chen Zhong-ping Bai Xie-hong
(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
TheCaseforCaseReopenedis often placed in Fillmore’s Case Grammar and classified as the second phase of Case Grammar. This paper argues thatTheCaseforCaseReopened, written in the context of the rising second-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 is a work which aims to reveal the meaning-form relationship in clauses by following the basic principle laid down in Frame Semantics. Achieving an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cognitive processes and the choice of grammatical relations, and highlighting the underlying cognitive-semantic content as motivation for grammatical structure, this work witnesses the cognitive turn once again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clining Case Grammar, and thus cannot be labeled as Case Grammar.
Case Grammar; Scene View of Meaning; grammatical relation; cognitive turn
H0-06
A
1000-0100(2012)05-0081-4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項目“菲爾摩語義理論發展研究”(11WLH38)的階段性成果。
2011-10-17
編者按:本欄目圍繞3個論題組稿:一是從總體上反思認知語言學及其理論(陳忠平、白解紅,曹群英),二是緊扣認知語言學當下的熱點——轉喻研究(鄒春玲),三是繼續關注認知語言學的經典論題——隱喻(王松鶴、周華,李良彥)。從宏觀到微觀,從前沿到反思經典,是適合包括認知語言學在內的所有語言學分支學科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