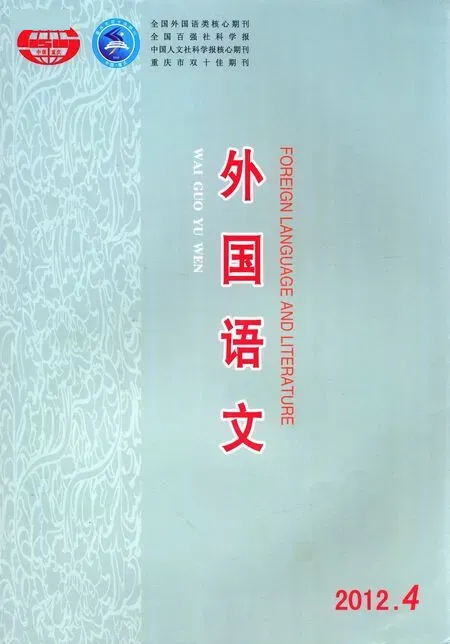墮落與再生——論《斗士參孫》中的“大利拉之悖論”
吳玲英
(湖南師范大學 外 國語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斗士參孫》是彌爾頓的代表作之一,評論家一致認同“他(彌爾頓)從未寫過如此有激情的作品”[1]319。“如此有激情”,部分是因為詩劇在很大程度上藝術地表現了詩人的生活遭遇,但更重要的是因為彌爾頓的作品中鮮有復雜女性的刻畫,而在《斗士參孫》里,大利拉卻占居關鍵地位。如同在他的整個三部曲(《失樂園》、《復樂園》和《斗士參孫》)里一樣,詩人在這部作品中尤其深刻地探索了人的墮落與再生。這部詩劇特別杰出之處就在于,大利拉這個造成參孫墮落的誘惑者被作者具有悖論意義地塑造成參孫精神再生的動力。
《斗士參孫》主要取材于《圣經·士師記》。根據《圣經》,參孫一出生就被神選中并被賦予神職,其藏在卷發里威力無比的神力將助他拯救以色列民族脫離非利士人的奴役。然而,參孫喜愛一名叫大利拉的非利士女人,而大利拉在首領的金錢誘惑下,謊騙參孫將神力的秘密泄露,并趁參孫熟睡之際,叫人剃掉他的頭發,參孫的神力隨之消失。非利士人于是輕易將他拿下,挖掉其雙眼,將他囚禁。但參孫的頭發逐日長出。一天,非利士首領聚會,叫參孫為他們表演巨力。參孫趁機雙手抱住房柱,屈身拖跨大殿,將在場的眾多非利士統治者壓死,而自己也同歸于盡。
彌爾頓的詩劇舍棄了這一圣經故事的前半部分,即大利拉如何誘惑參孫,使他這個以色列民族大力士淪落為非利士囚徒,而集中講述參孫墮落為囚徒后的故事。詩劇沒有過多表現或描述與大利拉無關的情節,而是從一開始就聚焦大利拉的背叛給參孫造成的絕境。詩劇的第二場,也是作品的中心部分,呈現參孫在獄中最后一天的經歷,即在與三位來訪者(父親瑪挪亞、妻子大利拉和非利士民族大力士赫拉發)的對話和對抗中獲得精神再生的過程,而大利拉則是其核心環節。亞里斯多德所定義的詩劇的開頭和中間均圍繞大利拉展開,而詩劇的結尾部分則體現大利拉的來訪所造成的結果,即獲得精神再生后的參孫最終的勝利。所以,大利拉的影響貫穿詩劇始終,難怪燕卜遜將大利拉視為詩劇主人公[2]224,如同撒旦被他視為《失樂園》的主角一樣[2]211。
一
《斗士參孫》一開始就極力烘托主人公參孫的悲慘與絕望。此時的參孫身陷囚牢、雙眼被挖、雙腳被銬,每天用天賜的巨力扛著重枷給敵人推磨,整夜呼吸牢里窒悶惡濁的空氣。如被縛的普羅米修斯一樣,參孫深感“心頭的創傷”[3](SA,185)和“靈魂的折磨”(458)。特別是雙眼失明,更加劇了他由肉體蔓延到精神的苦痛。
在彌爾頓之前,已有多位作家刻畫過失明帶給參孫的極端絕望;但由于詩人本人也正體驗著失明之苦,因此劇中參孫的吶喊比其他作家的憑空想像更為刻骨銘心,更使人能親身體驗參孫的痛楚。詩劇開篇表現深陷黑暗和精神迷茫之中的參孫渴求指引的那兩個詩行特別具有震撼靈魂的效果:“請借我你的手,給我引導,再往前一點/穿過這些黑暗的步伐,哪怕只再往前一點。”與之相比,艾略特在《四個四重奏》中的呻吟“噢,黑暗,黑暗,黑暗”以及埃斯庫羅斯讓被縛的普羅米修斯喊出的“光亮、光亮”都顯得蒼白。彌爾頓這段哀嘆失明的獨白(67-104)是英美文學史上表現肉體和精神失明的經典段落。彌爾頓如此著力表現參孫的痛苦是為了凸顯他由于違背上帝旨意而墮落所造成的后果。伴隨視力喪失的哀痛,參孫審視著自己更加黑暗的內心,看到的是生活毫無意義、毫無目的和毫無希望。參孫歷經著比哈姆雷特更慘痛的自我分裂,“過著半死不活的生活”(101)。
參孫曾擁有“上帝所賜的力量”(36),被稱頌為“以色列民族大力士英雄”,但他為何如此受困?詩劇的第一部分不斷重復這樣的短語:“被人出賣了”(34),“因一個女人的哀懇哭求,/軟了心腸(將神秘)泄露給她”(49-50),“在她舌劍唇槍襲擊下,/開放了本應對女人緘默的堡壘”(235-236),“和一個不潔不貞的女人結婚”(320-321),等等。可見,在參孫看來,使他墮落、置他于絕境的就是他詛咒的這個女人;而這個女人在參孫眼里是“人面獸心的魔鬼”(230)、“可怕的陷阱”(231)、“陰險的娼婦”(537)、“毒蛇”、“妖婦”(748)、“女騙子”(750)、“女巫”(819)、“大毒蛇”(936;997);總之,她是誘惑、貪婪、虛偽、褻瀆、背叛的代名詞。
大利拉其名其人直到詩劇第725行才出現,而在這之前,彌爾頓一直用“這個女人”、“那個女人”來指代她。在“這個女人”登臺之前,讀者已從參孫的獨白中感受到并從參孫的身上看到其可怕的毀滅力量:她的誘惑致使“萬夫莫當”(126)的大力士參孫耽迷聲色,完全“作了女人的俘虜”(563),并最終受困。所以,彌爾頓筆下的大利拉既不可能簡單如燕卜遜所解讀的“輕浮的貴婦人”或女權主義者所聲稱的“彌爾頓的女妖”或卡麥榮所闡釋的“沉迷于騎士情結的淫婦”或伍茲所分析的“厭女經典中有名的惡棍”。大利拉在三次謊騙參孫失敗后,第四次終于用詭計套出他心中的秘密。熟悉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讀者,尤其在讀過第一百三十八首情詩中的詩行“當我的愛發誓其真話,/我相信她,盡管我明白她在說謊”后,不難理解參孫的行為之悖。雖然大利拉狡智的誘惑性和表演的欺騙性有待在后面與參孫的論辯中才得以揭示,但她出場前參孫談及她時痛苦和憤怒的反應足已讓讀者想見這個女人在其墮落中的作用;正是這個“人面獸心、陰險叵測的女人”(230)在“愛情正濃之時,被敵人給的黃金動了心”,致使他“掉進了/媚眼妖態、虛情假意的陷阱,/把陰險娼婦的胸懷當作了安樂窩;/把頭發和體力的保證完全交給她”(537-540)。
英國文學傳統將這個叫大利拉的女人與荷馬的刻爾喀、塔索的阿米達、維吉爾的黛朵、喬叟的克萊西德、斯賓塞的阿卡狄亞等同歸于“女誘惑者”,她們都擅用自身無法抵御的誘惑力迷惑、削弱和延耽男人,使之偏離神圣的事業。而在她們之中,大利拉最具毀滅性,那不僅因為她自身的誘惑力難以抵抗,更因為她邪惡和狡詐,同時也因為她易受他人誘惑,為金錢利益而背叛,是“所有妻子中最壞的”。同彌爾頓的其他誘惑者如科瑪斯和撒旦相比,大利拉最大的誘惑來自其無以倫比的女性魅力;但和他們一樣,大利拉擁有無懈可擊的智慧、無人能及的表演技巧、無以抗爭的言語力量。在這一點上,大利拉從根本上有別于文學傳統中的其他“女誘惑者”。
二
在大利拉出現之前,參孫申斥大利拉的段落以及合唱隊對她的評論都讓讀者感到參孫和大利拉的獄中相見應該是詩劇里最易把握的情節。參孫對大利拉的態度很直接,似乎很容易解讀。但實際上,大利拉與參孫的對話卻是詩劇里最令人困惑的部分。參孫口中的大利拉似乎只是可惡、可恥、可恨因而易于歸類的女人,然而大利拉出場后的表演發人深思、令人疑惑,以至于燕卜遜斷言:“現代評論一定會為大利拉這位被冤枉的妻子叫屈。”[2]224大利拉的復雜性由此可見一斑。歌德曾在聽完他人為他朗讀大利拉的辯詞后大呼:“多偉大的詩人(彌爾頓)!簡直把復雜的大利拉刻畫得入木三分!”[4]228
其實,復雜的大利拉體現的是誘惑的復雜性。正是因為這種誘惑,參孫“從光輝榮耀的絕頂,/墮落到厄運的萬丈深淵”(SA 168-169)才如此耐人尋味。也正因為如此,參孫的再生更值得探究:大利拉的誘惑曾經致使體格巨人參孫墮落,而她的再次誘惑卻促成參孫再生為精神巨人。要在變幻莫測、真偽難辨的誘惑面前避免再次墮落,參孫必須超越自己過去僅為體格巨人的局限,積累精神巨人(基督式英雄)所需的“內在精神”,尤其是其核心“信仰”和“忍耐”。在彌爾頓看來,“內在精神”只有在這種繁雜的矛盾沖突中、在直面鏡像的過程中,在重重誘惑的考驗中才得以建構和完善。大利拉致使參孫墮落,但也是參孫再生的原動力。這一悖論,同基督教中“道成肉身即為了獻身”、“出生即為了死”、“死即是勝利”等眾多悖論一樣,是基督教特別深刻之處,同時暗含了彌爾頓對“誘惑”的獨特見解。
“誘惑”是彌爾頓創作中自始至終的焦點,而“誘惑所帶來的痛苦和善惡爭斗是他主要詩作的主題”[5]109,也是17世紀英國作家們共同的關注。彌爾頓在其神學著作《教義》里指出:“誘惑可能是上帝用以試煉人們,也可能是上帝用來允許人們被惡魔所誘惑”(WJM,XV,87);它值得期待,以苦煉心態、熬煉意志,“使信仰經過試煉,便生忍耐”(89)。彌爾頓斷言,“誘惑”在完善人的品性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離開誘惑的試煉,人的美德虛弱且不堪一擊:“我不能贊頌逃避現實的美德,它沒有實踐過,就沒有生命。”(98)人的品德必須經過各種誘惑的不斷試煉才能成為真正的美德:“上帝為什么要賦予我們內心以情欲并使我們周圍充滿誘惑物,不正是因為這些東西在適當的控制下是美德的組成部分嗎?”(319)在《失樂園》里,彌爾頓通過夏娃之口反問道:“如果沒有單獨受試煉,只憑外力,/哪有信、愛、德可言?”(PL.9.335-36)彌爾頓反復強調人的“內在精神”只能通過誘惑的不斷試煉才能獲得,并堅信“理智早已根植在所有人心中,憑借它人們可以抵御各種誘惑”(WJM,XIV,130)。彌爾頓的三部曲便是他這一神學思想的藝術再現,揭示了誘惑面前追尋“內在精神”的意義,而《斗士參孫》被視為這一追尋旅程的“終曲”[6]195。
詩劇沿用彌爾頓前兩部史詩的“誘惑模式”,將參孫完全徹底地暴露在誘惑之下,讓他充分發揮自由意志,完全憑借理智與信仰抵御三重誘惑,并從中洞見自己過去墮落的根本原因,從而逐步建構和完善其“內在精神”,最終獲得精神再生。在由三位來訪者組成的三重誘惑中,大利拉情節尤為重要。在她到來之前,參孫的父親瑪挪亞前來探監將已陷絕境的參孫進一步推入深淵,為他在面對大利拉誘惑時的爆發奠定了基礎;而參孫最后戰勝大力士赫拉發的誘惑則是他在抵制大利拉的誘惑中成長起來的“內在精神”的展示。
參孫的父親年老世故、久經風霜,已見慣人們祈求之美好變為禍患,因此常感嘆“人生一切,/想來哪一件不是夢幻無常?”(SA 249-50)盡管如此,他仍為參孫的悲慘境遇所震驚,開始懷疑上帝的公正,并自行扮演拯救參孫的救贖者角色,力勸兒子接受他的安排,放棄對上帝的信仰和對神啟的等待。其實,這正是導致參孫墮落的最致命而他至今仍沒有認識到的根本問題,即信仰的動搖:“懷疑神明的預言”(43)并“指責神的安排”(210)。參孫被困并掙扎于自己的罪孽感和被上帝拋棄的恐懼感這兩者的沖突里,此時的他不只深受肉眼失明之痛,信仰的缺失更讓他深感精神失明之苦。如同斯賓塞的《仙后》中深陷洞穴的蓋伊恩一樣,參孫已墜入絕望,看不見未來,感受不到希望,只覺得上帝已將他遺棄,剝奪了他身體和精神的雙重光亮,他“死已過半”(79)。
實際上,在參孫墮落之前,尤其在他奇妙的出生和無與倫比的神力上,神的大能已多次顯現。但如同伊甸園里的亞當夏娃只需遵守上帝唯一的禁令——勿食“禁果”——一樣,參孫同樣只需履行一個職責,即保守自己神力的秘密,因為這“緘默的堡壘”(236)和“緊要機密”(394)是參孫的神力所在;而根據神的旨意保守秘密本身就是順從神意、持守信仰,這正是參孫身為英雄的關鍵。但參孫沒能領悟,更沒能珍惜,而是“把上帝秘密給我的寶物,/為了一句話,一滴淚,泄露/給一個狡詐的女人”(199-201)。
父親的到來加深了參孫對大利拉的仇恨。但正是在與父親的爭論中,在指責大利拉的過程中,參孫逐漸意識到是自傲使他忘記了他的神力歸根結底來自上帝,這才是自己墮落的根本原因。正如亞當夏娃必須歷經失去樂園之痛才能學會順從,參孫也在墮落后的困境里,尤其在接下來與大利拉的言語交鋒中,才領悟到信仰和忍耐的意義,即忍耐就是對神意的絕對信仰和對自己的堅定信心。在基督教看來,忍耐是一切的基礎;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后書》中呼吁,“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難中,仍存忍耐和信心”(1:4),而《雅各書》更明確地寫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煉,就生忍耐”(1:3)。而在彌爾頓這部詩劇里,“其基本主題就是忍耐”,而忍耐和信仰是參孫內在精神的核心,也是“他獲得精神復生的標志”[7]111。參孫最終拒絕父親“贖他出去”的建議,也就是拒絕放棄信仰和拒絕惰怠舒適生活的誘惑,而選擇忍耐。這實質上暗示參孫的精神開始復蘇,為他隨后戰勝大利拉的誘惑做好了準備。
三
從根本上講,參孫的墮落是由于他屈服于大利拉的誘惑,因為他相信了大利拉的甜言蜜語(honied words)而背棄上帝的神諭(the holy Word of God)。在大利拉的誘惑下拋棄上帝賦予的神圣使命,這實際上意味著把對上帝的信仰讓位于對大利拉的順從。因此,參孫要獲得精神再生必須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大利拉的探監為此提供了契機,參孫同她在精神上的較量也成為他的內在精神成長的關鍵和動力。如果說詩劇第一場是為了著重表現參孫墮落后的悲慘境況以反襯大利拉的誘惑和背叛,那么詩劇第二場的中心,即大利拉的探監,直接展現和揭示了大利拉誘惑的復雜性和欺騙性,從而使參孫經歷了最嚴峻的誘惑考驗。在參孫要戰勝的三重誘惑中,大利拉情節最長,占350詩行(710-1060),而瑪挪亞和赫拉發部分僅分別為73行(578-651)和183行(1061-1243)。杜拉姆指出,“這部關于再生的詩劇主要取決于一個情節,即大利拉情節,它在詩歌里處于中心位置”[8]246。盡管參孫的精神復蘇在大利拉登臺之前已經開始,但只有在與大利拉的言語對抗和抵制她的誘惑中,參孫才真正認識到自己墮落的根本原因和大利拉的本性,從而在思想上發生飛躍并在精神上得到升華。
當參孫的妻子大利拉終于登場時,合唱隊首先看到她的出現,用“這個”、“那個”、“什么東西”等指物代詞來指稱大利拉,影射其人性的缺失。詩劇接著用15個詩行(710-725)生動地描述大利拉的萬種風情,塑造了一個17世紀貴婦人的典型形象:裝束時尚、炫耀賣弄、濃裝艷抹。這一切不只是揭示出大利拉自傲和膚淺的本性,也為她在后面的系列表演埋下伏筆。面對被她摧毀的曾經戰無不勝的參孫,大利拉驕傲地宣稱自己將由此被視為“女英雄”而名留青史、受人稱頌;與之相反,參孫回想起自己過去“聲譽日濃,膽氣沖天,/好像地上的小神仙到處招搖/受人羨慕”(529-31),心中卻充滿罪孽感,尤其感到有罪于以色列民族和上帝。這里,彌爾頓巧妙地運用對比的手法揭示出參孫和大利拉是本質上完全不同的兩類人。大利拉膚淺虛榮,而參孫的悔恨表明他即使在墮落之后身處絕境心中仍有上帝和以色列人民,這是他最終將獲得精神再生的基礎。有學者注意到,彌爾頓將參孫和大利拉都“形容為船”[8]163,那其實也是用對照來暗示他們之間本質的區別:參孫是“上帝托靠的錦纜樓船”(198),其來自內部的精神力量永恒強大,而大利拉則只不過是“裝備華貴”(718)的船,魅力僅在外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她華麗的裝束對于失明的參孫再也不會有她想像和期望的誘惑力。
大利拉上場后立即實施誘惑。她“好像鮮花滴露的樣子哭了起來,/話語似乎融成了淚珠”(728-29)。與她裝束的高調和登場時的張揚相反,她在參孫面前的表現卻異常謙卑,字里行間的膽怯似乎在傳達她的懺悔,也似乎在表明她的順從和不安。但她滿身的香水味卻暴露出她前來實施誘惑的真實意圖。為了實施誘惑,她必須在精神上麻痹參孫;而語言同美色一樣是大利拉的主要武器。筆者曾專文論述過,彌爾頓善于將語言的直樸與真和善相關聯,如《失樂園》里墮落前亞當夏娃的語言和《復樂園》里耶穌的用語都非常簡單明晰,與撒旦的言語風格形成截然對比,完全沒有后者的慷慨激昂而又婉轉多義。在《斗士參孫》里,大利拉的語言也充滿撒旦式的模糊、復雜和隱藏的語義。她選用不同范疇的詞匯,運用一切可能的言語技巧使其說辭有吸引力、震撼力和說服力。
大利拉首先為自己的背叛辯解說,“我未料到這件事的意外發展/竟引出這樣大的禍害”(736-37),以此表明她只不過是犯下無心之過。但參孫憤怒地一針見血:“快滾開,你這妖婦!這是你慣用的,/也是你們女騙子慣用的伎倆”(749-50),直接揭露了大利拉隱藏在懺悔的神情、顫抖的聲音、迂回的表達后面的虛假和欺騙。第一招失靈后,大利拉轉而將責任歸咎于女性固有的“缺陷”:因為自己“心智稍欠”,因此男人更應該為墮落負責。大利拉進而以此為借口將責任推卸給參孫:“你也不該輕信軟弱的女人!/……我們彼此很相像,或是同類”(784-87)。大利拉的話語的確擊中了參孫的要害,但與其意愿相反,她的責備恰恰迫使他內省,認清問題的本質。從一個特定角度看,他們的確“很相像”,甚至“是同類”,他們都犯下了罪孽;而他自己也的確因為相信女人而背叛了上帝。因此,大利拉成為他的鏡像,使他在大利拉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不僅如此,他進一步認識到,他之所以違背神諭,把上帝賦予他神力的秘密告訴大利拉,是因為他無數輝煌的戰績使他驕傲自大,“好像地上的小神仙到處招搖”(530),把上帝的告誡置之腦后,完全忘記了自己的神力和榮譽都是上帝的賜予。在基督教看來,驕傲是“七大重罪”之首,是一切罪孽之源,撒旦和亞當都因此而墮落。也就是說,在受大利拉引誘而泄露秘密之前,他其實已經犯罪。所以他承認:“是我自己對自己虛偽,你才對我虛偽。”(824)
由于沒能達到目的,大利拉隨即轉而求助于她獨特的“愛情”論,聲稱她出賣參孫的動機是出于愛情,是擔心“用情不專”(798)的參孫會遺棄她。況且,非利士人承諾過只將參孫看管,并無惡意,而她以為被看管的參孫就能“變成我的和愛的俘虜”(809)。大利拉的這一“愛情法規”(811)暴露出她的自私、忌妒和占有欲。在大利拉與參孫長達248行(748-996)的言語較量中,“愛情”一詞反復出現十八次;但具諷刺意味的是,“背叛”一詞也不斷重現,從而使“愛情”和“背叛”交織在一起。大利拉具有毀滅性的“愛”在本質上正是對愛的背叛,它是《失樂園》里撒旦在伊甸園偷窺亞當夏娃擁抱時的嫉恨的扭曲表現。然而,深受其害并處于精神復蘇之中的參孫識破了大利拉的真正意圖,用事實一一揭露其狡計,指出她的背叛并非真正出于愛情,而“是禁不起敵人黃金的誘惑”(831)。他還就她的“愛情法規”針鋒相對地說:真正的愛情不是“日夜廝守”(807),更不是把所愛之人“變成”“俘虜”(808),而是在真愛中給予對方完全的信任和充分的自由,這才是正確的“愛情法規”。這一愛情觀其實也是奮筆疾書“離婚冊”的彌爾頓本人的切身感悟。
接著,大利拉轉向國家和宗教等更高權威,將她當時所面臨的、即使最頑強的人也會被嚇倒的“進攻、誘惑和圍剿”(846)作為自我辯護的理由。她用一系列動詞描述首腦們對她“哀求、命令、威脅、逼迫”(852)。一連串的并列句、沉重的句式、語調、措辭都似乎在烘托她聲稱的壓力,一切都在逼迫她認識到俘虜參孫是“多么的公正、多么的正直、多么的光榮”(857)。大利拉似乎是在這樣的壓力下才犯下如此“輕率的”(747)錯誤。但參孫立即揭穿大利拉的詭辯,指出大利拉宣稱的愛情至上、愛國主義、公眾道德、自然正義都只不過是金錢的幌子而已。在與大利拉的交鋒中,參孫的內在精神在增長,“目光”也越來越敏銳,總能迅速透過她的誘惑表象看到本質。
大利拉見虛偽和狡辯被披露,只得再次懇求參孫給她贖過的機會作為補償,她要將失明的參孫帶回家中,使之“用別的感官去享受人生”(916)。她對未來的描繪暗含著性的快樂和生活的舒適。但參孫指出,她只不過是為了控制他,使民族英雄淪落為無助的孩子供她操控(920-925),或性對象供她利用(793-810)。因此,她的誘惑性建議遭到參孫斷然拒絕:“我們的關系早已一刀兩斷;/你不要幻想我會再上當,又落在/你擺布的圈套里”(929-931)。
最后,大利拉試圖與參孫進行身體接觸,要求與參孫“握手作別”(951)。身體接觸是文學中永恒的母題,是消除隔閡和整合分離的最后寄托和期盼。詩劇從一開始,墮落的參孫曾在孤獨絕望里苦苦尋求與他人、與上帝乃至與自己接觸和融合。但是,正是因為與大利拉的身體接觸曾經蒙蔽了自己的心智,給自己和民族帶來毀滅性后果,所以參孫不愿也不會再接受這危險的誘惑。他嚴厲斥責道:“你不要找死,一旦叫我摸到你,/我就會按捺不住憤怒,撕碎你的骨頭”(952-953)。在參孫看來,無論大利拉這個“狡詐的女人”再說什么或做什么,都不過是“圈套、陷阱和羅網”(SA 932),是“迷魂湯、甜言蜜語”(934)。于是,大利拉只得灰溜溜地離去,其形象無異于《復樂園》里在耶穌面前無計可施而只得“現出原形”(PR 4.449)的撒旦。參孫曾經在大利拉的誘惑面前倒下,而現在面對大利拉的再次誘惑,參孫通過堅定地抵制而站立起來,獲得精神再生;或者反過來說,正是因為他在與大利拉的交鋒中獲得了精神再生,他才能成功地抵制并擊敗她的種種誘惑。
四
在大利拉到來之前,參孫雖然在精神上已經開始復蘇,已經開始認識到自己的問題,但他還一直處于深深的絕望、自責和自我懷疑之中。他感到自己身體已被摧毀,體格力量也已喪失,因此認為自己已被上帝拋棄。然而,這實際上意味著當初上帝選擇他來解救以色列人是錯誤的,全能的上帝沒能做出正確的預見。在基督教看來,懷疑上帝的全能顯然是犯罪。這些都表明參孫還沒有樹立起對上帝的絕對信仰。這其實是他墮落和所有問題的根源。因此,他的再生自然也將以重新樹立堅定的信仰為根本。
參孫的再生過程藝術性地再現了彌爾頓的神學思想。在《教義》第十八章里,彌爾頓明確指出墮落之人完全可以從精神上獲得“超自然”的再生,既“形成正確判斷和實施自由意志的能力”,又“吸收新的、超自然的力量進入再生人的精神世界”(WJM,XV,367)。接著在第十九章和第二十章,彌爾頓分別對再生的根本——懺悔和信仰——進行討論,指出“在再生的人身上,懺悔先于信仰”(387),而“信仰是靈所結的果子”(395),是“確信所望之事、堅信未見之事”(395)。他進一步指出:“我們靠信仰,而不是憑眼見。”(399)也就是說,參孫必須經過認識到問題根源,真誠懺悔,才能樹立信仰,而信仰是絕對的、無條件的。
大利拉情節的戲劇性功能不僅僅是讓誘惑者再次誘惑參孫,使參孫從中得到試煉,同時也是把她作為參孫的鏡像,讓參孫從中看清自己墮落的本質,并因此懺悔自己的罪孽而不是把一切責任推給別人;只有這樣,他才能真正樹立起信仰并獲得再生。正是在與大利拉的以“聲譽—動機—愛情—寬恕”為爭辯框架的整個對話中,參孫直面鏡像,經歷了頓悟—懺悔—蛻變—再生的過程。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參孫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自己必須完全認罪、懺悔,企求寬恕,重新樹立對上帝的絕對信仰,最終獲得精神再生。
彌爾頓將妻子和丈夫的見面稱為“相見并幸福的交談”。但處于詩劇中心地位的這場諷刺性的“幸福交談”是參孫內心掙扎的轉折點:在大利拉來訪之前,參孫深陷身體和精神的雙重黑暗之中,而她離開牢獄時,參孫已獲得精神再生,不再懷疑神意和自己,不再受“甜言蜜語之誘餌”(1066)的誘惑,不再如詩劇開篇時絕望地乞求外部的引導:“請借我你的手,給我引導”,而是如彌爾頓在《教義》中所書寫的那樣,堅信明智是抵制誘惑的美德,而“能抵抗一切誘惑的品德,/那才最重要”(1051-1052)。參孫堅信信仰才是走出人生絕境的唯一道路,而以信仰為基礎的忍耐方能使他“成為自己的救星”(1289)。只有建構和完善以忍耐和信仰為核心的“內在精神”,參孫才能克服并超越使他墮落的個人英雄主義,成長為基督式英雄和精神斗士,同時他的神力也才能重歸。
參孫的精神再生直接體現在大利拉走后他對最后一位來訪者赫拉發的反應。大利拉來訪之前,參孫一味抱怨和指責“睡神早已把我遺棄”(631),身體和精神都瀕臨死亡;而大利拉走后,他精神煥發,堅信自己依然是上帝挑選的斗士,而他心中“在引領我做決不平凡之事”(1383)的強烈沖動就是神意。他要求合唱隊“不再繞圈子”(1064),因為他“猜謎的日子已經結束”(1064)。此時他得知非利士人的大力士赫拉發兇惡而至,于是勇敢地迎接他的惡意挑釁,表現出大無畏的氣概。他說,大利拉這個“上帝派來責罵我、鞭策我”(1001)的女人,已使他從墮落中崛起并從微弱里激發出力量,使他從被毀的“體格巨人”再生為強大的精神斗士。于是,不可一世的赫拉發不幸成為參孫精神再生后的第一個手下敗將。在拿赫拉發試手之后,參孫隨即滿懷信心地前去參加非利士人的慶祝聚會,并將其殿堂摧毀,完成了上帝賦予他的使命,終于證明了“參孫”這一名字的真正含義,即“上帝之子”和“義人的太陽”。
[1]Saillens,Emile.John Milton:Man,Poet,Polemist[M].New York:Barnes and Nobles,1964.
[2]Empson,William.Milton’s God[M].London:Chatto&Windus,1965.
[3]彌爾頓.復樂園·斗士參孫[Z].朱維文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文中引文多出自該書,不再贅述。)
[4]Leishman,J.B.Milton’s Minor Poems[M].London:Hutchinson,1969.
[5] Frye,Northrop.The Return of Eden:Five Essays on Milton’s Epics [M].Toronto:Uni.of Toronto Press,1965.
[6] Miller,David M.John Milton:Poetry[M].Twayne:Twayne Publishers,1978.
[7]肖明翰.試論彌爾頓的《斗士參孫》[J].外國文學評論,1996(2).
[8]Durham,Charles W.and Christin A.Pruitt.“All in All”:Unity,Diversity and the Miltonic Perspective[M].Selinsgrove:Susquehanna UP,1999.
[9]Jose,Nicholas.Ideas of the Restora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 1660-7[M].Cambridge,Mass.:Harvard UP,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