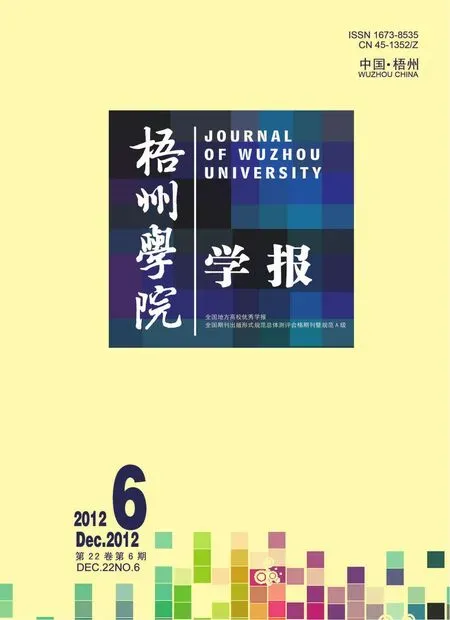精神生態失衡的悲劇
——精神生態視域下的《逾矩的罪人》
席戰強
精神生態失衡的悲劇
——精神生態視域下的《逾矩的罪人》
席戰強
(河池學院中文系,廣西宜州 546300)
《逾矩的罪人》是勞倫斯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國內對其研究較少。小說講述一個婚外情故事。勞倫斯在小說中書寫了比特麗絲、海倫娜和男主人公西格蒙德精神生態的失衡,特別是對西格蒙德精神生態失衡造成的悲劇人生的書寫,彰顯了其精神生態觀。即和諧的精神生態應當是拋棄占有和征服欲望,與自然、社會和諧相處。同時要更改彰顯個體生命的自然天性以達到靈與肉的和諧統一。人精神生態的和諧有賴于社會生態(人與人之間、男女兩性之間)和諧,精神生態與社會生態相互依存。
勞倫斯;精神生態;《逾矩的罪人》;和諧;啟示
一、精神生態與勞倫斯
所謂生態,簡單地說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狀態,以及生物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它們與環境之間的密不可分的關系。對生態問題的研究從最早對自然生態的研究漸漸延伸到對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層面上的研究。因為,隨著自然生態危機的日益嚴重,人們開始認識到自然生態危機與人類的思想文化觀念所操控的行為密不可分。因為人類也是生物的一種,而且人類這一生物種類是所有生物種類中唯一具有控制、支配并決定其他生物種類生存狀態的一個高級靈性物種,對于其他生物的生存狀態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即人類的思想意識、文化理念對于自然界其他生物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因此,1973年挪威著名哲學家阿倫·奈斯(ArneNaess)提出了深層生態學。深層生態學在關注自然環境生態的同時也把人納入到整個地球生態系統中,從而對人類個體本身的關注也進入了生態學研究的范疇,并將生態學發展到哲學與倫理學領域,提出生態自我、生態平等與生態共生等重要生態哲學理念。特別是生態共生理念更具當代價值,包含人與自然平等共生、共在共容的重要哲學與倫理學內涵。我國學者魯樞元先生認為在“生態”這一大系統中包含有“自然生態”、“社會生態”與“精神生態”三個子系統。在這三個子系統中,自然生態指的是自然界,社會生態指的是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生活方面,精神生態指的是人的內在情感生活狀態。魯樞元先生認為,自然生態的破壞必然影響到人類的整個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但精神生態在整個生態系統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為此,魯樞元先生指出了“精神生態學”這一概念并定義為:精神生態學“是一門研究作為精神性存在主體(主要是人)與其生存的環境(包括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文化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學科。它一方面關涉到精神主體的健康成長,一方面關涉到一個生態系統在精神變量協調下的平衡、穩定和演進”[1]148。隨著自然生態的破壞,人類失去了與自然和諧共存共生的環境,人類對自然的征服欲、支配欲和占有欲延伸到了人類社會自身,從而在造成自然生態破壞之時也同時造成了社會生態的異化和精神生態的失衡。生態學者們認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提高了人類的物質生活水平,但卻沒有提高人類的精神生活水平,并且隨著物質財富的累積、市場化的全面推進,人類的精神生活反而出現急劇下滑的趨勢”[2]。為此,對人類精神生態的研究愈加迫切。
由于生態危機(包含自然生態危機、社會生態危機和精神生態危機)的出現,相應地出現了反映生態危機或關注生態問題的文學創作(生態文學),20世紀初期的英國作家勞倫斯的文學創作就獵涉到生態問題。其創作背景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工業化社會,此時的英國乃至整個歐洲的自然、社會、精神生態都急劇變化,瀕臨危機。勞倫斯在小說創作中的社會批判和文化批判的主旨是對現代工業文明下的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危機進行書寫與剖析,并在其中蘊含其生態前瞻意識。對于勞倫斯小說的研究,國內學者多集中在其《兒子與情人》、《虹》、《戀愛中的女人》、《查特萊夫人的情人》這幾部長篇小說,而對于《逾矩的罪人》這部小說的研究甚少。《逾矩的罪人》是勞倫斯繼《白孔雀》之后創作的第二部長篇小說,主要講述的是一個因婚外情而導致的悲劇:小說主人公西格蒙德是一位小提琴師,是家庭的經濟之柱。由于收入微薄,家庭生活開支難以為繼而兼職做家庭教師。由于生活拮據,妻子比特麗絲對他頗多抱怨和不滿。家庭沉重的負擔和精神壓力最終使他陷入與學生海倫娜婚外戀從中尋求精神寄托,最后因對家庭的內疚和情人的不可捉摸而痛苦不堪,最終懸梁自盡以求解脫。筆者認為,在小說中,勞倫斯講述的這一個婚外情故事并非是在做道德上的、倫理上的評判,而是借此對人類精神生態問題進行剖析,體現了勞倫斯生態意識的前瞻性。
二、《逾矩的罪人》對精神生態的書寫
在《逾矩的罪人》中,對于人類精神生態失衡的揭示,主要體現在比特麗絲、海倫娜和西格蒙德這三個人物身上。
從小說著墨不多的敘述中我們知道,比特麗絲出身于一個殷實的家庭,自小就在法國新教學校讀書,受過良好的教育,她和西格蒙德也是因為相愛而結合在一起,甚至為了與西格蒙德的愛而與家里人不和并在家中失寵。然而愛情和婚姻是兩碼事,愛情是浪漫的,而婚姻則是現實的。婚后迫于生活的壓力,他們互相指責抱怨,彼此心中留下的是怨恨和不滿,愛情早已消失。比特麗絲常常因為西格蒙德微薄的收入而大發脾氣,在得知丈夫的移情別戀后,比特麗絲從內心到言語都充滿對他的厭惡與反感,并將情感轉移到孩子身上,以彌補夫妻情愛的缺失。海倫娜是一個外表美麗、嬌媚迷人的女人,深深地吸引著西格蒙德,“她那雙像大海一樣蘊含著風暴的藍眼睛,也像大海那樣永遠充滿了自信、孤獨;她那厚實、雪白的喉部是世上最結實、最美妙的東西;還有她那雙像絲綢一樣柔軟、像銀蓮花一樣輕巧的小手,這一切連同大海和丘陵就是他的明天”[3]17。她身體豐腴,金發如陽光燦爛,眼睛如同大海般蔚藍。然而,海倫娜的內心深處又有一種強烈的占有欲,她不僅想完全擁有西格蒙德的肉體、而且她渴求占有他的精神和屬于他的一切。而且反復無常、難以捉摸。“她置身于冷漠之中,在她與一切自然的日常事物間存在著一種隔閡,好像她屬于一個未知的種族,永遠不能講述自身的故事。”[3]142
有論者認為比特麗絲和海倫娜這兩個女人是勞倫斯筆下的“悍婦”和“大女人”形象[4]。但如果從勞倫斯對人類精神生態問題的探討這一主題構成的一貫創作風格來看,她們同樣是屬于精神生態失衡的典型人物。因為比特麗絲無疑是一個“怨婦”形象,怨婦必然涉及到精神生態失衡的問題。而海倫娜所追求的只是充滿夢幻色彩的愛,而不是現實中真實的愛。因而海倫娜也是一個精神生態存在嚴重問題的人物。
勞倫斯對精神生態失衡的書寫重點是男主人公西格蒙德。有評論認為:“男主人公西格蒙德就是一個‘自然人’形象。他英俊健壯、感情細膩、有知識、懂藝術;他的內心充溢著擺脫一切枷鎖,從而獲取自由,即恢復其自然本性的渴望。但這樣一個所謂的‘自然人’一出場便顯出與社會、與家庭、與資本主義條件下一個正常人的一切極不和諧甚至是格格不入的一面,從而也注定了其悲劇性的結局”[5]。“西格蒙德的悲劇又是勞倫斯所崇尚的‘自然人’的必然結局。在勞倫斯的眼里,西格蒙德是一個符合他的理想的‘自然人’。他體格健壯,感情豐富、深沉,又有很高的音樂素養;他的內心充滿了擺脫一切束縛,從而得到自由,即恢復其自然本性的渴望。”[6]但筆者認為,西格蒙德并不是什么“自然人”或“文明人”,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感的現代人,是一個因精神生活壓抑而導致精神生態嚴重失衡的男人。他的移情別戀完全是因為精神生活的壓抑所致,為精神生活的壓抑而尋求一種精神的寄托。小說中并沒有描寫或暗示西格蒙德品性浪漫,也沒有描寫他與妻子性愛的矛盾,更沒有描寫他與社會的脫節,不適宜在這個社會生存。相反,他如同一個正常的社會人一樣謀求生存,只是生活的緊張,收入不能滿足家里幾個孩子的教育及生活的開銷,操持家務的妻子難免有不滿的說辭和臉色。為此,一對經自由戀愛而結婚的夫妻因生活重負而造成家庭不和諧,從而導致精神上的痛苦與壓抑。他與學生海倫娜產生的“愛情”只能說是一種因精神生活壓抑而產生的一種壓抑情感的遷移,從小說中寫到他們海濱度假來看,西格蒙德對海倫娜的情感并非是一種愛情,他對海倫娜的情感仍然是一種矛盾復雜的情感,是借對方來緩解自己的精神壓力。因而西格蒙德的移情別戀既是對生活壓力的釋放,又是其作為精神主體的精神人格不健全的一種體現,是其精神生態失衡后的一個美麗的錯誤。西格蒙德的移情別戀并不是什么追求完美的愛情而是因為生活壓抑所致,在其移情別戀的過程中始終充滿了矛盾與痛苦,才會有一種深深的負罪感占據其靈魂深處。這種負罪感就是追求個人靈魂的自由解脫與家庭責任的沖突。為了擺脫精神生活的壓抑苦悶,他戀上海倫娜,但在內心世界里,海倫娜也并非是他心中的唯一,并非是他要追求的完美。所以,想著自己給妻子和孩子們帶來的痛苦就使其負罪之感陡然而生,同時又因為海倫娜的無辜而覺得對不起海倫娜,這種矛盾心理,這種負罪感一直在陪伴著他,從而更加劇了他精神生態的進一步不平衡,這種精神生態的不平衡直接導致了他最后以自殺的方式結束自己精神痛苦的一生。在小說中,作者有意識地不斷強化死亡這一陰影,這不是勞倫斯有意安排的結局,而是生活的正常法則,試想,一個并非大奸大惡的人,一個有著高度家庭責任感的人,不可能是一個隨意尋花問柳之人,在痛苦之時尋找情感的排泄必然是更加痛苦的,罪孽感也加深,因而自殺必然成了唯一的解脫之法。死亡無疑就是精神生態嚴重失衡的必然結果。這種死亡在勞倫斯筆下并非少見。如《戀愛中的女人》中的杰拉爾德就是一個因精神生態嚴重失衡而死亡的絕好例證。
由此可見,西格蒙德不愿受到家庭婚姻生活的束縛而移情別戀于自己的學生海倫娜,以期在與情人的濃情蜜意中獲得自由,獲得精神生態的平衡。然而在與情人的交往中同樣感覺到精神的不平衡和不自由。因為情人對他的愛也是一種肉體的和精神的占有。從此徘徊于情感與責任的矛盾當中,最后因對家庭的內疚對情感及自由的無望而自縊身亡。由此我們可以勾畫出西格蒙德的悲劇人生軌跡:“移情別戀”——“負罪感”——“死亡”。為了擺脫生活的壓力而移情別戀,因移情別戀而產生痛苦的負罪感,因負罪感而自殺以徹底擺脫痛苦。三個階段環環相扣,入情入理,演繹了一出悲凄動人而又令人惆悵憐憫的悲劇。可以說,西格蒙德是一個精神生態嚴重失衡的悲劇性人物。
勞倫斯的小說創作常常將筆鋒指向人物的內心生活和精神世界以探討人類精神生態失衡這一嚴重問題。而其對人類精神生態的揭示從其第一部長篇小說《白孔雀》里就初見端倪。從此,對人類精神生態的關注和探討貫穿其整部小說創作。勞倫斯對精神生態危機的關注與勞倫斯當時所處的生態環境有著極為重要的關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英國正處于工業文明高速發展時期,工業文明的發展導致了自然生態的破壞,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斷裂,人性受到壓抑,西方社會出現了信仰真空,人與社會、人與自我的和諧關系出現了斷裂。因而勞倫斯在其創作中總是緊緊抓住人的自然本性如何遭受到摧殘,人與人之間和諧關系如何遭受到破壞和人的精神生態如何走向崩潰甚至于死亡這一中心點來切入,以期揭示“在工業化和機械文明漸成為主宰一切的社會力量的時期,人們在精神上、道德上和相互關系上的變化”[3]3。可見,精神生態學者從自然的、社會的、人類個體的道德、倫理等方面闡釋了精神生態危機的產生和如何治理這一危機,而勞倫斯則是以文學的語言、生動的形象揭示人類社會精神生態危機并提出了其獨特的生態觀。因而,精神生態之于勞倫斯或勞倫斯之于精神生態是一種不謀而合的關系。
三、《逾矩的罪人》對構建和諧精神生態的啟示
精神生態與自然生態、社會生態是密切相關的,是整個生態系統中的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并在人類世界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生態學者們認為,是人類生活方式、思維模式、價值觀念、倫理道德導致了自然生態危機和社會生態危機,因而精神生態的危機才是更深層的生態危機。在《逾矩的罪人》中,勞倫斯對精神生態失衡的書寫及其蘊含其中的精神生態哲思,無不對當今構建和諧精神生態具有啟示意義。
首先,人類精神生態的和諧源自于社會生態的和諧,同時社會生態的和諧也離不開精神生態的和諧。兩者相互依存共生。在小說中,社會生態是不和諧的,夫妻之間沒有相知、寬容與諒解,正是惡化的夫妻關系和家庭的壓抑促使西格蒙德移情別戀,也正是妻子的嘮叨和責罵徹底摧毀了西格蒙德的男性意志并在家庭中失去了男性應有的權勢和地位。而西格蒙德與海倫娜的關系也是不和諧的,他們同樣是互不了解,海倫娜對西格蒙德的愛只是一種占有,她“追求的是充滿夢幻色彩的愛,而不是現實中真實的愛,即勞倫斯所倡導的理想的愛:精神與肉體的合二為一”[4]。正是這種社會生態的不和諧使西格蒙德在精神上和心靈上受盡折磨,從而一步一步走向悲劇。
其次,個體精神生態的平衡與否,與個體生命自然天性的彰顯密不可分。個體生命的存在價值在于個體自然性的理智彰顯。生命主體的自然天性得不到彰顯,生命之花不但不能結果反而會很快地凋謝,但這種彰顯必須是理智的。從西格蒙德悲劇性的一生來看,生命之花過早凋謝與其自然天性的壓抑緊密相關。作為一個頗具天賦的藝術家,其天性中潛在的東西,或者說是藝術基因必須會使得他豁達、大度、開朗,其稟性應該是詩意浪漫的,然而,生活的瑣屑事務,家庭柴米油鹽卻要系于其一生,這就必然抑制其天性的彰顯。西格蒙德的移情別戀似乎是其天性的彰顯,要尋找心靈棲息的港灣,而這一棲息的港灣對于一個藝術家而言就是所謂的愛情,只有在所謂的愛情天堂里才能使一顆受傷的靈魂得到安慰。然而,海倫娜實則并非是他的知音,而是一個沒有理想追求庸俗的女性,對他并不是理解而是只想將對方占為己有。在此,西格蒙德的自然天性并沒有得到彰顯反而因此陷于矛盾痛苦的境地,這就為他后來的自殺埋下了伏筆。
其三,個體自然天性的彰顯往往離不開社會倫理道德及傳統習俗。人,作為社會集團成員的一分子,離不開社會集團這一社會系統。社會的組成往往有其共同的游戲規則,人的主體活動往往受限于社會集團。社會生態系統有其“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叢林法則,作為生命個體的自然天性是追求自由獨立,真誠率性、無欺。但社會這一復雜的生物圈相對于自然生物圈而言則更具“動物性的野蠻”。西格蒙德要想保持其率性而為,自然為社會法則所不容。而人作為個體存在于社會約定俗成的法則中同樣潛移默化地打上社會法則的烙印,如家庭責任感,對所愛的人負責、對子女的責任,還有內心世界里產生的社會認同感。如他人如何看待我,我在他人心目中會如何如何等等。社會生態圈內顯性的、隱性的法則無不左右著作為生命個體的人的自然天性的舒展。
四、結語
總之,在《逾矩的罪人》這部小說中,勞倫斯側重于精神生態的揭示,人的精神生態的和諧同時還有賴于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兩性關系的和諧),精神生態與社會生態相互依存。這一生態思想無疑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而當今世界,尤其是當今中國,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劇,“人類活動造成的環境污染和生態失衡同時也向人類的精神世界彌漫,造成精神生態的失衡。主要表現為‘人的物化、類化、單一化、表淺化’,人的‘道德感、歷史感的喪失,審美能力,愛的能力的喪失’”[2]。因而對于精神生態的重視與治理刻不容緩。
[1]魯樞元.生態文藝學[M].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2]朱鵬杰.中國“精神生態”研究二十年[J].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5).
[3]勞倫斯.逾矩的罪人[M].程愛民,譯.北京:譯林出版社,1994.
[4]蘇燕.解讀勞倫斯《逾矩的罪人》中的女性[J].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5).
[5]張錦.“自然人”的悲劇——勞倫斯《逾矩的罪人》評析[J].文史縱橫,2007(1).
[6]王正文,程愛民.試論《逾矩的罪人》的社會意義及創作特色[J].外國文學研究,1998(3).
I106.4
A
1673-8535(2012)06-0030-05
席戰強(1966-),男,廣西天峨人,河池學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現代文學和勞倫斯。
(責任編輯:覃華巧)
2012-09-12
廣西教育廳科研項目(201010LX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