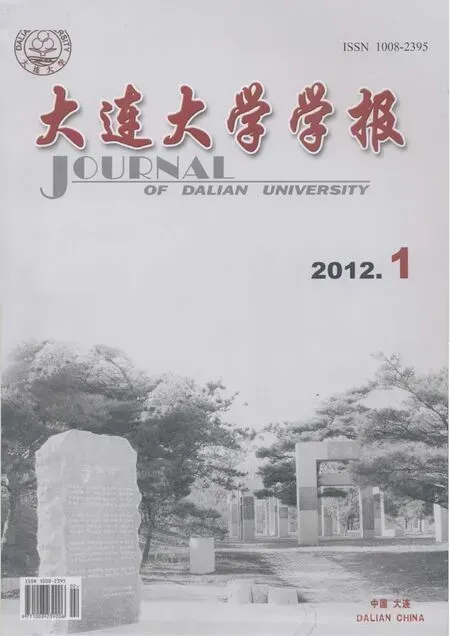“全學聯”與戰后日本學生運動
王新生
(北京大學 歷史學系,北京 100871)
“全學聯”與戰后日本學生運動
王新生
(北京大學 歷史學系,北京 100871)
在戰前學生運動的傳統、盟軍總部在日本推行非軍事化及民主化改革、日本共產黨成為合法政黨并積極開展活動、生活困難且學費不斷上升等背景下,戰后初期建立大學生組織“全學聯”并展開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盡管后來因黨派之間的矛盾該組織發生分裂,但仍然領導了包括反對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及美軍在日基地在內的反體制運動。
日本;戰后;全學聯;學生運動
“全學聯”的全稱是“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聯合”,成立于1948年9月,是以在校大學生為主要成員的學生組織,對戰后初期日本學生運動發揮了重要的領導性作用。囿于篇幅所限,拙文主要分析70年代以前的“全學聯”及其領導的學生運動。
一、學生運動與“全學聯”
戰后初期學生組織出現并積極進行活動首先與戰前的傳統有關。1918年東京帝國大學的學生結成“新人會”,是最早的學生組織,同時還有京都帝國大學的“京都勞學會”和早稻田大學的“民人同盟”等。這些學生組織積極參與擴大選舉權的“普選運動”,并試圖與工會組織聯合行動。后來其他大學也出現學生組織,而且出現了聯合的趨勢,各大學組織結成“學生聯合會”,大學預備學校結成“高等學校聯盟”。1923年,以東京帝國大學的“新人會”、早稻田大學的“文化同盟”為中心開展學生自治運動,并組織學生進行社會運動,例如爭取選舉權運動、推動工會組織發展、反對軍事訓練等,從而培養了許多無產階級社會活動家及日本共產黨的干部。
1928年日本出現金融危機及經濟危機,學生運動也達到戰前時期的高潮。不僅提出減少學費、改進授課、解除不稱職教授等教育方面的要求,而且也要求擴大自治權利,并時常為此舉行罷課活動。盡管大學生們積極參加這些校內斗爭,但隨著國家政權逐漸法西斯主義化,政府開始干預校園生活,不僅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學生被開除,而且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教授也遭到鎮壓。1933年,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教授瀧川幸辰被文部省解職,教員與學生對此進行了堅決的抵抗,但最終歸于失敗。1938年,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教授河合榮治郎在軍部的壓力下被解除職務,意味著大學中的反體制勢力消失[1]。
其次,戰后初期學生運動的興起與“盟軍總部”在日本推行的非軍事化、民主化改革有關。以美國為首的盟軍總部在日本推行非軍事化、民主化改革,因而支持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工會組織、學生組織不僅得到迅速發展,而且經常舉行罷工、罷課、示威等活動,要求改善勞動、生活、學習條件。戰爭結束剛剛兩個月,水戶舊制高校(相當大學預備校)的學生就發動了要求罷免軍國主義分子校長以及恢復進步教授職務的斗爭,并舉行罷課活動,結果政府文部省被迫罷免校長等3名教授的職務,同時恢復進步教授的職務。其后,上野女高、物理學校、靜岡高校等學校也出現校園民主化的斗爭,提出解散戰爭時期的校園報國團體、開除戰犯教師、進步教員復職、允許組成學生團體等口號。
與此同時,學生組織“自治會”紛紛成立。1946年5月,早稻田大學召開學生大會,制定學生自治會章程,并獲得學校當局的承認,組成全日本第一個全體學生參加的學生自治會。各大學紛紛仿效,同年11月,作為學生自治會聯合體的“全國學生自治會聯合”成立,但沒有實質性的活動。12月,早稻田大學學生自治會發動6000名學生上街游行,提出復興教育、解凍存款等要求[2]。
另外,學生運動的高漲與日本共產黨成為合法政黨并積極開展活動有關。戰前馬克思主義在校園盛行,因而共產黨在大學生中影響較大。戰后初期日本共產黨一方面發動群眾進行和平革命,同時在青年學生中積極發展成員,當時黨員的1/3是在校大學生[3]。1946年2月,“日本青年共產同盟”成立。其后,“東京都學生聯絡會議”、“關東學生政治協議會”、“關西學生政治協議會”等受共產黨影響的地域學生組織逐漸建立。1947年,東京的主要工會組織準備在2月1日舉行總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反對解雇工人。為支持這一活動,約40所大學的3萬名學生在皇居前人民廣場舉行“關東聯合學生大會”,提出“校園民主化”、“復興學校”等口號,會后舉行了游行示威。對蓬勃發展的工人、學生運動感到威脅的盟軍總部制止了“二一總罷工”,并在2月7日發表了盟軍總部民間情報教育局(CIE)的備忘錄,聲稱“學生自治不得涉及學校行政”。盡管如此,學生組織及其運動仍在繼續發展。1947年2月16日,全日本國立大學學生會議在東京大學召開,籌劃成立“國立大學學生自治會聯盟”。經過數次協商后,同年11月在京都大學召開“國立大學學生自治會聯盟”(簡稱“國學聯”)成立大會,東京大學、北海道大學、大阪大學等19所大學50名代表參加。聯盟的綱領是“努力促進全國學生自治會組織的統一,以確保學生生活的穩定以及校園民主化”,“努力組成國立、公立、私立大學均參加的全國學生自治會聯盟”。
戰后學生運動興起的另外一個原因是生活困難,學費不斷上漲。進入1948年后,通貨膨脹進一步加劇。例如:消費物價指數1945年9月為100,1947年3月上升到139,1948年3月達到301。更為嚴重的是,1948年3月,國立大學決定將學費提高3倍。受其影響,剛剛在1947年提高過學費的私立大學又將學費提高2倍[4],結果導致大批學生退學。例如在國立大學的萬名退學學生中,因學費問題退學學生在全部退學學生中的比例為40%[5]42。各大學學生自治會召集學生大會,反對強行提高學費,并動員學生拒絕交納學費。同年4月28日,“國學聯”召開全國代表者會議,要求撤回提高學費的決定,會后派代表與文部省交涉。社會黨出身的文部大臣拒絕了學生的要求,并暗示對那些拒絕交納學費的學生將給予處分。結果引起學生的極大憤怒,在6月23日到25日,共有114所大學舉行了24小時罷課活動,并在東京舉行游行示威。盡管幾乎沒有達到斗爭的目的,但學生們充分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和聯合斗爭的必要性。
1948年7月初,在早稻田大學召開“全國私立大學學生自治聯合會”籌備會議,有58所大學的200名代表參加。圍繞是否參加“全國國立、公立、私立大學及大學預備學校代表會議”發生對立,部分持反對態度的學校退出。盡管如此,“全國國立、公立、私立大學及大學預備學校代表會議”在7月初召開,共有138所大學的400名代表參加。會議就盡快組成作為學生統一戰線的全國學生自治聯合會達成共識,同時決定與工人、農民聯合斗爭,參加工會組織的共同斗爭委員會,并提出為復興教育而斗爭的方針。1948年9月18日到20日,“全學聯”召開成立大會。最后大會通過了反對殖民地式的教育體制、保障學問自由和學生生活等斗爭目標和口號,并選舉東京大學文學部學生武井昭夫為“全學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本部設在東京大學校內,當時有145所大學、30萬大學生參加[6]。面對學生運動的激烈以及“全學聯”的成立,政府在1948年10月8月向各國立大學發出《關于學生政治活動》的通知,宣稱“校內不允許政治活動”。與此同時,政府準備向國會提出旨在加強大學管理的《大學法案》。“全學聯”不僅針鋒相對地提出以排除行政干預為主要內容的大學法案,而且發動學生進行全國性罷課,東京30多所大學的15000名學生舉行示威游行,迫使政府放棄了將法案提交國會審議的計劃。
隨著冷戰國際體制的逐漸形成以及朝鮮半島局勢的日益緊張,美國的對日政策開始發生變化。早在1948年初,美國陸軍部長羅亞爾就在一次演講中聲稱“力求在日本確立穩定而強有力的自主的民主,使日本自立,”“在阻止將來有可能在遠東發生的集權主義戰爭方面發揮作用。”同年10月,美國國家安全保障委員會提出“美國對日政策的建議”,主張將占領政策從“非軍事化”轉為“經濟復興”,并在日本建立市場經濟體制。12月,美國政府提出“穩定經濟九原則”,以扶植日本經濟自立。另外,美國國務院政策制定委員會主席凱南也到日本,與麥克阿瑟商談對日政策的轉變。凱南回國后提出以復興經濟、防止共產主義化、盡快媾和、逐漸終止賠償、美軍長期駐扎沖繩等主要內容的對日政策報告書。在美國的支持下,吉田茂保守政府在1949年4月頒布《團體等限制令》,加強對政黨等政治團體的控制,并開始在國家公務員、國營企業內清洗共產黨員。同年7月4日美國獨立紀念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發表“日本是不敗的反共堡壘”,同時宣布解雇第一批國營鐵路工人。同年7月和8月連續出現了國鐵總裁不明死亡的“下山事件”、電車撞毀民宅致人傷亡的“三鷹事件”以及列車出軌致人傷亡的“松川事件”,吉田政權利用這些事件打擊日本共產黨和工會組織,導致工會組織及其會員急劇減少。同時,宣稱《團體等限制令》也適用于“全學聯”,并根據該法令解散了“朝鮮人聯盟”等4團體。為加強對學生運動的鎮壓,麥克阿瑟將盟軍總部民間情報教育局顧問易爾茲派往日本各大學,7月19日在新潟大學進行首次演講,呼吁將紅色教員和罷課學生趕出校園。各大學學生開展反對運動,擾亂演講會場,甚至將易爾茲趕下講臺。盡管如此,國立大學校長決定設立“研究委員會”,清除“紅色分子”。對此,“全學聯”提出“實施全面媾和、占領軍撤出日本、反對易爾茲演講、反對清除共產黨”等口號,并決定與工會組織一道行動,開展抗議活動。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遠東地區形勢進一步緊張化。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前夕,盟軍總部下令剝奪日本共產黨員的公職,戰爭爆發后又頒布命令,禁止日本共產黨出版發行其機關報《赤旗》。同年7月,創設7.5萬人規模的自衛隊前身——警察預備隊,隨后在新聞界、產業界清除共產黨。“全學聯”發表非常事態宣言,反對戰爭,反對清除共產黨,并舉行抵制考試、罷課等活動。各大學當局封鎖校園,壓制學生運動,并避免學生與警察的沖突,但反對活動持續不斷,結果文部大臣被迫宣布放棄在校園清除共產黨的措施[7]。
二、黨派矛盾與學生運動
如同前述,日本共產黨對學生組織及其運動具有較強的影響,例如“全學聯”首任中央執行委員長武井昭夫1946年在舊制高校讀書時加入日本共產黨。但隨著運動的發展,雙方出現矛盾并逐漸激化。其原因:一方面戰后初期盟軍總部下令釋放政治犯,以德田球一為首的日本共產黨領導人得以出獄,因而將占領軍看作“解放軍”,主張“占領下和平革命”,因而對“全學聯”領導下的罷課、游行示威等學生運動持批評態度,甚至下令解散大學中黨的基層組織,禁止“全學聯”發動學生舉行總罷課,并指責“全學聯”領導者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另一方面,日本共產黨認為學生僅僅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學生運動不是革命斗爭或階級斗爭,只是為革命斗爭創造條件,因此,學生運動應將重點放在參加地域性的人民斗爭上。與其相反,“全學聯”領導者認為隨著大學生數量的迅速增加,已經成為社會的一個階層,學生運動本身能夠構成反體制運動,是推動革命的先驅性力量。由于意見的對立,“全學聯”內部也出現分裂,支持共產黨的大學自治會拒絕執行“全學聯”的指令,導致1949年10月20日總罷課的計劃沒有能夠實現。
1950年1月7日,設在莫斯科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指揮部——共產黨及工人黨情報局發表《關于日本形勢》的文章,全面批評日本共產黨主流派的斗爭路線。認為在美國對日本實施的是殖民統治,而且準備在遠東地區發動新的戰爭,因此,“和平革命”完全是一種幻想。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政治局所感》進行反駁,但內部發生分裂,以宮本顯治為首的主張接受批評者被稱為“國際派”,以德田球一為首的反對批評者被稱為“所感派”。1951年2月,占主流的“所感派”轉而接受共產黨及工人黨情報局的批評,將“國際派”開除出黨,其中包括武井昭夫委員長等“全學聯”領導者。被開除的學生在1951年11月組成“反戰學生同盟”(簡稱“反戰學同”),1958年5月改組為“社會主義學生同盟”。
1951年9月,舊金山對日媾和會議召開,日本與部分國家簽訂和平條約,并與美國簽訂安全保障條約。同年10月,日本共產黨召開第5屆全國協議會,通過了新綱領,認為日本革命的性質是從美國統治之下解放出來的“殖民地革命”、“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因而在農村開展游擊戰是最重要的斗爭方式。根據這種認識,日本共產黨組織“山村工作隊”、“中核自衛隊”,并勸說學生離開校園前往農村開展武裝斗爭。“全學聯”領導下的學生運動也帶上暴力斗爭的色彩,在集會、罷課活動中頻繁與警察沖突。此時出現的京大天皇事件、澀谷事件、東大波波羅事件進一步激發了學生們的斗爭意志。
1951年11月12日,天皇訪問京都大學,約200名學生準備了追究天皇戰爭責任的質問書。警方出動500名警察護衛天皇,大學當局要求解散自治會,并處分了8名學生,即所謂的“京大天皇事件”[5]157;1952年1月17日,東京大學駒場校園學生自治會準備在澀谷站前廣場召集反對重新軍備講演會,但是警方沒有批準其申請,結果學生發起抗議活動,并與警察發生沖突,多名學生被捕,即所謂的“澀谷事件”;1952年2月20日,東京大學學生劇團“波波羅”上演描述“松川事件”的戲劇,發現會場內有3名便衣警察,并對他們進行拷問。第二天警方進校園逮捕兩名學生,并向抗議集會的學生開槍,即所謂的“東大波波羅事件”。在剛剛結束占領的1952年5月1日,為抗議片面媾和、反對政府制定防止破壞活動法案,在日本共產黨的影響下,“全學聯”的學生、工人、在日朝鮮人等強行進入禁止使用的皇居前廣場,與警察發生沖突。警察使用催淚彈、對空鳴槍等方式驅散人群,在沖突中有1200多人被捕,幾十人受傷,兩人死亡,其中一人是法政大學學生近藤居士,為戰后學生運動中最初的犧牲者。該事件被稱為“血腥的五一節事件”。其后,陸續發生了東京巖之坂派出所被襲、東京新宿站東口火焰瓶、大阪吹田枚方等暴力事件,結果反而推動國會通過了鎮壓反體制運動的《防止破壞活動法》。
1952年6月,“全學聯”召開第5屆大會,武井昭夫等27名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被撤職,組成以玉井仁為委員長的新領導機構,決定執行共產黨決定的武裝斗爭路線。同時發生了主流派對非主流派的私刑事件,即支持日本共產黨“所感派”的“全學聯”領導機構認為支持日本共產黨“國際派”的反帝學園是美國情報局間諜,將10多名反帝學園的成員軟禁在密室中進行拷問。在此期間,不少的激進派學生離開校園,在農村發動群眾進行反體制暴力斗爭。另一方面,即使在結束占領后,根據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及其行政協定,美國在日本本土仍有7000多所基地,這些基地不僅圈占土地,而且對當地居民的生活也形成騷擾,因而引起當地居民的強烈反對,并成為學生斗爭的重要目標之一。
由于進行激進的武裝斗爭,日本共產黨在1952年10月舉行的大選中喪失了眾議院的全部席位,得票數也從上一次選舉的298萬張選票下降到89萬張。1953年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去世,國際共產黨主義運動出現向“和平共處”調整路線的趨勢,因而日本共產黨及其影響下的“全學聯”也開始摸索新的斗爭方式。1954年6月,“全學聯”第7屆中央委員會決定放棄政治斗爭,為“生活與和平”組織學生運動。1955年7月,日本共產黨召開第六屆全國協議會,決定終止武裝斗爭路線,主流派與非主流派和解,確立以宮本顯治為首的集體領導體制。日本共產黨中央機構的政策轉變對學生活動家帶來沉重打擊,無法重新適應校園生活,并引起不少學生組織紛紛解體。正因如此,50年代上半期,“全學聯”及其領導的學生運動處在低潮時期。
50年代后半期學生運動再度出現高潮,其背景是學生反對提高學費運動與反對美軍基地運動。1956年2月,為阻止國立大學提高學費,包括2203名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學生在內的4000名東京大學生舉行國會請愿游行,此后又爆發了反對核武器實驗、反對小選區制及反對教育有關法案的大規模學生運動,各地均出現了罷課、示威游行。在此背景下,同年6月召開的“全學聯”第9屆大會,進行自我批判,決定重新實施大眾性政治斗爭,并重視與國民各個階層的聯合,發揮先驅性作用。此次大會選舉香山健一為“全學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新委員長。東京都西部的砂川町居民從1955年起結成同盟反對美軍基地。1956年秋天,政府強行進行土地測量。為支援當地居民,“全學聯”動員各地3000名大學生,與農民、工人一道進行斗爭,并與警察發生沖突。堅決的抵抗終于迫使岸信介內閣發表中止測量的聲明,是1950年反清除共產黨員運動來的首次勝利,但內部卻存在不同的意見。1957年,“全學聯”發動學生進行“反對核武器實驗”、“反對文部省實施教師勤務評定”等斗爭,特別是在同年5月舉行的反對核武器實驗集會中,全日本共有170所大學、380個學生自治會、35萬大學生參加,僅在東京就有25000人參加。
1956年發生了蘇聯對斯大林的批判以及蘇聯出動軍隊鎮壓匈牙利騷亂的事件,日本共產黨中央領導機構表示支持。日本的左翼勢力分裂為共產黨路線、結構改造路線、反共產黨路線三派。本來就對日本共產黨中央領導機構不滿的學生進一步增加了離心傾向,“全學聯”主流派將蘇聯和日本共產黨看作斯大林主義、官僚主義,主張實施“反帝反斯大林”的斗爭路線,激化了雙方的矛盾。1958年5月底,“全學聯”召開第11屆大會,對前一階段斗爭進行總結,并決定反帝及擁護和平斗爭路線。為加強對“全學聯”的影響,日本共產黨中央機構召集“全學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黨員,但雙方發生沖突,“全學聯”做出“不信任日本共產黨中央機構”的決議。對此,日本共產黨中央機構宣布其決議無效,并對香山健一等72名“全學聯”領導機構成員進行處分。“全學聯”在發動學生參加了反對《警察官職務法修正案》的斗爭并迫使政府收回其法案后,同年12月,被日本共產黨除名的香山健一、島成郎等學生黨員組成“共產主義者同盟”(簡稱“共產同”);另外還有一個反對日本共產黨的派系——1957年1月組成的“日本托洛茨基主義者聯盟”,同年12月改組為“革命共產主義者同盟”(簡稱“革共同”),在戰后日本學生運動史上被稱為“新左翼”[8]41。1958年11月,“全學聯”召開第13屆大會,“革共同”掌握主導權,選舉東京大學助手鹽川喜信為新的委員長,“全學聯”與日本共產黨脫離直接的關系。“共產同”派系反對一國社會主義革命、反對和平共處、議會主義、二元革命,主張世界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暴力革命、一元革命,是一個激進的學生組織,因而被日本共產黨指責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共產同”在大學生自治會中的影響逐漸擴大,因而在1959年6月召開的“全學聯”第14屆大會上,掌握主導權,主要領導職務均被其占據,包括當選為新委員長的唐牛健太郎[9]。“共產同”勢力急劇增長的背景是政府準備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而引起的國民反對。
1957年6月,岸信介首相訪問美國,并發表了修改日美安全條約等內容的“日美新時代”聲明。1958年9月,藤山愛一郎外務大臣訪問美國,開始具體內容的談判。對此,社會黨、“總評”工會等134個社會團體在1959年3月組成“阻止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國民會議”(簡稱“國民會議”),開展反對運動,日本共產黨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該組織。“共產同”主導下的“全學聯”決定參加“國民會議”組織的統一運動,并提出以實力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條約,打倒岸信介內閣。在同年10月30日舉行的統一行動中,有90所大學、35萬名學生參加游行示威。在11月27日舉行的統一行動中,全國有200萬工會組織成員參加罷工,法政大學、東京大學的學生與工人一道沖進國會。第二天“全學聯”5名干部被捕,社會黨、總評工會、日本共產黨均對沖擊國會表示遺憾。1960年日美安全保障新條約進入簽署階段后,“全學聯”的斗爭進一步激化。同年1月16日,岸信介首相由羽田機場前往美國簽署新條約,盡管“國民會議”中止在機場舉行的示威游行,但“全學聯”卻實施緊急動員,約700名學生占據機場大廳、食堂,并與警察發生沖突,唐牛健太郎委員長等80人被捕。
在國會審議日美安保新條約過程中,各界群眾不斷舉行反對活動。4月26日,全日本舉行總罷工,有82所大學的25萬學生參加,東京有1萬人聚集在國會前靜坐。盡管“全學聯”主流派、非主流派分別行動,但兩派均連日在國會周圍舉行抗議活動。6月3日,“全學聯”的9000名學生沖擊了首相官邸。6月10日,為美國總統艾森毫威爾訪問日本做準備的總統秘書哈格蒂在羽田機場被“全學聯”非主流和工人包圍,最后出動直升飛機才將其解救出來。6月15日,“國民會議”舉行第18次統一行動,全日本有580萬人參加。東京有11萬人在國會周圍舉行游行示威。“全學聯”決定在國會院內舉行抗議集會,17000人的隊伍集中在國會周圍,其中有1500人突破警察防衛圈進入國會院內。警察用警棍、水槍、催淚彈阻止學生,學生用石塊還擊。沖突中的負傷者72人,被捕者167人,東京大學文學部三年級學生樺美智子死亡。盡管未能阻止日美新安保條約的成立,但“全學聯”領導下的學生抗議活動不僅使政府終止了美國總統的訪日計劃,而且也迫使岸信介首相辭職,在戰后學生運動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三、組織分裂下的學生運動
如同前述,在“全學聯”內部,既有擁護日本共產黨的派系(因日本共產黨本部在東京代代木,所以也稱“代代木派”),也有反對日本共產黨的派系(即“反代代木派”)。在“反代代木派”中,又分為“共產同派”和“革共同派”,前者重視行動,后者重視組織。在“革共同派”中,又分為主流派和“第四國際派”,因而在1959年6月被“共產同派”掌握了“全學聯”的主導權。在反對日美新安全保障條約的斗爭中,“共產同派”利用斗爭不積極、未交納會費等借口罷免了“代代木派”和“革共同派”的代表權,進一步鞏固了主導權。但共產黨反主流派組成“東京都自治會聯絡會議”,對抗“共產同派”領導下的“全學聯”,學生組織出現分裂。
1960年7月初,“全學聯”召開第16屆大會。圍繞“共產同派”政治局提出“安保斗爭”沒有獲得勝利的總結,中央領導機構分裂為“戰旗派”、“無產階級通訊派”、“革命通告派”。但“革命通告派”很快消失,“戰旗派”和“無產階級通訊派”也很快發生分裂,大多與“革共同派”合并,因此,“共產同派”結成兩年后解體。其解體的原因既與該派系過激的斗爭方式有關,也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關,即高速增長帶來的消費主義、享受主義改變了青年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與此同時,日本共產黨所屬學生組織建立“全國學生自治會聯絡會議”。
1961年4月,“全學聯”召開第27屆中央委員會,組成了以“革共同派”所屬學生組織——“日本馬克思主義學生同盟”(簡稱“馬學同”)為中心的領導機構。當時自民黨、社會黨、民社黨準備提出針對恐怖事件的法案,但在是否應限制社會團體等具體內容上社會黨與自民黨、民社黨產生對立。自民、民社兩黨向國會提出《防止政治暴力行為法案》,社會黨、總評工會反對該法案,并發動工人舉行抗議活動。“全學聯”也表示反對,并發表“緊急事態宣言”,呼吁學生進行斗爭。在國會討論該法案時,學生不斷舉行游行示威,大約有60名學生被捕。盡管法案通過了眾議院的審議,但最后自民黨放棄了該法案。1961年7月,“全學聯”召開第17屆大會。在大會之前,反“馬學同派”的“社會主義學生同盟”(簡稱“社學同”,由“共產同”成員組成)、“革共同關西派”、“社會主義青年同盟”(簡稱“社青同”,為社會黨的青年組織)反對“革共同”及“馬共同”的宗派主義及意識形態化的學生運動,主張聯合所有學生進行斗爭。三派學生組織在東京飯田橋的鶴屋旅館開會商討對策,因而被稱為“鶴屋聯合派”[8]52。
“全學聯”第17屆大會召開后,主流派與反主流三派發生激烈沖突,甚至出現暴力事件,“馬學同”成員從附近木材商店上取得木棍,將反主流三派驅逐出會場,是學生運動中最初的武斗。當時指導武斗的是“全學聯”書記長清水丈夫,因其筆名為岡田新,所以木棍式武斗被稱為“岡田式暴力沖突”。“馬學同”單獨召集會議,原“共產同”成員北小路敏成為新的委員長,并提出“反帝國主義、反斯大林主義”的激進運動方針。反主流最大派系“社學同”聯合其他反主流派系組成“全學聯再建協議會”,結果“全學聯”分裂為“馬學同全學聯”、“反馬學同三派聯合”、“代代木派”三大組織。盡管處在分裂狀態,但學生運動仍在繼續發展。1962年5月,池田勇人自民黨內閣準備制定“大學管理法”。同年11月,“三派聯合”發動學生進行全國性罷課,并以東京大學駒場校園學生為主,匯集2500名學生游行到文部省抗議,有5名學生被捕。其后,“三派聯合”與“馬學同”聯合召開“東京都統一學生自治會代表者會議”,并在東京大學校園舉行了6000人的統一罷課行動。在各界的強烈反對下,池田內閣不得不在1963年1月宣布放棄提出“大學管理法”的設想。1963年到1965年,學生運動的主要斗爭是反對簽訂日韓條約。特別是在1965年國會審議日韓條約時,為阻止外務大臣椎名訪問韓國,東京大學、法政大學、早稻田大學的“馬學同”派學生600人在羽田機場舉行示威游行。在國會批準日韓條約的10月底11月初,各派學生均舉行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并在國會周圍靜坐示威。在此期間,各派學生還舉行了反對美國“北極星號”核潛艇進入日本港口的抗議活動。
1963年4月,“革共同”分裂成主張建立革命黨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派”(簡稱“革馬派”)和重視群眾斗爭的“中核派”。日本共產黨所屬學生組織“民主青年同盟”在1962年8月建立“保衛和平及民主主義全國學生會議”,稱為“民青系全學聯”。1966年2月,原“共產同”的部分學生建立新組織,稱“第二共產同”,并在同年年底與從社會黨所屬學生組織分裂出來的“社會主義青年同盟”(簡稱“社青同”)、“中核派”與部分原“共產同”部分學生組織組成的“社會主義學生同盟”(簡稱“社學同”)聯合組成“三派全學聯”(后來“中核派”參加進來,所以亦稱“四派全學聯”,“中核派”成員秋山勝行任委員長)。至此,存在三個“全學聯”,即“革馬派全學聯”、“民青系全學聯”和“三派全學聯”,其中“三派全學聯”影響較大。
1967年2月到7月,“三派全學聯”動員學生參加了“第二次砂川斗爭”反對政府擴大基地面積;同年10月8日,為阻止佐藤榮作首相訪問越南,“三派全學聯”指揮學生前往羽田機場,頭帶安全帽、手持木棍的學生與防爆警察發生沖突,導致京都大學學生山崎博昭死亡,受傷者600余人,被捕者58人,為“第一次羽田斗爭”;同年11月12日,為阻止佐藤首相訪問美國,“三派全學聯”3000人在羽田機場附近與防暴警察發生沖突,為“第二次羽田斗爭”。此次事件表明學生運動成為獨立的斗爭力量,而且開始利用頭盔、四棱木棍進行實力沖突。
為阻止美國核動力航空母艦“企業號”進入長崎縣佐世保港口,以“三派全學聯”為中心的各派學生組織與工會組織、市民團體從1968年1月17日到23日在佐世保與防暴警察連續發生沖突。參加斗爭者共有65000人,其中學生4000人;負傷者519人,其中學生229人;被捕者69人,其中學生64人。同年2月到3月,“三派全學聯”與千葉縣成田地區的農民一道反對成田新機場建設,并與防暴警察發生大規模沖突,有1000多人受傷,185人被捕;同年3月,各派學生組織與市民一道反對在王子地區建立美軍戰地醫院,并與防暴警察發生沖突,158人被捕;同年4月28日,東京都學生組織與市民利用“沖繩日”進行集會,并演變成騷亂,與防暴警察發生沖突;同年10月21日“國際反戰日”,學生組織在東京舉行集會,并在新宿地區爆發大規模騷亂,電車、派出所等被燒毀,警方派出大批防暴警察加以鎮壓,450學生因騷亂罪被捕[5]297。
在上述斗爭過程中,學生組織也出現新一輪的分化組合。曾與“三派全學聯”聯合斗爭的“中核派”在1968年7月組成單獨的“全學聯”,反“中核派”的各學生組織聯合組成“反帝全學聯”,但因內部矛盾激化而解體,其中原屬“社青同”的“解放派”單獨組成“全學聯”。至此,共存在共產黨民青派、中核派、革馬派、解放派等4個“全學聯”,其影響力也大為降低。1969年10月,創價學會學生部建立“新學生同盟”(簡稱“新學同”),擁有315所大學的27萬名成員,聲稱走“第三條道路”[10],但未發揮較大作用。實際上,學生運動衰退的最大原因是隨著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6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國民的物質生活明顯得到提高,50年代末以洗衣機、電冰箱、黑白電視機為中心的“消費革命”及60年代中期以汽車、空調、彩色電視機為中心的“消費革命”將大眾的注意力轉移到經濟領域。因此,學生組織及其以社會斗爭為主要內容的運動逐漸失去社會基礎,不可避免地走向低潮。
[1][日]菅孝行,貝原浩.全學聯[M].東京:現代書館,1982:19.
[2][日]高木正幸.全學連と全共闘[M].東京:講談社現代新書,1985:11.
[3][日]兵本達吉.學生運動の歴史とその終焉[J].正論:203.
[4][日]社會問題研究會.全學聯各派—學生運動事典[M].東京:雙葉社,1969:22.
[5][日]山中明.戰后學生運動史[M].東京:群出版,1981:42.
[6][日]本橋信宏.「全學聯」研究:革命闘爭史と今後の挑戦[M].東京:青年書館,1985:13.
[7][日]秋山勝行,青木忠.全學連は何を考えるか[M].東京:自由國民社,1968:220.
[8][日]高木正幸.新左翼三十年史[M].東京:土曜美術社,1988:41.
[9][日]大野明男.全學聯—其行動與理論[M].東京:講談社,1968:70.
[10][日]津山巖.第三個全學聯[M].東京:全貌社,1969:25.
Zengakuren and Students’Movement in Postwar Japan
WANG Xin-sheng
(History Department,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s such as the tradition of prewar students’movement,the demilitarization and democratic reform by GHQ in Japan,the active movements by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which was legalized after the war,the difficulties in life and the tuition rising,students from a number of universities founded a students organization: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Students’Self-Government Associations,which is shortened as Zengakuren,and initiated large-scale social movements.Though there was a split in it due to the contradictories among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and groups,the organization took the lead in antiestablishment movements,for instance,the movements against the amendment of the Japan-U.S.Security Treaty and U.S.military bases in Japan.
Japan;postwar;Zengakuren;Students’Movement
K313.5
A
1008-2395(2012)01-0001-07
2011-12-11
基金課題:日本住友財團資助項目
王新生(1958-),男,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歷史學博士,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日本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