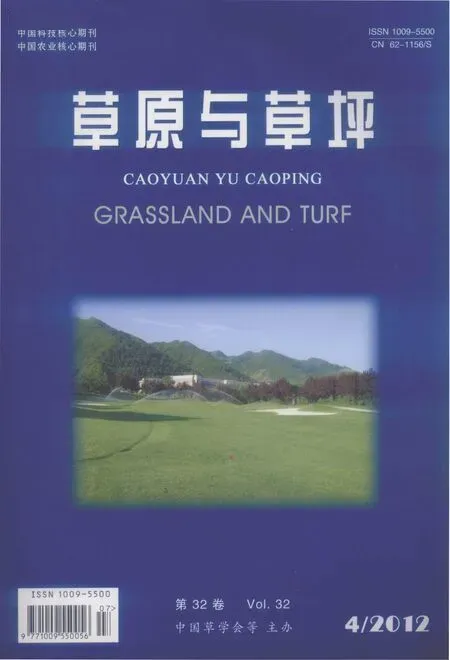定西黃土丘陵溝壑區水土流失研究進展
馬海霞
(定西市水土保持科學研究所,甘肅 定西 743000)
自20世紀50年代,我國就開始探討有關小流域的有效治理方法和途徑,是世界上較早開展小流域治理的國家之一。在總結以往防治水土流失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我國于1980年提出了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的思想,并在全國范圍內設點推廣以小流域為單元進行綜合治理的水土保持工作。20世紀末以來,我國實施了大規模的生態恢復工程,小流域綜合治理從此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1]。黃土丘陵溝壑區是我國生態環境脆弱、貧困人口集中分布的主要地區之一,水土流失也是該地區生態環境惡化的主要原因,同時,是導致當地群眾貧困落后的主要根源。我國水土保持的長期經驗證明,在半干旱黃土丘陵溝壑區以小流域為單位的治理是防治水土流失的最佳形式[2]。開展小流域治理,從生態經濟學的觀點看,既是解決水土流失的主要途經,也是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的好辦法。伴隨著小流域水土流失綜合治理實踐的不斷深入,國內一些學者對其治理模式、措施,尤其是效益評價等方面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在綜合相關文獻的基礎上,回顧了定西市安家溝、九華溝和高泉溝小流域水土流失綜合治理模式、措施等方面的相關研究,以期對后續研究有所參考和啟示。
定西市位于甘肅省中部,區內大部分屬干旱黃土低山丘陵溝壑區,氣候類型為典型的大陸性季風氣候。境內河流基本上都是洪水季節性河流,主要有西鞏河、東河、西河、稱鉤河等。年均降水量只有420mm,且時空分布極不平衡,75%以上的降水集中在7~9月,而且多以暴雨形式出現,常形成暴雨徑流,導致嚴重的水土流失,加之降水與農作物需水供需錯位等,致使定西地區水資源嚴重缺乏。通過小流域綜合治理,調控徑流,充分利用水資源勢在必行。
定西市土壤主要是黃土母質基礎上發育起來的灰鈣土和鹽漬土,流域內自然植被覆蓋度低,自然覆蓋度陽坡在25%~35%,陰坡及部分梁頂在50%~60%。喬木主要有油松(Pinus tabuliformis)、側柏(Platycladus orientalis)、山杏(Prunus armeniaca)等,灌木有沙棘(Hippophae rhamnoides)、檸條(Caragana ssp.),草本植物為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紅豆草(Onobrychis vichfolia)、針茅(Stipa bungeana)、百里香(Thmus mandschuricus)。主要的農作物有馬鈴薯(Solanum tuberosum)、春小麥(Triticum aestivum cv.Leguan)、玉米(Zea mays)、胡麻(Linum usitattissimum)及豌豆(Caragana kansuensis)等。
1 水土流失研究
1.1 安家溝流域水土流失研究進展
通過對安家溝流域15個徑流小區1986~1999年的水文監測資料進行總結得出,相同坡度等級下5種土地利用類型坡地的單位面積年產流量之間及單位面積年產沙量之間都存在顯著差異,大小順序均表現為:坡耕地>人工草地>喬木林地>自然草地>灌木林地[3]。進一步研究得出,不同土地利用類型坡地徑流量和侵蝕量與降水特征值(雨量、雨強、歷時等)和下墊面因子(坡度、土地利用、前期土壤水分狀況等)關系密切。抵抗徑流侵蝕的能力依次為沙棘>荒草>油松>苜蓿>小麥。多年生植被(如沙棘、油松等)的徑流侵蝕隨生長年數增長而減弱,以生長初期最為嚴重,隨后逐漸減弱并穩定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因而認為,不同土地利用類型下的徑流侵蝕不僅取決于該植被類型,更重要的是決定于該植被所處的生長發育階段[4,5]。前人通過對安家溝流域不同降水強度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區組實驗,研究得出不同雨強平均徑流系數為林地>耕地>栽培草地>天然草地,進一步得出在黃土丘陵生態脆弱區草地具有良好的降水蓄積效果,同時表明林冠層、灌木層和枯枝落葉層對降水的截留、阻滯和削弱具有顯著功效[6]。且對溝坡水土流失治理的研究得出,溝坡生態修復可采用反坡臺、雨鱗坑和“上壩下塘”等工程措施,根據溝坡環境條件,植被建設應先恢復到與水熱條件相符的潛在景觀,其植被可先以灌木為主。在該地區可以采用甘蒙檉柳、甘蒙檉柳+白刺、楊樹和楊樹+沙棘等幾種植被恢復模式[7]。
在小流域治理模式上,安家溝流域采用了生態經濟型治理模式(林農復合經營模式、雨水集流庭院經濟復合經營模式)和水土流失防治型治理模式(生物措、工程措施、生物工程相結合),從梁峁頂到溝底層層攔蓄天然降水,使水土流失的危害減少到最小[8]。蔡國軍等[8],孫飛達等[10]針對安家溝流域的自然特點,提煉出了3種典型的農林復合模式,即:林-糧復合經營模式、林-草-畜復合經營模式和庭院經濟復合經營模式。分別分析了3種模式的組成、結構及功能,對3種模式的經濟效益進行了評價。結果表明:與坡地農田系統相比,3種典型的農林復合模式均具有較高的經濟效益,其中,庭院經濟復合經營模式效益最大,林-草-畜復合經營模式效益次之,林-糧復合經營模式效益最低,但均高于對照模式。結合不同農林復合生態系統的主要生態功能,進一步組合為5個比較典型的農林復合優化模式:陡坡地水土保持林模式、緩坡地退耕還林(草)模式、梯田地農林復舍模式、房前屋后雨水集流庭院經濟模式,侵蝕溝水土保持林模式。在實際生產中,應結合具體情況,營建相應的模式,以追求最大的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
1.2 九華溝、高泉溝流域水土流失研究進展
九華溝流域的水土保持綜合治理開發,采取治坡與治溝結合,工程措施與植物措施對位配置,將導致水土流失的主導因子即降水徑流,通過徑流調控體系和徑流開發利用體系變為有效水資源,變害為利,實現水土資源的科學合理利用[11]。經過5年的綜合治理開發,該流域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控制,全流域內綜合治理面積由37.3km2增加到71.6km2,治理程度由44.9%提高到86.3%,年平均徑流模數由17 000m3/km2降低到 1 557.28m3/km2,土 壤 侵 蝕 模 數 由 原 來 的5 460t/km2減少到915t/km2,減沙效益達83.06%,林草覆蓋率由24.0%提高到57.1%,流域年總收入由502.65萬元增加到1 404.64萬元,農民人均年純收入由757元增加到1 486元,人均年產糧由427kg增加到654kg。徑流調控技術在農業總產值的總增量中,科技進步貢獻率占56.71%,對流域內農民的脫貧致富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12-14]。
高泉小流域,以“全部降雨就地入滲攔蓄”為指導思想,坡耕地修建水平梯田,使降水就地攔蓄入滲,改善糧油作物的生產環境;村莊道路以營造小型攔水工程為主,發展“四旁”林果業,改善人們的生活環境,收到日益顯著的社會效益、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15]。在對高泉溝流域1988~1995年8年31個觀測小區定位觀測的63次產流資料模擬分析得出,影響小區產流量的主導因子是小區水平投影面積、坡度、產流雨量、降水總量,以及土壤和植被類型[16]。且董榮萬等[17]通過在高泉溝小流域建立的水土流失監測網絡,系統研究了小流域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與土壤侵蝕的關系,小流域水土流失時空變化規律及小流域水流泥沙概念性耦合模型,揭示了定西黃土丘陵溝壑區土壤侵蝕規律,并建立了坡面土壤侵蝕數學模型。得出,人為因素減水減沙的貢獻率分別為79.11%和85.69%,由降水減少引起的減水減沙的貢獻率分別為20.89%和14.30%;并應用水流泥沙概念性耦合模型,對“兩期”治理效果進行了分析評價,探索了模型法評估水土保持減水減沙總效果的途徑。朱興平[18]以高泉溝流域為試驗區,對黃丘五副區小流域水土流失的時空變化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小流域水土流失的時段分布不均勻,空間差異懸殊。從時間上看,一次降水的水土流失在不同產流時段上差異較大,徑流量、輸沙量主要集中于某一產流時段內;年內各月間的水土流失在數量上變化較大,5~8月分別集中了年徑流總量、輸沙總量的90.95%、97.79%;年際間的水土流失量各異,多年的水土流失量大小主要取決于暴雨次數多、雨強大的個別年份。從空間上看,梁峁坡面為主要產流區,溝谷為主要產沙區,溝坡溝底難利用地侵蝕最嚴重,梁峁坡面的產流量對溝谷產沙量的影響極顯著。
2 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思考與展望
通過對定西黃土丘陵溝壑區小流域水土流失研究進行綜述,得出幾點思考與展望:
(1)小流域治理的實踐證明,生態環境建設是基礎,水土保持是干旱貧困山區脫貧致富的戰略抉擇;經濟發展是保證,在生態環境治理的同時,進行綜合開發,發展生態農業,是促進生態經濟系統良性循環、實現脫貧致富的重要途徑。
(2)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應具有多樣化。不同類型區、同類型區不同流域由于自然、社會和經濟條件相差很大,因此治理模式不盡相同。在治理模式的選擇時,不能千篇一律,應按因地制宜、因害設防、對位配置的原則來確定水土流失治理模式。
(3)生態清潔型小流域建設技術,是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建設對水土保持技術的新的需求,是未來小流域治理發展的主要方向。生態清潔型小流域是水土保持技術外延的拓展、內涵的拓深,是生態水土保持的具體的應用技術。
[1] 李巖,王立群.小流域綜合治理及其效益評價研究進展[J].北京林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7(3):62-66.
[2] 林積泉,王伯鐸,馬俊杰,等.小流域治理環境質量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研究[J].水土保持研究,2005,12(1):68-71.
[3] 陳鵬飛,陳麗華,王宇,等.黃土丘陵溝壑區不同土地利用類型對坡地產流、產沙的影響[J].生態與農村環境學報,2010,26(3):199-204.
[4] 衛偉,陳利頂,傅伯杰,等.半干旱黃土丘陵溝壑區降水特征值和下墊面因子影響下的水土流失規律[J].生態學報,2006,26(11):3847-3853.
[5] 衛偉,陳利頂,傅伯杰,等.黃土丘陵區不同降雨格局下土地利用的水土流失效應[J].水土保持通報,2006,26(6):19-23.
[6] 李廣,黃高寶.雨強和土地利用對黃土丘陵區徑流系數及蓄積系數的影響[J].生態學雜志,2009,28(10):2014-2019.
[7] 黃奕龍,陳利頂,傅伯杰,等.黃土丘陵小流域溝坡水熱條件及其生態修復初探[J].自然資源學報,2004,19(2):183-189.
[8] 柴春山.半干旱黃土丘陵溝壑區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模式篩選[J].防護林科技,2006(5):38-40.
[9] 蔡國軍,張仁陟,莫保儒,等.定西安家溝流域3種典型農林復合模式的評價研究[J].水土保持研究,2008,15(5):120-124.
[10] 孫飛達,于洪波,陳文業.安家溝流域農林草復合生態系統類型及模式優化設計[J].草業科學,2009,26(9):190-194.
[11] 劉儉.希望之路-水土保持生態環境建設的探索與實踐[M].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1.
[12] 王海英,劉桂環,董鎖成.黃土高原丘陵溝壑區小流域生態環境綜合治理開發模式研究—以甘肅省定西地區九華溝流域為例[J].自然資源學報,2004,19(2):207-216.
[13] 成昌軍.九華溝流域綜合治理開發途徑與模式[J].中國水土保持,2002(11):38-39.
[14] 趙克榮,陳麗華,肖洋.黃土區徑流調控技術體系[J].中國水土保持科學,2008(4):97-102.
[15] 韓靖國.高泉小流域的環境治理[J].中國水土保持,1992(2):46-48.
[16] 梁天剛,沈正虎,戴若蘭,等.集水區徑流資源空間變化的模擬與分析[J].蘭州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99,35(4):83-89.
[17] 董榮萬,朱興平,何增化,等.定西黃土丘陵溝壑區土壤侵蝕規律研究[J].水土保持通報,1998,18(3):1-9.
[18] 朱興平.黃丘五副區小流域水土流失的時空變化[J].中國水土保持,1995(12):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