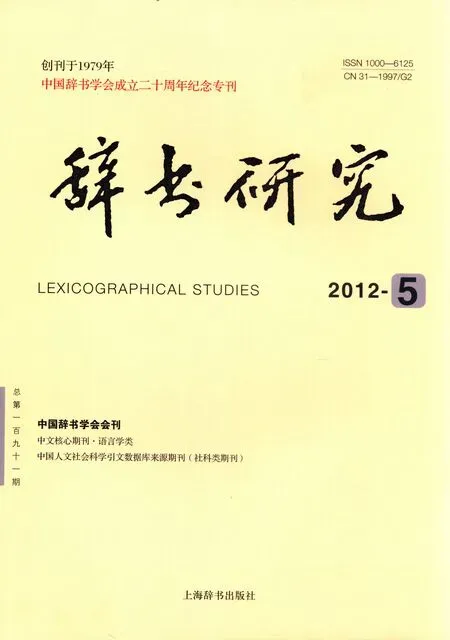打假批劣顯精神
徐慶凱
(上海辭書出版社 上海 200040)
在中國辭書學會的二十年中,我切身體會到,這個學會的鮮明特點是,在組織學術研究、開展學術討論、加強學科建設的同時,十分關注、積極參與凈化辭書園地和提高辭書質量的實際工作,做了揭批偽劣辭書和舉辦中國辭書獎這兩大實事,從而對中國的辭書事業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貢獻。
1992年10月,我赴京參加中國辭書學會成立大會。在分組討論時,我揭批了王同億主編的《語言大典》抄襲剽竊、胡編亂造等嚴重錯誤,希望學會關注這類現象,為凈化辭書園地盡一份力。此事引起了與會者的共鳴和學會領導的重視。學會第一副會長巢峰在大會的閉幕詞中對辭書界的打假批劣發表了看法,主要內容如下:
現在辭書界剽竊成風,差錯成風,拼湊成風。《辭海》、《現代漢語詞典》被人抄襲不計其數。辭書編纂隊伍中出現了一些掮客,他們把編辭書當作撈取政治資本和金錢的手段,不管坑害廣大讀者與否。有一本《語言大典》,公然把《辭海》中的《中國歷史紀年表》和《中國少數民族分布簡表》兩個附錄加以影印,當作自己的附錄。這本書許多條目照搬《現代漢語詞典》。我社有的同志翻閱《語言大典》,發現其收詞和釋義簡直不可思議。例如在“一”字頭下,大部分詞目是任意湊合的自由詞組,既無查閱的必要,也無查閱的可能,根本不成其為詞目,如“一袋”、“一盤”、“一箱”、“一茶杯”、“一個鉛字”、“一段臺詞”、“一截粗木頭”、“一套房間”、“一聲喊叫”、“一次又一次的損失”、“一天干兩天的活”、“一股勁兒地嗚嘟嗚嘟吹奏”等等。釋義則如:“一胖一瘦”釋為“一個胖的一個瘦的”;“一直被人叫著”釋為“在一段時間中保持粘著和固定,看來像由于粘合力或粘著力或粘住”;在“一部分”這一條中甚至出現“作為國家政策的一部分的消滅宗教”這樣的例句。這樣的詞典,怎么能不加批判、抵制而任其流傳?我以為我們的辭書編纂和出版中有一種墮落行為。評劣就是要與辭書編纂與出版中的墮落現象作斗爭。我們要促使辭書事業在健康的道路上發展,就一定要做好打假打劣的工作。
這一段話,義正詞嚴,吹響了中國辭書學會打假批劣的號角,拉開了其后中國辭書界“三大戰役”的序幕(見2003年12月17日《中華讀書報》載巢峰的《中國辭書界的“三大戰役”》一文)。
三大戰役
返滬后,我進一步檢查了《語言大典》,又發現了大量觸目驚心的問題,于是寫成《如此詞典,匪夷所思——評〈語言大典〉》一文在《辭書研究》1993年第3期上發表。刊出前,《文匯讀書周報》根據該文校樣于5月15日以頭版頭條發表《〈語言大典〉竟是“謬誤大全”》的報道,披露了該文的要點。5月22日該報又以頭版頭條發表《杜絕謬種》的報道,說該報上期揭批《語言大典》的報道“在讀書界產生了強烈的反響”。
此后,于光遠、曾彥修、巢峰、王寧等知名人士相繼發表了批評《語言大典》的文章。批評的對象陸續擴展到王同億主編的其他詞典,如《現代漢語大詞典》、《新現代漢語詞典》、《新編新華字典》、《英漢辭海》、《英漢科技詞天》、《法漢科技詞匯大全》、《俄漢科技詞匯大全》等。
在開展批評的同時,由于《新現代漢語詞典》和《現代漢語大詞典》大量抄襲《現代漢語詞典》和《古今漢語實用詞典》,又由于《語言大典》抄襲《辭海》中的《中國歷史紀年表》和《中國少數民族分布簡表》兩個附錄(共二十多萬字),《語言大典》和《現代漢語大詞典》大量抄襲《中國成語大辭典》,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商務印書館、辭海編輯委員會、上海辭書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等五個單位和部分作者于1993年7月至9月先后對王同億和海南出版社提起訴訟。這五起案件經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分別審理后判決被告敗訴。被告不服,上訴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又經分別審理,最后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這是我國最大的辭書著作權訴訟案件。此案的審理和判決,備受社會各界關注,也擴大了對王同億系列詞典集體性批評的影響。
在這次集體性批評中,報刊上發表了數十篇論文,為數更多的以雜文為主的短評(其中瓜田的《無知卻有膽 快去編辭典》最出色)成為一大特色,還有一批評論性報道(其中莊建的《我們丟失了什么?——從王同億、海南出版社涉及的五起著作權侵權案說開去》分量最重),再加上華君武的漫畫;廣播電臺、電視臺也施展了他們特有的手段。這一場規模大、氣勢足、內容扎實、形式多樣、持續數年的集體性批評,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1995年,上海辭書出版社選錄了六十五篇批評《語言大典》的短評,編成《發人深思的笑話——〈語言大典〉短評集》一書出版。印數兩千冊,很快銷售一空。
1997年,中國辭書學會秘書處將批評王同億系列詞典的論文四十三篇編成《我們丟失了什么——“王同億現象”評論文集》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在1999年出版,對打假批劣的第一戰役做了總結。
但王同億并不甘于失敗,他回到湖南家鄉繼續炮制劣質詞典。2001年,他拋出了由他主編、京華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紀現代漢語詞典》,并用改頭換面的手法,對該書略加增補,又在內蒙古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高級現代漢語大詞典》。這兩部詞典,除抄襲剽竊有所收斂外,胡編亂造依然如故。詞目中充滿著污言穢語,如“狗日的”、“狗娘養的”、“狗雜種”、“放狗屁”等等。釋義則信口雌黃,如“不破不立”釋為“現多指公安機關受理的刑事案件,能偵破的,就立案,不能偵破的,就不立案”,“暴卒”釋為“兇暴的士兵”,等等。例證不僅堆砌得不可思議,如“一”字條第二個義項“最小的正整數”就有八十個例證;而且許多例證的內容令人不可容忍:思想荒謬的如“寧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無權”,黃色下流的如“有色心無色膽的只能色迷迷地看”,惡俗不堪的如“屙屎帶放屁——順便”,如此這般,不勝枚舉。
對于王同億再造偽劣詞典的行為,中國辭書學會常務理事會在2001年6月決定予以批評。該會辭書編輯出版專業委員會在同年8月舉行的研討會上落實了這一決定。同年10月,中國辭書學會又聯合中國教育學會舉行座談會繼續展開批評。兩次會上的發言都整理成文并先后發表。此外,報刊上還發表了其他批評文章和評論性報道。中國辭書學會學術委員會把這些文章編成《需要批評 需要反思》一書,在2003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匯集了打假批劣第二戰役的成果。
自稱為“王同億重出江湖”的事件發生后,中國辭書學會加大了對辭書市場調查研究的力度。2002年底,向新聞出版總署圖書司提供了六十種有問題辭書的名單,并報告了這些書中的主要問題。不久,圖書司司長閻曉宏約見中國辭書學會會長曹先擢、副會長韓敬體和學術委員會主任周明鑒,告知他們總署在市場檢查中發現了一些可能有問題的辭書,又接到學會提供的有問題辭書的名單和許多讀者對偽劣辭書的投訴,決定開展2003年辭書質量專項檢查,委托中國辭書學會承辦。由總署確定的對二十一種辭書的專項檢查隨即啟動。2003年10月,總署公布了不合格辭書的名單。其中最為嚴重的是,印刷工業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內容相同、字數相同、定價也相同僅書名不同、開本不同的兩部書。一部叫做《中華辭海》(32開),一部叫做《新編中國大百科全書》(16開)。它們是孿生出來的一對怪胎,不倫不類,抄襲剽竊,胡編亂造,差錯泛濫。不合格辭書的名單公布后,發表了《“非常態”的偽劣辭書》、《有名無實的“百科全書”》等一批評論文章。這就是打假批劣第三戰役的大致經過。
在三大戰役中,不僅揭批了偽劣辭書,而且還對從源頭上遏制偽劣辭書提出了不少建議。鑒于偽劣辭書都是由不具備辭書出版資質的出版社出籠的,因此建議出版行政部門實行辭書出版準入制,規定出版辭書必須具備的條件,不具備條件的出版社不得出版辭書。條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定數量合格的辭書編輯,為此建議舉辦辭書編輯培訓班,編輯經過培訓并通過考試取得證書后方可持證上崗。建議建立出版社以社會效益為主的考核制度,防止為了追逐利潤而出版偽劣辭書。建議出版行政部門組織辭書專家定期進行辭書質量檢查,發現偽劣辭書及時處理。建議對偽劣辭書的出版者給予行政處罰,沒收其非法所得,并對偽劣辭書的編纂者追繳其稿費,不讓他們成為最大的受益者。建議立法保護精神產品消費者的合法權益,購買偽劣辭書的讀者應有權索賠。建議新聞媒體介紹辭書應認真審核,力求合乎實際,不能讓偽劣辭書的編纂者、出版者自吹自擂,欺騙讀者;同時對偽劣辭書加強輿論監督,使之原形畢露。
以上種種建議,有些已被采納。早在1994年2月24日新聞出版署召開的提高辭書質量、促進辭書繁榮的座談會上,時任新聞出版署黨組成員、圖書司司長的楊牧之即已表示贊同與會專家提出的加強辭書質量檢查、辭書編輯須經培訓獲得資格方可上崗、出版社須具備條件才能出版辭書等項建議。2006年,新聞出版總署先后發出《關于規范圖書出版單位辭書出版業務范圍的若干規定》和《關于開展辭書出版人員資格培訓工作的通知》,從2006年到2012年,新聞出版總署教育培訓中心和中國辭書學會合作,已舉辦七期培訓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中國辭書學會還在2008年發布《辭書工作者學術道德和職業道德自律準則》(載《辭書研究》2008年第2期),其中,“反對唯利是圖、見利忘義、不擇手段追逐暴利的行為”、“反對抄襲和變相抄襲”、“確保辭書質量、杜絕劣質辭書進入市場”等準則都明確地把矛頭指向偽劣辭書。
兩位代表
中國辭書學會的打假批劣,參與者甚多。他們對祖國和人民懷有深厚的感情,不能容忍寶貴的國家資產被用來制造文化垃圾,敗壞祖國文化,愚弄和毒害廣大讀者。同時,他們對辭書事業懷有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不能容忍辭書的園地被糟蹋,辭書的名聲被玷污。因此,他們堅持不懈地投入打假批劣的斗爭。其中有兩位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有必要在此略加記述,以便于學習和發揚他們正氣凜然、祛邪不止的精神。
一位是歷任學會第一副會長、代會長、名譽會長的巢峰。1992年他在中國辭書學會成立大會上吹響了打假批劣的號角之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以組織開展這項工作為己任,運籌帷幄,精心部署,逐步推進。他在各種大小會議上都會提及打假批劣。重要的如:1993年在中國辭書學會第一屆年會上題為“《語言大典》的教訓”的開幕詞;1994年在中國辭書學會專科詞典專業委員會首屆年會上題為“‘王同億現象’剖析”的講話;1995年在首屆中國辭書獎頒獎大會暨中國辭書學會第二屆年會上的兩次講話;等等。他一再建議實行辭書出版準入制和培訓辭書編輯,作為遏制偽劣辭書的手段。
他還寫了一批相關的文章。主要的有:1994年發表的《剎一剎著書出書中的粗制濫造風——兼評王同億主編的〈語言大典〉》,2001年發表的《辭書編纂必須堅持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評〈新世紀現代漢語詞典〉》,2003年發表的《中國辭書界的“三大戰役”》、《辭書出版準入制勢在必行》和《凈化辭書市場的五大措施》。這些文章在辭書界、出版界、文化界有較大影響。
另一位是長期擔任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曾任副會長、現任顧問的周明鑒。他對優質辭書愛護有加,多方幫助;對劣質辭書則絕不容忍,務必鏟除。他住在北京,常到甜水園圖書市場瀏覽,發現可疑的辭書,就自己掏錢買回去檢查,從而發現了許多問題,積累了大量資料,通過學會向新聞出版總署圖書司報告。拿到王同億的《新世紀現代漢語詞典》后,他隨機檢查了該書的五分之一,每頁都有紅筆劃出的條條杠杠,貼著密密麻麻的浮簽。后來他又發現王同億的《高級現代漢語大詞典》其實是此書的翻版。批評這兩部詞典時,他一口氣寫了三篇文章:《〈新世紀現代漢語詞典〉評析》、《詞典都是“東抄西改”編出來的嗎?》、《可悲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2002年底中國辭書學會向新聞出版總署提供的六十種有問題辭書的名單,許多都是他的發現。如前所述,這是新聞出版總署開展2003年辭書質量專項檢查時確定書目的三個來源之一。檢查結果公布后,他發表《有名無實的“百科全書”》一文,揭批了煌煌四十六冊、用大禮品盒包裝、定價五千八百元而內容一塌糊涂的《現代生活實用百科全書》。
影響深遠
中國辭書學會打假批劣的壯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致力于推動開展學術批評的楊玉圣,曾經兩次論及辭書界的打假批劣。他說:“圍繞《語言大典》等王同億現象的集體性批評,的確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辭書界的‘無法無天’態勢,其積極意義無疑是歷史性的。”又說:對王同億現象的批評,“不僅給辭書論壇注入了生氣和活力,而且強有力地顯示了學術批評的魅力與威力;它不僅張揚了辭書界的正氣之歌,而且為九十年代中國的學術批評開啟了一條陽光大道。”(見1996年10月2日和1997年10月8日的《中華讀書報》)這是很高的評價。但是還可以看得更廣更深一些。于光遠在《值得重視的一個消極文化現象——評王同億主編的〈語言大典〉》一文中說:“它(按:指《語言大典》)的用處看來只是為研究當前我國文化現象提供一個對象。它使我們去想不少問題,它也使我們通過這種思索了解不少問題。”這樣的詞典為什么能夠出版?為什么被吹捧和抬舉得那么高?為什么被揭批后還可以發行?“這就要深思一番了。這不是這個人或者那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風氣的問題。接著我們還可以問,這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風氣?并且進一步要問這種社會風氣是如何造成的?這樣的問題一個一個問下去,得出行動方面的結論,進行教育,改進工作,我想對于我們的國家的文化事業是大有好處的。”(載1994年第2期《辭書研究》)對于后來揭批的偽劣辭書,也都可以做這樣的深思。
從辭書編纂出版的角度說,打假批劣,對所有的辭書編纂者、出版者都有警示作用,告誡他們決不可造假制劣,否則將面臨嚴重的后果。當然,無視警告、敢于冒險的大有人在,但終究少得多了。尤其是由打假批劣引出的辭書出版準入制、辭書編輯培訓和持證上崗制以及辭書質量專項檢查的實行,對于整頓辭書出版秩序、從源頭上遏制偽劣辭書、提高辭書質量、建設辭書編輯隊伍已經起了并將繼續發揮重大作用。
從辭書研究的角度說,這些年不僅揭批了偽劣辭書,而且揭批了偽劣辭書的炮制者為自己開脫的種種奇談怪論,光是關于抄襲行為的就有一大堆。被人揭發其抄襲行為如整個詞條的注釋、例句一字不動地照抄,照抄注、例,僅增刪個別無關緊要的字等五種手法后,王同億竟答辯說:“凡編詞典,都離不開這‘五種手法’。”他又說:“詞典具有承繼性強烈的特點,按照傳統模式,東抄西改而已。”他還說:“作為語言構成成分的語詞,人們應有共同的認識。……以‘抄襲’為名,將‘共識’據為‘專利’的作法是不適當的,也是行不通的。”(按:王同億將“共識”絕對化,并將“共識”和“對共識的表述”混為一談。)他又說,詞典的條目是“記錄”的結果,不是“創作”的成果,沒有獨創性,因此不是享有著作權的作品。(按:歪曲別人所用的“記錄”一詞,毫無根據地抹煞詞典的獨創性和著作權。)他還說,他的行為是對他人詞典的“適當引用”。(按:他的行為和著作權法規定的“適當引用”毫無共同之處。)對于諸如此類的胡言亂語,都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嚴加駁斥,這是辭書研究的一個成果。另一方面,偽劣辭書為辭書研究提供了大量反面素材,也對辭書研究的深入開展甚為有益。
現在,辭書界的打假批劣已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是斗爭還將繼續下去,永無盡期。希望中國辭書學會始終站在這個斗爭的前列,為凈化辭書園地、提高辭書質量、繁榮辭書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