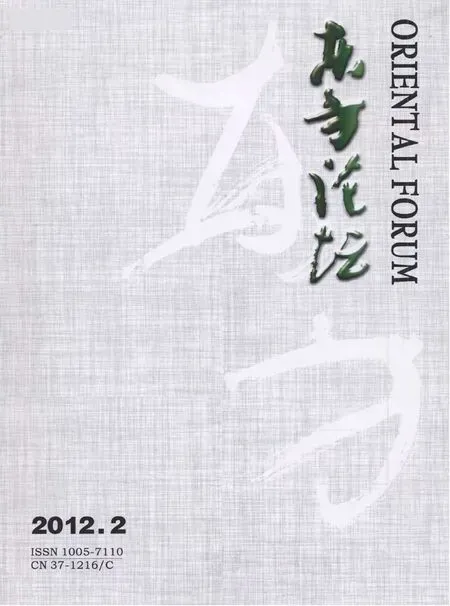神秘主義與中國當代先鋒小說
神秘主義與中國當代先鋒小說
董 外 平
(北京師范大學 文學院,北京100875)
從語言敘事、主題內容、美學癥候三個方面來看,中國當代先鋒小說呈現出鮮明的神秘主義特征:首先,先鋒小說通過隱喻、象征等手段將語言歸入神秘之列,又以迷宮式的敘事策略將小說敘事藝術引向神秘的深淵;其次,先鋒小說通過罪孽、苦難、宿命、死亡等生命主題傳達了宗教、哲學關于生命現象的神秘主義理解;再次,先鋒小說通過神秘主義的書寫締造了小說一種寓言式的詩性品格。神秘主義不僅僅是個別先鋒小說家的創作傾向,而是先鋒小說具有整體性、流派性的藝術特征。
神秘主義;先鋒小說;語言敘事;生命主題;詩性品格
1980年代中后期,中國傳統理性精神遭遇歷史性潰敗,理性主義權威受到普遍質疑,于是西方非理性主義思潮在中國蓬勃興起,影響了一大批欣喜若狂的中國作家。中國當代先鋒小說家接受了西方非理性主義思潮的洗禮,其直接結果是導致先鋒小說家神秘主義意識的蔓延以及對非理性敘事的迷戀。馬原說:“生活不是邏輯的”,“存在不是邏輯的”[1](P416),在他看來,生活與存在是有點神秘的,“神秘是抽象的也是結結實實的存在,是人類理念之外的實體。”[2]神秘主義意識促使中國當代先鋒小說家文學觀念及創作方法的蛻變。先鋒小說家毅然拋棄傳統現實主義文學觀和創作方法,堅持一種神秘主義的文學觀與創作方法。格非認為:“文學是一個神祗,只有那些感覺到在世界的胸膛里始終有神秘事物敲擊著的人們,才會感到親切的共鳴。”[3]殘雪曾多次在創作談中聲稱自己的寫作是一種“非理性的”、“潛意識的”的神秘寫作,她認為文學經典不是一種靠智慧和理性就可以達到的境界,而是“一種虔誠的、有點神秘的感悟。作家在創造時絕對不會是清晰的,應該說,他們寫下的,是自己從未體驗過的、出乎自己意料的……”[4](P252)在殘雪看來,世界經典的作家大多是神秘主義創作的熱衷者,比如但丁、莎士比亞、卡夫卡、博爾赫斯。余華早期對現實主義文學失望至極,他說:“真實似乎只對早餐這類事物有意義,而對深夜月光下某個人敘述的死人復活故事,真實在翌日清晨對它的回避總是毫不猶豫。”[5]現實主義文學想象力的衰竭已成文學一大重癥,顛覆日常真實的神秘敘事不失為余華的一種拯救之法。此外,馬原和孫甘露也有著同樣鮮明的神秘主義文學主張。馬原認為寫小說就是要給讀者創造一種新的經驗,這種新經驗是讀者曾未體驗過的,甚至是超驗的。孫甘露則宣稱,小說的神秘性、不可解性以及新鮮的閱讀經驗是他寫作的目的。由上可見,神秘主義不只是某一作家的偏好,而是中國當代先鋒小說家一種集體意識。神秘主義對于中國當代先鋒小說來說,它具有整體性、流派性特征。
一、可說與不可說之間:語言敘事的神秘
維特根斯坦說:“確實有不可說的東西。它們顯示自己,它們是神秘的東西。”[6](P104)海德格爾說:“根本上必須保持不被說的狀態,乃被抑制在未被道說者中,作為不可顯示者而棲息于遮蔽之域,這就是神秘。”[7](P306)《奧義書》說:“言語不能表達者,為言語本身……”[8](P155)宇宙生命的奧秘往往超出語言描述的范疇,經驗敘述常常捉襟見肘。因此,如何直面不可言說的世界,描繪出人類可能性的生存處境與前景,是所有現代作家必須深思的命題,這對于中國當代先鋒小說家來說更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中國當代先鋒小說家受西方神秘主義文學的啟發,從神秘主義詩學習得象征、隱喻的力量,又從現代派小說悟出迷宮式的敘事策略,完成了一次盛大的“不可言說的言說”的文學實踐。
神秘主義認為語言不可言說,并不意味著語言真正失去言說的功能。神秘主義所謂“不可言說”是指在理性邏輯中無法言說,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實現海德格爾所說的“敞亮”。海德格爾提出的解決方案是“詩意的棲居”,海氏認為詩意言說是語言由“遮蔽”走向“澄明”的必經之路。海氏的觀點與中國古代詩學觀念不謀而合。葉燮說:“詩之至處,秒在含蓄無垠,思致微妙,其寄托在可言與不可言之間,其指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離形象,絕議論而窮思維,引人與恍惚之境,所以為至也。”[9]中國古代詩學強調言外之意、象外之象、言近旨遠,正是海氏詩意言說之義。宗教神秘主義常用象征、類比、悖論、寓言、神話等詩意言說方式,比如印度教就“運用隱喻、象征、詩的想象、類比以及諷喻等”神話的描述方式,因為“這種神話方式的語言不太受邏輯與常識的約束。”[10](P30)在神秘主義哲學家H·奧特看來,象征是不可言說的言說,不可言說的東西借助作為臨界經驗的象征語言可以表達出來。概而言之,“不可言說的言說”就是終止邏輯、理性、判斷,采用多義的、朦朧的、夢囈式的的語言,借用隱喻、象征、想象、意象等手法的詩意言說。中國當代先鋒小說家多采用這種神秘的語言形式。
殘雪的小說語言具有巫術語言的特性。眾所周知,巫師施法時念念有詞的咒語是一種不同尋常的原始語言,它駕馭了語言原初的意義和指涉功能,時至今日,這種巫術語言仍然在民間一些相士、道士和陰陽先生中流傳使用。巫術語言具有神的屬性,承擔著人與神對話的功能,它打亂了一般的語言邏輯,超越了語言能指與所指固定的對應關系,表現出囈語的特征。殘雪不無悲觀地意識到,人類先祖創造出來的這種原始語言在文明的過程中已漸漸喪失它的本義,淪為人類征服世界的工具。為了恢復語言的本義和神性,殘雪儼然一位現代巫師,用咒語進行創作,以致她的小說語言出現一種奇異的形態:日常語言的邏輯性、因果聯系性被打破,只剩下一堆雜亂的語言碎片。殘雪小說中許多人物的語言邏輯混亂,前言不搭后語,缺乏應有的過度與連接,超出語言的常規形態。《蒼老的浮云》中缺乏邏輯的人物語言俯拾皆是。如“楮樹上已經結果子了,等果子一熟,你就會睡得很熟很熟,……她身上老長瘡,就因為她脾氣大。”“街上的老鞋匠耳朵里長出了桂花,香的不得了。”這些不合邏輯的語言或許只有巫師才能參透。巫術語言本質上是一種象征性語言,它具有一種巫術的力量。殘雪小說經常出現的那些隱喻和象征猶如一道道符咒,神秘而令人顫栗。《公牛》中“公牛”移動的“背”仿佛“一道紫光”劃過,既陰森恐怖又暗藏玄機,事實上“公牛”一直是小說中一個幽靈般的隱喻或象征,它象征命運不可預見的災難性。
格非喜歡用意象構建隱喻和象征的神秘世界。格非認為那些不可言說的神秘之物,只能通過一些意象去隱喻和暗示,才可能讓人瞥見那些神秘存在的微光。格非特別偏愛“雨”這個意象,小說中許多離奇事件都是在雨水籠罩的神秘氛圍中發生的。例如,“一會兒雨水漣漣,它使樹木變得神秘,使人感覺的觸須變得像蠶絲一樣纖弱……(《雨季的感覺》);“賈蘭坡的尸體因為那場大雨的浸泡而增加了分量”(《欲望的旗幟》);“蕭旅長的失蹤使數天后在雨季開始的戰役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陰影”(《迷舟》);“趙少忠又一次沉浸在那場夏日的淫雨之中”(《敵人》)。格非通過象征將記憶、死亡、命運、性與雨的意象聯系起來,使小說彌漫著一股神秘的南方氣息。格非小說存在一個巨大的隱喻世界。《褐色鳥群》中的“水邊”,《敵人》中的“白果樹”,《人面桃花》中的“普濟”和“花家舍”,都是人終其一生也無法破解的存在性隱喻。這些反復出現的隱喻,都是命運的某種征兆,預示著命運不可支配的神秘力量。
中國當代先鋒小說家除了大量使用隱喻和象征性語言,在敘事層面還往往采用迷宮式敘事策略,以神秘來述說神秘。面對“不可言說的”的表達困境,東方神秘主義采取了諸多敘說策略。“佛教和道教對于這種自相矛盾的地方并不掩蓋而是加以強調。老子《道德經》就是以一種令人費解、似乎不合邏輯的風格寫成的。”[10](P35)禪宗的公案精心設計一種荒謬的謎,使弟子以奇特方式認識到邏輯推理的局限性,在剎那間體驗到實在。中國當代先鋒小說家敘說世界的方法類似東方神秘主義的言說策略,他們并不用科學去勘測事實,而是設計種種迷宮強化事件本身的神秘,將離奇的現象和事件以離奇的面貌原原本本地展現出來。馬原的“敘事圈套”、格非的“敘事迷宮”、孫甘露的“謎語敘事”以及殘雪的“夢幻敘事”,都是這種敘事策略的典型應用。迷宮式敘事策略常借用空缺式、循環圈式等敘述結構營造神秘的小說氛圍。
佛教神秘主義強調“空”,道家神秘主義強調“無”,認為“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老子·四十章》),中國古代詩歌常以“空”、“無”之境來表現神秘之美。先鋒小說家常常有意在文本中設置繁多空缺結構,借以凸現世界的不可知性。格非一向以營造“空缺”著稱,《迷舟》是其典范之作。《迷舟》中對于導致主人公蕭喪命的關鍵情節,即蕭到底有沒有叛黨通敵沒有做任何交代或暗示,作者故意空缺,蕭的喪命成了一個無法解釋、也不能解釋的謎。除此之外,小說還設置了一系列空缺事件,使得所有事情變得異常蹊蹺、迷惑而詭秘。余華作品也大量存在這種空缺的藝術。《十八歲出門遠行》對于“我”所遭遇的司機有意省略了一些交代。司機與那些搶蘋果的老鄉是什么關系,為何被搶了蘋果司機還掛著一絲笑容,這給讀者留下了一個個謎團。同樣在孫甘露的《信使之函》中,空缺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信使到底是何方神圣,信到底是什么天書,耳語城到底在宇宙哪端,小說無意告知,都成了謎中之謎。
佛教神秘主義宣揚因果報應、生死輪回,認為世界處于因果循環、不斷輪回之中。中國當代先鋒小說家感慨命運的反復糾葛,常采用循環圈式的敘述結構來宣泄這種佛教神秘主義的生命之感。余華的《現實一種》描寫了一個詭異的報復循環。山崗的兒子皮皮無意殺死了山峰的兒子,山峰怒不可恕殺了皮皮,接著山崗在妻子慫恿下殺了山峰,山峰的妻子借公安機關處又死了山崗。如果小說可以無限延續,這種報復將會無休止地循環下去。《許三觀買血記》反復講述了主人公十一次賣血經歷。賣血作為小說一而再出現的循環事件,貫穿主人公一生的生命歷程,如同西緒弗斯的神話,不斷重復一個動作,沒有一點溫情,沒有任何緣由。格非的《褐色鳥群》是一個典型的圓形文本。陳曉明認為《褐色鳥群》埋設了三個“圓圈”故事,三個“圓圈”相互牽連又相互否定,現實在虛虛實實中變得捉摸不定,整個小說沉浸在一片神秘的氛圍里不能自拔。
二、可解與不可解之際:生命主題的神秘
徐志摩曾說:“生命的現象,就是一個偉大不過的神秘。”[11]誠然,生命對于有限的存在者來說,無疑是神秘的。生命是什么?它從哪里來,又將歸何處?這是哲學家永恒探討的“斯芬克斯之謎”,也是人類一切宗教所必須解決的第一個問題。生命的神秘與日俱增地撞擊著先鋒小說家的感知世界,于是他們試圖通過文學去訴說這種神秘感,去傳達各自種種關于生命的神秘體驗,從而將自我內在的精神空間安置到個體生存和人類存在的整體性境域之中,回到對存在的質疑與拷問之中,追究命運的荒誕本質和靈魂的痛苦掙扎。于是,罪孽、苦難、宿命、死亡等神秘生命現象,成為中國當代先鋒小說司空見慣的主題。
1.宗教皈依
宗教是人類的避難所,每當罪孽深重的靈魂無處藏身時,宗教就成了他們最后的救贖。中國當代先鋒小說家馬原、扎西達娃、殘雪、余華、北村,都不同程度地在小說中表現出一種宗教皈依意識,本文以余華和北村的作品為例,試圖闡釋先鋒小說濃厚的宗教神秘主義色彩。
北村說:“因為圣經不但說‘在世間有苦難’,又說‘在主里有平安’。這就是我的小說對苦難得以擺脫的途徑所作的答案。救贖是唯一之路。”[12]在北村的許多作品中,罪孽之人最終在神的昭示下,走向救贖之路。《張生的婚姻》中悲痛欲絕的張生偶然翻開滿是灰塵的《圣經》,受到神的感召皈依了基督;《施洗的河》中的劉浪痛苦絕望之時,在當地傳道士的啟示下皈依了基督;《孫權的故事》中的孫權被判死刑入獄后,受到基督徒劉兄弟的指引,在閱讀《約翰福音》第八章時皈依了基督;《情況》中的飄萍最后在一個素不相識的基督教女孩的感召下皈依了基督。皈依了基督的北村總是試圖給身陷苦海的靈魂指引一條救贖之路,并且宣告人們,只有皈依上帝,在上帝的光輝照耀下洗去罪孽,才有可能獲得拯救。
余華雖然曾表示對《圣經》的喜愛卻走向了佛教的超度之路。北村的苦難皈依了基督教,而余華的苦難皈依了佛教。雖然沒有實證證明余華受佛教神秘主義的影響,但是在他的作品中,我們能明顯感受到佛教神秘主義的思想,郜元寶斷言:“余華的小說肯定有佛家出世的思想。”[13]與基督教皈依上帝即可脫離苦海不同,佛教主張在苦難的堅忍中超越苦難,在苦難中涅槃。佛教神秘主義認為,世間無常,眾生必受無量諸苦,人生就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憂悲老苦,怨憎會苦,恩愛別離苦,所欲不得苦,取言要之五盛陰苦。”[14]佛教三法印之一就是,生本不樂,一切皆苦。既然人生本苦,人又不能擺脫它,那該如何去戰勝苦難呢?佛教神秘主義主張堅忍,以期待佛祖將苦難眾生普渡到幸福的彼岸。余華小說的苦難敘事與佛教神秘主義的苦難涅槃觀念極其相似。
余華總是無節制地描寫苦難,表面看來,余華的苦難好像永遠沒有救贖,但是仔細體味,余華并沒有絕望到放棄救贖,而是選擇了一條特殊的救贖之路,即苦難主體通過對苦難的直面與堅忍實現對苦難的超度。《活著》中的苦難遍及主人公福貴渺茫的一生,即便連失七個親人,他也仍然一如既往地面對生活。苦難的經歷不僅沒有使他墜落,反而使他的生存意志更加堅定。福貴說:“我認識的人一個挨著一個死去,我還活著。”福貴在對苦難的堅忍中,超越了世間一切苦難。《許三觀賣血記》中,苦難在許三觀詼諧幽默的調侃中變得那么平淡無奇,苦難被樂觀主義消解,達到一種超凡脫俗的境界,變成一種無悲的受難。當苦難不成為其苦難時,苦難也就不再構成對生命的毀滅性威脅,苦難主體由此進入佛教神秘主義的涅槃之境。
2.宿命怪圈
宿命是中國神秘主義文化一個重要的概念。儒家神秘主義認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15]道家神秘主義也說:“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16]在神秘主義看來,世間一切變化皆歸于命運,命運支配一切,決定一切,人在命運面前無能為力,這就是宿命。宿命是非理性的、偶然性的、神秘性的,命運之神總是借助偶然的、神秘的事件實現操縱和主宰人們的命運。先鋒小說家心懷異常強烈的宿命感,常常在小說創作中表現出濃郁的宿命意識。余華被稱為最富宿命意識的作家,宿命猶如一層揮之不去的陰云籠罩在余華的小說中。《命中注定》的標題本身就預示著宿命的含義,這個故事具有濃厚的佛教神秘主義善惡相報的意味,陳雷的死似乎是三十年前搗毀燕子窩的報應。《難逃劫數》也是典型的宿命主題。小說主人公廣佛一次又一次忽視兇殺事件將要發生的征兆,本可逃避牢獄之災的他卻一步步落入命運的陷阱,這就是“難逃劫數”。扎西達娃的《懸崖之光》以簡短的篇幅講述了一個荒謬的宿命故事。“我”居然因為影子挑殺了“博士先生”被當做謀殺犯押走。“我”覺得很荒謬,卻又無可奈何,只能歸罪于人世間的不平和命運的不公。此類宿命事件在先鋒小說中比比皆是,因為無法解釋,均可歸入神秘主義的范疇。
從某種意義上講,宿命是一種“必然”,但這種“必然”是通過“偶然”表現出來的,一切偶然發生的事情仿佛都在冥冥之中早已事先預定好。《迷舟》揭示了偶然性因素在人命運中的毀滅性力量。主人公蕭在被警衛追殺的過程中,如果之前母親沒有把他的槍順手塞進抽屜,他就可以在一瞬間反制敵人,變被動為主動;如果不是碰上母親抓雞栓住了門,他就有可能迅速虎口脫險,逃過此劫。然而,偶然性在關鍵時刻扼住了命運的咽喉,釀成了難以預見的災難性后果。《大年》中豹子要襲擊丁家的消息被一個小孩獲知,小孩告訴其父,不料父親因痔瘡發作而沒有理睬,小孩又告訴其母,恰巧母親是個啞巴,無法把消息正確地告知丁家。原本有可能采取防范措施的丁家最終沒能躲過一場災禍。《鮮血梅花》在一連串偶然事件中走向一個必然的結局:虛弱不堪且沒有半點武藝的阮海闊注定報不掉殺父之仇,他唯一可做的是接受命運之神的宣判。這些難以捉摸的偶然性因素實際包含了先鋒小說家對命運、歷史、人生的獨特思考,在他們看來,真正掌控生死命運的、推動歷史步伐的、決定人生前途的,不是馬克思所謂的自然規律與社會規律,而是規律之外的理性不可把握的神秘力量。
3.死亡之謎
叔本華曾說“死亡的困擾是每一種哲學的源頭”[17],因為死亡作為一種生命現象,不是經驗的,而是超驗的。維特根斯坦說:“死不是生活里的一件事情,人是沒有經歷過死的。”[6](P103)海德格爾也認為:“死亡作為此在的終結乃是此在最本己的、無所關聯的、確知的,而作為其本身則是不確定的、超不過的可能性。”[18](P310)死亡作為一種生命體驗,與其他生命體驗不同的是,人不可能在死亡之后來訴說死亡。因而作為超驗現象的死亡,本質上是神秘的。在里爾克看來,死亡充滿了無數神秘,它比世界一切無生命的東西以及其它自然生命更加神秘。因此,無論宗教、哲學、文學,在它們試圖描述死亡時,都必定陷入神秘主義的吊詭。死亡是先鋒小說最鐘情的主題之一,當先鋒小說家努力捕捉這一神秘的生命現象時,留給讀者的是一個個死亡之謎。
《世事如煙》描繪了一幅幅近乎怪誕的死亡風景,所有的死亡神秘至極,根本無法從文本中找到任何蛛絲馬跡,永遠弄不清死亡的真相也無所謂真相。《河邊的錯誤》采用偵探小說的手法,一樁樁死亡案件在漸漸澄明中又不斷遮蔽,故事越往下發展,懸念更加繁雜,死亡由此變的玄而又玄,陷入一座無底迷宮之中。小說雖模仿偵探小說的戲法,卻摒棄了偵探小說結局一定真相大白的慣用伎倆,在余華看來,所謂真相只是一廂情愿的幻覺。余華堅信,文學的使命是發現世界可能存在的東西,而不是去論證世界已經存在的東西,那是科學的使命。所以他在小說中只是本然地描繪出種種死亡的神秘跡象,而不是像偵探家一樣去破譯死亡的密碼,甚至還有意為死亡涂抹些神秘的色料。對余華來說,他所感興趣的不是“為什么死亡”,而是“世界居然會有死亡”。格非同樣對死亡本身興趣十足,他總是在小說中給死亡事件鋪上一層神秘、詭譎和恐怖的面紗。《褐色鳥群》中青年的死在兩種截然不同敘述中顯得虛虛實實、迷亂不清,《敵人》中的人物接連莫名其妙地喪生,死亡好像時刻潛伏在人的周圍。格非抽空了死亡的實體,死亡變成一些魂飛魄散的表像。對于格非來說,他注重的并不是死亡的意義,而是死亡給予的神秘體驗。
佛教神秘主義普遍“否定死亡的終極性,想象在死亡之外還有一種繼承的存在——通過復活、輪回或超生,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從現實超度到沒有死亡的世界。”[19]扎西達娃根據佛教這種神秘的死亡觀念,在《西藏,隱秘歲月》中賜予了主人公次仁吉姆不死之軀,即“次仁吉姆就是每一個女人”,次仁吉姆成了一個不死的象征。宗教神秘主義試圖通過“靈魂不死”之說來解開“死亡之謎”,在它們看來,死亡是生的延續,而不是生的對立面。實際上,宗教神秘主義并沒有破解“死亡之謎”,而是繞到生的問題,死亡是被擱置的,而且用經驗世界的“生”替代超驗世界的“死”,意味著“死”仍是一個無法自我超越的謎。
三、神秘化與詩意化:神秘主義創作的詩性品格
神秘主義是一種詩性世界觀,具有詩性品格。劉小楓在《詩化哲學》認為:“詩意化的世界就是這樣設定的,即超驗的大我通過一個稟有感性的小我,把有限之物、時間中的物(包括個體的人和世界中的事物)統一領入無限中去。”[20](P36)劉小楓所謂的“詩意化”實際就是“神秘化”,“詩意化的世界”指的就是超驗的神秘世界,而且“神秘化”是“詩意化”的條件,“詩意化”是“神秘化”的結果。西方象征主義詩派為了使詩歌表現出一種神秘莫測的美,常采用神秘主義的創作方法:在題材的選擇上,象征主義詩人毅然拋棄傳統現實主義詩歌題材,轉向充滿夢幻、錯覺、畸形、丑惡、虛無、焦慮、恐怖等的神秘題材;在意象的創造上,象征主義詩人摒棄傳統詩歌司空見慣的意象,創造出繁多奇絕的、荒誕的、陌生的、神幻的玄學意象;在結構的經營上,象征主義詩人樂于編織時空跳躍性強、天馬行空般的非邏輯性結構。象征主義詩派廣泛地將“神秘”引入詩歌的殿堂,使歐美傳統的詩歌美學發生了歷史性變革,從此詩壇刮起一股神秘的詩風。神秘主義作為現代詩歌的一種美學征候,如果將其引入小說,那么就意味著小說的詩意化,于是西方現代主義小說以神秘主義的創作姿態改寫了小說的歷史,米蘭·昆德拉斷言:“從1857年開始,小說的歷史將是‘小說成為詩’的歷史。”[21](P110)納博科夫稱斯蒂文森的偵探小說《化身博士》是“一個更接近于詩歌,不是一般散文體小說的虛構故事。”[22](P247)神秘主義的注入,使小說獲得了一種詩性品格。
毋庸置疑,中國當代先鋒作家通過神秘主義創作帶領中國當代小說融入了世界文學“小說成為詩”的現代潮流。殘雪是一位極具現代主義詩人氣質的作家,她的小說呈現出獨具一格的詩性品質。殘雪常以夢境和幻覺為前提,不遵守邏輯和理性規范,運用非邏輯、非理性的語言破壞小說的連貫性,并且大量使用象征和隱喻,發展了小說一種天然的詩性特征。王蒙說他把殘雪的小說當詩來讀,的確,殘雪許多小說可以和象征主義詩歌媲美。如《山上的小屋》是一首象征夢魘現實的詩;《天堂里的對話》是一首象征纏綿悱惻的愛情的詩;《布谷鳥叫的那一瞬間》是一首象征童年記憶的詩;《黃泥街》是一首象征“文革”黑暗歷史的詩;《蒼老的浮云》是一首象征虛無與荒誕存在的詩;殘雪自稱《突圍表演》是“一首詩,一首長詩,完全是詩的世界”[4](P29),它象征著女性真實的歷史境遇和生存處境。殘雪小說的詩性品格得益于原始的巫性思維的靈動展現。維科認為原始思維是人類對世界的一種詩意的認知形式,維科稱之為詩性思維。巫性思維是一種典型的詩性思維,理所當然具有維科所謂的“詩性智慧”。楚文學歷來具有詩性的傳統,屈原的《離騷》語言精美華麗,想象奇詭神秘,感情濃烈奔放,代表了楚文學詩情洋溢的浪漫主義風格。殘雪繼承了楚文學浪漫主義的詩性傳統,她將夢幻帶入小說的表現之維,編織了一個亦真亦幻的詩性世界。
馬原與扎西達娃對西藏的神秘書寫向世界展示了一個詩意的棲居地。西藏神秘的自然風光與人文景觀賦予了青藏高原無盡的詩情畫意,同時也帶給了馬原和扎西達娃無比充沛的想象力,于是他們的創作充滿了幻想的激情和詩性的情懷,西藏在其筆下變成一首首瑰麗的詩。馬原的《虛構》、《岡底斯的誘惑》與扎西達娃的《西藏,隱秘歲月》、《西藏,系在皮繩結上的魂》完全可以讀作一首關于西藏的詩。那里有古老的神話傳說,有奇絕的高原風景;那里有金碧輝煌的寺廟,有虔誠的宗教信徒;那里遍布神的足跡和蹤影,人們在神的庇佑下,悠然自得;那里是一個似夢非夢、詩意盎然的虛幻世界。在閱讀過程中,讀者會不自覺地跟隨作者的敘事節奏慢慢流入一個超越時空的詩意空間。
格非的《褐色鳥群》與孫甘露的《信使之函》堪稱中國當代“小說成為詩”的經典之作。《褐色鳥群》是一部逼近艾略特《荒原》的作品。小說主人公“我”孑身一人生活在其中,如同《荒原》中的詩人,感受到的是徹骨的孤獨,他沒有時間感,也沒有空間感,仿佛被世界無情拋棄,與他邂逅的兩位美麗女子,不過是其情欲無處發泄產生的情色幻覺。這個世界已被現代文明毀滅,鳥群是虛幻的,美麗的女子也是虛幻的,一切都是虛無與荒誕的。我們把《褐色鳥群》闡釋為《荒原》一樣的詩作,一點都不為過,它以詩意的內涵表達了《荒原》同樣的主題:現代文明是一個必將走向荒蕪的文明,人類不得不為背叛上帝付出慘重代價。孫甘露的《信使之函》與其說是一個短篇小說,不如說是一部敘事長詩。孫甘露模糊了小說與詩歌的文體界限,他以詩歌的體例構建小說的框架,并且通篇引入現代主義詩歌的神秘象征,使得小說無論形式還是內容都具有詩的特征。如果把《信使之函》鑒定為一首詩,那么它將是中國當代詩歌發展的另一種可能的形式。
中國文學具有詩性的傳統,但是中國當代先鋒小說的詩性品格又與中國傳統文學的詩性品格存在很大差異,它既是對中國傳統文學詩性品格的繼承,更多是一次盛大的超越。中國很多古典小說夾雜大量的古體詩詞,如《紅樓夢》、《金瓶梅》、《三國演義》等,古體詩詞雖然營造了小說詩性的氛圍,但它是外在于小說的,更多地起點綴作用,本身并不是小說構成的內在因素。中國現當代文學出現過一種“詩化小說”,如廢名、蕭紅、汪曾祺的小說,他們的小說雖然從形式到內容都顯出詩的旨趣,具有濃郁的抒情性,但仍然沒有脫出傳統詩性風格的范疇,它們只是古體詩詞意蘊與抒情風格的仿制,并沒有創造出現代意味的“小說成為詩”的詩性風格。而中國當代先鋒小說同時超越了古典小說與現代“詩化小說”的詩性范疇,它賦予小說的詩性不在于古體詩詞的意象、意蘊和抒情風尚,而是現代寓言式的美學內涵。也就是說先鋒小說的詩性品格是一種寓言風格,米蘭·昆德拉所謂的“小說成為詩”指的就是卡夫卡以來小說的寓言風格。質言之,寓言與詩、神秘主義本質上是同一的,神秘主義、寓言、詩三位一體,相互滲透,相互作用,三者均是對無限宇宙的一種不可言說的言說。卡夫卡的小說、艾略特的詩歌、奧尼爾的戲劇,作為世界神秘主義文學的典型代表,均被稱作“現代寓言”,同時也被稱為“現代史詩”。
寓言風格是世界現代主義文學開創的一種小說的詩性風格,也是中國當代先鋒小說神秘主義創作追求的美學風格。當王蒙說殘雪小說可以當作詩來讀,他絕不是指殘雪小說具有中國古體詩詞的韻味,而是指其中孕育著一個強大的不能言說的指向詩的寓言世界。事實上,先鋒小說很多都可以看作中國社會歷史的“現代寓言”。殘雪的小說是一部中國當代黑暗歷史的寓言,余華的小說是一部丑惡人性的寓言,格非的小說是一部“存在”的寓言,馬原與扎西達娃的小說是一部西藏的寓言,北村的小說是一部信仰的寓言。寓言式的神秘書寫使先鋒小說突破了傳統詩性小說的構架,為現代詩性小說樹立了一種成熟的典范,從而中國當代先鋒小說也完成了自身的美學建構。
[1] 馬原.馬原文集(4)[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
[2] 馬原.關于《岡底斯的誘惑》的對話[J].當代作家評論,1985,(5).
[3] 王宏瑋.缺失和斷裂——格非小說敘事策略解讀及神秘性探因[J].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5,(4).
[4] 殘雪.為了報仇寫小說——殘雪訪談錄[J].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3.
[5] 余華.虛偽的作品[J].上海文論,1989,(5).
[6] [奧]維特根斯坦.邏輯學導論[M].賀紹甲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7] 毛峰.神秘主義詩學[M].北京:三聯書店,1998.
[8] [波蘭]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沒有上帝…[M].楊德友譯.北京:三聯書店,1997.
[9] 王吉鳳.從“詩性智慧”看中國傳統的詩性思維[M].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5).
[10] [美]卡普拉.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M].灌耕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1] 轉引自譚桂林.論現代中國神秘主義詩學[J].文學評論,2008,(1).
[12] 林舟.苦難的書寫與意義的探詢[J].花城,1996,(6).
[13] 郜元寶.余華創作中的苦難意識[M].文學評論,1994,(3).
[14] 轉引自周景雷.像佛陀一樣活著——論余華小說的佛教意識[J].藝術廣角,2003,(4).
[15]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8.
[16] 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7] 陳炎.“向死而在”——洪峰小說引起的哲學思考[M].時代文學,1989,(1).
[18] [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M].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三聯書店,1987.
[19] 洪治綱.追蹤神秘——近期小說審美動向[J].當代作家評論,1993,(6).
[20] 劉小楓.詩化哲學——德國浪漫美學傳統[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86.
[21] [捷克]米蘭·昆德拉.小說的智慧[M].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2.
[22] [美]納博科夫.文學講稿[M].申慧輝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1.
責任編輯:馮濟平
Mysticism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Vanguard Novels
DONG Wai-p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The vanguard novels are endowed with distinct features of mysticism, judging by their language form, subject matter and aesthetic syndromes. First, vanguard novels lead language onto a road of mystery with metaphor and symbolisation and then drive the narrative art to a mysterious abyss by using the maze-like narrative strategyy. Second, they convey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mysticism about the life phenomenaon through sin, misery, fate, death and other life themes. Finally, they create an allegorical poetic style through the writing of mysticism. It is argued that mysticism is not only the creation tendency of a few vanguard novelists, but also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all vanguard novelists as a whole.
mysticism; vanguard novel; language of narration; life theme; poetic character
I207
A
1005-7110(2012)02-0051-07
2011-10-12
董外平(1983-),男,湖南衡陽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生,主要從事中國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