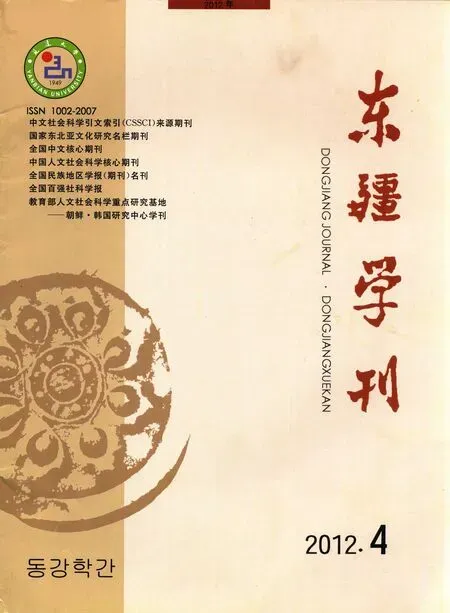生態批評視閾中的《污染海域》
宿久高,楊曉輝
《污染海域》是日本當代推理小說作家西村京太郎的代表作之一,發表于1971年。作品發表之際,日本先后發生了“水俁病”、“森永奶粉事件”、“薩利德邁安眠藥事件”等多起公害事件,引起了日本社會的強烈反響和廣泛關注。為了應對和消除這些公害事件對日本國家和社會產生的嚴重后果,日本政府積極采取對策,先后制定和頒布了“公害對策基本法”(1967)、“大氣污染防治令”(1968)和“噪音防治法”(1968)等一系列法規,并認定“疼痛病”、熊本與新瀉的“水俁病”等為公害病。這一系列舉措,為日本環保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并指明了方向[1](8)。
《污染海域》講述的是一起公害污染、公害殺人事件。小說以律師中原收到一封來自17歲自殺少女梅津由佳的來信拉開序幕。該少女——主人公梅津由佳是新太陽化工廠的一名工人,工廠位于伊豆半島的錦浦。由佳因長時間在廢氣彌漫的環境中工作,患了哮喘病,痛苦至極。她認為這與自己從事的工作有關,因而要求公司補償,可公司的回答卻是:如果住院就開除。中原律師雖然能干、正直、善良,但為了生計,也不得不以代理能賺錢的訴訟案件為先。所以,由佳的信就被擱置起來。直到某一天,中原從報紙上得知由佳從游船上投海自殺,良心受到譴責,才奔赴現場調查這起事件。在調查過程中,他遇到了質樸的高中教師吉川,這是一位領著一群高中生投身于家鄉環保事業的教師。同時,他還遇到了“公害調查團”的團長、公害“專家”——吉川的老師冬木教授等人。冬木等人出于私利、竟然無視公害事實,公然斷言該地域沒有污染。作者以中原出于正義,著手調查少女投海自殺事件為主線,揭示了海洋污染給民眾帶來的身心傷害,凸顯了“利己主義”等精神生態危機對人類的危害這一主題。
生態文學研究者魯樞元曾將生態學分為“自然生態學”、“社會生態學”和“精神生態學”,并將梁漱溟指出的“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人與自我的關系”等人的復雜性與其提出的生態學三分法中的自然生態、社會生態、精神生態相對應。他認為:就現實的人的存在而言,人既是一種生物性的存在,又是一種社會性的存在,同時,更是一種精神性的存在。其觀點強調了精神生態在人類社會中的位置和研究價值。[2](146-147)筆者認為,該作品對人類精神生態的積極探索,使得小說成為了一部充分展示作者生態智慧的作品。小說的題目《污染海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生態觀及對現代社會的深度思考。
一、人與自然的對話
“我們關于自然的知識及對自然的理解,對我們的行為具有決定意義”[3](28)。早在日本古代,人與自然的對話已悄然開始。那時的人類尚未意識到自我,對自然抱有依偎和敬畏之情。隨著歷史的推移,特別是到了近代,日本的現代化進程加快,工業立國思想浸潤著人們的心靈,人類中心主義開始抬頭。自然成了被征服的對象,人與自然的伙伴關系和平等對話關系被徹底摧毀,處于矛盾與對立之中。誠然,大自然是脆弱的,但只要不過分施壓,它仍然富有彈力和韌性[4](93)。正是因為人類的施壓超過了自然的承受力,大自然才對人類的勝利進行報復。西村京太郎的《污染海域》,描寫的正是日本戰后在經濟復興、工業發展過程中破壞自然、破壞環境,導致大量公害事件發生,從而招致嚴重后果的過程。
上世紀 50年代,日本在四日市建起了全國第一個石油聯合企業城,工廠廢水排入伊勢灣,使得海水變臭,大氣渾濁。僅幾年光景,整座城市便黃煙彌漫,上空幾百米厚度的煙霧中漂浮著多種有毒氣體和有毒的重金屬粉塵[5](31)。1961年,四日市哮喘病大發作,市民在病痛的折磨中艱難度日,幾年后,一些哮喘病患者不堪痛苦而自殺[1](8)。上世紀 60年代后期,日本經濟繼50年代后又迎來了以出口急劇增長為背景的第二個高速增長期,增長速度維持著世界第一的水平。70年代,石油制品的消費量達到了世界最高水平。然而,這種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以犧牲農業、林業和漁業為代價的。梭羅曾經慨嘆道:“感謝上帝,人類現在還飛不起來,所以還不能像蹂躪地球一樣去蹂躪天空。”[4](99)但是,一百年后,梭羅的感慨不僅在美國,在大洋彼岸的東瀛也變成了現實,藍天、大地、海洋無不充滿了人類破壞的痕跡。《污染海域》就是在這種歷史和現實的大背景下創作出來的。
《污染海域》發表于1971年9月,正值日本四日市哮喘病患者劇增之時。小說中的錦浦海域,曾是一個海天一色的小漁港。自從這里建了化工廠以后,昔日美麗的自然、這片純凈的海域和清新的空氣被化學工業吞噬殆盡,人們終日為污濁的海水和空氣所困繞。片片褐色的油污漂浮在海面,臭氣熏天;座座煙囪吐出的毒煙形成厚厚的天幕,令人窒息。“殘缺不全的大自然,成了一首被抽掉了某些更令人興奮的樂章的交響樂,一本失去了很多章節的書。”[4](91)工業霸權摧毀了原有的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人類對自然的肆意掠奪與侵占,招致了自然對人類的懲罰。冬木教授前一天還斷言,錦浦海域沒有污染,而遇害后被扔入大海的他,尸體上卻沾滿了油污。冬木的死被斷定為他殺,是因為他死后,胃里灌滿了偽造的干凈鹽水,而尸體上卻沾滿了海里漂浮的廢油。這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另一方面,高中教師吉川帶領著高中生“專家”,建起了“錦浦高中公害研究所”,三年如一日,奔走于山間、海邊,做著親近自然、拯救自然的努力。小鎮的每個角落,都留下了他們的身影和足跡。鯉魚旗下,每隔一小時記錄一次風向;用溫度計測氣溫,用手表記時間。手里的溫度計各式各樣,女學生拿的,還有可愛的人偶形溫度計。鯉魚旗也好,溫度計也罷,都是他們走進深山、靠近大海、與自然對話的工具。他們用最柔和的方式感悟自然,實現人與自然之間最質樸的對話。
二、人與人的對話
當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破壞了人與自然的和諧時,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對話關系也被無情摧毀。梅津由佳在與廠方交涉無果的絕望中最終投海自殺。律師中原正弘出于自責和義憤,毅然挺身投入到案件調查之中。但隨著調查的深入,中原意識到公害調查和訴訟是一場困難重重的持久戰。人與人的關系,因利益的不同而處于相互排斥甚至尖銳對立的狀態。
主人公梅津由佳因工廠不承認自己患病是公害所致,而住院治療又要被開除,于是在絕望中走向絕路。她在投海自殺之前,曾試圖與企業管理層對話,期望通過對話喚起對生命的共鳴,尋求一種生命關懷。但企業在巨大的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又怎能愿意開辟對話的空間!律師中原幾度去找新太陽化工廠的管理人員,甚至去找企業老板佐伯大造討說法,希望通過對話,喚回理性,為那些控訴無門的漁民開拓可能的生存空間,但也是無果而終。
受害的漁民在對話無果的情況下,竟也采取了默許公害的態度。查明公害產生的原因,超出一般漁民的知識和能力范圍。如要漁民舉出因果關系的證據,實屬不易;若通過科學檢驗方法取證,勢必拖延訴訟,而且也無力承擔巨額的訴訟費用。而受害人若等得到賠償后再行醫治,恐怕早已處于絕境之中。這一點,從中原的嘆息中也可窺見一斑。
受害的漁民為了生存,抑或為了眼前利益,只好選擇了自欺欺人和欺騙他人的妥協方式。與其等待漫長的公訴,還不如在謊言的世界里實現人與人的對話。這種對話可以換來企業捐贈的市立醫院,換來高中的若干現代化教學設備,更重要的是還可以將污染的海產品賣給不知情的市民而換來維持生計的鈔票。
利己主義的魔咒已經將人與人的對話推向了不可實現的境地。原為師生關系的冬木教授與高中教師吉川之間竟然展開了師生對決。受雇于新太陽化工廠的冬木,率領“調查團”,僅用兩天時間就完成了所謂的公害調查,并發表了“中間報告”,向當地民眾宣布該地域沒有公害。為了眼前的蠅頭小利,背棄了道德良知和責任。但冬木遭害前,與自己的學生吉川之間的最后一次對話是富有良知和值得慶幸的。冬木在彌留之際,終于被眼前這個領著一群天真的高中生,進行空氣和海水污染檢驗的吉川所感動,他讀完了吉川和高中生們記錄的公害日志后,在最后一頁寫道:“慚愧。我竟然不如這些高中生。吉川君,你是對的。”[6](206)
冬木與吉川通過對話達到了生命共識,只是這種共識來得太遲,冬木在被企業利用后還是難逃被殺害的厄運。
三、人與自我的對話
人類精神生態的健康是當今自然生態健康的前提,而健康的人類精神生態需要汲取自然生態中的健康營養[7](88)。在被人類異化的自然面前,人類的精神生態也無法保持平衡,這其中包含人與自我對話的建構失衡。在工業立國的背景下,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農民、漁民變身為工人,農村人口急劇流向城市,人的心態也隨之發生變化。人自身原本包含精神與物質、肉體與心靈兩個方面。作為完整的人,應該兼顧兩者[8](11)。但現代人在物質欲望的驅使下,往往看重物質欲望的滿足,而忽略了精神追求,精神受到了污染。這也是導致人與自然關系由和諧走向沖突的根源所在。
在《污染海域》中,主人公中原由佳自殺前,人們并沒有深刻認識到受害者的苦痛和公害的危險。觀念的改變源于由佳之死。律師中原在赴錦浦調查公害事件的途中,遇到一位出租車司機,司機的偏頗言論,在某種程度上與中原曾有過的想法不謀而合:企業進駐后,貧窮的小鎮搖身變成繁華的城市,高樓大廈拔地而起,有了酒吧,有了脫衣舞劇場,就連近處的藝妓,只要招呼,都會踴躍而至。那些整日喊“公害、公害”的家伙,真是煩死人。不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哪里有錢賺?但由佳的死令他幡然醒悟,開始自我反思,并從靈魂深處進行自我批判,進而毅然決然地投身于公害事件的調查中去。出租車司機的偏頗言論,非但未讓中原動怒,反而使他深刻反思自己此前的態度和行為。
錦浦的工廠、醫院均是新太陽化工廠老板佐伯大造出資建造的,整個小鎮都置于他的權利和金錢桎梏之下。物欲堵塞了人的心靈渠道,科技文明腐蝕了人的健康心態。在這個污染越來越嚴重的小鎮,人的精神空間也被侵蝕殆盡。
鎮里的公害事實一目了然,但在這位學者專家的“專業考證”下,錦浦搖身變成了一座活力四射、人們安居樂業、其樂融融的現代化小鎮。物質欲望的膨脹遠遠超過了自我精神欲求,“在自然生態系統蒙受嚴重損傷的同時,人們的精神狀態也在隨之惡化[9](36)。”
比利時生態學教授 P.迪維諾 (Paul Duvigneaud)早在 70年代初在他的《生態學概論》的最后一章中,就正式提出了“精神污染”這一概念[9](21)。這種精神污染具體體現在自我和道德感的喪失。人作為生態系統中的一個鏈條,自然萬物中的一名思考者,在敵對的人與自然的關系之中,是無法尋回原初意義的人的善良本性的。而三年來憑借一己之力和非凡見識,率領一群高中生,從事公害調查的高中物理教師吉川的行為,如同黑暗中的一抹曙光,讓有良知的人們在絕望中看到了生的希望。吉川憧憬的是一個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相處的美好世界。他與冬木的斗爭,可稱為“竹槍戰術”:一方是由所謂專家學者指揮的調查團,配備精良,一方是高中教師率領的學生團,工具簡單、粗陋;一方是直升機、發煙筒、二氧化硫自動檢測裝置,一方是自行車、鯉魚旗、學校化學實驗室、宣傳冊等。勢不均力不敵、幾乎赤手空拳的吉川,在幾近挫敗之時也沒有退縮。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認為,大眾幸福 (the general happiness)是唯一有價值的和值得追求的東西[10](59)。“從人類生存的角度看,以行動者的共同利益作為道德和行為的基礎優于僅僅以行動者的個人利益作為道德和行動的基礎[10](37)。”吉川的行為不是為了滿足自我欲望,他是通過自我反省、發現,并將大眾幸福和大家的共同利益作為自我價值實現的前提而付諸行動的。人類認識自我,是認識和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前提之一。只有這樣,人類才能擺脫自身行為的盲目性和愚昧性,真正主宰自己。只有清醒地認識自己,人類才能實現與自我的對話,進而超越自我,走向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美好未來。
四、結語
與自然為友,天長地久。生態文學表層上探討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但求其深層研究意義,是探討人與人、人與自我等精神層面的問題。對于生態文學而言,也許自然環境只是外在的物態,更重要的是人的心態[11](378)。所以,從生態批評角度解讀西村京太郎的《污染海域》,深入分析和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社會和經濟發展與自然的關系這一作品主題,具有重要的現實和理論意義。這不僅能使我們清晰地了解上個世紀 70年代日本社會的生態環境和精神意識狀態,而且為我們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的和諧對話,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文明社會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啟迪。
[1][日 ]佐島群巳:《學校中的環境教育》,東京:國土社,1992年。
[2]魯樞元:《生態文藝學》,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3][德 ]漢斯· 薩克塞著:《生態哲學》,文韜譯,北京:東方出版社 ,1991年。
[4][美 ]唐納德·沃斯特著:《自然的經濟體系——生態思想史》,侯文蕙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
[5]張庸:《日本四日市哮喘事件》,《環境導報》,2003第 22期。
[6][日 ]西村京太郎:《污染海域》,東京:德間書店,1987年。
[7]鐘燕:《生態批評視野中的 <海風下>:一個“藍色批評”個案分析》,《湖南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0年。
[8]吳先伍:《現代性境域中的生態危機:人與自然沖突的觀念論根源》,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
[9]魯樞元.《生態解困:期待一場精神革命》,《綠葉》,2007年第 3期。
[10]魯樞元.《生態批評的空間》,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
[11]陳真.《當代西方規范倫理學》,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
[12]魯樞元.《精神生態與生態精神》,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