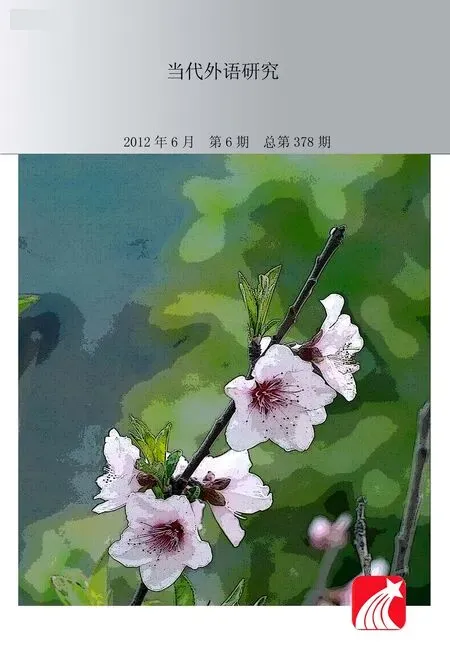哲學與翻譯①
羅斯瑪麗·阿羅約(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著
梁真惠(北京師范大學)譯
在整個西方哲學史上,無論是翻譯實踐還是翻譯實踐提出的哲學問題都鮮有人關注。實際上,直到近期,哲學思潮和翻譯研究的關系顯然也是失衡的:翻譯家或者是翻譯理論家對哲學的興趣遠遠大于哲學家對翻譯問題的思考(Pym 2007:25)。直到20世紀最后幾十年,當代西方哲學越來越意識到哲學和翻譯之間無法回避的聯系時,這種動態關系才得以改變。有人說翻譯對當代哲學思想不僅產生了濃厚興趣,而且到了“著迷”的程度,因為當代西方哲學提供了一種“觀念”,由此展開了“哲學可能性(如果不是實際發生的話)問題的討論”(Benjamin 1989:9)
哲學的可能性問題與根深蒂固的傳統語言觀和翻譯觀密不可分。法國當代哲學家雅克·德里達的解構主義哲學(尼采之后最有影響力、最活躍的哲學思潮之一)思考的就是哲學與語言以及翻譯之間的關系。他認為,哲學要為自身保留一席之地,即保留系統探索真理的特權,就不得不承認“單一明確意義”(univocal meanings)存在的可能性。這個單一明確的意義能夠擺脫任何一種語言的限制,在語言之間穿梭時始終保持不變。那么,相信可譯性的存在也必然意味著堅信翻譯是“意義或真理在語言之間的傳輸(transportation)”(Derrida 1988:140)。
1.翻譯即意義的傳輸:本質主義翻譯觀
影響深遠的本質主義翻譯觀完全植根于西方形而上學和猶太基督教傳統的一個根本假設,即形式與內容(或語言與思想、所指與能指、語詞與意義等二元對立概念)不僅是可以分離的,而且是相互獨立的。語言被視為表達思想的工具,傳達著一個固定不變的意義。語言的作用就是外衣,保護著它所攜帶的意義,從而使意義能夠被安全地送到這里或那里。
上述觀念的基本理論依據可以追溯到柏拉圖的本質主義(essentialism)哲學傳統那里。蘇格拉底在《克拉底魯》(Cratylus)中這樣推理事物的本質:既然事物“不可能在同一時間同等地屬于所有的人,也不可能總是屬于所有的人”,那么它們一定是獨立于主體而存在的,并且“有它們自身的特性和一成不變的本質”(Hamilton & Cairns 1961:424-425)。這樣一來,如果“事物不受主體的影響”,如果“名稱本質上含有一個(永恒的)真理”,這個永恒真理代表它們所指的事物,那么我們就可以認為這個“真理”的確能夠超越任何一種語言系統的形式束縛,在任何時間和任何地點都可以完美地復制出來,哪怕是語詞或者語境,甚至語言發生了變化(譯者按:這就是柏拉圖‘絕對存在’觀念的由來)。
主體(人)與客體(事物)可以分離,意義與語詞可以分離,這種觀點傾向于認為翻譯就是一種非人稱(impersonal)的轉移,即本質意義在語言之間的游走。在這個過程中,必須抗拒或譴責譯者的干涉作用。實際上,對譯者這個中介人(agency)的拒斥一直以來都是西方傳統翻譯理論最關心的問題之一。一般來說,這些規定性的傳統理論旨在維護譯者與作者、譯文與原文之間壁壘森嚴的界線。
本質主義翻譯觀也存在其倫理依據,人們常常用外衣這個比喻來闡釋它。語詞是外衣,用以保護意義這個裸體,并賦予它風格。譯者不允許去觸摸文本的意義裸體,只需要小心改變包裹它的外衣。這個比喻形象地說明譯者的任務就是機械地服侍,對原文抱一種敬畏的態度,不能越雷池一步(Van Wyke 2010)。本質主義翻譯觀拒絕接受譯者的創造性角色,摒棄譯文的政治性作用,否認翻譯對身份構建和文化構建的影響,并且秉持古老的偏見:與創作相比,翻譯是一種次要的衍生形式。這種觀念把譯者視為一個無所作為的隱形者,從而大大降低了譯者地位。
2.翻譯即操控與變形:后尼采主義模式
德里達明確指出翻譯與哲學之間的親密關系,他的思想來源于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對西方形而上學的批判。“尼采最先把哲學任務和對語言的批判性反思聯系起來”(Foucault 1973:305)。尼采對西方形而上學的批判成為當代各種反本質主義哲學思潮(anti-foundationlist trends)的橋頭堡,比如后現代主義、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新實用主義哲學等等,開辟了質疑探詢的新道路,如女性主義研究和后殖民主義研究。
1873年尼采在《論非道德意義上的真理與謊言》(“On Truth and Lies in a Nonmoral Sense”)一文中概括了實質上是“反柏拉圖主義”語言觀的理論基礎。他認為,語言毫無疑問是人創造的,沒有任何本質意義和概念能夠與包裹它的語言纖維清晰地分離,因而意義和概念無法被完整地傳輸。語言是任意的約定俗成的符號系統,概念是這個系統的一部分,它必然是人創造的,是“來源于不相等事物的等式”(譯者按:從并不相同的現實事物中概括出一個共同的等式即概念)。這個結論可以如此證實:雖然我們從來沒有在自然界中發現那片理想的“葉子”,也就是“葉子原型,其他所有的葉子不管是編織的、素描的、涂彩的、卷曲的,還是油畫的,都從這個原型而來”(1999:83),但我們仍然把它當作一個概念來使用。簡而言之,語言之所以起作用就在于約定俗成的力量引導我們忘記那些差異,幻想著那個“相同”或“共同”的東西能夠被我們復制出來。
概念和意義不是被發現的,而是被建構的。由于建構它們的語境永遠不可能相同,因此概念和意義永遠不可能被完全復制。每一片葉子都是不同的,不可能忠實地復制那個理想的原型葉子,因為原型葉子只存在于我們的習慣思維中。同樣,每一個文本的復制都不可能是那個所謂原文的完整意義,而是建構了另外一個不同的文本,這個文本攜帶了它(再次)成文時的歷史印記和社會語境。這個建構出來的文本也許被接受,也許被拒絕,甚至可能被視為對原文的可靠復制。譯文和原文這種對立關系的形成不可能獨立于語境之外和我們的習慣思維之上,“而一定是建構出來的和普遍認可的”,因此“總要受到不斷的修正”(Davis 2002:16)。
尼采對柏拉圖思想進行批判,讓我們認識到翻譯不再是本質意義在不同語言和文化間的游移。就翻譯概念而言,這種批判讓“我們不得不用變形(transformation)這個概念來代替它:即一種語言或文本對另一種語言或文本進行的操控和變形”(Derrida 1978:20)。這種批判產生了廣泛影響,早期對這些影響進行闡釋的有博格斯(Jorge Luis Borges)。他于1935年出版《〈一千零一夜〉的譯者們》,把翻譯看成是寫作的一種合法形式。此外,他審查了19世紀《一千零一夜》的幾種阿拉伯文本翻譯,指出盡管譯者明確聲稱其譯文忠實于原文,但譯本卻歷史性地證明他們對翻譯的態度和觀點。在這幾種譯文中,異化和歸化并用,重新建構原文,凸顯了譯者的作用:譯文成了一面鏡子,從中折射出譯者本人的興趣和當時的社會歷史語境(Borges 2004:94-108)。博格斯沒有批評《一千零一夜》譯者們的不忠實譯法,反而肯定了他們在翻譯過程中的建構作用,為我們揭開了今天已經成為翻譯學研究領域重要論題的討論序幕:翻譯在文化建構和身份建構中的作用;異化和歸化策略之間的不對稱性;最重要的是譯者的介入作用;以及翻譯使“創作”的傳統觀念變得復雜化等問題。
作為原文和譯文關系中不容忽視的創造性要素,“差異”(difference)已經成為當代各種哲學思潮的一個關鍵詞匯,這或明或暗地揭示了后尼采哲學對翻譯的影響。譯者在翻譯時不可避免地要做出種種選擇,因此,在譯入語允許的情況下對原文進行改寫時,譯者必然顯形。這種深刻的洞察使翻譯研究最終擺脫了兩千多年來貶低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創造性作用的傳統偏見(試比較Venuti 1995)。
3.人文學科的翻譯轉向
尼采對“生產意義的語言”進行了重新思考,闡釋了真理和習慣思維之間的關系,也就是真理和權力之間的關系,不僅對當代哲學和翻譯研究,而且對整個人文學科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甚至可以說當今人們對語言的再次青睞以及語言對當代思想的重要作用實際上已經模糊了不同學科(這些學科的目標都圍繞著主體性和文化展開)之間的界限。
在這種語境下,翻譯——被視為一種操控和變形——變得至關重要,不僅重新界定了文化被建構的種種方式以及文化間的相互聯系,而且也重新界定了文化概念本身,即文化是翻譯的一種形式(Bhabha 1994)。在比較文學領域,與翻譯相關的論題正被用來重新構建該學科的研究范圍和研究目標(Apter 2006)。同樣,翻譯問題對于跨學科研究變得意義重大,它揭示了語言政策對殖民化的影響(試比較Rafael 1988)以及女性研究和翻譯研究之間的關系(試比較Simon 1996)。
語言和權力糾纏在一起,這種深刻的認識讓我們日益關注自己是如何構建和關聯異文化的,以及這種關聯又是如何改變和重新界定本民族文化的。因此,對翻譯——無論是一般意義上的翻譯活動還是翻譯概念本身——的日益重視也昭示著對國際化和全球化問題的普遍關注。翻譯和全球化之間的聯系使專家學者們不僅提出了人文學科的“翻譯轉向”,而且實際上把人文學科干脆就稱為“翻譯研究”(Bachmann-Medick 2009:11)。
令人激動的是,當代哲學介入翻譯研究開辟了翻譯研究的各種新方向,也足以證明翻譯已經擺脫傳統的本質主義觀念。這種介入給翻譯學科注入新的活力,讓我們認識到譯者的政治身份在翻譯中的重要作用。也許我們接下來的任務就是著力運用我們從當代哲學和翻譯研究關系中獲得的這種創建性洞見,開始對譯者——包括筆譯者和口譯者——職業領域的研究。
附注:
① 原文2010年刊登于《翻譯研究手冊》(HandbookofTranslationStudies)第一卷第247頁至251頁上。作者Rosemary Arrojo教授書面授權梁真惠翻譯發表該文。
Apter, Emily.2006.TheTranslationZone:ANewComparativeLiterature[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chmann-Medick, Doris.2009.Introduction: The translational turn [J].TranslationStudies2(1): 2-16.
Benjamin, Andrew.1989.TranslationandtheNatureofPhilosophy:ANewTheoryofWords[M].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Bhabha, Homi K.1994.TheLocationofCulture[M].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Borges, Jorge Luis.2004.The translators of theThousandandOneNights(2ndedition) [A].In Lawrence Venuti (ed.).TheTranslationStudiesReader(Esther Allen trans.)[C].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94-108.
Davis, Kathleen.2001.DeconstructionandTranslation[M].Manchester: St.Jerome Publishing.
Derrida, Jacques.1978.Positions(Alan Bass trans.) [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errida, Jacques.1988.TheEaroftheOther:Otobiography,Transference,Translation(Peggy Kamuf trans.) [M].Lincoln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Foucault, M.1973.TheOrderofThings:AnArchaeologyoftheHumanSciences[M].New York: Vintage.
Hamilton, E.& H.Cairns.1961.TheCollectedDialoguesofPlato(Benjamin Jowett trans.) [M].Princeton: Princeton UP.
Nietzsche, Friedrich.1999.On truth and lies in a nonmoral Sense [A].In Daniel Breazeale (trans.& ed.)PhilosophyandTruth:SelectionsfromNietzsche’sNotebooksoftheEarly1870’s[C].New York & Amherst: Humanity Books.79-97.
Pym, Anthony.2007.Philosophy and translation [A].In Piotr Kuhiwczak & Karin Littau (eds.).ACompaniontoTranslationStudies[C].New York: Multilingual Matters.24-44.
Rafael, Vicente.1988.ContractingColonialism:TranslationandChristianConversioninTagalogSocietyunderEarlySpanishRule[M].Ithaca: Cornell UP.
Simon, Sherry.1996.GenderinTranslation:CulturalIdentityandthePoliticsofTransmission[M].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Van Wyke, Ben.2010.Imitating bodies, clothes: Refashioning the Western conception of translation [A].In James St.Andre (ed.).ThinkingthroughTranslationwithMetaphors[C].Manchester: St.Jerome.17-46.
Venuti, Lawrence.1995.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AHistoryofTranslation[M].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