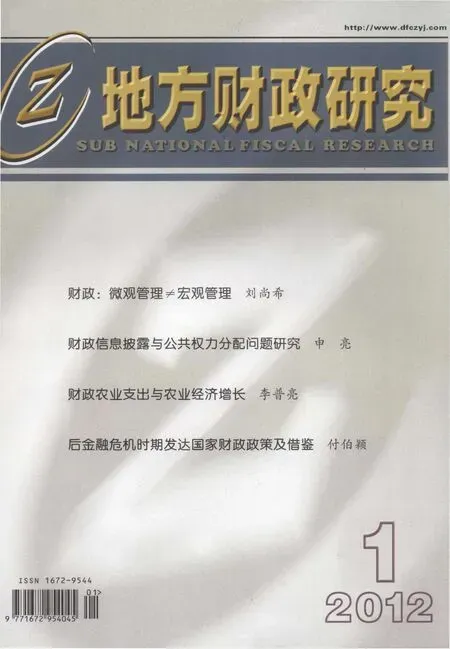進(jìn)一步修訂完善我國土地稅制
楊孟著
(中南大學(xué)公共政策與地方治理研究中心,長沙 410083)
一、改“城鎮(zhèn)土地使用稅”為“土地稅”
《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zhèn)土地使用稅暫行條例》(下稱《條例》)第二條對“城鎮(zhèn)土地”的范圍作了這樣的規(guī)定,“城市、縣城、建制鎮(zhèn)、工礦區(qū)范圍內(nèi)”使用的土地,不包括“非城鎮(zhèn)土地”。顯然,這樣的規(guī)定是很不合理的。從理論上講,土地是不可再生資源,是基礎(chǔ)性自然資源和戰(zhàn)略性經(jīng)濟(jì)資源,理應(yīng)以所有土地資源(規(guī)定免繳者除外)作為土地稅的計(jì)稅依據(jù)。事實(shí)上,“城鎮(zhèn)”一詞對“土地”的范圍限制太死,與“寬稅基”稅制改革方向相悖。另外,“使用”一詞也相當(dāng)模糊,若以此為依據(jù),試問:囤積、閑置的土地到底是“使用”還是“未使用”?稅種稱謂改“城鎮(zhèn)土地使用稅”為“土地稅”,并相應(yīng)擴(kuò)大土地稅征收范圍后,就不會出現(xiàn)此類問題。因?yàn)榘凑諊H上通行的做法,土地上附著物產(chǎn)權(quán)所有人或土地租約人即為該土地的法定納稅人。
事實(shí)上,《條例》第六條“下列土地免繳土地使用稅”中的第五款“(五)直接用于農(nóng)、林、牧、漁業(yè)的生產(chǎn)用地”,指的就是“非城鎮(zhèn)土地”。由該條款與《條例》第二條有關(guān)規(guī)定出現(xiàn)的“前后矛盾和相互沖突現(xiàn)象”來理解,《條例》關(guān)于“城鎮(zhèn)土地”的范圍實(shí)際上已包括了所有的“城鎮(zhèn)土地”和“非城鎮(zhèn)土地”。否則,《條例》第六條第五款也就多此一舉了,不屬“城鎮(zhèn)土地”的范圍,當(dāng)然也就不屬城鎮(zhèn)土地使用稅的征收范圍。
二、改“從量計(jì)征”為“從價計(jì)征”
《條例》第三條“以納稅人實(shí)際占用的土地面積為計(jì)稅依據(jù),依照規(guī)定稅額計(jì)算征收”,應(yīng)修改為“以納稅人實(shí)際占用的土地評估價值為計(jì)稅依據(jù),依照適用稅率計(jì)算征收”,也即改“從量計(jì)征”為“從價計(jì)征”。同時,應(yīng)補(bǔ)充完善有關(guān)土地資產(chǎn)評估的程序、方法、遵循的原則和時間間隔等內(nèi)容。
(一)實(shí)行“從量計(jì)征”存在四大弊端
1.扭曲計(jì)稅行為。在“從量計(jì)征”條件下,“依照規(guī)定稅額計(jì)算征收”中的“規(guī)定稅額”的確定,是“根據(jù)市政建設(shè)狀況,經(jīng)濟(jì)繁榮程度等條件,確定所轄地區(qū)的適用稅額幅度”(《條例》第五條)。在實(shí)際計(jì)稅過程中,以“適用稅額幅度”(計(jì)稅時體現(xiàn)為稅率檔次)作為土地稅的計(jì)稅依據(jù),“門牌號屬于某地段,就按某地段稅率計(jì)征”便成了既定約束條件下唯一可行的計(jì)稅辦法。結(jié)果導(dǎo)致部分納稅人采用“堵前門開后門或側(cè)門”變更門牌號降低稅率檔次等手段進(jìn)行“合理避稅”行為的產(chǎn)生,造成土地稅收的大量流失。如長沙市某一中型企業(yè),其廠門位于人民路某繁華地段,稅率為每平方米3.2元,而廠區(qū)中部和尾部則位于一般居民生活區(qū),稅率僅為每平方米1.1元。對于這種情況,“門牌號屬于某地段,就按某地段稅率計(jì)征”便成了既定制度約束條件下唯一可行的計(jì)稅辦法。正是源于該辦法本身存在缺陷所誘發(fā)的“合理避稅”動機(jī)的產(chǎn)生,該廠才按照法定的程序?qū)㈤T牌號由人民路某號改為某地區(qū)附某號,自然適用稅率也由每平方米3.2元降為1.1元,由此全年減少稅款近14萬元。湖南省地稅局發(fā)布《關(guān)于明確城鎮(zhèn)土地使用稅“適當(dāng)降低等級稅額”和“深度折減”政策的通知》(湘地稅發(fā)[1996]026號)一文,便是對“適用稅額幅度”確定方法存在嚴(yán)重弊端的最好佐證。
2.缺少收入彈性。稅收收入隨著國民經(jīng)濟(jì)的增長而有所增長,用稅收術(shù)語來說就叫做稅收收入彈性。從“土地稅”的性質(zhì)和《條例》規(guī)定的根本要求兩個方面來考察,其稅收收入的增長應(yīng)與國民經(jīng)濟(jì)的增長存在著很強(qiáng)的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可現(xiàn)行的“土地稅”計(jì)稅辦法根本不體現(xiàn)這種關(guān)系——增加“土地稅”收入只能靠提高稅率檔次唯一手段。2006年12月31日,國務(wù)院總理溫家寶簽署第483號國務(wù)院令發(fā)布國務(wù)院第163次常務(wù)會議通過的《國務(wù)院關(guān)于修改 骉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zhèn)土地使用稅暫行條例骍的決定》就證實(shí)了這一點(diǎn)。
3.無法反映納稅人經(jīng)營環(huán)境和行業(yè)特點(diǎn)因素。對于文化娛樂、飲食服務(wù)、商品流通等行業(yè)來說,它們的經(jīng)營成果跟所在地區(qū)的“市政建設(shè)狀況,經(jīng)濟(jì)繁榮程度”呈高度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而對于加工制造業(yè)來說,這種關(guān)系則十分弱小,或根本不存在關(guān)系。如果按照現(xiàn)行的計(jì)稅辦法計(jì)征“土地稅”,就會造成土地占用面積較小的某些服務(wù)業(yè)靠國家無償提供的“經(jīng)營環(huán)境”大發(fā)其財(cái);土地占用面積較大的某些由政策性投資等形成的加工制造業(yè)則身受其害。這既不符合稅收的公平與效率原則,也違背了區(qū)別對待、負(fù)擔(dān)合理的稅收政策。
4.不符合稅制簡化原則。稅率檔次多、不規(guī)范、可操作性差,難以適應(yīng)市場經(jīng)濟(jì)條件下經(jīng)營情況復(fù)雜多變的需要。
(二)實(shí)行“從價計(jì)征”的條件已經(jīng)成熟
如果說“土地稅”實(shí)行“從量計(jì)征”是因其開征之時(1989年1月1日)不具備實(shí)行“從價計(jì)征”的條件的話,那么,時至今日實(shí)行“從價計(jì)征”的條件則完全成熟。主要體現(xiàn)在:一是土地管理工作納入了科學(xué)化、法制化的軌道。土地的使用、轉(zhuǎn)讓和交易日趨規(guī)范化。二是土地交易市場較為發(fā)達(dá)和完善,土地價格日趨市場化。三是土地資源的相對稀缺性日益突出。四是土地資產(chǎn)評估等社會中介組織和機(jī)構(gòu)較為發(fā)達(dá)和完善。
從理論上講,以土地資源為計(jì)稅依據(jù)的稅收屬于資源稅的范疇。隨著財(cái)政部、國稅總局《新疆原油、天然氣資源稅改革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的發(fā)布實(shí)施,資源稅計(jì)征方式正式由“從量計(jì)征”改為“從價計(jì)征”。綜合我國當(dāng)前資源稅改革的背景和趨勢考察分析,無論是將來繼續(xù)將土地稅作為一個獨(dú)立的稅種,抑或是將土地稅調(diào)整為資源稅的一個稅目,由“從量計(jì)征”改為“從價計(jì)征”都是繞不過去的一道“坎”。在這種意義上,不失時機(jī),加快“轉(zhuǎn)軌”,對于積極配合和穩(wěn)步推進(jìn)資源稅改革必將產(chǎn)生深遠(yuǎn)的影響。
(三)實(shí)行“從價計(jì)征”的意義
土地稅由“從量計(jì)征”改為“從價計(jì)征”后,除了能夠從根本上消除土地稅“從量計(jì)征”存在的弊端外,還具有以下三個優(yōu)點(diǎn):
1.能夠充分發(fā)揮稅收在促進(jìn)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和優(yōu)化資源配置中的功能作用。某一稅種稅收功能作用效果的好壞,取決于該稅種計(jì)征效果的好壞。因“土地稅”實(shí)行“從價計(jì)征”并同時計(jì)征附加稅后具有更加符合稅收彈性、公平和效率原則等顯著優(yōu)點(diǎn),當(dāng)然發(fā)揮這種作用的強(qiáng)度和力度也就優(yōu)于“從量計(jì)征”了。
2.能夠增加稅收收入透明度和收入剛性。從稅收制度上徹底堵塞“土地稅”征管方面存在的“合理避稅”漏洞,減少國家稅收的大量流失。
3.符合國際慣例。“從價計(jì)征”是目前世界上發(fā)達(dá)國家普遍采用的計(jì)征方法。如日本的地價稅就是采用“從價計(jì)征”的形式。
三、適應(yīng)“從價計(jì)征”需要,規(guī)范完善土地稅稅目、稅率和免繳范圍
(一)研究制定“土地稅”稅目
綜合考慮我國的土地政策、土地用途、土地改良程度等因素,科學(xué)合理地設(shè)置“土地稅”稅目。這里僅提供一個思路,具體的稅目確定依據(jù)和方法從略。值得注意的是,稅目應(yīng)宜細(xì)不宜粗,也即要保持一定的稅目數(shù)量,以利于征收管理,使其稅制更具實(shí)用性和可操作性。《條例》第六條所列示的免繳土地稅的七種情形均可單獨(dú)地作為“土地稅”稅目。這樣處理后,可以不必再設(shè)置減免稅條款,如有減免稅事項(xiàng),只需在適用稅率條款中規(guī)定其“減免稅事項(xiàng)”稅目適用零稅率或優(yōu)惠稅率即可。不過,我國法律法規(guī)大都習(xí)慣于單獨(dú)設(shè)置減免稅條款,很少采用“減免稅事項(xiàng)”稅目實(shí)行零稅率政策的做法。
(二)科學(xué)設(shè)計(jì)“土地稅”適用稅率
《條例》第五條規(guī)定了各級政府應(yīng)“根據(jù)市政建設(shè)狀況,經(jīng)濟(jì)繁榮程度等條件確定所轄地區(qū)的適用稅額幅度”。實(shí)行“從價計(jì)征”后,該條應(yīng)修改為“根據(jù)市政建設(shè)狀況,經(jīng)濟(jì)繁榮程度等條件確定與各稅目相應(yīng)的適用稅率”。“適用稅率”包括固定比例稅率和超額累進(jìn)稅率。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對于土地閑置和囤積行為(未改良土地),應(yīng)采用懲罰性的超額累進(jìn)稅率;對于與經(jīng)營環(huán)境呈高度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的行業(yè),如文化娛樂、飲食服務(wù)等行業(yè),應(yīng)在稅率設(shè)計(jì)上采用較高的固定比例稅率;對于其中洗浴按摩等某些高消費(fèi)行業(yè),可考慮在固定比例稅率的基礎(chǔ)上計(jì)征附加稅;對于與經(jīng)營環(huán)境呈弱相關(guān)或不存在相關(guān)關(guān)系的行業(yè),應(yīng)在稅率設(shè)計(jì)上采用較低的固定比例稅率;對于應(yīng)該給予一定的稅收照顧和扶持,但又不在“免繳范圍”之內(nèi)的產(chǎn)業(yè)和產(chǎn)品(如高新技術(shù)企業(yè)),除了采用較低的固定比例稅率外,可考慮實(shí)行標(biāo)準(zhǔn)扣除額制度。
(三)規(guī)范完善“土地稅”免繳范圍
《條例》第六條“下列土地免繳土地使用稅”分七款分別對七種情形下的土地稅免繳范圍作了明確的規(guī)定,但仍有不全面和欠妥之處,需要進(jìn)一步補(bǔ)充完善。建議將“(三)宗教寺廟、公園、名勝古跡自用的土地”修改為“(三)宗教寺廟、非盈利性名勝古跡、公園等用地”;補(bǔ)充增加“(八)企業(yè)‘三廢’治理及福利設(shè)施、環(huán)境綠化用地”;補(bǔ)充增加“(九)居民住宅(未超出規(guī)定面積)、保障性住房用地”。
四、將城建稅歸并為“土地稅”
城市維護(hù)建設(shè)稅的計(jì)稅依據(jù)為納稅人實(shí)際繳納的增值稅、消費(fèi)稅和營業(yè)稅。事實(shí)表明,該計(jì)稅辦法存在重復(fù)征稅,不能體現(xiàn)權(quán)利與義務(wù)相對等原則,與分稅制體制(涉及國稅和地稅兩個稅務(wù)機(jī)關(guān),特別是涉及有關(guān)查補(bǔ)征收及其代理征收的激勵問題)沖突,以及加大稅收政策協(xié)調(diào)難度等弊端。將城建稅歸并為土地稅,納入土地稅制,這些問題(包括城鄉(xiāng)政策有別問題)將不復(fù)存在。
〔1〕 楊孟著.城鎮(zhèn)土地使用稅計(jì)稅辦法探索[J].湖北財(cái)政研究,1994(11).
〔2〕 楊孟著.我國城鎮(zhèn)土地使用稅計(jì)稅辦法存在的問題及改進(jìn)設(shè)想[J].財(cái)會月刊,2009(2).
〔3〕 楊孟著.改進(jìn)城鎮(zhèn)土地使用稅計(jì)稅辦法芻議[J].稅收征納,2009(5).
〔4〕 楊孟著.土地稅也該“從價計(jì)征”了[N].財(cái)會信報(bào),201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