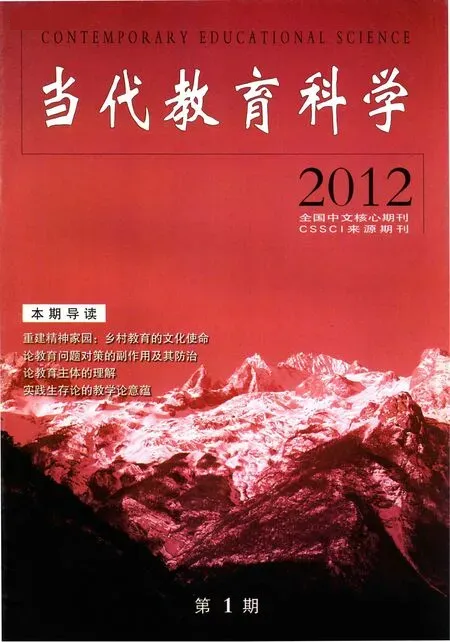實踐生存論的教學論意蘊*
● 張耀東 楊寶清 白向瑋
實踐生存論的教學論意蘊*
● 張耀東 楊寶清 白向瑋
教學論研究的實存論鏡像存在著諸多問題,實踐生存論為教學論走出困境提供了方法論指導。實踐生存論視域下的教學實踐活動是學生發(fā)展的生存方式,是人、自然和社會歷史的統(tǒng)一,是一個充滿意義的世界。現(xiàn)代教學論研究的實踐生存論轉向成為一種必然,教學論研究的主題論域、研究者角色、研究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都在發(fā)生著轉換。
實踐生存論;實踐;生存論;教學生存論
一、教學論研究的實存論鏡像
受近代實存論哲學的影響,教學論研究烙上了實存論的陰影。所謂實存論是近代哲學的存在論或本體論結構,即超驗的、抽象的實體本體論。它是古希臘存在論的一種極端的發(fā)展形式,古希臘存在論是關于存在是什么以及存在如何存在的理論。從根源上講,存在論是在人們先行地將一切具體存在者及其所指懸置起來,在徹底追問人的世界的最終根源、依據(jù)中產(chǎn)生的,存在論是對“存在之思”的哲學理論基礎。它所關注的不是我們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而是這個世界之外的超驗的彼岸世界,生活世界中的任何現(xiàn)象和事物都是不真實的存在,都只是存在者,并非“存在”本身,真正的“存在”,是隱藏在事物背后的超驗的、非歷史性的實體,其他一切現(xiàn)象、世界中的事物都是它外化、異化或者派生的結果。
教學論研究中的實存論鏡像主要表現(xiàn)為:(1)追求“終極知識”和“絕對真理”。由于實體本體論認為我們的感官所觀察到的事物并非真實的存在本身,隱藏在它后面的作為其基礎的超感官的終極存在才是真實的存在。因而,對客觀事物的認識不是真實的認識,而對隱藏其后的實體或本體的認識才是本質(zhì)的認識,認識了終極存在的本質(zhì)和規(guī)定性,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認識的問題,洞悉和獲得關于世界的終極知識和絕對真理。而通達實體的根本途徑就是運用理性通過概念和邏輯的演繹到達彼岸世界的終極存在,它體現(xiàn)了一種知識性的思維路向,傳統(tǒng)哲學的這一路向主要通過“知識論哲學”、“邏各斯中心主義”、“傳統(tǒng)理性主義”等概念形式表現(xiàn)出來。教學論研究便是如此,教學論在不斷地追問教學現(xiàn)象之后的教學本質(zhì),以本質(zhì)規(guī)律掩蓋豐富生動的教學現(xiàn)象;教學論在孜孜不倦地探求著鐵的理論規(guī)律,試圖使其能夠放之四海而皆準;教學論陷入一種理性抽象的思辨之中,而對活躍的變革性實踐卻冷落在旁。重視工具性價值,忽視目的性價值,將教學活動視為文化傳承的重要途徑和手段,課堂演變?yōu)椤爸R課堂”,不再是充滿生命氣息與活力的 “生命課堂”。課堂教學任務也只是停留在傳授知識、發(fā)展智力這一層面。(2)將復雜豐富多樣的生命活動簡化還原為單一抽象的邏輯。傳統(tǒng)哲學認為現(xiàn)實的世界是復雜多樣、變動不居的,復雜的事物總是由單一或確定的事物演化或派生出來的,并且統(tǒng)攝于單一的東西。為此它先把世界分裂為對立的兩個世界:本真世界與假相世界、理性世界與感性世界、必然世界與偶然世界、精神世界與物質(zhì)世界,在這兩個世界的二元對立中,前者是“本質(zhì)世界”,而后者是“非本質(zhì)的世界”,后者必須還原為前者并從前者那里獲得存在的根據(jù)。因此,人們在解釋事物時總是從先定的原則、本質(zhì)或普遍規(guī)律出發(fā)來說明事物存在的根據(jù)和合理性;同時,原則、本質(zhì)或普遍規(guī)律成為了現(xiàn)實生活中“應當”、“如何”和“怎樣”的標準或依據(jù),成為規(guī)范人的思想和行為的最終根據(jù)即本體。我們所說的整體主義、本質(zhì)主義的哲學理念正是這種“教條主義”思維方式的理論表現(xiàn)。傳統(tǒng)教學論將內(nèi)涵豐富的教學過程僅僅簡化為“五段教學法”、“教學五環(huán)節(jié)說”,始終用統(tǒng)一的環(huán)節(jié)和步驟衡量每一節(jié)課堂教學,無疑是一種還原主義,掩蓋了教學的復雜性,更抹殺了人自身活動的多樣性。(3)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如上所述,傳統(tǒng)哲學在理解世界時,傾向于把世界分裂為兩個二元對立的世界,這種把世界“一分為二”又“合二為一”的思維方法看似接近于對立統(tǒng)一的矛盾思維,但其目的恰恰是為了消解對立,以其中的一方去統(tǒng)攝、壓制、取代和否定另一方,從而確立“本質(zhì)”的一方。傳統(tǒng)哲學的這種思維方式實質(zhì)上是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與辨證的思維方式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教學論研究中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盛行,將事實與價值割裂、主體與客體對立、知識與能力及情感分離、理論與實踐脫離、科學世界與生活世界分隔,割斷了種種有機融洽的聯(lián)系。
實存論哲學的思維方式造成了教學論研究對現(xiàn)實人的生命的抽象、抹殺和遺忘。首先,它必然導致對人真實的創(chuàng)造本性和超越本性的抹殺和遺忘。追求本質(zhì)先在的還原主義和化約主義是實存論思維方式的重要特征,按照這種思維方式來理解現(xiàn)實人的生命、人的存在根據(jù),并不在于人自身,而在于人之外的彼岸世界中的先在本質(zhì)。人的一切存在和行動,甚至于人的未來,早已經(jīng)在先驗本質(zhì)里被規(guī)定了,先驗本質(zhì)是人之外或之上的絕對權威,是懸在人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而人則被理性抽空變成了一具沒有血肉、情感與欲望的僵尸。先驗本質(zhì)“反客為主”,成為宰制、統(tǒng)攝和總攬一切事物(包括人在內(nèi))的主體,人的主體性和自我發(fā)展、自我創(chuàng)造的本性被徹底閹割了。
其次,它必然導致對人多重的、豐富的矛盾本性的瓦解和抽象。如前所述,從兩極對立中理解事物即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是實存論基本的思維方式,在這種思維方式的支配之下,一切矛盾都被消解于無形之中。在多重矛盾關系中,存在著一種起基礎性、決定性作用的、充當中心和權威的一方面,并以此來支配和控制另一方面。依此去理解人,它所要尋找的就是人的“原型”,認為一旦找到了“原型”,就可以從它出發(fā)來解釋人的一切。結果,人多重的、豐富的現(xiàn)實生命整體被還原和化約成單一的一極,人被看成是理性的動物,而人非理性的一面被忽略和取消了;或者被理解為單一的與動物沒有根本區(qū)別的物質(zhì)性,如舊唯物論,或者被理解為單一的脫離自然的精神性,如唯心論,人不再被認為是物質(zhì)性和精神性的統(tǒng)一體;或者把人看成是現(xiàn)實性的存在,而抹殺了人的無限發(fā)展的可能性。
最后,它必然導致對人的歷史性與發(fā)展性的抹殺和遺忘。由于實存論把整個現(xiàn)實的世界分裂為雙向度的兩個世界,并以其中的一個世界統(tǒng)攝、支配著另一個世界,如本質(zhì)世界與現(xiàn)象世界,彼岸世界與此岸世界等等。因此,在實存論者看來,現(xiàn)實世界和人的發(fā)展只不過是后者向前者的無限趨近,是前者的工具和手段,前者是后者的目的。彼岸世界中的“實體”,是超歷史、在時間之外的至善至美的東西,是始終“在場的”萬變中之不變者,是永恒的存在,人的發(fā)展,總是受其牽引和控制,所以,人和整個世界的發(fā)展只不過是概念演繹或辨證發(fā)展過程的外在表現(xiàn)形式而已,只不過是一個假象和理性的“狡黯”。實存論的這種發(fā)展觀和歷史觀造成了對真實的人的發(fā)展和歷史本性的遮蔽。
二、實踐生存論及其教學意蘊
哲學的實踐生存論轉向其實質(zhì)是本體論的轉換,即從傳統(tǒng)的抽象本體論向實踐本體論或實踐生存論的變革,這一變革使哲學研究的對象從天國降到人間——現(xiàn)實的生活世界,把人的實踐活動作為理解整個世界的基礎,從而突顯出了哲學的生存論意蘊。相對于物質(zhì)本體論而言,把哲學的本體論理解為實踐本體論才能夠更好地克服傳統(tǒng)哲學的人與自然、思維與存在的二元對立以及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只有以實踐作為整個世界的本體,才不會把自然看成是與人相對立的異在,而是當作人的無機身體,或使自然成為人,從而賦予自然以某種主體性或主體地位,并建立起人與自然的對話關系;同時,只有以實踐作為整個世界的本體,才能敞開哲學的社會歷史維度和人類性視野,構筑起人、自然和社會和諧統(tǒng)一的生存論結構。運用實踐生存論審視教學,有著新的意蘊。
(一)教學實踐活動是學生發(fā)展的重要生存方式
實踐生存論從人的實踐活動及其產(chǎn)物來理解人,而不像實存論那樣從超驗的實體(精神實體和物質(zhì)實體)出發(fā)來說明人的存在與生存。實踐是人的生存方式,它不僅使人成為人而區(qū)別于其他的動物,確定了人的主體性地位;而且為人的生存、生活提供了現(xiàn)實的物質(zhì)生活資料,創(chuàng)造出屬人的生活世界;更為重要的是實踐活動對人的生命意義和生存價值的敞開提供了現(xiàn)實的可能性。
實踐不僅使人成為人本身,從動物的存活轉變到人的生存;而且改變了人及其周圍的感性世界,為人創(chuàng)造出一個屬人的生活世界。從另一個方面來說,通過人的實踐活動使人的生命意義和生存價值得以顯現(xiàn)和確證。人的生命意義和生存價值在于通過人的實踐使自己從自然界脫穎而出,成為實踐活動和世界的主體,并通過人的實踐活動把自己的本質(zhì)力量客體化,使這種實踐活動及其產(chǎn)物成為人自己的本質(zhì)力量的確證。實踐是人存在的方式。在實踐活動中,人成了一種實踐性存在物,實踐構成了人的整體性。在人與物的關系上,人“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在人與人的關系上,人“是社會存在物”;在人與己的關系上,人“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1]
教學實踐活動是學生發(fā)展的重要生存方式。學生的發(fā)展有其自身的內(nèi)在自然規(guī)律,但是學生的發(fā)展并不是毫不依賴其他活動而孤立地展開,而是依賴于教育教學實踐活動,在教育教學實踐活動中得到加速成長和發(fā)展。學生發(fā)展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其中教學實踐活動是其重要的方式。
(二)人、自然與社會歷史的實踐統(tǒng)一
傳統(tǒng)實存論哲學將人與自然對立起來,以一種“主體——客體”二元對立的思維關系處理著人與外界自然的存在;同時實存論將人從特定的社會歷史中剝離出來,人成為一種孤立的抽象的存在。實踐生存論以人的實踐活動為中介和橋梁,實現(xiàn)了人、自然與社會歷史的真正統(tǒng)一。哲學的這種人、自然和社會統(tǒng)一的生存論結構克服了近代認識論哲學導致的主體和客體、思維和存在、理論和實踐、自由和必然的分化和對立及其“實踐是現(xiàn)存感性世界的基礎”與“外部自然的優(yōu)先地位”兩個命題的對立和互斥。
實踐生存論是通過人感性的、歷史性的實踐及社會化活動所實現(xiàn)的關于“自然、人、社會”三位一體的自為生存理論。在這一理論體系中,“自然、人、社會”不再以自在的實體形式存在。自然是活生生的自然,是社會化的人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稱之為“自然界的生活”,自為性、現(xiàn)實性、開放性、歷史性是人化自然的基本特征;人不再是抽象的自我意識,而是以全面發(fā)展與人類解放為旨歸并處于具體歷史活動中的人,自覺追求類生存是人的所有歷史實踐活動的最高標準;社會則是正在歷史性地生成的人類共同體,生活世界的自由自覺活動是類主體生命意義的現(xiàn)實性展現(xiàn)。
(三)教學是一個充滿意義的世界
黑格爾曾認為,“人生活在兩個世界中:在一個世界中人具有他的現(xiàn)實性,這方面是要消逝的,這也就是他的自然性、他的舍己性,在另一個世界中人具有他的絕對常住性,他認識到自己是絕對的本質(zhì)。”[2]按照黑格爾的理論,人實質(zhì)上生存于兩個世界之中,即一個是具有現(xiàn)實性和有限性的事實世界,另一個是具有理想性和無限性的意義世界。也就是說人所生存的世界具有現(xiàn)實性和意義性兩個維度,那么師生所存在于的課堂教學實質(zhì)上是一個事實世界與意義世界的統(tǒng)一。課堂教學不僅僅是一個充滿知識與秩序的事實性場景,它也是一個滲透著自由與超越的體悟之旅。課堂教學是有著兩重屬性的存在,即實體或有形存在與意義——價值或無形存在。對意義的追尋,對人的生命和世界的根本意義的理解和解釋,是課堂教學活動的根本出發(fā)點,也是課堂教學活動的本質(zhì)之所在。課堂教學作為學校教育活動的基本途徑,是教師與學生的精神生活的重要平臺,是教師與學生的精神家園,它能精神慰藉、精神依歸、精神支持,它應該成為教師與學生詩意地存在的一個“意義世界”。[3]
教學作為一個意義世界是“人”的世界。教師與學生作為教育教學活動中的人,無疑是一種尋求意義的存在,教師與學生在課堂教學活動中總是尋求著、體驗著、感悟著作為“人”的存在意義。教師與學生作為人,其對意義的追尋,歸根結底源于教師與學生作為一種未完成性的存在、一種主體性的存在和一種精神性的存在。課堂教學作為一個意義世界是“關系”的世界。人所存在的意義既不是單純地來源于主體人內(nèi)部,也不是單純地來源于外部世界,而是衍生于人與他人、與他物的相互作用關系之中。課堂教學作為一個意義世界是“精神”的世界。課堂教學在對學生進行知識教育的同時,還注重對學生倫理道德、理想信念、心理健康、情感態(tài)度等方面進行教育,其實赫爾巴特在其“教學的教育性”這一理念當中就滲透了課堂教學的精神性意義。
三、現(xiàn)代教學論研究的實踐生存論轉向
哲學的實踐觀轉向,使被傳統(tǒng)哲學顛倒了的世界重新顛倒過來,使哲學關注的視域或視界從超驗之城還原到了經(jīng)驗之域,使哲學深深扎根于它的現(xiàn)實生活和人的生存之中,真正回到了生活和人的生存的本源處——人的現(xiàn)實的感性實踐活動。實踐生存論為教學論研究提供了轉型的方法論依據(jù)。
(一)教學論研究主題和研究域的重新厘定
課堂教學是學生生存與發(fā)展的重要方式,以探討學生通過學習如何實現(xiàn)發(fā)展為核心,重新界定研究問題域,從研究課堂教學策略模式與方法,進而深入到教與學行為方式變革層面,這是一次重要的研究轉型。教學論研究主題是關注學生的生存狀況和生命價值。關注學生的生活世界,賦予課堂教學以生活意義和生命價值,是當代課堂教學改革的重要特征。
課堂教學并不在于向學生傳授多少知識,也并不在于向學生進行多大程度上的秩序與紀律規(guī)訓,而在于促進學生幸福快樂地存在和成長,使他們體驗和感悟到存在的意義與價值。當然課堂教學確立追尋意義的價值取向,并不意味著課堂教學對知識與秩序的否定,而恰恰相反,課堂教學改革將會重視知識背后的精神意義,重視師生交往中的人生意義,追尋意義的本真在于向真實的、完整的人靠近。未來的課堂教學改革將從關注“如何有效認識”的范式轉向關注“如何有意義存在”的范式。[4]
(二)研究者研究角色的轉換
在實體本體論視野下的科學研究活動中,研究者只能站在自然之外,以旁觀者的身份來認識和研究自然界;研究者始終保持價值中立的態(tài)度,以客觀的態(tài)度對待研究對象。受自然科學研究的影響,社會科學研究者試圖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式,以旁觀者的身份,擯棄個體的主觀傾向,采用客觀中立的態(tài)度,在一定“距離”之外開展研究。通過實踐生存論反思當前教學論研究中研究者所扮演的角色,發(fā)現(xiàn)他們并沒有與研究對象一道參與具體的活動,沒能與研究對象融為一體,因此沒辦法切身體會到作為研究對象的教師和學生等在教學中的真實感受,這樣也就難以獲得全面真實的資料并形成可靠的研究結論,教學論研究者成為了“孤獨的研究者”。可見,研究者必須轉換自身角色,不能僅僅作為一個課堂教學活動的局外旁觀者,而要成為課堂教學活動的局內(nèi)參與者,在真實的參與中做研究。教學論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不應是主客對立的關系存在,而是相互協(xié)作相互交融所構成的研究共同體。“只有把自身教學的反思作為自身教學論研究內(nèi)容的教學論研究者,才能做到‘化理論為方法,化理論為德性’,也因此才能有資格和可能干預、影響和導引教學實踐”。[5]
(三)教學論研究的思維方式轉變
從“知性思維”向“生活性思維”的轉變。教學生活世界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人作為價值和意義之源的、以人的自我生成、自我發(fā)展和完善為指向的屬人的世界。因此,教學論研究的生存論范式不只是一味地關注科學知識世界,而是更多地關注教學生活世界,從人自身或從人的生活世界出發(fā)來看教學世界。也就是所說的那樣,“以主觀方式”把握“作為人的具體活動,作為實踐”的教學生活實踐。教學論研究的“生活性思維”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把教學生活世界視為“客觀世界”的傾向。
從對象性思維向參與性思維的轉變。“對象性思維”是指研究者在教學生活世界之外冷眼旁觀,通過各種主觀的形式審視教學生活世界,以尋求教學規(guī)律、教學原則的一種思維形式。教學論的生存論范式要求研究者在考察教學生活時,不能置身于教學生活世界之外,遠距離地、高高在上地觀察、審視教學生活中的問題和現(xiàn)象,而是以一種參與者的眼光分析、考察教學生活。
從實體思維向關系思維轉變。實體思維即以“實體”觀念看待事物的方式,事物由若干個實體構成。這些實體彼此不相關聯(lián),每個個體是孤立的、固定的、靜止的。因此,實體思維堅持二元對立的觀點、否定事物之間的內(nèi)在相互聯(lián)系、主張事物的靜態(tài)化。實體思維方式導致教學論研究總是從一極擺向另一極,在教師與學生、知識與能力、直接經(jīng)驗與間接經(jīng)驗、科學與人文等兩極之間反復較量,并沒有恰當?shù)靥幚砗盟麄冎g的關系,最終導致學生的畸形發(fā)展。從實體思維轉向關系思維有助于克服教學論研究中的鐘擺現(xiàn)象。從“實體思維”到“關系思維”,教學論研究需要關注教學整合、教學和諧、教學中的具體關系問題。
(四)教學論研究方法的轉換
教學論研究應根據(jù)研究對象的特征、研究的任務和性質(zhì),采取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定性與定量研究相補充的多元研究方法、多元研究范式“優(yōu)勢互補”的混合研究策略,力求選擇最合適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呼喚一種混合方法研究。混合方法研究(Mixed Methods Research)是指研究者在同一研究中綜合調(diào)配或混合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技術、方法、手段、概念或語言的研究類別。[6]混合方法也經(jīng)常被稱為多元方法(multimethods)或交叉對比的方法(triangulation of methods)。混合方法研究并不是取代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第三種方法,而是力圖使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在單獨研究和交叉研究中的優(yōu)勢得到強化,而盡可能使其不足降到最低限度。混合方法研究使得在解決研究問題中多樣化方法的運用得以合法化,而不是限制多種方法的運用。混合方法研究超越了傳統(tǒng)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之間關于主觀與客觀、價值介入與價值中立、部分與整體、一般與個別等方面的二元對立。
[1]馬克思,恩格斯.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7.
[2]張世英.論黑格爾的精神哲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273.
[3][4]趙文平.追尋存在的意義:當代課堂教學改革的價值取向[J].當代教育科學,2008,(24).
[5]徐繼存.教學論導論[M].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1,7.
[6]R.Burke Johnson&Anthony J.Onwuegbuzie J.,2004,Mixed Methods Research:A Research Paradigm Whose Time Has Come Educational Researcher,Vol.33,No.7,pp.14-26.
*本文系石家莊經(jīng)濟學院科研計劃項目 “河北省獨立學院在建設京津冀都市圈的人才培養(yǎng)定位”研究成果,項目編號:XN201018。
張耀東 白向瑋/石家莊經(jīng)濟學院華信學院,研究方向為教育管理 楊寶清/石家莊經(jīng)濟學院華信學院,研究方向為思想政治教育
(責任編輯:孫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