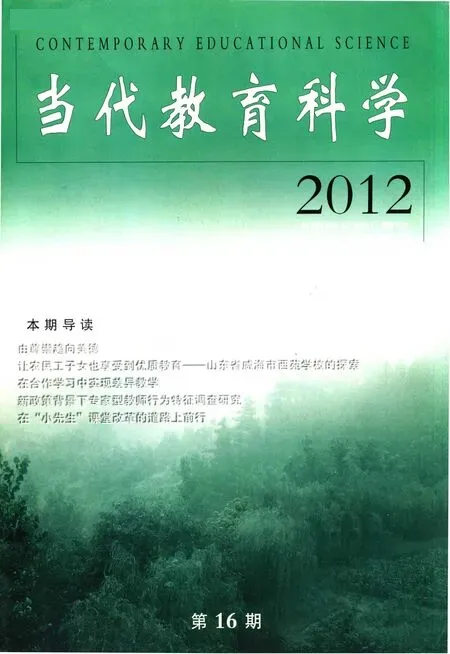生物科學史教育中的問題透視*
● 俞麗萍
生物科學史教育中的問題透視*
● 俞麗萍
科學史在融入生物課程教學實踐的過程中出現(xiàn)了一些偏差,主要表現(xiàn)在:對科學史上的錯誤理論沒有給予理性的評價;將科學家描述成道德品質(zhì)的典范、完美無缺的神人;科學的發(fā)現(xiàn)過于簡化,缺少科學發(fā)展的艱難曲折過程;僅利用科學史提高學習興趣、強化科學知識的傳授。剖析與糾正這些問題,對充分發(fā)揮科學史的教育功能具有重要的意義。
生物;科學史教育;科學精神
一、對科學史上的錯誤理論沒有給予理性的評價
在教學中,對于科學史上正確的理論和假說,教師不惜贊美之詞,但對于現(xiàn)在看來是錯誤的理論或已被證偽的假說,則以“已被證明是錯誤的”簡單地一筆帶過,甚至把它看作是真理發(fā)現(xiàn)路上的絆腳石而被批判。例如,古羅馬時期蓋侖提出了血液運動“生命靈氣”的學說,在今天看來它的錯誤之處在于沒有認識到血液循環(huán)而認為靜脈系統(tǒng)與動脈系統(tǒng)是無關(guān)的,于是在教學中蓋侖成了阻礙科學發(fā)展的罪人。很少有人意識到蓋侖對血液運動的論述在生物學史上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蓋侖的學說在當時是舉世公認的科學。從今天的角度來看,蓋侖的理論有部分是正確的,例如他證明動脈是送血的,而不是送空氣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的中樞是腦而不是心臟、心臟中有瓣膜等。再如,光合作用發(fā)現(xiàn)史中,海爾蒙特從實驗中得出的結(jié)論是:植株的營養(yǎng)只能來自于水。這一結(jié)論的錯誤之處是忽略了減少的少量土壤干重以及大氣成分參與植物生長的作用。但是海爾蒙特的實驗具有它的積極意義:他開創(chuàng)了實驗生物學定量分析的先河(對土壤和柳樹稱重),否定了亞里斯多德關(guān)于植物營養(yǎng)只來自于土壤的觀點,在科學知識上也是一次進步。我們要用辯證的思想,寬容的胸懷,理性地看待科學史上的錯誤理論。錯誤理論也可能包含有科學創(chuàng)新之處,如提出新的問題,采用新的方法,包含新的正確的內(nèi)容。科學探索,無論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都能對人類的進步產(chǎn)生重要的影響。科學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理解。科學發(fā)現(xiàn)與當時的科學技術(shù)水平、社會經(jīng)濟條件、主流文化、政治意識或宗教信仰等有關(guān)。蓋侖的某些錯誤之所以產(chǎn)生,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羅馬人統(tǒng)治的時期人體解剖是嚴格禁止的,因此蓋侖所進行的解剖對象主要是豬、狗和猴等動物而不是人。而他所說的心間隔上有小孔,血液能通過小孔往返于心臟左右兩邊,這是他的猜測,他的生理描述脫離了實際而屈從于宗教神學的需要。海爾蒙特得出不正確的結(jié)論,與他所處的時代背景也有關(guān)。海爾蒙特并不是不了解土壤和大氣的作用,而是受當時哲學理論(所有物質(zhì)皆起源于水,世界本原是水)的束縛,他試圖通過柳樹實驗來驗證哲學學說,將科學研究與非理性的宗教熱情渾然一體。
歷史上每個具體科學成果的取得,幾乎都經(jīng)歷了否定之否定的過程。理性地評價現(xiàn)在看來是錯誤的理論,有助于學生理解科學與社會、文化、技術(shù)的相互關(guān)系,有利于培養(yǎng)學生嚴謹?shù)目茖W態(tài)度,形成科學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利用科學史上過去被廣泛承認而現(xiàn)在已經(jīng)被證偽的理論,尋找該理論合理之處與錯誤之處的證據(jù),具有重要的教學意義。一方面它能夠促進學生理解科學的本質(zhì):科學需要且依賴于經(jīng)驗證據(jù),當發(fā)現(xiàn)新的證據(jù)和對已有事實有新的解釋時,科學知識將會改變,科學知識具有暫時性和發(fā)展性,科學無法脫離社會、文化、宗教與政治而獨立發(fā)展等;另一方面它能夠促進學生概念的轉(zhuǎn)變。有學者認為,學生所持有的許多“迷思概念”與科學史是相平行的,可以利用科學史上的錯誤理論與學生頭腦中可能的錯誤概念加以比較,從而促進學生概念的改變。[1]
二、將科學家描述成道德品質(zhì)的典范、完美無缺的神人
教學中將科學家描述成完全客觀公正、超脫社會影響的“圣人”,對待與自己不同觀點的人心胸開闊,沒有任何私人利益摻雜其中,品德高尚,完美無缺,塑造了一座座連科學家自己都難以做到的高高在上的“圣像”。介紹了較多天才科學家而不是普通的科學家,特別關(guān)注科學家小時候就表現(xiàn)出來的、而且與以后研究領(lǐng)域有關(guān)的特殊才能。有關(guān)科學家生平的描述以科學家的研究或發(fā)明為主,而有關(guān)科學家屬于常人的一面如日常生活、嗜好、缺點、要面對的挫折或恐懼等卻很少提及。如中學生物課本對林奈的描述:“林奈從小喜愛大自然,對植物特別有興趣,只要有機會,他就鉆到樹林里去觀察和采集植物。老師和同學都稱他是‘小植物家’……”。對施旺和施萊登的描述是“思想活躍,善于辭令,對顯微觀察一絲不茍……”。還有達爾文和華萊士對創(chuàng)建“自然選擇學說”的優(yōu)先權(quán)互相謙讓,成為科學史上的佳話。對于科學家的描述雖然不算是夸大或杜撰,但有可能使學生對科學家產(chǎn)生一些扭曲的觀點,如科學家一出生或從小就有超群出眾的才質(zhì),將來注定要當科學家,科學家與我們是完全不同的一群人,或者是十分偉大的人,自己根本沒有能力達到科學家的那種境界,不愿意也沒有信心成為那種人。
科學家生活在一定的社會中,不可避免地會受到社會上各種價值觀念、哲學信念的影響,科學家并非如我們所想象的那樣客觀公正,心胸廣闊。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多數(shù)科學家固然有不少高尚的品行,但是他們也是人而不是神,既有人性的光輝與偉大,也有人性的弱點與失誤[1]”。科學家也會為爭奪科學發(fā)現(xiàn)的優(yōu)先權(quán)而奔波、為自己的理論受到攻擊而惱怒。例如施旺性格懦弱而缺乏足夠的自信,他不愿意在公開場合拋頭露面與其他學者面對面地辯論,更不能忍受來自德國科學機構(gòu)最高層的尖刻的批評,以至于不能接受德國8所著名大學的教授職務。施旺雖然是現(xiàn)代組織學的創(chuàng)始人,但他的有些觀點也是錯誤的,例如他認為細胞并不是由其他細胞形成的,而是由細胞間液“營養(yǎng)液”凝集而成。他更錯誤的一個觀點是認為細胞物質(zhì)即施旺氏細胞胚基(后來改稱為原生質(zhì))是無結(jié)構(gòu)的。達爾文迫于當時神學思想、道德及政治壓力,遲遲不肯發(fā)表有關(guān)進化論的文章,他甚至留下一份遺囑做好了在死后才發(fā)表其成果的準備。當收到華萊士寫給他的關(guān)于自然選擇而進化的論文時,達爾文和普通人一樣震驚,因為它與達爾文悄悄準備了20年的理論觀點不謀而合。達爾文自己的說法是:“我并不在意贏得優(yōu)先發(fā)表的地位,但如果有其他人在我之前先發(fā)表了我所提出的理論,我當然會苦惱”。
為學生樹立科學家的光輝形象、良好榜樣,這無可厚非,但是不能歪曲歷史的真實面貌。對科學家的客觀描述有助于學生認識科學家的真實面貌,可以拉近學生與科學家的距離,理解科學家“人性”的一面,去除學生對科學的敵意或疏遠。正如美國學者詹姆斯·洛溫所尖銳指出的,“教科書通過英雄化這一過程把有血有肉的人變成了虔誠的、完美的造物,他們沒有矛盾,沒有痛苦,沒有人情昧,也沒有可信性”。科學家不是神,學生才有可能走近他;科學家是人,學生才可能以后成為科學家。另外,充分利用著名科學家有關(guān)發(fā)現(xiàn)的錯誤,可以培養(yǎng)學生不迷信權(quán)威,敢于質(zhì)疑權(quán)威的氣魄和敢于創(chuàng)新求異的思維品質(zhì);還可以引導學生正確理解科學的本質(zhì):科學家的研究成果會不斷地受到質(zhì)疑與檢驗,即使是舉世聞名的偉大科學家也不例外。這也說明科學事業(yè)的發(fā)展不斷地自我否定,“科學其實就像人類的其他事業(yè)一樣,并非毫無瑕疵,但科學家們會努力將這種瑕疵減少至最小化,以追求這個領(lǐng)域的最高成就”[2]。
三、科學的發(fā)現(xiàn)過于簡化,缺少科學發(fā)展的艱難曲折過程
初中生物課本中關(guān)于青霉素的敘述:“1928年,英國的細菌學家弗萊明在研究細菌時發(fā)現(xiàn),在只接種了葡萄球菌的培養(yǎng)基上,竟然長出了青霉。當他正在為培養(yǎng)基受到霉菌的污染而懊惱時,一個偶然的現(xiàn)象引起他的注意:培養(yǎng)基的其余部分都布滿了葡萄球菌的菌落,只有青霉菌菌落的周圍沒有葡萄球菌的菌落。這是為什么呢?弗萊明經(jīng)過深入的研究發(fā)現(xiàn),青霉能夠產(chǎn)生一種殺死或抑制葡萄球菌生長的物質(zhì),他把這種物質(zhì)叫做青霉素。后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了,這時青霉素已經(jīng)能夠大量生產(chǎn),它挽救了成千上萬傷病員的生命。弗萊明因此獲得了諾貝爾醫(yī)學或生理學獎。”高中生物教材關(guān)于摩爾根發(fā)現(xiàn)白眼果蠅的敘述:“于是,從1909年開始,摩爾根開始潛心研究果蠅的遺傳行為。一天,他偶然在一群紅眼果蠅中發(fā)現(xiàn)了一只白眼雄果蠅。”科學發(fā)現(xiàn)好像是個很偶然的,很輕松的工作。這樣不僅不符合科學發(fā)展的實際,也給學生留下了科學發(fā)現(xiàn)來得很容易的錯誤印象。
事實上,從1928年弗萊明發(fā)現(xiàn)青霉素到二戰(zhàn)時青霉素能大量生產(chǎn)挽救傷員的生命,這期間青霉素的研究遭遇過很多的困難,比如在用天竺鼠做口服實驗時,出現(xiàn)了極高的致死率;葡萄球菌接觸了青霉素后,可快速產(chǎn)生抗性;青霉素的分離純化極其困難,且活性不穩(wěn)定;菌株產(chǎn)量極低;設(shè)備經(jīng)費很少。所有這些都是弗萊明自己所無法解決的,這些可能打擊了弗萊明的信心。因此弗萊明很快就不看好青霉素做為藥物的用途,1934年起他停止了青霉素的研究。青霉素從實驗室走向臨床,變成救人無數(shù)的良藥,最終是由牛津大學的霍華德·弗洛里實驗室開發(fā)出來的。從1938年開始,錢恩和弗洛里組織了一支由20多名病理學家、生物學家、細菌學家、醫(yī)學家等組成的強大的研發(fā)隊伍,攻克了鑒定、提純等技術(shù)難題。但是青霉素的命運仍十分坎坷,牛津大學拒絕為錢恩申請青霉素的專利保護,拒絕錢恩組建試驗工廠探索工業(yè)化生產(chǎn)青霉素條件的要求。后來由于二戰(zhàn)爆發(fā),巨大的戰(zhàn)爭傷亡對抗菌藥物產(chǎn)生了迫切的需求,在美國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青霉素才大規(guī)模的生產(chǎn)。青霉素這種特效藥花了近十年的時間才走完從發(fā)現(xiàn)到臨床應用的過程。1945年弗萊明、弗洛里和錢恩三人共同獲得了諾貝爾醫(yī)學和生物學獎。同樣,發(fā)現(xiàn)突變的白眼果蠅,花費了摩爾根和他的學生整整兩年的時光。西班牙醫(yī)生塞爾維特第一次提出了關(guān)于血液由右心室經(jīng)過肺動脈和在肺組織內(nèi)與它相連結(jié)的肺靜脈流入左心房的正確看法。因為觸犯了統(tǒng)治階級的宗教,這位正要發(fā)現(xiàn)血液循環(huán)的科學家,被宗教裁判所連同他的著作一道被送上火刑場,使血液循環(huán)的發(fā)現(xiàn)推遲了七十多年。
將科學研究過程中遭遇的困難和辛勤的勞動,特別是科學發(fā)展過程中的曲折、爭議及外力影響等簡化甚至刪除,學生就無法看到科學家在研究過程中所面對的真實問題、困難疑惑,也無法了解科學研究與新觀念的建構(gòu)、新儀器的發(fā)明、科學家的思考習慣與信念以及外在的文化、政治、宗教及經(jīng)濟等因素都有關(guān)聯(lián)。很容易讓學生誤以為科學只是隱藏在某處等待一個天才科學家在某一瞬間看透或發(fā)現(xiàn)它,或者科學完全獨立于外在世界。因此,簡化的發(fā)現(xiàn)史首先無法增進學生對于科學本質(zhì)的了解;其次,簡化科學發(fā)現(xiàn)的過程,還傳遞給學生一種假象,似乎偉大科學家基本不走彎路,這樣的科學史不能讓學生體驗科學探索是充滿挫折、失敗、謬誤、猜想、頓悟的不斷探索的過程,誤以為科學是一帆風順的事業(yè),不利于培養(yǎng)學生百折不撓的求知精神和堅忍不拔的意志品質(zhì);再次,簡化科學發(fā)現(xiàn)的曲折歷程,似乎邏輯清楚、有實驗驗證便可得到公認。實際上,實踐對真理的檢驗往往要經(jīng)歷一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又次,簡化的發(fā)現(xiàn)史往往把科學的主要貢獻歸功于一個科學英雄,使學生難以正確領(lǐng)會科學發(fā)現(xiàn)中所需要的團隊精神。其實人類偉大的發(fā)明,很少只是一個人的天才創(chuàng)造。
四、僅利用科學史提高學習興趣、強化科學知識的傳授
例如,在光合作用發(fā)現(xiàn)歷程的教學中,呈現(xiàn)并分析科學史上的實驗,目的僅僅是為了得出光合作用的原料、產(chǎn)物、條件、場所等知識性的結(jié)論。再如將某項發(fā)明完全歸功于某位科學家,并突出科學發(fā)現(xiàn)所帶給科學家的聲譽與地位,以此來調(diào)動學生學習科學的積極性以及投身科學的熱情,其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加強科學知識的教學。實際調(diào)查也表明,多數(shù)教師利用科學史來展示知識的發(fā)生過程和激發(fā)學生學習的興趣,這兩者共同的目的是為了學生更好地學習知識。正如有學者所尖銳指出的,“雖然在我國的基礎(chǔ)科學教育中教科書也融入了少量科學史,教師在教授科學時也插講一些科學史中的故事,但如此做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給科學知識裹上一層‘糖衣’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不是為了讓學生更好地理解科學的形成過程”[3]。將科學史作為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為了科學史自身的目的去進行教學。這樣,科學史就變成為說服的工具,以說服學生去掌握目前教師所認為的“絕對真理”。
在科學史教學中,教師們更多地看到了科學史所擔負的使科學知識合法化以說服學生掌握這些知識的功能,而沒有重視通過真實的科學史學生可以從中獲得關(guān)于科學事業(yè)及其發(fā)展的有益啟示。其實,以科學史的介紹作為認知背景,引發(fā)學生的認知沖突或者激發(fā)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這未嘗不可,然而我們同時應該以科學史中蘊含的懷疑與批判精神去引導學生以懷疑的眼光看待目前的科學理論,以科學家詮釋現(xiàn)象的思路與方法引導學生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加以驗證,使學生更真實地理解科學的本質(zhì)以及科學技術(shù)與社會的關(guān)系,而不應該僅以便于知識傳授為目的。仍以光合作用的發(fā)現(xiàn)史為例,除了建構(gòu)光合作用的知識,更重要的是領(lǐng)悟科學家的思維方式,體驗科學家設(shè)計實驗的思想,并能對經(jīng)典實驗設(shè)計的不足進行質(zhì)疑,嘗試提出改進這些實驗的方法。接受科學方法的訓練,如設(shè)置對照實驗,控制單一變量,定量分析的方法,同位素示蹤法等。領(lǐng)悟科學知識是怎樣產(chǎn)生的,把握科學的本質(zhì),從而培養(yǎng)敢于質(zhì)疑的科學精神和態(tài)度,激發(fā)學生投身科學獻身科學的斗志。
[1]劉德華.“點擊”學校課程—走在十字路口的科學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2]Koshland,D.E.Jr.The price of progress[J].Science,1988,(241).
[3]徐學福.科學的相對性及其在課程和教學中的滲透[J].比較教育研究,2001,(8).
俞麗萍/江蘇省泰州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副教授
本文系泰州師范高等專科學校重點課題“HPS視野下生物課程教學研究” (項目編號2010-ASL-12)成果之一。
(責任編輯:劉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