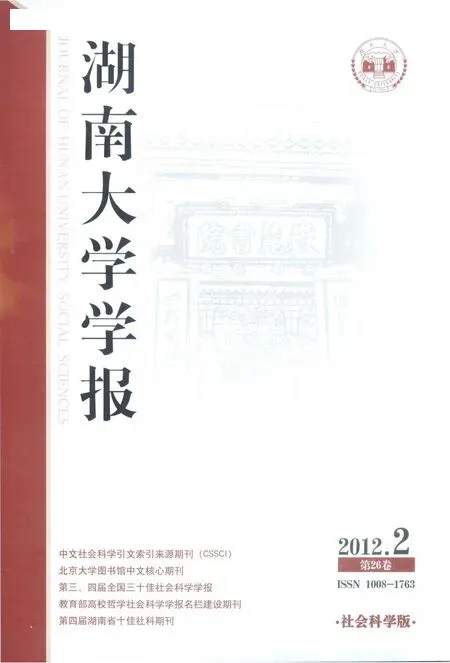王一庵平民儒學思想析論*
賈乾初,陳寒鳴
(1.山東大學 威海分校 法學院,山東 威海 264209; 2.天津市工會管理干部學院,天津 300170)
王一庵平民儒學思想析論*
賈乾初1,陳寒鳴2
(1.山東大學 威海分校 法學院,山東 威海 264209; 2.天津市工會管理干部學院,天津 300170)
王一庵盡管晚年做過低微的下級教育官員,但就其一生行誼來看,仍屬泰州學派平民學者。他繼承了心齋之學,并在誠意慎獨方面有自己的新發展。一庵的誠意慎獨之學是他平民儒學思想的理論依托,“自強”“法天”觀念彰顯了一庵平民儒學思想的主體意識,“隨分而成功業”體現了一庵平民儒學思想的事功觀。一庵以講學集會為實現其平民政治理想的主要手段。這種手段的蒼白表明,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覺民行道”的“外王”取向,始終徘徊于“內圣”內涵的邊緣上,難以真正向外拓展。
王一庵;誠意慎獨;主體意識;平民儒學;覺民行道
王一庵(1503—1581),名棟,字隆吉,號一庵,泰州姜堰人。他以族弟的身份師事王心齋(艮),是泰州學派的第一代嫡傳弟子,后來學者將之與王心齋、王東厓(襞)父子并稱為“淮南王氏三賢”或逕稱為“淮南三王”。亦有將之與王陽明、王心齋并稱為“越中淮南三王夫子”①《王一庵先生遺集》卷首《年譜紀略》(附出處事跡),東臺袁氏編校本。者,有《一庵王先生遺集》傳世。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將一庵之學概括為主要兩端:“一則稟師門格物之旨而洗發之”,“一則不以意為心之所發”。②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三十二《泰州學案一》,第73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意謂一庵認同了心齋之學的“格物”說并有發展,且一庵在“誠意”方面有新創造。黃氏所勾勒出的一庵之學總體面貌,為學界基本認同。總體而言,一庵充分繼承了心齋之學,但同時又有自己的新發展,如吳震研究一庵思想后指明,一庵之于心齋的思想關系,大略可用“受格物之旨”、“得家學之傳”二語來定格,然而一庵在“從格物認取良知”方面、尤其是誠意慎獨方面,都有著自己的創新和貢獻。③吳震:《泰州學派研究》,第247頁,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因之,他將一庵之學直接定位為誠意慎獨之學,無疑是精準的。我們這里主要立足于泰州學派的平民儒學主流,據此來討論一庵的平民儒學思想,希圖藉之深化對一庵思想價值的認識。
一 游走于士紳與平民之間的王一庵
余英時先生曾說,王陽明“龍場悟道”所暗示的理學內在轉捩,從政治文化角度探析,暗示出陽明由“得君行道”向“覺民行道”的路向轉移。“明代理學一方面阻于政治生態,‘外王’之路已斷,只能在‘內圣’領域中愈轉愈深。另一方面,新出現的民間社會則引誘它掉轉方向,在‘愚夫愚婦’的‘日用常行’中發揮力量。王陽明便抓住了這一契機而使得理學獲得了新生命。”①余英時:《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第196頁,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年。不可否認,此時的王陽明作為遭貶的官員,這一轉移有其不能“得君行道”的外在政治環境觸發的原因——“良知”學說的出現當然與王陽明的個人政治際遇有密不可分的聯系。然而,“覺民行道”或“以道覺民”路向一開,且這路向又恰開啟于中古社會晚期母體內部商品經濟孕生,及新興市民階層躍登社會歷史舞臺之時,遂使得陽明學于明代思想史上獨放異彩,培育出諸多“躬行實踐”、“英雄莫比”的思想人物。
一庵的老師王心齋,無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由心齋本其一介布衣身份而開創的泰州學派,在“愚夫愚婦”的“日用常行”中所做“以道覺民”的工作,在實踐中極大地推展了陽明學的這種轉向。由士紳儒學到平民儒學,王心齋和他創立的泰州學派,凸顯了強烈的個性特征。“事實上,在很長一段時間,泰州以外的王學,都是一個近乎封閉的士大夫群體,他們并不熱衷于向平民宣教。”②鄧志峰:《王學與晚明的師道復興運動》,第226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因之,泰州學派立足“百姓日用”的平民儒學指向,在陽明后學中,特色鮮明,且形了自身的傳統。這一傳統的主要特點是:其一,傳道對象大眾化;其二,儒學理論簡易化與儒學經典通俗化;其三,心性自然化;其四,傳道活動神秘化;其五,社會理想道德化。③陳寒鳴:《論明代中后葉的平民儒學》,《河北學刊》1993年第5期。一庵作為心齋的第一代嫡傳弟子,很好地繼承了上述泰州學派的平民儒學傳統。
與陽明、心齋坎坷的人生遭際不同,一庵的生平沒有極端的波動。他既不像陽明那樣由仕宦生涯而事功顯著,也不像心齋那樣將布衣身份保持終生。而是游走于士紳與平民之間。
一庵父名王贊,號伯林,業醫。一庵七歲時受父命“習舉子業”,但“時年十有一歲,遇瘟疫流行,奉先公命,備藥材,施救村鎮。一日行至沙村莊,遇馬噬嚙,幾為所傷,仍命業儒。”④《王一庵先生遺集》卷首《年譜紀略》(附出處事跡),東臺袁氏編校本。經過這番曲折,一庵回歸業儒的正途。據《年譜紀略》載,嘉靖五年(1526),一庵24歲時,補郡庠生,師事陽明弟子泰州知州王瑤湖(名臣,字公弼,號瑤湖,生卒年不詳);嘉靖六年(1527),一庵食廩餼,與林東城(名春,字子仁,號東城,1498—1541)一同師事其族兄王心齋,“受格物之學,躬行實踐,久遂有所得”⑤《王一庵先生遺集》卷首《年譜紀略》(附出處事跡),東臺袁氏編校本。。自嘉靖三十七年(1558)56歲至隆慶六年(1572)70歲致仕回到泰州,一庵作基層教育官員有14年之久。先后任江西建昌南城訓導、山東泰安州訓導、江西南豐教諭、北直隸深州學正等職。任職期間,一庵以主持書院事務、大開講會為主要活動。他先后主講白鹿洞書院、正學書院,創太平鄉講會、水東大會等講會,“集布衣為會”、“名動當道”,產生了極大影響。“致仕歸里,清貧如洗。樂學不倦,開門受徒,遠近信從日眾。創歸裁草堂,著《會語續集》行於世。創《族譜遺稿》以睦族人。”“主會泰山安定書院,朝夕與士民論學,四方向風”。⑥《王一庵先生遺集》卷首《年譜紀略》(附出處事跡),東臺袁氏編校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庵講會論學以“布衣”即平民為主要對象。他逝世前對后人囑咐,也仍然是“會學一事”而已。可見,平民教育信念在一庵心目中所占地位。
《年譜紀略》所謂“志切高尚”、“清介”、“貧窮如洗”、“樂學不倦”諸語,大略勾勒出了一庵的人格風范。其中所記述的事跡數則,尤可見一庵對所受心齋格物之學,在百姓日用中的“躬行實踐”之處:
先生事親最孝,先公性剛直,一日與內不合即外居,先生廢寢食,泣拜三日勸歸,使父母歡悅。每事幾諫,不聽則拜,務諭親于道乃止。⑦《王一庵先生遺集》卷首《年譜紀略》(附出處事跡),“嘉靖十九年”條,東臺袁氏編校本。
時署縣事,有胡姓兄弟告爭家財,先生諭以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土,動以一本至情,胡感悟,兄弟泣拜,歸復共曩,終身永翕,儼然蘇公下淚,殊有感諭之風焉。⑧《王一庵先生遺集》卷首《年譜紀略》(附出處事跡),“嘉靖三十七年”條,東臺袁氏編校本。
時置豐事,有一寡婦子某,太學生,罪誣大辟。先生感渠寡母曲全之,私報數百金,概置不顧。⑨《王一庵先生遺集》卷首《年譜紀略》(附出處事跡),“嘉靖四十五年”條,東臺袁氏編校本。
初擢深州,接邸報,豐有鄉達某囑先生曰:某向知深州積金一罌,忘持歸,如署州事可取之。后先生果署州事,竟不理,及老歸田里,終身不齒其事。(10)《王一庵先生遺集》卷首《年譜紀略》(附出處事跡),“隆慶五年”條,東臺袁氏編校本。
一庵于孝道,可謂煞費苦心,模范踐行。除如《禮記》所教“幾諫”的辦法之外,他還要“諭親于道”才算到位。心齋之學尤重踐履,對“孝弟”的高度重視是泰州學派、尤其是心齋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在心齋看來,“孝弟”絕非只基于倫理學的考量,故其“以孝弟為教”實彰顯了他所認可的“外王”取向,此確如吳震所說,“心齋有關孝弟的思考不僅有倫理學的解釋方法,更有社會學、政治學的分析視野”(11)吳震:《泰州學派研究》,第183頁,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而一庵恪遵古禮,事親至孝,“諭親于道”的切己踐行,非惟是對心齋“格物之旨”、“孝弟之實”有深切領會,更重要的應該是他能領會心齋重視“孝弟之教”的社會、政治意涵或曰“外王”取向。如此,則一庵處理胡姓兄弟爭家財之事,以兄弟至情“感諭”教化之的做法,其高度認同“孝弟之教”的切實思想根源便可明了于心了。至若視金銀如無物,就更能說明一庵在“修身立本”方面踐行得非常之好。如他申述自己的理解說:“先師原初主張格物宗旨,只是要人知得吾身是本,專務修身立本,而不責人之意,非欲其零零碎碎於事物上作商量也。”①《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會語續集》,東臺袁氏編校本。如此“修身立本”,正是踐行心齋的“格物之旨”。
王一庵與林東城同時投師心齋,屬心齋第一代弟子中及門時間較長者,但二者的人生取向卻不很相同。東城嘉靖十一年(1532)舉會試第一后,大部分時間在京為官,直至卒于吏部文選司任上,所交游者率皆士紳名流。就心齋開創的泰州學派平民儒學主流而言,林東城顯然背離了這個傳統,完全成長為士紳之儒。一庵則與之不同。盡管他晚年亦走上仕宦之途,但據年譜所記,一庵與士紳名流的交游寥若晨星,語焉不詳,惟“集布衣為會,興起益眾”、“開門受徒,遠近信者日眾”②《王一庵先生遺集》卷首《年譜紀略》(附出處事跡),東臺袁氏編校本。的記錄清晰可見。如上文所言,一庵的教育對象主體是“布衣”即平民,顯然他是十分認同心齋教化“鄙夫俗子”的平民教育路徑的。如他說:
自古士農工商,業雖不同,然人人皆共此學。……天生我先師,崛起海濱,慨然獨悟,直超孔子,直指入心,然后愚夫俗子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靈、自完自足,不假聞見、不煩口耳,而二千年不傳之之消息一朝復明,先師之功可謂天高而地厚矣!③《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會語正集》,東臺袁氏編校本。
故而,一庵雖然游走于士紳與平民之間,卻未可遽以“士紳之儒”目之。鄧志峰認為,“王棟的一生,是一個有恒心而無恒產的士,為了自己的道德理想,步履維艱的一部辛酸實錄。”④鄧志峰:《王學與晚明的師道復興運動》,第215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從某種意義上說,王棟是那個朝代從事講學活動的中下層知識分子的一個典型。”⑤鄧志峰:《王學與晚明的師道復興運動》,第214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可以想見,王一庵長期但任基層教育官員,并且“清貧如洗”,在士紳圈子當中,不會有很大市場的。大約這也是《年譜紀略》對于他與士紳名流交往記述闕如的原因之一。一方面,享年79歲的一庵,一生只有14年擔任基層官職低微的教育官員;另一方面,他的講學活動的主要對象又以“布衣”為主;再加上他繼承了心齋的平民儒學思想,就此而言,我們認為一庵堪稱繼心齋杰出的“平民儒者”。
二 “誠意”、“慎獨”之學與一庵的平民儒學思想
(一)“誠意”、“慎獨”說:一庵平民儒學思想的理論依托
王一庵在心學理論上的新創造集中體現在他所提出的“誠意”、“慎獨”說方面。他對《大學》、《中庸》中的“誠意”、“慎獨”進行了富有個性特征的新解釋:
誠意工夫在慎獨。獨即意之別名,慎則誠之用力者耳。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才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所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世云獨知,此中固是離知不得,然謂此個獨處,自然有知,則可謂獨我自知、而人不及知,則獨字虛而知字實,恐非圣賢立言之精義也,知誠意之為慎獨,則知用力於動念之后者,悉無及矣。故獨在《中庸》謂之不睹不聞;慎在《中庸》謂之戒慎恐懼,故慎本嚴敬、而不懈怠之謂,非察私而防欲者也。⑥《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會語正集》,東臺袁氏編校本。
依據這種新解釋,“慎獨”體現的是“誠意”工夫。因為“意是心的主宰”,而“獨”卻是“意之別名”,換言之,“慎獨”正是體現的“誠意工夫”。一庵將“誠意”與“慎獨”做此種打通解釋,顯然是沿著心學主體意識的高揚與標舉道路,予以進一步的推展。他強調“有所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本體有“意”作“心之主宰”,“自作主張”、“自裁生化”,焉用“商量依靠”!這是一庵平民儒學思想非常重要的一個理論依托。
對這個理論依托,一庵論列頗多。除重點指出“誠意工夫在慎獨”之外,尚有如下數端。
1.誠意是立本工夫
一庵強調“誠意二字,正吾人切實下手立本工夫”,他分析說:“格物知至,方才知本在我,本猶未立也,故學者既知吾身是本,卻須執定這立本主意,而真真實實,反求諸身,強恕行仁,自修自盡,如此誠意做去,方是立得這本。若只口說知本在我,而於獨知之處尚有些須姑息、自諉、尤人、責人意念,便是虛假,便是自欺。自欺於中,必形於外,安得慊足於己而取信於人乎?故誠意二字,正吾人切實下手立本工夫,方得心正身修,本可立而末可從也。”⑦《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會語續集》,東臺袁氏編校本。
2.誠意立本則心有所主
“誠意”既然是“修身立本”的大節目,然而“誠意”作為“切實下手立本工夫”,其“切實”處何在呢?一庵聯系“正心”指出,誠意立本則心有所主。他在答人問“誠意既足以立本矣,何復有正心工夫”時,指出:“這卻只是一串道理,意是心之主,立本之意既誠,則心有主,故不妄動,而本可立、身可修。若自家不曾誠意立本,而望施之於人,僥聲感應,皆是妄想,皆是邪心,皆是中無所主,憧憧往來病痛。故意誠而后心正,非於誠后復加一段正心工夫也。”⑧《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會語續集》,東臺袁氏編校本。
3.敬在誠意中
一庵在答人“主敬不如主誠乎”的疑問時說,“今只泛言敬則中心有主,不知主個甚么?將以為主個敬字,畢竟懸空無所附著,何以應變而不動心乎?吾輩今日格物之學,分明是主修身體,誠意是所以立之之功,不說敬而敬在其中。蓋自其真實不妄之謂誠,自其戒慎不怠之謂敬。誠則敬,敬則誠,其功一也。”①《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會語續集》,東臺袁氏編校本。
由上可知,一庵將誠意工夫解釋得相當浹洽,這些解釋顯然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吳震指明,在一庵這里,“誠意工夫可以一攬子解決身心問題、本末問題(包含家國天下)。格物問題也自然可以由誠意工夫來解決,也就是說,反身立本的格物工夫有賴于誠意工夫,而誠意工夫又必須首先立定一個吾身是本的‘主意’,因此‘意’就成了所有問題的關鍵。”②吳震:《泰州學派研究》,第250頁,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在我們看來,一庵高度重視“意”的理論闡釋,除彰顯了他在心學理論上的新發展外,以此為機竅,強化主體意識,強調主體的把捉,透顯出了一庵平民儒學思想的立腳之處。換言之,一庵的誠意慎獨之學是奠定了他平民意識的理論基礎。
(二)“自強”“法天”:一庵平民儒學思想的主體意識
一庵的時代是儒學日趨世俗化的時代,人們的正常欲望被逐漸肯定,心學的發展亦體現此時代脈搏,而又不斷發展變化。③所以如此,顯然與其時商品經濟的孕生及與之相適應的新興市民階層躍登社會歷史舞臺密切相關。明乎此,才能埋解陽明“四民并業而同道”之言及由此而開啟出的儒學世俗化、大眾化的發展新路向。而泰州學派的平民儒學,則是這路向上必然會有的思想成果。立基于普通百姓立場而倡發平民儒學的泰州學派,更充分肯認人們的合理欲望,反對一味的“滅人欲”說教。這使其與處于官學地位的程朱理學迥然有別。一庵于此亦多有闡發。如謂: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荀子卻言:“養心莫善於誠。”非但不識誠,亦不識養字之意。人心一覺便是真體,不善養之則有牿亡之害。故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所必不能無者,一切寡少,則心無所累,得有所養,而清明湛一矣。此非教人於遏人欲上用功,但要聲色臭味處知所節約耳。④《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會語正集》,東臺袁氏編校本。
他認為,“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作為“人所不能無者”,是人的基本生理欲望,只要“一切寡少”“心無所累”“得有所養”,最后達于“清明湛一”便好。所以,于“人欲”上,關鍵不是在“遏”,而是在“節約”,或者是言“寡”。一庵又借辨明孟子、周子所言“欲”含義的分別而闡述道:
孟子止言寡欲,周子遂說寡焉以至於無,此非其養心者有疏密之異,特二公所指欲字之意不同。周子以心之情私感物而動者為欲,故不得不謂之無;孟子以身之形氣應跡而迷者為欲,故不得不謂之寡。讀者不以辭害義可也。⑤《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會語正集》,東臺袁氏編校本。
因之,一庵旗幟鮮明地指出:“察私防欲,圣門從來無此教法。”⑥《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會語正集》,東臺袁氏編校本。既然“圣門從來無此教法”,何以先儒們都從“察私防欲”這個從來沒有的教法上用功呢?問題出在大家對于“克己”的理解存在問題。一庵說:“先儒莫不從此進修,只緣解克已為克去已私,遂漫衍分疏,而有去人欲、遏邪念、絕私意、審惡幾,以及省防察檢紛紛之說,而學者用功,始不勝其繁且難矣。”⑦《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會語正集》,東臺袁氏編校本。那么,圣人所講的“克己”究竟應如何理解呢?念庵指明,這里的“己”是指的“身”,而不是“身之私欲”。他說:
然而夫子所謂克已,本即為仁由已之己,即謂身也,而非身之私欲也;克者力勝之辭,謂自勝也。有敬慎修治而不懈怠之義,《易》所謂自強不息是也。一息有懈,則焰然而餒矣。夫天,陽也,剛也。《易》之乾卦,著陽剛之德也。故乾以自強言之,示天下以法天之學也。告顏子而以克已言之,示顏子以體乾之道也。⑧《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會語正集》,東臺袁氏編校本。
這樣一來,“克己”被一庵解釋為“自強”“法天”的積極行動,而不是“察私防欲”那樣的消極作為。顯然,一庵對朱子在《四書章句集注》中將“己”理解為“身之私欲”的觀點,是持明確的批判態度的。
在“克己”的理解上,從朱子等人“察私防欲”的消極作為,轉變為一庵解釋的“自強”“法天”的積極行動,是否顯示出士紳之儒與平民儒者思維方式上的某種差異?無論如何,藉此我們可以發現,其中的確存在著宋明理學從“得君行道”的期許,到“覺民行道”的擔當之間的變化消息。人的基本生理欲望是“人所不能無者”,與其糾結于此,何如一意擔當而“法天”“自強”?這里無疑再次顯示了平民儒者無所倚待的主體意識。個人主體意識的不斷成長與發展,的確是心學發展的重要樞機。
在此種理解的基礎上,王一庵充分繼承了泰州學派平民儒學的宗旨。
(三)隨分而成功業:王一庵平民儒學思想的事功觀
一庵明言:
吾人為學不屑與鄉里庸眾之人共為之,終是自小。⑨《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會語正集》,東臺袁氏編校本。
他舉例認為,“大舜之所以為大”,是因為舜“善與人同”,“不獨自為善”,故而“與會為善,而使人人同得乎善,乃見其為善之大,正與天下化于孝,此之謂大孝一例。”(10)《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會語正集》,東臺袁氏編校本。這里,舉大舜為例,一庵表明了泰州平民儒學的一個重要立場:
雖耕稼陶漁之人,凡有向上之志、可接引者,皆可取也。(11)《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會語正集》,東臺袁氏編校本。
心齋泰州學派門下正是如此,如農人夏廷美、樵夫朱恕、陶工韓貞諸人出身為“耕稼漁樵”的平民儒者,并皆傳世,可稱卓犖。一庵更強調說:“鄙夫雖氣質凡庸,而良知本性未嘗不與賢知者等,故圣人必竭兩端而告之,非但良知人人自明,抑道本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舉其至近而遠者,自寓乎其中耳。”(12)《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會語正集》,東臺袁氏編校本。他在此指出了兩點:一是就良知本性上來說,鄙夫與賢者同;二是道(即良知)本來就是愚夫愚婦可以與知的。換言之,在良知本性面前,賢者與鄙夫平等,前者不存在什么先在的優越性。
反觀孔門,一庵認為平民教育本是孔門傳統,只不過是被秦漢以還的經生文士們給破壞了。在他看來,孔門教法是兼收并蓄,且各就學生材質大小,“造就曲成”之。此教法需要“有道君子”的擔當與包容。一庵道:
孔子欲得中道,而狂狷亦在;所思樂育英才,而鄙夫亦堪叩教。故包蒙藏疾,不棄一人;庸眾三千,兼收并蓄。夫然后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而造就曲成之盛,乃至七十余士,如造化之生物不息,而品物成章也。有道君子欲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則必有包容荒穢之量,然后可以收董陶長育之功。①《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會語續集》,東臺袁氏編校本。
也正是在恢復孔門平民教育傳統的立場,慨然以師道自任上,一庵高度評價了其師心齋的崇高地位,認為心齋的偉大之處正在于他使“愚夫俗子不識一字之人皆知自性自靈、自完自足”的平民教育功績。宜乎鄧志峰將一庵判作繼承心齋泰州“以師道為己任”主脈的“師道派”嫡傳②鄧志峰:《王學與晚明的師道復興運動》,第213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按:鄧志峰認為,王東厓(襞)雖承心齋家學,但仔細體認,東厓無論在思想還是行動上,都與乃父心齋相去懸絕。東厓實則受王龍溪(畿)影響甚大。鄧著第284—292頁。。
盡管一庵在實際行動方面無法與其師心齋相比,但他由是而形成了自己的“事功觀”:
圣人經世之功,不以時位為輕重。今雖匹夫之賤,不得行道濟時,但各隨地位為之,亦自隨分而成功業。茍移風易俗,化及一邑一鄉,雖成功不多,卻原是圣賢經世家法,原是天地生物之心。③《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會語續集》,東臺袁氏編校本。
他認為,作為一個“雖匹夫之賤”的平民儒者,在“不得行道濟時”的情況下,只須“各隨地位為之”,便也可“隨分而成功業”。扎扎實實地以自己的努力,使“一邑一鄉”移風易俗,即便成功不多,也是體現了“圣賢經世家法”,盡了“天地生物之心”。
由此來看,一庵這種“事功觀”所表明的平民儒者扎實的踐履,一方面沿著王陽明以來心學“覺民行道”的轉向,繼承了王心齋的平民儒學傳統,稱其為貫通二王并不為過;但另一方面,相比于其師王心齋周流天下,赤身擔當,慨然以師道為己任的宏大氣象,一庵這里無疑顯得有些無奈和無力。事實上,盡管一庵大興布衣集會,講學不已,但其身后再傳無聞,連他自己和學行思想也險些被歷史的塵霾所淹沒。如此狀況,實乃專制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必然結果。反觀近世,梁漱溟諸先輩傾心致力于鄉村建設運動,不也無果而終嗎?古今同然,個中消息,實堪體味。
三 王一庵的平民政治理想
一庵平生學行,以集結同志、開門受徒、興辦講會的平民教育活動為首要,以至臨歿遺言,也念念不忘“會學”。蓋以“布衣”為對象的講學集會為實踐其平民政治理想的主要手段而已。這一點與其師心齋一脈相承。
檢一庵所著《會語正集》與《會語續集》,他于講學過程中大力發揮了心齋的“淮南格物”與“安身立本”之學。
一庵概括心齋之學說:“先師《樂學歌》,誠意正心之功也;《勉仁方》,格物致知之要也;《明哲保身論》,修身止至善之則也;《大成學歌》,孔子賢於堯舜之旨也。學者理會此四篇文字,然后知先師之學,而孔孟之統燦然以明。”④《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會語正集》,東臺袁氏編校本。他以《樂學歌》、《勉仁方》、《明哲保身論》、《大成學歌》四篇作為心齋之學的代表作品,認為心齋之學繼承了“孔孟之統”,并且有力地發揮了“孔孟之統”。一庵為心齋的嫡傳高弟庶幾不謬。
對心齋的“淮南格物”說,一庵予以大力闡明:
先師之學,主于格物。故其言曰:格物是“止至善”工夫。“格”字不單訓“正”,“格”如格式,有比則、推度之義,物之所取正者也。“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謂吾身與天下國家之人。“格物”云者,以身為格,而格度天下國家之人,則所以處之之道,反諸和身而自足矣。⑤《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會語正集》,東臺袁氏編校本。
格物原是致知工夫,作兩件拆開不得。故明翁曰致知實在格物,格物乃所以致知,可謂明矣。且先師說物有本末,言吾身是本,天下國家為末,可見平居未與物接,只自安正其身,便是格其物之本。格其物之本,便即是未應時之良知。至於事至之物來,推吾身之矩,而順事恕施,便是格其物之末。格其物之末,即便是既應時之良知。致知格物可分拆乎?況先師原初主張格物宗旨,只是要人知得吾身是本,專務修身立本,而不責人之意,非欲其零零碎碎於事物上作商量也。⑥《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會語續集》,東臺袁氏編校本。
他復通過解釋《大學》三綱領中的“止于至善”來發揮心齋的“安身立本”之學說:
先師謂止吾身於至善之地,使身安而不危,則能妙出處而動合時宜,制經權而行無轍跡,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然后保家保國天下,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而非斷港絕河之學矣。⑦《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會語正集》,東臺袁氏編校本。
又云:
先師以“安身”釋“止至善”,謂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必知止吾身於至善之地,然后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故“止至善”者,安其身之謂也。欲安其身,則不得不自正其身。其有未正,又不容不反求諸身,能反身則身無不正,身無不正則處無不安,而至善在我矣。古今有志於明德親民,而出處失道,身且不保者,不明止至善之學故也。⑧《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會語正集》,東臺袁氏編校本。
可見,一庵充分繼承了心齋平民儒學的特質。侯外廬等先生所主編的《宋明理學史》深刻指出,心齋奠基于“淮南格物”基礎上的“安身之本”之學,“在古舊的語言形式下,蘊含了爭取人的生存權利和維護人的尊嚴的思想”,并且從中“推度出人己平等和愛人思想”。①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主編:《宋明理學史》,下冊,第439—44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我們之所以稱一庵的政治理想為“平民政治理想”,正是由此出發的。
王一庵極為認同心齋以師道自任,“隨處覺人”的“大成之學”。他說:“今學者茍知隨處覺人,不徒善一身而已,雖不能為大成之圣,是亦大成之學也。此先師擴孟子所未發處。”②《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會語續集》,東臺袁氏編校本。在他看來,在“君、師之職”已相違離的當下,毅然以師道自任,拿起被帝王拋棄的師教大權,奉行平民教育,乃是造成安定平和理想社會的根本手段。他說:
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師。自古帝王君天下,皆只師天下也。后世人主不知修身慎德,為生民立極,而君師之職離矣。孔子憫天下之不治皆緣天下之無師,故遂毅然自任,無位而擅帝王師教之大權,與作《春秋》同一不得巳之志。況不俟時位,隨人接引,則杷柄在手,而在在成能,此其所以賢堯舜而集大成者,凡以任師道故也。觀其汲汲周流,無非欲與斯人共明斯道,或上而君卿大夫、下而士農工賈,茍可以得其人,斯足以慰其望矣。孔,孟既沒,世鮮能師。至宋周子曰“師道立而善人多”,程子曰“以興起斯文為已任”,真得孔、孟任師家法,但不力主其說,以為運世承統第一事功。吾先師所以不得不自任也,而亦豈所得已哉?③《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會語續集》,東臺袁氏編校本。
如此踐行,則建立在血緣宗族之上的和諧社會政治局面是不難實現的。
那么,一庵認為如何實現他的平民政治理想呢?
首先,改善王政的四大方面:“井田”、“封建”、“肉刑”、“里選”。一庵指出,“王政之大端,莫要於井田、封建、肉刑、里選四者,今皆變壞而不可復矣。然限田可以救不井田之失,久任可以救不封建之失,嚴生刑而寬死則可以救不肉刑之失,先德行而后文藝可以救不里選之失。”④《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會語正集》,東臺袁氏編校本。這顯然深受其師王心齋在《王道論》中闡述的政治理想的影響。
其次,立師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而“熔鑄天下”。一庵在回答“使子為政亦能熔鑄乎?”之問時說:“熔鑄天下,必君相同德同心,方可整頓。此孟子所以不得行其志者也。若使得宰一邑而熔鑄一邑,理亦有之,但恐監司者掣其手足、與遷轉之速,則不能耳。然終是田制之偏、賦役之重,刑統濫於罰贖、學校弊於文辭,凡此皆關大政。熔鑄,夫豈易!然古人之學不襲時位,吾將以興起斯文為己任,使師道立,善人多,朝廷正而天下治。此吾所以熔鑄天下之一大爐冶,而非時位所能限也。”⑤《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會語續集》,東臺袁氏編校本。簡而言之,一庵認為以師道自任大興斯文,是“熔鑄天下”,實現理想政治局面的關鍵。
復次,從家庭、宗族的“勸善”入手,實行教化。一庵說:“吾人誠欲以善善世,必自有藹然親愛實意,先得其心,然后言易入而善易從也。如欲善父母,必親愛父母,而得父母之心;欲善兄弟妻子,亦必親之愛之,而各得其心。以至於宗族親戚、朋友鄉黨,獲上獲下,莫不皆然。未有情意不孚,而教化可行者也。故君子親得天下人,然后教得天下人。”⑥《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一《會語續集》,東臺袁氏編校本。無疑,在一庵這里,由血親情感出以發,以情感人,是“勸善”施教的教化工作取得理想效果的起點。一庵由是還寫了不少淺白順口的詩歌,來做這方面的工作。如他作詩勸人“尊敬長上”云:“天地生人必有先,但逢長上要謙謙。鞠躬施禮宜從后,緩步前行莫僭前。庸敬在兄天所敘,一鄉稱弟士之賢。古今指傲為兇德,莫學輕狂惡少年。”⑦《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二《鄉約諭俗詩六首》,東臺袁氏編校本。又勸人“教訓子孫”云:“子孫有教是詒謀,失教還為祖父憂。不獨義方昭訓迪,更尋師友擇交游。才須學也夸賢嗣,愛勿勞乎等下流。驕惰養成為不肖,敗家蕩產是誰尤?”⑧《王一庵先生遺集》卷二《鄉約諭俗詩六首》,東臺袁氏編校本。
問題在于,盡管一庵繼承了其師心齋泰州學派的平民儒學特質,作為一個平民儒者有區別于士紳之儒之處,然而,就其平民政治理想來看,仍無法跳出自然經濟生產方式的桎梏,只能在小生產的生產生活條件下,做一廂情愿的空想和蒼白無力的說教。此確如龔杰所指出的,王一庵“設想的‘士農工賈’在小農經濟條件下,以‘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父慈子孝’、尊兄愛弟為‘鄉約’,而達到‘邦家其昌’的‘安樂’景象,能否實現呢?他曾直言不諱地說‘成功不多’,對此沒有信心,說明他與泰州學派的許多學者一樣,洞察明王朝所面臨的經濟、政治、法律和教育上的嚴重危機,但又找不到出路,不得不在舊制度的深溝高壘中四處碰壁,輾轉彷徨。這就是泰州學派基本的政治特征。”⑨龔杰:《王艮評傳》,第228—229頁,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毋庸諱言,從對王道大政的熱切關注,到不無尷尬的試圖以師道自任而“興起斯文”,再到蒼白的勸善詩,一庵的平民政治理想,與其師心齋一樣,“百姓日用”推展開來的“覺民行道”激情,亦止于“百姓日用”所限定的底層精神格局。況且,一庵游走于士紳與平民之間,既無其師心齋的超凡魄力,更無同為泰州后學的顏山農、何心隱輩“異端”諸人的狂俠氣象。概而言之,王一庵的平民政治理想乃至泰州學派“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王道政治理想,亦不過止于道德理想主義的空想而已。“以道覺民”的“外王”取向,始終徘徊于“內圣”的內涵邊緣,難以真正向外拓展。它的寶貴思想內核和重要價值,還要到了小生產方式的“硬核桃”被徹底砸開之后,才能為我們所充分認識與分享。
On the Thought of Wang Yi-an’s Popular Confucianism
JIA Qian-chu1,CHEN Han-ming2
(1.Law School,Shandong University at Weihai,Weihai 264209,China;2.College of Tianjin Trade Union Administrators,Tianjin 300170,China)
According to his whole life,Wang Yi-an was a scholar of common people,although he once was a junior educational officer in the last years of his life.He inherited the thoughts of Wang Xin-zhai thoroughly and made new development in positive heart and restraining in privacy which was the base of his Confucianism of the popularity.The idea of self-renewal and according to the Heaven revealed his subject awareness.To establish accomplishments within fate was his view of achievement.Giving lectures and gathering adherents was the main way of achieving his political idea.The pale of this way show the fragility of external strength and internal holiness under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 in that time.
Wang Yi-an;positive heart and restraining in privacy;the subject awareness;Confucianism;fragility
B222
A
1008—1763(2012)02—0020—06
2011-05-10
賈乾初(1971—),男,河北滄縣人,山東大學威海分校法學院講師,法學博士,山東大學政治學流動站博士后研究人員.研究方向:中國傳統政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