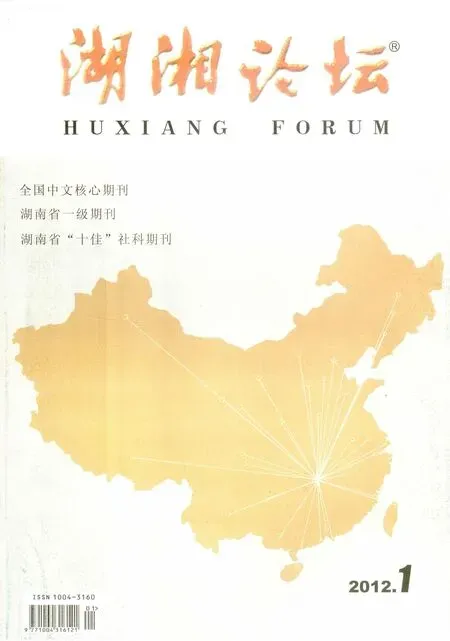經學與中國哲學關系的傳統認定及其反思
陳錦宣
(成都理工大學,四川成都611745)
經學與中國哲學關系的傳統認定及其反思
陳錦宣
(成都理工大學,四川成都611745)
在經學與中國哲學的關系問題上,自中國哲學學科建立時起就形成了中國哲學需于經學中求的傳統思維定勢,并且大多數研究者認同并采用了這種觀點。這種定位是奠基在上世紀初對“什么是哲學”和“什么是中國哲學”的認識基礎之上的,西方的學科分類標準對其亦產生重要的影響。當前隨著對“什么是哲學”、“什么是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合法性”等問題的深入反思和對經學地位的重新認識,先前的這種定位需要加以認真思考和重新認定。
經學;中國哲學;關系
經學與中國哲學的關系問題從中國哲學學科建立時起就存在,但是對此問題的探討和挖掘還不夠。中國哲學學科建立之后,形成了中國哲學需于經學中求的傳統思維定勢,研究者們大多認同并采用了這種觀點。如果對二者關系的傳統定位加以進一步認真反思的話,會發現其定位是奠基在上世紀初對“什么是哲學”和“什么是中國哲學”的認識基礎之上的,西方的學科分類標準對其亦產生重要的影響。當前隨著對“什么是哲學”、“什么是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合法性”等問題的深入反思以及對經學地位的重新認識,先前的這種對二者關系的定位需要加以認真思考和深入探討并予以重新認定。
一、傳統認定:中國哲學需于經學中求
經學與中國哲學的關系問題,是伴隨著“哲學”概念傳入中國、中國哲學學科的建立而產生的。眾所周知,明治初年日本啟蒙思想家西周造“哲學”一詞翻譯西方的“philosophy”,后經我國學者黃遵憲傳入,“哲學”此譯名最早出現于1887年黃遵憲所撰就的《日本國志》一書。在此之后,中國思想界即有了“中國哲學”概念的提出,在胡適之、馮友蘭等人的努力開創之下,中國哲學更演變為一門嶄新的學科。可以說,中國哲學學科的建立是王國維、蔡元培、胡適之、馮友蘭等人通過引進西方的哲學觀念及其學術研究范式完成的,創立中國哲學學科的過程,其實就是經學研究的退場過程,就是經學研究模式向現代哲學研究模式的轉換過程。因此,經學與中國哲學的關系問題,從中國哲學學科誕生之日起就存在了,但是這個問題一直為學界所忽視,學人們對之鮮有論及,或有論及而語焉不詳。
馮友蘭是少有的論及此問題的人之一。他于1931年發表專文《中國中古近古哲學與經學之關系》,探討了中國中古近古哲學與經學的關系,他認為:
“中古近古時代之哲學,大部分須于其時之經學中求之。在中古近古時代,因各時期經學之不同,遂有不同之哲學;亦可謂因各時期哲學之不同,遂有不同之經學。大概言之,其中有哲學成分之經學,為今文家之經學,古文家之經學,清談家之經學,理學家之經學,考據學家之經學,經世家之經學。”[1]P196-197
分析馮友蘭的論述,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第一,他認為經學與中古近古哲學關系密切,經學思想與哲學思想緊密相關,有什么樣的哲學思想就有什么樣的經學思想,有什么樣的經學思想就有什么樣的哲學思想。第二,中古近古哲學思想存在于經學思想之中,中古近古哲學家們大多沒有獨立的哲學體系,而有完整的經學體系,因此探求中古近古哲學家的哲學思想,需要到他們的經學思想中尋求。第三,中古近古哲學廣泛存在于經學之中,幾乎可以說所有的經學中都包含有哲學。馮友蘭對經學與中國哲學關系的認定我們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即:中國哲學需于經學中求。
馮友蘭的這種對經學與中國哲學關系的認定影響了后來大多數學者。比如這種思想就典型地反映在王葆玹先生對經學派別的劃分之上。他在《今古文經學新論》中談到:“我以為,歷史上的經學可歸結為三大派系,即今文經學的系統、古文經學的系統和形上學化的經學系統。”[2]P17對于“形上學化的經學系統”他作了如此的解釋:“所謂形上學化的經學,包括魏晉玄學、隋唐經學、宋代理學及明代心學等等,其特點是注重于形上學而輕視禮樂,或者說重視哲學而輕視類似于宗教神學的東西。”[2]P17可以看出,王先生實際上就是從經學中把他認為屬于哲學的部分單獨劃分為一個派系,而這個劃分的標準就是哲學的標準。事實上,他的這個劃分標準的前提就是承認中國哲學存在于經學之中,中國哲學需于經學中尋求。
時至今日,人們對經學與中國哲學的關系認定趨向基本定位于中國哲學需于經學中求,因為他們認為古代思想家的學術活動大多以經學研究為主,在眾多的經學論著所闡發的經學思想中包含著豐富的哲理,中國哲學即是通過注釋儒家經典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因此中國哲學需要到經學中去尋求并加以整理,使之系統化。
需要提及的是,章太炎在此問題上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認為經學中鮮有哲學。在其《國學概論》中,他提出:“討論哲學的,在國學以子部為最多,經部中雖有極少部分與哲學有關,但大部分是為別種目的而作的。以《易》而論,看起來像是討論哲學的書,其實是古代社會學,只《系辭》中談些哲理罷了。”[3]P30筆者認為章先生所持的是“中國哲學需于子學中求”的觀點,因為在他看來,雖然經學中有哲學,但是相比于經學,哲學思想的精華卻在子學中。章太炎曾把哲學分為四類:“以哲學論,我們可以分宋以來之哲學、古代的九流、印度的佛法和歐西的哲學四種。”[3]P47在這四類哲學中,他認為宋以來的哲學不如“九流”之哲學,故推重“九流”,以之為最。他明確提出:“宋以來的理學和九流比較看來,卻又相去一間了”,“‘九流’實遠出宋、明諸儒之上”。[3]P47-48所以說,章太炎持有的是經學與中國哲學關系不大的觀點,這也代表了一種認定的趨向。
二、傳統認定的原由探析
為什么馮友蘭等人在經學與中國哲學的關系上會做出中國哲學需于經學中求的認定呢?探討經學與中國哲學的關系問題關鍵是如何界定“什么是中國哲學”,因為對于“什么是經學”在學界是有共識的,而對于“什么是哲學”和“什么是中國哲學”的問題卻存在著相當大的分歧,對“中國哲學”的理解不同導致了對經學和中國哲學關系的認定相異。因此回答這一問題我們需要著重注意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這種認定是建立在對“什么是哲學”和“什么是中國哲學”的認識基礎之上;二是其認定與西方學科體系的傳入和全盤接受緊密相關。
“哲學”是西方傳入的概念,一直以來,對于“什么是哲學”的問題都是按照西方哲學的標準來進行界定的,因此在“哲學”一詞還沒有進入中國學者的“自我意識”形成“自覺”之前,對“中國哲學”的定義也只能夠按照西方哲學的標準進行界定。所以當我們以西方哲學的問題域來劃定哲學的研究范圍時,中國哲學也只能以“宇宙論、人生論和知識論”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
馮友蘭之所以對中國中古近古哲學與經學的關系做出以上的認定,根源在于他認為哲學就等同于“西方哲學”,他對“中國哲學”的界定采用了西方哲學對哲學的定義標準。他在其所著的第一部《中國哲學史》(兩卷本)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哲學本一西洋名詞。今欲講中國哲學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國歷史上各種學問中,將其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選出而敘述之。”[4]P1他所著的《中國哲學史》即是用中國歷史上的材料來套西方哲學的標準。所以,他如是界定“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家”:“所謂中國哲學者,即中國之某種學問或某種學問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也。所謂中國哲學家者,即中國某種學者,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家名之者也。”[4]P8他用西方哲學的標準來判定“什么是中國哲學”,在這樣的思想前提之下,他對經學進行了裁剪,符合者選取之,不符合者拋棄之,這種做法的后果是他不能看見存在于中國哲學中的“形式上的系統”,而只能努力地“在形式上無系統之哲學中,找出其實質的系統”。[4]P14因此,馮友蘭的認定只能說是在西方哲學視野下對經學與中國哲學關系的認定,這種認定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故胡適之、馮友蘭等所創建的“中國哲學”只能稱之為“中國現代哲學”,他們所寫的《中國哲學史》只能稱之為站立在中國現代哲學角度去重新審視現代之前的哲學文本所重新構建的“中國哲學史”,因此,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哲學史”,只能稱之為“現代中國哲學家眼中的‘中國哲學史’”。
另外,我們都知道,“經學”是中國傳統學術門類中最重要、最有影響力的學問,按照現在的學科標準,“經學”包括的范圍很廣,涉及哲學、宗教、史學、文學、藝術、政治、經濟等諸多學科,事實上在西方近代學術門類中,并沒有一個與“經學”相對應的學科。其實,中國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學科分類,就傳統來講,中國只有典籍分類法,后來這種典籍分類法不僅成為了圖書典籍的分類標準,而且也成為了學科的分類標準。中國傳統典籍分類標準經歷了從劉歆的《七略》之“七分法”向紀昀主持編定的《四庫全書總目》之“四分法”演變的過程。在《七略》中,劉歆把典籍分為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和方技略七大類。在這七大類中,最重要者為“六藝略”(即六經),儒家之六經處于獨尊的地位。《四庫全書總目》將典籍分為“經、史、子、集”四部,其中最重要者亦為經部。按照這種典籍分類,自然就形成了相應的以典籍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在西方學科體系傳入之前,中國無“哲學學科”,中國哲學還沒有經歷從傳統的“經學”、“子學”等中分離出來的過程。
但是這種以典籍為研究對象的“學科”與近代西方意義上的“學科”是完全不同的。隨著西學東漸的影響,西方現代學科體系被中國學術界所認識并全盤接受,近代中國開始沿用這個學科體系。在晚清吸收西方的學科體系實現學科體系轉型的過程中,經學的學科定位呈現的是逐漸下降的并最終被“消融”的過程。因為按照西方的學科體系,“經學”難以在其中找到相應的學科位置。按照西方的學科標準,“經學”涉及了哲學、宗教、史學、文學、藝術、政治、經濟等多個學科,所以如何將經學納入新的學科體系中,就成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解決這個問題方面,人們采取的是“解構”之后重新“建構”的方法。將經、史、子、集四部分類體系,先加以拆散,將其完全打破,然后再重新按照新的學科標準歸并到新的體系中去。可以說,在這個所謂的現代知識分類框架中,經學是被完全“分解”了的。按照西方的學科分類標準,《周易》、《論語》、《孟子》、《公羊傳》、《孝經》等被劃歸到了哲學學科;《尚書》、《左傳》、《谷梁傳》、《周禮》、《儀禮》、《禮記》等被劃歸到歷史學科;《詩經》被劃歸到文學學科;《爾雅》進入到語言文字學科;等等。
事實上我們知道東西方文化是不同的文化,西方的學科體系是在西方文化的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它是為了解決西方自身的問題而設計的,不是為了東方文化而設計的,所以說這種學科體系并不一定就適用于我們的學科建設和發展。我們只能在學習和引進西方學科體系的過程中經過對它的消化,充分兼顧我國傳統學術的特點,使之有機結合,而不能全盤地不分清紅皂白就加以吸收。當然,這個形成過程是清末中國積貧積弱,西方占據了各個方面的話語霸權,中國在此話語霸權下完全“失語”的反映。
綜上所述,這種傳統關系的認定原因就是中國學者在創建“中國哲學”學科的過程中全盤吸收西方的學科分類標準,以西方哲學的標準來衡量“中國哲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一認定就是“西方中心主義”思潮在經學與中國哲學關系上的反映,它是西方哲學語言和學科體系在中國占據話語霸權的結果。
三、對傳統認定的反思
如前所述,對經學與中國哲學關系的傳統認定是建立在對西方學科體系的引進和以西方哲學的標準來界定“什么是中國哲學”的基礎之上的,在此我們需要反思兩個問題:一是西方哲學是否就等同于哲學,西方哲學的標準是否能全世界通用;二是西方的學科標準是否適應于中國,這種現代的學科體系與中國傳統文化是否能“兼容”。
首先,哲學是否就專指西方哲學呢?上個世紀末,著名哲學家德里達訪問上海,與王元化先生談話時提出中國只有思想而沒有哲學,這個談話引起了學術界關于“中國有無哲學”問題的重視,此后,我國學者鄭家棟先生在1999年明確提出了“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這就引發了學術界對“什么是哲學”、“什么是中國哲學”、“中國哲學的‘合法性’”等問題的深入討論。時至今日,這場討論正逐步深入,所討論的問題由“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進入到對《中國哲學史》寫作方式的反思,再進一步深入到探討“中國哲學”是否需要重構及如何重構的問題。這場討論富有成效的成果之一就是中國學者對“哲學”、“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各自的定義和研究范圍有了更加清楚的把握,對三者之間的關系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在三者之間的關系上宜用“共相”和“殊相”(或“共性”和“個性”)的關系來把握,哲學既具有普遍性之“共相”,而這種“共相”具體表現為不同民族、不同地區哲學之“殊相”。所以說“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都只是哲學這一共相下的殊相之一。
既然“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是不同的殊相,那么二者就是不同的哲學,西方哲學的界定標準是不能夠用到中國哲學之上的。關于這一點,金岳霖先生早就有主張:“我們可以根據一種哲學的主張來寫中國哲學史,我們也可以不根據任何一種主張而僅以普通哲學形式來寫中國哲學史。胡適之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就是根據于一種哲學的主張而寫出來的。我們看那本書的時候,難免一種奇怪的印象,有的時候簡直覺得那本書的作者是一個研究中國思想的美國人;胡先生于不知不覺間所流露出來的成見,是多數美國人的成見。”[5]P6其實,金岳霖對胡適之的批評也適用于馮友蘭。在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兩卷本)問世之后,牟宗三更是指出:“中國學術思想既鮮與西方相合,自不能以西方哲學為標準來定取舍。若以邏輯與知識論的觀點看中國哲學,那么中國哲學根本沒有這些,至少可以說貧乏極了。”[6]P3因此,“以西方哲學為標準,來在中國哲學里選擇合乎西方哲學的題材與問題,那將是很失望的,亦是莫大的愚蠢與最大的不敬。”[6]P6在這個方面,當前學界更是達成廣泛的共識,如宋志明先生就認為:“西方哲學只是一種哲學,并非哲學的范本。照搬照抄西方哲學的研究模式不可取,賣弄西方哲學的新名詞更不可取……”[7]P105龔雋先生也強調:“我的主張是借用西方的敘述來激活中國哲學的問題,而不只是用西方哲學的概念柜架來剪裁中國哲學的史料,決定中國哲學的問題,使之簡單地成為對栽種哲學的說明。”[8]P43
在第二個問題上,現代的學科體系與中國傳統文化不能“兼容”,已經表現在作為整體的“經學”已被肢解上。而恰如湯一介先生所言:“對我國的‘經學’研究,可能綜合性的研究更有必要。”[9]P3-4因為經學是一個整體,傳統的經學思想認為各經有各經之功用,如荀子認為:“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荀子·儒效》)所以,在培養人方面,孔子曰:“文藝于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漢書·滑稽列傳》)經書構成了一個系統,只有集中在一起才能發揮經學的整體功能,產生效應。用西方的學科標準來僵硬地劃分中國的傳統學術,將經學“肢解”成各個部分,這是非常不恰當的。如彭林先生就對按照西方的學科標準來“分解”經學的傳統做法表達了自己強烈的不滿,提出“我們應當重新檢視百年以來盲目追隨西方大學文科體系的迷誤,以及由此而帶來的消極后果,給經學以應有的學科地位和必要的尊重”,并建議“在有條件的重點大學中設立經學系或者經學學院”。[10]P10-14事實上,西方的現代學科分類有其嚴重的局限性,正如尼采所嘲諷的:“因為我們現代人自身內毫無所有;我們只由于使我們填滿了,并且過分地填滿了陌生的時代、風格、藝術、哲學、宗教、認識,而成為一些值得注意的東西,就是成為走動的百科全書,一個誤入我們時代里的古希臘人也許將要這樣稱呼我們。”[11]P25西方的學科分類只能導致人的個性的缺失,使人成為“走動的百科全書”,這顯然與中國傳統思想的宗旨相背離。
既然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相區別,西方哲學的標準不能夠運用到對中國哲學的界定之上,加之西方的學科標準與中國是不相適應的,它與中國傳統文化不能“兼容”,那么對經學與中國哲學關系需要重新思考和重新認定。而筆者認為重新思考和認定二者的關系需要把握以下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重新定位要以對“中國哲學”的定義為基礎,而對“中國哲學”的定義要從中國傳統、中國哲學自身出發,找準中國哲學的研究對象,找出自身特有的問題域,而不是以西方哲學為標準;二是重新定位要把握經學和回歸經學的整體性,從整體上理解和研究經學,而不能肢解經學。
[1]馮友蘭.中國中古近古哲學與經學之關系[A].三松堂學術文集[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
[2]王葆玹.今古文經學新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7.
[3]章太炎.國學概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M].北京:中華書局,1961.
[5]金岳霖.審查報告[C].載: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M].北京:中華書局,1961.
[6]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7]宋志明.關于中國哲學研究的幾點看法[J].中國哲學史,2005,(4).
[8]龔雋.再論中國哲學史作為“學科”的合法性危機與意義[J].哲學研究,2005,(8).
[9]湯一介.中國經學與傳統學術[J].中國文化研究,2006,(春之卷).
[10]彭林.論經學的性質、學科地位與學術特點[J].河南社會科學,2007,(1).
[11]尼采.歷史對于人生的利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B2
A
1004-3160(2012)01-0086-05
2011-12-10
陳錦宣,男,四川宣漢人,成都理工大學廣播影視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哲學。
責任編輯:曹桂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