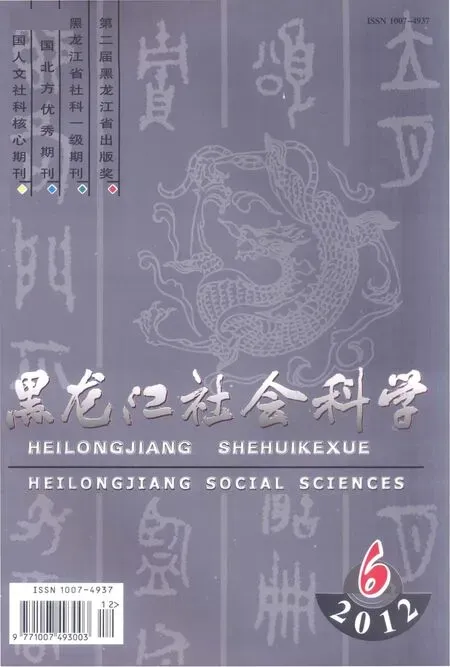經濟增長與民生建設關系的歷史演進
喬 榛,徐 龍
(黑龍江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哈爾濱150080)
民生建設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生活中最受關注的問題之一。回顧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的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一直都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這一基本經濟路線核心內容的確立無疑是中國改革開放后所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的一個重要原因。當中國從改革開放之初的經濟規模居世界第十五的位次上升到目前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時,我們感到在這種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屬于民生的建設步伐并沒有相應地跟進。進入21世紀之后,特別是在“十一五”后期和“十二五”規劃中,民生問題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視,并且成為全社會普遍關注的一個重要的問題。于是,經濟增長與民生建設的關系現實地擺在人們面前。其實,就經濟增長與民生建設的關系來看,它絕不是今天所面臨的新問題,對這一關系我們可以進行歷史的追溯。
一、經濟增長與民生建設關系所涉內容的歷史演進
人類社會自產生的那天起,因為其擺脫了被動生存的狀態,就一直為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而努力。然而,由于人類最初的生產能力極低,因此,一個最早出現的民生問題便擺在人們面前,即如何分配好人們集體勞動所獲得的極少的生活資料?從某種意義上講,在生產能力極低且長期停滯時期,分配好人們共同獲得的生活資料具有更加重要的生存意義。因為在一種自然選擇過程中,平均分配成為人們唯一的選擇,非如此人們是無法生存的。當人類社會的生產能力進一步提高,并且出現一定的剩余時,收入分配被賦予其他的形式,或者說基于剩余索取權的不平等,收入分配出現了差距,一些在社會中處于優勢地位的人獲得了生產的剩余,而絕大多數人掙扎在生存線上。自此,人類社會走上一條隨生產能力不斷提高、收入差距也相應擴大的道路。而且在一些理論中,這種收入分配差距被作為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基本條件。一直到人類社會的生產力發展到更高的程度,也就是生產力發展使人類擺脫了供給的約束而變成需求約束時,收入分配差距仍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一種障礙,因此,尋求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途徑成為一些國家努力的方向。這種屬于經濟增長與民生建設關系的最早一項內容,其演進伴生了人類社會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的全過程,而且其演進的軌跡完整地體現了一個螺旋式的循環過程。
在人類的生產活動中,或者說在人類追求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首先是建立在生產要素投入的基礎上。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就是勞動力。因為人類的生產能力極低,人類只有建立在集體的基礎上才能夠維持生存,因此,人口的規模不僅標志著集體的力量,而且也意味著一種較高的生產力。此外,無論在人類文化初期,還是古代世界、中世紀和現代殖民地,人們或者是在公有制基礎上表現為個人對氏族或公社的依賴,或者是在私有制的基礎上表現為人們的奴隸地位或受直接統治和從屬關系的地位。所有這些都表明人們參與生產活動屬于被動的生存選擇,而且人們是被束縛在生產活動中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勞動者能否參加勞動或今天所謂的就業還沒有成為一個民生問題。只有在勞動者與自己的勞動力發生分離,并且勞動力成為一種商品時,勞動者除勞動力之外再沒有其他的可以獲得生活資料的資源,因此,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成為一種謀生的手段。這時,勞動力能否出賣,即就業能否成為關系到勞動者生活的一個重要前提,如此,就業就成為一個民生問題。而這時的經濟增長與就業的關系也隨之成為經濟增長與民生建設的一項內容。勞動力成為商品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形成的一個重要前提,而“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或者說同一勞動場所),為了生產同種商品,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工作,這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1]。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就業問題并不是很突出的問題。只有到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到機器和大工業階段,就業問題才凸顯出來,因為在機器和大工業時期,人成為機器的附庸并受到機器的排擠,因此,失業成為工人階級揮之不去的一個陰影,而就業則成為關系人們生活的一個重要內容。
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中,始終被一種不確定性所籠罩著。在最初階段,由于生產力水平極低,人類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很低,因此,來自自然的變化帶給人類的威脅比較大。在這一時期,人類把發展生產力作為應付自然不確定性的重要手段,所以發展生產力或者實現經濟增長就成為人們的主要目標。在這種努力下,人類社會的生產力逐步提高,人類控制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斷增強。人類社會的這種生產能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來自自然的風險,但是,一個新的風險不斷積累,并且成為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這就是由人們之間的不平等所引發的社會風險。在生產力積累的過程中伴隨著人們之間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斷擴大,一部分獲得社會財富的較大部分,而另外絕大部分只能占有社會財富的較少部分,以至于富裕的人生活無憂,甚至是“朱門酒肉臭”,而窮苦的人面臨著生存的危機。如此,一個新的民生問題出現了,即社會保障問題。于是,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如何保障人們的基本生活,被現實地擺在人們面前。特別是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之后,一方面人們之間收入差距演化為兩極分化,另一方面這種兩極分化不僅成為一個重要的民生問題,而且也是一個對經濟增長起到制約作用的問題。自此,經濟增長與社會保障成為經濟增長與民生建設的內容。今天,如何處理好經濟增長與社會保障的關系是世界各國追求民生目標的重要方面。
如此可以看出,經濟增長與民生建設的關系既是一個古老的問題,也是一個內容不斷豐富的問題。人類社會的發展說到底是要解決人民的生存或者生活問題,而在實現這一目標的過程中,人們選擇的是一種迂回的途徑,首先是在實現民生目標的手段上做文章,因為如何促進生產發展和經濟增長是人類社會較長時間重點關注的問題,而作為目標的民生問題反倒成為一種“副產品”。當人類社會的發展積累了越來越高的生產力之后,民生這一原本屬于最終目標的問題才能夠凸顯出來,其包括的內容越來越多,除了以上的收入分配、就業和社會保障之外,教育、醫療、住房等諸多內容也進入民生建設的選項。這表明民生是一個隨著生產力發展逐步凸顯的問題,在生產力水平比較低的階段,民生問題隱藏在經濟增長的背后,而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民生問題才最終凸顯并越來越處于主導地位。在這個過程中,經濟增長與民生的關系也經歷了一個演進并逐步多樣化的過程。
二、經濟增長與民生建設關系取向的歷史演進
經濟增長與民生建設的關系體現在一個歷史進程中,其包含的各種關系有著不同的取向。在各種關系取向的演進中,映射出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歷程。
從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的關系看,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相互影響的不同程度是如何體現的,這包含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也孕育了豐富的理論資源。在人類社會的初期,經濟增長決定著收入分配。生產力水平低,人們所獲得生活資料少,在這種情況下,平均分配是唯一的選擇。否則,作為生產所依賴的群體難以生存,生產本身也將難以為繼。因此,生產決定了消費,或者經濟增長決定收入分配表現得非常突出。當然,在這一關系中,也能夠看到收入分配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也就是收入的平均分配保證了生產的順利和延續。實際上,這時體現出的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是一種雙向關系,即經濟增長的水平選擇了平均分配,平均分配使生產得以延續。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生產能力達到了產生一定剩余的程度,這時收入分配受到更高的關注,在社會中取得支配地位的人群以最大限度地獲得這些剩余為目標,因此,收入分配在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中取得了較為突出的地位。當然,這種收入分配以不平等為主要特征,經濟增長在這個階段處于停滯狀態。進入近代以后,特別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以后,人類社會獲得了一種經濟增長的新的機制,這使得生產力獲得了巨大的解放,經濟增長也因此獲得了非常突出的地位。自此,在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的關系上,經濟增長重新取得了決定性的地位,這使得經濟增長結束了過去漫長的停滯階段而進入了高速時期。在這一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經濟增長決定的收入分配呈現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隨著經濟進一步增長,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從過去的經濟增長的條件變成了經濟增長的約束,因此,收入分配開始轉向,最終又呈現隨經濟增長收入分配的差距在縮小,這就是著名“庫茲涅茲倒U曲線”[2]。由此可以看出,在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關系的歷史演進中,其關系的取向經歷了一個從雙向相互影響到單向影響、再到雙向相互影響的演進過程。
從經濟增長與就業的關系看,經濟增長與就業的相互影響的不同程度也有一個歷史趨勢。如前所述,就業成為一個民生問題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特別是隨機器和大工業的產生而產生的。因此,從民生的角度分析經濟增長與就業關系的不同取向,首先體現為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影響。盡管勞動者的就業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者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一個因素不再決定于勞動者自身所具有的生產能力,而是決定于資本對勞動者的需要。因此,就業成為受資本決定的一種經濟現象,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就業變成一個民生問題,之前,勞動者自然作為生產者的地位發生了改變,勞動者能否得到一份工作不再是個人的意愿,而是受資本決定的一種結果。如果把經濟增長理解為資本家獲得剩余價值的一種手段,那么就業就成為受經濟增長決定的一種結果,當經濟高漲時,就業會增加,工資也相應地提高;當經濟蕭條時,就業會減少,工資也相應地降低。不過,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特別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就業這一生產力的要素,其性質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它不僅僅作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一個因素,而且作為擴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一個重要因素,起到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自此,就業的民生意義進一步凸顯,而且成為對經濟增長具有重要作用的一個因素。如在凱恩斯的經濟學理論中,有效需求是宏觀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所以就業不再是體現勞動力參與生產的一個要素,而更重要的是它成為影響有效需求的一個重要因素。從這個角度講,或者從這個時期開始,就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顯得非常重要,而且經濟越是發達,這種作用會越明顯。
從經濟增長與社會保障的關系看,經濟增長對社會保障的影響和社會保障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也在歷史的演進中有著不同的表現。在生產力不斷發展的過程中,由于在生產力基礎上形成的生產關系使得人們之間出現了巨大的不平等,由此帶來了一定的社會風險。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保持經濟增長,必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這種社會風險,于是,當生產力達到一定水平后,經濟增長就提出了對社會保障的要求。具體說來,當歐洲的工業革命帶來生產力快速增長的同時,社會矛盾也隨之不斷積累,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孕育了最早的社會保障制度,早在1601年英國女王頒行了世界上第一部《濟貧法》。這雖然只是社會保障制度的一個雛形,但是,它反映出一個隨生產力發展、經濟快速增長而產生的結果。因此,從歷史的演進來看,是生產力發展或者經濟增長產生了社會保障制度。不過,在經濟增長最初引起社會保障問題之后,社會保障只是為了經濟順利增長而提出的一種要求,盡管這也是對民生的一種保障,但是絕不是在積極的意義上呈現的。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經濟增長所要求的秩序不僅涉及完備的市場秩序,而且也對社會秩序有著越來越強的要求。這時社會保障體現的民生特征就越來越明顯,同時,社會保障被賦予的意義也越來越豐富,它不僅是保障社會秩序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是促進消費需求的重要保證。當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時,社會保障所顯示的意義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激發人們的消費需求,這對于生產能力處于過程階段的國家來說,激發這種消費需求具有巨大的經濟增長意義。從這個角度看,社會保障在一定階段上體現了對經濟增長的巨大促進作用。在現代社會,社會保障不僅依賴經濟增長,而且也是經濟增長的一個條件,二者相互作用的特征非常明顯。
以上對經濟增長與民生建設的各方面關系取向的歷史考察,可以看出一個基本的趨勢:屬于民生的幾項內容,包括收入分配、就業和社會保障,都是隨生產力水平提高和經濟發展而提出的,因此,可以說是經濟增長使一系列的民生問題逐步顯現,而顯現出來的這些民生問題、尤其是民生的改善又對經濟增長具有越來越明顯的促進作用。如果說在生產力水平還比較低的時期,經濟增長作為主要的任務是任何一個國家無法回避的,而在今天生產力水平極大地提高之后,任何一個國家又都無法回避關注民生的問題。當然,在二者的關系中,有一個問題必須厘清,從總的趨勢來看,經濟增長與民生建設的關系取向是越來越看重民生問題,但是,經濟發展的程度或者生產力的水平又難以獲得一個準確的信息以對民生建設提出具體的要求,因此,不同的國家在處理經濟增長與民生建設的關系時,必須把握自己的尺度,這對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個挑戰。如我們過去非常羨慕的西方發達國家的福利和民生建設,現在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因此,我們不僅要明晰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民生問題,而且還要明晰二者的關系取向,更為重要的是如何處理好二者的關系。
三、經濟增長與民生建設關系理性處理的原則把握
經濟增長與民生建設之間已經形成互為膠著的關系,任何只注重一方面的選擇都難以成就現代經濟。就各國經驗來看,處理好這二者的關系并非易事,有的國家過于看重經濟增長,而忽視民生建設,最終經濟增長難以持續,社會秩序混亂,經濟陷入停滯的狀態;而有的國家則形成民生建設的剛性,這種狀況在世界經濟呈現越來越激烈的競爭環境下轉化為經濟增長的負擔,結果經濟增長相對緩慢,難以支撐民生建設的剛性需求,也使國家陷入困境。所以,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可以將二者妥善處理好的國家,特別是在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背景下,任何一個國家想獨自將這一關系處理好,都會面臨許多難題。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無所作為,理性地處理好經濟增長與民生建設的關系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一個挑戰。
首先,要把握好經濟增長與民生建設關系取向的適時轉化。在經濟增長與民生建設關系的取向上,經濟增長通常都是先受到重視的方面,正所謂經濟發展是一切其他方面發展的基礎,尤其是對一個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來說,要實現經濟起飛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因此,全神貫注地發展經濟無疑是一個正確的選擇。但是,當經濟增長實現了起飛,并且進入了一種持續發展的趨勢后,騰出一定的精力關注民生建設就變得非常重要。而這會有一個適時性的問題。一些新型工業化國家的經驗是,在經濟實現高速增長二三十年后,就應該把關注的重點由經濟增長轉向民生建設。當然,這并不是一個普遍的規律,各國根據自己的國情可以有不同的選擇,但有一個原則是必須把握的,就是經濟增長由供給約束轉變為需求約束時,就應該考慮加大民生建設的力度。而經濟增長的供給約束和需求約束的一個重要分界線就是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開始凸顯。
其次,要關注民生建設的剛性特征,把握好經濟增長與民生建設關系取向轉化的程度。經濟增長的趨勢呈現的是一個周期性特征,也就是一個時期經濟增長速度比較快,而另一個時期的經濟增長速度比較慢,因此表現為經濟高漲和經濟蕭條的交替變化。這種變化是因為有一種內在的經濟規律在起作用。但是,民生建設具有一種剛性特征,其變化的趨勢是內容不斷增加,水平不斷提高。造成這一趨勢的原因在于民生建設所受到的是人的需求規律的影響。也就是當人們的需求得到一定滿足之后,如果再想把這種需求調下來是十分困難的,特別是在一種民主的體制下,這種調整變得更為艱難。因此,在處理經濟增長與民生建設關系轉向時,把重點轉向民生建設沒有問題,但是一定要把握一個原則,不能使民生建設取向達到消減經濟活力的程度。也就是說,既要重點關注民生建設,又要使經濟充滿活力。為此,一種競爭格局的維持是十分必要的。
最后,要考慮經濟增長與民生建設關系取向轉化的國際經濟不平衡背景。世界各國發展歷史顯示出嚴重不平衡特征,有的國家發展水平比較高,甚至達到了發達的程度;而有的國家發展水平相對落后,正努力實現趕超的目標。這種不平衡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現實,并且影響著整個世界經濟發展的進程。過去人們普遍認為發達國家高福利化是一種榜樣,但是,隨著新興工業化國家和新型經濟體的崛起,其經濟的競爭力不斷提高,極大地擠壓了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空間,甚至許多發達國家在這種競爭中顯得較為弱勢,因此,其經濟增長步伐放緩,這對其高福利制度構成了嚴峻挑戰。在世界經濟不平衡的背景下如何處理經濟增長與民生建設的關系,也需要確立一個原則,這就是要動態地調整本國的經濟增長與民生建設的關系,推進民生建設是一個不容置疑的目標,但構建一種可以彈性調整的民生建設機制也是不可缺少的。
[1]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58.
[2] KUZNETS.Economic Growth and Inequality[J].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1955,45: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