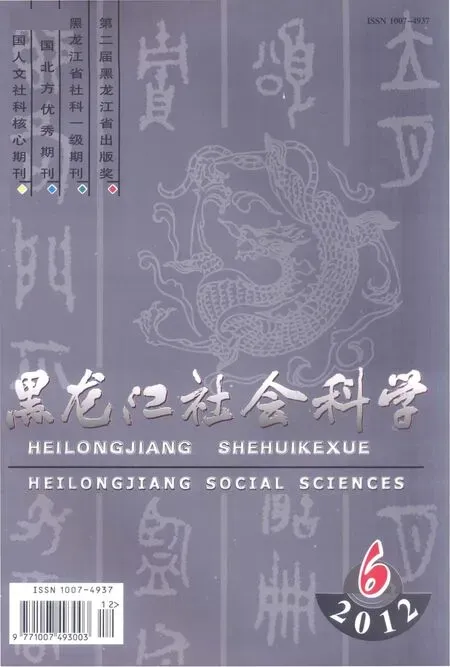從斯徒盧威的民族理念看“偉大的俄羅斯”
(鄭州師范學(xué)院 外語系,鄭州450044)
在俄國歷史發(fā)展和社會變遷的重大轉(zhuǎn)折時期,俄國的良心——知識分子們總會提出各種思想主張、政治理論,為俄國的現(xiàn)代化設(shè)計藍圖。具有歷史學(xué)家、經(jīng)濟學(xué)家、哲學(xué)家、出版家、政治活動家等多重身份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彼·伯·斯徒盧威(1870-1944)在20世紀(jì)初面對俄國社會發(fā)展的各種矛盾,提出“自由的俄羅斯帝國”——“偉大的俄羅斯”的國家理想。作為哲學(xué)家,斯徒盧威在哲學(xué)方面的主要成就并不是表現(xiàn)在對哲學(xué)原理以及宗教哲學(xué)的研究上,而是體現(xiàn)在政治哲學(xué)觀上,體現(xiàn)在他將自己的哲學(xué)觀點應(yīng)用于對民族、國家的歷史、現(xiàn)實及未來發(fā)展的深層思考之上。在斯徒盧威的政治哲學(xué)研究中,國家學(xué)說處于中心位置,“偉大的俄羅斯”的理想是其國家學(xué)說的核心,而民族問題則是其中重要的范疇。
一、斯徒盧威的民族理念
斯徒盧威提出個人和國家之間、“自由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具有深刻的矛盾與沖突,要調(diào)和這一矛盾和沖突,就要致力于將自由主義與愛國主義結(jié)合起來,將“偉大的俄羅斯”作為自己的最高信念和最終歸宿。斯徒盧威強調(diào)國家、民族與民族文化之間存在緊密的聯(lián)系,國家體制應(yīng)該是個人、民族、國家與文化的統(tǒng)一,是國家和具有文化共同性的民族的凝結(jié),是政權(quán)與人民在民族思想上的和解,是個人、民族、國家在民族精神和民族思想基礎(chǔ)上聯(lián)結(jié)成為統(tǒng)一的俄國國家政治整體,是有機的、民族精髓的構(gòu)成。“政治原則是我珍視的,但我對政治形式漠不關(guān)心。國家體制與國家的對外實力、與將民族與國家、祖國統(tǒng)一起來的民族思想相聯(lián)系,體現(xiàn)在國家體制精神中的教育是我呼吁俄國人民接受的思想改造之一。”[1]斯徒盧威認為民族作為柔性的自然現(xiàn)象是不定形的和易變化的,然而又集中表現(xiàn)了創(chuàng)造偉大文化和國家制度的潛在能量。民族精神在具有包羅萬象和多元特性的文化中構(gòu)成了自己的客觀化身,文化是形成強有力的和有意識的民族原則——國家的直接中介,文化是否豐富和深刻決定了它是否有可能使其他的民族和國家服從于自己。斯徒盧威把民族與國家的分歧看成是文化的分歧,國家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精華和能量的核心。“民族具有文化性,共同的文化遺產(chǎn)、共同的文化活動、共同的文化期望是民族的基礎(chǔ),而國家本身是民族形式上的重要活動家,因此國家具有文化力量。……民族的價值通過民族文化的價值來體現(xiàn),每一個大的民族都渴望建立一個國家體系,但是民族的思想與生活總是比國家的思想與生活更為廣泛、豐富和自由。國家的起源具有強制性,民族的起源與國家密切聯(lián)系,同樣具有超理性和神秘主義特點,但是民族的起源更為溫和、內(nèi)在,體現(xiàn)了人類在自由發(fā)展和聯(lián)盟中的精神力量,對人民沒有任何強制性。……民族性不會隨著國家體制的改變而消亡,民族作為文化概念不屬于國家概念的范疇。與民族和民族性相比,國家更易受到外界條件的制約,更缺乏穩(wěn)定性和力量。當(dāng)與民族的起源相結(jié)合時,國家起源具有了最高的神秘性,達到某種一致時,這些具有熱情力量的起源就包圍了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的人。”[2]斯徒盧威強調(diào)近代英國和普魯士的民族凝聚力是國家強大的重要原因。
在斯徒盧威心目中,“偉大的俄羅斯”永遠是第一位的,他堅信俄羅斯的復(fù)興首先應(yīng)該復(fù)興和鞏固民族精神,他把民族精神的復(fù)興同克服俄國知識分子反國家的背叛行為、與對鞏固國家經(jīng)濟實力具有巨大意義的思想相聯(lián)系,這樣的民族主義相信民族的鮮活力量,相信民族的權(quán)利和愿望,這樣的民族主義要增強民族的凝聚力,促進國家的統(tǒng)一,而不是分裂國家。“國家的實力不可能不受到民族思想的限制,不可能存在于民族思想之外。現(xiàn)代俄國的民族精神是在政權(quán)與自覺的、具有首創(chuàng)性的人民之間的和解,這樣的民族精神是要把國家統(tǒng)一起來,而不是分裂國家。國家的實力必然受到民族精神的限制,國家和民族應(yīng)該有機的結(jié)合。”[3]斯徒盧威是俄羅斯國家起源的諾曼說的擁護者,羅斯人在內(nèi)外的共同壓力下聯(lián)合成為民族國家,國家強大的思想成為民族自覺意識的核心,民族精神活躍和存在于國家之中,民族精神存在于每個人的生命之中,引導(dǎo)新老一代人思想的繼承,俄羅斯民族精神和文化就是俄羅斯帝國的精神基礎(chǔ),他堅信:“只有俄國人民擁有了真正的國家性精髓,并且準(zhǔn)備為保護它勇敢地與它的任何敵人作斗爭,只有在鮮活的歷史傳統(tǒng)基礎(chǔ)上和在對于現(xiàn)在及未來一代人都是彌足珍貴的成就的基礎(chǔ)上才能建成偉大的俄羅斯”[3]。
二、非俄羅斯民族的問題
俄國是個多民族國家,國內(nèi)的情況比較復(fù)雜,非俄羅斯族人被指責(zé)為掀起革命的主謀。而斯徒盧威卻認為正相反,“俄國的非俄羅斯人是政權(quán)最后的精神資源,正是他們供養(yǎng)著反動勢力。如果俄國只有單一的俄羅斯民族,那么與人民公開脫離的政權(quán)未必能夠存在。俄國應(yīng)該大膽解決邊界的民族問題,尤其是猶太人和波蘭人問題,要從俄國強盛問題的角度來對待他們”[3]。
猶太民族問題是以取消猶太人居住區(qū),吸引他們參與經(jīng)濟活動的經(jīng)濟(非政治)問題。斯徒盧威指出:“離開了近東我們就不能建立偉大的俄羅斯,在對近東的經(jīng)濟征服中,在黑海地區(qū)的軍事擴張中,忠于俄國國家體制、依戀俄國文化的猶太人是不可替代的先鋒和中間人,是實現(xiàn)‘偉大的俄羅斯’非常有價值的因素。……應(yīng)該給予猶太人全部的公民權(quán)利,使他們起到傳播俄國文化和經(jīng)濟的作用。為了實現(xiàn)這個目標(biāo)唯一的方法就是合法地解放猶太人。實質(zhì)上,在俄國盡管存在反猶呼聲,但沒有一個非俄羅斯民族比猶太人的政治環(huán)境更寬松,他們能夠參與到國家機構(gòu)中,文化上也被俄羅斯人同化。猶太人問題的解決,同‘偉大的俄羅斯’的經(jīng)濟問題具有無法割斷的聯(lián)系:解放猶太人要求俄國經(jīng)濟的恢復(fù),解放猶太人這樣的改革將在國家經(jīng)濟上升的環(huán)境下完成,并與我們的精神沖突減到最小;同時解放猶太人也將促進國家經(jīng)濟實力的提高。”[3]56
俄國是波蘭唯一的市場,波蘭王國在經(jīng)濟上對俄國的依賴遠甚于俄國對它的依賴,使波蘭王國作為俄國的附屬國沒有什么強制的經(jīng)濟動機,而是個純粹的政治問題。斯徒盧威認為“俄國應(yīng)該在波蘭執(zhí)行‘聰明’的政策。在波蘭王國的俄羅斯人只是官員和軍隊,在波蘭王國的領(lǐng)土上,俄羅斯人和波蘭人之間不應(yīng)該有文化的、民族的斗爭。俄國若要使波蘭依附帝國,應(yīng)該令波蘭人民滿意于俄國對波蘭人的待遇,珍視和俄國的聯(lián)系,從精神上依附俄國……這樣一來,俄國就可以利用波蘭在經(jīng)濟上對俄國的依賴,政治上對帝國的依附,使其成為俄羅斯人與奧匈的斯拉夫人聯(lián)合起來的前哨,通過它加強我們同斯拉夫人的自然聯(lián)系,其中包括西方的。……這樣的波蘭政策很大程度上會提高俄國在斯拉夫世界的威信,在經(jīng)濟上俄國、奧匈甚至?xí)墙鼥|的對手,但是這種競爭將由于兩國道義、政治上的一致而變得緩和。當(dāng)然,一切健全的國家都希望強大起來,如果俄國衰弱了,奧匈的斯拉夫性也不能保證我們避免她的入侵,正如1866年奧地利具有的日耳曼文化因素和政治上的優(yōu)勢不能拯救她免于普魯士的毀滅一樣。如果附屬于俄國的波蘭和奧匈的波蘭人有緊密的精神文化上的聯(lián)系,并像過去一樣成為人民不滿的發(fā)源地,如果俄國不能在經(jīng)濟、文化上鞏固在黑海地區(qū)的勢力,在將來某個美好的日子在歐洲的西部邊界我們就會有一場不可避免的大災(zāi)難。如果我們不解決自己的波蘭問題,不在自己的國家和管理的區(qū)域?qū)崿F(xiàn)政權(quán)與人民長久、有效的和解,我們就會不可避免地遭到并非來自東部,而是西部的沉重打擊。”[3]57,58國家之間的沖突源于利益沖突和實力對比,弱國會成為強國的獵物,這是歷史規(guī)律,國家之間的協(xié)約關(guān)系也不能避免相互的沖突。如果俄國的國家實力繼續(xù)削弱,強國終有一天會以任何借口入侵。國家的內(nèi)部政策應(yīng)該避免俄國的國家利益、國家實力和國家尊嚴(yán)受到損害,應(yīng)該爭取消除同奧匈、德國戰(zhàn)爭的可能性,協(xié)調(diào)好俄波關(guān)系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有效途徑。斯徒盧威預(yù)見“如果由于我們內(nèi)部政策的反動性而導(dǎo)致與波蘭的關(guān)系出現(xiàn)問題,當(dāng)我們沒有實行我們偉大的俄羅斯的自然經(jīng)濟基礎(chǔ)所在的黑海的歷史使命的時候,奧匈深知作為斯拉夫強國正是向我們擴張的時機;如果在國際事務(wù)和內(nèi)部政策中我們被迫成為德國的附庸國,或者是永遠處于其威脅之中,在適當(dāng)?shù)臅r候德國會煽動奧匈來攻擊我們。”[3]60
三、從民族理念看“偉大的俄羅斯”的國家理念
斯徒盧威認為國家政策的制定應(yīng)該以國家民族主義思想為依據(jù),國家民族主義思想不僅是政治層面的,而且是精神道德層面的,是要把所有人民連結(jié)成為一個國家民族的統(tǒng)一體,“國家的知識分子應(yīng)該擁有國家性的精髓,這個國家性精髓如果不在受教育階級中占統(tǒng)治地位,就不可能有強大、自由的國家。‘統(tǒng)治界’應(yīng)該懂得,如果‘偉大的俄羅斯’應(yīng)該從大的動蕩中產(chǎn)生,那么為了實現(xiàn)這些,需要人民自由地、創(chuàng)造性地參與運動。在參加運動的人民中,在那些不是以激進主義,而是以愛國主義精神推動了憲法的誕生的人民中,只是依靠政權(quán)的命令不能達到任何目的”[3]61。
為了實現(xiàn)心目中“偉大的俄羅斯”,斯徒盧威提出要在與斯拉夫民族文化密切聯(lián)系的黑海區(qū)域擴大經(jīng)濟和文化影響,因此社會各界對“偉大的俄羅斯”的理解與關(guān)注多集中于向外擴張的問題。列寧曾經(jīng)批判“偉大的俄羅斯”強調(diào)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問題:“任何自由派資產(chǎn)階級的民族主義,都會在工人中起嚴(yán)重的腐蝕作用,都會使自由的事業(yè)和無產(chǎn)階級斗爭的事業(yè)遭受極大的損失。尤其危險的是,資產(chǎn)階級的(以及資產(chǎn)階級-農(nóng)奴主的)趨向是以“民族文化”的口號作掩護的。黑幫和教權(quán)派以及一切民族的資產(chǎn)者,都在大俄羅斯的、波蘭的、猶太的、烏克蘭的等等民族文化的幌子下,干反動骯臟的勾當(dāng)。……民族文化的口號是資產(chǎn)階級的(而且常常是黑幫-教權(quán)派的)騙局。我們的口號是民主主義的和全世界工人運動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4]
實質(zhì)上,斯徒盧威的“偉大的俄羅斯”的國家理念是國家復(fù)興的綱領(lǐng),是關(guān)于個人、民族、國家、歷史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的思想,國家的自由和強大是“偉大的俄羅斯”的目標(biāo)與核心,是要將自由主義與愛國主義結(jié)合起來,建立一個工業(yè)發(fā)展,資產(chǎn)階級的、歐洲式的文明的法制國家,吸引人民尤其是知識階層參與國家生活,保障各種公民權(quán)利、政治權(quán)利和憲法的實施,實現(xiàn)經(jīng)濟上的強大、政治上的自由,保持民族精神和傳統(tǒng),推動俄國邁入先進的歐洲國家之列。“偉大的俄羅斯”的提出推動了理性的國家建設(shè)和俄羅斯社會發(fā)展前景問題的公開探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政治家和知識階層都加入了斯徒盧威提出的國家發(fā)展道路問題的探討,全社會關(guān)于大戰(zhàn)所引起的俄國命運、俄羅斯民族利益和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問題的激烈論戰(zhàn)表明斯徒盧威提出的問題的迫切性。
“偉大的俄羅斯”作為一種自由主義的國家理念,是在近代俄國現(xiàn)代化過程中產(chǎn)生和發(fā)展起來的思想,具有俄羅斯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意味,具有那個時代所造成的缺陷和弱點,受到了在俄國沒有任何根基的英國帝國主義和德國國家主義的影響,無論在知識界還是在政府當(dāng)局那些追求帝國主義和國家主義政策的團體中這些觀念都是無根基的,是難以被接受的。但是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俄國發(fā)展道路的一種思索,作為推動俄國向現(xiàn)代國家演變的重要力量,具有一定的價值,正如當(dāng)代俄羅斯學(xué)者茹科夫的評價:“斯徒盧威以自己的活動積極促進民族自由主義思想的確立,促進俄國政治力量在20世紀(jì)初關(guān)注保存和發(fā)展俄國國家體制問題,在20世紀(jì)末和新千年大門檻前不忽視其緊迫性。”[5]
[1] Гнатюк О.Л.П.Б.Струве как социальный мыслитель[M].СПб.,1998:231
[2] Струве П.Б.Отрывки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Patriotica.Политика,культура,религия,социализм[M].1997:66-68.
[3] Струве П.Б.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Patriotica.По литика,культура,религия,социализм[M].М.,1997.
[4] 列寧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35.
[5] Жуков В.Н.Предисловие//Patriotica.Политика,культура,религия,социализм[M].19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