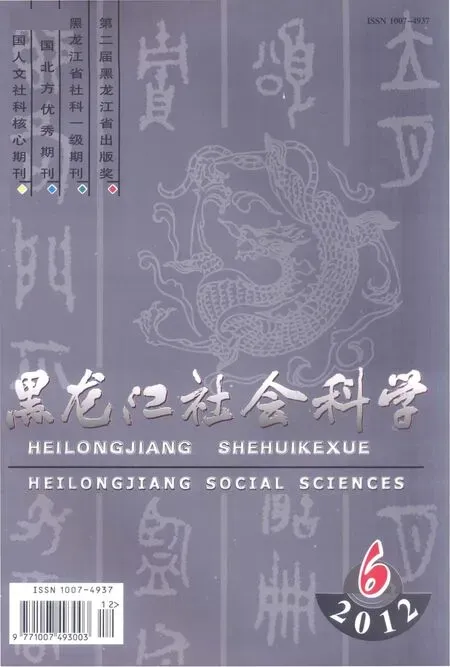中外言論自由權的憲法文本比較及啟示
(黑龍江大學法學院,哈爾濱150080)
一、言論自由的內涵
關于言論自由的含義有多種解釋,如“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是指從享有得以口頭、書面或其他形式獲取和傳遞各種信息、思想的權利,它包括三方面的自由:(1)尋求、接受信息的自由;(2)思想和持有主張的自由;(3)以各種方式傳遞各信息、思想和主張的自由”[1]。有的直接把言論自由歸納為思想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有的認為言論自由就是表達自由:“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或稱‘表達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意指所見所聞所思以某種方式或形式表現于外的自由。這是言論自由的核心內涵。若把這個核心展開,它還包括搜集、獲取、了解各種事實和意見的自由以及傳播某種事實和意見的自由。”[2]或認為“在西方的傳統中,表達(expression)一直被等同于言論(speech)。言論自由是大多數國家憲法中的術語,而表達自由則是司法實踐中和法學理論中的術語”[3]。也有人認為表達自由包括言論自由、學術自由、著作自由、廣電網自由。或者言論自由是表達自由的一種,表達自由是公民通過口頭或書面以及特定行為表達自己意見的自由。除了言論自由,表達自由還包括著作、出版、新聞、集會、結社、游行示威自由等[4]。可見,雖然言論自由本身的含義是比較清晰的,但它與表達自由的關系則比較復雜。筆者比較贊同最后這種觀點,即言論自由是表達自由的一種。因為表達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可以是口頭的,也可以是書面的;可以是言論的,也可以是行為的。言論只是表達的方式之一,因而言論自由隸屬于表達自由。
言論自由既是表達自由的一種,也是基本人權的一種。人權理論經歷了觀念時期和制度時期。觀念時期最著名的理論就是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提出的“天賦人權說”。“天賦人權”源于拉丁文“jus nafural”,應譯為“自然權利”。中國早年譯成“天賦人權”,后一直沿用。它是近代自然法學派的一個重要概念,意指人具有天生的生存、自由、追求幸福和財產的權利。由荷蘭的格勞秀斯、斯賓諾莎,英國的霍布斯、洛克,法國的伏爾泰、狄德羅、盧梭于17~18世紀提出。認為在國家形成之前的自然狀態下,人是自由和平等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與財產是人的固有品質,也是人固有的權利。這種權利受到自然法(人類理性)的指導與規定。“天賦人權”理論經過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1789年法國的《人和公民的權利宣言》(《人權宣言》)變成資產階級的法律原則。法國的《人權宣言》被1791年、1793年憲法列為序言,并把人權具體化為平等、自由、安全、財產、信仰、出版和結社自由等權利。《人權宣言》對世界的影響極其深遠。后來資本主義各國幾乎都仿效法國,將上述權利寫入本國憲法,現代各國憲法幾乎無一例外地載有人權保障的專門章節。在我國,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第四個憲法修正案,將“人權”、“財產權”寫入憲法。其中第33條第3款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而在世界上142部成文憲法中,有124部憲法規定公民有“發表意見的自由”,占到87.3%。可見,世界各國都非常重視對言論自由的保護,并且對言論自由只作盡可能小的限制。誠如康德所言:“言論自由就是人民權利的唯一守護神——但須保持在尊敬與熱愛我們生活于其中的體制這一限制之內。”[5]
二、國外憲法及相關文件中關于言論自由權的規定
綜觀各國憲法,有的既規定公民享有言論自由權,又規定了行使言論自由權的限制或例外情形;有的則只規定了言論自由權,并沒有規定行使該權利的限制或例外情況。但這并不意味著言論自由權是絕對的、不受限制的,限制只是體現在其他法律法規之中罷了。
美國1787《合眾國憲法》的第一條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關于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愿申冤的權利。”這是一條禁止性義務規則,要求國會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得制定意在削減言論自由的法律。但美國締造者們的這一初衷后來被其司法判例所更改。這就是引起很大爭議的對言論自由的限制——明顯且即刻的危險(clear and present danger)原則。這一原則是由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奧利佛·霍姆斯在1919年針對一個有罪判決做出的裁定中提出的。這一原則被其同胞亞歷山大·米克爾約翰所質疑,而根據后者的觀點,應區分情況:根據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的規定,涉及私人利益的言論自由可以限制;而根據第一修正案的規定,涉及公共利益的言論自由則不可限制[6]。
在英國,個人原則上可以不受法律約束地表達任何觀點,但它也是有限制的,如:廣播任何材料須預先得到批準之類的預先限制、“受到尊重他人利益的要求的限制,而他人利益在某種程度上是由誹謗法、藐視法和其他法規加以限制”以及“受到尊重公共利益之要求的限制,而這些公共利益是受禁止淫穢出版法加以限制的”[7]。由此可見,個人發表言論必須是在合法正當的范圍內,不能侵犯他人合法利益和公共利益。
印度憲法第19條第1款規定,一切公民均享有言論和表達自由,但第2款規定:“為維護印度主權完整、國家安全、與外國的友好關系、公共秩序、禮儀道德,或由于涉及藐視法庭、誹謗或煽動犯罪等問題而對上述第1款(一)項施加合理限制,也不妨礙國家為此制定法律施加此類限制。”也同樣對言論自由權的行使進行了限制。
法國1789年《人權宣言》第10條規定:“意見的發表只要不擾亂法律所規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見、甚至信教的意見而遭受干涉。”第11條規定:“自由傳達思想和意見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一;因此,各個公民都有言論、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規定的情況下,應對濫用此項自由負擔責任。”據此,言論自由權不得被濫用。
聯邦德國《基本法》第5條關于“言論自由”的規定:“(1)人人享有以語言、文字和圖畫自由發表、傳播其言論的權利并無阻礙地以通常途徑了解信息權利。保障新聞出版自由和廣播、電視、電影的報道自由。對此不得進行內容審查。(2)一般法律和有關青少年保護及個人名譽權的法律性規定對上述權利予以限制。(3)藝術、科學、研究和教學自由進行。教學自由不得違反憲法。”也對言論自由進行了限制。
巴西憲法第5條第9款規定:“除每個人依照法律規定對其在娛樂和公開表演中所犯的越軌行為負責外,思想、政治或哲學見解可以自由表達,以及提供信息不受檢查。通訊權利受到保護,出版書刊、報紙和期刊無須當局許可。戰爭、擾亂秩序的宣傳或宗教、種族或階級偏見的宣傳,以及與道德及良好習俗背道而馳的出版物和放肆行為都將是不可容忍的。”該條以列舉的方式明確規定了幾種被法律所禁止的言論行為。
新加坡憲法第四部分第14條第1款規定:每個新加坡公民都有言論和表達自由的權利,沒有直接規定限制性內容。
在上述各國憲法中,對言論自由權的規定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有的表現為授權性規則,有的表現為義務性規則,有的則二者皆有。
1948年12月10日,第三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這是第一個關于人權和基本自由的非強制性的世界宣言。其中第19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與此相一致,1966年通過、1976年生效的強制性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第19條也規定:“一、人人有權持有主張,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論國界,也不論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采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三、本條第二款所規定的權利的行使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這些限制只應由法律規定并為下列條件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權利或名譽;(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道德。”此外,《歐洲人權公約》(1950年)、《德黑蘭宣言》(1968年)、《美洲人權公約》(1969年)、《非洲人權和民族權憲章》(1981年)和《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1993年)等區域性人權宣言和公約都對言論自由作出了相應規定。
三、中國憲法中關于言論自由權的規定
言論自由權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政治權利,由作為國家根本法的憲法予以規定是理所當然的,我國也不例外。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現在,中國先后頒布了四部憲法,其中都有關于公民言論自由權的規定,這充分表明中國對言論自由權一直以來都非常重視。
新中國于1954年制定了第一部憲法,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部真正反映人民利益和意愿、肯定人民主人翁地位的憲法,其中第17條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必須依靠人民群眾,經常保持同群眾的密切聯系,傾聽群眾的意見,接受群眾的監督。”第8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國家供給必需的物質上的便利,以保證公民享受這些自由。”1975年憲法第28條是這樣規定的:“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罷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1978年憲法第45條規定:“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罷工的自由,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我國現行憲法——1982年憲法第3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以上四部憲法對于言論自由權的規定,相比較而言,1982年憲法較為言簡意賅。1978年憲法的規定因與“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關聯而略顯偏激,具有鮮明的時代烙印。1975年憲法則是把政治權利與社會權利放在同一條里規定,顯得擁擠而混亂,難以突出重點,甚而有輕忽權利的味道。1954年憲法相對來說更現實一些,它不僅把群眾路線寫入其中,而且規定由國家為言論自由提供物質保障,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但總體而言,我國憲法中對言論自由權的規定都顯得過于簡單,在四部憲法中都是授權性規則,沒有限制性規定,亦缺乏相應的權利保障條款。
無論是中國憲法,還是外國憲法,都毫無例外地賦予公民言論自由權。不同的是,有的憲法對言論自由進行了直接、明確的限制,有的沒有直接的限制性規定。與國外憲法規定相比,我國上述四部憲法中都規定了言論自由權,但都沒有對此項權利進行直接的限制,規定得比較簡單,都體現為授權性規則。現行1982年憲法的規定尤為簡單,幾乎所有的(除選舉權)政治權利被并列規定為一條,除此而外,再無其他規定。
作為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應該充分保障公民的各項權利,對權利做出盡可能詳盡的規定。不但應規定公民享有什么樣的權利,更應該規定在多大范圍內、如何享有權利以及侵犯權利的法律后果。因此,中國憲法可以參照法國、德國、印度等國憲法中關于此項權利的規定,對限制性內容作出具體的規定,以明了言論自由的界限。只有如此,才能更有效地約束公權力,防范其對公民私權利的侵犯。當然,從法制體系整體角度考慮,也可以作出這樣的推理:按照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則,除刑法中與言論相關的內容,如第243條誣告陷害罪,第246條侮辱誹謗罪,第249條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罪,第250條在出版物中刊載歧視、侮辱少數民族罪,第278條煽動群眾暴力抗拒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實施罪,第293條破壞社會秩序罪和第295條傳授犯罪方法罪等規定之外,公民言論自由權的行使應該是非常自由的。筆者認為,對言論自由權的行使可以進行限制,但只能在必要的情況下,由法律作出明確規定,且須經正當程序依法進行。
[1] 趙文廣.論言論自由權的界定與保障[EB/OL].(2012-02-08)[2012-05-11].file:///D:/My%20Documents/自由/9-論言論自由權的界定與保障.htm.
[2] 侯健.言論自由及其限度[EB/OL].(2011-12-14)[2012-04-23].http://www.gongfa.com/yanlunziyoujixianduhoujian.htm.
[3] 沈瑋瑋.論象征性言論的限制與保護——以美國法例[J].環球法律評論,2009,(1):38.
[4] 韋洪鳳.言論自由的法律界定[J].法制與社會,2009,(2):179.
[5] [德]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198.
[6] [美]亞歷山大·米克爾約翰.表達自由的法律限度[M].侯健,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3.
[7] 牛津法律大辭典[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