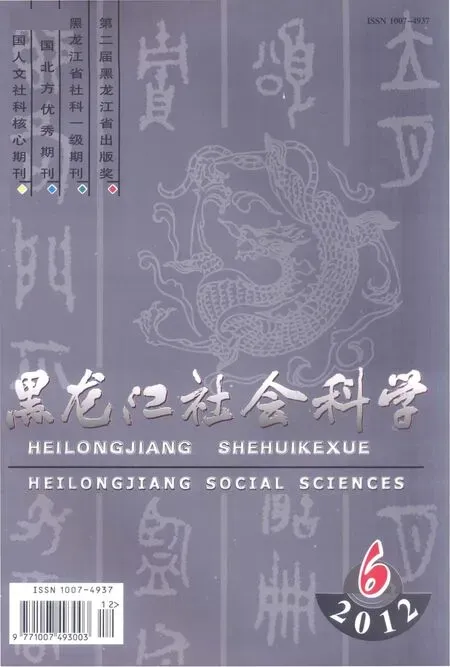學術期刊文后參考文獻著錄規則探究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黑龍江社會科學》編輯部,哈爾濱150001)
為了出版《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整合匯集全國的學術期刊資源,方便廣大讀者和出版工作者使用,并與國際出版界和學術界接軌,《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編輯委員會于1999年頒發了《〈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檢索與評價數據規范(試行)》,其后幾經修訂又于2005年頒發了《〈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檢索與評價數據規范》(以下簡稱《規范》)予以正式實施。《規范》的實施稿比試行稿有很大改進和完善,值得肯定。但仍有不少不盡如人意和不方便編輯工作之處,現僅就文后參考文獻的著錄規則發表筆者的意見。
一、存在的問題
國家標準GB/T7714-2005指出,文后參考文獻bibliographic references“為撰寫或編輯論文和著作而引用的有關文獻信息資源”;《規范》也指出,“參考文獻是對期刊論文進行統計和分析的主要信息源之一”。再從保護著作權來說,在參考文獻著錄中列出所參考的著作人的作品,也體現了參考者和引用人對他人勞動的尊重和肯定。可見,參考文獻雖然是一篇文章的附屬品,其地位和意義卻十分重要。但在編輯和寫作實踐中,筆者發現尚有下列問題。
1.未對參考文獻著錄作出“必須”或“可選”的明確規定,從而可能引發問題。撰寫論文是否參考了他人著作,本應依據實際需要而定,既不能參考了他人著作不加以說明,又不能為參考而參考,或故意為“顯示”什么而參考。所以應作為必備要件。但具體到某作者某論文時,應從實際出發,有則著錄,無則缺項。《規范》對此未作明確說明,可能會使一些論文作者為寫參考而寫參考;也可能使有些使用了他人著作的作者感受不到應予標出參考文獻的必要性和責任。
2.定名“參考文獻”,似有不妥。一是言過其實。據《辭海》“文獻”條云:文獻“原指典籍與宿賢”,“今專指具有歷史價值的圖書文物資料。如:歷史文獻。亦指與某一學科有關的重要圖書資料。如:醫學文獻。”當今更把在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產生過重大作用、具有重大意義的文件、決定、決議、報告通稱文獻,如“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重要文獻匯編”等。但遍覽今之文后參考文獻,雖有分量重、質量高、價值大的文獻,但更多的是一般性的資料,實在稱不得“文獻”。什么都是“文獻”,“文獻”太寬泛、太濫用了。二是覆蓋面窄。過去所謂“文獻”,當然都是紙質的;如今隨著科技的發展,文獻的載體形式增加不少,像錄音、圖像、網絡信息等,文獻就覆蓋不住它們了。若以“錄音文獻”、“圖像文獻”、“網絡文獻”稱之,人們恐一時難以接受;現以“電子文獻”稱之,有些恐又難以包容[1]。
3.對參考文獻未作質量與數量的規定,導致不少文章的文后參考文獻著錄水平和質量參差不齊。有的文章三四千字,參考文獻引了五六七八個;有的正式或非正式引了一句話甚至半句話,也把出處放在參考文獻中;有的所引著作很一般化,竟也置于冠以“文獻”的文后參考文獻中;有的參考文獻,其實就是注釋;有的標明引用著作的頁碼,似乎是方便查找對照,其實不過說明其是在“尋章摘句抄語錄”。撰寫文章參考他人著作或摘抄幾句話是可以的,但重在在他人觀點、方法的啟發下,進行自己的再創新、再發揚、再證實,而不宜以尋章摘句作為自己博學、尋證、傍權威甚至“掉書袋”的工具。所以,有人認為他們很看重參考文獻參考了什么著作;也有不少人很不看重參考文獻,認為這只不過是一種要求必走的“過場”和形式,所提供的信息量不多且價值不高[2]。
4.對出版信息處理不一致。文后參考文獻中著錄的作品,是第幾集(卷、輯)、第幾版,收錄的作品從何年至何年,《規范》和GB/T7714-2005給我們示范的是應置于參考文獻類型之前(如:[4]辛希孟.信息技術與信息服務國際研討會論文集:A集[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而對有的出版信息則放在其后邊(如:[2]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M].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同一性質的出版(版本)信息,所放位置不同,人們不明白。
5.對著作主要責任者所負責任及著作的分量、價值無法判斷。作品(尤其圖書)有專著、編著、匯編、編寫、編選、編注等形式,著作人亦有著者、主編、編者、編選者、執筆人等之分。如今的文后參考文獻,通通以“姓名+.”來表示著作主要責任人,既搞不清責任人的責任,又看不出著作的分量和學術成就,降低了參考文獻的價值。
6.對年代處理欠規范。一如“g.古籍”一節中,所舉中文文獻著錄格式的兩個范例:“[9]沈括.夢溪筆談[O].元大德九年茶陵刊本.北京圖書館珍藏.”與“[20]楊炯.楊盈川集[O].民國 8年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刊刻本.”,“元大德九年”與“民國8年”所表年代按對歷史紀年的統一要求,均應使用漢字數字大寫,但這里一用漢字,一用阿拉伯數字。二如“14.4.1中文文獻”與“i析出文獻”一節所舉范例:“公安部交管局.49~99五十年交通事故統計資料匯編[G].北京:群眾出版社,2000.”(例[24]與[8]基本相同),“49~99”應為1949-1999。即使原著確實如此使用,它系流行的“’49~’99”的變異,也不應照此搬來。因為我們這里一邊講“規范”,另一邊卻以不規范的東西為例,豈不自相矛盾?
7.標點符號使用,與漢語漢字表達傳統及規范不符。這個問題原本就突出,但施行稿與試行稿相比,并沒有本質性的改進及完善。
(1)原來對著作名稱均加“《》”,這樣可以醒目地提示讀者這是一本書或一篇論文,現在期刊的內文仍是這么做的。但《規范》卻在作者后、著作前的中間加“.”表示,不僅創設了標點符號的另一種使用方法,而且還與內文的用法不一致。更令人不解的是,在著作中涉及其他著作的情況下,依舊使用“《》”,同一范例中,有的用“《》”,有的不用,雖然可知是無奈之舉,但不能以理服人。
(2)數位作者的署名。過去,在大標題下署名時,數位作者相互之間一般以空格表示;如今《規范》要求,在大標題下及參考文獻中均以“,”分隔。但在內文有數人姓名出現時,則仍以“、”分隔。這種不相一致的處理方式也讓人覺得對標點符號的使用標準另搞一套。
(3)對外國人的中譯名。GB/T7714-2005標準范例[2]和8.5.1示例[3]中,“P.S.昂溫”在參考文獻中應用“昂溫PS”標示,這又與內文的標示方法不同。可以看到:“.”在參考文獻中有時不用,有時用于《史記·項羽本紀》情況下,有時又用于作者、譯者后下角;但均用于各參考文獻條目之后表示敘述完畢,起到“。”的作用。同是一個實心小黑點,豈可多功能、多用途?
二、對策與建議
由上可見,文后參考文獻著錄規則還存在不少問題和不足,甚至整個《規則》也是如此。對于《規則》的其他問題筆者已在另文中論及,這里主要就文后參考文獻著錄規則方面的上述不足,再提出若干不成熟的意見。
1.對“參考文獻”的命名再作商討,應代之以更適當的名稱。如上所述,鑒于“文獻”一詞在漢語里既有的、特定的含義,而現在的不少參考文獻名實不符,應尋求更貼切、更恰當的詞匯使用,如“參考資訊”、“參考資料”、“參考著作”等。這種詞匯本身比較中性,既可包括紙質的參考著作,亦可包括電子資訊;既可稱呼質高價重的參考著作,亦可指稱廣大的一般性的參考材料。
2.對參考文獻的質量與數量提出要求(或提出建議性意見)。應向文章作者和讀者傳達這樣的思想:首先,標注參考文獻,表示對著作權的尊重和保護;其次,提倡和鼓勵創新精神,用參考文獻多少與文章的創新性無直接和必然關系;再次,擯棄為引用而引用、為顯示權威性而引用、為顯示涉獵廣博而引用等思想。總之,提倡根據需要而引用,為了啟發自己的思路和創新精神而引用,把重點放在為了創新之上。另外,也要對數量適當限制(或建議),三五千字的文章一般二三個就可以了,五千至萬字之間四五個即可。要本著盡量少、少而精、實事求是的尺度進行引用;確實沒有參考和引用的,也不必硬湊數;未列參考文獻者,不能當“缺項”對待,也不證明有別的什么問題。
3.對出版信息應作規定,使之處理一致。鑒于目前《規范》的現狀及各期刊使用出版信息的情況,為方便編輯工作,宜統一放置于文獻類型之前。也就是說,在著作人的著作之后,接著列舉出卷(集、輯)數、從何年至何年、何種版本等。至于是使用“()”標注或依目前在著作后的“:”之后列出,可視哪種方式方便檢索而定。
4.還是顯示出著作人的責任、分工、勞動量以及著作的價值性為好。各個著作人在其著作中的責任、分工、勞動量是不同的,有的是主編,有的是副主編,有的是獨著撰稿者;其著作也有獨著、合著、合編、編著、編寫等之別。依現有《規范》是看不出、分不清這些的,應予改進。這是對著作人權利的如實反映和尊重,也會使讀者或有意借鑒參考文獻的人心中有個初步的印象與判斷。
5.對年代標注,需規范、應完整。即使原著作使用了諸如“’49~’99”或“49~99”之類的標示方式,亦應在判斷無誤情況下更正為“1949-1999年”。對使用古代王朝年號以及民國年份的,均應以漢字標明,如“元大德九年”、“民國八年”,使之統一起來[3]。
6.關于標點符號。參考文獻中的標點符號運用,與傳統的規定用法相抵觸或不一致,筆者認為:一是可以使之統一起來的,應予統一,如作者后均加“:”,凡著作可均加“《》”;二是即使出于計算機識別檢索需要,作者后的“.”以及其他項后的“.”和表示結束意思做句號使用的“.”,只要與有關語言文字規范部門溝通協商,取得共識,是可以解決的。如在有關語言文字規范中對標點符號的特殊使用加以許可,或由《規范》編委會在今后《規范》中進行說明,都是一種解決途徑。如果不這樣做,繼續聽任語言文字的“小規范”與“大標準”相互不一致現象存在下去,《規范》就有以“子法”違背“母法”之嫌,這是不應該的。
最后,還應指出的是,不僅參考文獻著錄規則,而且整個《規范》都有繁瑣、復雜、難操作的問題。不僅新編輯難以記憶、難以掌握、難以使用,而且過去當了數十年編輯、文字功底相當扎實的人來作今天的規范處理,他們也只能望洋興嘆,成了門外漢。本來,編輯們應把主要工夫下在稿件思想性、學術性及文字的處理和潤色上,技術性處理不會占去很大精力和時間,但是今天不同了,反倒在技術性處理上煞費苦心,可能還會出現問題;編輯案頭的《規范》要比字典、詞典翻得多,真有些主次不分、本末倒置、因小失大了。一個《規范》就有十幾節、幾十條、十多頁,而其中的一部分《文后參考文獻著錄規則》則又以GB/T7714-2005國家標準名義搞了十來節、數十條、十幾頁,何其多、何其繁、何其雜也!為了建立中國期刊數據庫(光盤版),眾多期刊編輯兼任了數字(電子)編輯,眾多紙質期刊都要以數字期刊為準部分地變作數字期刊,這就難為期刊編輯和紙質期刊了。
大道至簡。從簡入繁易,由繁向簡難。能以簡明的語言說明復雜的問題,以簡便的方法解決復雜的問題,這才是高明的,也是大眾歡迎的。如今我們把編輯工作的技術處理搞得這么復雜,困擾著新編輯、難倒了老編輯,難道這是搞《規范》的初衷和目的嗎?《規范》肯定是應該搞的,與國際接軌也是需要的,但使之繁瑣化、復雜化、難以操作總不能是方向和目的。這是搞任何規范、規則都應該明確和把握的規范、規則。希望在今后的修訂和完善工作中能體現這一點,因為這不僅是編輯們的心愿,也是廣大讀者、作者的期盼。
[1] 傅麗英,陳曦,宋栓虎.社科期刊“編排規范”制定與實施中的誤區[J].中國編輯,2003,(5).
[2] 楊大威.對學術期刊編排規范化的思考[J].邊疆經濟與文化,2011,(10).
[3] 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N].人民日報,1951-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