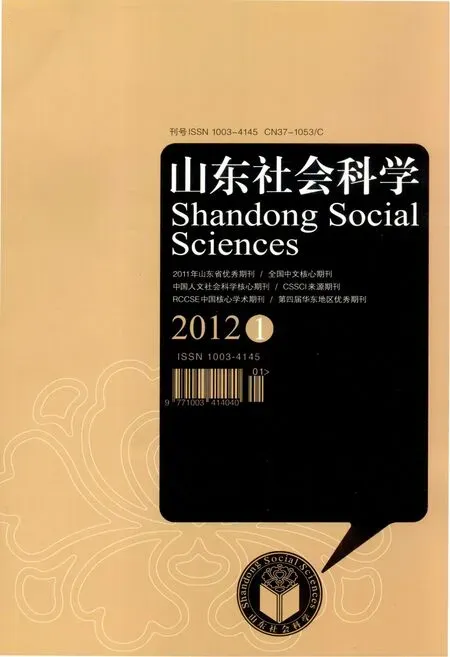自我身份追尋的心路歷程
——探析拉爾夫·艾里森小說《看不見的人》主題思想
喬 艷
(遼寧工程技術(shù)大學(xué)外語系,遼寧阜新 123000)
自我身份追尋的心路歷程
——探析拉爾夫·艾里森小說《看不見的人》主題思想
喬 艷
(遼寧工程技術(shù)大學(xué)外語系,遼寧阜新 123000)
拉爾夫·艾里森的巨作《看不見的人》于1952年出版,講述了一位黑人青年尋找自我身份的故事。為了突出對自我的尋求與發(fā)現(xiàn)這一主題,作者針對分析自我經(jīng)歷和生存社會,提出了主人公追尋自我的過程,也正是他的夢想破滅的過程。
看不見的人;自我身份;追求;主題
拉爾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1914-1994)出生于美國中南部俄克拉荷馬市。他一生中只寫了一部長篇小說《看不見的人》(The Invisible Man),然而就是這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被一致認(rèn)為是美國黑人文學(xué)最優(yōu)秀的作品,評論家稱其為“劃時代的小說,可以說是現(xiàn)代美國黑人生活的史詩”,并使其蜚聲美國乃至世界文壇。小說《看不見的人》以第一人稱自敘的方式來突出“自我”,把從“自我”拓展到整個社會,用黑人的困境有力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從而揭示人的個性和自我本質(zhì)的失落。文章描寫了一個年輕黑人在美國南部和北部遭遇種種不幸。按照正常的社會發(fā)展,這個年齡的青少年正是接受各種知識,在社會中廣受重視的一個團(tuán)體,也是社會發(fā)展的希望所在。然而,本文的主人公雖然處在社會廣泛關(guān)注的年齡段,但他卻孤身在外,形影相吊,飽受痛苦、孤獨(dú)的煎熬。雖然主人公在關(guān)鍵的時刻也能想起祖父的臨終遺言,除此以外他與家人的聯(lián)系少之又少。小說中僅在一處提到他給家人寫了信,這從側(cè)面反映作者對當(dāng)時黑人處境的反思,黑人最大的痛苦應(yīng)當(dāng)是得不到承認(rèn)、無法證明自己的社會地位和存在的價值,表現(xiàn)了西方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不正常的、無理性的關(guān)系,開始不斷追尋自我并思索自己的存在價值。
一、自我身份的迷失
主人公的自我身份迷失,也是自我探索的過程。幾個重要事件的影響,從側(cè)面烘托了主人公對自我身份迷失的困惑。
(一)社會的困惑
為了生活,主人公在所有的希望被毀滅以后,在一家油漆廠找了份攪拌油漆的工作,但很快就由于配錯油漆顏色而遭到黑人工頭猛訓(xùn)。然而,在對于主人公而言,社會的“黑人性”,必將同樣給他帶來災(zāi)難,在他被差譴到工廠地下室后,布羅克韋告誡主人公的那樣:“他們買了所有的這些機(jī)器,可是機(jī)器并不是萬能的;我們才是機(jī)器的機(jī)器”。后來布羅克韋擔(dān)心自己的位置被搶,與主人公進(jìn)行激烈的沖突,當(dāng)主人公與布羅克韋進(jìn)行搏斗時,他試圖扳住鍋爐的閥門,結(jié)果卻因機(jī)器的爆炸而失去知覺,被送進(jìn)了工廠的醫(yī)院。醫(yī)院的醫(yī)生在先進(jìn)的技術(shù)設(shè)備的武裝下,為主人公做了手術(shù),說這樣他就不會受到“動機(jī)的嚴(yán)重沖突,而更妙的是,社會不致由于他的緣故而遭受損失”。其實(shí)這反映了白人的統(tǒng)治對社會的不公,就黑人而言,因?yàn)樗麄儾坏貌幻鎸υ诎兹私y(tǒng)治的工業(yè)社會中,自我身份迷失是一種必然。
(二)自我的困惑
小說把尋找自我貫徹文章的自始至終。在整部小說中,小說的主人公沒有任何的姓氏,在文章中葉沒有任何關(guān)于小說主人公姓名的提示,他后來進(jìn)入兄弟會擁有了姓名,社會所給的一個姓名,對于主人公而言,并不是他本身所具有的。作者在《看不見的人》中,讓主人公無名無姓的寫法,具有深刻的含義。對于主人公而言,在白人的社會中,他的名字不會成為別人關(guān)注的對象,也就是說對于一個不被他人所重視的“無形人”而言,名字對他毫無意義;另外一個方面也反映了作者為探索黑人個性和價值做出不斷的努力,在作者看來,黑人的痛苦不是來自遭受的迫害,而是在社會中的地位,一個被忽視的群體,一個不能被體現(xiàn)價值和作用的群體。作者把這種思索從黑人青年的成長拓展到整個的現(xiàn)實(shí)社會,用以點(diǎn)帶面,點(diǎn)面結(jié)合的方式闡述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黑人和白人的特殊關(guān)系,揭示了當(dāng)時黑人群體個性和自我本質(zhì)的失落。然而小說又不僅僅局限在敘述黑人的問題上,作者通過黑人所經(jīng)歷的社會,描寫了西方現(xiàn)代人自我價值的問題。
二、追尋真實(shí)的自我
小說中主人公的祖父是一個前黑奴,平時就遵從謙恭和順從,在黑人中受人尊敬,也深受白人賞識。主人公受到祖父的影響,在開始的階段通過謙恭和順從得到了所謂的“成功”,但是自從被學(xué)校開除以后,主人公的命運(yùn)便變得多難和起伏,來到紐約,沒有工作,看清了黑人學(xué)校校長的虛偽,也感到了被社會所忽視,在爆炸發(fā)生,被電擊治療后,開始促進(jìn)主人公對于自我身份的思索。從主人公吃紅薯的經(jīng)歷,他“不禁突然產(chǎn)生了一種強(qiáng)烈的自由的感覺——我再也不用擔(dān)心誰會看見我,也用不著考慮怎樣做才得體”,進(jìn)一步表明了他對黑人歷史的重新確認(rèn),這也使主人公朝著追尋真實(shí)的自我邁出重要一步,使得主人公依稀開始思考自我。
加入“兄弟會”后,主人公的潛在能力得到了一定的發(fā)揮。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并深得黑人群眾的支持與擁護(hù)。他嚴(yán)格執(zhí)行紀(jì)律和制度,并不斷為之努力。從表面上來看,主人公似乎此時已找回“真正的自我”,他也希望通過兄弟會實(shí)現(xiàn)自己的理想,證明自己的價值。然而,他出色的工作受到了來自兄弟會內(nèi)部成員的反對,這讓主人公內(nèi)心感到失望,不斷懷疑自身存在。特別是在兄弟會的眼中,主人公充其量是一個用來說話的工具和兄弟會用來實(shí)現(xiàn)政治路線的一個棋子。在一次躲避追殺時,主人公躲進(jìn)一家雜貨鋪,進(jìn)行了喬裝打扮,結(jié)果被人很多人誤認(rèn),這使主人公開始深思找回自我的道路。
由于兄弟會中的黑人成員托德·克利夫頓在街上賣桑博娃娃時被白人警察無端殺害,導(dǎo)致了哈雷姆大混亂,主人公成功地發(fā)動和組織了大批黑人舉行為其送葬,然而,卻被冠以莫須有的罪名,主人公慌亂逃跑,企圖躲避拉斯的追殺,慌亂中,主人公最后掉進(jìn)了煤窯,在黑暗中他用摸索到的一只火柴盒里僅有的三根火柴,主人公燒掉了公文包和其中白人賦予他的各種身份材料。在地下室里,原本的慌亂變得寧靜,主人公變成了“無形人”,開始回憶和反思了自己的生活。他意識到自己一直在追求的是白人強(qiáng)加給黑人的生活價值。主人公通過偷接了電線,點(diǎn)亮燈泡,使地下室變得無比明亮。來表達(dá)“光證實(shí)了我的存在,賦予我形體”。充分體會自身身份的存在。在尾聲中,主人公這樣反思自己的過去:“我的問題正是在于我一直試圖走別人的路,卻從不想走自己的路。同樣,別人這樣稱呼我,后來又那樣稱呼我,卻沒有人認(rèn)真想聽一聽我怎樣稱呼自己。因此,雖然多年來我很愿意把別人的意見當(dāng)作自己的意見,現(xiàn)在我終于造反了。我是一個看不見的人。我走了漫長的道路以后又折回來了,我原先曾夢寐以求,想爬到社會的某一階梯,此刻又反彈到了原處。”在結(jié)尾處,主人公決定等待時機(jī),回到社會上扮演自己應(yīng)承擔(dān)的重要角色。
三、探索自我的人生價值和生存意義
小說主人公一直在遵守黑人家庭傳統(tǒng)的教誨謙恭、順從白人,以追求白人品質(zhì)為榮。而面臨的社會現(xiàn)實(shí),不斷啟迪主人公,必須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拋棄虛幻思想和盲目崇拜,要正視自己,尊重自己,才能真正找到自我。探索《看不見的人》主人公的自我追尋,感受主人公的心路歷程,從滿懷希望的走向大學(xué),在大學(xué)中刻苦奮斗,而后非常委屈又滿懷希望地離開大學(xué),走向更加多難多災(zāi)的現(xiàn)實(shí)生活,希望——奮斗——挫折,幾經(jīng)磨難,主人公的真實(shí)身份被他人強(qiáng)加的“身份”所遮蓋和遏制,在一次次的現(xiàn)實(shí)面前,開始了對自己的生存價值和地位有了深刻的認(rèn)識,意識到了社會的無情與異化。在經(jīng)過煉獄般的洗禮之后,主人公對現(xiàn)實(shí)世界中的自私、暴力和欺騙有了更加清醒和深刻的認(rèn)識,內(nèi)心開始激蕩,意識到自己在社會中始終處于“無形人”的地位,開始進(jìn)入內(nèi)心的另一個層次,逐步探索自我的人生價值和生存意義。這可以通過在小說結(jié)束前,作家埃里森并沒有讓他的主人公一味地消沉下去。相反,小說所暗示的是人只有遵從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發(fā)揚(yáng)黑人積極向上的價值觀,建立正確的道德秩序,才能在白人的主流社會中找到自我和達(dá)到自我價值的實(shí)現(xiàn),這在文章的結(jié)尾處恰恰得到體現(xiàn):“我正在褪去舊皮,準(zhǔn)備把它留在洞里。我就要出來了,沒有舊皮,別人還是看不見我,不過總算是在往外走。而且我以為時機(jī)正好。細(xì)想起來,甚至蟄伏也不能太過分了。也許這是我對社會所犯的最嚴(yán)重的過失:我蟄伏得太久了,因?yàn)檎f不定即使一個看不見的人也可以在社會上扮演重要角色。”
自我的人生價值和生存意義不僅僅在歷史上的美國黑人和白人之間有著普遍的現(xiàn)象,就是對現(xiàn)代人而言,探索自我人生價值和生存意義,可以啟迪我們要正視自我,張揚(yáng)個性,完善人格。探索《看不見的人》自我心路追尋歷程,感受主人公內(nèi)心世界質(zhì)變的過程,才能促進(jìn)我們清醒地認(rèn)識到自己的處境,發(fā)現(xiàn)自我的存在,保持中華民族在全球化的潮流中民族獨(dú)立性,弘揚(yáng)民族文化傳統(tǒng),借鑒西方文化中有益的東西,才能更好的發(fā)揮自身作用,承擔(dān)更多的社會責(zé)任,為社會做出應(yīng)有的貢獻(xiàn)!
[1]陳曉菊:《荒謬的極限處境與自我追尋——<看不見的人>之存在主義解讀》,《寧波大學(xué)學(xué)報(bào)》(人文科學(xué)版)2010年第5期。
[2]ELLISON,R.《看不見的人》,任紹曾譯,外國文學(xué)出版社 1984版。
[3]拉爾夫·愛默生:《自然沉思錄》,博凡譯,上海社會科學(xué)院出版社1993版。
[4]王長榮:《現(xiàn)代美國小說史》,外語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I106.4
A
1003-4145[2012]專輯-0015-02
2012-05-18
喬艷,女,遼寧法庫人,遼寧工程技術(shù)大學(xué)外語系副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yàn)橛⒚牢膶W(xué)。
(責(zé)任編輯:宋緒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