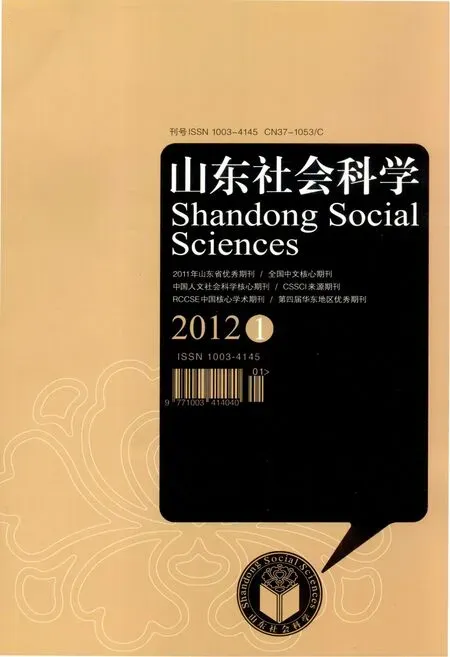理查德·萊特小說《native son》解讀
劉春紅
(漯河醫(yī)學(xué)高等專科學(xué)校,河南漯河 462000)
理查德·萊特小說《native son》解讀
劉春紅
(漯河醫(yī)學(xué)高等專科學(xué)校,河南漯河 462000)
理查德·萊特小說《native son》是美國“抗爭小說”之首創(chuàng),更是黑人文學(xué)代表之作。該作品運用現(xiàn)實主義的寫實之法,表現(xiàn)了美國社會20世紀30年代那種殘酷的種族歧視與階級斗爭還有黑人悲慘的生活狀況,它給人們進一步深入研究美國這時期歷史提供很好的參考資料。
《native son》;種族歧視;黑人文學(xué)
一、前言
1940年,理查德·賴特的《native son》公開發(fā)行,該作品描繪了一位和以前小說截然不同的黑人形象。《native son》不但在美國文壇異軍突起,也給美國社會以很強的震撼:新生代的黑人已不甘心生活在固定的社會模式中,他們寧愿準備為抗爭基本權(quán)利、維護人格尊嚴而死,也不愿意像他們的老一輩人那樣生活在恥辱之中。《native son》開創(chuàng)了美國“抗議小說”的先河,是黑人文學(xué)發(fā)展史的一個新的里程碑;同時,這部小說也使理查德·賴特一躍成名,奠定了他“現(xiàn)代美國黑人小說之父”的地位,并成為其代表作。
《native son》以20世紀30年代的芝加哥為背景,全書分為恐懼、逃跑和命運三個部分,敘述了一個黑人青年別格·托馬斯的一段生活經(jīng)歷。他被白人達爾頓雇傭后不久,失手殺死了這家的女兒瑪麗,充滿恐懼的別格想方設(shè)法逃避罪責甚至不惜嫁禍給共產(chǎn)黨員簡,在被人揭穿后不得不逃跑,最終被8000名白人警察抓住并送上法庭,受到了死刑的判決。這部小說之所以在美國文學(xué)史上的地位重大,不僅是因為它成功塑造了別格這一新黑人形象,而且還由于理查德·賴特依照現(xiàn)實主義的寫作手法,客觀地展示了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種族歧視以及階級壓迫和斗爭的基本狀況。
二、黑白對立
美國歷史中有兩條獨特的發(fā)展線索對理解這部小說意義重大:一個是20世紀上半期的美國黑人從南方向北方城市的大遷移;另一個是1929年到1940年間的大蕭條所帶來的巨大危機。向北方城市的大遷移可以稱得上是非裔美國人歷史的一個關(guān)鍵時期,是繼美國內(nèi)戰(zhàn)和解放黑人宣言之后黑人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它發(fā)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期,由于一戰(zhàn)的爆發(fā)極大地刺激了北部工業(yè)的發(fā)展,北部城市對勞動力需求巨大,因此南部的黑人逐漸逃離出來,向北方云集,但他們只能居住在擁擠破舊的平民區(qū),并不是和白人雜居和聚居。內(nèi)戰(zhàn)后,“三K黨”通過暴力手段迫使南方的許多州把黑人趕出議會和其他政府部門,通過了歧視和隔離黑人的“杰姆·克羅法”,并一直延續(xù)到故事發(fā)生的30年代。雖然南方的奴隸制問題得到了解決,但種族問題依然十分復(fù)雜嚴峻地存在著。
小說中的別格一家就居住在芝加哥的黑人聚集區(qū),又名“黑帶”。白人居住區(qū)和黑人居住區(qū)之間有一條分界線,白人不愿跨過,黑人更不敢逾越,黑人和白人似乎老死不相往來。別格一家人擠在一間破舊的棚屋里,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黑帶”中,還有許多沒有人居住的建筑。原來,白人為了提高租金使用了一大高招:利用供求法則,減少房源供應(yīng)以提高租金,這充分反映了黑人受剝削和被壓迫的事實,體現(xiàn)了黑人貧困的生活。黑人和白人的不同還體現(xiàn)在日常生活方面,面包的價格就是個極好的例證:在“黑帶”區(qū),一塊面包賣5美分,但在隔離地帶的白人居住區(qū),只要4美分。許多黑人沒有工作,食不果腹;少量做生意的機會也只不過是那些白人所不愿意從事的收看黑人尸體的殯儀館事務(wù)。
種族壓迫和隔離造就了黑人和白人在教育、社會經(jīng)歷以及行事方式上的巨大不同。在《native son》這部小說中,黑人被剝奪了教育、就業(yè)、娛樂等權(quán)利,別格及他的伙伴們每天做的事情也就只是抽煙、喝酒、打彈球,玩虛擬中的白人的游戲、想象白人的生活,他們被剝奪了接受正規(guī)教育的權(quán)利。黑人在那個社會里沒有任何可以選擇的機會和權(quán)利,別格去道爾頓家當司機也是走投無路才去的,因為如果他不接受這份工作,他們一家將不再被救濟,他只能按照白人制定的規(guī)則生活下去。他曾想搶劫白人的鋪子,但最后由于害怕而使計劃流產(chǎn)。想干又不敢干的心態(tài)正是美國種族歧視和壓迫的直接結(jié)果。這種壓迫和歧視給黑人行為帶來的另一種影響是恐懼和仇恨、暴力和殘忍。因為潛意識中對白人的恐懼和仇恨迫使別格本能地謀殺了瑪麗,迫使他肢解了她的尸體并在火爐里焚尸滅跡,迫使他把罪行栽贓給美國共產(chǎn)黨,迫使他殺死了自己的女友以免出賣自己。因此,從根本上說,別格殺人犯罪的行為應(yīng)該完全歸咎于美國的種族主義制度和壓迫。小說《native son》在揭示當時美國社會存在的種族歧視方面,毫無疑問地具有相當?shù)牧Χ群蜕疃取?/p>
三、紅與白的斗爭
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處于經(jīng)濟危機的大蕭條時期,廣大的工人、農(nóng)民處境極端痛苦,甚至絕望。據(jù)統(tǒng)計,美國有近四分之一的工人失業(yè),三分之一的人掙扎在生活的邊緣,農(nóng)民債臺高筑,沒有生計。而反觀當時的新興社會主義國家蘇聯(lián)則正呈現(xiàn)一派生機勃勃的繁榮景象。在這種鮮明的對照下,許多美國人對資本主義表示懷疑,轉(zhuǎn)而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chǎn)黨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美國共產(chǎn)黨迅速成為美國最有影響力的組織,吸引了包括黑人在內(nèi)的許多激進的青年作家、工人和農(nóng)民。到了30年代晚期,美國共產(chǎn)黨的人數(shù)從1929年的區(qū)區(qū)7000人躍升為8-10萬人,公眾對共產(chǎn)黨的興趣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國共產(chǎn)黨大量發(fā)展組織和工會,組織群眾廣泛進行階級斗爭,向群眾印發(fā)宣傳手冊和資料,宣講共產(chǎn)主義思想,壯大共產(chǎn)黨隊伍。小說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并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階級斗爭狀況。
值得關(guān)注的是,小說作者本人就是一個受美國共產(chǎn)黨宣傳而被深深吸引加入共產(chǎn)黨的年輕黑人作家。1932年,賴特加入了共產(chǎn)黨。此后他努力地學(xué)習(xí)馬克思主義,直接擔任黨內(nèi)工作,并很快成了一名主要的左翼代言人。隨后的10年是賴特政治生活的一個重要時期,也是他在思想和文學(xué)創(chuàng)作方面漸趨成熟,最終獲得國際聲譽的重要階段。小說中的瑪麗和簡可以說是一對革命伴侶,他們是被共產(chǎn)黨所吸引加入革命隊伍的白人,他們抱著對共產(chǎn)主義的高度熱忱進行組織和宣傳工作。雖然瑪麗出生于一個富裕的資本家家庭,但她同情人民,認為共產(chǎn)黨能幫助他們。共產(chǎn)黨員簡是共產(chǎn)黨先鋒組織勞工保衛(wèi)委員會的執(zhí)行書記,從他主動和別格握手、與別格交談的方式和內(nèi)容可以看出他對共產(chǎn)黨工作十分積極,并不失時機地向別格介紹共產(chǎn)黨,有強烈地把別格這樣的黑人吸引加入共產(chǎn)黨組織的意愿。他還送共產(chǎn)黨宣傳小冊子給別格。“干革命就離不開他們”,簡說,“必須把他們組織起來,他們富于戰(zhàn)斗精神,他們會給黨以生命”。在別格被抓住后,共產(chǎn)黨律師麥克斯主動為他在法庭上進行辯護,不僅僅是因為共產(chǎn)黨被牽扯與案件有聯(lián)系,更多的是因為他想利用一切機會擴大共產(chǎn)黨的影響,反擊白人的階級統(tǒng)治以聯(lián)合其他的社會階層。小說結(jié)尾雖然是共產(chǎn)黨沒能挽救別格的生命,但卻贏得了別格的心,他接受了麥克斯的階級理論。所有這一切表明,當時的美國共產(chǎn)黨活動比較積極,共產(chǎn)黨組織正在逐漸壯大。
但是,當時在美國占主導(dǎo)地位的是白人種族主義者,他們控制著國家機器,掌握著強大的軍備,從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上對美國共產(chǎn)黨廣泛壓制,對共產(chǎn)黨組織進行殘忍鎮(zhèn)壓,不惜以任何方式消除共產(chǎn)黨在全國的影響力。白人偵探布列頓從心里對共產(chǎn)黨存有偏見,他一直千方百計地想把這樁謀殺案歸咎于共產(chǎn)黨以找到借口鏟除共產(chǎn)黨組織,并以別格殺人之事作為借口逮捕數(shù)以百計的共產(chǎn)黨人,襲擊工會辦事處和工人組織。檢查官勃克利先生在談到共產(chǎn)黨為別格辯護時說:“那一幫子人你還能指望什么別的?我贊成把他們徹底消滅掉。我深信,你要是兜底兒把這個國家里的共黨的活動查一下,就會把許多未破的犯罪活動的根子挖出來。”這充分體現(xiàn)了資產(chǎn)階級對共產(chǎn)黨的偏見和要鏟除他們的決心。
另一方面,《native son》這部小說也反映了美國共產(chǎn)黨建黨初期的某些局限。美國共產(chǎn)黨成立于1919年,發(fā)展歷程比較短暫,機制也不健全,沒有充分發(fā)動人民群眾,也沒有自己的武裝力量。以白人為核心的黨組織也不能夠充分了解和滿足黑人的心理和實際需要。作為共產(chǎn)黨員的瑪麗沒有去過黑人貧民窟,根本不了解黑人的基本生活狀況,還以為黑人和白人過的是同樣的生活;雖然瑪麗、簡以及麥克斯希望和別格做朋友,成為階級弟兄,但他們從骨子里又認為黑人和白人是不平等的,常常使用諸如“你們民族”和“你們黑人”等帶有民族偏見的稱呼和語言。此外,賴特在小說中對美國共產(chǎn)黨的人道主義和改良主義也進行了描述,并表示了懷疑。美國共產(chǎn)黨寄希望于白人統(tǒng)治階級改善社會狀況、緩和階級和種族矛盾,根本沒有把武裝奪取資產(chǎn)階級政權(quán)作為奮斗目標:共產(chǎn)黨員麥克斯只是告誡白人要抓住機會創(chuàng)造一個公平民主的社會;麥克斯從始至終都認為別格殺人是錯誤的,那不是應(yīng)該的行事方式。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美國共產(chǎn)黨奉行的是非暴力抗爭,而這也是賴特1944年脫離美國共產(chǎn)黨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結(jié)語
賴特出生于黑人家庭,自幼過著艱難、曲折的生活,受到白人的歧視和壓迫,從小在充滿敵意的環(huán)境中長大,深感自己是社會的“棄兒”,因此對周圍的白人世界有一種又恨又怕的反常心理。《native son》從某種意義上說,客觀地反映了作者本身對當時美國社會的看法。正如他在作品中所寫的那樣,把別格的性格乘1200萬,就得出黑人民族的心理。同時,作品也隱含了作者的階級觀點和立場,并試圖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賴特的這部小說成功地把當時社會的種族歧視和階級壓迫客觀而又尖刻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不失為一部優(yōu)秀的抗議小說,也是研究美國歷史這段時期的寶貴資料。
[1]李鴻雁:《理查德·賴特的困惑》,《湘潭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05年第3期。
[2]理查德·賴特,施咸榮譯:《土生子》,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
[3]劉緒貽、李存訓(xùn):《美國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毛信德:《美國小說史綱》,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I106.4
A
1003-4145[2012]專輯-0019-02
(責任編輯:宋緒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