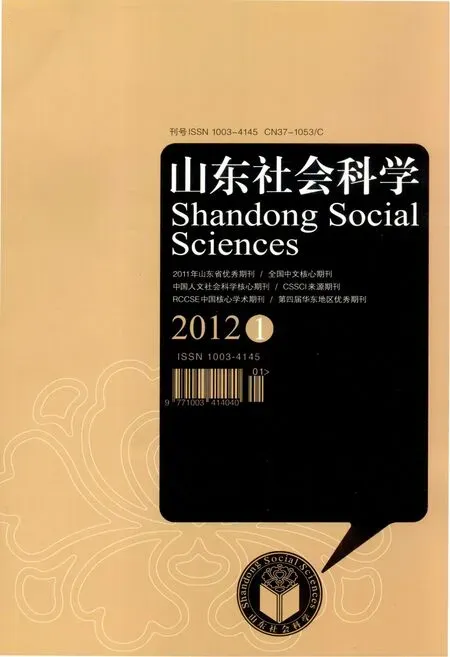韋伯的“理性化”在麥當勞化語境的闡釋
盧曉琳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北京 100875)
韋伯的“理性化”在麥當勞化語境的闡釋
盧曉琳
(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北京 100875)
在現代性語境中,韋伯展開了對“理性”和“理性化”的討論,他認為現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問題都來源于理性與非理性的緊張和對立,導致現代社會陷入無法自拔的困境,人淪為非人格化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麥當勞和麥當勞化將韋伯的理性與非理性帶入后工業時代的生產和消費過程,更加深刻地闡釋了韋伯的理性化理論。高效性、可計量性、可預測性和可控制性既是麥當勞化高度理性的表現,也是其非理性的重要因素。
韋伯;理性;麥當勞化;闡釋
一、韋伯的“理性化”
“理性”自啟蒙運動后作為現代性的內核,承載了現代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博愛等價值觀念,學術界對于“理性”的關注不曾停息,從馬克思的“異化”到韋伯的“理性化”再至哈貝馬斯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都是對現代社會經歷的理性化進程的自覺體察。韋伯作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社會學家之一,其論著涉及的范圍從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到統治類型、理性化和合理性等等,如此豐富的學術體系,對其研究的中心主題的確定就尤為重要,“大多數學者認為理性和理性化是貫穿韋伯學術研究及其作品的主題。”①韋伯創造性地將“理性”及“理性化”置于現代性的語境,描述現代西方世界是如何成功地變得更加理性,并且分析為什么世界其他地區未能首先實現理性化。
隨著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人類的物質生產能力飛速提高,但與此相伴的卻是人精神世界意義和價值的逐步淪落和喪失。在這種背景下,韋伯形成了他的現代性思想,“我們的時代,是一個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將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時代。”②在韋伯對現代性的前景的預測中,理性將會快速主導更多的社會部門,全社會的人都位于一系列理性架構中。基于對現代性的理解,韋伯最初在法律社會學領域關注理性,他將基于形式化法律的理性化稱之為“合理性”,即“合乎理性”。“理性”及“理性化”逐漸突破法律領域的局限,被廣泛用于宗教、經濟、組織、政治、藝術等領域。“宗教的發展過程是一個從非理性向理性宗教的進化過程。所謂非理性的宗教是充斥著大量神秘的、巫術的、情緒的、傳統的力量,總之是不可計算的,不能由人控制的因素在起作用的宗教。”③至于組織制度層面的合理性,官僚體制集中地體現出理性化的特點。“它的優越性,其主要來源是技術知識的作用,由于現代技術和商業方法在貨物生產中的發展,這種技術知識已經變得完全不可或缺。”④也就是說,官僚制行政意味著從根本上以知識進行支配,這是使它變得尤其理性的一個重要特征。
韋伯將“理性”概念應用于社會各方面的分析時,進一步將其區分為形式理性和實質理性。社會行動分為理性行動和非理性行動兩大類,⑤理性行動又分為工具理性行動和價值理性行動兩類。在韋伯那里,形式理性與工具理性基本同義,實質理性與價值理性也基本一致。形式理性行動是以計算和預測后果為條件來實現目的的行動;實質理性行動,則是主觀相信行動具有無需計算衡量的價值,不顧后果和條件如何都要完成的行動。在韋伯看來,現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問題都來源于形式理性與實質理性的緊張和對立。從形式理性出發,實質理性是非理性的,因為后者不經過理性計算的手段達到預期目的,忽視功能和效率;同樣地,從實質理性出發,形式理性是實質非理性的,因為后者只為追求功利的目的所驅使,勢必會漠視人的情感、精神價值的實現。所以,西方近代社會理性化的過程實質上是一個“形式理性”而“實質非理性”的過程。由于形式理性與實質理性的沖突,現代社會陷入無法自拔的困境。韋伯對理性化最終導致的后果的預計是人類自由的喪失和意義的喪失,人完全被物化、非人格化,只不過是經濟或行政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而已。進入后工業社會,麥當勞和麥當勞化更加深刻地闡釋韋伯理性化理論。盡管麥當勞并不是率先使用理性化要素,但它確實代表了理性化進程的一次飛躍。
二、麥當勞化的理性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餐飲集團,麥當勞為當代最有影響的社會進程提供了發展基礎。著名雜志《經濟學人》每年都會刊登“巨無霸指數”(漢堡包經濟學的一部分)來評價世界各種貨幣的購買力狀況。①[美]喬治·里澤:《麥當勞夢魘——社會的麥當勞化》,容冰譯,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8頁。麥當勞的發展模式被眾多領域采納、模仿。漢堡王、賽百味、肯德基、塔可鐘、星巴克等快餐店借鑒麥當勞的模式,成功地在快餐業占有一席之地。雖然它們對麥當勞的優勢地位構成了一定的挑戰,但對麥當勞化進程本身影響甚微。麥當勞高度理性化的發展模式還影響到了教育、政治、宗教、家庭、休閑、飲食、旅游、科學研究、醫療保健,甚至刑事司法體系,各種跡象表明,“快餐店的規則逐漸主宰美國社會的諸多方面乃至世界其他領域的過程”。②[美]喬治·里澤.《麥當勞夢魘——社會的麥當勞化》,容冰譯,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3頁。而麥當勞化的過程,就是韋伯理性化理論的闡釋和擴展,就是社會生活如何成功地變得更加理性,即高效性、可計量性、可預測性以及可控制性。
形式理性注重計算達到目的手段和衡量投入與產出,必然將效率置于首位,即意味著選用最佳方案來實現既定目標。麥當勞提高效率的方法大體可以概括為兩種:生產過程流水線化和簡化產品。麥當勞從創立之初就將高效性作為經營的首要特色。1937年麥當勞兄弟在加利福尼亞州帕薩迪納建立了他們的第一家餐館,為了最快地讓顧客從饑餓到吃飽,他們指導廚師將烹飪準備工作分為幾個簡單的、不斷重復的任務,使那些第一次步入餐廳廚房的人能夠快速掌握。麥當勞兄弟還開創性地將餐館的專業工人分為“燒烤工”、“攪拌工”、“油炸工”和“包裝工”(即給漢堡包包裝的人)。喬治·里澤在對醫療體系進行細致的觀察后發現衛生保健實際上也在麥當勞化,對病人的救助在一個精確的組裝線上完成:在許多方面,莫斯科眼顯微外科研究會就像一個現代化工廠。傳送帶從5個工作站旁依次緩慢滑過,定期停下,然后再繼續前進。每個工作站都配有一個戴著消毒面具、穿著消毒工作服的工作人員。在傳送帶繼續移動之前,每個工作人員都只有3分鐘時間來完成自己的工作,他們每小時都可以完成20項任務。但是,組裝線上的工作人員是眼外科醫生,傳送帶上是躺在擔架上的病人。③[美]喬治·里澤.《麥當勞夢魘——社會的麥當勞化》,容冰譯,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頁。
另一個提高效率的方法是簡化產品。烹飪方法復雜的食物當然不符合麥當勞等快餐店的標準,麥當勞的主要產品是原料簡單、容易加工和食用的食品。在麥當勞最多的是所謂的“手指食品”,即無需任何容器就可以食用的食品,漢堡包、炸薯條、炸雞、比薩餅、墨西哥玉米卷都屬于手指食品。麥樂雞是完全意義上的手指食品,雞的骨頭、軟骨、雞皮等降低吃雞肉的效率的因素都被剔除了出去。甚至在駕車過程中,顧客也可以容易地食用恰好一口可以吃下去的炸薯條。產品被高度簡化的結果之一是對快餐店有特殊要求的顧客常不能如愿,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快餐店的高效率來自于他們只使用一種方法來加工食品。漢堡包只有一種制作方法——全熟的漢堡。至于未熟透的漢堡或炸焦的油炸食品,麥當勞不會提供。總之,亨利·福特有關汽車的言論已經被擴展到了漢堡包上:“你訂什么顏色的汽車都可以,但我生產出來的汽車只有黑色的。”
麥當勞的理性化不僅表現為高效性,還包括可計量性:計算、計數與定量。在韋伯看來,近代歐洲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是理性主義的產物。只有在合理性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的支配下,才會產生出經過推理證明的數字。可計量性為生產流程和最終產品都設立了數字化的標準。在流程上,它強調速度;而在結果上,它強調產品的數量以及產品的尺寸。麥當勞對食物品質的要求也有著精確的測量標準。每個麥當勞漢堡的原料要正好1.6盎司,10個漢堡包配以1磅肉。未經加熱的漢堡包直徑要精確為3.875英寸,其中面包片的直徑為3.5英寸。漢堡包肉餅標準規定:脂肪含量應在17%至22.5%之間;拒絕使用任何添加物;肉餅必須由83%的肩肉與17%的上選五花肉所混制。①管家琪:《快餐大王麥當勞》,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130頁。
熱衷于對事物進行計量化的不只是餐飲業。在教育界,對于某一門課的教學是否能取得最好效果,人們大多數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一共有多少學生能夠通過這個系統得到教育,以及他們能得到什么樣的成績,而對他們學習的質量和學習體驗卻不夠重視。在文學創作中,強調故事講述的量而不是質的后現代主義小說在簡單、快速地大量生產。②王欽鋒:《后現代主義小說的麥當勞化》,《國外文學》2004年第1期。在電視傳媒業,電視節目的安排也是根據量化的因素決定的。電視節目的收視率,而不是它的質量,決定了它可能帶來的廣告收入,由此決定了這檔節目能否長期存在。③殷樂:《電視模式的全球流通:麥當勞的商業邏輯與文化策略》,《現代傳播》2005年第4期。
麥當勞化的第三個特征是可預測性。在理性社會里,大多數情況下,人們總想預知可能發生的一切。他們既不需要也不期待出現意外和驚喜。為了保證可預測性能超越時空的變化,理性社會必須強調紀律、秩序、系統化、標準化以及流水線操作等等。麥當勞所有的連鎖經營店的外觀都是統一設計,醒目的巨大金色拱門標志構成了和千百萬顧客之間無言的許諾,年復一年,“餐復一餐”,麥當勞都是可預測的和穩定的。每一家店內的柜臺、菜單牌、桌椅、垃圾箱以及從柜臺可以看見的“廚房”都是完全相同的。我們都生活在一個日益可預測的世界中。這讓大部分人感到可靠和放心,所以我們都開始期望甚至去索求這種可預測性。然而,一個可預測的世界也很容易變成一個令人厭煩的乏味的世界。如果我們試圖去擺脫這種厭煩情緒,我們就會很容易發現,就連人們經常借以逃避現實的地方本身,也已經開始變得高度可預測了。現代露營者不再使用簡易帳篷,為了減少不可預測性,他們會開著旅行房車去冒險,或者在汽車后加一個拖車,上面裝上高級自動彈開式帳篷。④[美]喬治·里澤:《麥當勞夢魘——社會的麥當勞化》,容冰譯,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頁。產業化的露營活動催生了更大程度的可預測性。大部分美國人會選擇在這類產業化的露營地活動,如最早出現的美國露營集團(KOA)。當包括娛樂活動在內的一切活動都理性化時,人們就最大限度地生活在理性化的“鐵籠”之中了。
理性系統的低效性、不確定性、不可預測性大都來源于人。這里的人大部分情況下是系統內的員工,因此,麥當勞化要變得更加理性化,就需要增強面向員工的控制。傳統意義上的廚師這一角色從麥當勞消失了。麥當勞為每一個步驟制定了簡單的規則說明,以便使所有人都可以掌握,消除烹飪時由廚師個人因素引起的不確定性。麥當勞提供的大部分食品都是預先經過粗加工、按固定標準切好,即做過預先處理的。員工們只需在必要時對食品進行再加工,通常僅僅需要對食物進行加熱即可提供給顧客,他們做出自主決策和鍛煉自己技術水平的機會很少。除了對食品進行預加工,麥當勞還開發了多種機器以加強對員工的控制。人工操作炸薯條時,由于員工的判斷不同,可能會導致薯條火候不夠,或是炸的時間過長,甚至燒焦。雷·克羅克對此十分惱怒,他曾表示:“想采用這種人工方式制成完全相同的薯條,無異于癡人說夢,因為每個負責炸薯條的員工都會以自己的評價標準來判斷什么樣的薯條是最佳薯條。”⑤[美]喬治·里澤:《麥當勞夢魘——社會的麥當勞化》,容冰譯,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頁。克羅克用一種新型薯條機取代人工操作的法式薯條機。這種薯條機在薯條制成后會響起鈴聲,且自動將薯條從熱油中撈起。
三、麥當勞化的非理性
在韋伯看來,理性與非理性是同一現實行動的不同側面,理性系統不可避免地要產生非理性,而非理性對理性的限制和妥協,甚至可以破壞理性。在擁有高效率、可計量、可預測、可控制等理性特征的同時,麥當勞化也可以被看作是低效率、不可預測性、不可計量性和不可控制的原因。
麥當勞化的非理性就表現在它是一個非人性化的過程。麥當勞化使個人的自由受到限制,威脅真正人的生活的世界。按照韋伯的分析,在高度理性化和科層化的政治和經濟系統中,人們的行為是完全按照系統的要求來發生的,作為經濟或行政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只能按照職位的要求來行動,沒有任何自主性和自由。“餐廳經理→第一副經理→第二副經理→組長→接待主管→接待員”,明晰的崗位分工在縱向上形成了垂直指揮系統;“人事經理→排班經理→訂貨經理→訓練經理”、“接待員→操作員→維修人員→美工”,橫向上形成聯絡協作系統。人們按照制度和職業要求完成自己的工作,具有不同特質的主體的人卻不停地重復履行有限幾個極度簡單的動作,被迫收斂起人的特性而表現得像個機器人,只能在很小的程度上發揮技術和創造力。
麥當勞化的組織甚至為員工制定好了“劇本”,員工和顧客的對話成為被規定好的儀式化對話——“您好!歡迎光臨。→請問您在這餐廳吃還是打包?→請問您需要什么?(把內容輸入POS機)→您點的餐已經備齊→一共xx元;這是找您的零錢→謝謝,歡迎再次光臨。”正如麥當勞現任的首席運營官查理·貝爾多次重申:“我們要確保員工們可以集中精力提供最好的服務。他們不僅要快速、友好、準確地服務,而且還要體現麥當勞熱情好客的精神。”①[ 美]拉里·萊特,瓊·基頓:《重塑品牌的六大法則:麥當勞是如何為品牌重注活力的》,呂熠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86頁。但從它的非理性的一面看,恰恰體現出最完美的官僚主義制度并不關注要做什么,人們只需按照規定完成所負責的工作,然后傳遞給系統中的下一個步驟即可。這與著名哲學家雅斯貝斯在《時代的精神狀況》中描述的如出一轍:“一切工作都在每一個有關的人都須遵循的詳細的規則下進行。過去人們在這類事情上通常是等待‘事情的自己發生’。現在他們卻預先設計好一切,單個工人在許多方面幾乎等同于機器零件的結果。”②[德]卡爾·雅斯貝斯:《時代的精神狀況》,王德峰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頁。
四、結束語
基于對現代性的洞察,韋伯一方面把西方文明和現代工業生產的特征看成是“理性化”,用它來解釋現代資本主義世界人的存在條件和狀況,并充分肯定“理性化”在使人擺脫宗教倫理桎梏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韋伯又憂慮于人們雖然掙脫了宗教的枷鎖,卻又陷入物的羈絆之中。而在資本主義已經成熟發展的今天,韋伯“理性化”理論中的理性與非理性在現代經濟組織中表現得更加突出,“麥當勞化”作為對韋伯理論的闡釋,概括了逐漸主宰社會諸多領域的對高效性、可計量性、可預測性和可控制性的追求。
隨著麥當勞化的擴展,麥當勞化的非理性也受到人們更多的指責和詬病。盡管存在某些障礙,但是在不久的將來,并沒有什么因素可以阻擋麥當勞化的大潮,或者扭轉這個趨勢,畢竟“現代性是一項未竟的事業”(哈貝馬斯語),人們為達到既定目的而尋找最佳方式的過程是依據規則、制度或更大的社會結構形成的,而這也是形式理性化和麥當勞化的要旨所在。
C91
A
1003-4145[2012]專輯-0044-04
2012-03-01
盧曉琳,女,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社會工作專業在讀。
(責任編輯:宋緒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