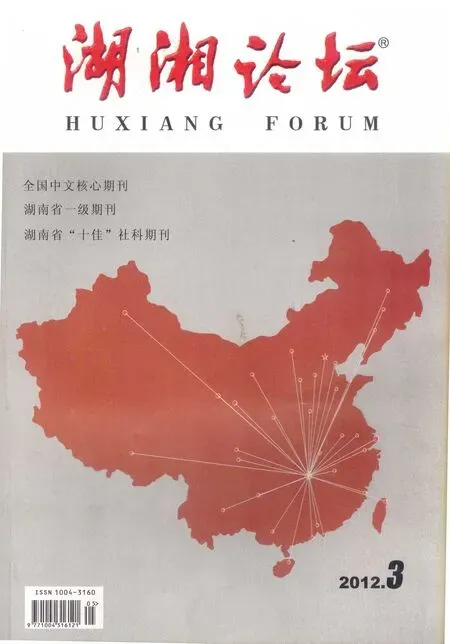苦難中蘊涵的美學力量——論余華作品的美學特征
黎子瑩
(湖南師范大學,湖南長沙410081)
苦難中蘊涵的美學力量
——論余華作品的美學特征
黎子瑩
(湖南師范大學,湖南長沙410081)
余華不平凡的經歷決定了他感受苦難的方式不同,不同時期他的創作體驗、人生境界也不相同,因此他在不同的作品中呈現出不同的美學特征。本文以余華小說為研究對象,重點分析他《十八歲出門遠行》的荒誕美、《活著》的苦難美和《兄弟》的暴力美。
余華作品;美學特征;荒誕美;苦難美;暴力美
苦難始終是余華小說反復渲染的主題。余華的人生經歷毫無疑問影響了他對人生美好的看法,余華出身于醫生的家庭,并且童年生活還了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這使得難和死亡在他的心靈中留下了無法醫治的創傷,這也許成了他描寫人性惡的源頭。苦難在余華的小說中展示出了不同的風格。他前期的小說里面,“苦難”可歸納為兩點:內容上表現出來的罪惡和本質上蘊含的宿命,主要反映在作品《十八歲出門遠行》中,體現了一種荒誕的審美姿態。進入90年代,余華放棄了自己從前所擅長的帶有明顯先鋒烙印的解構式語言、圈套式情景布局和怪誕審丑的構造元素,而是采用了更接近傳統的現實主義敘事手法和平實質樸的語言元素,創作了《活著》等作品,在小說中間展現出來的苦難具有了新的意義和形態。余華2003年8月去了美國,在那里度過了7個月的時間。回國后,發現自己已經沒有了漫長敘述的欲望,于是中斷了大長篇的寫作,打算寫一部稍短些的作品,以幫助自己逐漸恢復敘事能力。于是《兄弟》便應運而生了,在作品中,余華握著他一貫擁有的暴力之劍,在不動聲色中冷漠地向我們敘述了那段“文革”歷史與現實生活,寫了很多人的死亡,展示了一個個鮮血淋淋的場景,小說充滿了暴力敘事的美學特征。
一、《十八歲出門遠行》的荒誕美
余華的早期作品中在創作時多使用具象的美學符號,更注重強調的是人類本性中的丑陋與兇險對人類自身的毀滅。與此相適應,余華在早期創作中大量使用了怪誕——變形的藝術手法。荒誕派作家尤金尤奈斯庫說過:“荒謬就是沒有目的,人感到迷惘。他所有的行為成為毫無意義、荒誕不經和沒有用處。”余華曾被莫言稱作是“當代文壇上第一個清醒的說夢者”,《十八歲出門遠行》還被他看作是一篇“條理清楚的仿夢小說”。
在作品《十八歲出門遠行》中,余華采用第一人稱的手法,記敘了“我”出門遠行,可是我沒有任何真正的目的。迎面開來一輛汽車,我搭上了這輛汽車便往走過來的方向去了,中途汽車拋錨,一車的蘋果被經過的野蠻農民哄搶,司機不但沒有阻攔,而且“他的表情越來越高興”,最后司機干脆與農民一起跳上搶劫的拖拉機走了。種種不近情理的細節,種種不可思議的舉動,初步顯示了怪誕—變形手法在余華那里所蘊涵著的巨大創作能量。但怪誕絕不等同于脫離現實,其重要藝術品格之一就是“怪”與“真”的矛盾統一。它自始至終充滿了種種不確定的、令人難以捉摸的情境,而它描述的所有東西既是有邏輯的又是準確無誤的。它用許多種可能性分解了故事本身所包含的意蘊,讓人真切地領會到了清晰準確的動作和一種由悖謬的邏輯關系構成的統一,并產生了夢幻一般的美麗,使得小說在意蘊層面上更偏向于一種哲學意味。余華指出:“人類自身的膚淺來自經驗的局限和對精神本質的疏遠,只有脫離常識,背棄現狀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邏輯,才能自由地接近真實。”這樣余華用一種極而言之的“仿夢”形式,栩栩如生地展示了世界的荒誕無常以及青年人在這種荒謬的人生面前的深度迷惘。小說里面荒誕人生的陰暗丑陋與青春初旅的明朗歡快構成劇烈的碰撞和鮮明的反差,因而作品具有非常強的審美張力。
余華的小說受到荒誕派和卡夫卡的表現主義的影響,人物的知覺功能,感覺功能以及想象等等都具有非常態的加工能力,都失去了真實性,都被改造、夸張和變形,甚至在妄想癥病人的眼里能出現現實生活中未曾出現的東西,具有一種“無中生有”的本領。獨特的“陌生化”效果,豐富了對于常人顯得過于正規、過于平板的心理世界。這樣一種審美視角的轉換戲劇性地提示了世界的荒誕無常和人處在此世界中的深刻迷惘,無疑給我們的美學視野帶來了一種全新的體驗。
二、《活著》的苦難美
到了1997年,余華提出自己開始放棄先鋒試驗。創作的《活著》是一部令人感到非常沉重的小說,它用一種淡漠的話氣,平和樸實地刻畫了社會底層民眾的生存故事,并在悲劇性的氛圍中,展示了各種人性的善良和光輝,發掘人格與尊嚴的偉大,探尋人物內心深處溫暖的光環。它是一篇盈溢著底層人物心酸血淚的作品,小說自始至終貫穿著一種“苦難意識”,這種對苦難的恣肆濃烈且赤裸裸地渲染和暴露,使得余華的作品展現出了一種獨特的風格。
《活著》主要講述了在舊社會中一個敗家子福貴,開始瘋狂地嫖娼,放肆地賭博,傾家蕩產之后,用下輩子的辛酸血淚來償贖自己前半生荒唐的故事。從福貴自身來說,不管是他在舊社會經歷了由榮華富貴到一貧如洗的辛酸的苦難,還是進入新社會后,許許多多的的社會政治運動給他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和痛苦,這些變數不定的社會因素是福貴苦難產生的重要原因。從小說里面,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到“文革”結束這個過程中,這條明顯的時間線索以及在此線索中所展示的對福貴苦難的根源,無不凸顯了一個中國老百姓在動蕩不定的歲月長河中活著的執著和精神重量,同時也從另外一個方面展示了現代中國底層民眾的生存狀態。在福貴的生活以及其親人的死亡中最終能夠昭示出忍耐、寧靜和溫情的受難,自己始終堅持著的一種人性的光輝,這也恰恰是在殘酷的境遇里面中國底層的老百姓應付生存困境的一種努力。福貴可以說是小說中唯一一個“活著”的幸存者,但是從自身來說,他的“幸存”卻時時刻刻都在感受著死亡和苦難。對親人的死亡以及對死亡所產生的無奈、難舍、悲憤,他都必須能夠承受下來。他的人生路途,就是對生命的無奈,活著的無奈。正如余華說的:“我尋找的是一種無我的敘述方式。”他以看似冷酷的方式來講述一個觸目驚心的故事,但實際上我們聽起來卻平常無奇。他盡力把自己的感情隱埋在自己的心里,消除了如今大部分人對事情情感評價和思考判斷的解釋,把苦難展示得冷漠而沒有節制,這樣產生了“殘酷的余華”的稱謂,這樣的寫作手法也叫做“零度情感寫作”。實際上,在余華的小說世界中間,并不是沒有信仰,沒有立場,沒有價值,他完全不是為了揭示苦難而去描寫苦難,在那個漆黑一片且沒有盡頭的苦難世界里,也綻放出了生命的曙光。并且這在余華的后期小說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這一線曙光,不僅僅來源于作者自己對苦難不悲觀,不絕望,而且來源于作者對自己苦難認識的超越和升華。《活著》是在苦難中對生命本真的贊揚,它的獨特之處是:讓人看到了死亡的時候,卻努力去避免死亡的發生,這樣使人看到絕望的時候卻永遠都不會感到絕望。
三、《兄弟》的暴力美
余華在文革中讀完小學和中學,此后從事過五年牙醫。作為一個在童年時期經歷過文革的人,余華對這一歷史時期有著自己較為真切的認識,接受了那個特殊社會時期的話語暴力,以及各種殘酷的武力斗爭和人性惡的瘋狂宣泄,這使得余華形成了對社會現象本身的懷疑和人際關系的不信任,他唯獨能相信的便是暴力和人本身的存在。然而,余華對文革這樣一個復雜的社會畸變運動,僅僅從壓抑和暴力層面去解讀,顯然走入了現象主義的誤區,對文革本身童年體驗的感性和史實題材的難以駕馭,使得這種認識局限更為集中的體現在了余華的小說《兄弟》里。
《兄弟》選擇的是一個極端的故事,余華強調:“那是一個精神狂熱、本能壓抑和命運慘烈的時代”,而余華的“本能壓抑”更多地偏向了性欲和暴力的壓抑,陷入了一個暴力的迷津,將文革描述成為一個潛藏在人心中的惡的猝然發作,以及對人性、倫理和秩序顛覆的過程。在《兄弟》中,苦難、死亡與暴力怪誕形影不離。在小說上部里面,六個戴紅袖章把從昏迷里醒來的宋凡平圍起來打,并且把他從候車室里一直打到了候車室外的臺階上,宋凡平被他們打得鮮血淋漓,當他進行拼命抵抗,被打到臺階上時,一腳踩空了,身體沿著臺階往下滾,六個戴紅袖章跑下來,又圍著他一頓亂踢亂踩,還把木棍折斷成鋒利的木棍,像刺刀一樣往宋凡平身上捅,宋凡平的腹部被一根木棍捅進去了,使得宋凡平渾身痙攣起來,那個紅袖章又將木棍從他身上拔出來,宋凡平立刻挺直了,腹部的鮮血呼呼地涌了出來,染紅了地上的泥土,宋凡平一動不動了……渾身疼痛的他這時一點疼痛的感覺都沒有了,一個赴死之人突然沒有了生時的苦痛,他靠墻坐下來,長長地呼吸了兩口氣,左手舉起了大鐵釘,插在自己的頭頂上,右手揮起磚頭,他想到了死去的兒子,他微笑了一下,輕聲說:“我來了。”余華在小說中不斷地應用家庭的溫情來化解“文革”暴力對人肆意踐踏所造成的恐懼感和緊張感。在每一次暴力血腥敘事的背后,作者常常通過對許多事件進行細節描寫來表現宋平凡、宋平凡那個地主父親、李蘭、李光頭、宋剛之間的相濡以沫,而且用了非常詩意的語言,開辟了另外一個“詩”性的世界而不是“血”性的世界,呈現出獨特的藝術魅力。《兄弟》下部中,沒有了屠宰肢體的刀光劍影,取而代之的是金錢暴力。價值判斷與人的幸福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是以擁有金錢的多少來作為標準的。這樣對金錢占有的欲望左右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甚至對未來的所有想象,人在金錢中沉浮。小說通過劉作家和趙詩人兩個“知識分子”形象的塑造,刻畫了愛情、金錢和人格的顛倒淪陷;并且余華在面對逝去去的年代的時候,自己有充分的自信去緩和與時代的對立,但是在面對自己還在經歷的時代的時候,所經歷的荒謬并不能緩解自己的緊張感,因而只有不斷地進行揭示,讓自己成為作品的主要人物來進行表演。
縱觀余華小說創作二十年,我們可以看到余華探索人性真諦的清晰步履,無論是其前期先鋒意識下的作品,還是后期的作品,余華都不遺余力地借助自己對苦難的解讀,來抒發和宣泄對社會本質的認識,力求探討和召回真正意義的人性關懷。盡管其荒誕、苦難、暴力的表象使人駐足,但其背后有著更能觸動人內心的對社會和人性本質的隱喻式的表達,從而以其審美方式引起讀者的共鳴,這是余華作品之所以經久不衰的原因所在。
[1]余華.活著[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
[2]余華精選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3]余華.兄弟[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4]董素青.平淡之語敘苦難之深——論余華《活著》中的苦難意識[J].龍巖師專學報,2004(2).
[5]鄭阿平.中國式的生存哲學的闡釋——解讀《活著》[J].唐都學刊,2007(4).
[6]張勇.以寫實方式展開對苦難的敘述、追溯和救贖——論余華長篇小說《活著》[J].巢湖學院學報,2008,(3).
I2
A
1004-3160(2012)03-0110-03
2011-11-29
黎子瑩,女,湖南岳陽人,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學生。
何良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