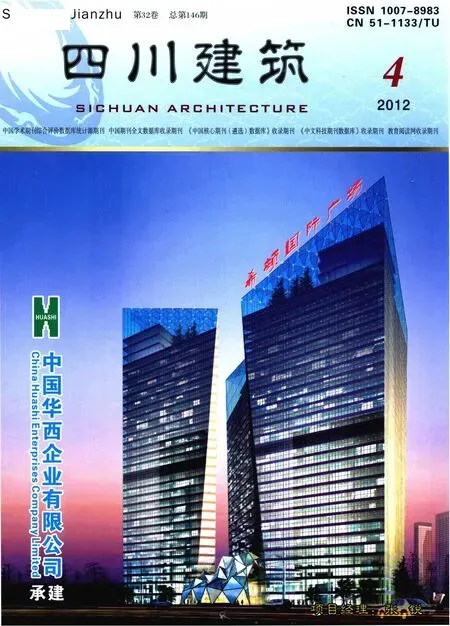傳統文化與漢代園林審美思想
崔璐璐
(重慶交通大學土木建筑學院,重慶 400074)
園林首先是物質生活環境,本質則是精神的居住。這決定了只有在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上踞于統治地位的階層,為滿足生活享樂與精神欲求,才有條件建造這種文化上高層次、經濟上高消費的園林。而園林作為一種文化載體,實際也是審美主體思想、心性的必然反映,體現著主體的哲學、美學追求。
張家驥在《中國造園史》中談到:如果不把造園實踐置于社會的發展和運動之中,從造園與社會生活錯綜復雜的關系去考察,對一個時代的園林的基本特征,也難形成比較清楚的概念。
要探究漢代園林發展的成因和特定定義,僅局限于園林本身遠遠不夠,而是需要深入到社會生活方式尤其是美學思想和文學藝術形式發展的內在關聯,以及相應的時代特征等背景文化層面。
1 漢代儒學思想與園林
人對審美的需要是園林藝術發展的動力。中國傳統美學以儒、道思想為主體。儒家的藝術精神,常需要在仁義道德根源之地,有某種意味的轉換;而莊子所開創的藝術精神則相對直接,可視為純藝術[1]。
中國園林是以“山水”為審美對象的自然風景式園林,其中的審美再造刺激物,既有純自然狀態的“山水”,又有人化的自然,還可以是建立在山水自然基礎上的“意境”。這一切都離不開“山水——自然”這一審美對象,離不開儒學的貢獻。漢代園林尚處于中國古典園林生成期,其審美觀方式受儒家影響頗深,而莊子的純藝術精神似乎不占主導地位,只對東漢后期文人隱逸思想的發展有直接作用。
1.1 漢代儒學思想的發展
先秦時期的儒家學說具有極強的人文和社會政治傾向,提倡中庸、博學、擇善而從。但在漢代之前,儒家思想始終沒能與當時的政治實踐結合。西漢中期,儒家思想得以成為漢代的正統政治思想,其鮮明的政治傾向及其致力于建立新的社會秩序的努力,都與漢武帝時期加強君權、強化中央集權和文化專制的要求不相矛盾。
漢代儒學是在先秦孔孟之道基礎上發展和豐富了的新儒學,最主要的特點是雜糅各家學說于儒學中。當其在東漢最終建構完成之后,以宇宙自然法則作為依據,君主制度作為推行力量,循吏為代表的行政系統的教育與灌輸,加上便于推廣與普及的數字化、簡約化的語詞系統,實現了思想“標準化”的時代。
在漢人看來,黃老(或老子)思想的基本出發點,原本是和儒家一致的,漢初眾多思想家引用黃老思想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補充和修飾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具有時代的適應性。
1.2 漢代儒學思想的重要理論
1.2.1 陰陽五行體系
以人為中心的陰陽五行體系的完成,是漢儒重要的理論建設,被今天一些學者視為“漢代的思想骨干”。其框架以道、儒二家的追求來設立。一般地說,道家側重從世界的生成和運行角度去談陰陽五行,儒家側重從倫理、道德和意識去談陰陽五行。兩家理論的綜合,就是漢代陰陽五行體系的總貌。
陽:天、君、男、夫、德、樂等等;陰:地、臣、女、妻、刑、禮等等。這明顯是為了論證儒家的天人感應而人為地構筑的陰陽體系。
五行排列順序:漢代以前“木”的地位不高;漢代“木”上升至第一位。《尚書·洪范》第一次全面表述了金、木、水、火、土五行的關系,木作為五行之始,代表了生命、生殖、發展、生長之意。《周易》:“生生不息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國語》:“正德、厚生、利用”。漢代木結構建筑體系第一次確立。
1.2.2 天人之際理論
董仲舒的天人之際理論,把天作為人間秩序和理性的背景,并將這套解釋自然與歷史的宇宙法則論述得最為充分。“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以天人同類證明的天人合一論;以同類相動證明的天人感應論。
董仲舒之后的諸儒和思想家司馬遷、京房、劉向、劉歆、王充、郎回、襄楷、班固、張衡、馬融等,更將天與人的關系,發展到天上與地下萬事萬物的一一對應關系。
《史記·天官書》:仰則觀象于天,俯則法類于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圣人統領之。
張衡《靈憲》:星也者,體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錯峙,各有所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于是備矣。
可以看出,討論和闡發得最多的,是天象的意義。
1.2.3 讖緯學說
陰陽五行、天人之際思想得到極致的發揮是漢代的讖緯。《漢書·藝文志》數術略第六部分就是形法:“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兇”。
從秦漢之際到東漢之末,緯書之學由興而盛、由盛而衰,把古代中國關于宇宙的觀念、天文地理知識、占星望氣之術、神仙傳說與故事,與傳統道德和政治學說糅和在一起,顯示了兩漢時期思想的體系化與標準化趨向,也促成了國家神學的誕生。
1.2.4 隱逸思想
知識階層“為王者師”憑借的是“真理”,但當思想逐漸定型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并通過教育傳播成為普遍知識,知識階層的地位便下降成為“帝之臣仆”,出、處的矛盾逐漸銳化。于是,文士階層中一部分在權力壓迫下放棄所謂“君子”理想,轉入“文吏”;另一部分則高揚強烈的理想主義精神。
文人園林的基本內容之一是文士的隱逸生活之樂。園林作為士大夫遁世的去處,既是自然山水的摹寫,也是士大夫內在世界的外化。世道混亂不得志時,士人寄托于優雅的環境增加修養,等待時機出山來改善社會。
2 漢賦與園林
“貴文”思想對園林的影響,不僅體現在“文以載道”和對“文心”的追求,反映著園林與文學、繪畫等士人藝術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和同步發展。園林的題名用典、園景的意境創造方面都竭力追求士人文化的內涵與神韻。園林已經成為文人階層特有生活方式的現實反映,園居生活中時時處處都流露出濃郁的人文氣息。
藝術的本質,是面向感,隆形態的感性思維,而文學的根本規律是以形象反映社會生活,即運用形象思維把握世界。文學沒有畫面限制,自然環境、山岳江川、宮殿房屋、風土百物,琳瑯滿目。
西漢前期的辭賦,尚帶楚辭所特有的南方色彩;中期以后的辭賦,則已吸收了先秦時代南北文學中的多種成分,如《詩經》的四言句式,楚辭的華麗表現,戰國諸子散文的論辯色彩和夸張渲染的手法等等,成為全國性的文學樣式。
司馬相如:“合綦組阻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這里指出賦乃是以美麗的語言形式來描述宏大的世界。
漢代建筑最典型特點是類型空前豐富、體量宏大、鋪張,建筑審美成為重要審美內容之一。漢賦人量自然景物的描寫帶有審美特征,為魏晉南北朝的山水審美打下基礎。
3 漢代審美思想與園林藝術特征
3.1 自然審美
深究園林以自然為審美對象的原因,還要歸功于孔子儒家思想的首倡。源于早期原始思維、集中體現于《詩經》的這一文化傳統,經孔子及其后學的重新發掘,滲透到了社會文化的各個層面,對以后園林中的自然審美對象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這一倡導在歷代文人中的影響潛移默化,歷久不衰,形成了中國古代重視實學和技藝的優良傳統,并由此促進了動植物的培植、豢養與審美,極大地豐富了園林的景觀。
園林崇祀對象的變化,從娛神發展到娛人的功能轉換,意味著從感官上的快感,導向心性情志即精神的愉悅。儒家強調的正是園林建筑精神、思想而非感官的審美。
3.2 比德與比道
孔子最早提出山水審美的命題,而且認識到山水具有比德與比道兩種層次。比德以“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為代表;“子在川上曰”、“登山”、“觀水”“鳶飛魚躍…拳石勺水”“曾皙言志”等則是比道的典型,即透過自然界的四時變化和萬物運作,直視天地間生生不息、無所不在的“道”——生命的超越精神。
比德說,使山水花卉鳥獸草木魚蟲等擺脫了原始巫術和宗教神話,而作為情感抒發的發端和寄托。在儒學的這種積極倡揚之下,經過理知的中介實現了情感的建構和塑造,導致人們從倫理、功利的角度來認識自然之美、對于大自然山水風景,構建了自覺的審美意識。文學中的比德方法,在屈原、宋玉至兩漢的騷賦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而山水比道則是發現了山水具體形態以外的超越性。是面對山水的宇宙和生命本體性的哲學思考。作為儒家美學理論整體框架的一部分,比德審美觀點方式的進一步發展,己不僅是人的倫理道德標準與自然萬物的比附,而是將審美主體最終帶入了一個超越的天地境界。
3.3 山水審美對漢代園林的影響
山水審美對包括園林在內的藝術的影響,一是在思維方面強化了形象思維,二是在形式上奠定了中國特有的仰觀俯察的時空觀念和構圖方式。班固《西都賦》描述了這種園林創作的審美意象:“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其觀景的載體就是作為苑中苑的長楊榭。另如石闕、封巒二觀建于“岡巒糾紛,干霄秀出”的石門山,“崇丘陵之墩酸兮。深溝嵌巖而為谷。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巒石關施糜乎延屬。”。以建筑結合山川自然而創造園林景觀的意象,也是相當明顯的。
山水自然的積極意義是使人從中獲得精神的愉悅;從負面上講,山水自然則是作為社會失意后人生幸福的補償形式出現,成為士人漂泊心態的歸宿,使其生活方式上與自然更為接近。同時期隱逸文化的發展加速了山水審美的進程。
4 結束語
漢代文學充分如實地反映了漢代園林的布局、環境和活動,為人們展開了一幅幅生動的畫卷:并且漢賦對造園的指導意向亦十分明顯。
漢代是一個大融合的時代,其博大輝煌的文化,建立在對各種文化百川匯流式的兼容和重新詮釋,堪稱“有容乃大”:東漢佛教才開始傳入,影響未深,因此漢代文化表現出華夏文化的原生狀態。兩漢時期這種特有的文化氛圍,決定了漢代藝術異于其他歷史時期的內容,決定了漢代園林的基本格局:以強盛的大一統帝國為背景,以自然山水為主要審美和寫仿對象的人工游憩空間。審美客體的確立和想法相對成熟,為后世文論、畫論對園林的深遠影響直接打下基礎。
[1]徐復觀.莊子的山水觀——中國藝術精神[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82
[2]金春峰.漢代思想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3]李澤厚,劉綱紀.中國美學史——先秦兩漢編[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
[4]李澤厚.美的歷程[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
[5]王毅.園林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